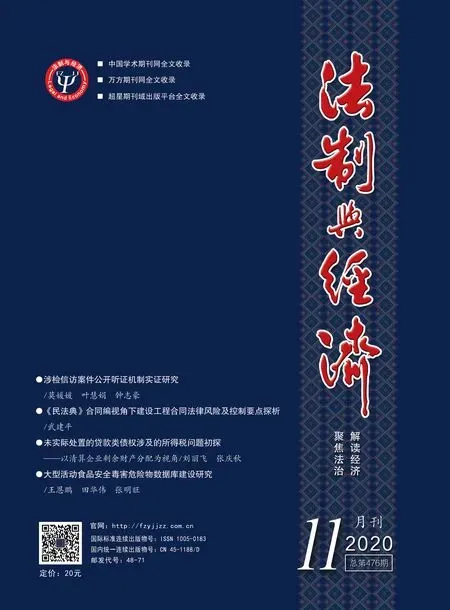生前预嘱的本土法治化研究
张 恒 丁唯一
(西南医科大学法学院,四川 泸州646000)
对于生前预嘱,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概念是,“生前预嘱,指人们在自己健康或者意识清醒时所签署的,指明在其不可治愈的伤病终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1]生前预嘱制度在我国所面临之困难是比较大的,但发展空间也绝不容忽视。
一、社会发展对生前预嘱的现实需要
(一)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临终医疗问题的强烈需求
据有关预测,到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到2035年左右将达约4亿人。[2]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临终医疗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当老年人处于不可治愈的疾病末期,痛苦终日伴随,这种痛苦既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当然,这种痛苦绝非仅仅针对患者,其家属亲人也无法摆脱。生前预嘱的出现便正是其所需要的,患者通过在健康或清醒时签署生前预嘱文件,表明其拒绝或希望得到的医疗救治,缓解痛苦,让生命更有尊严。
(二)人们对生命尊严及生命质量的重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众的关注点逐渐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人格领域,人们对生命质量也有了新的理解。以往大家可能更多追求生命的绝对长度,现在,人们更多地关注生命的相对长度,即生命质量是否合乎心意,生命尊严是否得到满足。这恰恰与生前预嘱的理念不谋而合。而且,我国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中人格权编也明确自然人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这直接体现了生命尊严的社会关切。
二、我国生前预嘱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可行性
(一)传统文化及社会大众对生前预嘱的误解
生前预嘱方式是患者签署预嘱文件,交由亲属和医疗机构执行,这与我国传统文化是有所出入的。传统孝文化认为对亲人的奉养,延长亲人生命是重要内容,而生前预嘱中亲属帮助患者执行拒绝医疗的行为自然被认定为“不孝”。而且,大众对患者亲属的舆论压力也不容忽视,这使得患者亲属多选择站在生前预嘱的对立面。因此,如前所述,由于现实的诸多因素,我国民众对生前预嘱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对生前预嘱误解也较大。但是,随着我国生前预嘱相关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现实及自身权利的更多思考,其对生前预嘱的了解必然会不断加深,进而对生前预嘱的接受程度也会相继提高。
(二)我国生前预嘱法学基础理论仍存在较大争议
1.生命权、患者自主权等生前预嘱相关核心权利与现行法律表面上的冲突
就当下而言,大多认为生前预嘱是对患者生命权的直接剥夺,其社会危害性明显,继而签署的生前预嘱文件也难具合法性。然而,在笔者看来,法律所保护的生命权绝非是狭隘的,生前预嘱是对生命权的更加切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诠释,是对生命尊严等生命利益的实现。我国《民法典》第1002条也对生命尊严作了规定:“自然人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笔者认为,此条虽未对生前预嘱作出规定,但其为生命尊严等生命新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空间。因此,生前预嘱的订立是患者对自身权利的支配,生前预嘱的执行也只是医疗机构在患者意愿下的合法执业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的排除是显而易见的。而至于患者自主权,我国现行法律也仅有《执业医师法》和《侵权责任法》中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概括规定,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中是否包含拒绝医疗等内涵,从现行法律尚难看出。虽然我国现行法律还未对患者自主权作出明确规定,但笔者相信,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法律个体,我国法律对患者自主权的回应也并非遥遥无期。
2.生前预嘱制度架构存在空白
现实来说,生前预嘱的制度设计仍存在空白,其订立主体、执行主体、生效条件、执行程序及责任追究机制,在我国还处于学者讨论研究阶段。但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国内关于生前预嘱的研究已有时日,其成果也颇丰。我国学者关于生前预嘱的本土化争论虽然激烈,但也逐渐形成了对生前预嘱概念内涵、制度保障,立法逻辑的构想,其对我国生前预嘱的发展起到了相当明显的指引作用。
三、国内外生前预嘱研究实践进展
(一)亚洲地区相关立法
作为亚洲地区生前预嘱制度的先行者,新加坡在1997年颁布的《预先医疗指示法》对预先医疗指示的制度构建进行了规制。其将预先医疗指示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末期临终病人,并要求预先医疗指示的成立条件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两名见证人的见证下签署。而且,其还要求预先医疗指示必须在专门登记机构登记才能生效并执行。另外,韩国在2018年正式实施的《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也对患者拒绝维持生命医疗作了回应,其规定,患者可通过填写“事前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意向书”和“维持生命医疗计划书”的方式要求拒绝医师使用维持生命治疗。
(二)欧洲地区发展情况
生前预嘱类似制度在欧洲一些国家也已经通过立法得到规定,包括瑞士、奥地利、德国等国家,其中以德国较为典型。德国的生前预嘱以预立医嘱形式呈现,并将其纳入民法典规制之中。德国民法典规定,只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均可以书面方式签订“预立医嘱”,以提前决定其在丧失行为能力后相关医疗权利如何行使等事项。[3]
四、生前预嘱制度构建的思考
(一)适当扩大生前预嘱内涵并立法加以明确
目前,生前预嘱对象大多针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末期的病人,但回归社会复杂的现实情况,不难看出,这种概念定义的局限性是巨大的。生活中有很多疾病状态并非所谓的末期病人,但其遭受的痛苦绝不亚于末期病人,例如永久植物人状态和极重度不可逆的实质损害性疾病等类似状况,作为自然人,他们的生命尊严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应对其有所考虑,允许生前预嘱对其予以涵盖。
(二)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纳入订立主体
现今各国关于生前预嘱及类似制度的规定,其订立主体多被限制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认为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清楚地了解自身权利,并作出相关处分决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此种能力是缺乏的,而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真实意思难以获知,因此不宜将其包含在内。笔者看来,这种考虑不太必要,首先,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与生命尊严,无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然人地位毋庸置疑,继而他们也天然享有生命权与生命尊严。其次,虽然这类人行为能力欠缺,难以对自身权利作出决定,但可引入监护人与法定代理人制度,在严格监管下,可由其代为行使,但是,此处代为行使权利的法定代理人,其信赖的近亲属为首要选择,若前述条件不具备,则可由民政部门、社区组织等担任代理人。
(三)设立生前预嘱代理人和公证制度
生前预嘱代理人指在患者意识不清醒时代为进行意思表示的人。生前预嘱公证制度,即将预嘱文件到公证机构予以公证,提高其法律地位与效力。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可由患者近亲属或极度信赖的人担任代理人,可以是委托代理或法定代理;需要另外指出的是,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政部门、基层自治组织等可担任代理人。将公证制度引入生前预嘱,并非是将生前预嘱固定化,而是一种提高生前预嘱法律地位的一种法定程序,患者可随时变更与撤销生前预嘱,只是需要遵循一定程序。
(四)医疗机构执行资格需加以限制
由于生前预嘱程序较为特殊,执行的技术操作性强,对医疗机构配套设施服务要求较高,所以,需对执行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资质有所限制。具体体现为:执行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应有较为完善的医疗技术服务条件,且具有执业经验丰富、医德医风良好的医疗人员,以达对生前预嘱有匹配的服务支持,同时,医疗机构执行生前预嘱的资格应由卫生行政部门综合考量予以认定,实行行政许可,未获许可的医疗机构禁止参与生前预嘱的执行。
(五)完善行政监管与当事人监督多方位结合的监督方式
对预嘱代理人代理行为与医疗机构执行行为的监督是不可缺少的,且二者不可分割。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应采取行政监督与当事人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且以行政监督为主。卫生行政部门对生前预嘱执行全过程实行全面监督,即医疗机构执行生前预嘱应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授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应积极参与监督指导其执行过程。而对于代理人的监督,可由与患者有利害关系的亲属及基层组织参与监督,以期过程合理合法。
(六)生前预嘱的执行程序应严格限制
笔者认为,生前预嘱在执行时应有以下程序要求:首先,对于生前预嘱的执行条件,应由三名及以上执业经验丰富和资历较高的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予以认定,其认定应在患者和代理人全程监督下进行,医师有义务准确告知病情实际状况。其次,生前预嘱的执行应先由患者或代理人出示生前预嘱文件并证明其合法性,然后告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参与生前预嘱程序,再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医疗机构执行生前预嘱。
(七)明确相关主体违反生前预嘱之责任
在生前预嘱未得到有效执行时,对相关主体的责任应当有所明确。一方面,代理人未经患者允许或无故撤销生前预嘱合法程序或拒绝履行代理人义务时,应解除其代理人资格,并由其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当代理人与医疗机构在不符合生前预嘱执行条件下故意执行或错误认识情况下执行的,应认定为侵犯患者生命权,以故意杀人或过失致人死亡对相关责任人追责。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前预嘱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其具有较大的现实需求性,但我们应清楚认识到,生前预嘱制度的中国化很难一蹴而就,其本土化进程仍需时间的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