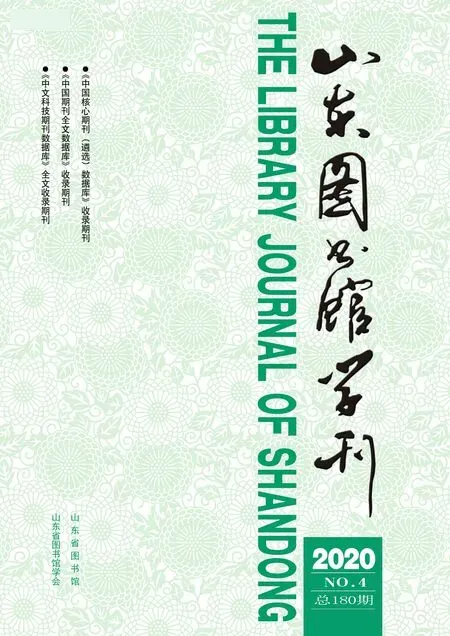晚明名妓阅读活动研究
冯丽娜 刘庆旭
(1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四川成都 610000;2南京工业大学浦江校区图书馆,江苏南京 211200)
明代是女妓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一环,亦是乐籍文化的终结与顶峰,代表着女妓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度[1]。在现有女性阅读的研究中,多以名门望族[2]或以传统女德[3]为核心进行梳理或著述。本文主要针对处于社会底层,与传统道德和家庭伦理相悖,被迫从事不光彩职业的青楼女子的阅读活动进行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知名妓女。在广泛搜集和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主要探讨晚明名妓的阅读因素、阅读环境、阅读内容、阅读目的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1 晚明名妓的阅读因素
1.1 自身因素
名妓的家庭出身、生活阅历、自我意识等都会给自身阅读、生活习性与人生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身为名妓,只懂乐舞伎艺,不晓诗书,将无法与士人歌舞演乐、饮酒助觞;只晓诗书,不懂乐舞伎艺者,亦无法适应职业发展以维系生活、安身立命。
1.1.1 名妓身世
名妓的身世隐藏着她们的文化底蕴与阅读基础。一般而言,名妓的身世可能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乐籍制度下世袭官妓之女。她们的身世从出生那天就注定了,从小跟随父母接受良好的伎艺修养,比如给正德皇帝唱过曲的教坊世袭乐户顿仁,其后代即是名妓顿文,顿文有此家世,加之聪慧过人,熟唐诗、学鼓琴,雅歌《三叠》,故而名闻曲中[4]。第二种源自罚良为娼制度。一人犯罪当诛,其子孙辈中男子多发配边疆戍守或为奴,妻、妾、婢、女、侍等女流一概打入教坊或送入娼门为妓。清代章学诚说:“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5]便指此类。而罪臣妻女都是大家闺秀,同入青楼,她们与其她女子不同,“有妙兼色艺,慧传声诗,都人大夫,从而酬唱”。[6]第三种是被人贩鬻卖于行院的良家女子。妓院对买来的雏妓集中培训,主要教其识字念书、诗词歌赋、笙管丝弦、书法绘画、女红厨艺等,但随着女妓年龄的增长,多不愿倚门卖笑,便潜心学艺,比如名妓董小宛,其父曾是私塾教书匠,家里本就一贫如洗,不幸父亲早逝,小宛被人贩卖身青楼,凭借“天姿巧慧,容貌娟妍”,加之“顾影自怜,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很快便跻身“金陵八艳”之列[7]。第四种是因战乱、家道中落陷身青楼的名门闺秀。她们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诗礼之家,自幼饱读诗书,通晓琴棋书画,谨遵“三从四德”,因其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沦落青楼后,稍加训练便可走红。比如名妓李因,自幼天资聪颖,痴迷读书,弃绝铅华,黄宗羲在《李因传》中载:“生而韶秀,父母使之习诗、画,便臻其妙。”[8]葛徵奇在《竹笑轩吟草》序言中也说:“(李因)资性警敏,耽读书,耻事铅粉,间作韵语以自适。”[9]
综上,出身教坊者,深谙音律、吟诗作画乃是入行的职业培训,为其阅读生涯埋下了伏笔;出身名门、官宦者,受到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亦或私塾先生的教化,读书习字乃是其原有生活状态;出身良家女子者有自幼读过私塾的,有受过父母良好教育的,亦有在妓院经过专业培训的,这些种种皆为其阅读之路奠定了基础。
1.1.2 自我觉醒
不畏社会言论,自主选择生活。晚明社会,娼妓制度被法律认可,娼妓职业尴尬地存生于以体面职业为主流文化和依靠奔波忙碌糊口的下层文化的夹缝中,不俗不雅、不伦不类。更何况,贞洁操守乃是传统社会中女德的核心,根植于女性的心灵深处,拿来出卖,理应被世人所诟病与鄙夷。但名妓并未因此沉沦,比如身处珠市的王月生仍保持着矜持高贵的心态,茶会知己、品饮香茗,“好茶,善闵老子,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10];范珏在清逸的茶香和袅袅的炉烟中读诗诵经,心如止水,淡泊笃定[11];马如玉,“凡行乐伎俩,无不精工,熟精《文选》《唐音》,善小楷八分书及绘事”[12];杨宛,能诗,有丽句,善草书[13]。可见晚明名妓不畏世人言论冲击,勇于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品茶、焚香、读书、赋诗、题字。
关注自我成长,挖掘自身价值。这种朦胧的自我觉醒意识源头有二。其一源自晚明的个性解放运动,名妓逐步关注自我成长、重视自我感受、实现自我价值。在读物选择上涉猎广泛,主要追求思想愉悦与精神解放,李维在《板桥杂记》英译版《序论》中说:“这些歌妓沉淫在书法、藏书、画论里……。”[14]当然,也有实现自身价值者,比如董小宛担起冒襄编写全唐诗集的助手,从稽查誊抄到细心商定,不分昼夜,读《楚辞》,读杜甫、李商隐的诗歌,也读王建、花蕊夫人和王珪的宫词[15];柳如是主动提出帮钱谦益点校图书,她聪颖过人,图史校雠兼通,遇临文、探讨或微讹、辨正,遂上楼翻阅典籍,虽缥缃盈栋,某书某卷某册,立时抽拈,百不失一[16]。其二源于名门望族、文人骚客、朝臣官宦的青睐与认可。著名女性心理学家谢尔曼认为:“妇女的自我评价相当一部分是依据其他人喜欢她们的确定程度而定的……这意味着妇女的自我尊重是由于她们从其他重要人物那里得到的信息形成的”[17]。名妓的自我肯定正是源于“重要人物”对自己的喜爱与认可。因为入选重要人物的诗词、获得重要人物的题字是赢得名气的最好招牌。
1.1.3 现实功用
一是顺应职业发展需要。明代文人对艺妓的要求,一是文学艺术修养,二为姿容风貌,三为居所清洁幽雅,即“艺、色、居”三方面。因此,在嘉万之际,秦淮青楼名妓辈出、卓尔不群、才貌双全,大都诗文书画俱能。《嫖赌机关》提出了对上层妓女的十项要求,前三项分别为“文雅”“脱俗”“翰墨”[18],可见,风雅宜人、读书识字、陶冶情操乃是名妓之所以“名”的重要条件。正如史学家章学诚所说:“女冠坊伎,多文,因酬接之繁。”[19]此外,名妓需要文人的追捧,她们渴望获得文人的赠诗题画,从而提高自身知名度。因此,名妓成名之前必须通文墨、懂诗书、知礼节、善谈吐,这是职业所需。晚明“花榜”选美乃社会风气,上榜之妓,并非胜在色情皮肉,而是赢在才艺学识,曹大章的《秦淮士女表叙》载:“今之所表,才技独详……予者不得为曲,受者不得而私,情兴丰姿,概置不论。”[20]此外,《金陵女士殿最》称:“日成众妓,不下百人……谱名花而俪色,摩艳曲以成声。呕尽闲心,刊为豪举。”[21]可见,青楼品鉴成为文人评选女妓的大型集体活动,也是女妓成名的绝佳机会。
二为早日从良,脱离烟花巷。名妓多为心性高洁之女,虽身陷风尘却不自轻自贱,不放弃对美好姻缘的追求,她们努力提高自身伎艺,尤其是在阅读方面,不仅为了提升自己,还为了遇到懂得欣赏和珍惜她们的士人。《续板桥杂记》中记载,王四兰姿玉质,喜清幽,“虽在风尘,常自秘匿,不甚见客”[22];明剧《西楼记》中名妓穆素徽虽是青楼宠儿,却说:“风尘浪得名,沦落何时已……只是性厌铅华,无奈阗门车门”[23];苗姬舍弃玉衣锦缎,不施粉黛,谢绝铅华,“益自匿不求侵暴,移栖旧院,门常闲,未尝以艳招人。”[24]传奇《红梨记》中名妓谢素秋厌倦了烟花繁华,“妾虽名在烟花,心同冰檗……虽落花无主,暂尔随风,而贞柏凌冬,不妨傲雪”。[25]然而,越是名妓,越难脱身,老鸨将名妓视为摇钱树,所以,名妓的巨额赎金不是一般人能付得起的,更何况娶妓女回家,将会遭到家族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而所谓“从良”的“良”字即是好人,对于青楼女子来说,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名士文人自然是理想之选,如礼部侍郎、文坛盟主钱谦益挣开礼法枷锁,以“匹嫡之礼”迎娶柳如是,并为其建设五楹三层的“绛云楼”,钱柳二人每天吟诗作赋,饱览群书[26];名妓吴娟以其腹中书香、诗词歌赋以及书画才艺赢得士人林茂赏识,两人诗词唱和,相得益彰,遂结为连理[27];名妓孙瑶华,嫁给了忧国忧民,慷慨解囊的新安江左大侠汪景纯,两人婚后“读书赋诗,屏却丹华”[28]。
1.2 社会因素
以乐籍制度与行院体系为背景的时代大环境下,明代青楼名妓有着相对稳定、富足、自由的生活空间。正是这种相对优越的外部环境造就了青楼名妓独立、自主、个性鲜明的人格特征。也正因此,明代青楼名妓才赢得广大文人士子的青睐。
1.2.1 青楼重视教育
《五杂俎》载:“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然扬人习以此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29]可见,“养瘦马”即包含雏妓的文化教育。一般而言,有四种人可能从事青楼教师职业。一是老鸨亲自担任教师。《虞初新志》载:“(董小宛)七八岁时,阿母教以书翰,輒了了。”[30]在鸨母的教导下,小宛刻苦精进,识翰墨、工诗词、知音律、善歌舞,为其日后成名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已成名妓女担任教师。《露书》载:“今燕(赵彩姬)老居琵琶巷口,每闭门,时号‘闭门赵’,常教授女郎,所著有《青楼集》一卷。”[31]又如名妓郑如英,嗜书如命,手不去书。《金陵杂题绝句》记载:“旧曲新诗压教坊,缕衣垂白感湖湘。闲开闰集教孙女,身是前朝郑妥娘(郑如英,时年七十二岁)。”[32]三是聘请名师讲学。绝大部分名妓都接受过名师的正规教育。如薛素素,“羡长好诗,师王行甫。人亦以薛校书呼之”[33];王少君“学字于公瑕(周天球),学诗于宗汉(余翔),学琴于太初(许性成)”[34];《亘史》载:“徐翩,字飞卿……同日就四师,授以艺:字则周公瑕;琴许太初;诗陆成叔;曲朱子坚”[35]。四是冶游文人的指点。晚明文人热衷于结会集社,切磋诗文、品议朝政,而文人集社多选在秦淮河畔的歌馆中,通过与冶游文人的日常交往,耳濡目染,女妓从中受到文化熏陶和内涵的提升,而文人从名妓身上也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和一种被认可与崇拜的满足。
1.2.2 社会文化开放
万历年间,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个性解放运动兴起,纵欲之风席卷整个社会。而晚明书籍的编纂、出版、收藏也极为兴盛,据缪咏禾先生粗略统计,明代出版物至少有3.5万种,尚不包括大量的童蒙书、劝善书、日用小类书等[36]。
综合晚明社会发展形态与文化氛围,可以窥见晚明名妓受到社会文化开放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一是男女受教育权利的平等观念。李贽提出男女均应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随即公开招收女学生[37]。冯梦龙也极力赞美女子的才智[38],“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陷井与价值观念被揭穿、摒弃。二是重视女性教育,女性读物日益丰富。明代的富家女子、平民女子乃至青楼名妓,都需要读书识字。《于氏家训》明确规定女子不许出闺门,教其《小学》《列女传》《内则》等,要求其做到朝夕讲诵,以达到“薰陶渐染,以成其德性”[39]。三是鼓励女性著书立说。据《历代妇女著述考》载,明代有女性著述236部,其中包含许多名妓作品,如范翩的《锦香词》、郝婉然的《调鹦集》、冯湘的《淡宜吟》等[40]。
1.2.3 阅读场所扩大
名妓大多生活在繁华的市区,经济繁荣,文化兴盛,书籍丰富。青楼是名妓赖以生存的场所,幸运者亦有机会陪同名士交游雅集、打猎游玩。所以,明末名妓的阅读场所主要集中在青楼妓馆和山水之间。
一是青楼妓馆。晚明张梦微的《青楼韵语》中有一处描写名妓居所,“一张天然几,摆着古花觚,内插几支花,天然几旁还摆了书柜,柜上摆设些古玩,柜下则收藏着几部古书”[41],可见青楼妓馆是名妓藏书、读书的重要场所。如名妓董小宛,其房中撤去繁华之物,摆设只有书帙、瑶琴,外有芭蕉遮掩屋簷,悠然读书,宛如山中隐士[42]。名妓王微“竹映回廊堪步屧,云连高阁可藏书”,俨然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山中女子[43]。谭元春称赞(王微)道:“心心留好月,夜夜抱奇书。女伴久相失,荒村独晏如。”[44]。再如顾媚、李十娘等人的眉楼、寒秀斋等,清幽雅致,书香萦绕,是聚集欢宴之宝地,亦是产生清辞丽句的文艺沙龙。
二是山水之间。晚明江南一带,水运便利,物产富饶,堪称温柔富贵乡,花柳繁盛地,引无数巨绅、贵士、硕儒到此缉文墨,理弦歌,一决高下。每年秋试之时,便是妓院兴隆之际。《板桥杂记》载:“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45]《秦淮画舫录》载:“士大夫得以优游艺事,与曲中诸姬作文字之饮。而诸姬亦藉是涵濡气质,相得益彰。”[46]可见,青楼中的文酒声妓之会既是士大夫“优游艺事”的韵事,亦是名妓借此与文人交游,受其文学艺术薰陶的机会。陈继儒在《微道人生圹记》中说:“(王微)自幼有洁癖、山水癖、书癖……”,她在阅读之时,全神贯注,即使窗外有虎,依然神态自若[47]。《淮海英灵集》载:“王微……住无常地,往来西湖,游三楚三岳。”[48]《列朝诗集》载:“……(王微)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所与游皆胜流名士……登大别山,眺黄鹤楼、鹦鹉洲诸胜,谒玄岳,登天柱峰,溯大江,上匡庐,访白香山草堂……”[49],成年之后的王微,才情超群,编撰《名山记》数百卷,其《远游篇》《浮山亭草》《宛在篇》等诗集也都与山水有关,颇能代表晚明游方名妓之风流[50]。
2 晚明名妓的阅读内容
2.1 遍览经史,博涉百家
晚明不少名妓遍览经史,博涉百家。比如顾媚、董少玉、崔嫣然,皆爱文史,《板桥杂记》载:“(顾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51];“(崔嫣然)知文史,弱质丽姿,见宾肃客,言笑动止,不爽尺寸,居人礼义中人……”。[52]亦有精通儒家经典的杨玉和杨云友,《列朝诗集》载:“(杨玉)十岁时,已能诵《语》《孟》《诗》《书》”;“(杨云友)涉书传,通六艺”[53]。博涉百家的名妓不多,但依然有阅读量能与李清照不相上下的米小大,其“涉猎文艺,粉摇墨痕,纵横缥帙,是李易安之流也。”[54]
2.2 喜吟诗词,博闻强识
诗词是晚明时期的主要阅读内容。马如玉,“凡行乐伎俩,无不精工,谙熟《文选》、唐诗。”[55]沙才,不止精熟唐诗,还能点评,《十美词纪》载:“沙才者……工诗……几上有自评唐诗及《花间集》。”[56]朱无瑕,师从朱长卿,得《唐诗正音》《品汇》后,悉心收藏,不分朝夕,每日吟诵[57]。李因熟读《古诗十九首》《庄子》《离骚》《晋书》《花间集》等,喜爱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词[58]。顿文,可将唐诗倒背如流,《板桥杂记》载:“顿文,性聪慧,识字义,唐诗皆能上口。”[59]苗姬,“识字从韵语广测,展卷即上口成诵,间喃喃喜吟未敢陈也。”[60]柳如是,自号河东君,钱谦益称其“柳儒士”,沈虬在《河东君传》中记载:“知书善诗律,分题步韵,倾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61]在与四方名流的诗词唱和中,柳如是亦能对答如流,出口成章,冠绝时人。
2.3 诵读经卷,皈心佛道
晚明时期,部分名妓喜诵佛经。如郑如英,“亲铅椠之业,手不去书,朝夕焚香持课,居然有出世之想”[62]。范钰,“惟阖户焚香瀹茗,相对药炉,经卷而己。”[63]名妓除诵读佛经之外,亦有皈依佛道者,大致可分三类。一类皈心佛门。朱无瑕,“闭门深思,有郁郁不可解者”,后归栖霞禅师而终,其住所名为“绣佛斋”,遂著《绣佛斋集》[64]。晚年的佛教女居士周绮生,言论举止得度适礼,远离红尘,毁容礼佛,虔心奉法,勤谨修持,以终其生[65]。马如玉情思淡泊,无儿女缠绵之情,“受戒栖霞苍霞法师,易名妙慧,专功学佛,遍游太和、九华、天竺诸山”[66]。以上均为看破红尘,一心向佛,不再出嫁的名妓。二类信奉道家。朔朝霞,字曙光,金陵名妓,终为女道士,有《红于词》[67]。李香君,与侯方域挥泪诀别后,立志守身,后无再嫁,在养母帮助下,逃至栖息山做了女道士。[68]从可查资料来看,信奉道家者数量较少。三类徘徊于佛道之间。马守真,信奉佛、道,《列朝诗集小传》载其病逝前夕,“燃灯礼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七矣”[69],马守真追求道家的“真”,其画作上常落“守真”名款或钤朱文印“守真玄玄子”,以示心迹。[70]卞赛,自称玉京道人,撰有《玉京道人集》,“在道作道人装……长斋绣佛,持戒律甚严,刺舌血书《法华经》以报保御。”[71]可见,马守真与卞赛彷徨于佛、道之间。
2.4 普习女教,好览戏曲
晚明名妓为日后从良做准备,在读物选择上多倾向选择一些与闺阁女子基础教育相一致的书籍。前文中提到女妓有源自罚良为娼制度者,有被贩鬻行院的良家女子,有因战乱、家道中落陷身青楼的大家闺秀,这类女妓自幼熟识《百家姓》《千字文》《小学》及儒家经典《论语》等,再如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宋若莘的《女论语》,等等。此类女妓将读物与其她女妓分享,女教书籍不日便通过手抄、传阅、赠送等方式流传开来,部分名妓纷纷受到女教书籍的熏陶渐染,养成德性。
琴曲技艺是青楼女子的必修课,因此大部分名妓都通晓音律、吹箫、度曲、鼓琴、琵琶。尹长春,洗净铅华,举止文雅,性情温和,专攻戏曲表演,余怀在迟暮之年曾邀她表演《荆钗记》,演到《见母》《祭江》时,悲壮淋漓,声泪俱下,在座宾客包含戏曲老演员皆自叹不如[72]。陈圆圆亦擅长戏曲,在《西厢记》中饰贴旦红娘角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73]。马湘兰独创戏曲《三生传》,讲述书生与青楼女子间三生转世的爱情故事[74]。梁小玉亦擅戏曲创作,其在《合元记传奇》中,塑造“不受乾坤之拘缚”的才女黄崇嘏形象,并亲自登台扮演,发出“愿天速变作男儿”的心声[75]。江上名妓冯静容,演戏意度潇洒,风韵不减徐娘,每场出演,声情并茂,座无缺席[76]。杭州名妓朱楚生,精通戏曲,演剧全力为之,与名士张岱切磋戏曲,关系甚好[77]。可见,名妓不但喜欢戏曲,能够对剧本进行深入解读与揣摩,还自行创作,并能将戏中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
3 名妓阅读的影响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女性文化是被传统文化所遮掩的一个弱势图层,而晚明名妓及其所创造的名妓文化突破了男权主导下背离人性、歧视女性的传统道德,她们以自己的才华和行为证明了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享受阅读的快乐和创作的美好,她们通过自身努力赢得了尊重与人格的独立。
3.1 系列诗文集相继产生
明代中后期,文人与女妓的频繁交往为女妓诗词歌赋的精进奠定了基础。至明代晚期,女妓诗词已蔚为大观,如柳如是二十一岁著成《戊寅草》,后又有《湖上草》35首,《尺牍》31通,与钱谦益唱和《东山酬唱集》中存诗18首;葛徵奇将李因的诗集刊印出来,存于《竹笑轩吟草》(初集、二集、三集),其中诗522首,词22阙;顾媚爱作诗,其诗词《海月楼夜坐》《花深深·闺坐》《虞美人·答远山夫人寄梦》等收入所著《柳花阁集》;梁小玉爱读史,著有《古今咏史录》十卷、《诸史》百卷、《千家记事珠》三百卷、《古今女史》若干卷,其亦爱赋诗,七岁韵赋《落花诗》,长大后涉猎群书,又作《两都赋》,《乡嫘集》二卷、《草木鸟兽经》《乐府骊龙珠》《山海群国志》《古诗集句》等;孙瑶华著有《远山楼稿》,诗句一出,诗人词客皆为之逊色;冯梦祯“能文章,工诗”,“下笔成琬琰,秦淮一曲几于独秀”[78]。晚明许多名妓热爱读书、思考与创作,留下了许多诗词著作等文学成果,这种阅读能力的养成与创作天分的激发,一方面体现出名妓在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觉醒,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在成果背后所付出的时间与努力,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是名妓苦于阅读,精于学习的结果,而这些成果必将成为女妓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垂之永久,不可磨灭!
3.2 女性价值得到认可
明代文人的诗酒结社活动与女妓诗词的编纂与选辑,都客观地促进了青楼女妓的诗词创作。李鼎说:“据余目所见,林天素画擅一时,风髮雾鬓,而多高韵;王修微诗惊四座,读书谈道,而多胜情。”[79]从他的盛赞中,可以看出明代男性的审美品位发生了变化,名妓们熠熠夺目的文采更令他们折服。降及明末,在声势浩大的重情思潮下,女性传记的编纂风潮行诸实际。女性传记的整理体现了明代文人对女性才艺、学识、贞节、情操、品质等方面的要求,从明成祖命解缙等人编纂《古今列女传》,到后来王世贞的《艳异编》《续艳异编》、吴大震的《广艳异编》、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潘之恒的《亘史钞》,再到秦淮寓客之《绿窗女史》与冯梦龙的《女史》,无不体现了明代文人这种强烈关注女性、认可女性、肯定女性的呼声。当然,也有一些文人、名士欣赏名妓的文笔与才学,为其书写传记,辑录诗集。正是这些散传打破了前期文人“以史为鉴”的创作传统,使女性传记不再单纯地成为女学说教的工具。明末女传的创作与整理活动亦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整理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名妓所带来的影响更是整个社会对女性价值、女性文化与文明的重新审视与反思。
3.3 艺术才能得以启蒙
名妓自身就是一个文化艺术群体,她们是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者亦是创造者。艺术不仅滋养了名妓的高雅气质,提升了名妓的审美层次,也是其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的资本,融入高层文人圈的敲门砖。擅长艺术的名妓与其天资悟性、博览群籍、誊抄卷册、广结名流是密不可分的。青楼女子多工楷书,尤擅小楷、小行楷、八分书楷,如董小宛的扇面小楷,行笔峻快,锋影秀拔,堪称书法精品;柳如是的字,柔中带刚,冷峻却有骨感,人称“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郝昭文,“小楷法黄庭坚甚工,亦能诗”;杨宛叔、朱无瑕擅诗词亦懂书法,人称“工诗善楷”;卞玉京,“知书,工小楷”;王月生,“善楷书”[80]。在绘画艺术方面,明代个别名妓开创了女性画家画山水的先河。晚明很多名妓深谙丹青之道,柳如是,“工于尺牍,深得虞褚之字法,其山水画淡墨淋漓,不减元吉、子固”;范珏,“摹仿史痴、顾宝幢,檐枒老树,远山绝涧,笔墨间有天然气韵,妇人中范华原也”;马湘兰,善画兰,后以“马湘兰”著称,《玉台画史》称马湘兰:“双钩墨兰,旁作筱竹瘦石,气韵绝佳”;还有薛素素、顾媚、寇白门亦是画竹兰好手[81]。文人士大夫的喜好往往会影响这些心思细腻的青楼女子,反过来,青楼女子的作品也激发了士大夫创作的灵感,从而带动了明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3.4 社团文化应势而起
名妓共有的文学雅趣、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以及身份的特殊性,使明帝国的名妓经常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文化社团。尤其是以江南为轴心的东南大部分州府,都有名妓活动,妓业的繁荣发展为名妓群体的规模出现提供了必备条件。
爱好戏曲的名妓经常性的客串演戏,形成戏曲社团。“南曲中,妓以串戏为韵事,性命以之”,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多次记载此类活动,如一次姚简叔约顾媚、李十娘等与名伶候童及张岱家妓马小卿、陆子云等演戏,由于行家张岱在场,名妓们竭尽所能,张岱对戏曲颇有造诣,经常给名伶、名妓们指点一二,名妓通过客串演戏,得到诸如张岱等艺术家的点评,演绎水平得到很大提高[82]。爱好阅读的名妓经常交流心得,诗词唱和,形成读书社团。比如顾媚、李十娘等人的眉楼、寒秀斋等,书香萦绕,聚四方名士,集八方文客。兹以眉楼为例,其铺陈精致,装饰儒雅,“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安;瑶琴锦瑟,陈设左右”[83],邀请各界文人雅士,品评诗书,畅所欲言。此外,晚明士妓经常诗文会友、小饮小聚,社友文化活动十分频繁,淮南社建立时,新安王太古曾邀请善作诗词的周绮生加入诗社以壮社力[84]。士妓社团文化的相互交织,产生了许多传世的清词丽句和艺术作品,比如余怀的《板桥杂记》,吴梅村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圆圆曲》,陈子龙的《秋塘曲》《春日风雨有感》,孔尚任的《桃花扇》,等等,均成为流传后世的名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