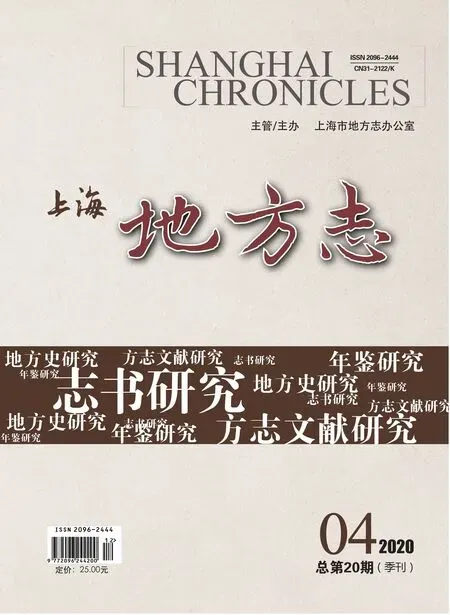慈善的方志书写与记忆的文本形塑*
我国的修志传统与农耕文明有着内在的关联,有着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本特质。农业社会中,小农式生产方式难以应对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故而灾疫不断,与之相对应,政府救济和民间慈善从未停顿,志书中关于灾疫与慈善的记载也很少缺席。方志中的慈善书写贯穿了宋元以降方志定型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大体量的记载中若隐若现的,是地方精英对话语权力角逐、历史记忆争夺、地方文化构建的痕迹。而修志传统与慈善传统彼此交互契合,绵延不衰,亦体现出文本和表达互动的力量,以及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
一、慈善的方志书写
我国自然灾害频繁,破坏严重,影响巨大,历来政府都重救助,并以民间慈善为辅,共同应对灾害。方志则对灾害与应对都做了全景式记录和演进式书写。
宋真宗时邢昺曾说:“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①《宋史》卷431《邢昺传》,第12799页。灾害经常造成饥荒等严重后果。“九农失业,民庶嗷嗷”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7,第3554页。,“流民饿殍,充满道路”③赵抃:《赵清献公文体》卷7《奏状论久旱乞行雩祀》。,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宋代全国一般灾荒之年死亡人数就在10万以上,大灾大荒之年死亡在百万人以上。灾荒年间饥民和流民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少则万人,多则百万。④如嘉定元年的淮民大饥流于江、浙者百万人,见《宋史》卷67,第1466页。发生在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的丁戊奇荒⑤发生于华北地区的这场罕见特大旱灾饥荒,被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与迁移,破坏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破坏城镇及交通运输,大量损耗财富,动辄“功费骚动半天下”⑥《宋史》卷92《河渠志二黄河中》,中华书局1997年,第2301页。元祐七年(1092年)赵偁于其上奏中称:“自顷有司回(黄)河几三年,功费骚动半天下”。转引自李华瑞:《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事关国计民生与统治稳定,历代官府都颇重救荒,在“荒政”方面多有建树,尤其是南宋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和朱熹等人的大力倡导与推行,“荒政”等慈善措施开始步入正轨。随着慈善思想的日趋成熟,慈善措施的范围越来越广,不再局限于灾后应对,开始向日常救济、文化慈善等方向扩展。方志记载也随着慈善的发展而逐步演进。
比如,据宋代文献记录统计,两宋各种灾害①含水灾、旱灾、蝗螟、地震、风灾、雹灾、潮灾、寒冷、疫灾、鼠害等。合计发生1931次,其中严重灾247次、大灾48次、特大灾23次。②李华瑞:《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政府疲于救灾,且无长效。为改变状况,南宋朱熹倡建社仓。初始所办不多,据梁庚尧《南宋社仓分布及资本来源表》,南宋仅33个州郡有办,行都临安府全无一例。在朱熹任提举常平的浙东绍兴府,也只有附郭会稽、山阴二县建了社仓,而六个外县都没有建。于是,在宋元浙江地方志中,除《嘉泰会稽志》设“社仓”一目外,如《咸淳临安志》《景定建康志》《宝庆四明志》《嘉泰吴兴志》《景定严州续志》等都未载宋代社仓。即如《嘉泰会稽志》所载:“诸路既不能皆如诏(指孝宗下诏推广朱熹社仓),而府外之六县亦止报府,言一面措置,竟不以已立社仓为言。惟会稽、山阴二县至今为小民之利”。③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3《社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又如至少在宋代就出现孤儿院(慈幼局)、养老院(安乐院、养济院、安济坊)、施药局(惠民局)、义仓(平粜仓、预备仓、盐义仓)等慈善机构(北宋苏轼守杭时就创办了养老院),现存宋代方志中记载亦少。同样,现存最早的镇志系宋代常棠所撰的绍定《澉水志》④澉水在海盐县东三十六里,《水经》所谓“谷水流出为澉浦者”是也。唐开元五年(717年),张庭珪奏置镇。,该志叙述简核,8卷仅44页,分15门(地理、山、水、廨舍、坊巷、坊场、军寨、亭堂、桥梁、学校、寺庙、古迹、物产、碑记、诗咏),并无有关慈善的记载。而在后续800年间5次编修的《澉水志》中,除清康熙吴为龙《再续澉水志》已佚外,明嘉靖董榖《续澉水志》(卷七“孝节”)、道光方溶《澉水新志》(卷九“人品”)、民国程煦元《澉志补录》(“人物”)中,均有与慈善相关的内容。可见,当慈善越来越被政府认可,影响日趋强大时,方志中的记载也在逐渐增加。比如,明清方志中关于慈善组织(如善堂、善会)等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善会善堂非常集中的江南地区的地方志中,在“善堂”等项目下保存有大量的史料。⑤[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序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
而随着近代西方慈善理念传入与方式的推广,传统慈善有了很大的改变,新兴的慈善方式与组织不断出现,如万历《黄岩县志》记载黄岩人赵处温通过设立专项储蓄,用以周济乡里之事;光绪《嘉兴府志》录有6所明清嘉兴的同善会,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则录有8所慈善组织;《民国南浔志》记载了南浔师善堂;光绪《桐乡县志》记录了1872—1887年间桐乡21个保婴会共救助了超过4000名婴孩,且“死亡不足十一”的慈善成果,等等。
可以说,宋代以降方志定型以来,尽管内容繁简不一,方志对慈善有着长时段、全景式的记录,涵盖灾害救济、日常救济、医病施药、养老慈幼、慈善教育等慈善事业,义仓、义学、善会等慈善组织,并关注慈善的主体——士人官员、乡绅富民甚至僧道、妇女的慈善活动,以及慈善组织的创办、活动方式和经费来源,慈善思想的成果传播等等。在方志的“善行”“教义”“乡贤”“人物”“赈恤”“蠲恤”“义举”“建置”“杂志”等不同篇目之下,“无数的慈善模范密密麻麻地依次排列着”⑥[美]韩德林(JoannaHandlinSmith)著,吴士勇、王桐、史桢豪译:《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无数的善行义举和与慈善相关的内容也被记录着。
作为历史研究尤其是自宋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基础文献,方志的史料价值备受肯定。在有关灾害和慈善的研究中,中外学者几乎对方志资料都有所采用,颇为倚重。①如周秋光《中国慈善史》、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美]韩德林《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等等。如《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②国家气候中心张德二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4年12月。采用的7835种文献中,方志是最为主要的资料来源。方志里的灾害记载时间早,内容全,系统辑集后基本可见灾情大概。③该书系统辑集我国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1911年三千多年间的各种天气、气候、大气物理现象和水旱等各种灾害,以及政府救灾措施的记载,共4大册约880万字。如乾隆八年(1743年)夏或是史上最炎热的夏天,北京、天津、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极端炎热,所涉地的方志里均有记录④如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同治《续天津县志》)。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民国《高邑县志》)。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乾隆《浮山县志》)。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乾隆《青城县志》)。。又如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美]韩德林《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周秋光《中国慈善史》、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等,搜集、整理、运用了大量方志资料,对慈善组织、慈善活动、慈善事业的发展等做了精彩系统的论述。从这个角度,也可验证方志对慈善内容的记录是较为全面和可靠的。
二、二者的身份契合
所谓“一乡有善士,胜于一邑有好官,谓其情更亲而机亦顺也”⑤刘衡:《州县须知》“劝谕生监敦品善俗以襄教化告示”,见《官箴书集成》第六册,第116页,黄山书社1997年12月。。两宋起始,尤其是明清以来,乡绅成为具有知识和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⑥中国士大夫作为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在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中受到青睐。张仲礼、费孝通、萧公权、曲通子和何炳棣是关于士绅研究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介乎官僚与民众之间的乡绅广泛地活跃在民间慈善的各个方面,在慈善活动中担任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角色,成为慈善的核心力量。有学者称:“贵族们是国家的希望,他们虽说在家行善,但足以影响府县,改变州和村的习俗。”⑦[美]韩德林(JoannaHandlinSmith)著,吴士勇、王桐、史桢豪译:《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同时,就修志而言,在经济实力、政治地位、文化水平、地方话语权力、地方历史文化和基本地情等关涉志书编纂的众多方面,地方乡绅无疑都占据着优势甚至掌控的地位。⑧陈野:《关于修志传统与农耕文明内在关系的探析》,《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8期。于是,慈善与修志形成了一种互动互利的局面。
一方面,在士绅看来,办书院、修方志等公益事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慈善,为善乡里,造福一方的愿景,对地理认知与文化认同的渴望,使热心慈善的士绅往往同时也是修志的中坚力量。
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组织——杭州善举联合体的总董丁丙,是丁氏家族的族长、士人,是抢救四库全书、重建文澜阁的大功臣,是详细记录了杭州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之书《乐善录》的编撰者,同时也是名志佳作《武林坊巷志》与光绪《杭州府志》的修纂者、各种地方文献的刊印者。此外,仅清代乡镇志书的编修者中,就有诸多参与修志士绅的善举记载。如光绪《双林志续纂新辑》的纂者蔡汝钅皇(字元襄,光绪二年丙子举人),“外和而中刚,未尝立崖岸,至其所不可,必有执持。”⑨[清]施补华撰:《泽雅堂文集》卷8《蔡元襄哀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1册影印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陆心源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生平急公好义,有豪气,尝随其叔父雪樵先生(即同治《双林记增纂》的编纂者蔡蓉升)创办蓉湖书院及崇善堂,颇著勋劳,蓉湖书院列其名焉。碑记列其名,至今镇人犹称颂不止。”①蔡松辑纂:民国《双林镇志新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二十二册(下)影印嘉兴市图书馆藏1915年稿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他如《三江所志》陈宗洛(诸生)秉性慈善,热心里中慈善公益事业;光绪《善和乡志》程文翰(诸生),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多为善举;光绪《唐市补志》龚文洵(诸生),为人乐善好施;同治《鹦鹉洲小志》胡凤丹(诸生、湖北道员、著名学者、藏书家),生平乐善好施,热心文化事业;光绪《梅李补志》黄宗城(举人、沛县训导),以行善为务;同治《江湾志稿》陆宿海(诸生),专心里中善举;光绪《罗店镇志》钱枏(增生),热心里中善举;同治《续修茜泾记略》陶炳曾(附贡生),为人乐善不倦;《茜泾记略》陶宗亮(国学生),品高行洁,为善不吝;光绪《枫泾小志》许光墉(附贡生),生平乐于为善;同治《盛湖志》仲廷机(举人、严州知府、道员),生平笃志好学,好为乡里善举;等等,不胜枚举。
正如生活在欧洲城邦里的土地贵族建立了公益捐赠制度,对他们来说,管理城邦是一种权力和对国家的责任。“这个阶级把为城邦牺牲自己视为一种责任,因为贵族身份要求这样”。“同样,他们觉得有责任让事情运作起来,即使自己出资,也应该让自己由于慷慨大方而享有声望……”。②[法]保罗·韦纳著,韩一宇译:《人如何书写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第63—64页。
另一方面,“士绅的公益事业的文化包装,由德行超卓、深孚众望之人举行的慈善活动所表达,这意味着士绅公益事业投资是处于严密的文化审察之下,同样它也有助于巩固士绅在地方社会的统治地位”。③[加]卜正明:《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与此相应,士绅的慈善活动在方志中被更多地记录下来。
以光绪《桐乡县志》为例,在这部个人修纂的县志中,严辰④严辰(1822—1893年),原名仲泽,字缁生,号达叟,桐乡青镇(今乌镇)人。不仅于《卷四·建置中》的学宫、书院后设义学、善堂、善会予以详述,于《卷十五·人物下》设义行广记善士,更于志中收录了多篇与自己相关的善事诗文,如《严辰设立桐乡青镇两处义学记》《严辰桐乡青溪书院祭三贤堂祝文》等等,甚至收录了俞樾《沈茂庭事释疑》一文,专门辨析善士沈茂庭被“墙坏压而卒”⑤古代,畏、压、溺被视为“丧事三不吊”之范围。是否有为不善而隐匿一事,澄清为善不报的谣言。可以说慈善的内容在全志中无处不在。而他本人,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举人,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刑部主事。不久辞归乡里,服务桑梓。同治三年(1864年),江浙粮荒严重,严辰自上海募米运至乌镇,赈济贫民。后又开办善后局,修筑运河桥梁,以利交通。四年,创办立志书院于青镇,任书院山长。十年,又于书院前河埠之西建文昌阁。其后,任桐乡桐溪书院、濮院翔云书院山长多年,建立乡镇义塾6处,为乡里培育人才。又创建积谷仓,钱谷并储,得谷数千石、银三万余,分存各典当,产生利息。光绪八年、十五年,乌镇附近先后两次灾荒,幸有严辰创议,早有储备,将积谷与储蓄用于赈济,百姓赖以度荒。他修学宫,办书院,筑桥铺路,行善济贫,“凡地方应行兴革之事,无不尽力倡办”,是受乡人尊敬的乡绅。他的善行,被完整地记录了在他经10年辛苦亲自编纂、又耗资4000元的县志中。
值得一提的是,严辰曾因善事结缘于李鸿章和左宗棠。县志的《撰述志·三感篇记》记录,在光绪癸未年(1883年)春发生的秀桐两县客民诉讼事件中,严辰等绅士、富人被“巫控”,幸得“李公一纸书”,才摆脱困境。另在同治三年(1864年),为了筹办赈济事务,严辰曾专程赴杭州进谒浙江巡抚左宗棠,他为此事作诗曰:“我为遗黎曾乞命,一言许救万民饥”⑥《墨花吟馆感旧怀人集》之《左宗棠》一诗,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后来,左宗棠还捐廉为张扬园(即张履祥)先生立祠,县志里也做了记录。慈善把严辰与朝中大员联系在一起,巩固了他在地方的权威和地位,而修志则为他创造了最好的书写自身行为的机会。
另外,晚明以来,一些人并不具备崇高的政治和文学地位,甚至不识字,却因做善事获得了社会地位,并被记录于方志,留存于地方记忆中。身为官员的救荒组织者们在地方志和他们个人的文集中,为民间慈善富户留下的大量文字记载,本身也是对义行的鼓励。①周致元:《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在可能进入乡邦文献的鼓舞下,乡民也认为理应由士绅领衔修志。明弘治《徽州府志》编纂者汪舜民在序中即明言,修志过程中,乡人为使“宗族乡里人物文献得以表彰,故积极行事,共襄厥成”②明弘治《徽州府志》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由此,士绅们获得了更多来自富人、乡民的支持,在地方事务的运作上更加游刃有余。
三、记忆的文本形塑
随着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渗透,方志不再局限于资料库的定位,其“文本”特性受到重视,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研究和解读的对象③近十余年来,先后有冯玉荣《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谢宏维《文本与权力: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潘晟《南宋州郡志:地方官、士人、缙绅的政治与文化舞台》、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胡克诚《不同历史记忆中的李维钧与梅会李氏——清代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中的利益差异》、范莉莉《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等文,从等不同角度对方志作了“文本”关注。。一向被视作具有公共历史存记性质的地方志,不再仅仅是具文的官方典籍,而是拥有文化优势的人群(掌握书写权力的本地官绅)表达个人主张、谋求家族利益的对象和途径。④范莉莉:《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由此,更进一步地影响一地社会记忆的形成与历史记忆的传承。与“文本”研究一样,在“记忆”研究渗透到各个学科之后,近年来,也有个别研究涉及了方志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⑤如王一娜《方志中的记忆与官绅关系——以晚清知县邱才颖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胡克诚《不同历史记忆中的李维钧与梅会李氏——清代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中的利益差异》、张勤《记忆视角下的史志研究及其实践意义》,等等。
根据包弼德对婺州(金华府)(今浙江省金华市)及其属县历代方志的考察,宋元方志的编写就已不是出于中央的命令,而来自地方的主动性,并存在着地方精英对国家需索的抗衡,有些地区的士人已控制了地方志的编纂。因此方志在简要记录地方政府活动的同时,也记载了士人们的看法和生活。由这类方志文本构建出地方精英(绅)的历史记忆,与国史对应的朝廷(官)、传说对应的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其中蕴涵着地方社会官、绅、民之间在权力、信仰、利益等关系上的矛盾与纠结。
在而明清以来士绅主持或参与编纂的方志中,关于官、绅慈善的记录,不仅在内容多寡上有变化,书写方式也逐渐产生出着微妙的变化。如梁其姿发现,晚清的志书在叙述慈善机构的时候,关于政府救助的颂词逐渐消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政府歌功颂德,把救济穷人的功劳归功于政府。甚至还有给富人写的祝颂词,如宋嘉泰间卓田的《满庭芳·寿富者三月十八》以“好是钱流地上,仓箱积、赈济饥贫”表达敬意,“多阴德,子孙昌盛,指日绿袍新”表达祝愿。语言形式主义的最终破裂,表现了对民间慈善救济机构的观念的变化。⑥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这些变化也代表着士绅的慈善功劳与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认可与尊重,知识权力与话语空间也得到确认与拓展,体现出方志文本对历史记忆形塑的过程。
虽然明清时期官方的慈善管理呈弱化趋势,在大灾之时甚至陷入无力掌控的局面,政府也逐步放开慈善准入门槛,鼓励士绅富商积极参与,但是无论民间慈善如何发展,基于慈善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官方的社会救助与慈善管理从未也不会完全退出,在必要的时候还会果断地予以强化。我们也看到政府对方志的修纂并不在完全控制之中,存在着地方精英对国家需索的抗衡现象,但是总体而言,对修志的管理并未脱离原有的轨道,清末民初甚至从府县向乡村延伸拓展。
四、结 语
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家与国的同构状态,封建专制本质决定“家国同构”观念不仅不能促进家与国的良性互动,反而使两者拉开了距离和走向对立。①舒敏华:《“家国同构”观念的形成、实质及其影响》,《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月第4卷第2期。当然,事情都是辩证的,通过研究自宋以来相关府县、乡镇的修志活动和志书文本,可以观察到方志形塑古代文化传统的独特路径,也可以感触到古代修志得以开展的内在动力,来自地方官府、宗族力量和国家意志的缠结、互动和整合。他们在“家国同构”的范畴内近距离接触和“对峙”,推动社会进步革新,促进自身发展蜕变,成就了修志传统的长盛不衰。可以说,稳定的乡绅阶层是修志的文化推手,地方文化整合则在专制皇权掌控之下,修志如此,慈善亦相类似。因此,慈善与修志的互利互动,善士与志人的身份契合,记忆通过文本得以形塑,其中若隐若现的,是地方精英有对话语权力角逐、历史记忆争夺、地方文化构建的痕迹。而这,仍在“家国同构”的框架内,并未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