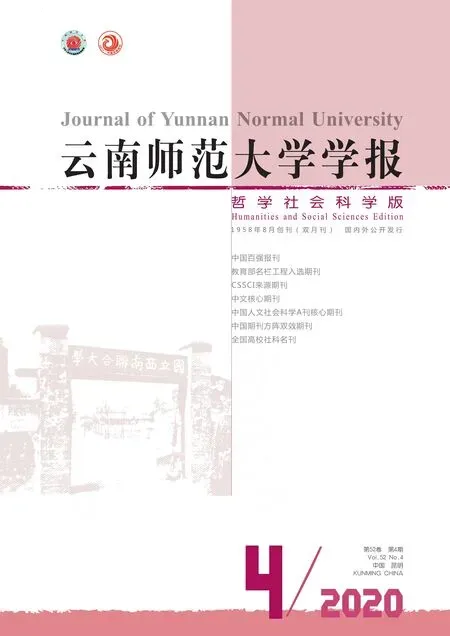本体之真:中国传统绘画美学对视觉写实的超越*
刘连杰
(云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写实”概念是经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舶来品,尽管从其传入之初就已经中国化,但却是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绘画美学写实观念为标准,强调透视、解剖、光影等造型原理,在画面中刻意营造逼真的视错觉,实质是从事物本身转向视网膜映像的再现,最终偏离了趋向事物本身的写实意志,(1)刘连杰.一己之见:西方写实绘画的视觉机制与哲学反思[J].思想战线,2019,(3).成为“小己主观地位的远近法”,(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48.是“人站在一个固定地点看出去的主观景界”(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11.。以此来衡量中国传统绘画是否写实,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绘画不重视“师法自然”的写实,而是强调抒发主观性情的“写意”,实在有失公允。实际上,中国传统绘画美学具有更强烈的趋向事物本身的写实意志,但不同于西方透视画法对视网膜映像的逼真再现,它始终警惕视觉的主观性,强调超越视觉局限性的本体之真。
一、“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中国传统绘画美学对视觉局限性的批判
事物需要通过视觉显现,但事物并不仅仅停留为视觉景象。知觉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视觉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或侧面,正是因为事物具有对视觉隐藏起来的丰富性,事物才能超越视觉景象而作为一“物”在视觉之外独立存在。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应该区分“由诸透视外表构成的层次和它们所呈现的事物的层次”(4)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6.。事物并不封闭于视觉之中,不会在视觉中被消耗殆尽,视觉也不可能完全占有事物,视觉总是已经先行接受了事物的召唤和引导。因此,用视觉标准来衡量事物的真实性,恰恰是缘木求鱼,从事物本身的立场而言,视觉恰恰是有局限的。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发现了视觉的这一局限性,并从哲学高度进行了批判。《庄子·秋水篇》指出:“井鼃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5)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563.视觉会受空间、时间和成见的影响,而偏离事物本身的方向。而封闭于视觉之中的人,往往会盲目相信视觉而不自知,“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561.对此,庄子还着重讲述了“埳井之鼃”(赵谏议本作“埳井之蛙”)的寓言,后人由此演绎出了“井底之蛙”“坐井观天”的成语。如果将之与西方绘画透视写实观相比较,这一寓言就会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蛙在井底之所见,乃是由蛙眼与井口直径形成的锥形空间,这极似西方透视法的小孔成像空间,即暗室中由小孔投射进来的光线所形成的明亮的锥形空间。蛙离井口越近,视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总之,景象会根据视点的变化而变化。而在井外的东海之鳖则不同,它向埳井之鼃讲述的是一种超越时空局限的景象。东海“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7)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598.,始终保持为自身。从事物本身出发,“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8)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577.,这种大小观不能用透视中的远近法来表现,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观物方式。因此,不是用视觉来裁剪事物,而是应该让事物来引导视觉。
视觉的局限性在观大物时尤其明显,南朝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9)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83.眼睛只能看见山水大物的局部,这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成了一个问题,而作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远近法才得以被提出,即“迥以数里,则可围于方寸之内。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10)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83.也就是说,这里的远近法不是一套可以独立于事物本身的透视法则,它为表现山水的整体之形服务,只有采用推远法,才能在画面中表现出山水大物的整体面貌。可见,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切不可以不变应万变,更不可毕其功于一役,因为这种远近法同样是有局限的。与宗炳同时期的王微就指出:“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11)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85.视觉是有局限的,所见并不周全,但何以会不周全,当代却多有误解。陈传席将“太虚”解释为想象之物,认为眼睛看不见想象之物,故所见不周,而山水画既要画想象之物,也要画眼见之物。这种解释既无哲学思想的印证,在王微全文中也极显牵强。“太虚”一词出自《庄子·知北游》,王微之前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有“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句,韩伯康独创“大虚”理论以释《易传》,王微之后梁代沈约《均圣论》有“天地之在彼太虚,犹轩羲之在彼天地”句,均指万物存在于其间的虚空,是至大无外的整体。实际上,对“所见不周”的解释,被王微称赞为“纵漭瀁之极”的庄子早有论述,即“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1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572.,看清细节就看不见整体,看见整体就看不清细节。王微指出“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乃是提出绘画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即“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13)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85.,既要远画山水的整体,又要近画山水的局部。这是对宗炳远近法的补充和超越。
王微的这一观物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同样指出了“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的局限性,认为“真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玩习不能究错纵起止之势。真山水之阴晴,远望可尽,而近者拘狭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对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与王微一脉相承,但更具操作性,即“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14)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634~635.落实到画面,他要求“正面溪山林木,盘折委曲,铺设其景而来,不厌其详,所以足人目之近寻也。旁边平远峤巅,重叠钩连缥缈而去,不厌其远,所以极人目之旷望也”。(15)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640.远望以画出整体山川的来龙去脉,近观以画清局部山川的溪流林木,方得视觉之周全。
西方透视画法截断视觉投向事物本身的目光流,停留于视网膜映像中的视觉景象,甚至师法遵循机械光学原理的镜中影像,将视觉景象或镜中影像等同于事物本身,而中国传统绘画则强调更为完整、投入到观看行为中去的视觉全景。正如明王履在《华山图序》中所言:“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16)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708.“师心”即摈弃常法,“师目”即遵循目光之流,“师华山”即让目光之流接受事物本身的引导。西方透视画法往往停留于“师目”,而中国传统绘画将“师目”进一步延伸到“师华山”,更强调对事物本身的实写,而不只是对视网膜映像的复制。
美国学者高居翰指出,“中国人向来便不在户外作画”(17)高居翰.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2009:23.,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人“师法自然”,只因中国画不胶着于视点,依据事物本身的需要而不断地远望近观,这就不像西方透视画法那样有一定法可依,而只能“目识心记”“不可定取”。当然,如何能够将这些“不可定取”的各种视觉景象,按照事物本身的要求,在画面中组织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西方透视画法虽然也会在视点上精心选择,但一旦选定,往往会以远写远、以近写近,有光学成像的定法可依。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来说,因为视觉景象分散,事物本身的统一性就只能“主乎意”,正如郭熙所言:“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18)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633.虽“主乎意”,却不是一任性情的现代“写意”,而是“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19)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642.,即合于事物本身。
总之,中国传统绘画的写实意在于超越视觉景象直指事物本身,不在视点问题上胶柱鼓瑟,也不因视觉中介而守指忘月,正如宗白华所说“这是全面的客观的看法”(20)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11.。
二、“叩其两端”“允执其中”:中国传统绘画美学对视觉主观性的超越
事物本身存在于视觉景象之外,但又要通过视觉景象显现,这必然使之带有人的主观印迹。从视觉方面而言,任何一个视觉景象都不可能穷尽事物本身,事物本身总在召唤着视觉变换视点,通过不断超越单个视觉景象的方式走向自身,保证自身的客观普遍性。
对视觉局限性具有清醒认识的中国传统哲学,在视点问题上更是强调要顺应事物本身的召唤,不封闭于单一视点的视觉景象中,善于在视点的变换中、在各个视觉景象之间的侧面关系中显现事物本身的客观普遍性。
孔子云:“叩其两端”(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0.“允执其中”(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3.。“叩其两端”,即不执于一端,“允执其中”不是简单地找出“中点”,正如孟子所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如果把“中”仅仅理解为“中点”,“执中”就仍然是执于一点,同样会“举一而废百”。这里最关键的是“权”,按朱熹的解释,“权,秤锤也,所以称物之轻重而取中也”。(2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7.秤锤的作用在于保持秤杆的平衡,保持平衡即为“取中”,但“中”并非一固定之点,需要根据所称之物的轻重而变动。“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厅非中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中”需要根据事物的整体关系来确定,如果“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叩其两端”,作为哲学隐喻,就是要在对两点的权衡中超越任何一点,不局限于任何一点。执于一点易,在两点的侧面关系中超越任何一点难,因而程子认为“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7.。
孔子的“执中”思想被朱熹作为“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即《中庸》。子思认为舜之治就在于能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不自用而取诸人也”,(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权衡各家意见,方能善政。孟子据此批评了杨子“取为我”和墨子“取为他”的观点,虽立场不同,却都偏执于一端。他认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6.”的做法,就其视觉意义而言,就是要在视点的不断变换中,超越单一视点之所见,以显物象之真。
那么,人是否能够超越单一视点之所见、特别是一己之所见呢?《庄子·秋水篇》中有一段著名的“濠梁之辩”: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28)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606~607.
惠子认为,庄子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视点而知道鱼的快乐,而庄子认为惠子此言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你又不是我,怎么就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既然你能知道我不知道鱼之乐,即使在后来的辩解中也至少知道我非鱼,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知道鱼之乐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惠子的观点自然难以站得住脚。这样,庄子以近乎诡辩的方式反证了人是可以超越自身立场的,至少惠子你不能证明人不能超越自身立场嘛。尽管人只能立于“我”之一端,但同样可以“叩其两端”。
“叩其两端”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直观体现,就是“路看两头”(29)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96.,如果依单一视点的透视法来画,路只需看一头就行,近宽远窄,而如果看两头,则既要考虑从这头看到的景象,又要考虑从那头看到的景象,透视法就不足取了,因而中国画中的路往往是远近同样宽窄的。这不是因为不懂透视法,而是其写实观念的不同所致,中国画更强调超越单一视点直指事物本身,在多个视觉景象的侧面关系中求取物象之真。董其昌画树“须四面取之”(30)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141.,王维要求“石看三面”(31)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96.,郭熙认为“山有三远”(32)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639.,均有此意,只有通过“目所绸缪”,对事物做多角度的观察,才能更全面客观地表现事物本身。对此,中国画史上曾经还有过一段著名的公案。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记载:
李成画山上亭馆及塔楼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往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33)沈括.梦溪笔谈[M].长沙:岳麓书社,2004:121.
“仰画飞檐”就是采用“自下往上”的固定视点,所画只是单一视点之所见,沈括将这种画法讥之为“掀屋角”,认为李成不懂中国画法。其理由正在于事物本身并不封闭于某个单一视点之中,如果从东边的视点来看,则山之西边的景色为远景,按远近法理应画得更小,但如果从西边的视点来看,则山之东边的景色却变为了远景,应当画得更小才是。如果两个视点都固执于自身的视觉景象,这画就没法画了。
沈括的批评恰恰说明了中国画所要表现的乃是事物本身,而不是视觉景象。关于这一点,五代时荆浩在《笔法记》中说得更为明确,他对绘画中“屋小人大”“树高于山”的现象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认为这是“有形病”。如果从视觉景象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西方透视画法中可谓比比皆是。但中国画认为这只是偶然形成的视觉景象,而非事物本身,因而荆浩要求画家“须明物象之源”。所谓“物象之源”,即要从事物的视觉景象返回事物本身这一源头,站在事物本身的立场上描绘事物。针对“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的错误认识,荆浩认为,“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34)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605~607.“度物象而取其真”,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把它描绘成什么样子,不能因为视觉偏好而进行选择性地描绘(执华为实),更不能改变事物本身的样子(屋小人大、树高于山)。选择性地描绘或改变事物本身的样子,或许可以欺骗视觉(苟似可也),但所描绘的就不再是事物本身了(图真不可及也)。因此,“度物象而取其真”就是要超越视觉景象直指事物本身,这才是中国画的“写实”(“图真”)观念。
正是因为这样的写实观念,中国画不局限于“人站在一个固定地点看出去的主观景界”,而是要从多个视觉景象的侧面关系中求取物象之真,反对“近大远小”的滥用,强调“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的超视觉比例。需要强调的是,事物本身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它依然要通过视觉景象才能呈现,但又不局限于单个视觉景象,而是在多个视觉景象的侧面关系中呈现,这就需要在多个视觉景象之间“叩其两端”而“取其中”。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作为绘画写实的衡量标准的现成的事物本身,这就使得在多个视觉景象之间“取中”成了一种哲学智慧,而非机械复制。有了这一认识,再思张璪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35)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19.,才更能悟得其中三昧:只有“外师造化”,让视觉接受事物本身的召唤、引导,才能“中得心源”;同样,只有“中得心源”,运用哲学智慧,方能在多个视觉景象的侧面关系中超越视觉景象“外师造化”。宗炳讲绘画当以“应目会心为理”(36)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83.,一“应”字揭示出了事物本身对视觉的召唤,而画家在对这一召唤的回应中心有所会。
三、“以物观物”:从视觉之实到本体之真
为了克服视觉的局限性,超越“属我”的视觉景象,中国哲学进一步提出了“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的区分。北宋邵雍认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性者,万物之所以为万物也,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37)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2.只有“以物观物”“不立私意”(38)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66.“从天不从人”(39)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7.,方能尽物之性;反之,一任自我,遮蔽物性,则是“以我观物”。所谓“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40)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2.“因物”而不“任我”是中国哲学直指事物本身的基本思路。
那么,如何才能“因物”而不“任我”呢?邵雍提出了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反观”,即超越自我站到事物本身的立场中去,“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41)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49.“理”即物性,重物性即为“贵中”,所谓“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42)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4.。要做到从事物本身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事物本身之外的立场出发,就要“虚心”,进入无我境界,“虚心”方能“待物”“不我物,则能物物”(43)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2.。以物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我为衡量标准。正如同一弓,无力者以为弓强,有力者以为弓弱,就是“我物”;不以我力之有无来衡量弓之强弱,方能使“物各付物”,是为“物物”。在邵雍看来,观物就要“利物而无我”(44)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4.,我退物进,我进物退,因此,“我”只能“藏而用之”,犹如“道生天地万物而不自见”(45)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3.,如执着于“我”,则犹如“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则刃与物俱伤矣”(46)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69.。
二是“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47)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49.,不局限于我的视点,学会从他人视点观看,方能得物之真。这仍然是为了“因物”,由于观不可能脱离视觉而直达物,物只能通过视觉呈现,但视觉的“属我性”容易造成“我执”,引入他人视觉,既能利用视觉中介,又能消除“我执”。同样,我的视觉也能消除他人视觉的“他执”,将我的视觉和他人视觉都放回“物”的位置上,做到“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48)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49.,从而实现“以物观物”。而我之所以能从他人视点观看,保证他人视觉与我之视觉对物的同等有效性,乃是因为我之视觉与他人视觉均本于物(之所以有我之视觉与他之视觉,乃是因为物具有可从不同角度来观看的各个侧面),接受事物的召唤与引导,“人与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49)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2.。“我与人皆物”,才能不凌驾于物,接近物,与物相通,“不立私意”地去表现物。
“以物观物”即“不立私意”,人之用情,同样如此。西方文化重移情,先有一己之情,再移之于物,中国文化重“感”情,“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50)钟嵘.诗品译注[M].周振甫,译注.中华书局,1998:15.,情根于物,是“物情”。情之由来,在中国文化中与西方正好相反,先有情,然后才能移情于物;先有物,然后才能感物而生情。感物而生情,不是将一己之私情涂抹于物,而是“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发而中节者也”(51)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2.。人之有情而不任我,才能不“我物”而“物物”。与事物本身召唤视觉一样,情也是对事物召唤的回应,“应物”方能“中节”,符合事物本身。
从“以物观物”的立场出发,中国画强调“以形写形,以色貌色”(52)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583.,所写之形色并非视觉景象中的形色,而是事物本身之形色。明代徐渭认为,“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呴呴也。”(53)徐渭.徐渭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89.“本”为木之根,物之源,“相”从目从木,指以目接物,如果局限于视觉景象,即为“相色”,如果原物之源,乃为“本色”。绘画要“贱相色,贵本色”,就要超越视觉景象,“明物象之源”,正因如此,画中山水要比仅仅“以目接物”的视觉景象中的真山水更加真实。董其昌感慨:“昔人乃有以画为假山水,而以山水为真画,何颠倒见也!”(54)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四)[A].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2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511.王世贞在谈园林时说:“世之目真山巧者,曰似假。目假之浑成者,曰似真。”(55)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五十九)[A].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2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73.
中国画不停留于视觉景象,而是力求超越视觉景象直指事物本身,正如龚贤所说:“惟恐是画,是谓能画”(56)朱良志.南华十六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23.,这使得中国画没有定法可依,无法机械复制,因而更讲哲学智慧,也对画家提出了更高要求。元代绘画转向“写意”,并非现代所谓的一任性情,而只不过是更强调这一哲学智慧罢了。朱良志认为:“得出中国画发展到元代就进入‘表现’阶段的观点,是对文人画发展史的误解”,(57)朱良志.南画十六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31.文人画“不是画其相,而是显其性”(58)朱良志.南画十六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25.。但此“性”不只是朱良志所说的“生命真实”,这多少会给人以写主观之意的口舌,这里更重要的是物性之真。
“以物观物”“不立私意”“贵本色”,中国画所追求的是事物本身的真实,即本体之真,它不同于视觉之实。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说西方古典绘画“写实”,也还是准确的,其对视网膜映像的复制就是写物的形色之实。但20世纪之初的中国学界,在实业救国的紧迫形势下,仓促地认“实”为“真”,如康有为在比较西方古典绘画与中国明代绘画时就说“彼则求真,我求不真”(59)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7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78.,这就不准确了。在中国画中,“真”并不等于“实”,相反,太“实”或太“虚”,都是缺点,“虚实相生,乃得画理”(60)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12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539.。就山水画而言,“山实虚之以烟霭,山虚实之以亭台”(61)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807.,做到实处不窒,虚中有物。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画具有强烈的求真意志,对于中国画来说,“真”高于“实”,“实”只是呈现于视觉景象中的形色,而“真”超越视觉景象直指物性,即物之为物的根本。荆浩认为“木之生,为受其性”(62)荆浩.笔法记[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4.,松、柏各有其性,而绘画能尽物之性,方可谓“图真”。清代石涛强调绘画“其在气”(63)石涛题自画松[A].玉几山房画外录·卷上[M].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民国九年:8.,其独创“一画”论,正是要究“众有之本,万象之根”(64)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147.。西方写实画法强调明暗远近,而石涛认为视觉景象中的明暗远近并非事物之本,在他看来,“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事物的“明暗高低远近”只是天地一气的派生,天地一气才是事物之根本,“一画”之法正是为表现作为事物之根本的天地一气而立,所谓“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65)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147.。
总之,中国传统绘画美学强调超越视觉景象的“属我性”,将人放回世间之物的本然状态,涤除主观之意,虚而待物,不将一己之意凌驾于物之上,保持物之所以为物的本然状态,在“以物观物”中追求“无我之境”,正如王国维所言:“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66)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这是绘画的最高境界,其所呈现的不是一己之见的视觉之实,而是物之为物、物之所由的本体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