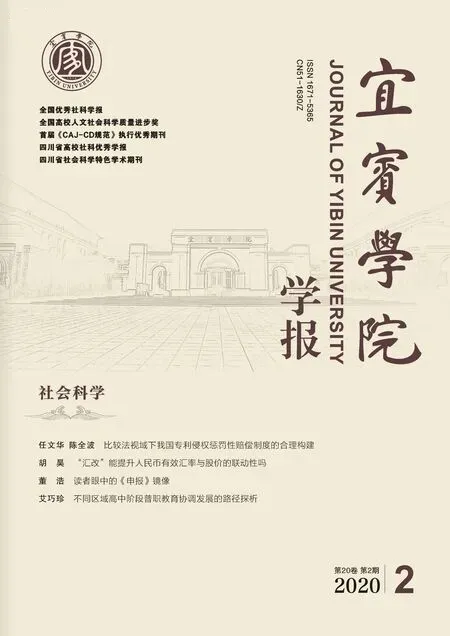读者眼中的《申报》镜像
——一个媒介史书写方式的转换尝试
董 浩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报刊)史书写在经历了现代化范式、革命范式等主要书写范式之后,逐渐开始反思这些书写范式的不足,不仅从其他学科引介许多的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如计量史学、口述史、新史学等,而且受其启发,有发展出自己本学科新闻(报刊)史书写范式之势头,如新报刊史。这种报刊史书写方式的独特之处,如黄旦所言,新报刊史是“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自己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1]5等。而且其基于对以往新闻史研究范式不足的反思认为,报刊史研究要实现范式的转变,则需要首先打破“路径依赖”,即跳脱出现有的、主流的、报刊史书写叙述范式的桎梏,以批判的眼光思考、质询现有的“陈腐老旧”的书写范式,以期发现和另辟研究新路径。换言之,即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现有的报刊史研究范式,如现代化范式、革命范式等,虽然有助于勘定、绘制、构建、奠定了报刊史——包括的知识脉络、范围、边界等在内的——最初的“知识版图”与“知识谱系”。但这些范式因自身的一些原因,有意无意地遮蔽或消解了报刊史书写的丰富多彩,使得报刊史的书写常常被反复的、同质性的“操弄”。历史的面貌本来应该是一个丰富的、多向度的,由不同“主体”建构的产物。由于“主体”的多样,所以即使是对同一个历史事物的认识,不同的主体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报刊史研究也应该是多个维度的、多个主体的呈现,应该是多样色彩,甚至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一种“存在”,这也许才是报刊史的“本真”、多彩。这也许就是新闻传播学科一些学者极力提倡新报刊史书写的缘由之所在。而本文从读者的视角对《申报》的媒介形象所进行的考察,就是在这种范式下所进行的一个尝试。
目前,虽然关于《申报》的媒介形象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大多是依循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范式,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传播者的《申报》的相关研究,包括《申报》的经营管理、改革、编辑等;二是对于《申报》的历任掌控者的研究,包括对美查、席子佩、史量才等的研究,尤其最后一任掌控者史量才的研究更多;三是《申报》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的视角等的相关研究,要么多是偏重于宏大叙事,要么多是从传播者视角来切入进行研究,而相对缺乏采取新的视角对《申报》进行的探照,以发现一个别样的《申报》或像葛兆光所讲的“一般知识与思想”。其实,也许在读者眼中谁是《申报》的主人,并没有那么重要。也许在读者眼中,无论人事更替、世事变幻,《申报》还是《申报》。
故为了丰富人们对于《申报》的媒介形象的认识,本文将尝试着运用新报刊史、阅读史等方法,捡拾各种散见于日记、自传、书信、报刊读者来信等文本中不同读者关于《申报》的“记忆碎片”,以期能够拼贴、描摹、刻画出一个更加立体、全面、丰富、多维的《申报》形象,进而更好地认识与理解《申报》。而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修正以往的新闻史研究对《申报》庞大、异质的读者群有意无意的忽视、遗漏。在《申报》的研究中,虽然“读者群体”是一个不可忽视和越过的研究“主体”,但由于做以往报刊的读者研究有着诸多的不便与困难①,因此,关于《申报》的读者研究相对薄弱。不过,近年来,随着新报刊史、阅读史等新的史学书写方式的出现以及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与丰富,为从读者视角研究新闻史提供了一定的可资借鉴的“借镜”。故为了更好地开展本研究,本文拟将《申报》众多而异质的读者分为普通大众、士绅读者、新生代“青年读者”、清季与国民党统治者等“主体”来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文将尝试着运用新报刊史等方法,通过捡拾各种散见于日记、自传、书信、报刊读者来信等文本中不同读者(普通大众、士绅读者、新生代青年读者、清季与国民党统治者)关于《申报》的“记忆碎片”,以期能够描摹、刻画出一个更加立体、全面、丰富的《申报》形象,进而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申报》。
一、 普通大众:“代表所有报纸”的“申报纸”与被信以为真的“奇谈”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一直以来,《申报》都被塑造为一种“高大伟岸”而又与读者有着“距离感”“疏离感”的形象。但事实上,可能在不同的读者眼中,《申报》有着不同的形象。清末民初之际,对于当时还以邸报来类比理解西方传入的新闻纸的人们来讲,《申报》算得上当时的一种新媒体了。故其常常被当作一种可以“代表所有报纸”的“申报纸”,甚至其传播一些在如今看来是“奇谈怪论”的言说也会被普通民众信以为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一)可以代表“所有的报纸”的“申报纸”
《申报》在普通大众眼中的媒介形象,是一种可以“代表所有报纸”的形象。其也被一些普通大众统称为“申报纸”。正如徐铸成所言:“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2]8。关于民间把申报纸等同于报纸的习惯,曹聚仁老先生也曾这样说过:“我们乡间,凡是报纸,都叫做‘申报纸’,一个专有名词当作普通名词用,可见这家报纸的权威”[3]109。“申”是因春申君黄歇而得名的上海的简称,应属专用词[2]8,但是为什么报纸会被等同于“申报”呢?
据考证,这是因为《申报》的创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因而被读者尊称为“老申报”。具体而言,即在《申报》创办前出版的报纸,基本上大都是外报的中文版,内容多译自外报,读者只限于买办阶层和“高等华人”。[2]9而《申报》在创刊后,其内容面向普通大众,“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每句及人名地名尽行标明,庶几稍识字者便于解释”[4]。为了维护、自证其“中国血统”,《申报》以古代“采风”之说来比附新报,称其为“(邸报)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5]。纯正的中国血统——现代版的“太史采风”,为其带来的是自身的合法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接受。当然,这也是当时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新闻纸实现中国本土化的最佳方法与路径。
尽管《申报》被当时的士绅所鄙夷,为“记载猥琐、语多无稽、不学无术、无关宏旨”[6],但是《申报》的出现,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却是一种“解放”。在报纸出现之前,人们了解社会的动态,主要是通过乡绅这一媒介的中介。当然也有其他的通道来获取来自远方的消息,但是这些渠道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奏折、邸抄与书信,再加上流言网络,便是中国前现代传播体系的主要构成。[7]64在众多的选择中,前三项是属于乡绅读书人的,只有最后一项——流言、小道消息——是普通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作为对于由政府(乡绅)控制的信息系统的重要补充的“小道消息”,沿着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流通”,“是当时中国村民(更不必说城里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的”[8]42信息源。但是,最后确认真实与否或者是最终的解释权还是需要乡绅来完成。乡绅对于关于社会、知识具有最终的解释权,但在报纸出现之后,乡绅的这种对于知识、消息的垄断权就被无情地打破了。故《申报》常常被普通大众认为是一种可以代表“所有的报纸”的“申报纸”,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二)被普通民众信以为真的《申报》“奇闻怪谈”
《申报》在带来“信息获取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信息真伪”的判断问题。而当时的普通民众由于长期世代处于“信息真空”状态、对士绅的信息依赖,以及小道消息为普通民众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的信息生态环境下,普通民众对《申报》所传播的信息深信不疑,即使是“一切狐怪异闻”“稀奇怪异”之事[9]19。《申报》早期为了打开销路,普通民众是其重要的目标受众,奇闻异事则成为其报道的重要选题。其在《本馆自述》中也讲到:“网罗轶事,采访奇闻,论可解顿如听说诗之鼎,言足以志恍,师作史之迁。”[10]
《申报》传播的“奇闻异事”——其实是《申报》所呈现的“拟态环境”被普通民众当作“现实世界”的真实而被认知。孙玉生老先生在回忆其童年时所阅《申报》日记中这样写道:“余幼时,阅同治间老《申报》,忆有一事,甚为可异……报中载有省县地址,商人与宰之姓名,当非向壁虚造”[11]36。无独有偶,著名学者缪荃孙在写给友人汪康年的信中,也回忆到早年阅读《申报》的轶事:“同治年《申报》有一则云,洋行中畜一犬,无故乱吠,人问其故,有知之者曰: 无他,止( 只) 是吃洋屎太多耳”[12]3057。正如周树人所言:“他不要看新闻,却仍是信托它,凡是有什么事情,只要是已见于《申报》,那么这也就一定是不会假的了”[13]543-544。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新闻纸这个新生事物的初步接受过程中的“试探性认知”。虽然,在今人看来可能有失偏颇。
二、 士绅观《申报》:从认为是“锁闻屑谈”到现实转向的“急先锋”
《申报》的创刊意味着“第一次形成了一张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2]9。《申报》的出现不仅对于普通的大众读者具有现实的意义,对于士绅读者同样具有极大的影响。简言之,即使得士绅阶层通过报纸实现自我以及这个阶层的现实转向:报纸促使士绅撤离由经史子集填充的“前人世界”、超越“周遭世界”的限制,建构了一个新人新世界。正如卞冬磊所言,“1872年创办的《申报》,逐渐进入、重构了这个古老的传播体系,成为读书人依仗的新的信息来源。这一新式媒介,将人们带入更为广阔、确定的现实世界,扩大了人们对同时代人的了解”[7]64。这不单单是媒介技术的发展,更是作为一个新的“变量”,在注入旧的落伍的社会信息系统后,所引发的社会系统的连锁反应。
清季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加强皇权,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大兴“文字狱”等在内的举措,限制甚至是禁止汉族士大夫参政、议政。这就导致清季乾嘉朴学或称之为考据学兴盛一时。因文字狱打击,文人动辄得咎,士绅读书人和古代作者的“隔空对话”——可以有效地规避现实的“政治红线”,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只有也只能沉浸在前人的世界。因“彼时社会以帖括为唯一学问”,那么,对于理解士绅读书人最初对《申报》的“不屑”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报纸所载亦多琐碎支离之记事,故双方俞无接近之机会”。[14]129但为何后来许多士绅读书人还要阅读被认为是“锁闻屑谈”、不受文人待见的《申报》呢?这十分值得玩味。
近代中国国家命运多舛,战争不断,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系统是一个封闭性的“T”型的传播体系:“在统治阶层内横向流动的水平流程”和由统治权力“流向被统治阶层,即自上而下的单向垂直流程”[15]20,在此时已经不能满足士绅们的信息需求。而报刊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体制外的信息通道重构了传统的信息传播系统,或者说至少在当时使帝国原有的“T”型的信息传播系统演化、过渡为“工”型信息传播系统,那多出的底下一“横”就是由报刊构造的新信息通道。发生于1883年至1884年的中法战争,“由于《申报》和香港的中文报纸的存在使这场发生在越南的战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公共的战争”。而且现在更加奇妙的是,“朝廷自己也成了读者群的一分子,只能够在《申报》和其他中西文报刊中读到局势的进展”[16]41-42。现实迫切的信息需求,迫使士绅读书人接近《申报》等报纸。
1884年以后,“在战争结束后不再摘录《申报》的内容,因为它又重回昔日的品味”,但是发生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又使得上海新闻纸(《申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读书人的关系骤然的紧密起来。“见《申报》言海上战事”[17]487“据三月间《申报》云,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出使议和”[18]23,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新闻纸对战争的报道,使士绅读书人从沉于科举考试的“迷醉”中暂时跳脱出来,关心国家的兴亡,可以能够超越“周遭世界”的限制,实现对远方发生的事物的感知,建立了一个和“同时代人”的“共同世界”。
这些个体虽然可能更多的是互不相识,但他们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的担当意识在无形中促使他们形成了一个“以国家(天下)利益为中心的共同体”。他们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但是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命运。正如舒茨所言:“他我的身体固然不呈现出来,也就是不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直接性,但是我知道他和我共同存在,他的意识体验和我的意识体验一同前进着”[19]233-234。《申报》作为新的媒介,其功能不只是传播信息,更是作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重组了士绅的时空观念,也形塑、重构了人们的交往关系,加速了士绅跳脱“前人世界”转向现实世界的进程。
三、 “新生代”青年读者看《申报》:一种传播新知的媒介
从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来看,自西而来的报刊引进中国之后被寄予了太多的希望,简言之,我国报刊除了具有西方报刊的特性功能外,还承担着具有中国特殊国情的功能。“因此,中国的报章就被赋予了西方报刊所没有的、力挽狂澜的沉重感。这一角色定位决定了晚清报刊的整体面貌,其结果之一便是其内容远远超出新闻的范畴,还要承担提供时务、论述、西学知识体系的任务”[7]11。其中作为传播知识的媒介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早期的中国报纸,其形式和内容均是仿照“书本”的样式。像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在其早期还是采取书本的样式,更别说像《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等更早的报纸了。
作为学问的报刊,是产生于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殊的报刊认识论。学界对于此的认知和讨论,除了有“报刊可以起到新知的作用”,还有另一认识:“报刊本身就是一种新知”。[20]139以报刊为媒介传播知识在中国的报纸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主要是在第一种意义上的讨论。在中国近代报刊的读者中,也许(也应该是)《申报》是作为“传播新知的媒介”的典型代表。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早期《申报》在扩大其读者群的同时,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传播知识的效果。“《申报》文理不求高深,但欲浅显令各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能识字者即能阅,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习文墨,故自《申报》创设后,每店日费十余文可以有益众友徒,亦何乐而不为哉?”[21]《申报》的“无心之举”却出乎意料的产生 “传播知识”的客观效果。
其后,《申报》职业主体意识觉醒,开展了一系列主动向社会传播知识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行动。“《申报》副刊《常识》介绍科学和新知,吸引了无数青年人,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22]9。曾经是一名学徒的沈鸿通过《申报》副刊《常识》介绍的知识产生兴趣,经过努力成为一个有为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一名中科院院士。这是报刊扩大视野、传播知识,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例子。《申报》在1924年6月29日创办的《平民周刊》,也是为初识字的人服务的。正如陶行知在报上所言:我们希望这些同胞,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得些看报的快乐和做人的道理。[23]545
《申报》除了鼓励普通大众学习知识,还创办了许多的文化事业,传播知识。从1932年至1934年间先后创办了申报职工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等,扩大中华书局业务,出版大量图书,如“申报月刊丛书”《中国各省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上海名人辞典》等。[22]23通过这些文化事业的发展,《申报》在实现自身集团化的同时,也帮助了普通大众、读者获得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机会,帮助了许多渴望改变命运的普通人。李公朴这样评价史量才及《申报》所做的贡献,“史先生为国家为人类做事情,创办申报流动图书馆、补习学校等文化事业,处处为我们青年利益、国家前途设想……”[24]故在“新生代”青年读者看来,《申报》是一种“传播新知的媒介”。
四、 清季与国民党统治者眼中“爱恨交加”的《申报》镜像
具有78年历史的《申报》(1872—1949),历经(清)同治、光绪、宣统三代以及民国。只有有着漫长“生命年轮”的《申报》才能生长、演化出如此悠长的历史和生存智慧与经验。在近代报刊史上,探讨“有闻必录”的兴起往往可以追溯到《申报》,它“也许是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报纸”。操瑞青在《建构报刊合法性:有闻必录兴起的另一种认识——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谈起》中认为:早期“有闻必录”不仅是规避言责的策略,它还发挥了另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建构报刊话语在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与《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媒体属性有关。[25]99在《申报》的生存智慧与经验“结晶”中,“有闻必录”是其吸引读者、迅速发展崛起,也是其奠定历史地位的一大“秘诀”。
《申报》的读者不是单一的或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因此,《申报》会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主题,不断调整其目标读者群结构、构成比例。具体而言,《申报》特定的读者,大致可以分为统治者和普通大众,简而言之,就是《申报》不断调整其自身与“特定读者”—— 统治者和普通大众的关系。《申报》与普通大众的关系比较稳定,而《申报》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则“分分合合”“爱恨交织”。
“今日之新闻,即明日之历史”[26]。由于《申报》秉持“有闻必录”的理念来从事新闻业,因而,在其发展史上与统治者的合谋、联盟以及冲突、博弈不断,分分合合也就不足为奇。统治者对《申报》对其的报道可谓是“爱恨交加”。
《申报》创刊后,逐步涉及官场纷争。并由此其与统治者的“爱恨情仇”纠缠交织在一起,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1873 年,因杨月楼案,而与上海地方官员交恶,并引发江浙官员对报纸的痛恨;1874 年,报道左宗棠在新疆借款,引起左宗棠大怒。斥其为:“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资之”“干涉时政”“拉杂亵语”“纤人之谈”[27]517-518;1875 年,报道浙江巡抚派员赴粤购买军火,浙抚大为不满,特派人指责《申报》馆,认为《申报》馆泄露军情机密[28]91;1878 年,又因刊发《星使驻英近事》而引发与郭嵩焘的一段官司等事件。《申报》与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博弈不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胶着”的状态,与《申报》的“有闻必录”的理念密不可分。
“官场与报界的冲突反而促成了政府各级官员对新闻纸的正确认知。‘有闻必录’作为《申报》采集新闻的重要原则,亦逐渐为官场所接受。官员们甚至发现了新闻纸的其他功能”[29]116。了解夷情、国家政治动态等都离不开新闻纸——这一新的信息传播管道。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30]42即使是对《申报》对其自身的报道不满的统治者,但同时又对《申报》有着复杂矛盾的、不可名状的认可,或者由于适应这种新媒介,而带来一种“运筹帷幄”的满足感。左宗棠“因西北战事的报道而与《申报》势同水火,将报道的失实等同于公造谣言。在他担任两江总督后,对《申报》“有闻必录”的习惯逐渐适应,恶感渐减”。1878年《申报》在报道俄罗斯潜占黑龙江边界的事件有对左宗棠的肯定,以及《申报》对左宗棠的奏折《严禁鸦片先加洋药土烟税厘》的刊登等使其逐步适应了新媒介,认识到政务的适度公开可在某种程度上杜绝谣言的产生。[29]116与左宗棠不同的是,郭嵩焘不仅在驻英法期间,通过阅读专门从国内邮递的《申报》了解国内动态,并且,还在“退隐乡下的十多年间,仍然借助于《申报》,关注朝政和民生,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读报心得[31]64。如他在1880年(光绪六年)三月初十日的日记,抄录了“载户部奏筹备饷需十条”、1881年(光绪七年)写下读“星变陈言四条”后感、1888年(光绪十四年)的日记留下“《申报》载船政局委员董紫珊太守毓琦治河二策,甚奇而确”[32]30,188,787这样的笔墨。可见《申报》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矛盾共同体”,一方面对其有些言论大为不满;另一方面,《申报》又正在逐步成长为统治者须臾难离的、了解国家政治动态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信息管道。
其后,在《申报》发展史上,统治者对《申报》“又爱又恨”的矛盾感更加强烈的纠缠在一起。但《申报》与统治者经过不断调试彼此的关系,逐步加强了对彼此的认知和适应。《申报》一方面植根民间,另一方面亦努力寻求官员对其地位的认同,在夹缝中谋求生存”[29]117。统治者也学会了利用媒介来宣传,引导舆论,塑造政治形象以及获取政治资本等。有学者认为:1879年中国官场上“清流”的崛起和《申报》的报道密不可分,这两者隐然间“互为犄角”:“《申报》议政,是出于商业需要,目的是赢得政府官员读者群;‘清流 ’看《申报》,是出于政治需要,目的是能够跟上官场上的洋务话题”,其实质上是一种“合谋”:体制内外的两种言路互动互利,最后实现双赢。由《申报》与“清流”之间的这种“合谋”关系,可以得知:“清流”人物本身(不仅)成为《申报》读者[33]75,而且还学会利用《申报》来适应官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制造舆论。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幻,《申报》进入到史量才经营时期,但其“有闻必录”的新闻理念并没有因经营者的更替而动摇,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史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22]170。《申报》的“报格”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独立自主”“站在为人民说话”的立场上。在史量才刚刚接手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袁世凯的“帝制闹剧”,《申报》连续发表多篇时评予以批评,当自称“臣记者”的薛大可来贿赂《申报》时,被《申报》断然拒绝,足可见《申报》之独立报格。《申报》也因而为统治者所不容或者是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异类”。
在面对日本侵华的民族危亡时刻,《申报》坚持民族大义,不顾国民党的“不准刊登抗日”的禁令,依然宣传、动员人民抗日。创刊于1931年9月的《申报·读者通讯》专栏,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地反映民众的意见,自觉地代表民众,反映并引导抗日舆论,担负起“人民喉舌”的角色。这与其“有闻必录”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统治,史量才毫不屈服,坚持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丑陋嘴脸”,其中最著名的是史量才与蒋介石之间“充满火药味”的对话“传说”。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34]24《申报》的独立报格,使得它成为民国统治者眼中的“不识时务者”,又被认为是“可恶至极”的、专门与政府作对的“反叛者”。
结语
故综上可知,通过转换研究《申报》的书写范式,即将报刊的读者转变为读者的报刊这一视角之后,确实可以发现一些以往新闻史、媒介史研究所忽视与遮蔽的面向。概言之,即《申报》在不同的读者眼中有着不同的形象。详而言之,即在普通大众看来,《申报》的形象是可以代表“所有的报纸”的“申报纸”镜像,甚至是“奇闻怪谈”也会被普通民众信以为真;而士绅所“观”到的《申报》镜像,经历了一个由“锁闻屑谈”到“现实转向”的“急先锋”的过程;“新生代”青年读者“看”《申报》,更多地把它作为“传播新知的媒介”;清季与国民党统治者眼中的《申报》镜像则是一个“爱恨交加”的形象。当然,这种分类可能存在界限、边界的模糊,甚至是交叉、重叠等问题。不过,本文想强调的是,尽管采取这种新闻史书写范式来书写新闻史,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只要我们大胆地去探索与尝试,即变换认识视角、尺度、范式之后,一定可以探寻出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别开生面的新闻史书写路径。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要勇于转变、更新自己的认识论。
注 释:
①除了研究范式的“遮蔽”外,还有着诸多其他的困难:一是年代久远的报纸读者早已故去,无法进行访谈;二是史料留存的困难与残缺不全,导致关于读者的史料相对“奇缺”;三由于读者的异质性、混杂性,导致读者分类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