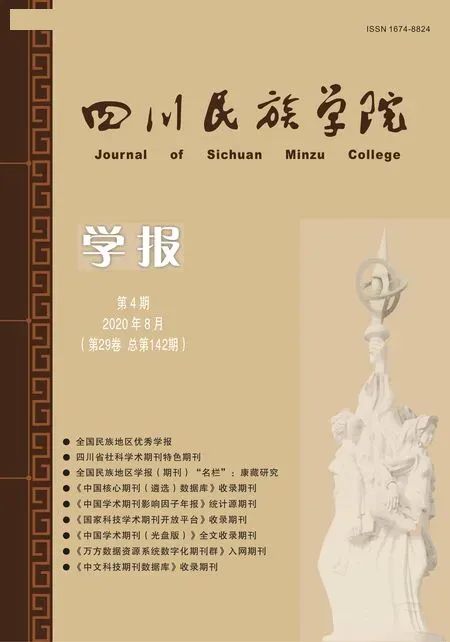与儒同行:日本古学派的形成
王智汪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
古学派是日本江户时代儒学派别之一。古学者原多为朱子学追随者,后怀疑朱子学,认为与孔子、孟子原意不同,而倡古学,呼吁不依赖后人的注疏,而从孔孟的原著中直接探索儒学的真意。古学派因其创始人荻生徂徕立社名为萱园,又被称为萱园学派。古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为近世唯物主义哲学的传播作了充足的先期准备工作,而且其宣扬汉文学,提倡经史考证,对后世学术界和思想界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对后来的日本思想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古学派的先驱——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1622-1685年)名高与,初名义矩,幼名佐太郎,字子敬,号素行,别号隐山或因山,通称甚五右卫门。公元1622年,山鹿素行出生于会津的一个浪人家庭。六岁从塾师学书计,九岁入林罗山门,时称文三郎,十一岁为人讲《小学》《论语》《贞观政要》等书。山鹿素行是最早从宋儒之学转向古学的学者,是日本近世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主张回归到古典中去,开启了复古主义的先河,为古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最初师从日本著名的朱子学家林罗山学习儒学,但后来又学习了兵法、神道,钻研老庄、佛法。他在《谪居残笔》中这样记述自己的思想历程:“余自幼年至壮年,专攻程子、朱子之学理,中年爱好老子、庄子,玄虚之说而信以为本。”[1]129山鹿素行终于想要“直接阅览周公孔子之书,以此作为规范”来进行钻研,他认为“应详文字训诂,虚心平气,直以圣人之言体穷日用之间。”[1]130因而可以说正是“这些各种思想体系的相互矛盾和对立,驱使他转向了古学。”[2]山鹿素行的古学思想突出特点是他反对理学那些看起来是“雅尚玄远”,但实际上无用的主张。山鹿素行认为:“大凡为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效命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3]32他反对朱子学最高本体“理”和“气”论,认为朱子学的“理”论和为实现这一“理”论所必需的“人人合一、持敬守静”等观念和行为,一般人是难以操作的,也使人产生玄虚不实的困惑。并且对朱子学“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划分表示了怀疑。他肯定人欲的正当性,“人物之情欲,各不得已也。……先儒以无欲论之,其差谬甚矣。”[3]216
这里,除了“周孔之道”以外,素行几乎不承认还有谁是“道统”的继承者。因为迄于周孔,所谓“道”应该是“日用当行”之道,而且这种“道”对“性心意情志气思虑”等也从未有过宋儒及朱子学似的“强分”。真正的圣人之道,乃是不离“人情”的日常实践之道,“道”而绝非反人情的禁欲主义和漫无边际的形而上思辨[4]。山鹿素行这种否定朱子学并进一步否定儒学“道统”的观点,显然与幕府的观点相左,所以《圣教要录》刊行后第二年,素行这里的“道不可罪”中的“道”有点类似于朱熹的“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5]的“理”,但二者性质是截然相反的。朱子的“理”是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而山鹿素行的“理”是“圣人有情”中的“理”:“圣人亦人也,尤有人情之欲。”[3]364
二、古学派的发展——伊藤仁斋
伊藤仁斋(1627-1705年),名维贞,后改名维祯,字源助,号仁斋,初号敬斋,又号古义堂。他私谥古学,因悟到朱子学敬义观点之非,才改为仁斋。他受张载、罗顺奄、吴苏原的影响很深,从而形成了古学派独特的思想。仁斋11岁开始读《大学》,19岁便能做汉诗,自称他是继承宋代理学之学,先后著有《心学原论》《性善论》《太极论》等。37岁以后开始对孔孟程朱儒学发生怀疑,思考多年后略得头绪。于是开始授徒,草定《论古孟议》和《中庸发挥》等书。46岁那年,京都失火,延及他的学堂,仁斋携《古义》书一套短衣赤身而逃出,后侨居京都大恩寺,几日不食,生活相当困难,但他仍能好学不厌,并爱与百姓一起劳动。早年,他服膺朱子,苦苦追求“格物致知”的生活哲理,“格物致知”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取得知识。他日夜苦读程朱遗书,还依朱子静坐法静坐,在心灵深处“进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人生思考,也没什么收获”,结果差点精神错乱,其过程与王阳明的经历差堪相似(1)王阳明要实践一下怎么做到朱熹说的格物穷理。于是一连七天静坐在他办的书院里观察(就算“格”)竹子,想悟出竹子的道理。他废寝忘食、目不转睛地看着、想着,一直坐得支撑不住,病倒了,也始终没有体会出竹子的道理来。。所以,如果不在人伦日用中实践道德,都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还很危险。
宽政五年(1665年),仁斋曾致书当时有名的官方大学者安东省奄(2)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想通过他来拜明的遗民朱舜水为师,后因种种原因而未果。在学术上,伊藤仁斋主张应该回归古典,从《论语》《孟子》寻求真正的古义,因此他的学问被称作“古义学”,古义学派是整个古学派的一个重要支柱。因伊藤仁斋生于京都近卫之南、崛河之东街,故古义学又称崛川学派;又因所居古义堂,以此也称古义堂学派。古义学派后经由其弟子伊藤东涯、并河天民、中江崛山等发展壮大。
仁斋在理论上所作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天地一大活物”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天地所以为一大活物,就在于宇宙充满了元气。这种元气在时间上是无限存在的,它既无生又无死:“斯气也既无所生,亦无所不生,万古独立,颠扑不破,岂容以虚无目之邪?”[6]215而天地一大“活物”,包含着元气万古不灭和是万物本原的内容,元气是宇宙最后的本原,如果在气之上再去求所谓本原,显得很荒谬。宇宙怎么起源的,“天道”也就无可道了,唯“人道”可道,仁斋说:“凡圣人所谓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至于天道,圣人所罕言,而子贡不可得闻之所以也,道即人道,而非天道,孔子罕言天道”,仁斋的“道”限制在“人道”的范围之中,“人外无道,道外无人”[7]46。在哪里寻找这种“人道”呢,仁斋认为唯有在圣人的作品《论语》《孟子》两书之中。其中,《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论语一书为万世道学之规矩准则,以为道至乎此而尽矣,学至乎此而极矣”,“若使孔孟复生于今世,其所说所行不可过《语》《孟》二书,则舍《语》《孟》二书而其何以能之,”[6]64“天下之理,到《语》《孟》二书而尽矣,无可复加焉,勿疑。”[6]77仁斋非常推崇《论语》的作用,“若五谷之可常食,《论语》之于道,乃食中之嘉谷也,施之四海而有准,传之万世而无弊”[6]77,他还认为《孟子》则是对《论语》的注疏,要想透彻全面地理解《论语》,就需要认真地领会《孟子》的含义。因为“《孟子》之书为万世启孔门之关钥也。”[6]79仁斋进一步说:“《孟子》之书,又亚《论语》,而发明孔子之旨者也。”[6]78
仁斋死后,他的儿子伊藤东涯继承了他的思想和家学。伊藤东涯(1670-1736年)生于宽文十年,卒于元文元年,名长撒,字原藏,号东涯,又号糙糙斋,私谥绍述,为仁斋长子,他为人谨慎、恭良、勤俭,胸怀宽广。虽口才不好,讷讷似不能言,但他满腹经纶,儒学造诣很深,为世人所敬仰。伊藤东涯终生未仕,一生在家讲学,学徒众多,在当时影响很大。伊藤东涯的哲学成就很高,忠实地继承了其父仁斋的家学思想,但又并没囿于其父思想的范围,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创新,东涯不但认真地继承了仁斋的衣钵,系统地整理校订了其父的遗书,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使得古学派的思想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古学派的成熟——荻生徂徕
荻生徂徕在其复古主张中偏重于对古文辞学的研究,主张使用古文辞的解读方法来直接把握古人的原意,以六经为据,以“古文辞”的解读方法返归中国儒学古典,到中国唐虞三代的先王之中去真正理解“圣人之道”,探求儒学真谛。为什么要回到原典中去?因为用宋儒的言辞是无法理解先王之道。他认为人类的语言在历史中是会发生变迁的,现代的语言与古代的语言是不同的,应该直接去阅读唐人古文,使用古人的语言(唐话)(3)江户时代,日本的“唐话学”(“唐话”即当时的汉语)发展很快,学习及研究汉语的人甚多,出现了一大批汉语辞书及读本、课本。这些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俗语、方言等情况,乃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资料。去理解经典的内涵,先王和圣人的作品意思是清晰的,根本无须借助后人比如朱子的解释。“世载言以迁,言载道以迁,道之不明,职是之由。”[8]221只有直接使用古文辞的解读方法直接去把握古人的思想原意,懂得了原意,才能“知古今之文辞所以殊,则古言可识,古义可明,而古圣人之道可得而言焉。”[9]251上能明理,下能知“道”,可谓懂得了古文辞之法。徂徕也不认同伊藤仁斋的仅从《论语》《孟子》中寻求古“道”的做法。他认为宋儒和仁斋一样都是用现代的语言去理解古典而不能切实把握古典的真正意义:“程朱诸公虽豪杰之士,而不识古文辞,朱熹昧乎古文辞,故其解古书,不能顺其词以究作者之心。”[9]252虽然仁斋提倡古义学,主张对经典进行重新定义,但徂徕认为仁斋也不懂得古文辞,依然是“以《孟子》解释《论语》,以今文解释古文”,这和宋儒犯的是同一性质的错误,那就是宋儒是背叛了圣人之道,而仁斋是没有把握住圣人之道。他说:“宋儒不奉文礼之教,而以心性为学,是名为仲尼之徒而实叛之也。”[10]122
因此,徂徕提出应当从更古老的《诗》《书》《礼》《易》《乐》《春秋》中去探求“道”,因为“学问之要,卑求诸辞与事,而不高求诸性命之微,议论之精。”[7]49他说:“六经其物也,《礼记》《论语》其义也。义必属诸物,而后道定焉。”[7]48就是说,六经所记述的历史事实是最基本的东西,而《礼记》《论语》不过是赋予这些历史事实以意义。对“道“的切入点应该从文字开始,而不是一开始便注重哲理的理解:“故学问之要,卑求诸辞与事,而不高求诸性命之微,议论之精 ”[9]512,“世载言以迁,言载道以迁,道之不明,职是由之”[9]256,“以今文视古文,以今言视古言,故其用心虽勤,卒未得古之道者。”[9]251荻生徂徕为了研究“道”而先从研究“道”的表达载体——语言开始,把语言作为认识“道”的最小载体。这种方法也使荻生徂徕发现了儒学经典中的“道”,这样理解的“道”已经不是伦理纲常的大“道”了。“道”就在人间,它就在万物存在的地方,是作为生活的规范而体现在社会组织之中。这里的“道”就是这样的实在与普通,而不是朱子那样把“道”看成是玄而又玄的脱离人间的价值评判的标准。
徂徕学以“物”批判朱子学的“理”,以“气”来打倒朱子学的“理”,从而建立起以安邦治国,经世致用为己任的古学。永田广志评价说:“徂徕学清算了过去的儒学,为日本儒学带来一股清新之气。”[10]141徂徕讲“物”而不太言“气”,“物”范畴是“气”范畴必然转化的结果。“物”是徂徕学立论的基础,“盖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教以物者,必有事焉。教以理者,言语详焉。”[9]200故“物”是实证性意义的客观存在,而不是“理”的虚无。徂徕学的核心则是阐明先王之道,朱子学的核心则是阐明天地间之“理”,朱子企图以普遍的“天理”来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诸多事象作出一贯的阐释,而徂徕认为“理”完全是主观的解释,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理无形,故无准,“天理说”只会导致人在主观泥塘中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先王孔子皆无是言,宋儒造之,无用之辨也,要之未免坚白之归耳。”[9]205
徂徕认为先王之道并不是关于对“理”的议论,而是具体、实在、个别的“物”的事理,“盖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教以物者,必有事事焉。教以理者,言语详焉。物者众理所聚也,而必从事焉者久之,乃心实之,何假言也。”[9]205“物”的内容就是包括了诗书礼乐等四教六艺在内的“礼”,“物者,教之条件者。古之人学以求成德于已,故教人者教以条件,学者亦以条件守之,如乡三物、射五物是也,盖六艺皆有之,成德之节度也;”[9]206“礼者道之名也,先王所制作四教六艺,是居其一,所谓经礼三百,威仪三千,是其物也。”[9]219
学问的对象就存在于这些客观外在的诗书礼乐等“物”当中,就在先王之道中,而不佞谓《诗》《书》辞也,《礼》《乐》事也,义存乎辞,礼在乎事,故学问之要,卑求诸辞与事,而不高求诸性命之微,议论之精,则有所凭据,可识后世纰缪所在也。“徂徕由于以古文辞为主体,因而提倡独特的所谓‘唯物论’”[10]151,“故欲知今者必通古,欲通古者必史,史必志,而后六经益明,六经明而圣人之道无古今,夫然后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论世,亦唯物。”[8]123在这种先王之物中,“礼”是极其重要的:孔门之教,致知在革物,物者先王之礼之物也。躬从事于礼,能使其物来恪,而知生;苟不从事于斯,而徒欲扩其是非之心以成其知,可谓不学无术矣,其究必至肆其私智以乱先王之典焉[9]157-158。而对于“物”,圣人只提示了原形而不加以议论,因为议论往往是因为怀疑,而怀疑导致争论,争论导致了歪曲和误解,圣人无限的大“道”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先王之道包罗万象,故圣人干脆不对“道”做任何议论和阐发,让后人自己去体会。而宋儒则妄想以有限的语言来描述圣人无限的大“道”,导致了先王之道中的“物与名离”,致使先王之道日益萎缩:“吁嗟,先王之道,降为儒家者流,斯有荀孟,则复有朱陆,朱陆不已,复树一党,益分益争,益繁益小,岂不悲乎。”[9]200
联系幕府后期的商业社会对“天理”的冲击,朱子学却无力应付这种现实落差,“日本儒学到了古学派的时候,日本成功地恢复了由孔子设想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本来特性,日本儒学始终认为古学派的最大作用是成功地适应现代化的逻辑。”[11]徂徕学突出点就是区分了天道与人道,即所谓“夫天不与人同伦,犹人不与禽兽同伦。”[9]255徂徕根本不讲“天道”,所以他的“道”只能是“先王之道”或“圣人之道”的“人道”。在荻生徂徕看来,“道”的本质与核心就在于治国平天下,在于其政治性。朱子强调修身对为政者的重要作用,而荻生徂徕则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君子修行成就犹如无瑕之玉,无关怀下民疾苦之意,不知治国之道,何益之有?也就是说,道德是道德,政治是政治,其间并无关联,政治优于道德,“一味而仁即一味不仁也。所谓仁而已矣,所谓无不仁云者,绝无其事也。仁即不仁者,信乎不谬也。”[12]820-821徂徕的弟子青陵则指出:“汲他国货财来自国者,霸道也,智之株式也;物多出于自国之土者,王道也,仁之株式也。”[12]69反映了流行于这一“王霸”理念,如果身逢“治世”而“移汤武之事于今日,可谓大谬也。”[12]88这样,徂徕学中“道”的内涵就不是朱子学中的“天道与性”,而转换成具体的礼乐刑政“物”的内容,因而它既不是自然之道,也不是理的外化,更不是来自人的天赋道德,因而它们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变革的,也就是说礼法制度是人为的,是可以改变的,“道”在徂徕的世界观中已不是普通的自然法则,而是人类的普遍规范。在道论上,徂徕肯定了天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定了天人之间的连续性,把“道”的范围仅仅限定为“人道”,即“圣人之道”“先王之道”,这种“道”的属性应当是“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物我相分”,“道”的重心是在形而下的“人道”方面,即“物”上,而不是在形而上的“治心”与“修身”的方面,徂徕学还原了原儒真实的“道”的本意。
——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