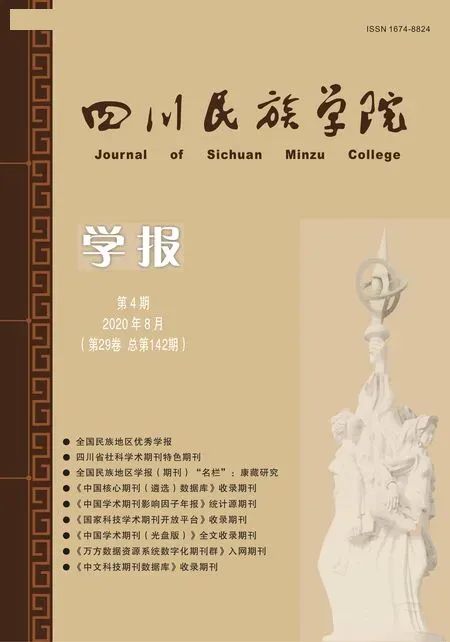庄学本藏彝走廊人文探访的回顾与价值
王才道
(塔里木大学,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庄学本(1909——1984)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上海《良友》《中华画报》等的特约摄影记者,怀着满腔热情进入藏彝走廊(当时称边地),开展了近10年的人文探访。以文字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了当时西部民族地区的面貌,并以专著、旅行日记、新闻和画展的方式向外传播。庄学本不仅是中国纪实摄影大师,也是藏彝走廊民族地区考察的先驱。
一、边疆危机与学科使命:探访藏彝走廊的背景
20世纪初,国外不断有探险家、学者等带着各种目的进入藏区“考察”。斯文·赫定于1901年前往藏北探险考察,被西藏地方政府阻拦。1907年斯文·赫定翻越克什米尔到达我国西藏西部,再由藏北南下抵达西藏腹地,对西藏部分山川地形绘制了地图。杨赫斯本在1902至1904年间被任命为英国的西藏特派员,1903至1904年,杨赫斯本与锡金政治专员约翰·克劳德·怀特一起带领英国探险队进入西藏,表面上是代表第三方解决锡金与西藏边界问题,而其真正目的是想在西藏建立英国的霸权地位。在20世纪初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将印度殖民地视为跳板不断干涉我国藏区问题,西南边疆冲突不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军占领,面临着边疆领土危机,“失掉东北而开发西北” 的思想成为一种社会共识[1]。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学界知识分子力图用自身专业为国家做出应有贡献,因而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民族学也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段民族学中国化思潮正风靡学术界,是中国民族学实际应用的探索阶段[2]。大量知识分子纷纷进入田野,考察中国的现实国情,同时期的吴泽霖深入西南边疆,撰写大量有关边疆的著作,提出多元边疆、边疆建设的原则、边疆的两种社会建设等有建设意义的观点[3]。林耀华1940年完成的一系列康藏地区的民族志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以藏区为对象的人类学家参与边政学思考的重要作品[4]。在此政治与学术背景的影响下,庄学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决心投身于西南腹地和边疆考察事业,萌发了西部步行摄影的大胆念头,计划用照片形象地把祖国西南边区民族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人,加强相互了解,以期开发西南地区。
二、职业任务与学科实践:藏彝走廊人文探访的经历
1934年,第一次西行机会缘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组织专使行署赴藏致祭。庄学本拟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上海《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专使行署进藏考察。到达成都后,因遭到入藏专使的拒绝,致使他的入藏计划落空,进而选择了考察素有“白地”之称的青海果洛藏区,为了旅行的需要在蒙藏委员会办了一张 “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护照。最终庄学本以西北专员的身份,从成都出发,经由理县、马尔康一路北上,进入阿坝草原地区,随后在川青两省交界的果洛进行了民族调查和摄影,再经由松潘、叠溪、茂县返回。在此其间,庄学本在阿坝地区无意间调停了当地土司与甘肃军阀的战争,在“白地”果洛的考察期间拍摄上千张照片,并撰写旅行日记在《良友》《中华画报》《申报》上连载,随后还出版了《羌戎考察记》,在南京举办摄影展。
第二次西行是在1935年-1938年间,此时庄学本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护送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行署摄影师。经由南京、西安、兰州、西宁、果洛、玉树等地,期间九世班禅大师在青海塔尔寺和甘肃拉卜楞寺等地举行了盛大法会。在法会期间,他利用旅途间歇在青海进行了四次短途考察,把贵德的蒙古族和藏族、海北的土族、大通与民和的撒拉族等少数民族的照片以及旅行中的见闻,以《西游记》《青海旅行记》等为题,连载于《良友》《申报》。除此之外,庄学本在出发前接受了短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培训,被委托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和文物标本的收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庄学本一心想回上海抗日,经由甘孜、炉霍、道孚、康定等地快速返回。在1938年1月回到成都,但此时上海已经沦陷,他有家不能回,欲弃笔从戎,也未能实现,进入彷徨无奈状态。
第三次西行是在1939年后,此时正值西康建省,需要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庄学本被聘为摄影师,次年为西康省政府参议顾问,继续从事摄影工作和民族考察。这一次西行是庄学本藏彝走廊人文探访的顶峰,考察的范围主要包括:丹巴、越西田坝、冕宁、西昌、昭觉、盐源、木里、永宁、泸沽湖、九龙、康定、理塘、巴塘、得荣、白松、义敦、巴安等地;探访了藏、彝、普米、苗、傈僳、纳西等少数民族;在此期间取得丰富成果,所著《西康彝族调查报告》由西康省政府支持出版,《新西康专号》《康藏猎奇记》《康藏民间故事》等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表,并且摄影作品汇集成“西康影展”,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市展出,吸引大约20万人参观。
三次川西边区人文探访,激起了庄学本探访“禁地”西藏的热情,1942年他应邀参加康藏贸易公司到了印度,拟随公司开辟的驮运路线进入西藏,但未能实现。庄学本在印度滞留的三年时间里,探访过新德里、孟买、大吉岭、噶伦堡等地,拍摄有一千多张反映印度民族风情的照片,并在1945年出版了《西竺剪影》画册。
三、使命担当与学科发展:藏彝走廊人文探访的价值
庄学本的川西边区考察意义重大,从学科与职业、国家与个人等不同视角,学者们对庄学本有不同的解读。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看,庄学本对藏彝走廊人文考察涉及范围广泛。如关于少数民族体质测量、民族地区地震的考察[5]、民族志摄影[6]、民族风俗的考察等[7],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留下丰富的知识遗产。而从庄学本的职业角度来看,尤其当国家使命、学科发展与个人兴趣爱好相结合时,有学者认为他是“被重塑的职业偶像”或“被想象的学术先驱”[8]。不论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角度还是摄影师的职业角度都存在客观价值,作为一名特殊时期的摄影记者其主要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明记录:藏彝走廊民族志的书写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经典话题,也是区域各民族文化的汇集之地,在民国时期部分地区还处于民国政府与土司统治双重管理之下。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而土司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走向终结[9]。残存的土司制度及土司制度下人民的生活状态即将成为过去,而藏彝走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除藏族外,还居住着彝族、羌族等民族,各民族文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是一个民族文化富集之地。庄学本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以全新的记录手段来书写了这一段文明,而正是作为“新媒体”的画报与作为新媒介的摄影术“相遇”, 促成了直观、纪实的视觉传播策略和摄影直观呈现藏彝走廊文明的方式[10]。在地方民族志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自1934年投身藏彝走廊民族考察事业,他在十年的时间里探访了今天的藏彝走廊和印度,著有《羌戎考察记》《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康藏猎奇记》《康藏民间故事》等作品。庄学本的摄影考察图片,几乎囊括了中国藏彝走廊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整个社会形态,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都以文字书写和摄影方式进行了最自然、最直接、最朴素的记录。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很高的视觉档案和调查报告,也为我们了解过去的藏彝走廊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二)前沿宣传:社会大众与藏彝走廊各民族相互认识的媒介
民国时期,藏彝走廊既位于藏文化的边缘地带,同时也处于汉文化的边缘。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交通不畅,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偏远落后之地,很难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此时,新的国家政权成立,新的对藏政策、新的生产技术等对藏彝走廊的各权贵和大众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生存信息;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外界来说,“边疆危机”促使人们急切想知道藏区的情况,庄学本在此时就充当了社会大众与藏彝走廊各民族相互认识的媒介。庄学本在人文探访过程中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深入藏彝走廊,志在团结各民族开发边疆。当他走遍藏彝走廊大多数地方,与当地土司、地方官员或百姓交流时,总会传达新的政策、新的观念。另外他还以自己的能力为当地解决问题,如调解军阀鲁大昌与莫桑土司之间的矛盾。随着庄学本藏彝走廊摄影资料的增加,伴随着其著作的发表和照片传播,为外界了解藏区提供了重要路径。如在重庆、成都、雅安等地举办的“西康影展”,尤其是重庆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影展受到国民党政府高层和文艺、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重庆大公报》《成都中央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媒体报道了此次影展。在重庆、成都、雅安举行“西康影展”的数据大致如下表(表1)所示:
“西康影展”原名“孙明经、庄学本甘孜州老照片展”,其筹备中以半步行半骑行的方式历程约二万里,费时3年(1937至1939年), 搜集了23 县(1)23县大致是:石渠、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丹巴、九龙、雅江、理化、巴安、义敦、得荣、越西、冕宁、西昌、盐源、盐边、汉源、荥经、天全、雅安。共300幅反映藏彝走廊自然地理、人物生活与生产的老照片。“西康影展”向大众传播了川西地区的现实情况,庄学本为康藏地区进入大众视野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整理出《十年西行记》,并于1948年在南京、上海、杭州举办“积石山区影展”。此外庄学本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为国人了解西部边疆以外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庄学本以真实的影像直观地介绍了藏彝走廊的风土人情,从边疆视角凸显国家概念,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出了应有贡献。
(三)职业担当:对国家西部边疆开发的回应
中国在抗日战争背景之下,强烈需要加强民族团结、抵御外敌,要求对西部边疆的认识和开发进程进一步推进。而自古以来国家对西部边疆开发都有回应,从和亲到驻藏大臣的设置都是国家对边疆的回应,驻藏大臣全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康熙四十八年(1709)始置,正式设置时间当为雍正五年(1727年)[11]。公元1912年北洋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将蒙藏事务局改为隶属国务院蒙藏院。公元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次年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20世纪初,帝国主义乘中国对西南边地无暇顾及的机会,不断侵扰西南边地,妄图构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获取资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西南地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知识阶层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边疆研究逐步发展起来。庄学本作为上海《良友》《中华画报》等的特约摄影记者,从自身的专业角度出发,主动融入西部边疆研究之中,通过摄影和新闻报道向外界传达西部边疆的情况。1938年后,庄学本任西康省参议顾问,更是积极地履行作为一名政府参议的职责,专职从事民族考察,从考察的范围、成果及影响来看达到了民族学考察的顶峰,庄学本在藏彝走廊人文探访十年期间的报道、摄影照片、著作为西南边疆开发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或参议顾问,是对当时边疆开发的有力回应,庄学本通过藏彝走廊摄影所呈现的边地意象建构社会大众的边疆——国家意识,最终促成边区向国家大后方的“转换”,为抗日战争期间政府、学校等西迁作出了贡献。
(四)田野实践: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先驱
庄学本不仅是一名纪实摄影师、画报记者,而且是一位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先驱。刚开始到“禁地”西藏考察是出自一位专业摄影师兴趣,或者说在社会思潮影响下一位专业记者的职业担当。因为庄学本首次在藏地考察时并不是以一位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的,他学习过摄影,但没有参加过专业的人类学课程学习。1935年庄学本结束首次入藏考察,返回南京举办了个人影展,展示了藏地风貌,初具人类学研究的风格。后经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介绍,庄学本才开始在该院人类学组学习人体测量,这也是庄学本仅有的人类学知识学习经历。在随后的几次入藏考察中,庄学本既是一位摄影师,也是一位人类学田野工作者,更是一位爱国有志青年。他的工作具有复合性,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首先,庄学本利用自己摄影师的身份成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驱[12]。20世纪60年代影视人类学的术语才开始传入中国,但在此之前,庄学本等人就已经开始从事影视人类学的实践,从1934年自费到果洛草原考察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至1944年的10年人文探访期间,庄学本在藏彝走廊的少数民族地区,用镜头记录了五千多幅少数民族风情的影视材料。庄学本不仅是影视人类学的先驱,也开展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1935年学习完人类学体质测量后,被聘为摄影师。同时,负责为中央研究院测量少数民族体质,还为中山文化教育馆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此外,也是海外民族志书写的先驱。第四次入藏未果情况下,在印度三年工作期间他对印度的风土人情做了记录,开始海外民族研究。庄学本在藏彝走廊考察的经历也是一位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经历,庄学本在田野调查中形成了自己的方法:以当地人做向导、将照片赠予被拍摄者、买酒、放留声机、为被访者解决问题等,这种长时段(十年)的以他者的身份融入其中、参与其中,成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典范。庄学本涉及的人类学领域、方法和成果为人类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在学科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员。
结 语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下,庄学本的四次西部边疆人文探访是一位摄影记者在时代潮流中的个人与社会价值体现。庄学本以“先进”的手段对普通大众真实生活的记录,在20世纪上半叶实属罕见,成为藏彝走廊地区研究的先驱,但在2009年的广州摄影展上,庄学本成为一位“陌生人”[13]。今对其价值进行再认识,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并纪念庄学本诞生110周年。人类学是一项关于人及其文化活动的研究,庄学本所从事的摄影工作正好就是对于异文化人群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原始记录。其价值在当时也许只是展览、宣传、教育等。但对于现代文明来说,当时的摄影成果却是现在了解历史文明、研究过去的重要原材料。个人兴趣和时代要求塑造了庄学本,再一次证明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融入时代的潮流中,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庄学本的藏彝走廊人文探访为我们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作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深入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深入开展田野调查研究,记录时代的文明,回应国家方针政策。在各民族之间架起一道相互了解的桥梁,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