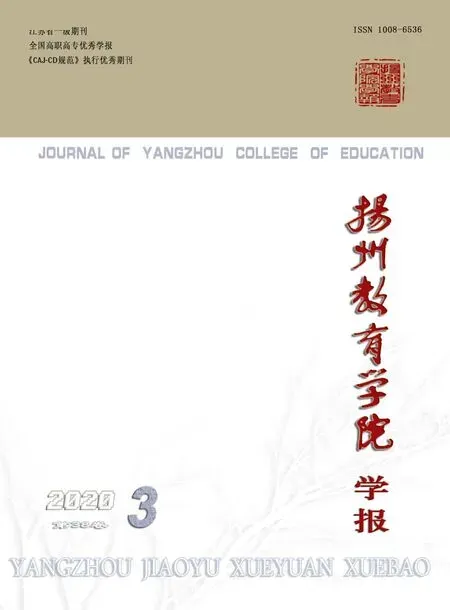从焦循的文学经历窥其文学对经学的影响
——兼论焦循文学与经学的关系
李 沛 姗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焦循是清代少有的“文人的学者”类型,其文学思想和经学思想可谓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焦循的文学经历对其经学著作和经学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如青少年时期的文学积累是其“性灵观”形成的重要基础,和著名文人汪中的交游对其文学、经学观念的转变产生影响,在和袁枚关于著作与考据的论辩中不断完善其经学思想等等。但是历来学者关于焦循文学思想及其丰富的文学经历对其经学的影响的研究十分不足。钱穆较早地将具有“文人的学者”特点的焦循与其他考据学家区别开来,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屡次夸赞焦循的“文学”天才,如“里堂论学极多精卓之见,彼盖富具思想文艺之天才,而溺于时代考据潮流,遂未能尽展其长者”[1] 455。“里堂一极富文艺天才之人也,……然里堂治经途辙,亦复与当时风尚不同。”[1] 467虽然钱穆把焦循在经学中的精卓之见归为其思想文艺天才的影响,但钱穆并没有在文学是如何影响经学这一层面上展开来说,只是作了一个笼统而大致的论断。李畅然在《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中虽然略微提及了焦循文人品格对经学著作的影响,但其主要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论述焦循的文人心粗对其《孟子正义》注疏的不良影响,如“焦循之所以对文义把握不严格,恐怕和其文学性的认知心理有极大的关系。……文学气质强烈的人思维活跃,但往往不能固定于一处;所以虽好生新见,但由于对对象专注不足,局部求通,不顾整体,故其见解不可靠者亦多”[2]304。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以狐狸型和刺猬型来形容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特点,狐狸型的人物喜欢从事多方面的追逐,而刺猬型则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贯穿在一个单一的中心见解之内[3]。而从焦循作文和治经的特点来看,焦循实为狐狸型和刺猬型的结合。焦循作为文学气质较为强烈的人,往往思维活跃、好生新见,这符合焦循治经兼下己意、不复人言的特点,而这正是狐狸型的特点;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焦循重视博通,擅长从前人的著述和学术史发展的趋势中总结经验,他在文学和经学论著中都有总结性的观点提出,如“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观[4]5514、主张汉宋兼容的学术观等等,这又明显是刺猬型的特点。由于焦循兼具文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导致其文学和经学思想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其文学和经学总体来说呈现出交织的特点,所以单从经学或者文学的方面去阐释焦循的经学观和文学观都会显得单薄。然而学者多受到乾嘉汉学主导论以及焦循经学通儒身份的影响,必然会产生其文学思想隶属于经学的观点,而这显然是片面且不客观的。所以,首先得厘清焦循的文学与经学系统是一个交织并融的状态而不是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在此前提下,进一步从焦循丰富的文学经历中分析其对焦循经学著作和思想的影响。
一、焦循文学、经学思想的交汇
学界普遍认为焦循文学思想隶属于其经学思想,如较早进行焦循研究的何泽恒便认为在焦循的学术体系中“无经学亦不得有文学”[5]377,这是受到了乾嘉汉学主导论以及焦循经学通儒身份的影响。然而,焦循文学与经学中相类似的观点很难说清楚是谁影响谁的关系,也许焦循偏重于往经学方面解释,但这并不能证明焦循的经学观决定了其文学观,二者更像是互为表里、交汇并融的关系而非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决定论的视角去分析焦循经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一)“善与人同”
焦循在其文学及经学主张中都强调“善与人同”,如在经学著作《论语通释》中便指出“善与人同”的含义所在:“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故君子不同也。惟不同,而后能善与人同。”[4]2478-2479可见,“善与人同”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一味求同,焦循强调的是“惟不同而后能善与人同”,即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又能理解并包容他人及周遭环境的不同。在文学主张上,焦循也同样强调“善与人同”,如其《易余籥录》记载道:“余按王氏(王安石)之文,独成一家,其善正在不与人同,其经术学问皆然。当时韩魏公、司马温公必欲其同于己,所以不合耳。圣人之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惟其不同,所以通天下之志。”[4]5528焦循认为王安石、韩琦、司马光的文学主张都有求同之弊,只欣赏与自己文风相近的文章,而不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各人文章的差异。焦循认为“善与人同”之所以重要,因为此旨正是圣人“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之道在文学或者经学上的体现[4]4380。
(二)阴阳思想
焦循擅长以“阴阳的旁通变化”来对其易学著作进行阐释,然而在文学方面,焦循也以性情之阴阳来划分文学体裁。如《里堂家训》有:“人秉天地阴阳之气,刚正清粹中,亦必间以柔靡。有时阴气所动,以四六、词泄之,不使犯入诗、古文。……如是而为四六、为词,不特无妨于诗、古文,且有裨于诗、古文也。”[4]4383-4384以此条观之,焦循认为性情之阴体现在文学表达上则为骈文和词,性情之阳则为诗和古文,而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实现性情阴阳的调和,所以焦循特别反对“词为无用之学”的观点,认为词的写作是有益于诗文创作的。《易余籥录》有:“人禀阴阳之气以生,性情中所寓之柔气,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纯之气长流行于诗、古文。且经学须深思默会,或至抑塞沉困,机不可转,诗词足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则有益于经学者正不浅。古人一室潜修,不废啸歌,其旨深微,非得阴阳之理,未足与知也。”[4]5536在此处,焦循分两部分论述诗词、经学与阴阳的关系,当诗、词相对时,则诗阳词阴,而当诗词与经学相对时,则经学为阳诗词为阴。焦循认为在经学研究及创作中处于“每不可遏”“机不可转”的状态需要抒发的途径时,便可以借助“词曲一途分泄之”,或者“诗词足以移其情而豁其趣”。总而言之,焦循把以诗词为代表的文学作为性情中偏阴的表达,以经学作为性情中偏阳的表达。经学须深思默会,而文学则可以作为宣泄情感的手段,这正是二者分属阴阳显著的不同。焦循又说:“古人一室潜修,不废啸歌,其旨深微,非得阴阳之理,未足与知也。”“一室潜修”可谓是精研经学学问之比喻,“不废啸歌”可作为以诗词表达性灵之喻,焦循认为古人以经学、文学互补协调,所以只有明晓阴阳之理,才可以通古人深微之旨。
(三)“性灵观”
焦循在《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中提及“性灵”的主张,“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4]5891。意思是在经学写作中要先以博览经典为基础,然后根据个人的心得和想法,提出富有创意的见解,并能贯通古代圣贤、经史百家的观点,由此到达学术的至臻境界。此外,焦循也将“性灵”运用到其文学主张上,焦循认为诗词有助于性灵的培养,尤其是孩童刚踏入学问之途时,最适宜授之以诗,以“瀹其性灵”“导其善志”[4]5872。如焦循在教导叶英之子时,尽管叶英提出了“幸勿授以时文、诗赋也”的要求[4]4363,但焦循仍坚持教授诗文,而不肯靡于当时的风气之中:“近之风气,教子者多以《尔雅》汩其性灵,余每力为之争,而不肯靡于风气。”[4]4363可见,以诗词为代表的文学是有益于培养性灵的,而《尔雅》之学只会让孩童“虚灵尽钝”。焦循虽然言及“惟经学可言性灵”[4]5892,似乎将文学排挤出“性灵”的阵营,与上述“诗词”有助于“性灵”的说法相悖,但只要了解当时的学术风尚及其弊病便知焦循此言的目的所在。乾嘉学术界径以考据为经学,孩童争相诵读《尔雅》,学者“人人许郑”,经学著作大抵人云亦云,毫无新意和“性灵”可言,所以焦循只能力倡“惟经学可以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企图将“性灵”之说与经学结合得更为紧密以救经学之弊。但这并不意味着焦循将诗词为代表的文学排挤出“性灵”的阵营,若是如此,《尔雅》相较于诗词,更接近于经学研究的领域,但是焦循却每每强调要以诗教为先。可见,焦循并不否认诗词中也蕴含着“性灵”。焦循曾言及“诗词足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则有益于经学者不浅”,而此“有益于经学者不浅”之处,正是从诗词有助于“性灵”养成的方面来说的。
二、焦循文学经历对其经学的影响
焦循早年的文学积累对其“性灵观”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此后的文学经历对其经学思想的产生和深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清代“学者社会”的重要特征便是学者间的交游和函札往来,清儒们通过这两个途径交换知识、表达观点,焦循也不例外。
(一)焦循早年的文学积累对“性灵观”形成的影响
《雕菰集》中关于叶英(号霜林)为子向焦循拜师时的描写十分生动:“江子屏与霜林至,霜林前匍匐再拜不起,余惊不敢答,继而从容言曰:‘吾有子,欲从君游,此所以乞也。’明日其子至,余授以学。”[4]6050焦循在《里堂家训》中还详细提及其中细节:“叶霜林以其子托余教之,谓余曰:‘不愿儿作状元,愿儿作通人,幸勿授以时文、诗赋也。’余曰:‘不然,未有不为通人而状元者。’卒授以时文……近之风气,教子者多以《尔雅》汩其性灵,余每力为之争,而不肯靡于风气。”[4]4363从上述两段引文可以看出,尽管焦循对叶英十分敬重,但是在如何教育学子方面却丝毫不肯让步,坚持以诗文相教授。因为焦循认为学童若先以《尔雅》为学,则会导致“虚灵渐钝”,相反,若以诗歌为教,则能“瀹其性灵”“导其善志”[4]5872。焦循是以孩童的“性灵”培养作为教学的第一要务,所以才始终坚持诗教为先。而回首焦循幼时的学习经历,也同样从诗词开始,可知焦循如此坚持教导孩童学习之次序,不仅是有感于当时考据风气对孩童学习的“戕害”,更是从自身学习经历出发,对孩童作出的最中肯的建议。正是早年学习诗文的经历让焦循能超脱于当时人云亦云的考据风气,认识到保持自身“性灵”在经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终成为一名“汇而通之,……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的经学大家,所以其早年的文学经历尤其值得重视。
现根据赖贵三的《〈焦循年谱新编〉纪要》对焦循的文学经历进行爬疏,主要有:
1.三岁时,嫡母口授《毛诗》及古孝弟忠信故事,范征麟以字音反切相授。2.六岁始入塾读书,从范征麟学,授以诗,辨别音韵。3.十一岁,范征麟令读古文,遂好为古文。族父熊轼一一改正其诗,并奖而进之,于是知作诗之门径。4.十二、三岁时,好为小诗,父焦葱以《诗品》示之以教,循受而录之,藏诸箧二十余年。又读三苏文,即解为论序。5.十六、七岁,习为诗、古文辞。6.未弱冠时,极为阮承勋所爱,时时呼至斋阁为文章。7.二十五岁,尝冬夜与汪晋蕃饮于汪中斋阁,快论至三鼓,雪深二尺许;汪中酣卧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焦循又以所撰序事文就正于汪中,令焚之,曰:“序事文须无一语似小说家言,当时时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之鹄。”8.三十岁时,郑柿里以古文与焦循相靡切,而焦循学柳州文也。9.三十三岁,受阮元之邀往山左,归扬州后有《游山左诗钞》一卷。10.三十四岁,阮元督学于浙,复招循游浙东,为阮元辑《淮海英灵集》。[6]
由此可见,从三岁学诗到而立之年,焦循与诗文的关系都十分密切,而且家族、师友间的文学氛围十分浓厚,如嫡母谢孺人、父亲焦葱以及表兄范征麟、妇翁阮承勋都对幼年焦循的诗文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与汪中、郑柿里以及阮元的交游也增长了焦循的阅历,从而促进了焦循诗文的写作。尤其是阮元,其邀焦循前往山左及浙东等地游学,极大地激发了焦循的文学情思,留下了大量的诗作。
焦循在经学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就,而“性灵观”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其经学论著中,时常能发现焦循“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的不断尝试,例如其将自身的《易》学体系和思想运用于阐释《尚书》《论语》《孟子》等经典中,其《论语通释》《尚书补疏》《孟子正义》便是其中典范之作。焦循主张“博览众说而自得其性灵,上也”[4]4376。他十分强调“博通”,即在博览群书后能以己意通贯经典,其中的“通”便是以“一己之性灵”为基础的。焦循屡次疾呼考据之弊,因为考据不能与“性灵”相通反而执一害道,焦循呼吁要以“经学代考据”,又常常提及“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可见焦循希望以“性灵”之学代替人云亦云的考据。焦循教导孩童以诗教为先,认为诗教能疏导“性灵”,而授以《尔雅》则会起反作用。纵观焦循早年的学习经历,可以发现诗教占了绝大的比重,直到十七八岁受到刘墉和顾凤毛的影响,才开始致力于经学。“性灵观”对焦循的经学著作产生重大影响,而其“性灵观”的形成又不能不追溯到其早年的诗教经历,文学对其经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与汪中的交游经历对焦循经学著作写作观念的影响
焦循在年青的时候,曾与当时的文学大师汪中有过一段雪夜畅谈的经历,焦循至老对此仍念念不忘,其在《亡友汪晋蕃传》中记载:“余尝冬夜与晋蕃饮容甫斋阁,快论至三鼓,雪深二尺许,容甫酣卧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不二十年,超宗、容甫、晋蕃先后没世,回思若旦夕事,悲哉!”[4]6044在此次交谈中,汪中曾教授焦循为文之法,这次教导对焦循一生的学术观念和创作都影响甚大。汪中是清代的文章大家,对时人多否而少可的章学诚也深赞汪中的文学成就[7]。据赖贵三《〈焦循年谱新编〉纪要》记载:在此次雪夜畅谈中,焦循将自己写好的文章给汪中过目,“(焦循)又以所撰序事文就正于汪中,令焚之,曰:序事文须无一语似小说家言,当时时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之鹄”[6]。汪中教导焦循作序事文应该以《左传》《史记》等书作为模范和标准,这个建议对焦循的影响非常大,焦循在日后著书、为文时,非常注重从《左传》《史记》等书中汲取知识。他常常强调:“叙事之文,尤为重大。……至于难状之状,难写之情,一经点次,如见如诉,宜从《左》《史》入手,参之以《庄》《列》诸子,广之以韩、柳诸集。大之能包括一切,细之能穷极毛发,繁简长缩不拘也。”[4]4381“叙事文,《左传》《史记》尚矣。”[4]5534而且焦循不仅“时时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之鹄”,而且也做到了处处“以《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之鹄”,其经学著作也时常借鉴“以史为师”的方法,如在《易学三书》《孟子正义》的撰著中,焦循时常从《左传》《史记》等史书中寻找灵感和突破。
焦循《撰孟子正义日课记》中记录:“廿三日壬午,晴,西北风,天气寒。阅《春秋左氏传》。”[4]4036自此后连续七天,焦循都致力于《左传》的阅读,而且在廿七日丙戌日记中记载:“晴,阅《春秋左氏传》。灯下改《易章句·豫·彖传》《巽·上九传》《姤·上九传》《序卦》‘受之以《复》一条’。”[4]4037虽然焦循并没有明言阅读《左传》和修改《易章句》之间的联系。但是焦循撰写《日课记》的目的在于“因将纂成《正义》,恐志有懈弛,立薄逐日稽省,如前此注《易》云”[4]4023。《撰孟子正义日课记》是为了《孟子正义》的成书而撰写的日记,大都是修改增补《孟子正义》亦或是关于日常读书、天气情况、自身疾病的记录,只有廿七日丙戌修改《易章句》的日记最为特殊,可以猜测焦循兴许是从阅读《左传》中得到相关的灵感,才将之前成书的《易章句》进行再次修改。此后,焦循还阅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其中有一则“十二日己巳,阅《三国志》,至《阎温传注》引《孙宾硕传》,采入《正义》卷一”[4]4045。可见,焦循时常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有所灵感和顿悟,从而对其经学著作进行增补和扩充。李畅然也认为:“这次博览群书对提升《孟子正义》的质量有很大帮助。”[2] 287虽然汪中的建议只是针对作文而言,然而焦循触类旁通,将其借鉴到经学著作的写作当中。尽管到了晚年,增补《孟子正义》和《易章句》时,焦循仍然奉汪中的建议为作文的不二法门。
(三)在与袁枚关于文学与经学的论辩中完善其经学思想
焦循在《里堂家训》中将依附于考据之名而生成的学问分为“本子之学”和“拾骨之学”,并认为“本子、拾骨之学非不可为,特非经学之尽境尔”[4]4378。也就是说经学绝不止于本子和拾骨之学,那什么才是经学的至臻之道呢?焦循认为:“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4]5893经学之道需虚实相结合的观点是由与袁枚和孙星衍关于文学与经学的论辩中产生的。袁枚在《散书后记》中有:“(著作和考据之学)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专事依傍;一类劳心,一类劳力。二者相较,著作胜矣。”[8]又在《覆家实堂》中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文,道也。考据,器也。器易而道难。‘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古文,作也。考据,述也。述易而作难。”[9]袁枚在考据之学如鲜花着锦之盛时发出如此贬低考据之语,故立遭孙星衍的论难。孙星衍在《答袁简斋前辈书》中道:“侍推阁下之意,盖以抄摭故实为考据,抒写性灵为著作耳。……是著作亦器也。……是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据。”[10]孙星衍首先辩驳袁枚的“古文,道也。考据,器也”的说法,提出著作和考据都是“器”。进而对袁枚将著作、考据分而为二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古人著作即其考据”。焦循十分赞同孙星衍对袁枚“道器之分”的辩驳,认为此说“用彰圣学,功不在《孟子》下”[4]5890-5891。但是却十分不满孙星衍“古人著作即其考据”的说法,并连续在《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与刘端临教谕书》两封函札中力申“以经学代替考据”的主张。
关于袁枚将著述和考据分为道器之说的观点,孙星衍已经攻之甚伟,但是袁枚对于当时以“考据”代名的经学的贬低,孙星衍并没有集中对此进行发难,而焦循则对此一一进行反驳,如在《与刘端临教谕书》中提出:“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一反袁枚以核实归之考据(经学)、以“凭虚而灵”归之著作的说法,认为经学之道至大至广,既包括核实之学,即“证之以实”;又需要凭虚而灵,即“运之于虚”。意思是经学论著既要有自己的性灵贯彻其中,但也要注重实证的方法。李贵生在《论焦循性灵说及其与经学、文学之关系》中指出,假如经学真的只是本子与拾骨之学,乃主因、核实而滞、专事依傍和劳力之学,而完全没有主创、凭虚而灵耻言蹈袭和劳心等要素,那袁枚之说并非无理。但是焦循认为经学有其通的一面,要达到通的境界,除了要证之以实外,还要运之以虚。而袁枚以考据为经学的全部,复以核实与凭虚判分考据与著述,并未能窥见经学之道[11]。所以焦循“证之于实,运之于虚”的理论实则是针对袁枚以“文人”的眼光对经学的贬低而作出的回应。
袁枚为贬低经学而抬高文学,还提出:“古文,作也。考据,述也。述易而作难。”焦循为此特意作了《述难》五篇,屡称述之难亦不下于作也。何泽恒在《焦循研究》中也认为:“里堂《述难》之作,亦针对简斋而发。简斋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述易而作难。’里堂则曰:‘作述无差等,各当其时而已。’”[5]365袁枚极力贬低经学家的学术成就,而焦循则每每与袁枚立相反之说,为经学正名。此外,焦循首次在经学主张中力倡“性灵”之说,也与袁枚有关。虽然焦循在《尚书补疏》《孟子正义》中都对“性灵”之旨阐发极详,认为“善即灵、灵即神明、性灵即性善”,但这都本于《尚书》的旧疏故训,并进一步延伸到对《孟子》的解释中。焦循真正将“性灵”与其经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阐发,最早还是见于《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与此?”[4]5891众所周知,袁枚的性灵说是针对诗文而言,他在《散书后记》将“凭虚而灵”归为著述的特点,同样也认为抒发性灵是诗文所独有的优势。焦循于此十分不满,便以“性灵”一词转而说经学,据《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焦循认为在经学研究中,个人的心得和想法(即“一己之性灵”)也十分重要,要在参领圣贤之书的基础上提出富有创意的见解(即“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何泽恒在《焦循研究》中认为焦循“性灵”一词,亦袭自袁枚,乃转以之说经学[5]316。而李贵生认为焦循“性灵”之说应非袭自袁枚,而是焦循作为经学的巨擘,特意赋予“性灵”新的含义[11]。但无论焦循“性灵”之说是否直接源自袁枚,但“性灵说”与焦循经学思想的关系也因与袁枚的辩难而结合得更加紧密,因为袁枚以“性灵”归属于诗文而以此贬低经学,焦循不得不提出“惟经学可以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的主张[4]5892,以经学与“性灵”密不可分的关系来驳斥袁枚“性灵仅寓于诗文”的观点,以此捍卫经学的地位。由此可见,焦循“证之于实,运之于虚”“述难”以及将“性灵”与经学紧密结合都是在与袁枚的论辩中形成的观点。袁枚作为著名诗人而非学者,其提出的崇诗文而贬经学考据的观点尽管失之客观,但却为焦循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启发。在与袁枚的一次次“针锋相对”中,焦循对考据、经学和“性灵”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体悟,“以经学代替考据”是焦循反对考据所走的第一步,也是针对袁枚将经学归于考据所作的争辩;接着,焦循以“惟经学可以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来强化经学与“性灵”之间的关系;最后,焦循提出经学之道需“证之于实,运之于虚”,强调经学既需要实证之科学又需要“凭虚而灵”的“性灵”的参与,在经学与“性灵”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个实证。焦循的经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而与袁枚关于文学与经学的论辩实则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三、结语
焦循被誉为“通儒”,指其学问贯通于各个领域。然而阮元在《通儒扬州焦君传》中用大篇幅记叙焦循的经学成绩,只一笔略过其文学成就:“君于治经之外,如诗词、医学、形家九流之书,无不通贯。”[12]480焦循的文学思想确实是被严重低估了,而且后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兼具学者及文人身份的焦循的文学思想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学者们或单就焦循的文学而论文学,或将文学隶属于其经学体系中去研究,而这显然是片面且不客观的。阮元以“斯一大家,曷可遗也”来提醒今世及后世学者不要忽视焦循的学术成就[12]481,阮元的提醒从今天焦循的经学影响上来看是成功的,然而其文学影响确实是被大家遗忘了。焦循早年丰富的文学经历为其“性灵观”的产生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在焦循其后的求学旅程中,如早年与汪中的交游经历以及与袁枚关于文学与经学的针锋论辩,都对焦循经学著作的写作及经学观念的形成、深化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在对焦循“通儒”身份进行研究时,要摆脱乾嘉汉学决定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在焦循的学术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惟有这样,对“通儒”焦循的研究才能更全面和客观。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