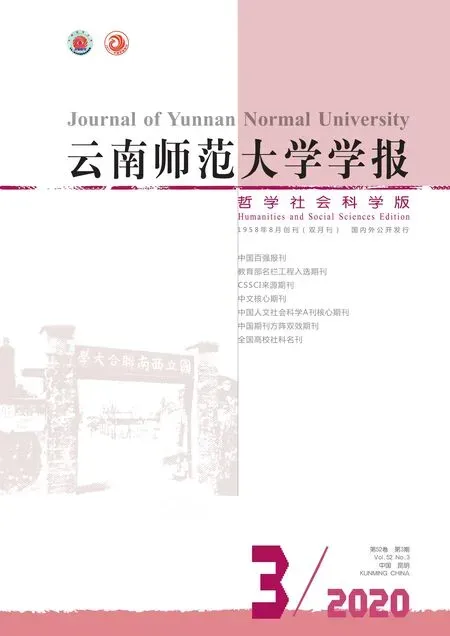论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诗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4)
刘禹锡一生“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1)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A].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682.,交往及唱和过的诗人殆难计数。就中,柳宗元情谊最笃,而白居易历时最久。从元和三年(803)到会昌二年(842),此唱彼和几近40年。即使天各一方,亦未稍废。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将自己与刘禹锡的唱和诗编成《刘白唱和集》上下两卷,共收入两人唱和诗138首。此集后来又由白居易续编4次,增至5卷。而由白居易一次次不惮其劳、不厌其烦地编集唱和诗的热情,足以看出他对两人桴鼓相应的诗谊的珍惜以及对刘禹锡这位旗鼓相当的诗友的推重。
对刘白二人的唱和诗,除了历代诗论家只言片语的评点外,最值得我们重视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10余篇专题论文,包括硕士学位论文《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研究》(2)王玫.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期刊论文《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简论》(3)熊飞.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简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等。而卞孝萱、卞敏的《刘禹锡评传》(4)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及吴汝煜的《刘禹锡传论》(5)吴汝煜.刘禹锡传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等学术专著也对刘白唱和诗有所涉及。不过,这些论著较多地致力于本事的钩稽、作品的解读、思想艺术特色的探析及政治文化背景的观照,创获殊丰。但仍有进一步拓展、提升与深化的余地。兹就前贤时彦锄犁罕及者加以申论,侧重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梳理刘白唱和诗发生、演进及嬗变的轨迹,探讨刘白唱和诗的创作倾向、艺术风貌及历史地位。
一、酬酢之始:扬州初逢席上的即兴吟唱
检视刘白二人长达40年的唱和历程,依据刘禹锡的仕履踪迹,约略可以划分为4个时期,即:扬州初逢以前;重入庙堂时期;三牧上州时期;晚居洛阳时期。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与白居易初逢于扬州。此前,他们闻声相思已久,也早就有诗唱和。从现有文献看,白居易元和二年(807)十一月担任翰林学士后,便与贬居朗州的刘禹锡时有书信往来及诗歌酬唱,并不顾忌后者为动辄得咎的戴罪之臣。刘禹锡作于元和三年(803)春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是最早的一篇酬答白居易的作品: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
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
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
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6)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102.
看得出,刘禹锡对白居易诗洗尽铅华、不事雕饰的艺术风格极为推崇,对白居易清如玉琴、穆如春风的人格魅力也极为神往。长庆元年(821)冬,谪守夔州的刘禹锡作有《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
虽陪三品散班中,资历从来事不同。
名姓也曾镌石柱,诗篇未得上屏风。
甘陵旧党凋零尽,魏阙新知礼数崇。
烟水五湖如有伴,犹应堪作钓鱼翁。(7)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361.
据《旧唐书·宪宗纪》,长庆元年十月“壬午,以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为中书舍人”(8)刘昫,等.旧唐书(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492.。诗题称“白舍人”,可知作于此际。诗中以“甘陵旧党”喻指永贞革新集团,慨叹当年患难与共的革新志士在风刀霜剑的侵袭下相继辞世。篇末则表达了与白居易偕隐五湖的愿望,而相见恨晚之意则冥于其中。
宝历二年(826)秋天,刘禹锡奉旨卸任和州,返回洛阳待命。这对于他来说,不啻是重入庙堂、待机起用的福音。他与因病罢苏州刺史的白居易约定在扬州会合,然后结伴返回洛阳。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的酬酢之始。酒酣耳热之际,白居易即兴赋写《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莫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9)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1957.
诗中对刘禹锡的坎坷遭遇深致不平之鸣,慨叹其挟王佐之才却长期沉沦下僚、蹉跎岁月,在寂寞中耗尽壮心。“满朝官职独蹉跎”既是抨击“斯人独憔悴”的不公现象,也有针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实政治之意。
刘禹锡的和诗则表现出比白居易开朗和达观的情调: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10)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402.
首联囊括了诗人辗转流徙巴楚等地的惨痛遭遇,折射出其内心的深沉感慨。颔联感叹旧友凋零、今昔异貌。如果说上句包蕴着诗人对亡友缱绻难已的怀念之情的话,那么,后句不仅暗示了自己贬谪时间之长久,而且表现了世事的变迁以及回归后恍若隔世的特殊心态。颈联或有自伤淹蹇、自叹沉沦之意,但“沉舟”“病树”后续以“千帆过”“万木春”,则又平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在结构上,它与白诗中的“举眼风光”一联相呼应,却摈弃了前者的晦暗色彩和低沉旋律,而出以相对明朗、亢奋的笔墨。在手法上,它则实现了诗情、画意、哲理的高度融合,情韵悠长,耐人寻味。尾联顺势而下,敦请白氏藉饮酒听歌,振作精神,一起拥抱明天。这种精神状态,或者说精神境界的差异,一直呈现在刘、白二人的唱和诗中。相对于白居易的低沉,刘禹锡虽也难免情绪产生波动,总体上却显得较为昂扬与通达。白居易后来誉其为“诗之豪者”,正是自觉这位老而弥笃的诗友有着自己所缺少的豪迈。
二、五色驳杂:重入庙堂后的悲喜人生
扬州初逢时,刘禹锡生死相契的挚友柳宗元已于7年前不幸病故于柳州贬所,举世再无风雨同舟、安危与共者,他亟需找到一位心息相通的诗友来弥补柳宗元去世所留下的空白。白居易在扬州的适时亮相以及亮相后表现出的同病相怜、同气相求意向,恰好满足了刘禹锡的精神需求和心理渴望。而白居易这边,虽然当年一同大力创作讽喻诗的元稹依然健在,并且依然与他唱和不休,但政治上的穷达之异已使他们之间少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同时,刘禹锡身上还有着为求荣达而不惜剑走偏锋的元稹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不忘初心、不畏挫折、始终保持着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这对自感精锐不足的白居易也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惟其如此,扬州把晤之后,他们的友谊不断加深,而唱和的热情也渐次升温。因此,重入庙堂以后与扬州初逢以前相比,唱和的密度提高了许多。
刘白二人一同返回洛阳不久,白居易便被征为秘书监,赴长安履新。刘禹锡的任命却迟迟不见下达,闲处洛阳,宦况冷落。这让白居易颇为牵挂,在奉使江南的途中,他也不忘以诗代笺,送达问候。刘禹锡酬以《答乐天临都驿见赠》:
北固山边波浪,东都城里风尘。
世事不同心事,新人何似故人。(11)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431.
《古诗·上山采蘼芜》有句“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新人何似”云云当取义于此,用以表达双方对旧日情谊的持奉,颇见拳拳。白居易读后,又写下《临都驿答梦得六言二首》(12)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432.,既感叹时序如流,韶光易逝,又引出古代同样命运多舛的“谢守”和“冯公”,以之为参照,劝勉刘禹锡莫问前事,且吟新诗。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终于调回长安就任主客郎中,旋又兼任集贤殿学士。刘禹锡以为灿若云锦的前程已迤逦展开,命运的转机或将翩然降临。然而,在内有宦官专横,外有藩镇跋扈,又兼朋党倾轧无已的情势下,有心提拔刘禹锡的宰相裴度根本无力掌控局面,人事安排也受到多方掣肘。因此,刘禹锡总是与晋升的机会擦肩而过。与此相应,他与白居易的唱和诗也被抹上了几丝阴郁的色彩。《答白刑部闻新蝉》一诗有云:
蝉声未发前,已自感流年。
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
晴清依露叶,晚急畏霞天。
何事秋卿咏,逢时亦悄然。(13)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457.
秋蝉尚未鸣叫之前,诗人已自感流年似水,自伤沦落不偶;一旦秋风把时断时续的蝉声送入耳膜,便觉得格外凄凉。“凄凉”二字,既是形容蝉声,更是刻划心境。蝉声本来未必“凄凉”,盖因诗人一时心情悲颓,听来顿生“凄凉”之感。不说“凄凉一入耳”,而说“一入凄凉耳”,径直以“凄凉”修饰“耳”字,不仅是为了切合平仄律,更为点明“凄凉”主要不是来自蝉声,而是来自与双耳相关合的心境。“晴清依露叶”看似安逸,接云“晚急畏霞天”着一“霞”字,则又流露出身处矛盾漩涡中的忧谗畏讥之感。结句“逢时亦悄然”一语双关,暗示自己虽遭逢明时,却悄然淹乎众侪。
大致作于同时的《同乐天送河南尹冯学士》一诗也向白居易袒露了仕进无路、用非所长的郁闷心情:
可怜五马风流地,暂辍金貂侍从才。
阁上掩书刘向去,门前修刺孔融来。
崤陵路静寒无雨,洛水桥长昼起雷。
共羡府中棠棣好,先于城外百花开。(14)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468.
“刘向”和“孔融”既是比拟由左散骑常侍、兼集贤殿学士出任河南尹的冯宿,又何尝不是自况?诗以“可怜”二字领起,托出诗人对喜获重任的冯宿的不胜欣羡之情。而“寒无雨”“昼起雷”云云,既是“景语”,也是“情语”,象征着诗人的心情冷寂而又干涸,得不到雨露的滋润,还不时有电闪雷鸣突袭于其间。
此时的刘禹锡尽管心情极度压抑,有时也不免用比兴手法出以怨望之语,但从总体上看却比白居易用笔明朗。比如同样吟咏深秋,刘禹锡虽也展示秋景的萧索,却力避衰飒之气、追求闲淡之致。如《和乐天早寒》:
雨引苔侵壁,风驱叶拥阶。
久留闲客话,宿请老僧斋。
酒瓮新陈接,书签次第排。
翛然自有处,摇落不伤怀。(15)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468.
白居易《早寒》诗云:“黄叶聚墙角,青苔围柱根。被经霜后薄,镜遇雨来昏。半卷寒檐幕,斜开暖阁门。迎冬兼送老,只仰酒盈尊。”被薄镜昏,霜寒雨密,帘幕“半卷”,阁门“斜开”,这种种衰飒意象,宣示了诗人内心的悲凉与凄惶。而刘禹锡的这首和诗固然也呼应原唱渲染萧瑟秋景:雨骤风狂,苔鲜半壁,黄叶满阶。这本当令人触目伤怀,而诗人却从容若素,以待客、饮酒、读书等一系列足以娱情遣兴的活动来消解眼前的枯寂。“翛然自有处,摇落不伤怀”。因为已找到安置心灵的驿站,所以他不会作悲秋之叹。
《答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一诗更见用笔不俗、气魄非凡:
衙前有乐馔常精,宅内连池酒任倾。
自是官高无狎客,不论年长少欢情。
骊龙颔被探珠去,老蚌胚还应月生。
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16)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532.
白居易原唱题为《府斋感怀酬梦得》,篇末感叹“不闻枯树再生枝”,暮年苍凉之感溢于言表。有鉴于其悲颓,刘禹锡在和诗中叠用“骊首探珠”“老蚌怀珠”“桂花秋荣”等广为人知的典故,开导与安慰诗友:三春时节,繁华似锦,桃花李卉混杂于百花丛中,并不显得特别绚丽夺目。桂花则不同,它在“众芳摇落”的秋日飘香,除了菊花同时傲霜开放外,再没有其他争奇斗艳者,于是它也就成为秋天的宠儿了。世上有“赏桂”之说,何曾有“赏桃”“赏李”之称?因此,抢占春光的桃李何足羡哉?“枯树之叹”可以休矣!诗人巧妙地将人生哲理融合在典故之中,不服老迈的壮阔胸襟与豪迈情怀跃然纸上。
三、别情依依:出牧苏州时的深切感怀
大和五年(831)十月,刘禹锡被外放为苏州刺史,得以暂时远离党争,免受“池鱼”之殃。苏州位于江南富庶之地,名列“上州”,与他当年谪居的朗、连、夔、和4州不可同日而语。他与白居易唱和的精品佳作也多诞生于该地。
刘禹锡出牧苏州期间,回环在他与白居易唱和诗中的主旋律是相思之情。但并不拘囿于此,对友人的思念往往是与对身世的感怀糅合在一起的。如《郡斋书怀寄江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更值得玩味:
谩读图书三十车,年年为郡老天涯。
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
绮季衣冠称鬓面,吴公政事副词华。
还思谢病吟归去,同醉城东桃李花。(17)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574.
此诗纯属有感而发,其着力点与落脚点均在诗题中的“郡斋书怀”四字。虽是寄赠之作,却略无应酬意味。或许是厌倦了多年漂泊天涯、埋身簿领的郡斋生活,诗人又萌生了归隐田园之思。诗中自嘲“谩读图书三十车”,慨叹“一生不得文章力”,即杜甫早已表达过的“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意,说到底,是一种仕途偃蹇、夙志难酬的怨尤,是以曲尽其致的方式渲泄内心无法压抑的牢骚。这样,接下来以“绮季”和“吴公”来反衬自我也就顺理成章了。刘禹锡强调绮季的“衣冠”与“鬓面”相称,而吴公的“政事”亦与“词华”相副,正是为了凸显自己“才命两相妨”的不幸遭际,反衬现实生活中自身政治地位与文学才华的不相匹配。而这也正是他在尾联中倾吐“谢病吟归去”的迫切愿望的实际诱因。
《秋日书怀寄白宾客》一诗与此格调相近:
州远雄无益,年高健亦衰。
兴情逢酒在,筋力上楼知。
蝉噪芳意尽,雁来愁望时。
商山紫芝客,应不向秋悲。(18)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581.
首联即感喟官冷年迈。如是的感喟在“书怀”之作中反复出现,透露出诗人永远难以化解的矛盾心结:既以脱离政治斗争漩涡、暂得全身远祸为幸;又以僻处远州、壮志难酬为憾。两种情愫在现实生活中不免随着政局和情势的变化而此消彼长,各有起伏,却始终无法绝迹,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人生诉求的复杂性也因此得以显现。颔联承前慨叹“甚矣吾衰也”:尽管举杯痛饮时自觉兴致尚在,但举步登楼时却由步履的日趋滞重感知到筋力的驽钝。这样的感知带给他的显然不是快意。因此,颈联中也就只能回旋着厌闻蝉鸣、愁望秋雁的惆怅之情了。尾联以向往隐逸作结,仍是披露磊落不平的胸中沟壑。
因为二人都已到耳顺之年,刘禹锡在与白居易的唱酬赠答诗中多次以“晚达冬青”为题,各自抒写对桑榆晚景的认知。《乐天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一诗说: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
秋隼得时凌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
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
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19)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572.
白居易原唱《代梦得吟》中有“后来变化三分贵,同辈凋零太半无”“不见山苗与林叶,迎春先绿亦先枯”等句,明显流露出孤独、寂寞之感和来日无多的忧伤。刘禹锡的和诗则有异于此。诗人承认,自己与诗友同属“老夫”,不可能再像年少时那样叱咤风云、指点江山,而只能蹉跎岁月,这是概莫能免的自然规律。然而大可不必因此而嗟叹,因为祸福相倚,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应以积极的心态看待消极的外部环境,譬如衰秋和寒冬固然是令人不适的时令,却为“善假于物”的雄鹰和神龟提供了高飞或畅饮之便。如果顺时而动、顺势而为,又善于把握机会,何尝不能另有所获?这已见卓识,但诗人随即又攀升至新的哲学高度:化用“东隅”“北叟”一系列等典故,形象地阐发了祸福、升沉、荣辱可以相互转化的哲理。“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关键是要有“振臂”的信心与勇气。这样描写桑榆晚景,大有“晚达冬青”之概,确实要比白居易旷达与超迈。
《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一诗也足以显示刘禹锡因擅长哲学思考而形成的卓异见地:
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
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20)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581.
此诗的题旨是悼念元稹等不久前亡故的友人。白居易原诗题为《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其一曰:“并失鹓鸾侣,空留麋鹿身。只应嵩洛下,长作独游人。”其二曰:“长夜君先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悼往伤逝的色彩极为浓郁,几近吞声呜咽。刘禹锡和诗自也必须呼应题中之义,为亡友一掬伤心之泪。首联与尾联便都径直标出“伤”“恨”“泪”等哀婉之辞。假如通篇这般措笔,那就混同于寻常的伤逝之作而未能跳出白居易原唱的窠臼。但绝非等闲之辈的刘禹锡出人意表地在中间嵌入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一联,顿然擢升了全诗的境界。没有陈叶的凋零,何来新叶的生长?同理,若无前波的偃息,岂有后波的汹涌?蕴含在这看似写景的笔墨中的是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如此将人类与自然相联系,从进化论的视角对生死现象作整体考察,在当时是无人堪与比肩的。
四、豪放不羁:晚居洛阳期间的纵饮狂歌
开成元年(836)秋,刘禹锡获准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和白居易一起赋闲洛阳。两人唱和的黄金岁月随即到来。这是他们酬唱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勘破世事的他们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期。
白居易将他们此时的生活状态称作“中隐”,这种介乎出与处、忙与闲之间的独特生活形态,为他们的唱和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的便利。当时,在东都留守裴度的倡导和主持下,“洛阳文酒之会”经常不定期举行。如果说德高望重的裴度是“洛阳文酒之会”的当然领袖的话,刘禹锡与白居易则不失为“洛阳文酒之会”的核心(或曰中心)人物。今人着眼于其创作成就及实际作用,将参与聚会的诗人统称为“刘白诗人群”。(21)肖瑞峰.刘禹锡与洛阳文酒之会[J].社会科学战线,2015,(7).
但刘白二人唱和的时空却远远逸出了“洛阳文酒之会”。他们既参与众人的“群聚”,更乐意两人的“独处”,创造各种机会来驰骋才思、切磋诗艺。可以说,他们的唱酬是全方位的,也是全天候的,春去秋来,从不间断。写于秋高气爽之际的《秋晚新晴夜月如练有怀乐天》一诗说:
雨歇晚霞明,风调夜景清。
月高微晕散,云薄细鳞生。
露草百虫思,秋林千叶声。
相望一步地,脉脉万重情。(22)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712.
“月高”云云,意谓随着秋月的渐渐升高,原有的“微晕”悄然散去,更显得月色皎洁,寰宇澄澈;云彩则越来越薄、越来越淡,就像细细的鱼鳞点缀于寥廓的天穹。这两句初看其貌平淡,似非名言隽句;细品方能察知其写景之切、状物之工。在语言形式上,除了尾联对偶稍欠工整外,其余都是严格而又妥帖的对仗句,颇见整饬之美。
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居洛阳期间的唱和诗较多地以饮酒为题,或者诗题中虽不出现“饮酒”字样,却以饮酒为主要内容。即如白居易的《赠梦得》,题面与酒全然无涉,中间却既说“岂宜凭酒更粗狂”,又说“花前剩醉两三场”,饮酒仍然是其主旋律。刘禹锡的奉和之作亦是如此,且看《乐天以愚相访沽酒致欢,因成七言聊以奉答》:
少年曾醉酒旗下,同辈黄衣颔亦黄。
蹴踏青云寻入仕,萧条白发且飞觞。
令征古事欢生雅,客唤闲人兴任狂。
犹胜独居荒草院,蝉声听尽到寒螀。(23)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710.
描写刘白二人“沽酒致欢”的情形。醇厚而又绵长的杯中物将他们的思绪牵引到“曾醉酒旗下”的少年时代,勾起他们对“蹴踏青云”的骄人往事的温情回忆。但“蹴踏青云”的光荣历史终究难以掩盖与涂饰“萧条白发”的悲凉现实。要从这一现实中逃逸出来,在诗人看来,除了“且飞觞”外别无他法。于是,每次“相访”时,他们必定要“沽酒致欢”。然而,他们绝非只知买醉的酒徒,深厚的文化修养使他们饮酒的过程充满雅趣。比如行酒令时,他们不断征引古人的逸闻趣事。惟其如此,才达到了“欢生雅”的现场效果。至于“兴任狂”,则是以“闲人”自居的刘白进入微醺状态后的现场表现:忘乎所以,一任狂放。当然,在兴高采烈的表象下,我们隐隐还是能触摸到一些他们试图遮蔽的东西。
将刘、白二人此时的唱和诗相并读,我们不难发现刘禹锡虽也无法摈弃迟暮之感,而且已敛抑锋芒,不再讥弹时政、议论风发,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气骨,不失雄豪之风,在生命问题上显得比白居易要通达得多、透彻得多。《酬乐天感秋凉见寄》一诗说:
庭晚初辨色,林秋微有声。
槿衰犹强笑,莲迥却多情。
檐燕归心动,鞲鹰俊气生。
闲人占闲景,酒熟且同倾。(24)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712.
颔联中的“槿”“莲”以及颈联中的“燕”“鹰”,都是秋凉时节习见的物象。诗人将其一一攫入笔端加以描摹,藉以映现自己的秋日情怀。较之早年贬居朗州期间赋写的《秋词二首》,纵然已不见了“我言秋日胜春朝”那样的高度自信,却也没有皈依传统的悲秋主题。“槿衰犹强笑”或带有一些不甘与无奈,“莲迥却多情”则展示了一种情思绵邈却波澜不惊的坦然与从容。待得“檐燕归心动,鞲鹰俊气生”一联推出,则将前文的些微感喟扫荡殆尽,而示人以一派生机与活力,与《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二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各臻佳境:刘白唱和诗的创作风貌及其异同
纵观刘禹锡与白居易唱和的4个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友谊的加深以及时空条件的改善,他们见面的周期越来越短,应酬的热情越来越高,唱和的频率越来越密。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论及唱和的意义及作用:“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相戒”“相勉”“相慰”“相娱”,正是刘、白二人唱和的初衷。遵循这一初衷,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境遇、不同的背景下,赋予唱和诗多种功能。
刘白唱和诗的体裁多为五七言近体,但也有古体、杂体(如《叹水别白二十二》)以及新出现的长短句(如《忆江南·和乐天春词》)。其中,《叹水别白二十二》尤堪注目:
水。
至清,尽美。
从一勺,至千里。
利人利物,时行时止。
道性净皆然,交情淡如此。
君游金谷堤上,我在石渠署里。
两心相忆似流波,潺湲日夜无穷已。(25)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陶敏,陶红雨,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499.
此诗写于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名分退归洛阳后,刘禹锡与他思念日深,遂赋写了这首以难以排遣的相思之情为主旋律的“宝塔体”。诗不仅以水起兴,而且以水经纬全篇,试图藉“流波”传递“两心相忆”的深情。“至清,至美”“利人利物,时行时止”,这是对水的评点,也是对彼此品格特征及生命历程的写照。形式上,则采用“一七令”,句式从一字到七字逐步增衍,追求参差错落之美。尽管这多少带有游戏笔墨的意味,却使唱和诗的体裁变得更为丰富。至于《忆江南·和乐天春词》以词体来唱和,也体现了对唱和诗体裁的一种全新探索。
刘白唱和诗的题材则包括咏物、写景、抒怀,而以抒怀为主。其所抒固然都是一己之情怀,但其中往往融入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诚然,他们从不直接抨击时政、揭露时弊,像他们自己早年分别创作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为代表的讽喻诗和以《聚蚊谣》《飞鸢操》为代表的讽刺寓言诗那样。他们也极少议论国家政事及朝廷人事,有时甚至还对血雨腥风的现实政治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努力将其人其诗打造为不带电、不传电、不触电的绝缘体。但从他们对冬寒夏热、春雨秋风的敏锐感知和不无忧惧的咏叹,却不难触摸到严酷的时代氛围,体认到他们内心深处不堪国势日蹙、危机日深的感伤。他们并没有真的忘怀国事,只是在表象上与现实政治有些疏离。从某种意义上说,刻意回避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别样的关注。而且,除了少量作品为时风所染偶涉“绮靡”外,他们所抒写的情怀大多是健康的、诚挚的、不假虚饰的,有时甚至是高尚的、纯粹的、拔乎流俗的。尤其是刘禹锡,作为历尽劫波的永贞革新集团的骨干成员,始终不忘初心、不改初衷,在唱和诗中没有如同执政所希望的那样,对当年的政治立场与历史选择流露一丝悔意,相反,不时或隐或现地表现出对理想的持守和节操的捍卫。
应该说,刘白二人势均力敌,艺术上各有千秋,难加轩轾。不过,刘禹锡的唱和诗有两点优长是为白居易所欣羡的,其一就是他在诗中所表现出的豪迈、壮阔胸襟和旷达、乐观情怀以及生生不息的辩证法思想。这种超凡拔俗的胸襟、情怀与思想,不是偶然闪现的,犹如惊鸿一瞥,而是贯穿始终的,宛若草蛇灰线,绵延于他与白居易唱和的全过程。诸如扬州初逢席上创作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重入庙堂时期创作的“翛然自有处,摇落不伤怀”“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三牧上州时期创作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晚居洛阳时期创作的“檐燕归心动,鞲鹰俊气生”“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等等,前后呼应,相互烘托,共同支撑起他人难以摘取的“诗豪”桂冠。将两人的同题之作加以比照并观,不能不承认,就生活态度的开朗、乐观以及对人生哲学的思考、感悟而言,刘禹锡明显要高于白居易。正因为这样,刘禹锡的奉和之作,往往在思想高度上比白居易原唱有明显的提升。比如年近古稀时,刘白二人的唱和诗较多地以“咏老”为题。如果将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示》与白居易的《咏老赠梦得》相比较,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刘禹锡的“骨力豪劲”、超拔同侪之处。而白居易之所以慷慨地将“诗豪”这一桂冠奉赠予他,当有自愧不如之意。
另一点让白居易心折的是,刘禹锡唱和诗的语言更为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白居易早年和元稹一起创作讽喻诗时,为了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使闻之者易谕、见之者易晓的目的,努力趋向于平易通俗的语言风格,“其辞直而径”“其言直而切”。这种基于大众化的艺术追求,固然使白居易的作品接近“老妪能解”的地步,赢得了远比李杜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但同时也使他渐渐形成了务求显豁的语言习惯,不仅要“直说”,而且要“说尽”“说透”。这才遭致翁方纲《石洲诗话》的批评:“诗至元、白,针线钩贯,无所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尽耳。”等到白居易意识到自己遣词造句方面的弊病,想要加以救治时为时已晚,因为积习很难改变。而刘禹锡的诗歌既有“精锐”的一面,又有“含蓄”的一面,因此在自救自疗的过程中,他有意识地对标刘禹锡。对此,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有精到的分析:
大和五年,微之卒后,乐天年已六十,其二十年前所欲改进其诗之辞繁言激之病者,并世诗人,莫如从梦得求之。乐天之所以倾倒梦得至是者,实职是之故。盖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2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352.
这一论断应当本于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的自我剖析:“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27)白居易.白居易集(第四册)[M].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1452.若论诗名,刘禹锡在当时其实不敌白居易,而白居易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诗坛内外的美誉度逊于刘禹锡。《哭刘梦得尚书二首》开篇说“四海齐名白与刘”,当仁不让地先言“白”后言“刘”,中间说“杯酒英雄君与操”,意谓两人同为诗坛翘楚,成就在伯仲之间。但他对创作中的软肋是深具自知之明的。他称赞刘禹锡诗“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正是因为后者已臻于他苦苦求索而不能至的“理想之境界”。的确,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与白居易的“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同为唱和诗的颈联,二者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一形象、含蓄、深蕴哲理;一枯燥、直白、了无余味。白居易特意拈出这两句作为范例赞叹有加,折服之意也是毕见于字里行间的。
诚然,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诗中也有一些内容无聊、艺术粗糙的应景之作。但它们只占很少的篇幅。唱酬之际,刘白二人的创作态度都是认真的、严谨的、精益求精的,并且一直是试图与对方争雄的,无论首唱抑或奉和,都倾力而为,殚精竭虑,绝不敢掉以轻心、率尔挥毫。唯其如此,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诗不仅以唱和时间之久、唱和频率之密、唱和作品之既多且精,构成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多见的景观,而且就情感的浓度和抒情的深度而言,为后代文人唱和提供了可以效法的一种典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刘禹锡酬答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实现了诗情与哲理的水乳交融,映现于其中的超尘拔俗的胸襟、情怀与哲学思想认知,不是偶然闪现的,犹如惊鸿一瞥,而是贯穿始终的,宛若草蛇灰线,绵延于他与白居易唱和的全过程。这就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认知高度。同时,刘白晚居洛阳期间的唱和,又直接促致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刘白诗人群”的形成。作为这个创作群体的翘楚人物,刘禹锡与白居易是后代所艳羡的“洛阳文酒之会”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的唱和诗也是脱颖于其间的最具艺术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成果。(28)肖瑞峰.刘禹锡与洛阳文酒之会[J].社会科学战线,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