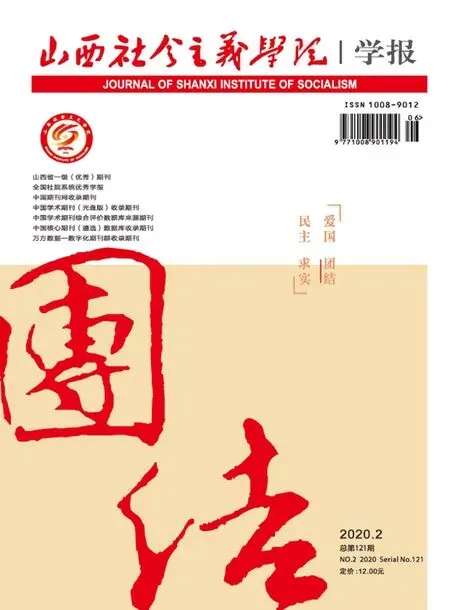伟大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建
张献生
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 100800
确立和实行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同新中国一起诞生的,它的形成和确立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成果,它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与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和任务联系在一起,建立在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独特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是在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跨越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历史潮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统一战线、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进行实践探索、开拓创新、总结升华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
一、此路不通:仿效西方多党制和一党专政的破产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势日益衰退,人民饱受欺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政治发展改变和超越了几千年来循环往复的旧轨,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发展过程。无数志士仁人走出国门,面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英勇斗争。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历史进程中,开始了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
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点燃了“倾覆满清,建立民国”的第一个火把,并于1905年建立了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经过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胜利后,新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如何建立?由于现代政党最早产生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并形成了以代议制为中心的议会政治制度和竞争性的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所以,中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首先和主要是从西方欧美国家获取思想武器。孙中山说,“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2]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共和政体,规定国家政体为内阁责任制,内阁由议会产生,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有组阁的权利。
国会的设立,为政党活动提供了竞争舞台。组党结社成为一种时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最多时曾达300多个。围绕1913年进行的第一届国会选举,各政党以争夺国会两院议席为目标,以实现组阁为目的,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1913年2月选举结束,国民党获得两院议员总数45%以上,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仍很强大,地主买办阶级决不会允许政党政治在中国实行,对专制统治造成威胁。1913年3月,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在竞选获胜一个月后,就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组阁执政梦想破产,多党竞争敲了丧钟。1914年1月,国会被袁世凯强制取消,各省议会也先后解散,那些各种各样的议会政党也随之烟消云散,中国政治从此陷入严重动荡局面,时人哀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民国初年仿效西方搞多党议会制,是对封建专制的彻底否定,是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一次可贵尝试。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是脱离了中国国情,偏离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其一,缺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国初期除了金銮殿上没有皇帝外,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异常反动和强大,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尚未成长起来,难以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匹敌。其二,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大多数政党是为选举而成立,组织涣散无力,没有也不能对民众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一触即溃。其三,缺乏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政治基础。各政党没有看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根本任务是彻底铲除封建专制,打倒帝国主义,根本出路是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是各党之间恶性竞争、互相攻击,从而给了袁世凯以可趁之机,使多党竞争议会制在中国昙花一现,迅速破产。最初力倡英美多党政治的孙中山不得不改弦易辙,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于1924年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共合作,才使国民党焕发新的生机,中国革命才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了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联盟。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迅速崛起,野心膨胀,从联共走向分裂,并于1927年公开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蒋介石歪曲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和新三民主义理论,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其核心就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独裁专制思想登峰造极,公开赞同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疯狂迫害中国共产党、第三党及其他党派,并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面对国破家亡的民族矛盾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937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虽然国民党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等政党的合法地位,设立了国民参政会,但其骨子里仍然是“限共、溶共、防共、反共”,一党独裁体制并没有实质改变,并多次制造摩擦,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美国《星期晚报》豪塞尔评论说,“蒋氏大权独揽,其地位与昔日之帝王相同”,“称之为法西斯主义,未必完全不符”。[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不愿进行任何民主改革,特别是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强烈要求,顽固坚持独裁反共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并悍然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等革命力量。1948年,召开了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颁布了确立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的宪法。国民党这种自决于人民的反动行为,天怒人怨,日益孤立,遭到彻底失败,最终落了一个被赶出大陆、落荒海岛的结果。
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政体的建立,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也是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社会基础极其狭隘,不能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要求,而是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不断巩固和强化专政独裁政体。在两次国共合作中,不是努力把多元社会的势力容纳到政党和政治制度中来,而是极力排斥中国共产党等党派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参与,阻碍其他政党团体发挥积极的进步作用,从而严重削弱了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合法性,严重阻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其失败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仿效西方多党制的破产和一党专政的失败,充分说明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多党竞争此路不通,一党专政也是死胡同,政党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二、历史必然:多党合作的形成和发展
近现代社会中,社会结构是政党制度得以确立和延续的基础,政党活动则是建立政党和政治制度的决定因素。在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官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是代表一切内外反动势力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两大对抗阶级之间存在着中间阶级和阶层,其中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团结争取的重要力量。阶级关系基本格局的发展演变,形成三种类型的政党,即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等中间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不仅顺应了合则兴、合则成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坚,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的基础、动力和鲜明特色。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把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目标、任务、动力和道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党际关系、探索建立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正确指导。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新中国政治体制,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根基。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不外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三种。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认为,“现在所要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这不仅明确了中国国体、政体的性质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合作最早是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首次合作,开展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共同发动和领导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和中国社会的进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使革命遭到失败。抗日战争时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广泛团结和联合各方面拥护抗日的党派、团体和人士,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战胜利后,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立场,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悍然发动内战,国共合作再次破裂。
“质是与存在同一的直接的规定性,……某物之所以是某物,乃由于其质,如失掉其质,便会停止其为某物。”[19]任何事物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必有其内在质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决定了事物之间的界分。例如,“车”可以有各种形态,包括火车、轿车、牛车、自行车、独轮车等……但是,任何能被称为“车”的事物至少应当具备“有轮子可以滚动行驶”、“能载人或物”等要素,此即“车”的质的规定性。再如,“房”可能是一栋摩天大楼,也可以是一间茅草屋,一口窑洞;但是,一堆土或一堆砖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房”。由此便知,凡是能被称为“房”的事物至少应当“有一定内部空间”,“可以居住”等条件,这便是“房”的质的规定性。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两次合作,体现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合作则赢、分则必败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反映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任务必须实现革命力量团结的内在要求。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各民主党派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新的政党合作、创建新的政党制度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大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结果。从中国民主党派构成的社会基础看,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从中国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看,最基本的是爱国、反帝、民主。从中国民主党派的总体状况看,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不是群众性的政党,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干部集团;政治主张具有多面性,而以进步性、民主性为主导。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民主党派数量较多,但党派人数有限,发动和组织爱国民主运动是民主党派的主要斗争方式,难以形成统一的、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既有一定的进步性,又存在一定的软弱性、动摇性和中间性,其进步性决定了民主党派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其软弱性和动摇性决定了民主党派只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选择,难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所以各民主党派一成立,就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民主政治团结奋斗。
支持民主党派建立组织、开展活动。1941年中间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对国民党失望的同时,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反对独裁和争取民主之必要。章伯钧、丘哲等代表中间党派找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沟通,请中共对将要成立的统一组织给予支持,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随后,中共南方局利用各种资源,竭力扶持、宣传中间党派,并在经济上给予切实援助,使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于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1944年底,一批进步学者在重庆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提倡民主、科学精神,讨论时局,发表政见。为庆祝和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性日子,改名为“九三座谈会”。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许德珩时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你们又都是科学文化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1月“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同年5月召开大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的斗争中互相支持。早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民主抗战、加强党派合作等意见,中间党派参政员积极赞成,不少人联名提出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施民主宪政,使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实行宪政”的决议,并从1940年起,掀起了大规模的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组织各党派参加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热烈拥护,他们或者在各种集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或者以党的《政治主张》《对时局的宣言》等形式,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为使谈判内容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推动,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发表《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提出“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重庆谈判后,中共与民盟进一步协商,正式达成加强合作的“君子协定”。特别是1946年旧政协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充分协商、默契配合、互相支持、步调一致,共同进行斗争,最终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粉碎了国民党分裂民盟、孤立中共、抵制民主联合政府、实行一党专政的图谋。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悍然发动内战。各民主党派坚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共同为推翻三座大山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从产生到合作的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像西方英美国家的政党那样,产生于议会中两个势不两立、激烈争斗的政治派别,也不像西方英美国家的政党那样,以赢得选举、竞争执政权为政党的存在价值,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和发展,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不断凝聚政治共识,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团结奋斗。正是在这个根基上,逐步建立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大厦。
三、基本要素:政治基础、合作机构、政权构成
政党制度是国家法律规定或实际生活形成的政党的社会地位作用、政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政党制度宏伟大厦的构建,不仅需要深厚的根基,还需要支撑的“四梁八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团结奋斗中,不断架梁立柱、增砖加瓦,终于使这座巍峨大厦与新中国一起诞生。
(一)奠定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具有共同认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多党合作一开始就赋予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民主党派也不是自然而然地接受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成员还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在多党合作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品德,越来越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认同,从而把国家前途和民族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后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并在通电中指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说,“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政治决议指出,“中共采取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与本党历来主张的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权则完全相同,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一致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中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指出,“通过新政协会议解决国是,即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各民主党派相继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位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声明,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标志着民主党派放弃了“第三条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
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还体现在具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即共同的政治纲领。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协商建国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与会代表,制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肯定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宣告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明确“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纲领,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多党合作中形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共识,从而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建立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既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础,还需要稳固的机构和形式。周恩来指出,“要合作就要有一个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曾两次进行国共合作,都没有形成和建立制度化的合作组织机构。第一次是实行党内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独立性,但两党始终没有制定共同纲领和设立专门的机构。[4]第二次是实行党外合作,在共同抗日的形势下,出现了两种政权、两种军队、两条路线、两个战场,“两个党在不同的区域内执政、合作,没有建立固定的合作机构,是一种无固定形式、无共同纲领、不完善的合作”[5]。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是随机性的,国民党不允许有组织形式,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内容、方式和机构,从而导致这种合作缺乏稳定性、时效性和约束力,使多党合作经常面临复杂情况和曲折,一旦形势变化就发生变故,最终分道扬镳。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正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非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也是社会上的进步党团,难以建立正式的规范的多党合作机构。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党的领导人主动交党外朋友,与民主党派签定“君子协定”,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政权,形成了经常化的沟通、交流、协商的工作机制和合作方式。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驻地,就成为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交流合作的重要场所。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作为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的职能部门,联系团结协调各民主党派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统战部成为做好多党合作工作的职能部门。尽管如此,要建立新型政党制度,还需要创设多党合作机构,形成稳定规范高效的多党合作机制。
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不仅协商建立了新中国,而且确立了多党合作的机构和方式,完成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创制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指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将长期存在,“政治协商会议主要是党派性的,是党派的联合,人民团体的联合”。也正是在这次会议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进行了充分协商讨论,共同确定了参加会议的单位与代表组成,协商确定了国旗、国歌、国号和纪年,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从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政治协商就成为多党合作的基本方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成为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
(三)确立多党合作的政权构成
建立人民政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基。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各政党活动重心总是放在夺取、参加和执掌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既是共同推进革命的政治力量,也是人民政权的基本构成。1940年7月,毛泽东在纪念抗战三周年时强调,“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普遍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吸收大量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统计,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边区政府各厅厅长到县长、乡长、科长等的任职中,非中共人士共有3592名,其中救国会重要骨干柳湜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从而开创了多党合作中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人民政权的先河,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雏形,并为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作为制度形态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与民主党派在人民政权中合作共事作了明确。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要求,“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在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提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人民在现阶段中国,“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不仅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政治理论准备,也为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政权提供了依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约占30%。新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委,都充分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人士参加人民政权。在政权结构中,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56名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7人。政务院4名副总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2名;15位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等机构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有15人,担任副职的有42人。[6]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全国委员会5名副主席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180名委员中,有民主党派60多人。在行政区和省市政府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42人担任副主席或副市长。[7]从此,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在人大、政府、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就成为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并不断规范化、制度化。它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政权组织形式,保证了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扩大了人民政权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
综上所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遗产的继承,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移植,也不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模仿,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足近代中国两头小、中间大,多阶级、多阶层的社会结构,抓住多党派、多联盟共同推进民主革命的历史机遇,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的规律,在由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历史跨越中,独辟新径、独创新制。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内生性政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