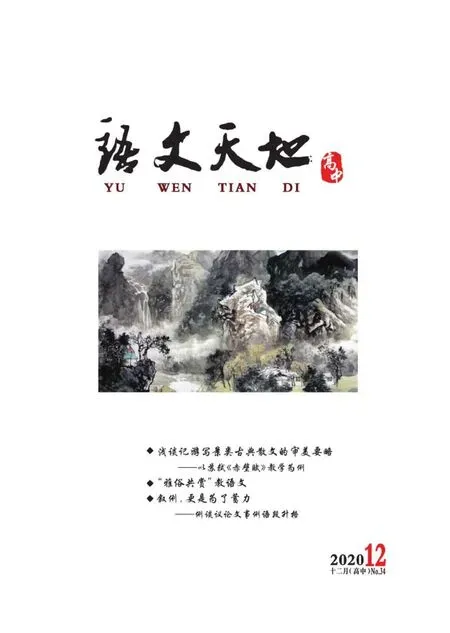打破时序,寻找物象
——谈记叙文构思小妙招
陈 佳
一篇优秀的记叙文往往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形象的鲜明性、构思的巧妙性、主题的深刻性、语言的文学性。形象的鲜明性,往往要通过典型而生动的细节描写加以体现;主题的深刻性,则要从人生、社会、文化等层面加以挖掘;语言的文学性,是长久之功,需要深厚的阅读积累,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构思的巧妙性则可以通过学习借鉴而习得,是考场作文得高分的利器。那么记叙文的构思有哪些小妙招呢?
一、场景的切换——让画面讲故事
学生在写作记叙文的时候,往往喜欢用最简单的一事到底的结构,采用这样的写法,如果能够注意详略,写出事件的波澜,懂得起承转合,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则极有可能写成毫无变化和悬念的文章,如一马平川,让人一看到底,寡淡无味。
好的记叙文是块状的,不是线状的,形象一点说,应该像一串糖葫芦,是一颗一颗的,饱满而有颗粒感。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会用场景的切换来构思记叙文,用一个一个画面讲故事。鲁迅先生的名篇《药》采用的就是典型的用场景的切换来讲故事的结构,从“茶馆”写到“刑场”,再从“刑场”写到“茶馆”,最后写到“坟场”。每一个场景都有其描写的重点,画面感很强。
如作文题《有一种声音》,有一位学生选择的声音是妈妈做藕饼时切藕的声音,那是她觉得最动听的声音。文章写了三个场景——场景一:儿时,母亲在厨房忙着做我最爱吃的藕饼,幼小的我,听着妈妈切藕的声音,缠绕在母亲的脚边玩耍,画面温馨而美好。场景二:我孤身南下,离开了温润的小村庄,尽管在外面也能买到藕饼,但依然无比怀念妈妈做的藕饼和那切藕的声音,画面有一点伤感的味道。场景三:妈妈来城市照顾我,我们在生活上产生了一些小矛盾,那天晚上,厨房又传来妈妈切藕的声音,我瞬间泪目……
文章三个场景,全都围绕藕声在讲故事,虽然侧重点不同,最后都传达出母女之间深深的感情。这样构思出来的文章,画面感强,生动而丰富,比较有可读性。
二、插叙的运用——让时间慢下来
在每个孩子学习写作的最初,老师就教大家按照时间顺序把事情写清楚,但是后来,学生按照时间顺序写出来的文章往往又被老师批评:流水账!那么怎么办呢?除了注意详略得当之外,有没有更巧妙的方法来避免这样的困境呢?我们可以运用插叙的手法,切断时间轴,把整个时间线上的事件进行重组,从而让时间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短篇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就是描写一位受伤的士兵被抬进临时改为战地医院的他的母校的过程,中间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插叙了“我”的回忆与反思,那一刻,时间停了下来,准确地反映出纳粹德国时期青少年真实的思想状况。
如作文题《等待》,有一位学生写作的主题是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当我们飞奔向前追寻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也要等一等我们身后的年迈的家人。他这样构思他的作文——时间一:眼前,一位学骑自行车的小男孩,摇摇晃晃从远处骑车过来;时间二:插叙回忆,我小时候爷爷教我学骑自行车的情景;时间三:回到眼前,小男孩后面跟着一位年迈的老人,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时间四:插叙回忆,那时候爷爷拿着大蒲扇跟在我的自行车后面,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进而很自然地引出主题:我们在追风逐梦的时候要等一等,回头看一看身后的亲人。
这篇文章所描写事件的现实时间只是学车小男孩从远处向我骑来又远去的一两分钟,但是作者运用插叙的手法,让时间慢了下来,有了时空的穿梭,产生了纵深感。这样的构思,就巧妙了许多。
三、物象的选择——让情感可触摸
学生写起记叙文来首先想到的便是写人、记事,期望通过人物和事件来表达某种情感,而往往忽略了非常重要的“物”。一篇记叙文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物象,或作为情感的载体,或作为人物的映衬,都非常有意义。就事件而言,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寻找到情感的凝聚物,可谓“我寄愁心与明月”,使得抽象的情感有了可触摸的物化的对象,就更加形象可感了,这里的物象可以是一个物件、一种花草、一支歌曲,等等。
如现代作家肖复兴的散文《喝得很慢的土豆汤》,文章所要表现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浓浓的亲情。文章多次提到喝土豆汤的场景:“那一次的土豆汤,我们喝得很慢很慢,临行密密缝一般,彼此嘱咐着,一直从中午喝到了黄昏。许多的味道,浓浓的,都搅拌在那土豆汤里了。”“那一天下午的土豆汤,我们喝得很慢。”“那一个下午,我的土豆汤喝得很慢。”“我看见,小姑娘和她的爸爸那一锅土豆汤也喝得很慢。”作者把这种亲情浓缩在一碗又一碗的土豆汤里。在喝土豆汤的那一刻,作者说:“亲情,在这一刻流淌着,浸润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
你看,找到了情感的凝聚物,使得亲情这样的较为普通的主题,讲述起来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抓手,也能翻出新意,打动人心。
就人物而言,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寻找到一个和人物互相映衬的合适的物象,两者相得益彰,可谓“人面桃花相映红”,使得人物更加形象鲜明,丰富饱满。
如作文题《味道》,有一位学生描写老房子隔壁住着的一位姓沈的姨娘,这位沈姨数十年如一日地等着她外出经商的丈夫。她不爱笑,但又对身边的孩子充满暖意,她坚强独立,又总带着微微的苦楚。为了把这个人物的味道写出来,作者特意在沈姨的门口“种”上了一株腊梅,“沈姨家的院里栽了一棵孤零零的腊梅。每逢年前的那些天,便都争相绽开了琥珀般晶莹的花瓣。幽幽的冷香拂过每一片屋瓦,萦绕在冬日灰沉沉的空中,经久不散。沈姨便是一个像腊梅一样的女子。”“沈姨只是静默着,不争辩,不回应。渐渐地,当流言平息,沈姨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话语,像是那株腊梅,只独自开在角落里。”“那腊梅香总是浸得沈姨空落落的,却也有着固执和坚强。”在这篇写人的文章里,作者找到了与主人公沈姨的形象具有精神契合点的梅花,作为一个物象巧妙地植入文章中,使得人物的形象特点更加鲜明生动,让人仿佛看到了沈姨的孤独与坚贞,嗅到了沈姨的苦涩与幸福。
其实在学生的日常习作中,用物象来烘托人像,这样的构思并不少见:有学生想要表现乡下的奶奶如何热爱她的土地,热爱劳动,就把沉甸甸的麦穗形象和奶奶弯腰劳作的形象放在一起写;有学生要描写正直刚正的爷爷,就用爷爷常用的笔直有力的钢笔作为文中的重要物象和爷爷的形象放在一起写……物象的运用,既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又映衬了人物的形象,是很巧妙的构思。
记叙文写作构思的巧妙性,是记叙文写作尤其是考场记叙文写作非常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直接影响到文章的可读性,需要学生在平时写作中反复实践和探索,相信会有更多新的创造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