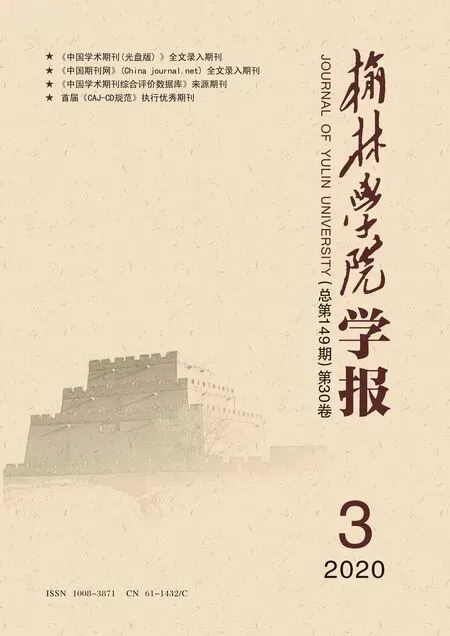单振国小说的救赎主题及其可能性
杨静涛,加纯华
(1.榆林学院 文学院;2.榆林学院 艺术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一、引言
单振国最初是以散文创作开始他的文学之旅的。如果从1991年10月4日发表的处女座《从来……》算起,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其间,笔耕不辍的单振国已经出版了《土地的歌谣》《幸福树上的鸟》《美丽的陕北》三部散文集。
单振国的散文对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和劳作在这块厚土上的人们寄予了炽热的感情,炽恋的爱意。他笔下的黄沙、密野河、二郎山、窑洞,是他骨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艺术创作中化为地理图式的精神符号,散发着一种人情化、人性化、人格化的诗意般的审美意绪。他的笔下,那唱信天游的陕北女人们“不怕穷,藐视强权和金钱”,“她们热爱这片生身热土和这里的男人们,热爱他们以不倦的劳动与创造张扬出的生命风采,热爱他们以蓝天的高远和大地的憨厚播下的信天游。”[1]那唱信天游的陕北男人们“颧高鼻直,腮长眉浓,能歌善舞,坦率豪放,渗透着一种游牧民族的天然个性”,他们“都有一股吕布的英雄气,手持方天画戟,飞扬跋扈,勇冠三军,藐视天下英雄,敢为爱情舍生忘死。”[2]在单振国笔下,陕北的男女老少都有一股雄强、豪放、爽朗、率真的精神和气质。他写人被自然、社会挤压、胁迫、强扭,被贫困、饥饿、孤独束缚、侵蚀、吞食;写人生存的坚韧与生活的卑微,写卑微中的自尊,弱小中的坚毅,孤立中的坚守,血污中的抗争。正如散文集《美丽的陕北》书题所显示的,单振国的散文是对陕北客观、真实的写照,是对陕北人的认识、描写、赞美和歌颂。
单振国以一只“幸福树上的鸟”的婉转歌喉,尽情歌唱着古老“土地的歌谣”,诚心竭力地赞美着脚下这块“美丽的陕北”大地。这些情感与意识,思想与精神共同构成了单振国散文创作的底色,也建构了单振国整个文学创作的精神世界。
之所以在评论单振国的小说创作时论及他的散文创作,是因为二者之中始终贯穿着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践行着他的文学观念。
二、救赎书写与罪感意识
单振国尝试过多种题材的创作,其小说题材也更为多样化。他的小说有对历史的挖掘,如“故事新编”《吕布之死》,全然虚构的《红颜之战》及叙写革命传奇的《为了和平》《抗日狗》《黑龙山传奇》,也有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如展示乡村的《过年》《山嫂的故事》《母狼》,描写城市众生的《应承》《放贷》《母亲的手铐》《缴钱不杀》《鸽子找妈妈》,讲述爱情往事的《一样的月光》《唢呐情》《今夜,心雨霏霏》,甚至还有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宇宙树》。
细读单振国这些不同题材的小说,不难发现它们大多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文学母题——救赎。
《一样的月光》是一篇纯净的爱情小说。单振国将一段师生恋写得唯美、极致、浓烈。小说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64年的爱情故事。陕北青年肖玉峰在大学毕业前的劳动实践中与刚参加工作的小程老师相识、相知、相恋,毕业分配时小程老师帮助他争取到了留校的名额,但是割舍不下亲人和故土的肖玉峰还是忍痛不辞而别,返回了陕北,结束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使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与对话激情饱满、感情丰沛。单振国将他的抒情能力很好地呈现在作品中,美丽、诗意的月儿湖,安静、辽阔的渭北平原,把一个青春凄美、忧郁又不失躁动、激荡的爱情故事衬托得越加完美与触动人心。小说汪洋恣肆、文采飞扬,既有对逝水年华的追忆与眷恋,也有陕北男人旷达与坚毅的情怀。整个故事在“很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结束,勾连了之前发生在师大校园里的预谋对老校长的批斗、小程老师父亲高官的身份以及小说开头肖玉峰捐资百万在月儿湖修建学校时所说“是为了纪念一个人,代她完成一桩几十年前的心愿”等细节。短短一句话的结尾欲说还休,营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如何猜度小程老师命运都不为过的浓重悲剧氛围,给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预留了沉重的想象空间,也为肖玉峰的救赎提供了更多的心理依据。交织在这个爱情故事中的已开始酝酿的大批判与随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既作为疯狂时代背景而存在,又成为在场并未出场的人性展示的舞台,因之,《一样的月光》又不仅仅是对纯美爱情的救赎,作为一种强烈的对比,肖玉峰几十年后的捐资助学其实是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唤和救赎。
小说《应承》讲述的是关于“承诺”的故事。许二瓜对何二寡妇临终前的应承、刘顺对为保自己而进了局子的老哥们的承诺构成了小说的主线,两个关于“应承”的故事在交互穿插中编织、汇聚成一个让人动容又无地自容的感人故事。为了一句应承,许二瓜离开生活了五十年的村子,进城谋生活,给何二寡妇在上海读大学的养女按月打伍佰块钱。同样为了一个应承,刘顺重操旧业,年轻而苍老的生命唯一的支撑就是给一个汇款本本里按月打钱。春节来临前的大雪之夜许二瓜对离“家”已久的刘顺的想念和担心让我们感动。我们的感动不仅来源于老人深深的孤独感,更来源于老人和刘顺这两个底层生命间互相依靠,互相温暖——正是这种想念,这种依靠,这种温暖,让他们相濡以沫,共御寒冷——既有自然界的寒冷,也有社会的寒冷。伴随着老人日益深沉的想念,我们也禁不住想念起流浪汉刘顺来,想念起在寒风中“挣扎”的刘顺来,即使我们已经隐隐地知道,就像老人所隐隐地感觉到的一样,他是一个偷盗者。在诚信缺失、信任危机的现代社会,老农民许二瓜和流浪汉刘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让这种可贵的品质闪闪发光。这些底层人物明亮的、富有光彩的内心世界,同他们所身处的黯淡无光的生存境遇,形成鲜明的对照,让我们不禁在感慨中认真思索。
《放贷》是一篇更为切近现实的小说。神府一带经济高速发展的“盛景”催生了民间借贷的疯狂:全民借贷,所有人都被裹挟到民间借贷的暴利场中。连小说中以吃低保,打零工过日子的王绿豆和老乞丐马四娃这样的底层弱势群体也无例外。王绿豆把村里卖地的分红、女儿的聘礼和自己辛苦积攒的8万块钱求告着放给王金罐,他没有大的妄想,他只盼着能多吃点利息,为女儿置办像样的嫁妆,给智障儿子娶媳妇,给残疾的老伴治病。马四娃把乞讨半生攒下的6万块钱也拿出来放贷,他要尽快攒够钱赶在死前修整庇佑了他十几年的关老爷庙。王绿豆的盘算很实际,也无奈,但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马四娃就是想还个心愿,知恩图报,感谢关老爷的照应。王金罐携款跑路,民间借贷的风险完全转嫁在每个放贷者身上。王绿豆和马四娃的辛苦钱瞬间蒸发,血本无归。马四娃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栖身的破庙,给王绿豆留下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也照亮了王绿豆,他顾不得心疼自己的损失,心心念念要弥补对于马四娃的“过失”。在被问到有什么困难时,他希望政府能够尽快修缮破旧的关老爷庙,因为那里还住着一个讨吃老汉。小说结尾王绿豆突然响起的掌声,犹如一记耳光实实在在打在所有人的心上。
而长篇小说《亲亲的山峁亲亲的水》可以看做是单振国对救赎主题的集中书写。依靠新时代的新政策,青年农民陶永亮意外地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从此,这个身价变了,身份却无法改变的人物,走上了一条色彩丰富、秩序却有点儿混乱的生活道路。小说开头,陶永亮从县城回到村里,本来是带着一种 “出出积在心里已经有十多年的恶气”的报复心理,但最终被亲情、乡情打动,他有了带领龙池湾人脱贫的要求,愿意主动帮扶父老乡亲共同致富。陶永亮身上蕴积的中国农民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和良好品质也体现在与三个女人情感的纠葛中。对胡美丽这个“婆姨”,陶永亮虽然接受不了她的粗俗和恶习,最后却也反省自己不要过分,尽量体谅对方。对田水草,他虽然一直有“非分之想”,但并没有真正的“非礼”,特别是没有利用金钱而去占有的欲念。对于受到自己资助读完大学愿意以身相报的何丽娜,陶永亮最终以“兄妹”相待。胡美丽、田水草、何丽娜既让陶永亮的生活陷入不同程度的迷乱,却也从中见出这些普通人身上坚守的原则——善良和责任。小说结尾有一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当陶永亮为了替受辱的田水草报仇而犯下命案进了监狱后,前来探监的田水草仍然向他表达了继续带丈夫求诊的愿望——她愿意和陶永亮一起打拼的原因,就是要为瘫痪在床的丈夫寻找生活的依靠。陶永亮失望的表情背后,闪现出的却是人性的最后的光芒。
在其它作品中,单振国从不同角度延续着对“救赎”主题的讲述。《唢呐情》是对纯美爱情的救赎,《缴钱不杀》是对纯净心灵的救赎,《朋友大楷》《山嫂的故事》《女儿》《谁之错》是对人间温情的救赎,《鸽子找妈妈》《过年》《一片苦心》是对家庭的救赎,《看看儿子的事业》《潇洒走一回》《飞向阳光的信天游》是对淳朴世风的救赎,《红日熔金的秋天》《心内心外看桃红》是对高贵精神的救赎,《母亲的手铐》是对母子之爱和责任的救赎,《母狼》《祁连山剿狼》是对“底线”的救赎,对世道人心的救赎,《黑龙山传奇》《抗日狗》是对民族气节的救赎……即使在只有千余字的微型小说《最后的面试》中,也充溢着救赎的主题——对“礼”的救赎,对操守的救赎。
这个救赎的文学母题使单振国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心灵闪闪发光,细读这些作品,不难发现,所有人物的自我救赎均来自于某种特定的“罪”。因“有罪”而生“救赎”成为单振国这一类小说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
刘再复、林岗将罪感形容为“欠了债似的感觉”,陈刚认为“所谓罪感意识,其实根植于古老的灵肉冲突,根植于人心中的价值理想与肉体感官欲望的冲突……从而造成人的内心冲突和精神痛苦,使人有这一种沉重的犯罪感……”徐威则认为罪感意识是“个体对内心深处生成的罪恶感的一种认知。这种罪恶感可以是具体对某人、某事,也可以是对社会、历史甚至整个人类负有罪感和愧疚”。
肖玉峰毅然放弃了小程老师为他争取来的留校机会,也放弃了他们的爱情,不是他不想留校,不是他不爱小程老师。“自己之所以有条件来念大学,除了父母一直支持外,还有村里乡亲们的帮助,是他们这家一升米、那家一块钱地把我送进高中、送到大学,直到今天毕业。如果没有乡亲们几年来对我无私的帮助和鼓励,我是万万不会有今天的。乡亲们希望我能够学成归来,为他们的孩子当老师。直到现在,在我们乡镇里还没有一个真正从师专院校毕业的老师,有不少代课老师仅仅是个初中学生,甚至还有念三四年小学的人在代课,教育质量可想而知。”这一段“语气和情感十分恳切”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肖玉峰的“罪感意识”:对于家人和乡亲们多年来供养他读书的一种愧疚感与负债感,以及由此而生的报恩与责任担当。
三、“救赎”的有效性
“救赎”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词语,一般来说涉及到人的灵魂的堕落与拯救,罪恶与忏悔,天国与来世等等。本文使用的“救赎”这个词,虽然没有宗教内涵,但是也必然与生命的存在危机与终极归宿也有着紧密关系。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可以说需要救赎的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是人的诗性精神,二是一切生命共有的家园,核心就是对生命的救赎,对生态和谐的救赎。植根于大自然的“生命文化”逐渐异化成了植根于技术、资本和权力的“死亡文化”,在“死亡文化”指引下的人类实践活动,悖逆自然之道,不断破坏自然生态,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道德危机,“生命之网”蜕变为“死亡之网”。人类丧失肉体和灵魂的双重家园,处于无根而危险的生存状态中。人类从肉体到灵魂都需要救赎。
从散文创作对“美丽的陕北”的赞美到小说创作对心灵的救赎,单振国见证了陕北由贫穷到富有的巨大变化,也让他看到了繁荣背后道德、精神的滑坡与缺失。单振国的小说传递的是“向善、向美、向真”的伦理观念,“用小说这个文学样式来呼唤、救赎、弘扬生活和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就成为他对文学的追求,成为他小说创作的动因。正是基于这种“呼唤、救赎、弘扬生活和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的文学追求和创作动机最终形成了单振国小说的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的根本,关涉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作家有怎样的世界观,他的作品就会有怎样的叙事追求和精神视野。刘小枫指出:“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3]单振国的小说在展示陕北人生存境况的同时,常常以老人、女性,甚至是儿童作为叙述主体,以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善与美完成救赎故事的讲述,实现了他用真、善、美的伦理观念来救赎日渐麻木的现代人的心灵的创作愿望。救赎是源于对精神危机的忧虑,对道德沉沦的批判。在单振国看来,导致精神危机和道德沉沦的根源即在于人们“唯钱而崇拜”的心理,“钱把(使得)道德、良知严重沦丧”。他的相当一部分小说中金钱成为必不可少的叙事元素,用以制造人物个体性的道德境况。《应承》《放贷》《缴钱不杀》《过年》《一片苦心》《谁之错》等无一例外。当然,金钱并非万恶之源,金钱既是作品中不同人物生活的目标,是他们背负精神负重的因由,同时也是他们实施救赎的工具。肖玉峰(《一样的月光》)、刘顺(《应承》)、王绿豆(《放贷》)、姜永昆(《谁之错》)、诗人、歹徒(《缴钱不杀》)都走在这条路上。
单振国小说救赎主题背后隐含着的是对现实的批判。从纵向来看,通过对历史的演绎来彰显道义、气节的力量,以传统伦理的呼唤完成对现代伦理的质疑;从横向来看,通过对农民故事的讲述来弘扬善美、责任的价值,以乡土伦理实现对城市伦理的批判。单振国的小说创作从伦理层面对现实进行反思,从中烛照现代伦理与传统伦理、乡土伦理与城市伦理间二元对立的结构矛盾与伦理冲突。两相对比中,最终都凝聚为一个明确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即对自然、善美人性的肯定与褒奖,对一切扭曲、异化人性健全生长的伦理观念的突围与释放。
通过这种突围与释放,小说中的人物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个体救赎,而通过这种肯定与褒奖,单振国也完成了他对建构和谐、健康的社会伦理秩序的一次艺术实践。
总体上看,单振国的中篇小说比短篇小说好。中篇小说《一样的月光》《应承》《放贷》在故事的讲述中注意环境的描写,情境的渲染以及人物心理的刻画,营造一种整体的氛围,通过故事的铺陈讲述一步一步走向某种意义的表达。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对叙述节奏的把握和人物行动心理描写的驾驭稍欠火候。《宇宙树》《过年》《一片苦心》等更像是一通未经文学加工的“大白话”,作者似乎总是从故事一开始就急于奔向结尾的主题宣示,失去了其中篇小说叙事时的耐心,预设的主题催促、拉扯着人物急速行走,情节推进表面、单一,人物的心理描写,性格塑造等略显粗疏平面,故事也随之硬化,作品几近主题与观念的演绎,导致作品内蕴太过明确,缺少了更多可供阐释的空间和咀嚼的韵味。
这些缺陷,自然首先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经验与写作技巧的不足,但究其根由,还是与作者的叙事伦理有关。在通读他的全部散文与小说作品之后,我不能怀疑单振国对于创作的真诚。不过,坦率地说,我并未获得阅读的满足。仅以传统伦理、乡土伦理来否定现代伦理、城市伦理的二元价值判断,既失之于简单、粗暴,又过于轻率——以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来实现对自然、善美人性的肯定与褒奖,对一切扭曲、异化人性健全生长的伦理观念的突围与释放,是一时之效,还是长久之功?若是“一时之效”,那么“救赎”如何成为可能?如是“长久之功”,又如何理解如今的诸多社会乱象?张爱玲说生活远比小说更富于传奇性。生活是如此复杂,蕴含着无限的可能,简单化的处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复杂的世界,需要一种复杂的形象和复杂的精神来诠释它,这是小说的基本使命,也是小说所要面对的艺术难度。假如小说不再表达复杂的世界,而只是像故事的那样专注于单一、贫乏的经验,那么小说的存在就将变得可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