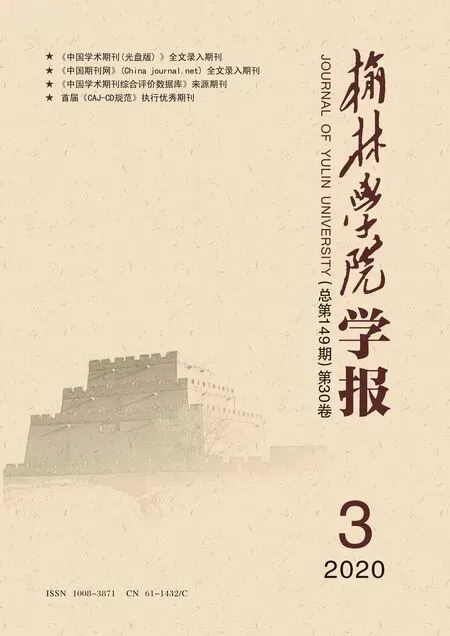论《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物原型
曹雪花,马德生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人生》以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为中心,讲述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奋斗之事和情感之事。小说自发表以来,人们对高加林形象的研究不计其数且褒贬不一,但在对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研究中,学术届一致认为高加林的原型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但是在阅读有关路遥的资料和相关论文之后,笔者发现高加林的原型为路遥本人,或者说更接近路遥本人的经历,而王天乐的人生经历是路遥创作《人生》的催化剂。无论在生活经历,情感态度还是思想状况方面,高加林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路遥本人。
学界将王天乐作为高加林的原型,常常引用王天乐的话作为依据。“见面后,我们长时间没有说话,吃过晚饭后,他才对我说,你可以谈一谈你的个人经历,尽可能全面一点,如果谈过恋爱也可以说。于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展开了长时间对话,一开始就三天三夜没睡觉。总共在这里住了十五天。他原打算刚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写一篇小说叫《刷牙》。但就在这个房间里,路遥完成了中篇小说《人生》的全部构思。”[1]由此来看,路遥与王天乐的交谈加速了路遥创作《人生》的进程,并且王天乐的人生经历也为《人生》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在厚夫的《路遥传》中,厚夫也曾提到:“王天乐所说的路遥在这次‘激动人心’的兄弟晤面时,完成了中篇小说《人生》的全部构思不是事实。现有的资料证明,路遥早在1979年就开始创作这部中篇小说,不过写的很不顺,一直写写停停,但王天乐的人生际遇给路遥创作《人生》提供了灵感。”[2]也就是说,王天乐的人生经历为《人生》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动力而并不能说明王天乐为高加林的原型人物,王天乐的人生际遇使路遥联想到了整个中国农村有志有为的青年人的命运,路遥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深有同感,并由此创作了此篇小说。
另外,在路遥、王愚《关于<人生>的对话》一文中,当王愚问及路遥在创作高加林的人物形象时,是否有原型时,路遥说他家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的弟弟就是高加林这样的人[3]。在对话中,路遥只提到原型是他的弟弟,但并未明确指出是他的哪一位弟弟。更为有力的是,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就明确地指出了《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的原型是王天乐。“尤其是他当过五年的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4]。众所周知,路遥为帮助他的弟弟王天乐走出农村六次写信给曹谷溪,并托好友在中间周旋,最终在谷溪的帮助之下,王天乐以延安县的农村户口被招到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当采煤工人,实现了走出农村的第一步。王天乐的煤矿生活为孙少平的人物创作提供了借鉴,孙少平的煤矿生活直接来源于王天乐的经历。“研究路遥年前后写给谷溪的六封书信,我们可以解读到一个具有‘多面性’性格的作家路遥。一方面 ,他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帮助弟弟王天乐改变命运另一方面,他又从王天乐的处境由己度人,深人思考中国广大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的出路问题,催熟了中篇小说《人生 》,甚至为日后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找到了现实灵感。”[5]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引用、梳理和分析,笔者发现王天乐是路遥创作《人生》的催化剂,并非是高加林的人物原型。那么,高加林的人物形象来源于谁?
一、生活经历角度
从生活经历上来看,高加林与路遥的生活经历极为相似。在文革期间,路遥从生活的最底层一跃成为县城中的风云人物,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但是,生活向路遥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68年底,延川县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路遥作为县革委会副主任首当其冲,路遥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被迫接受现实接受高强度的劳动。回乡之时,他恰好赶上大队的打坝修水利。在寒冷的冬天,路遥拿着几斤重的撅头,一言不发,用高强度的身体劳动表达着自己的悲愤,控诉着命运的不公。恰巧,高加林在教师职位被顶替不得不回乡劳动时,高加林的反应与路遥的态度如出一辙。被顶替的高加林在回家之后苦闷、抑郁、愁眉不展,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他通过强大的劳动量来折磨着自己的身体、释放着精神上的抑郁。在劳动的时候,“他就把上身脱个精光,也不和其他人说话,没命的挖起了地畔。……泡拧破了,手上很快就出了血,把撅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的干着。大家纷纷劝他慢一点,或是休息一下再干,他摇摇头,谁的话也不听,只是没命地轮撅头……”[6]由此来看,高加林发泄愤怒的方式与路遥极为相似,且都是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来释放自己。虽然身处农村,但是路遥对国际的时事政治极为了解。在1968年冬天的打坝造田时,“路遥几乎不说一句话,可在这个时候他却显得十分活跃,他常常成为谈话的主角,谈论国际新闻时事,谈论西方国家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的斗争……他那渊博的知识,使我这个比他高两级的学生不得不自愧弗如。”[7]路遥善于把握实时动态,积极了解国家大事,只要提及国家大事便侃侃而谈。同样,深处农村的高加林在高中时期就关注着国家大事、国际动态。在高加林被迫去县城卖馍的时候,他也不忘去县文化馆阅读报纸以了解时事,尤其关注国际问题。不仅如此,他还曾希望进国际学院读书。由此看来,高加林的发泄方式和兴趣爱好与路遥极为贴近。
二、婚恋观念角度
在感情问题上,高加林与路遥都是以功利性的态度来对待爱情与婚姻。登上过人生“巅峰”的路遥已不满足于农村身份,他要走出去,奔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而实现这一目标,唯有借助外力——北京知青。所以他在选择交友对象之时,委婉拒绝了农村姑娘的追求而毅然选择了北京知青林虹,并且全心全意地对待林虹,但林虹有了正式工作之后却与路遥分开了。失恋的路遥曾绝望过、自杀过,但是痛定思痛之后,他为自己“披麻戴孝”以告别曾经的自己。一次的失败不足以打倒他,即使遭众人反对,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想找个北京知青作为婚恋对象。海波曾劝他找一个本地人比较稳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捡。但他一听生气了,反问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么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11]路遥对待爱情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他不仅是在选择一位婚恋对象,也是在选择一种人生道路。其实,路遥在农村的时候被延川中学的姑娘表白过,但是被他拒绝了。当时“路遥生性强悍,但在这方面却不行;加上当时正为自己的前途着急,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于是就和那女子打开了‘马虎眼’:首先告诉女孩子说:‘我也是平常人,那个副主任职务只是个‘名’,一离开学校就是农民。那女孩子答:‘你是农民,难道我不是?我就喜欢农民。’王卫国又说:‘我啊,农民也不是个好农民,耕不了地,下不了种,庄稼活十样里面九样不会。’那女孩子又答:‘你不会我会,地里的活都有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待着,什么都不要管。’王卫国一听大惊,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那女孩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12]
路遥为了实现“人生飞跃”的目标而婉拒了农村姑娘的表白。这一幕不得不让人想起了高加林与巧珍,巧珍一直暗恋着高加林,默默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处处为高加林着想。在帮高加林卖馍回家的大马河桥上,巧珍劝高加林留在农村发展,高加林半开玩笑地说:“我上了两天学,现在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当个农民,劳动又不好,将来还不得把老婆娃娃饿死呀!”巧珍说:“加林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待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13]高加林婉拒巧珍地口吻与路遥婉拒农村姑娘的口吻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路遥拒绝了延川女同学的表白,而高加林接受了巧珍的表白。虽然高加林接受了,但是他一直在提醒自己,一旦这样,自己就真的成为农村人了。他时不时地为自己的冲动而后悔自责,以至于在去县城之后,高加林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还是将巧珍抛弃而选择了对他人生之路更有利的黄亚萍。黄亚萍承诺给予他更大更广阔的天地,那就是以后有机会去更大的城市——南京成为真正的记者,以施展他满腹的才华。不仅如此,黄亚萍在生活上也满足了高加林的自尊心,使他彻底摆脱了农村的气息。黄亚萍为高加林买最好的衣服,搭配最时兴的成衣,与高加林过着最时兴的恋爱生活。黄亚萍是高加林实现人生飞跃的跳板,或许他并不爱黄亚萍,他所爱的只是黄亚萍所代表的城市阶层身份。从这一点上来看,高加林的爱情又何尝不具有功利性呢?
三、思想性格角度
在“第十五讲评介《路遥创作年表》时,程光炜先生说,他发现路遥因童年时期不幸的经历养成自卑又自负的性格”[14]。路遥从小家境贫寒,因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被过继给伯父。但贫困依然缠绕着他,穷是生活的常态,家境的贫寒使他从小形成了自卑的心态,直到成年中年,自卑都不曾离开他一时一分一秒。为了掩盖他的自卑心态,物质成了最好的选择,他不讲究吃穿,但是他特别喜欢抽高档烟,喝洋咖啡,尤其在创作的时候,嗜烟如命,非好烟不吸。曾经不止一位朋友这样劝他,但都无济于事,都被他反驳回去了。海波曾劝到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抽三四块钱一包的烟,每天最少两包,一月光烟钱就得花掉两百块钱,而他每月的工资仅为一百多块钱,还不够抽烟。就此,我多次建议他把烟的‘档次’降下来,至少做到量入为出。不同意,说,这不是生理上的需要,而是心理上需要;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而保持庄严的心情,为的是进行庄严的工作。”[15]香烟是身份的象征,路遥要用香烟满足他心理上的需求,以填补物质上贫瘠,慰藉精神上的缺失。幼年经历造成的自卑心态是伴随一辈子的,不管今后的生活是富是贵,自卑感无法被消磨。心理学上说,人的某种习性往往是与他维持自身的某种强大有关。路遥嗜烟如命也可能与他过于自卑而导致追求内生的自尊有关,香烟是他的自尊,所以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也要抽高档烟来维持自尊。
高加林何尝不是自卑又自负的呢?高加林的自卑来自高明楼等人的金钱上的压倒性优势,他只能通过自我安慰的方式来试图用精神上的富有战胜高明楼等一类人。他的自卑还来自于张克南等人城市身份上的绝对性优势,他只能用躲避的方式来逃避现实。高加林是自卑的,他的自卑与路遥一样都是来源于穷,一贫如洗的穷。路遥是用烟、咖啡来掩盖自卑,而高加林则是用穿用自负的心态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在县城时,黄亚萍将高加林从头到脚装扮一番,咖啡色大翻领外套,天蓝色料子筒裤等等,全都是上海出的时兴成衣。高加林乐意黄亚萍对他的“改造”,他的穿着代表了他的身份,代表着他摆脱了农村的烙印。他的装扮既掩盖了他农村身份的自卑感又满足了他的自负心理。从思想性格上来看,高加林的自卑又自负的心理状态与路遥本人的心理状态十分贴近。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活经历、婚恋观念还是从思想性格上来看,高加林的这一人物形象直接来源于路遥,而非其弟王天乐。路遥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出发来塑造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这使得高加林的人物形象更为鲜活生动。路遥对《人生》的写作不只是他本人的一次文学疗伤,而是以作家之责,用他自身的生活经历为样本,以点及面,将上世纪80年代农村知识青年的现状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继而来抒发农村知识青年被限制在黄土地的惆怅悲愤之情。高加林的进城之路,从道德的角度评判,他无德面对家乡父老;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做法虽有欠缺但无可厚非。用程光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路遥早先的不幸经历,一句话,就是穷怕了,所以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高加林只要能离开穷的没有指望的农村,使出什么手段都可以。”[16]《人生》虽然没有为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知识青年提出一条明确而又具有可行性的人生之路,但是故事的结尾已然给出了世人答案。《人生》结尾处写到“并非结局”,确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知识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他们尝到过城市的“甘甜”,品味过农村的“苦涩”。城乡差距像一根针似的扎在农村人的心间,走出农村,奔向城市已然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即使在前进的道路上障碍万千,阻碍重重,但这也不能成为他们甘心留在农村的借口,高加林如此,路遥亦如此,千千万万高加林式的人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