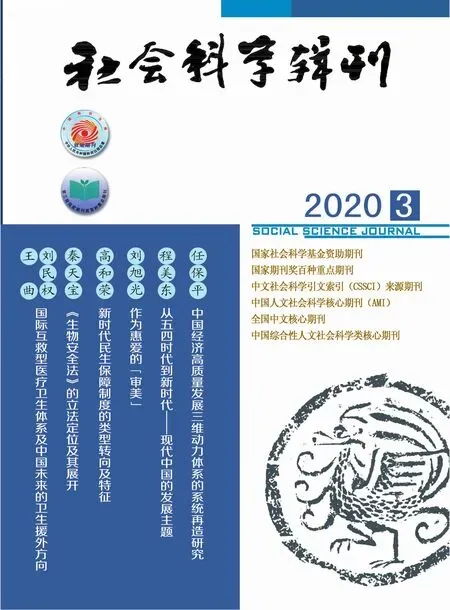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何以客观?
赵 磊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范畴究竟有没有客观实在性?这个问题的导向意义在于,自庞巴维克以来的庸俗经济学家,以价值与价格的“不一致”为由,断言劳动价值论“是以精细的虚构哲学的外衣出现”〔1〕,指责马克思凭空捏造出劳动价值论以及价值范畴。针对有关价值与价值形式“不一致”的指责,我提出了“价值不能直接量化”〔2〕的命题。然而晚近以来,关于价值与价格不一致的指责依然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所秉持的基本论据。①比如,晏智杰说:“企图在价格之外还去寻求什么价值,不过是搞神秘主义。事实上,劳动价值论所说的价值不过就是市场价格的一种即长期的稳定的价格而已,因而我认为价格和价值这两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等价的’。”晏智杰:《本本主义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经济评论》2003 年第 3 期。有人甚至以现象学关于“现象之后根本不存在别的事物”〔3〕的主张为依据,指责马克思对本质的追问。我认为,这些指责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视。因为在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观点中,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理由:既然价值与价格不一致,那么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又在哪里呢?因此,如何理解价值的客观实在性,这个问题不仅是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难以理解的困惑,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思维必须面对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围绕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展开了六个问题的讨论:第一,价值对象性;第二,两种价值量;第三,波函数坍缩与价值测量;第四,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第五,“社会过程”与“价值决定”;第六,现象学并未否定对本质的追问。
一、价值对象性
马克思说:“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4〕“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5〕在我看来,若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想理解价值范畴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马克思关于价值范畴的定义很明确,也很深刻:商品价值的实体“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6〕;价值是商品社会性质的“内在规定”,而价格则是价值的“外在形式”而已。换言之,价格是价值显现出来的状态。所谓状态,就是事物的具体形状、形态,是事物的外在表象。马克思为什么特别强调商品价值的“内在规定”(抽象劳动)与“外在形式”(价值形式)的区分呢?因为价值形式遮蔽、掩盖了价值的存在,甚至歪曲了价值的本质。以致于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断言:价格与价值本身就是一回事,就是“均衡价格”,没有必要把二者区分开来。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与价格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说:“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7〕什么是指数?所谓指数,就是“数量变动的相对数”。既然“价格是价值量的指数”,那么价格与价值在数量上就不会完全一致。马克思的价值范畴要揭示的谜题之一,就是价格与价值为什么会不一致。
马克思对价值的定性虽然极为深刻,但问题是,价值的本质恰恰是人们理解价值范畴最为困惑的地方:既然价值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那么,人们又凭什么确定价值是价格的本体呢?既然价格与价值并不一致,那么,人们又如何通过价格去把握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呢?对于这个困惑,马克思有着丰富的论述。在 《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章中,通过对价值形式的演化过程的辩证考察,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商品的价值对象性。马克思说:“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8〕
这段话中的“价值对象性”,既是理解的难点,也是理解的关键。什么是“对象性”?马克思说:“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9〕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 卷这句话的页注中,第一版的译者给出了一个注释:“对象性的原文是 《Gegenstandlichkeit》,意思是:客观现实性,客观存在的东西。”〔10〕由此可见,所谓“价值对象性”,是指商品价值的客观实在性,通俗讲就是商品价值所具有的“看得见”“听得到”“摸的着”的“可感知性”。为什么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即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具有幽灵般的神秘性?在马克思看来:第一,因为“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所以“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可见,价值对象性不是“实体范畴”,而是“关系范畴”。第二,既然价值对象性是“关系范畴”,那么,只有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关系”(在货币产生之后,这种交换关系就是“价格”),价值对象性才能呈现出来。第三,既然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不是物质实体性的),那么,价值对象性就有着幽灵般的神秘性。价值之所以“总是不可捉摸”,道理就在这里。第四,虽然“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但是,人们直观感知到的价值对象性却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形态(即自然物质的原子)。这也正是价值本质被掩盖,甚至被歪曲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虽然价值对象性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关系性”以及“非实体性”的特质,但是,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却是“物质性”和“实体性”的。马克思对价值对象性的“表现”进行了这样的强调:“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11〕因此,在商品以“某种比例”进行交换的关系中,人们直观看到的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而不是价值的实体(抽象劳动)或者价值的本质(社会关系)。与人们对使用价值“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不同,而且也与人们对价值形式(价格)的客观实在性的直观感受不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或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只能间接地被人们所把握。
为了展现价值对象性的外在表象,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价值形式。这为理解价值对象性或者价值的客观实在性,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马克思说:“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 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 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 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 A 的价值的镜子。”〔12〕在商品 A 与商品B 的交换关系中,商品 A 的价值对象性成为“可以感知”的东西,也就是成为商品B 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既然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原子也没有,它是纯社会性的,是不可捉摸的,那么价值就无法直观地“感知”。可是在商品A 和商品B 的交换关系中,由于商品B 的自然形式成为商品A 的价值形式,这使商品A 的价值对象性转化为“可以感知”的东西,即转化为商品B 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总之,两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互为映射对方价值的镜子。形象地说,价值对象性或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就映射在这面镜子之中。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理解使用价值的客观实在性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理解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却是非常困难的。即使马克思已经揭示了“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人们也依然难以把握价值对象性那幽灵般的神秘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关系这一类非实体性的范畴具有客观实在性吗?所谓客观性(objectivity),指认识对象所具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所谓实在性(reality),指实际的存在;所谓客观实在性,就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注意,实在性不等于实体性。实体性(entity)是指“存在”所具有的粒子性或物质性(比如使用价值的物质构成),而实在性不仅可以指具有粒子性或物质性的存在,也可以指不具有粒子性或物质性的存在(微观的存在比如量子力学的“波”,宏观的存在比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关系”)。实体性肯定是实在的,但实在性未必是实体的。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价值虽然并非实体性存在①马克思虽然使用过“价值实体”“物化劳动”等说法,但明确指出价值不是“实体范畴“,而是”关系范畴“。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拙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意蕴》,《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 年第6 期。,但仍然具有客观实在性。
二、两种价值量
马克思分析了价值形式映射出来的价值对象性,还进一步分析了价值形式所呈现的数量关系——价值量。马克思说:“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13〕价值形式是怎么表现价值量的呢?马克思以交换价值的“计量”为例,描述道:“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 量鞋油或y 量绸缎或z 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 x 量鞋油、y 量绸缎、z 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么,x量鞋油、y 量绸缎、z 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14〕
在上述有关价值量的分析中,马克思所说的“由此可见”的两个结论值得关注。先看第一个结论:“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同一种商品”,就是某种特定的商品(比如小麦);所谓“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就是某种商品在与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交换时形成的各种比例关系;所谓“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是指商品交换的各种比例关系背后“等同的东西”,这个“等同”的东西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当然,这个“等同”的东西自身并不能直接表示出来,而只能被使用价值数量的“各种比例关系”间接呈现出来。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价值量”,其实是价值形式的数量,还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再看第二个结论:“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交换价值只能是“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这种内容就是以劳动时间作为实体的“价值”。关键是,交换价值作为劳动的“表现方式”,却与“某种内容”(即劳动)“相区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区别呢?这种区别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区别。交换价值之所以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就在于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数量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交换价值以可以感知的使用价值的面目出现,以此来表现价值和价值量。
马克思这两个结论的意思是说,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价值实体(一般人类劳动)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而只能借助于“表现形式”(使用价值)才能呈现出来——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15〕不仅如此,价值量的大小(劳动时间的量)也只能借助于“价值形式”的数量(使用价值量),才能显现出来。总之,在商品经济的现实过程中,价值只能借助价值形式(比如价格)才能得到测量和量化。所以,这里的“价值量”其实是价值形式的数量,这里的价值量化其实只是价值在现象层面上或形式上的量化,而并不是价值在实质规定上的量化。一言以蔽之,能够直接量化的只能是价值形式(或价格),而不是价值。问题是既然价值不能直接测量或量化,可是为什么在 《资本论》 第一卷中,马克思却明确提出了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价值量”概念呢?
换言之,对于不能直接测量的价值,马克思却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做出了分析和测量。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这种“价值量”呢?在以劳动时间为单位测量两个商品的“价值量”时,马克思说:“在商品 A 和商品 B 如麻布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20 码麻布 =1 件上衣,或 20 码麻布值 1 件上衣’ 这一等式的前提是: 1 件上衣和20 码麻布正好包含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16〕
在这个交换等式中,衡量上衣和麻布按一定比例交换的标准,并不是等量的效用(不同质的效用没法比较),而是等量的人类一般劳动(抽象劳动)。在这里,马克思定量分析了价值实体的数量——劳动时间。问题是这里的“劳动时间”虽然具有计量上的含义,但它并不是对商品的价值形式进行计量,而是对商品的价值实体进行计量。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17〕
可见,价值实体(劳动时间)的计量与价值形式(价格)的计量,虽然计量结果都是“价值量”,但这两种“价值量”往往会不一致。因为“相对价值量”并不是价值实体的数量(劳动时间),而是“价值形式”的“数量”(比如价格)——即马克思所说:“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18〕
由此可见,在 《资本论》 中马克思分析了两种“价值量”:一种是价值形式的数量关系(比如价格),一种是价值实体的数量关系(以劳动时间为单位)。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价值量”并不是现象层面的“价格计量”,而是定性意义上的“价值量”。毋庸讳言,马克思从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对价值范畴进行了分析。但是,马克思依据劳动时间所做的价值量的分析,不同于价值形式的数量分析(比如价格计量)。马克思所说的价值量由“劳动的量来计量”,与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价格计量”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计量”,是价值在本质层面的“计量”,是对价值本质的把握;而西方经济学讲的“均衡价格”则是现象层面的“计量”,属于现象层面的刻画。总之,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这个“决定”,指的是对商品价值的内在规定的决定,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均衡价格”不在一个层面上。
问题在于,价格计量的客观实在性是一目了然的,而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价值计量的客观实在性却并非一目了然——人们直观看到的是商品的价格量,并不是商品的价值量(而且价值与价格在数量上也并不一致)。换言之,既然马克思以劳动时间为单位所做的“价值计量”,是指价值在本质层面的计量,而不是现象层面的价格计量,那么,马克思在本质层面上做出的价值计量的客观依据又在哪里?质言之,价值在定性意义上的数学分析科学吗?本文接下来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马克思说,在未来社会“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19〕。这时,直接计量劳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未来社会中对劳动的直接计量呢?笔者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对劳动的计量已经不同于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计量,这种不同在于:其一,一旦商品货币关系趋于消亡,那么劳动就越来越不需要通过价值关系迂回地表现出来;其二,由于不需要借助价值关系来表现劳动,因而不仅产品中耗费的劳动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每个人的劳动是全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也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与商品经济必须通过价格来间接计量劳动相比,未来社会对劳动的直接计量,仍然是劳动在形式上的计量而已。
三、波函数坍缩与价值测量
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对价值作定性意义上的数学分析是否科学?这是理解价值范畴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难点所在。对于这个难点,我以量子力学为例。类似于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范畴,量子力学也有一个核心范畴叫波函数。所谓波函数,是量子力学用来描写微观系统状态的函数。为什么量子力学需要波函数来描述微观世界呢?因为在经典力学中,人们可以用质点(物体)的位置和动量(速度)来描写宏观质点(物体)的状态——这就是质点状态的经典描述方式,这种描述突出了质点的粒子性。但是,在量子世界中,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即我们在观测微观粒子时,粒子的位置和动量(速度)不能同时具有确定值。①即“不确定性原理”或“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该原理由海森堡于1927 年提出,其含义是,观察者不能同时精确地测量到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微观世界(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就像蜂鸟正在扇动的趐膀一样。如果我们用眼睛去观察蜂鸟的翅膀,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蜂鸟翅膀扇动的模糊景象(类似于波动)。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蜂鸟翅膀的速度,但却不能准确判断蜂鸟翅膀的位置。如果我们用照相机高速拍摄蜂鸟扇动翅膀的某个瞬间,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蜂鸟翅膀的清晰图像(类似于粒子)。也就是说,我们能看清蜂鸟翅膀的准确位置,但却看不清蜂鸟扇动翅膀的速度。不确定性原理表明,微观世界的粒子与宏观世界的物质其行为有很大区别。所以,质点状态的经典描述方式并不适用于对微观粒子状态的描述。
为了定量描述微观粒子的状态,量子力学引入了波函数,并用 Ψ 表示(Ψ 是希腊字母)。什么是波函数?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认为,波函数代表几率波。〔20〕海森堡指出:“玻尔、克拉迈斯、斯莱特的几率波意味着更多一些东西: 它意味着对某些事情的倾向。”〔21〕吴国林教授说,波函数“就是微观粒子的根据和意义”〔22〕。通俗地讲,波函数就是用数学语言把微观世界(量子现象)描述成为概率波或几率波。形象地说,波函数就是粒子运动“轨迹”分布的一种函数。吊诡的是,虽然波函数可以用数学进行分析和测量,但是,“量子测量将导致波函数的变化,无法直接测量”;“在量子力学中,可观测的量只能是力学量,而不是波函数。”〔23〕所谓“力学量”,就是指量子力学中的可观测量,比如能量、角动量等。也就是说,真正能够直观测量的,并不是波函数本身。
为什么波函数不能直接观测呢?这个问题涉及到“波函数坍缩”(即“波包塌缩”)。波函数坍缩与微观粒子的测量有关:在测量之前,根据已经求得的波函数,我们只能知道粒子处于它可能存在于其中的各种状态的几率,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处于其中的哪个状态。甚至可以认为,在测量之前,不仅我们不知道粒子处于哪个状态,实际上粒子自身也处于并不确定的各种可能状态的迭加态或纠缠态。总之,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实际测量,才能知道粒子的确切状态。奇特的是,测量结果使得粒子从迭加态突然变为一个确定的状态。这就是“波函数坍缩”或“波包塌缩”。“波包塌缩”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比如,当原子核发生贝塔衰变时(即原子核自发地放射出β 粒子或俘获一个轨道电子而发生的转变),由于我们并不知道衰变出来的电子飞向哪个方向,因而它的波函数就是一个不断向外膨胀的球面波。如果给定的时间“足够长”,那么这个球面就会“足够大”——类似于一个“波包”。可是,一旦我们测量得知电子的具体位置后,这个巨大的球面波(波函数)就突然“塌缩”了,塌缩成为我们测量到电子所处状态的那一点上,这就是“波包塌缩”。
综上所述,在量子理论中,微观粒子的波函数虽然可以用数学进行分析,但这个可以用数学描述的波函数却不能直接观测。一旦人们实际观测微观粒子的具体位置,波函数就崩溃了,波包就塌缩了。所以,人们测量到的只能是反映波函数状态的“力学量”,而不是波函数。问题是,科学家绝不会因为波函数无法直接测量,就拒绝对波函数进行定性的数学分析,更不会断言波函数是量子力学凭空虚构出来的。对此,吴国林教授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波函数的客观实在性:一是可观测性标准,波函数虽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却可以被间接测量到;二是因果效用标准,虽然不能直接观察波函数的实体本身,但根据波函数得出的因果预见却可以被直接观察到;三是语义标准,波函数的理论与其预测之间没有逻辑矛盾。〔24〕
由波函数这个范畴可以推知,试图直接测量劳动价值论所定义的价值,就如同测量波函数一样,其实是不可能的。对于价值范畴而言,能够直接测量、直接量化的只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可以这样比喻:经济学的价值,就类似于量子力学的“波函数”;而经济学的价格,就类似于反映波函数的“力学量”。我们虽然不能直接测量“波函数”,但是能直接测量反映波函数状态的“力学量”。同样的道理,我们虽然不能直接量化价值,但是能够量化反映价值状态的“价格”。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量子力学不能直接测量波函数,但是,对波函数做定性的数学分析甚至定性的量化却是必须的,也是科学的。因为只有使用数学语言和数学模型定义的波函数,人们才能科学描述微观世界的本质。同样的道理,虽然经济学不能直接测量价值,但是,对价值进行定性意义上的数学分析和测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因为只有使用劳动时间来分析和测量价值实体,人们才能科学描述价值的本质。这种定性意义上的数学分析和测量,就是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价值的科学依据所在。①马克思所说:“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 是用它所包含的 ‘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1 页。
四、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
如果量子力学的波函数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范畴,而且科学家对波函数的客观实在性也提供了科学论证,那么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又体现在哪里呢?进而言之,我们怎么把握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呢?如前所述,马克思揭示出两个重要的结论:(1)由于“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所以商品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具有幽灵般的神秘性质;(2)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使用价值的物质形态成为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的外在表象。然而,表象毕竟是表象,它与幽灵般的本质之间的内在关联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不仅可以通过事物的外在表象呈现出来,而且也必然通过事物的结构以及各种关系呈现出来,进而为人们的认识所把握。根据 《资本论》 的逻辑,我认为,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不仅体现在价值对象性的物质载体(使用价值)之中,而且还贯穿于“劳动决定价值”(简称“价值决定”)的过程之中。“价值决定”从结构和关系的向度,充分呈现了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
其一,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25〕换言之,价值量的变动与劳动量的变动以及价值量的变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这些结构变量的变动方向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在市场价格不断变动的过程中,正是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动方向和内在关系,把“价值决定”的秘密呈现出来,即把“劳动决定价值”的客观必然性呈现出来。
其二,马克思说:“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26〕换言之,如同重力作用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价值决定”的强制力同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
其三,马克思说:“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27〕也就是说,如果价值是由供求决定的话,那么价值量就纯粹是一个“不确定”的偶然现象(因为供求是“不确定“的)。然而,商品价格总是围绕着劳动耗费这个中轴线波动的客观事实,消除了价值“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从而消除了价值是由供求决定的假象——当然,这种假象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劳动价值论虽然揭示了假象背后的秘密,“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即价格形式。
其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众所周知,唯物辩证法的本体不是“精神”,而是“物质”;唯物史观的本体不是“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根据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的本体不是“效用”之类的心理评价,而是人类一般的“抽象劳动”。一言以蔽之,正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本体,构成了“价值决定”的客观依据之所在,构成了马克思的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的本源之所在。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本体具有客观实在性呢?诚如恩格斯所说:“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 ‘思辨的’ 形式,黑格尔就是以这种形式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以其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28〕
由此可见,只有在唯物辩证法这种“更加唯物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才能“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对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价值形式进行“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从而保证价值范畴的“唯物”性质和客观性质。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价值范畴虽然不能直接测量,但是它却是一个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范畴。有人或许认为:效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凭什么说决定价值的是劳动,而不是效用呢?这里涉及到理论的“选择性”问题。对于理论选择的分歧,维马斯提出了“元诠释”的标准,即当人们面临众多理论诠释的时候,只有那种具有“元诠释”的理论,才是解决选择分歧的理论。〔29〕所谓“元诠释”,就是最根本的解释。“元诠释”之所以是根本的解释,就在于它是本体论的承诺。以此观之,如果说效用、稀缺以及供求是决定价值的因素,那么与效用、稀缺以及供求相比,劳动在价值决定中才是“元诠释”的因素:(1)效用是劳动作用于自然界的共同结果,没有劳动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没有效用;(2)稀缺的状况取决于人类劳动的广度和深度,人类只有借助于劳动(脑力和体力)才能改变稀缺状况;(3)供求状况与人类劳动密切相关,不仅供给的产品和服务要靠劳动提供,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也只能在劳动提供的供给范围内得到满足。
效用当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1)与人类的劳动耗费这种客观存在相比较,产品的效用只能是第二性的存在。换言之,人类劳动是第一性的存在,是具有本体论承诺的存在。(2)与人类劳动耗费的客观实在性相比较,人们对效用的评价往往因人而异,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换言之,与其说效用是一个具有客观性的范畴,不如说它是一个评价标准颇具主观性的范畴。总而言之,与效用价值论和其它的价值理论相比较,劳动价值论才是“元诠释”。
既然价值范畴的客观实在性贯穿于“价值决定”的过程之中,那么“价值决定”的真实过程必然是一个“先在于”理论描述的客观过程。事实正是这样:“价值决定”的真实过程先于“价值决定”的理论分析,马克思把“价值决定”的真实过程称之为“社会过程”。对于“价值决定”的“社会过程”,马克思用科学语言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30〕虽然人们直观看见的只是”价格计量”的具体过程(即市场供求变化引起商品价格涨落),而并不是“价值决定”的具体过程;但是马克思抽象出来的“价值决定”的“社会过程”,是一个远比现实经济活动中”价格计量”更为本质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过程。“价值决定”的“社会过程”的客观实在性在于,虽然“社会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与价格涨落并不能一一对应,但是,“价值决定”却规定了价格涨落(即“价格量化”)的比例原则。简而言之,价格量化的“比例”并不是人们头脑里事先设计并计算出来的某种先验的比例,而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贯彻“价值决定”的客观结果。
对于“价值决定”的客观性,庸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根本无法理解。“价值决定”不是经济学的计算题,不是数理模型的主观构想,而只能是“社会过程”的实践结果。“价值决定”以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比例,绝不可能“先于”商品经济活动和实践而存在。换言之,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的实践活动与“价值决定”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绝不可能先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比例而存在。马克思说:“首先很清楚,对商品价值的估计,例如,用货币来估计,只能是商品交换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估计作为前提,我们就必须把这种估计看做商品价值同商品价值实际交换的结果。”〔31〕
为什么有人会把“价值决定”误解为经济学的计算题?因为从“逻辑先在”的角度讲,“价值决定”似乎应当是商品交换的前提。但是从实际过程看,或者从“事实先在”的角度看,“价值决定”则是另一种情形:第一,“价值决定”必须借助于价值形式(比如货币)才能实现;第二,“价值决定”是商品交换的结果,而不是商品交换的前提。换言之,“社会过程”与“价值决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价值决定”的“社会过程”,马克思有过极为深刻的论述:“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32〕“各种劳动化为当做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33〕
马克思这里强调的“经验证明”“经常进行”“习惯决定”,其实就是亿万次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经验过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过程”绝不是凭空虚构的过程,而是一个有亿万人参与其中,并经过亿万次生产与交换的实践过程,因而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过程。可见,虽然“价值决定”是马克思作出的理论抽象,但是“社会过程”却为这个理论抽象提供了真实的客观依据。正因为“价值决定”是一个有着充分的实证依据和可重复的经验证明的“社会过程”,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绝不是没有客观依据的臆想,而是科学的理论。
顺便指出,虽然“价值决定”以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比例,不可能先于商品经济的生产和交换的实践而存在;但是对于个人的具体交换行为而言,“价值决定”往往是先于个人的经验而存在的,所以具有“先验性”。因为个人所参照的“价值决定”经过了亿万次商品生产和交换实践的检验,从而获得了公理性。正如列宁所说:“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34〕总之,“价值决定”形成于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人的社会实践不仅仅是某些人或者某个人的实践,而是人类的总体实践,是亿万次实践反复验证的结果。“价值决定”背后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就是价值以及劳动价值论的客观依据之所在。庸俗经济学的前人以及传人,一边指责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是“主观臆想”,一边却无视“价值决定”的客观依据。这恰恰证明他们根本不懂得唯物辩证法。这让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论述。针对以价值与价格“不一致”来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恩格斯引述了桑巴特对劳动价值论的评价:“价值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不会表现出来;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是不存在的;它不是经验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概念按其物质规定性来说,不外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构成经济存在的基础这样一个事实的经济表现;价值规律最终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过程,并且对这种经济制度来说普遍具有这样的内容:商品价值是最终支配着一切经济过程的劳动生产力借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特有的历史形式。——以上就是桑巴特的说法。”〔35〕
桑巴特说,“价值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不会表现出来”,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是,与那些把“价值决定”等同于“价格量化”的庸俗经济学家相比,桑巴特对价值的理解已然非常深刻。注意:所谓价值“不是经验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是指人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直接看到价值,人们直接看到的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价格)。然而,价值“不是经验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价值不能在经验上得到证明,更不意味着价值是马克思虚构出来的范畴。
五、现象学并未否定追问本质
之所以有人认为价值是马克思凭空虚构的范畴,并将“庞巴维克质疑”奉为圭臬,这恰恰说明,他们只认可现实经济生活所呈现出来的表象,尤其是只认可货币这种价值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表象,从而把现象分析当做唯一的科学,拒绝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做进一步追问。问题是,“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36〕。科学探索之所以必须追问本质,就在于现象往往会遮蔽真相。人类是通过感官来认知世界的,然而感官却会欺骗人类;现象当然是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出发点,但现象并不等于真相。人类的感官是进化的结果,外界有很多事情和事物,人类的感官(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不仅感觉不到,而且也常常会产生错觉。其实,“眼见未必为实”。正因为“眼见未必为实”,所以我们必需借助理性的思辩能力和正确的抽象能力,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37〕因此,“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之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38〕。
从现象学的视域来看,对价值形式(价格)进行定量意义上的“测量”,或许类似于胡塞尔所说的“经验直观”;对价值进行定性意义上的“测量”,则类似于胡塞尔所说的“本质直观”。所谓直观(intuition),就是不经过中介而直接把握事实本身。直观包括经验直观和本质直观两种类型。〔39〕所谓经验直观,是在无中介的前提下直接观察事物。经验直观虽然“经验”,却也因其个别“经验”而缺乏普遍性。与经验直观不同,本质直观虽然也一种直接观察,但本质直观“不只是感性的、经验的看,而是作为任何一种原初给予的意识的一般的看”〔40〕。换言之,“本质直观绝不是在感知、回忆或相似行为意义上的 ‘经验’ ……。这种直观将本质把握为本质存在,并且不以任何方式设定具体存在”〔41〕。若按现象学的逻辑来定义,价值类似于“存在”(或“是”),而价值形式则类似于“存在者”(或“是者”)。
有人认为,现象学否定了对本质追问的意义。我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现象学的现象范畴并不是通常所指的“事物的表象”,而是蕴含着“面对事实本身”〔42〕的诉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如何区别现象学的现象概念与流俗的现象概念呢?……它首先与通常恰恰不显现,同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其情况是:它构成这些东西的意义与根据。”〔43〕在某种意义上,现象学的现象与本质是等价的。虽然现象学拒斥现象与本质的二分法——海德格尔说:“在现象学的现象之后根本不存在别的事物”〔44〕,但却并不否认对本质的追问(海德格尔对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其实就是对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就是对本质的追问过程。通过这一追问过程,胡塞尔认为,由于主体先验地赋予了认识对象的意义或本质,所以,认识的本体论依据以及知识的最终源泉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由此可见,现象学就是一种追问本质的学说或者一种追问本质的方法。比如,胡塞尔以一张红纸为例:从经验直观来看,红纸仅仅具有纸张的形状、颜色的深浅等等经验外观的具体状态。然而从本质直观来看,“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红和特殊的红的思想的意义,即从这个红或那个红中直观出的同一的一般之物;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而是一般的红”〔45〕。
显然,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是建立在唯心逻辑的基础之上的——胡塞尔说:“先验主体间性是绝对的并且是唯一自足的本体论基础,每个客观事物都从那里(客观的真实的东西的总体,并且也是每个客观的观念世界的总体)获得其意义和有效性。”〔46〕正因为如此,“现象学还原”与唯物辩证的“抽象力”有着本质区别,也与科学方法的实证特征相去甚远。对此,胡塞尔也不否认:“自然科学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他进行观察和实验。即他按照对经验确定着事实存在,对他来说,经验活动是一切均以之为基础的行为,它绝不能被单纯的想象活动所取代。”〔47〕问题是,离开了经验的实证,科学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正如吴国林教授所说:“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科学实验,谁又能通过自己的感官直观到原子或原子核等微观粒子,并进一步直观到原子或原子核等微观粒子的本质呢?”“因此,任何量子力学都不可能全部达到现象学所要求的的直观方法。”“对于微观现象来说,如果不在存在论意义上承认微观的客观世界的在先性和原初性,那么,仅从先验自我的原初性,借鉴和重新诠释统觉(apperzeption)、移情作用等心理学概念,企图说明他人与客观外在世界的产生于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48〕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逻辑,承认客观事物的先在性,这不仅是人类科学认识微观世界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科学认识宏观世界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