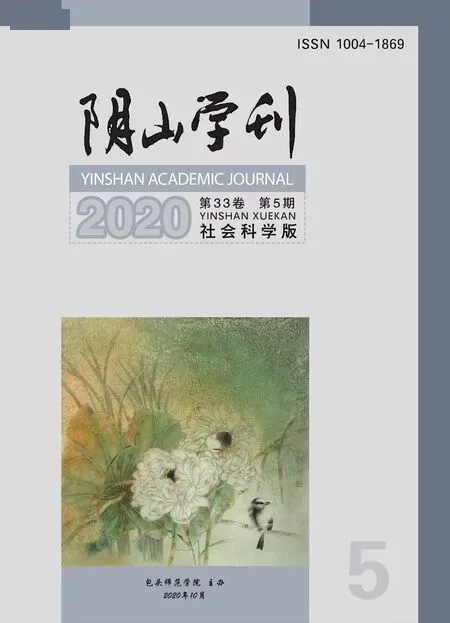“曲味儿”因异军突起的语言特色而溢出
张 福 勋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曲论家们在比较了传统诗词与曲的特点差异后,先后归纳了十个方面的不同,正好让我们从旁窥见散曲的独特面目。
一是“动”;二是“放”;三是“广”;四是“外旋”;五是“阳刚”;六是以豪放为主,别体才为婉约;七是不讲究“意内言外”,而是“言外而意亦外”,即是说,诗词讲含蓄,而曲讲淋漓尽致、痛痛快快,其用意要全然暴露于言语表面,不是含而不露、又吞又吐,而是满心而发,肆口而出;八是诗词之语体要用文言,而曲之语体要使用“天下通语”之白话,白描是其本色;九是诗词要避俗,而散曲则完全不避俗,俗风、俗意、俗言、俗语,比比皆是;十是诗词不用衬字,而曲则肆无忌惮地使用衬字。
总之一句话,诗词是写给读书人看的,而散曲则是唱给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听的。所以诗词之所忌(短),恰是散曲之所擅(长)也。
第二个就是这个“散”字。可以说这是散曲最吸引人、最能定性它本质特征的地方。而“散”主要是语言形式上的东西,这是散曲“曲味儿”最有魅力、最有鲜明特色之处。
以下分别从五个“味儿”论述其特色鲜明之“曲味儿”。
(一)极尽句式长短变化之能事,凸显其“散”体味儿。
在语言句子上,散曲作家完全根据自己思想感情的表达需要,彻底“松绑”,尽“情”发挥,不再被字数的严格限制所羁绊,采取更加“自由化”了的句式。当然每一个曲牌的句数、字数,都还有一定的讲究,不是绝对的自由,是一定规则要求下的自由。这里用得着宋代江西诗派重要成员吕本中给夏均父诗集作序的时候,发表的一段关于“活法”的精彩论述:“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又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诗集序》)我们所说的散曲打破句式对于字数的限制,就是“变化不测”,而“规矩”,就是曲牌对于句数和每句的字数的一定规矩。
元人散曲,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九字句、十字句,甚至多至三十字句,在一首曲中,混杂运用,腾挪跳荡,左旋右转,无所不能,又变化无穷,完全散体化了。可以说,散曲就是一种新型的那个时代的“自由诗”。
如陈草庵〔中吕·山坡羊〕每首曲的末尾部分,都是一字句加三字句连用,写“闲中自有闲中乐”,“东,也在我;西,也在我。”又写“功名将就”“便抽头”:“功,也罢手;名,也罢手。”朱庭玉〔南吕·梁州第七〕《妓门庭》每句均长18字。而大家熟知的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更是一句30个字:“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砍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如读散文一气贯下,起落振荡,抑扬顿挫,极尽摇曳生动之趣。烘托一种坚定的自信,做到声情并茂,撼动人心。
纵观中国诗歌语言句式的发展、变化,其总趋势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解放。由先秦四言,到汉魏五言,再到隋唐七言,再到宋之长短句,再到元曲的自由句式,就是这样一个发展总趋势。唯其如此,任何文学艺术才可以适应时代、社会由简单到繁杂地发展,才适应了人们思想感情之愈来愈多元、愈来愈繁复的发展趋势,这就是与时俱进的规律。诗词曲赋,莫不如是。
(二)语言不避重复,故意重叠又大量使用叠字、叠词、叠句,凸显其民间味儿。
任讷《散曲概论》专有“叠字体”一节加以论述,认为散曲中每多“通篇用叠字者”[1]。如孙周卿〔双调·蟾宫曲〕《自乐》:
“草团标正对山凹。山竹炊粳,山水煎茶。山芋山薯,山葱山韭,山果山花。山溜响冰敲月牙,扫山云惊散林鸦。山色元佳,山景堪夸。山外晴霞,山下人家。”
“山”字,15次重复,而且重复中有变化,或句中自对,或对句互对,总之是句句有重叠,但因多有变化,而不觉累赘。
无论是描写自然景物,或者是刻画人物性格,特别是表现人的浓烈感情,这种故意重复,能造成一种声势,表达那种不可遏制的感情效果。
如王实甫〔中吕·十二月过尧民歌〕写《别情》:“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这种故意的重复,读起来或唱起来,节奏明快、活泼跳跃,表达一种缠绵纠结,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别情”,效果特别突出。
从歌唱的角度讲,故作重叠,节奏感强,好唱、好记,也好传开。孔颖达《诗正义》论诗之句法长短、字之多寡,是“和以人声而无不协。”可见句式长短的变化是为了适应“人声”之和协。“合语吻”“达语情”。你看一首唐人的《阳关三叠》经过元曲家的艺术加工,重复歌唱,起到了更加强调、突出的艺术效果:
渭城朝雨浥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缕,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翠色,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柳色新。
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人生会少。富贵功名有定分,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旧游如梦。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
经过反复咏唱,这“劝君更尽一杯酒”,于是乎深刻于听众之心,永垂而不朽了。俞文豹说:“语意到处,他字不可代,虽重复无害也。”(《吹剑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重也有讲究,要做到字重而意不重,方为上乘。
吕济民〔正宫·鹦鹉曲〕《赠玉香》曰:“可人儿暖玉生香,弄玉团香,惜玉怜香,画蛾眉玉鉴遗香,伴才郎玉枕留香,捧酒卮玉容喷香,摘花枝玉指偷香。问玉何香,料玉多香,见玉思香,买玉寻香。”此曲凡十一句,而句句故以“玉”和“香”二字重复(每字都重复11次),形似轱辘,辗转滚动,形成一种浓厚的“玉”“香”四周充郁的氛围,但每一次的重复,又各有所指,不管与动词结合或与形容词结合,不管与名词结合或疑问词结合,都作为关键词被高高托起,目标显豁。意都不重复,见出其多样化的特点。须知,如果字重而意亦重,就成了拖沓,啰唆,让人不堪卒读了。若论救其弊端之良药,便是巧妙地将重字变来变去,于变化中,让人领略其生趣与灵动。
再比如张鸣善〔中吕·普天乐〕《雨儿飘》一曲唱道:“雨儿飘,风儿飏。风吹回好梦,雨滴损柔肠。风萧萧梧叶中,雨点点芭蕉上。”这是“风”并“雨”两字分开又都在首字的重复。下边则把“风”和“雨”二字合起来重复:“风雨相留添悲怆”。下句又把“风”和“雨”分开,但“风”和“雨”倒过来,而且一个在首字,一个却在第三字:“雨和风卷起凄凉。”有了如此的变化,便调动起了你的阅读兴味。但还要再变化,“风雨”“雨风”夹杂而用:“风雨儿怎当,雨风儿定当,风雨儿难当”。中间还又故意横插个“当”字的三次重复。真如杂技里边的杂耍,就那么一个小球,却变来变去,让你眼花缭乱,妙不可言。严沧浪说:“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良哉斯言。“重”而对“重”,你“复”我“复”,重来复去,逗起了禅趣。
(三)大量使用“儿化”,凸显其草根味儿。
民间口语,口吻灵动,绘声绘色,将人物表情、动作、心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儿化”便是(这种百姓口语)其中的一种语言特色。
老百姓说白话,尤其在北方(散曲就产生于北方)愿意用“儿化”,显示亲切、柔媚、生动、活泼。特别逼近口语,原汁原味。
刘庭信〔双调·折桂令〕写《忆别》“想人生最苦(是)离别”说“情儿分儿你心里记着,病儿痛儿我身上添些,家儿活儿既是抛撇,书儿信儿是必休绝,花儿草儿打听的风声,车儿马儿我亲身来也。”这12个“儿化”真是灵动活泼,逼真地表达了这“别”的心痛。
“儿化”有时候还能增加一种缠绵、殷勤的情感表达。也是刘庭信《忆别》这样写道:“梦儿成良宵短短,影儿孤长夜漫漫。人儿远地阔天宽,信儿稀雨涩云悭。病儿沉月苦风酸。”这“情”是绕也绕不开、躲也躲不过去了,多么缠绵悱恻呀!
“儿化”更多的时候,是逗趣的、幽默的,或略带些酸涩的嘲讽:
杨讷(他是个蒙古人,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中吕·红绣鞋〕《咏虼蚤》:“小则小偏能走跳,咬一口一似针挑。领儿上走到裤儿腰,眼睁睁拿不住(哟)。身材儿(可)怎生捞。翻个筋斗不见了。”欢快,幽默,充满了可爱的童趣。试想想,如果将“领”和“裤”后缀之“儿”字去掉,便顿觉没味儿了。
“儿化”的运用,也多种多样,呈现的是多样化的特点,而决不干瘪。我们看张可久〔仙吕·一半儿〕下的标题:
《秋日宫词》是“一半儿芙蓉一半儿柳”;
《梅边》是“一半儿清香一半儿影”;
《情》是“一半儿门开一半儿掩”;
《野桥酬耿子春》是“一半儿行书一半儿草”;
《赏牡丹》是“一半儿姚黄一半儿紫”;
《苍涯禅师退隐》是“一半儿青山一半儿水”。
“儿”在一句中连用,既切合曲牌之名,又悦耳动听。但“儿化”多数是每句单用。薛昂夫〔南吕·一枝花〕《赠小园春》:
“唾津儿浸满盆池,手心儿擎得起屏石,苔钱儿买不断闲愁,花瓣儿随手着流水,柳丝儿送不够别离……赚得东君不忍归,一撮儿芳菲。”
经过“儿化”的轮番轰炸,“小园春”扑面而来。
“儿化”有时候还混搭着其他的修辞手法,需要细心辨认。比如徐再思〔双调·水仙子〕《青玉花筒》是将“儿化”与“对衬”相结合:“两朵儿瑶花弄色,半缕儿香绵沁粉,一泓儿碧露涵春”。“一”“半”“两”,数词加量词,对得十分工整。
(四)运用方言俗语成风,凸显其北方味儿。
清代诗论家赵翼《瓯北诗话》(卷六)评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诗不避“俗”,认为:“专以俚言俗语入诗中”,而另一位诗论家翁方纲则更进一步认为“其巧处即其俚处”(《石洲诗话》)。
散曲语言重用白话,专以俗语、方言入曲,向民间汲取营养,俗而使活,俗而使奇,取得十分明显的艺术效果,这就是其“巧处”。
大家知道,元代的大部分散曲作家“终其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由“激而愤世”到“放而玩世”,于是找准了不被那些正统文人、上流社会看上眼的“土”的“下(底层)”边的却在老百姓中间普遍流行的曲体,自由发挥,“嬉笑怒骂,嘲讥戏谑,固无足怪”[1]。这是在巨石下顽强生长的文学新品种,是在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文学、上流文学、正统文学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民间文学,是摆不上大雅之堂的“土根”文学,与所谓“雅文学”分道扬镳的“俗文学”。
作为在北方土壤上(我这里所说“北方”主要指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区)生长起来的散曲,大量地使用颇具有这个地域文化色彩的口语、俗语、土话和大量的内蒙古西部方言,就不足为怪了。
有的方言的读音,不仅保存了在普通话里已经消亡了的入声,而且是古代切音法的具体运用。南宋大学问家洪迈曾在其《容斋随笔》里讲到“切脚语”,经考证,就是包头方言里的切音读法,如“巷”读为“黑浪”,“棒”读为“不浪”等等。这是很珍贵的语言研究的材料。
(五)为了凸显散曲之民歌味儿,使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衬字”,如象声字、叠音字、双声叠韵字,这些当然主要是为了契合歌唱的需要,使听众由听觉而打通感觉,听得清、记得住,又传得开。
衬字,可以说是散曲最耀眼、最个性化的鲜明特点。
所谓“衬”,就是添加,指在曲牌规定的字数(有定数)之外,还可增加许多字(无定数),极尽长短变化之能事,给了作曲家更大的伸缩空间,让他们可以更加自由自在地抒情、绘景、纪事,突破牌调谱式的限制,于拘束之中获得“旷然有伸缩回旋之余地”,“既得句法中活泼流利之用,又无谱律上偭(miǎn,违背)规越矩之嫌,最为合法”,因此在散曲中“衬字虽不能多,要不可废。能应有尽有。”[1]
“衬字”虽专就字法而言,然亦不脱于散曲之整体风貌,能于结构上起开启、承接、转折等。任讷说:衬字于“虚处既得转折贯穿之施”,而于“实处又得提携点醒之用”,并且还有凑足歌唱时音节之需要。以求得全曲整体的和谐一致。如钱锺书先生讲用字法强调要安排好字在句中的位置,“于句中之位置贴适,俾此一字与句中乃至篇中他字相处无间,相得益彰”,“配合协同”。万不能如“生客闯座,或金屑入眼,于是乎虽爱必捐,别求朋合。”(《谈艺录》)
至于衬字如何做到“贴适”,根据前人创作散曲的实践经验教训,至少可得出如下三点:在句头衬,不要在句尾衬;最重要的是在添加衬字时,以不打破原来的句法安排(有定数)为根本原则;所衬之字于朗诵或歌唱时,采用轻声一带而过,而不要占重拍之处。
衬字的作用,只是补足语气,凑足句中的一个或几个音节,以构成和谐统一的节奏,使个体得以一统,差别得以协调,散漫趋向集中。形成诵、唱时带来快感和美感,满足人们在生理上(如心的跳动,肺的呼吸)和心理上(人们需要有节奏的生活,快慢结合,高低相谐,以得到暂时的休憩,并将带来下一轮的期待)的需求。正如同四季之代序,昼夜之交替。使整首散曲作品,形成巨大的吸引力、感染力和美的魅力。
先来看一首特别著名的关汉卿的《不伏老》曲:
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开头正文七言两句只14字,而衬字(括号内,下同)却加进了38个字。使得这首曲子诵唱起来,往复回环,节奏紧迫,起落振荡,抑扬顿挫,极尽摇曳生动之趣。酣畅淋漓的气势,烘托出一种十分坚定的自信,做到声情并茂,撼动人心。
再如王廷秀〔中吕·尧民歌〕
呀,愁的是雨声儿淅零零落滴滴点点碧碧卜卜洒芭蕉,则见那梧叶儿滴溜溜飘悠悠荡荡纷纷扬扬下溪桥。见一个宿鸟儿忒楞楞腾出出律律忽忽闪闪串过花梢,不觉的泪珠儿浸淋淋漉漉扑扑簌簌揾湿鲛绡。
如果去掉衬字,就只剩下四言的“雨洒芭蕉,叶下溪桥,鸟过花梢,泪湿鲛绡”,是反映女主人公见雨下、叶落、鸟过而引起的无限愁情。而加上了67个衬字特别是象声的、重叠的方言、俗语、儿化的狂轰滥炸的连续运用,节奏浏亮,欲哭无泪的无奈与悲情淋漓尽致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可以看出,关于衬字的词性,并不都是由虚词充当,而也有实词。诸如:
用代词:
“觑了你(这)无下梢枯杨成何用,想着你(那)南柯一梦。”(谷子敬《城南柳》)
方位词:
“那厮正茶船(上)和衣儿睡。”(马致远《青衫词》)
数量词:
“(一个)汉明妃远把单于嫁。”(白朴《梧桐雨》)
形容词:
“(瘦岩岩)香消玉减,(冷清清)夜永更长,(孤零零)枕剩衾余。”(宋方壶散套《紫花儿序》)
象声词:
“惊得那(呀呀呀)寒鸦起平沙。”(郑德辉《倩女离魂》)
语气词:
“也么哥”“也波”“的这”“圪溜”“圪丢”“呀么”……
节奏感强的自由体新诗,每一诗句在主要词汇组成主要节奏之外,亦可添衬字。如刘大白作于1929年的《莫干山》:
朝朝暮暮,
(尽是)风风雨雨。
(挟着些)云云雾雾,
(向高山)喷喷吐吐。
花翻草覆,
藤飞树舞;
(不管)淋漓零乱,
(颠狂得)不由自主。
(记得)满山楼阁,
参差无数;
(怎)朝(也白茫茫)一片无寻处,
怎暮(也黑漫漫一片)无寻处?
(亏它近处)几星灯火,
(云)雾(也)难遮住;
(到晚来)依稀透露,
(约略是)邻家三五。
可以看出,在整齐的四言诗外,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或在句首或在句中都加进了没有定数的衬字,使得句式更加灵活、多变,活泼、跳跃。除了上述词性外,名词、动词、副词、介词、判断词、结构助词等等,一律都可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由于散曲从民间歌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借鉴了许多的做法,所以它的语言除了承接了诗、词那种典雅的传统之外,还特别沾染了民间语言那种质朴自然、鲜明泼辣的特点,形成了“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的独特风貌,获得了雅俗同赏的艺术效果。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
刘毓崧在《古谣谚·序》中论雅文学与俗文学两种语言的关系,说:“谈风雅者,兼诵谣谚之词,岂非言语文学之科实有相因而相济者乎?”[2]这“相因”“相济”四字,十分精准地概括了“雅”与“俗”这两种语言风格的相融相通的正确关系。
所以清代曲论家李渔在论述散曲(亦含杂剧)的“填词”做法时说:“戏文(是)作与(予)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予)不读书之妇人与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作曲家在创作时“未尝不引古事,未尝不用(古代)人名,未尝不书现成之句,而所引所用与所书者则(与诗词)有别焉。”而这个“别”就在于“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3]
这些创作经验的概括,即对我们今天的散曲作者,都有很强的现实和启发意义。
当然,我们强调散曲语言(当然涵括衬字)的明白、平易,并不等于要把那些应该抛弃的糟粕诸如蛮狠、猥琐、险刻、卑污、油滑、生涩、庸俗等,也不加批判地一股脑地接收过来。
散曲实际上就是元代的白话诗,用的是“天下通语”。尽量用白话,以白描为本色,不再陶醉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和婉约,而喜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直率和奔放,完完全全地“散”了。这是诗体解放的必然结果,其神髓与民歌灵犀相通。
我们看南方的《十送红军》:
“一送(里格)红军(下呀么)下了山。”
再看流行于北方的爬山调《割莜麦》,女声的对唱为“妹妹刨山药(土豆)”五个字,但衬字竟多达66个,比关汉卿的《不伏老》衬字还多出了28个,且读起来:
“(小)妹妹(在那山里凹里、沟里岔里、白胳膊膊、银手镯镯、珊瑚珠珠、玛瑙旦旦、金珥环环、手提着篮篮、拿着个铲铲、钻在地里、圪丢丢丢、圪嗒嗒嗒、圪丢圪嗒、圪丢丢丢、圪嗒嗒嗒)刨山药。”
最后是男女声合唱:“亲亲!”劳动的愉悦、爱情的甜蜜,满心而发,肆口而出,通过这衬字的堆积运用所造成的热烈欢快的节奏,主人公火辣辣的性格、赤裸裸的表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明﹞王骥德《曲律》所讲“尖新”之“尖”,﹝元﹞贯云石《阳春白雪·序》所讲“豪辣”之“辣”,于此可以领略再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