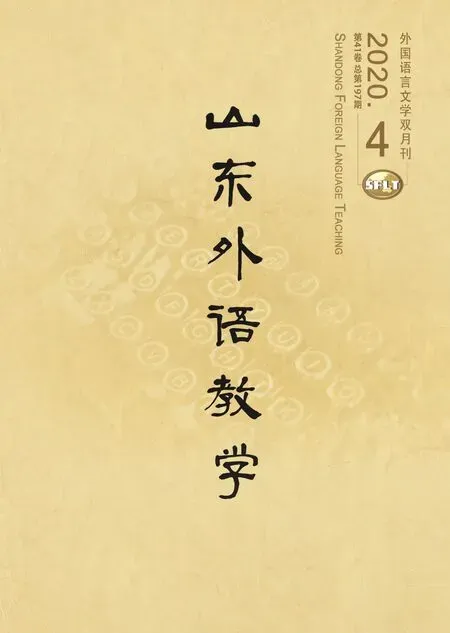纯真之谜:麦克尤恩小说《无辜者》中的寓言叙事
陈丽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1.0 引言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转型后的代表作《无辜者》(TheInnocent)在1990年甫一面世,就被评论界划入“心理小说”“间谍小说”“惊悚小说”或“成长小说”之列(Childs,2006:89)。这种多元划分不只是评论界关注《无辜者》蕴含的多元主题,而是这部小说对于人性纯真与暴力相伴相生的现象做出了独特的思考和追问。《无辜者》以冷战时期英美两国在柏林秘密开展情报工程事件为背景,以英国青年电子工程师伦纳德(Leonard Markham)的成长经历和情感波折为主线,叙述了伦纳德在犯下骇人听闻的暴力肢解事件后,仍坚信自身的无辜与本性的纯真,隐喻出英国在二战“胜利的阴影”笼罩下举步维艰的处境,体现了麦克尤恩对当时欧洲历史转型期诸多社会及道德问题的看法。从批评界的反应来看,对《无辜者》的评论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认为麦克尤恩善于捕捉普通心灵的变化,延续了心理小说的风格(Malcolm,2002:125)。二是小说的寓言性,以伦纳德纯真的丧失隐喻出二战后英国的国家认同危机(Childs,2006:78)。这些研究角度反映了评论者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基本上肯定了《无辜者》通过个体成长寓言呈现社会与历史的创作思想,却忽视了其对纯真悖论的关注。麦克尤恩研究专家海德(Dominic Head)曾指出,“主人公伦纳德迷茫、敏感的感受,为麦克尤恩提供了关联政治寓言与个人心理的契机”(2008:94)。可见,小说的主题思想、叙事结构和人物身份建构都与纯真的指涉息息相关。“纯真到底意味着什么”成为了小说的核心问题(Head,2008:97)。
笔者认为,《无辜者》中的纯真内涵应放在冷战时代情感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主人公伦纳德对自我纯真几近偏执地追求,以及他在行动上的善恶交织共同指向一个悖论,即对“纯真”的追寻总是伴随着对它的不断消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这一矛盾情感构成了小说的“纯真之谜”(the myth of innocence)(Head,2008:62),反映出麦克尤恩对纯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质询。在寓言叙事的文类框架下,“纯真之谜”难以言说的意指正是以伦纳德的个体形象来负载。通过表述一种经验层面的真实,转喻出残酷的生存本相。这种言外之意所容纳的文化哲理思考是不断演进的。西方寓言文类的叙事传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他在浪漫主义时期受到冷落,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重新走上理论前台(张隆溪,2003:55)。寓言叙事以故事层面的经验,传达意义层面生发的寓意和哲理,呈现了文本能指与寓意所指之间的断裂和差异。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契合了他们对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的看法。保罗·德曼(Paul de Man)认为寓言叙事展现了意义指向的含混,语言的自我解构阐明了言说的困境,“寓言正是书写这一不可读性的思想形式,表达出阅读和阐释的不可能。”(1979:205)。德曼的观点呼应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的寓言叙事的复义性。在本雅明看来,“所有具有意指作用的道具恰恰因为指向另外之物而获得了一种力量。”(2013:20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寓言叙事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认知框架,而应被视为对柏拉图式摹仿的颠覆,或者说寓言叙事被赋予了“反摹仿”(anti-mimetic)的成分。寓言叙事着眼于“把人和自然界某些普遍的抽象的情况或性质……加以人格化”(黑格尔,1997:122),人物风格化正是在隐喻机制运作中达成。由此,现代寓言小说不再以言与意的相似性为认知基础,而是召唤读者挣脱表层故事经验的牵制,借助于隐喻扩大认知视域,将经验世界投射于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中,仔细分辨消融于非自然情节中的深层寓意,“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具有挑战性的审美体验”(Richardson,2006:36)。在《无辜者》中,寓言叙事正是以含混、异化、生成的方式凝聚成小说的叙事动力。麦克尤恩在小说中以言说困境、空间寓言化和爱的救赎三个不同方面,质询纯真的悖论性。个体的纯真在追寻中不断消解,表达了麦克尤恩救赎式的生存美学以及对纯真本质的复杂态度。
2.0 言说困境:《无辜者》的命名和寓言阐释的间离效果
小说《无辜者》的标题命名经过三次改易。麦克尤恩最初打算将小说称为《特殊关系》(TheSpecialRelationship),后来又打算命名为《柏林来信》(TheLetterinBerlin)(Ryan,2010:66),但最终选定“The Innocent”,意在彰显这一标题所能涵盖的“深刻有力的隐喻性”(Ryan,2010:65)。的确,麦克尤恩几易其名或多或少表露出小说中“innocent”一词的语义双关性,既可以作“纯真”之义,又可当作“无辜”注解。这两层语义分别指向了主人公伦纳德的情感欲望和身体暴力,暗示出麦克尤恩意图讲述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冷战爱情故事,而是一则具有深刻意味的文学寓言:从经验返归纯真的英国青年。麦克尤恩最终选定“无辜者”这一小说标题,正是因为它指向了纯真指涉的言说困境,只能经由与之悖反的意义来建构:身体经验与欲望深渊。因此,如何再现冷战语境下个体追寻纯真的困境成为麦克尤恩首先考虑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不同于传统寓言叙事中以言与意二分式的文本建构方式,麦克尤恩有意借助于多视角交互共存的叙述策略,将外层叙述者和被边缘化的内层人物叙述者的视角并置,通过揭示记忆的选择性,突显寓言阐释的含混,折射出冷战历史语境下容易被遗忘的个体生存困境。
在小说的主体部分,麦克尤恩以外层叙述者来讲述伦纳德在柏林隧道的工作和情感波折,但在小说的第十七章中,麦克尤恩以自由直接引语切换至主人公伦纳德的视角,再现了他与玛利亚(Maria)彻夜商议处置尸体的场景。这一叙事话语模式祛除了外层叙述者声音的“音响效果”和对人物的叙述干预(申丹,2001:283),展示了伦纳德最终决定肢解尸体的来龙去脉。麦克尤恩巧妙借助于视角切换,赋予了人物一个申辩的机会,从而让读者意识到寓言阐释的复义性。因此,读者所看到的不再是纯粹、超验式的人性纯真,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衍生出虚幻与真实、表象与本质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
在小说这一桥段中,通过内层叙述者伦纳德碎片式的回忆,读者逐渐得知他不谙世事、天真直率的一面。在他看来,订婚之夜的那场打斗突如其来,玛丽亚的前夫奥托(Otto)之死绝对是“自卫”,并非是一起谋杀。这一论断正是伦纳德借玛丽亚之口表达出来,“她会对他们说,这是自卫。”(麦克尤恩,2010:271)然而,向德国警察报警的提议却被玛丽亚劝阻下来,理由在于两方面:一是“自卫”说辞无法自圆其说,二是“她急急忙忙地一口气说道,他们(警察)喜欢他,他们把他看作一个英雄……”(同上:272)。更重要的是,依据伦纳德的叙述,肢解尸体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玛丽亚的推理判断,“她把手按在自己的喉咙上,说道,他们不会相信我们说的自卫。谁都不会的。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我们就会进监狱”(同上:283)。换言之,奥托的尸体隐喻了二战后德国受压迫的民族精神,德国警察压根不愿意相信自卫杀人的说法。肢解尸体的合法性正是为了维护个体的自由存在。在自由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下,外层叙述者操控的叙事距离被消解,伦纳德之前与读者的疏离感也随之消除。他得以表露内心的恐慌,即自我纯真的丧失与自由的焦虑。然而,视角杂糅的手法也带来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伦纳德的心理活动与外层叙述者话语无缝连接,前者自然地混杂于叙述语流中;另一方面,叙述者的含混态度也会让读者无法辨识伦纳德记忆的真实性,进而也无法想象出伦纳德所谓的自我纯真如何催生了身体暴力。
此外,叙事的含混性开启了寓言阐释中的多重指涉空间,也召唤读者去积极介入文本空间的建构。“作者越是让文本中的人物代表一个概念(如智慧),就越能暗示出某个隐含的阐释方案的存在”(Whitman,1987:8)。小说中,麦克尤恩有意将玛丽亚三十年后的来信放置于内层叙事,散落在外层叙述者和伦纳德的记忆叙述之中。在内层叙事中,之前一直处于“噤声”的玛丽亚既是叙述主体,也是叙述对象。三者之间的视角交织共同形成棱镜式的互补关系,加剧了充溢于文本中的反讽张力。“反讽”作为寓言叙事的美学特征之一,成为“虚构性叙事的基本比喻”,“存在于作者与叙述者之间或间接引语中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永远存在的差异之中”(米勒,2002:73)。在书信中,玛丽亚讲述了自己担惊受怕地善后过程,恳求美国情报官员鲍勃·格拉斯(Bob Glass)转移柏林隧道中藏有奥托尸块的行李箱,躲过了苏联人和柏林警察的麻烦。她不断写信哀求身处英国的伦纳德回心转意,但最终嫁给格拉斯,在美国定居。不同话语层级的叙述者交替发声,叙述视角发生不断移位,不仅制造出美学形式上的间离效果,而且也推翻了伦纳德此前的种种叙述。更重要的是,玛丽亚对伦纳德断绝恋情的看法,也激发读者重新思考他维护自我纯真的真实意图。“有时候我生你的气,你真不该心怀气愤而默默地退出。你真是英国人的派头!真是个大男人的派头。如果你认为有人背叛了你,你就应该坚守阵地,为了你的东西而战斗。……可是我知道,是你不战而退的是你的骄傲”(麦克尤恩,2010:395)。在这封迟到三十年的来信中,玛丽亚动人的回忆撕裂了之前外层叙述者和伦纳德相互缠绕的叙事线条,暴露出伦纳德所谓的自我纯真,实则夹杂了人性的狭隘自私。在这个意义上,他多次提到的纯真不过是为了逃避他人指责的托词,而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得以实现,“在具体的叙述细节和隐含的意义中探寻相互对应的关系”(Quilligan,1979:26),突显出读者阐释与叙述真实之间的差异。同时,这一叙事结构所蕴含的非线性叙事延宕了叙事进程,表达出“空间性隐喻性质”(邹颉,2002:375)。
3.0 空间寓言化:自我异化
事实上,人性中的纯真与狭隘自私不仅体现在寓言阐释的言说困境,还隐喻出冷战历史语境下政治空间建构的法则。换言之,麦克尤恩通过叙述者视角的切换,凝滞了时空矩阵,为小说离奇残酷的情节推演提供了文本空间,巧妙完成了不可能的故事世界的逻辑连贯,身体暴力和亲密关系的异化获得了可能合理的场所,这一情节的合理性与柏林作为政治空间的隐喻密不可分。自我深感存在的困境,因而寻求突围之路成为一个关乎生存的哲学命题。
小说中,政治空间的寓言化首先通过纯真青年伦纳德象征的英国性(Brown,1994:107),以及他在柏林遭遇的种种异化感表现出来。早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性”(Englishness)概念就用以重构英国的核心民族身份,“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以其特有的具有男子气概的品质——勇敢、坚韧、强悍、诚实、坦率、热爱自由等等——构成了英国民族特性的基础”(陈兵,2017:124)。不仅如此,“维多利亚时期所推崇的克制、含蓄、隐忍、服从等道德观念,也成为深植于英国民众骨髓的人生信条”(梅丽,2018:18)。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英国性与帝国认同产生共谋,成为彰显英格兰民族文化自信的典型特征。然而,二战后英国国力大幅衰退,尤其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国加速了向美国转移世界权力的进程。在此影响下,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剧变,英国性不再是英国人引以为豪,用以区隔他者的民族特性,反而“变成了被他者化的客体,而原来所谓先进文明化身的‘英国性’,现在也成了异族眼中的怪异特质”(梅丽,2018:20)。小说《无辜者》无疑反映出麦克尤恩早年就已意识到“美国化”(Americanisation)对英国性的吞噬(阿布拉瓦内尔,2015:11)。这种想象书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文学中萌生的“美托邦”(Ameritopia)(阿布拉瓦内尔,2015:37),其原因在于“欧洲文化精英很难在文化上认同美国”(王晓德,2015:4)。
从最主要的叙事空间来看,麦克尤恩选择柏林展现伦纳德的生存困境,有意暗示出“美国化”成为欧洲国家,尤其是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维护国家认同和文化价值观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类似于战后英国状况的一则寓言”(Brown,1994:10),小说中伦纳德对英国文化中诸多民族性品质的异化感,也正是源于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型。在《无辜者》中,英国性异化危机的书写从伦纳德接触美国情报官员格拉斯开始。小说抓住了两个典型的英国性象征:言说方式和日常着装。在言说方式上,伦纳德处处留意自己的英式用语,时常使用标准、客套的英语句型。譬如,在首次与格拉斯的电话通话中,伦纳德精心设计了看似胸有成竹的开场白,“Leonard Marnham here. I think you’ve been expecting me.”(McEwan,1999:8)(“我是伦纳德·马汉姆。我想你在等我的电话吧。”)然而,格拉斯“严厉而干脆”的回复,立刻让伦纳德的矜持化为乌有,“让人家在电话里听出来那副窝囊相”(麦克尤恩,2010:13)。在日常着装上,小说出现了伦纳德对英式套装的不自信,他没有选择穿上剪裁精致的英式西服外套去和格拉斯碰面,反而觉得自己挑选“那件运动夹克衫和一条鲜红的针织领带”,更能“有那么一点美国式的强悍风度”(同上)。不难看出,初到柏林的伦纳德对自我异化困境的突围,建立在对英国性的反向理解之上。在伦纳德看来,传统英国人循规蹈矩、克己复礼的特性在自己身上显得“生硬古板,让人觉得可笑”(同上)。而格拉斯身上象征的美国性——务实、果敢、直率、开朗,更能让他消解潜意识中的自我异化感。
如果说伦纳德在柏林的异域地理空间中遭遇的异化感,隐喻出英国性的认同危机,那么他对美国流行音乐的迷恋,则深刻揭示了麦克尤恩对于政治空间建构法则的认知,即它是美国文化霸权战略的有序化生产,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无序化交锋之间动态平衡的结果。对于伦纳德而言,柏林的时间记忆“不妨用流行的美国歌曲来区分星期和月份”(同上:225)。柏林每月变换的美国流行歌曲突显出其文化输出中裹挟的情感力量。在伦纳德看来,广播节目“美国之声”中的流行音乐尽管内容如同儿歌一般天真,但是其“刚强有力”的节奏感却能让柏林隧道人员停下垒球比赛,三三两两跑向收音机,跟随《一天摇它二十四小时》边唱边跳,“似乎并不只是在音乐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而已,它是一首赞歌,一种典礼,他是这些球员团结在一起……”(同上:173)这种情感力量一方面再现了柏林政治空间中纯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物化效应,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冷战语境下人性的冷漠和自我异化。然而,这种情感修复维系的强度“只持续了三个星期,然后就失去它的魅力。……需要换另外一首来代替它……”(同上:173-174)可见,柏林作为政治空间的隐喻折射出麦克尤恩对人性复杂性的质询与反思。“柏林成为伦纳德蜕变和寻求自由之地”(Malcolm,2002:119)。麦克尤恩不仅用伦纳德这一寓言式人物完成对帝国身份危机的指认,也让伦纳德向读者提出一个隐含的价值悖论,即如何让自我在获得纯真的同时避免对他人之爱的狭隘和残酷。
4.0 浪漫之爱:可能的救赎
假如说小说借助多维叙述视角隐射了寓言阐释的复义性,以政治空间的建构法则彰显了自我异化感,那么小说不惜笔墨营造的伦纳德和玛丽亚的浪漫之爱,则充分展示了麦克尤恩借助于寓言叙事探究自我生存困境的突围之路。事实上,麦克尤恩“造境”式叙事手法,不仅体现了他试图揭开复杂人性的面纱,而且阐明了如何理解人性中的价值悖论。换言之,麦克尤恩在这部小说中如何定义自我救赎?寓言叙事何以能不拘泥于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单向度的阐释关系,进一步扩大到冷战历史语境,甚至启示当下社会关系结构的塑形?借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浪漫之爱”(Eros)的概念可以比较有力地呈现麦克尤恩以讽喻表达自我救赎的希冀。
“浪漫之爱”的概念出现于18世纪晚期,它关注个体的生活叙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亲密关系的变革》(TheTransformationofIntimacy,1992)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浪漫之爱”,认为它暗合了小说的兴起,属于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欲望、理想化投射和追寻构成了浪漫之爱的前提与核心元素(1992:39-40)。女性在浪漫之爱中不只是欲望的客体,也“积极地生产爱”(同上:46)。自19世纪欧洲文学以来,浪漫之爱的思想已经“介入到重构个体生活状况中”(同上:45),其文本表征与叙事方式密不可分。
在《无辜者》中,年轻的英国电子工程师伦纳德常被评论者认为是在浪漫之爱中从纯真走向经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个体纯真的丧失占据小说主题的重要位置”(Head,2008:91)。这一观点不仅反映了“纯真之谜”吊诡之处在于它衍生出的“经验”,也指向伦纳德的情感历程作为整个叙事进程的驱动力。在纯真与经验两个世界之间,伦纳德通过与玛丽亚炙热的身体激情与欢愉,触摸到了“天真无邪和深谙世故之间的那条界限”(麦克尤恩,2010:102),正是源于“他在这两个秘密世界之间跋涉时所消耗掉的这段时间里,他才是那个真正的自我”(同上:127)。纯真价值的认知正是借助于经验而获得。这个嵌入于文本内部的批评折射出麦克尤恩对于纯真话语的反讽解读。在伦纳德的身上,纯真与其说是产生浪漫之爱的特质,不如说是他得以接近自我本真的特质。
从传统的情节方式来看,《无辜者》的线性叙事模式表现出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诉求,应该纳入“以因果关系作为联结因素,形成具有共同目的性的事件组合的轨道中”(Richardson,2006:167)。既然如此,为何仍有研究者质疑“纯真”在叙事进程中的联结性?“伦纳德在于玛丽亚关系中的纯真妨碍了他处理情感与心理遭遇的复杂性。”(Head,2008:99)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浪漫之爱”中蕴涵的特质——欲望,作为一种叙事驱动力,调适出叙事进程的既定方向,即欲望驱动下的情节运行指向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唯乐原则”。小说中,玛丽亚似乎只是欲望的客体,她的存在看似只是对于情节驱动力的排解。然而,细察之下,读者可以发现麦克尤恩将欲望映射到叙事进程的真实用意:作为接近自我本真的投射性认同。玛丽亚并非只是欲望客体,而是作为伦纳德自我镜像的投射对象而存在。“浪漫之爱依存于投射性认同,即激情之爱的投射认同,使投射性伴侣彼此吸引和相互联系”(Giddens,1992:47)。伦纳德返回伦敦过圣诞节的四十八小时里,就觉得“离别使他痛苦不堪……他那么受人疼爱”(麦克尤恩,2010:216)。在柏林时,“居然有个姑娘仰仗他的庇护”(同上:217)。毫无疑问,欲望摒弃了之前爱欲的身体感受,转而隐喻为自我不断强化的投射性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伦纳德与玛丽亚的浪漫之爱虽然刻意描写了他们沉迷于性快感,但是伦纳德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却注入了身体暴力和主体性建构的诉求。小说中浪漫之爱的特殊性也正是在于伦纳德采用暴力形式维护自我纯真。自我在客体对象的投射性认同,形塑出想象性的自我,这种自我“将个人的自主置于道德责任的对立面,并且将人际相互影响的广大领域,甚者他们之间最亲密的领域,排除在道德判断之外”(鲍曼,2002:110)。因此,对于小说第八章中伦纳德对玛丽亚性虐待的“过火表演”(麦克尤恩,2010:144),以及第十八章中肢解奥托的血腥场景,读者并不难理解伦纳德对自我纯真的辩解。可见,麦克尤恩笔下的伦纳德并没有真正拥有纯真的情感,更像是逃避经验,“成为”(becoming)纯真的青年,面临的更多是情感困顿和道德救赎。
需要指出的是,麦克尤恩对于浪漫之爱的否定性书写也在提醒读者关注寓言化悖论的救赎力量。在爱的残酷、自私、狭隘书写背后蕴含着肯定性的意义。小说后记中,耄耄之年的伦纳德辗转收到玛丽亚的来信,解开了心中多年的疑团。当伦纳德怀揣信件重返柏林墙下,他经历了生命中的顿悟时刻,最终能够以宽容的姿态达成爱的和解。虽然伦纳德仍然坚信自己的伦理选择出于对纯真的追寻,但是这种追寻实际是“对事物的易逝性的欣赏,对把它们赎救到永恒的关注,是寓言的最强烈的动力”(杨小滨,1999:75)。正因为如此,在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看来,《无辜者》的阅读带来“长久的共鸣”(Malcolm,2002:110),犹如余音绕梁。实际上,这一情感共鸣折射出寓言叙事所能表述的经验层面的真实,转喻出了残酷的生存本相。
5.0 结语
在《无辜者》中,麦克尤恩通过纯真青年伦纳德形象负载的隐喻意义,实现了传统寓言中文本能指和意义所指之间的勾连,隐喻出冷战意识形态交锋中,自我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在这一传统叙事结构中注入了寓言阐释的复义性,由此突破了言与意二分的叙事语法成规,吸引读者去分辨表层故事与意义所指裂隙中隐含的真实。寓言阐释的言说困境并未影响麦克尤恩对冷战语境下政治空间建构的广角式呈现。麦克尤恩讽刺了冷战时期“美国化”影响的焦虑,以及这一现象造成的英国绅士形象他者化,其目的是突显“纯真具有双面的特质”(同上:62)。值得注意的是,麦克尤恩并未真正认同美国文化霸权对人性残酷的情感修复力,而是致力于谋求主体以投射性的自我认同,消解英国文化自信中的异化感,反映出麦克尤恩对二战后英国重塑帝国身份的忧思。不难发现,在对浪漫之爱的讽喻性书写中,麦克尤恩传达了保持纯真的情感方案,惟有以宽恕之心接纳他人的难解与选择,才得以完成与自我和解,体现了强烈的文化救赎心理。《无辜者》体现了麦克尤恩创作风格转型背后的寓言式思索,也体现了作者对后现代主义一贯的审慎态度,力图促成读者在解读寓言叙事中撬动喻体纹理下的意义裂隙,去推敲人性纯真指涉的真实,其背后蕴含的和解与救赎的生存哲理值得当今社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