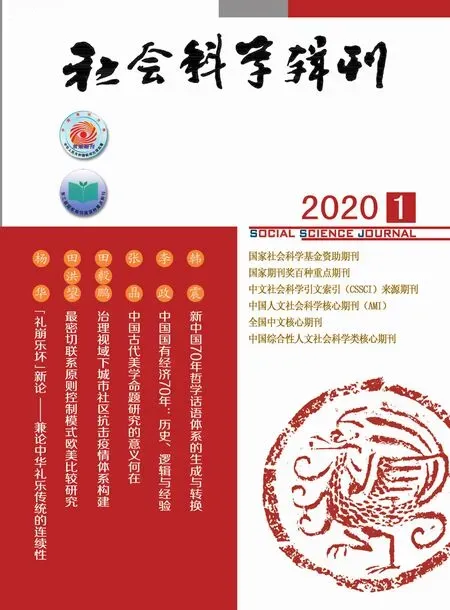新中国70年哲学话语体系的生成与转换
韩 震
任何知识体系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用以阐释并展开本学科的学术体系。一种学科的话语体系必须能够恰当地反映这一学科的性质和特点,这种话语体系才能够成为促进这种学科正常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话语形式。就此而言,学科体系的性质和发展规律决定着话语体系的性质和生成规律。但话语体系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形式,它反过来也能够促进或妨碍学科体系的构建和此学科的学术体系的展开。
一、有生命力的哲学话语必须有特定时代的实践基础
不仅学科体系决定着话语体系,而且话语体系连同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也深受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的影响,因此每个时代的话语体系都有自己特殊的时代印记,都是基于特殊历史时空体系中的人类实践而形成的。人创造自己的生活,也创造着自己的话语;人通过自己的话语叙述着自己的生活,并且通过话语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追求。在这种话语追求中,话语也成为塑造生活的创造性因素。
不同时代的人类实践活动,必定造就不同的话语方式,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古代,哲学的话语体系往往表现为朴素的、直观的甚至是猜测的,其话语方式往往是对世界本质的表达。在中国先是 “金木水火土”和 “天人关系”的演化进程,随后是 “气”与 “理”的思辨;在希腊也是从 “水”“气”“火”的直观到“原子”“理念”的思辨。到了大工业时代,近代学科化的科学技术日益成熟,因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主体性哲学的话语体系繁荣起来。哲学话语也就出现了 “内在性”的维度,如 “心灵”“先验形式”“感性直觉”“思维方式”“自我”或“主体”“客体”“对象”等等。到了当代,因为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哲学就涌现出 “主体间性”“不确定性”“涵义”“指称”“结构”“意义”等话语,或者说,现象学、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的哲学话语就应运而生了。
与此同时,在同一个学科、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历史进程之中,也存在话语方面的差异。换言之,没有适当的话语,就难以产生相应的学科,也难以产生特定的理论。就如恩格斯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只有那些符合社会实践需要或者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现实作用和时代意义。譬如,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让各种话语体系都有展示自己主张的社会语境;而当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儒家的话语体系就显得比其他话语体系更加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或者说,儒学更能符合封建统治者或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因而儒家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话语体系。如果没有社会的选择性需求,只是董仲舒倡导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可能成功。话语的生产、流通、传播、效应都是社会的产物。
在修辞学的意义上,同一时代某种学科的话语体系也不是具有同等的时代表达力。话语表达的差异,会影响语言的穿透力和说服力,因而也就影响这种话语体系的时代表达力,因此,“以言者尚其辞”(《易经·系辞上》),人们必须在修辞上下功夫,才能提高语言的表达力。同样地,在学科探讨和论辩中,我们必须提炼出更适合学科特点、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话语表达方式,才能促进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发展。孔子曾经说: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话语的力量首先要基于真理的认识,这是基础性的;只有真理性的思想,才能有真正的思想影响力。但是,真理也需要符合且贴切地表达客观性真理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就是话语的力量。没有恰当的语言或话语方式,就无法恰当地表达意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倒不出来”。为什么有些话语体系或话语方式更具有影响力,那是因为这种话语体系或话语方式更能反映某种特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点和特定时代的实践要求。
二、有生命力的哲学话语必须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由于近代以来作为学科的 “哲学”是受欧美思想影响的产物,连 “哲学”这个词都是日本人用汉语从西学的 “philosophy”翻译过来的,因此,近现代中国哲学的话语方式就必然是在中西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塑造的。中国的哲学研究明显带有西学影响的痕迹,不仅有许多西方哲学概念转换为中国词语,也有许多中国理念和思想转换为与西方哲学相近的概念和命题。一方面是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经典的大量译介,开启了让源自西方的、作为学科的哲学开始了讲汉语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开始学着用中国语言讲述源自西方的哲学学科。当把西方哲学放入汉语的语境中时,西方的原典思想也就同时被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结构化或者格式化了。另一方面从西方学了西方哲学又回到中国的学者们,如胡适、冯友兰等人,按照他们学到的或理解的西学话语方式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系统地梳理、重构与重述,中国传统思想和智慧也就被以西方哲学的逻辑和话语方式结构化了。因此,当代中国哲学话语是中西互动的产物,源自西方的哲学也开始成为中国人理解的 “西方哲学”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同样经历了中外思想的相互阐释、相互塑造的过程。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其理论体系和话语方式也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与外来理论的互动中展开的,当然中国革命的实践是这个相互阐释、相互塑造过程的社会基础。从最初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比较学术性的介绍,到后来基于革命实践活动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中国共产党人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首倡 “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2〕,希望能够让来自欧洲、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说与实践活动有关联的话,说现实生活中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话。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则更多地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因此更倾向于考虑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认为,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特点空谈马克思主义,而必须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毛泽东的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觉进程的理论和实践的起点,也开始了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语的进程。
三、新中国的哲学话语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为基础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飞跃,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学科的学术研究和话语方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在体制范围内,所有的哲学研究——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还是伦理学、宗教哲学、美学及其他部门哲学——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审视,原来的哲学话语体系与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迅速地马克思主义化,如 “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此等等。1949年以来,中国的哲学学科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哲学研究的话语变化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一部分。在中国哲学经历马克思主义洗礼的过程中,苏联教科书哲学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当然这里面主流应该是积极的,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是,即使在这个 “起步”阶段,中国哲学及其话语也不是简单地抄袭苏联教科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话语仍然有许多中国的特色。中国哲学研究必然反映中国社会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中国哲学的话语表达不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进程,而且也反映了不断变化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譬如,同样是实践的观点,在中国就创造性地形成了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等有浓厚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同样是辩证的观点,在中国就往往讲 “两点论”“一分为二”或 “合而为一”等范畴,以及 “矛盾”这一对 “contradiction”非常中国化的翻译表达。①即《韩非子》所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同样是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在中国往往就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化进入了更加制度化和学术性的发展阶段,因而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也塑造着中国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除了中央党校及地方和部门党校之外,还有官方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及地方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更有数量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哲学院系,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主要的教学和研究内容。长期以来,无论学科体系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哲学学科内排在序列第一位的二级学科。除此之外,还有作为三、四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例如,“哲学原理”的话语就是中国哲学研究第一序列的话语,当我们说 “哲学原理”时,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哲学都够不上 “原理”的称号。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传统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等都以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哲学话语作为基础性话语,并且在此基础上讲述本学科的话语,以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话语丰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改革开放之后,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希望其他哲学二级学科的研究与教学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益补充。
最后,既然中国哲学研究的所有二级或三级学科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那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在中国哲学研究和话语表达方面也就体现得更加自觉。中国哲学的话语,一直跟随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实践的步伐而改变。实际上,“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变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4〕。中国哲学学科的话语使用,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四、中国的哲学话语变化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开启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复兴伟大实践的逻辑起点,同样也开启了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的新起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大致走过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哲学话语同所有的学科话语一样,也反映和体现着社会历史的变迁。
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自1949年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一方面在国内,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旧的敌对力量保持压制或曰 “专政”;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环境先是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围堵与遏制之中,甚至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与美国进行了一场热战,即抗美援朝战争;之后,随着中苏论战和关系恶化,中国虽然以 “三个世界”的理论调整了原来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垒的看法,但基本的话语论调仍然是 “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而且,由于刚刚结束战争,当时的领导人多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因而话语表达仍然带有战争年代的特征,不仅表现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代表的政治斗争话语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如划分工作领域时所说的 “农业战线”“工业战线”“交通战线”“教育战线”“文化战线” “思想战线”,又如农村夏收、秋收时经常说的 “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好夏收、秋收 ‘战役’”,如此等等,因而在这段时间,在哲学话语里也往往充斥着矛盾的斗争性和对抗性。尤其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之中,不仅关注矛盾辩证法,而且特别关注矛盾对抗性的一面。关于 “一分为二”和 “合而为一”的讨论,不仅后者被看作是对前者的某种呼应和补充,而且很快也被批判的声浪所淹没。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是辩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过分强调矛盾对抗性的一面,忽视了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一面,也就容易走向片面和极端化。这种片面和 “左”的话语方式,既是当时社会实际逻辑的产物,也对社会 “左”的趋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从1978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这是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是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是主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白猫黑猫论”“小康社会”“摸着石头过河”成为家喻户晓的话语。最初人们往往只关注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增长,随着发展的步伐逐渐加大,人们也意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也是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发展,“先进文化”“文化繁荣发展”“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概念进入公共舆论和话语场之中。在这个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别是工科背景的专业人士逐渐走上领导岗位,因此社会话语开始出现了 “工程化”的特点,如 “希望工程”“春蕾工程”“211工程”“985工程”,连最不具有工程性质的思想领域也出现 “铸魂工程”的概念,如此等等。这是因为社会发展需要工程,而工程话语就影响了社会生活的话语。另外,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许多国外的话语尤其是欧美的话语,也伴随着不同的思潮涌入中国的话语场,如 “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文化差异”“价值冲突”“普世伦理”。但是,外来的话语往往只是刺激了中国人的思考,扮演了 “他山之石”的角色,而在中国真正起作用的话语往往是已经中国化了的概念。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还是在中国发展的“河流”中摸着作为中国问题的 “石头”,创造了许多具有中国气派和特色的话语。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5〕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哲学话语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具标志性的就是 “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第一的”和 “实践是真理标准”的观点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哲学界对国外哲学特别是欧美哲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也以差异性视域大大开拓了中国人民的视野,激活了曾经一度被禁锢了的中国人的思想。当然,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也给中国人民带来许多困惑或不安。在这个阶段,中国哲学界主要或是忙着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想,嘴上说的往往是半吊子的西方哲学的话语,或者就是学着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从西方哲学话语中寻找自我丰富的资源。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哲学研究的话语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基础上,国外特别是西方哲学的话语又重新大量进入中国哲学话语的论域之中,如在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之外,哲学研究也越来越借助 “生存论视域”“价值分析”“权力分析”“语言分析”“话语分析”等等;(2)话语样态日益多样化,不仅部门哲学话语日渐增多,如历史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语言哲学、文化哲学等,而且这些部门也带来了许多新的话语、概念和范畴,如 “价值”“结构”“历史性”“生存意义”“认同感”等等;(3)彰显人的主体性力量的话语得到发展,如 “认识的主体性”“人学”“以人为本”等等;(4)具有改革开放时代性特征的话语在哲学中得到凸显,如经济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发展哲学的学科开拓,以及对 “发展”“价值”“和谐社会”“文明差异与对话”等概念的话语阐释;(5)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也在改造中吸纳了许多西方的话语,形成新的哲学话语,如 “主体性”“主体间性”“人学”“价值认识”“认同与归属”“在场”“结构”“解构”等等。
三是从2012年到现在仍然进行中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原本粗放的发展开始走向高质量发展,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催生了许多新的话语,这些话语在哲学中也有所反映,譬如生态文明的哲学阐释、创新意识的凸显。更加明显的是,基于 “四个自信”的话语自信也愈加彰显。这种自信不是再回到自我封闭的状态,而是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自信。当然,新时代似乎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合题。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广阔,不仅走出了近代以来形成的某些自惭形秽的自卑心理,越来越自信地参与国际事务、贡献中国智慧,而且开始从更具普遍意义的角度思考国际关系,提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不仅行百里路者半九十,而且许多地缘政治的结构性问题让许多势力展开对中国或明或暗的遏制,尤其是美国的霸凌主义已经按照零和思维对中国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围堵,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与之相适应,一方面是中国社会话语越来越充满文化自觉与自信,我们不仅更加礼敬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开始提出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应对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不仅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而且也意识到必须以更加持续不懈的奋斗精神做好伟大斗争的准备。大家不难看出,如果说1949年以来是一个 “斗争”与 “对抗”的话语阶段的话,那么1979年之后是一个 “合作”与“和谐”的话语阶段,而2012年之后的社会发展就是前两个阶段的合题。大体上可以说,这是既要合作共赢,也要通过斗争争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过程中,排除各种干扰、争取更加有利的环境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目的是在实现民族振兴的同时,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合作与斗争相互纠缠交织且极为复杂的辩证统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更加需要科学、系统的战略性思维。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就需要 “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6〕。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哲学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往往是新术语、新概念的凝练者,因此哲学家要善于凝练反映中国问题和时代发展的标识性概念,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摆脱跟在别人后边跑、学着别人的话语讲话的境地。在话语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融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话语资源。
中国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中国并不是要推翻原来的世界秩序,而是随着世界力量的结构性变化更加合理地调整国家秩序。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秩序的变革是必然的。世界的哲学地图也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或接受,中国哲学曾经是边缘性的,甚至是被 “他者”塑造的。中国学者曾经跟着别人讲哲学,但在讲述的过程中,中国哲学掌握了许多话语,也就尝试着用这些外来的话语讲自己的问题。但使用这种话语,就类似中国人穿上未经改造的西服,总是有些不合身的感觉。现在,我们开始基于自己历史的传统话语,借鉴外来的话语方法,原创性地讲述21世纪的中国哲学话语了。“美丽中国”“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话语,已经展示了中国话语生产的能力。我们可以期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一个新的哲学思想和话语产生的时代。我们开始做自身发展进程的讲述者。这种讲述本身,不仅是对历史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拓展,同样也是对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话语的扬弃和超越。中国的崛起不应只是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崛起,也应该是思想力量的崛起、哲学思想塑造力量的崛起、哲学话语力量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