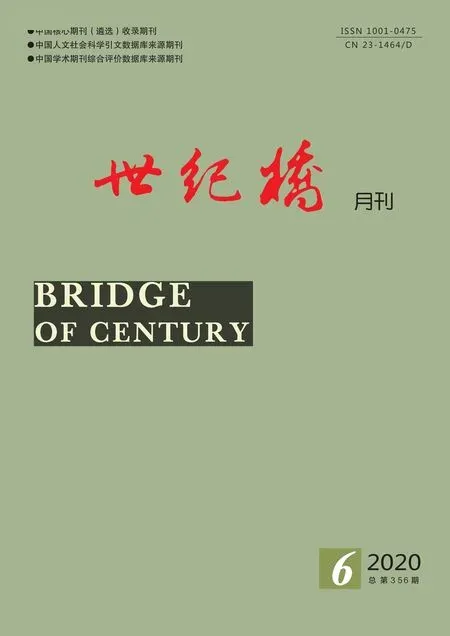毛泽东协商建国的理论与实践述论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回望历史,从协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准备,到适时发起、精心筹备、顺利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再到最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整个过程,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起的主导作用,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毛泽东的“民主联合政府”思想,为协商建立新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努力同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绝大多数人的革命政权。这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权理论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和俄国实际,强调无产阶级要尽最大努力联合同盟军,从而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合建国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立这样的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后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毛泽东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在坚持了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却又有新的发展,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详细论述,他认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所面临的建国环境,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大国,面临中外反动势力的合围绞杀,敌人力量异常强大,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方能取得革命胜利。因此,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步“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但这个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基于此,毛泽东将当时世界上国家体制划分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三种形式。他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必须采取最后一种形式,即“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2](P.675)他进一步指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都应采取这种国家形式。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指明了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2](P.672)。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构想已经有了系统思考。
抗战后期,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毛泽东考虑并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易于动员的政治口号。1944 年8 月17 日,毛泽东在谈判代表董必武向周恩来的请示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3](P.536)9 月1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即讨论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据此,林伯渠在9 月15 日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中间党派的大力支持,成为除国民党外的共同政治诉求。半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就“联合政府”作了说明:“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3](P.588)联合政府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4](P.276)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强调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5](P.1030)提出了在抗战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一般纲领:“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5](P.1056)为什么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自执政以来一直保持寡头专政,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战争还存在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即使在抗战胜利后,也要面对国内反动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反民主势力对和平民主的威胁。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程序,先召集一个圆桌会议,“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在取得了民族独立后,再“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5](P.1029-1030)。《论联合政府》成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除国民党之外其他政党的共同纲领,他们一致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总结革命经验,于1948 年4 月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人民大众所组成的统一战线十分广大,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6](P.1313)鲜明地指出了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前途。有人担心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会选择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针对疑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已有说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集中阐述了新中国“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而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工人阶级领导是因为中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完成国家复兴的任务,历史只能选择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工农联盟是因为工农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反帝反封建的主要依靠力量;现阶段的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6](P.1475),这些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这样就在《论联合政府》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专政的内涵,对政权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不难发现,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马克思的“人民”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下层民众,而毛泽东的“人民”不仅是一个反映下层民众的阶级概念,而且是一个相对于“敌人”的政治概念。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7](P.205)因此,“人民”概念反映到“民主联合政府”上来,也就有了相应的内涵变化。首先,国民党由联合对象变成了打倒对象,新中国的联合政府不包括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其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在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其在政治上代表各民主党派,也就构成了联合政府中的多党合作对象;再次,联合政府不单是政党联合,也包括阶级、团体、个人的联合,这也就可以解释毛泽东原来倡议的党际协商的“民主联合政府”变成了人民联合的“中央人民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新中国临时宪法的政策基础,成为建立国家政权的指导纲领,也标志着毛泽东成立新中国理论的彻底成熟。
综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明确回答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重大问题,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建立新中国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二、毛泽东是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发起者,为建立新中国拟定了设计思路
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专制,撕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发动内战,团结建国由此受阻。从1947 年7 月开始,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全面反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10 月10 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第一条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P.1237)此时,毛泽东虽已提出成立不包含国民党的民主联合政府宣言,但到1947 年底的“十二月会议”仍然认为“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宣言还仅仅是宣言。
那么,什么时候时机才算成熟呢?毛泽东认为,要蒋介石威信更加破产、部分解放区连成一片的时候。面对战争溃败,国民党依然垂死挣扎,于1948 年3 月29 日至5 月1 日召开“国民大会”(史称行宪国大),妄想在政治上延续法统。为尽快结束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针对国民党上演的独角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认为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且适逢重大节日,故于1948 年4 月30日正式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毛泽东对“五一口号”初稿进行了精心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第四条和第五条的修改:初稿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改为“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不仅突出了“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作用,巩固了统一战线,而且发出了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号召。删除初稿第五条,重新起草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改动成为“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标志着中共中央不仅正式宣告要成立新政权,而且提出了相应的建立程序,开启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精彩篇章。
“五一口号”的发布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在香港大本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日举行集会讨论,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派协商、不搞一党专政,其主张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1948 年5 月5 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与无党派人士12 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并通电全国,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民等之本旨”,要“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其他各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各种形式的宣言、声明、通电响应。新政协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标志着各界赞同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愿为此而奋斗。
“五一口号”不只是宣传口号,更是行动宣言,毛泽东随即着手筹划成立新中国。1948 年5 月1 日晚,毛泽东致信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代主席沈钧儒,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步骤、时间、会议名称等事宜诚恳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8](P.90-91)8 月1 日,毛泽东回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 月5 日电,解释“因交通阻隔”致回复不及时请“即祈谅察”,钦佩他们的响应“并热心促其实现”,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9](P.330)这种党派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对话,意味着围绕新中国建立的协商已经开始。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在于,一是国家大法对政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二是政党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来执掌政权[10](P.5)。因此,毛泽东在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时就已加紧部署拟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五一口号”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邀请民主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事宜)——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广泛的人民代表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联合政府(制定国家大法,选举成立中央政府)的新中国政权成立程序。然众所周知,新中国政权并不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建立的,而是政治协商会议行使了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直接由政协会议选举产生。
“五一口号”发布后的半年多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使原来的设想难以为继,一是军事政治形式发展迅速。军事上,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从1948 年11 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政治上,中间党派广泛支持中共联合政府主张,国民党政府处于极端孤立状态。二是召开大规模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条件不成熟。尽管我党此时已取得巨大优势,但国民党仍控制着广大地区和重要城市,敌特密布横行,交通安全堪忧。三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尽快建立新政权成为当时急切的政治需要,这也与斯大林对刘少奇1949年中期访苏时“希望中共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想法相吻合。四是民主人士的建议。章伯钧、蔡廷锴等人依据形势变化,建议由新政协代行人大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基于以上考虑,毛泽东及时作了程序上的调整,1948 年11 月3 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高岗和李富春的电报,“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11](P.815)据此,1948 年11 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就如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即由新政协产生或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问题及宪法草案问题,达成“先行交换意见,留待筹备会讨论解决”的协议。[12](P.214)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已经不提“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而是讲“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6](P.1379)这一程序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得以通过,随即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经协商一致后正式通过了由新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12](P.267),建立新中国的程序正式确立。
为了解决程序更换后的政权合法问题,毛泽东主张把政治协商会议开成一个更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国性大会。中共中央指示“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11](P.815)经协商后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不允许参加。”[13](P.164)这样既保证了代表的极其广泛性,又保证了代表的政治严肃性。经过反复酝酿与多方协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有45 个,包括党派代表、团体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和特邀代表;共有代表662人,包括正式代表510 人,候补代表77 人,特邀人士75 人。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党派代表之一来组织和参加的。这样广泛的人员构成代表了广大的民意,得到了各方的肯定。沈钧儒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筹备会上发言说:“今天所开始筹备的这个新政协会议,虽然不是通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因为它将尽可能广泛地包括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乃至各种职业、各种信仰的广大人民的代表,它的实际威信,一定是不亚于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13](P.200)林伯渠在1949 年9 月4 日的政协代表茶话会上讲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P.301)。由此,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充满自信地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8](P.343)而一些七八十岁从不参加政治性会议的老辈人士如张元济、周善培等,不顾衰老毅然参加,“真可以代表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故本席附带报告一下”[13](P.337)。由此亦可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意基础之广泛。
三、毛泽东是协商建立新中国的领导者,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多方面贡献。
“五一口号”发布后,毛泽东一方面指挥解放战争,一方面筹划政权建立,在军事继续南下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北上运动。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配合下,毛泽东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成为协商建国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一)对民主力量的组织和思想的引导
新政治协商会议是民主力量的大集合,为尽可能争取多数尤其是有重要地位的民主人士参加,毛泽东付出了极大努力。首先,在策略上提供指导。如1948 年8 月1 日,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的电报中指出,应“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9](P.331)其次,重视组织机构的设立。8 月24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将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专管政协、海外及国统区工作。中共中央于9 月26 日通过这一批示,并决定扩大其职责范围,包括国统区、少数民族、政权统战、华侨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等工作,在当前是具体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14]。再次,与民主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筹备期间,毛泽东多次致电或致信民主人士,内容涉及邀请参会、关心问候、协商事项等。如9 月29 日第一批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时,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亲自起草欢迎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15](P.45)对于身份特殊者,毛泽东更是关心非常,如两次写信给宋庆龄邀请其参会,并率党内主要负责人到北平前门火车站等候,亲自登上车厢迎接;亲自布置程潜北上的有关保卫和接待事项。此外,毛泽东经常与已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们进行广泛协商讨论,保证了广大民主人士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为具体商谈新政协筹备事务,毛泽东提议并审改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草案,于1948 年10 月11 日致电东北局,要求召集民主人士对此“恳谈一二次,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同意,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9](P.360),同时电告了上海局与香港分局。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了诸问题的协议,为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提供了依据。此外,毛泽东十分重视在思想上引领民主人士,通过座谈、交流和考察等活动,使民主人士对中共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增强了信任认同。在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敏锐警觉,以其犀利的笔锋直触要害,拨云见日。如针对少数党外人士赞同国民党“划江而治”和企图再谋“第三条道路”,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系列文章,明确回答了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新中国将实行怎样的制度以及民主人士及其党派的前途等问题。这些文章启发了民主人士,他们公开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16](P.180-185)从而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筹建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对重要文件的修改和问题的确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文件是奠定新中国诞生的理论基础。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对它们的制定极为关注,尤其是《共同纲领》毛泽东作了精心修改。据统计,仅对第三次起草稿就有200余处改动,此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13](P.254),可谓呕心沥血。1949 年9 月17 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出席并听取了相关筹备工作报告,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原则通过以上三个文件,提交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大会讨论;同意将大会宣言的起草及国旗、国歌、国徽等拟制工作移交大会。9 月21 日晚,筹备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8](P.342)会议历时十余天,三个文件全部通过。依据选举规定,毛泽东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言郑重声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大会圆满完成了以协商方式创建新中国的伟大使命,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
会议是在充分协商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建议发挥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如确定国歌、国旗、纪年、国徽等。1949 年9 月25 日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郭沫若、马叙伦等共18 人参加的协商座谈会,就以上争议诸问题进行协商讨论。会上,毛泽东在听取了大家意见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国歌,毛泽东同意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且认为“坚持原有歌词为好。”国旗争议最为激烈,主要集中于国旗是否应体现国家特征、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是否妥当。毛泽东认为:国外主要国家的国旗也并没有该国的什么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他进一步讲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四个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不仅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是“较好的国旗图案”。采用公元纪年虽大多数人赞成,但有人担心老百姓可能兼用其他纪年。针对此种考虑,毛泽东表示,不能强制老百姓不能用其他纪年,但政府对采用哪个年号还是要有个决定。关于国徽,因大家对当时已征集到的国徽图案都不满意,毛泽东就提出建议:“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13](P.264-265)以上争执的问题经毛泽东的解释说服后,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取得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三)对民主协商的倡导和积极的践行
民主协商的优良作风是协商建国圆满成功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在党内积极倡导号召,奠定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其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成为民主协商的典范。
毛泽东是民主协商的大力倡导者。在处理与党外民主人士的关系时,他要求共产党人以诚恳态度、平等精神、民主作风、宽容胸怀与民主党派进行团结合作。1948 年4 月27 日,毛泽东在写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的信中指出,拟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统一,不得强制。”[9](P.306)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指出必须克服“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6](P.1437)。毛泽东的报告为协商建国奠定了良好的作风基础。
毛泽东是民主协商的积极践行者。从他致民主人士的信件和电报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字里行间饱含的谦虚尊重之风、平等协商之情和丝毫无强迫之意,足见毛泽东同民主人士协商建国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后,毛泽东十分注重与他们在思想政治上的沟通,特意发布《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有关党委“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17](P.858)针对部分共产党员的牢骚,毛泽东耐心地解释:政协会议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参加,否则就是党代表会议;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社会联系很广,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这是我们所不能代表的;经过我们的长期工作,他们是能够进步的。这些解释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同意见,统一了党内思想,推进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
毛泽东非常重视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争取给他们尽可能多的发言机会。1949 年9 月26 日凌晨三点,他函告周恩来,要求逐一通知那些“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9](P.580)及时写好讲稿,以免时间上来不及。在毛泽东的倡导和践行下,六分之一的代表作了发言。新政协会议的民主精神,赢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誉。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说:“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轮番地举行,保证了大家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其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诚如胡乔木所总结的那样:“召开政协和拟定建国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胸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来一种宝贵的传统。”[18](P.563)这种优良传统传承下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四)对协商组织的创建和制度的确立
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创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协商组织,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新中国的长远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及时提出在新的基础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初步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针对有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委会上表示,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要有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要固定一下,就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毛泽东强调政协会议的大团结大统一。无论是代表的广泛参与,还是作风的积极营造,都充分反映了大团结大统一的要求。因此,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8](P.342),为人民政协奠定了基本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顺利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协商组织的成功实践。毛泽东审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明确了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一性质地位,也使人民政协在法律上得以确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毛泽东为这一制度的形成注入了红色基因,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6](P.1257)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民主党派的认可和拥护。1949 年1 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重要人士55 人联名发表声明,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领导地位的正式确定。二是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局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6](P.1437)确定了革命胜利条件下多党合作的思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并提出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的联合候选名单”,从法律上保证了各党派在政权中的合作;且这个多党合作是长期合作、稳定合作、全面合作,形成了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制度格局。三是以政治协商为主要实现形式。体现在筹建新中国的每一重大问题都由各党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后再进行。如筹备会常委会成员六人有四人为党外人士、筹备会六个小组三个组长为党外人士,亦可见协商之真、协商之广、协商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