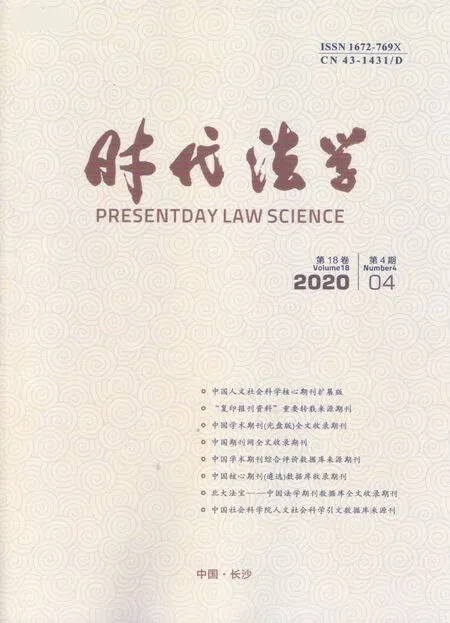论国家资格理论在实践中的适用
——以民国时期西藏为视角*
曾 皓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问题的提出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蒙元时起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方正式行使管辖权。”(1)朱晓明.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红旗文稿,2012,(4):16-21.但是,在民国时期(1912—1949年),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并干涉、阻扰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正常行使国家权力,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1939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司法院字第143号指令就指出:“中华民国之成立已阅19年,政府颁行一切法典,无论行政、司法,举不能适用于蒙藏地方。”(2)张晋藩.20世纪中国法制的回顾与前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45.1941年达扎活佛继任摄政以后,原西藏地方政府(本文所说的“西藏地方政府”如未加特别注明,都是指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又擅设“外交局”,妄图以“独立国”自居,居然将中央视为与之对等的“外国”(3)徐百永.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实践与检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43.。达赖集团及一些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据此认为“西藏在民国时期是‘事实国家’”(4)周伟洲.西藏通史·民国卷(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26-29.。一些西方的国际法学者也附和这种观点。例如,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于1960年了公布了《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该报告声称:“西藏在1912—1950年间拥有自己的人民、领土以及政府;并且,当时中国的法律不能适用于西藏,中国的法官、警察、军队以及政府代表都不在西藏。因此,民国时期西藏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国家。”(5)George N.Patterson, The Situation in Tibet[J]. China Quarterly, Vol. 1961, No. 6, 1961, pp.81-86.范普拉赫在其1987年发表的专著《西藏的地位》中也认为:“1911—1950年间,西藏具有国家资格的本质属性(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tatehood),因此至少在这一时期,西藏是独立的事实国家。”(6)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M].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87, p.140.时至今日,上述观点在境外国际法学术界仍然甚嚣尘上。据作者查证,2009—2020年,全球著名法律期刊数据库HeinOnline共收录了三十多篇“西藏问题”的英文国际法论文,其中支持或论证“西藏独立”的就近二十篇(7)See AmyKellam, Suzerainty and the 1914 Simla Agreement between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Jus Gent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egal History, Vol. 3, No. 1, 2018, pp.155-180; Maria Adele Carrai, Learning Western Techniques of Empire: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New Legal Framework for Managing Tibet,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0, No. 4, 2017, pp.801-824; RobDickinson, Twenty-First Century Self-Determin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Kosovo Status Settlement for Tibet,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26, No. 3, 2009, pp.547-582; Valerie Epps, Evolving Concepts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Legal Status of Tibet,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2, 2008, pp.217-242; LobsangSangay, Legal Autonomy of Tibet: A Tibetan Layer’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2, 2008, pp.335-356.。我国学术界已经从历史学的角度充分地论证了民国时期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8)例如,祝启源等著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多杰才旦等著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王贵等著的《西藏历史地位辨——评夏格巴〈藏区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郭卿友著的《民国藏事通鉴》、徐百永著的《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实践与检讨》等专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我国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等多个关于西藏的白皮书中也从历史学的角度有力地驳斥了“西藏在民国时期是独立国家”的错误言论。不过,我们还有必要从国际法中的国家资格的角度阐释清楚以下问题:为什么说西藏地方在民国时期控制了一部分地区与人口,并成立了有一定程度自治权的政府,西藏仍然不具备国家资格,不是国际法上的国家?如果我们把这个法律问题说清楚,将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层面开展法理攻防战,使我国政府一再申明的“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观点在国际上更具有说服力。本文将对上述国际法问题做一些粗浅的研究,以期能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有所裨益。
所谓国家资格(statehood),是指一个在确定领土上建立的政治实体,需要具备哪些特定要素,才能成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即建立国家的标准。国际法中并没有关于国家应当如何产生与创立的理论与规则,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也一再阐述:国家的成立及其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取得不决定于他国的承认。例如,在“波黑诉南斯拉夫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适用案”中,国际法院就认为,国家承认不是新国家成立的构成要素。因此,国家的创建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9)Vaughan Lowe, International Law[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1.。然而,一个政治实体要取得国际法律人格,以致其能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则属于国际法规范的事项。所以,判断一个实体是否具备国家资格是个法律问题。国际法学者一般习惯于把一个政权机构对领土实体(territorial community)行使有效权力,以及该实体与其他类似实体进行国际交往的一系列事件,作为判断该实体是否具有国家资格的标准(10)James Crawford, State [DB/OL]. Max Planck Encyclopedias of International Law, http://iras.lib.whu.edu.cn:8080/rwt/MPEPIL/https/N7ZGT5BPN74YA5DBP6YGG55N/view/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1473?rskey=AHqzQa&result=1&prd=MPIL,2007年4月上传,2020年5月10日访问。。规定国家的构成要素,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法规范是1933年《蒙特维的亚公约》第1条:“(a)定居的居民;(b)确定的领土;(c)政府;(d)与他国建立关系的能力。”这“四要件说”“客观且价值中立(value-free)”,因而得到了国际法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国际法学术界普遍认为,1933年《蒙特维的亚公约》关于国家资格的“四要件说”已经成为了国际习惯法规则(11)Hilary Charlesworth, Christine Chinkin, The Bounda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 Feminist Analysi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p.126.。1991年欧共体针对南斯拉夫解体专门设立的欧洲会议仲裁委员会,在其第1号意见中也大致认同这个国家资格的“四要件说”。只不过,该仲裁委员会认为“国家的特点是拥有主权”(12)Matthew Craven, The EC Arbitration Commission on Yugoslavia[J].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65, 1994, p.333.。但是,也有不少国际法学者对这“四要件说”提出了一些批评。例如,有人认为国家的构成要素应当还包括“民主正当性”(democraticlegitimacy);有人认为国家的构成要素应当附加更多的弹性标准(13)Rosalyn Higgins, Problems and Process: International Law and How We Use I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39-42.;有人认为“《蒙特维的亚公约》的规定既非穷尽,也非永恒不变。在特定情况下,自决、承认也可能成为创造国家资格的相关附加标准。然而,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构成国家的法律标准的特征是它们以领土单位之间的有效性原则为基础”(14)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M]. 8th e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575-576.。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各国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或立场对国家资格的认定标准有不同地认识或理解,要想在国际法中设立一个得到所有国家一致同意的国家资格规则,可能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即便假设存在各国一致认可的国家资格认定标准,但在具体个案适用时,相关国家还会对“统一要件”作各种不同解释(15)Martin Dixon,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M]. 7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07.。本文认为,作为国际法律人格者的国家要履行、承担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就必须同时具备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其中,国家的权利能力,表现为国家能够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国家的行为能力则是建立在以下两方面基础上的:其一,具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机体,如领土、人民、资源和财富等;其二,具有独立的意思能力,这表现为政府组织和主权的结合(16)曾令良.国际公法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02.。因此,“从国际法的观点看来,控制一定的人民,保有一定的领土,形成政治组织,具有主权,则有国家的存在。”(17)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64.依据这种国家资格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论证:民国时期的西藏绝不是一些境外反华势力与分裂分子杜撰的“事实国家”。
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控制的地区不是国家构成要素中的确定领土
领土是国家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行使属地管辖权的空间范围,也是连接国家与其人民的纽带。因此,确定的领土是国家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对于如何认定是否存在“确定的领土”,国际法不以领土的面积、连接性(contiguity),及其领土边界的确定性、稳定性为判断标准,而只考察国家是否已在领土上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实体”(political community)(18)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M].6th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71.。所以,有学者指出:“与其说‘确定领土’的要求是国家资格的一个独特标准,不如说它是政府和独立这两个标准的组成部分。”(19)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M].2nd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52.虽然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当局控制了一部分西藏地区,但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任何人都无权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元代开始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20)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蒙古皇子阔端和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凉州议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西藏归顺蒙古的具体条件随后得到蒙藏双方高层的认可,并通报各地,西藏因此正式归属蒙古汗国。蒙哥汗即位后,在西藏清查户口和实行分封制,使西藏在行政上与当时的蒙古本土及蒙古汗国的其他地区基本上趋于一致。忽必烈即位后,于1270年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参见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6页。。此后,历经明、清两代,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一直行使着有效主权管辖(21)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M].夏敏娟,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5-67.。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廷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申明:“乃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22)赖骏楠.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1840—1949(上卷)[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362.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随后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指出,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西藏(2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公报(北京)[J].1912,1(27):4-10.。这两个宪法性法律文件证明,中华民国政府合法继承了清王朝对西藏的领土主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因此,包括西藏领土主权在内的中国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继承。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西藏上层集团中少数亲帝分裂势力的阴谋彻底破产。所以,依据国家同一性与连续性理论,中国政府一直有效地拥有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24)[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44-246.。可以说,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领土主权链”。
民国时期,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长期、持续、明确地宣示了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2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公报(北京)[J].1912,1(27):4-10.1912年4月2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大总统令中强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2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346.此后的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及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等都一致重申,西藏为中华民国之固有领土(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民国治藏行政法规[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16-20.。这些宪法法律都明确地规定了西藏的法律地位,即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二)任何人都无权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分裂分子错误地将所谓的“分离权”作为“民国时期的西藏是‘事实国家’”的“法理依据”。但在国际法中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分离权”。因为“分离权”的提法违反了国家主权原则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原则。而国家主权原则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原则不但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还取得了国际强行法的地位,任何与之相抵触的规则或行动都是非法的、无效的。这正如弗兰克教授所说的:“如果国家享有领土完整权,少数民族就不能有分离权。因为,如果该国的少数民族有分离权,其母国的领土主权就会受到损害。”(28)Thomas M. Franck, 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168.由此可见,“分离权”根本就不是国际法上的合法权利。
虽然国际法院在“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中认为“领土完整原则的适用范围限于国家间之关系的领域”(29)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2010, p.403.,但这也不能作为存在所谓“分离权”的证据。因为国际法院的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瑕疵。国际法院将《国际法原则宣言》所说的“各国不得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领土完整”,作为其“咨询意见”的依据。然而,领土完整原则具有内外两层涵义:对外而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意味着一国有权禁止、抵御外国侵犯本国的领土及边界;对内而言,领土完整原则意味着,禁止一国内部的实体(如特定民族)以分离为由破坏该国的领土完整。另外,《国际法原则宣言》并未言明禁止“谁”破坏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因此,有学者指出,国际法院的这种解释犯了机械性错误(30)孙世彦.克里米亚公投入俄的国际法分析[J].法学评论,2014,(5):139-141.。可见,“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并不能证明存在所谓的“分离权”。而且,很多权威国际法律文件是明文禁止分离的。如《国际法原则宣言》就强调,不得将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解释为,授权或鼓励任何个人或组织采取任何行动以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第6项还明确指出:“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地破坏另一国国内统一及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联合国也是反对所谓“分离权”的。联合国认为:“如果联合国准备纵容对它自己的成员国的领土完整进行攻击或证明这种攻击是正当的,就会使自己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为,支持分离就意味着支持破坏国际和平与稳定,认可就是对国际法关于尊重其他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的违背。”(31)[美]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 [M]. 张铁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69-170.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一直支持国家维护本国的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国际法允许主权国家以武力方式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领土完整,允许主权国家动用军队镇压武装分离活动。由此可见,分离从未被确立为一项国际法上的权利。一些人和组织将不存在的“分离权”作为他们所谓的“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论”的“法律依据”,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
(三)民族自决不能作为分裂中国的法律依据
虽然国际法规定一些特定的政治实体有权依据民族自决原则获得独立,但是,民族自决不能作为民族分裂势力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法理依据。
1.民族自决权(32)在国际法中,民族自决权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在西方国际法学界,有的学者,如意大利学者卡赛斯(Cassese)把民族自决权分为对内自决权(the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 right)与对外自决权(the 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 right)。前者指一国国内人民得向其中央政府所主张之权利,扩张至该国境内少数民族则引申为,一国少数民族有免于政府迫害,要求保持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语言与风俗习惯等权利。而后者指民族得自由决定其国际法律地位的权利。对外自决权在20世纪60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有学者,如法国学者格诺斯(Gross)认为,“对外自决权”是“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对内自决权是“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还有一些美国学者,如赫尔珀宁(Halperin)、切尔菲(Scheffer)主张,民族自决权的对内与对外之分,已经不应对后冷战时代的复杂情势,应当将民族自决权进行更加详尽的分类。转引自姜皇池.论“人民自决”适用于台湾之可行性:实质要件之考察[J].台大法学论丛,1997,26(2):42.不适用于西藏。民族自决权并不是一项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利,其有特定的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关于人民与民族自决权的决议》以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等权威国际法文件都规定,民族自决只能适用于“被强权国家所控制、奴役的殖民地、附属地民族,以及在《联合国宪章》体制下的托管地和非自治领土上的民族”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争取独立的运动。因此,“运用自决的权利只能直接用来反对殖民统治,而不是原有的统治”(33)[美]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 [M].张铁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69.。这正如印度代表1998年在联合国大会就民族自决权问题发言时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尚未获得独立的殖民地人民才能援引民族自决权而要求独立……不得以民族自决为借口,来从事分裂他国、颠覆他国政府等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34)Hurst Hannum,Autonomy, Sovereign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 Accommodation of Conflicting Right[M]. Revised Edition,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 p.42.由前文可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国的殖民地”或“被保护国”。因此,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根本就不属于民族自决权适用的对象。
2.民族自决权不等同于“分离权”。在法理上,民族自决权与“分离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前所述,国际法中没有所谓的“分离权”。而民族自决权在国际法上有明确的权利渊源。并且,“在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自决权主要用于保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而并非一概适用于对少数民族要求分离独立的支持。”(35)Wolfgang Danspeckgruber ed.,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administration[M]. 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31.一些权威国际法律文件还明确指出,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国际法承认一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享有当然的从其母国独立或分离出来的权利。例如,1960年《关于人民与民族自决权的决议》规定,民族自决不得“部分或整个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指出,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各项规定“均不应解释为授权或鼓励整个或部分分裂或损害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1997年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宣布,“民族自决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采取任何行动去侵犯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可见,无论是国际条约还是国际实践都不支持把民族自决解释为国内一个民族能够“分裂其母国”的权利。所以,西藏地区的任何人或组织都无权以民族自决为由破坏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3.民族自决也不能导致西藏独立。一般而言,只有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有效地保护其境内少数民族的基本人权,而实行种族灭绝、种族同化、文化破坏等政策,“致使该民族在其国家联邦中的存在受到威胁”,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才有权要求以自决为由谋求独立(36)[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国际法 [M].吴越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55.。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自决类似于“救济性分离”(remedial secession),它实质上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学说所谓的“革命权利”。相应地,如果一国在其法律和政治制度中规定了民族平等、保护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政策,该国少数民族就不能援引民族自决进行分离活动或宣布独立(37)王英津.自决权理论与公民投票[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93.。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在宪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宗教、种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38)张国福.民国宪法史 [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410.而且,为了改善和加强汉藏关系,国民政府以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边疆政策”(39)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了“新三民主义边疆政策”,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与内地各省份一样施行“三民主义”。具体而言,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与幸福,使人民能直接行使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于民生主义上,提升少数民族的经济实力与生活水平。转引自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85-86.作为其民族立法与制定治藏政策的指导思想,并制定了保障西藏地方少数民族自治权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规定,在保障国家领土完整之前提下,中央政府授予西藏地方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40)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646-647.。例如,1913年《待遇西藏条例》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不以藩属待遇;原有土地统辖治理权照旧;封号照旧;各喇嘛俸饷照旧;裁撤外官另设行政机关以藏人治理;西藏矿产定为藏人生计;藏人晓汉文者得任民国官吏”。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要有西藏的代表参加。”(41)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大会制定)[J].国民大会特辑.1947,特辑:265-279.1947年《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罢免法》及其《实施条例》还规定“应从西藏地方选出四十名国民代表大会代表”(42)李鸣.中国民族法制史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421-435.。事实上,国民政府也切实地遵守了上述规定,让西藏地方的代表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在1946年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中,西藏地方共有16人作为“特种代表”参加;在1948年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中,西藏地方政府有13名代表出席,班禅堪布会议厅也有11名代表出席(4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3046-3053.。另外,在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中都有西藏地方的代表。可见,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充分尊重并保障了西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基本人权。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援引民族自决而谋求西藏独立。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一直有效地维护着对西藏的领土主权,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事实从未发生改变。西藏地方政府控制的地区,从来就不是中国国界之外的“外国领土”。
三、民国时期西藏地区居民不是国家构成要素中的定居居民
国家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领土实体。有永久性的居民,才能形成社会和一定的经济及政治实体,进而构成国家。有学者指出:“共同语言、文化、人种背景、宗教和人口多寡都不是定居居民的要件。居民的永久性是以国籍的形式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44)[日]寺泽一,山本草二.国际法基础[M].朱奇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103.倘若西藏在民国时期真的已经从中国分离出来而成为“事实国家”,那么西藏地区的居民就会相应地变成“外国公民”。而事实是,世代居住在西藏地区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一直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居民并非国家构成要素意义上的定居居民。
(一)从国籍法的角度而言可以认定民国时期西藏地区居民是中国公民
从民族学的角度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居住于西藏的藏族等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45)拉巴平措.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略论藏族与中华民族的内在关系[J].中国藏学,2006,(2):109.。更为重要的是,从国籍法的角度来说,西藏地区的居民都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而不是具有外国国籍的外国公民。
我国第一部国籍法——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采用父系血统主义立法原则。该法规定:“生而父为中国人者;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无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46)董霖.中国国籍法[M].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12.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出生于西藏的土著居民当然为中国公民。并且,依据《大清国籍条例》,他们所生子女自然取得中国国籍,也为中国公民。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没有变化,西藏地区居民的中国国籍自然不会有所改变。北洋政府于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籍法》,继续采用清朝的父系血统主义入籍原则。1912年4月22日发布的《取消蒙藏回疆藩属令》规定:“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47)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346.1929年国民政府颁行的《国籍法》也大体沿袭旧时规定(48)程维荣.中国近代行政法(1901—1949)[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98-299.。所以,依据中国的国籍法及相关行政法规,西藏地区的居民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
(二)就政治地位而言可以认定民国时期西藏地区居民是中国公民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建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将所有少数民族及其区域纳入到国家权力所管辖的范围之内,提出并实施“五族共和”的宪政思想(49)张淑娟.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215.。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也延续了“五族共和”的政策。1912年,袁世凯发布《劝谕蒙藏令》,提出“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国民政府还以政权组织法的形式,确保西藏地区的居民与其他行省居民一样能够选派代表出席全国会议,享有参政议政的公民基本权利。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员,西藏得选派五人;其选派方法,由西藏地方自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一参议员有一表决权。”1913年北洋政府先后公布的《第一届国会西藏议员选举法》,以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宪法性法律对西藏地方选举参、众议员的办法和名额等,作了详细的规定。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和《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施行法》规定,西藏地方得选举代表十名。193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大会组织法》也规定,应在西藏地方选出十名国民大会代表,并在其他省区从有选举权的西藏地区居民中选出六名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更是规定,在中央政府的立法、监察等机构中必须要有西藏地方代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历次全国性政治会议,如国民会议、国民参政会议、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宪国民大会”“行宪国民大会”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政治会议,都有西藏地方代表出席。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西藏地方代表仍在国民政府立法院和监察院任职(50)周伟洲.西藏通史·民国卷(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503-507.。试问:如果西藏地区居民不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又怎么可能享有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论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法律,还是通过查证西藏地区的居民参政议政的实际情况,我们都可以证明:居住于西藏的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国人。
(三)民国时期西藏地区居民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据我国学者胡岩考证,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这两位藏族领袖人物都接受和赞同‘五族共和’的口号,并表示要‘同谋五族幸福’。这说明他们明确认为藏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51)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J].西藏研究,1995,(1):45-50.民国时期康巴藏区的藏族精英有更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他们宣称:“康地亦为中华民国之国土,康人亦为中华民国之国民。”(52)李双,喜饶尼玛.民国时期康区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实践[J].青海民族研究,2018,(2):184.并且,世界各国与国际联盟及其后的联合国,都承认藏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西藏地区的居民是生活在西藏的中国人。
四、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不是国家构成要素中的有效政府
布朗利认为,国际法对“国家”最精炼的定义可能是,在特定领土上建立和维持具有排他性的法律秩序的稳定的政治团体。因此,存在具有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有效政府,是证明国家存在的最佳证据(53)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M]. 8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29.。阿库斯特也认为:“在特定领土上存在有效政府(effective government),表明相关实体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一般是证明其具有国家资格的前提条件。”(54)有效政府也是其他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因为,特定领土上政府的连续性,是决定国家的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领土主权的取得与维护,居民国籍的认定、授予以及对领土内居民的统治,主权权力的行使,代表国家对外交往,都取决于有效政府的存在。See Peter Malanczuk,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Law[M]. 7th revise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79-80.那么,何谓有效政府呢?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在1920年“亚兰群岛案”(Åland Islands Dispute)中提出了判断是否存在有效政府的标准:“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组织,该公共当局已经强大到足以在没有外国协助的情况下就可以在该国的所有领土上进行统治。”(55)LNOJ Sp.Supp.No. 4, 1920, pp.8-9.按照这一说法,“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独立性(independence)是认定有效政府必不可少的两个因素。有效性是指,政府有效控制了全部或绝大部分的领土与人口这两个国家构成要素;独立性是指,一国政府不隶属于其他国家政府。国际法又将有效性视为对内主权(internal sovereignty),把独立性视为对外主权(external sovereignty)。然而,这些标准也不是绝对的。”(56)Siegfried Magiera, Governments[DB/OL]. Max Planck Encyclopedias of International Law, http://iras.lib.whu.edu.cn:8080/rwt/MPEPIL/https/N7ZGT5BPN74YA5DBP6YGG55N/view/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1048?rskey=vvOqaQ&result=2&prd=MPIL,2007年4月上传,2020年5月7日访问。例如,刚果、克罗地亚和波黑在它们被承认为新国家,并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接纳为会员国时,它们的政府都未有效控制该国大部分领土。因此,有学者主张,政府在有效性方面的瑕疵,可以通过国际承认、取得一些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资格的方式来得以弥补(57)M. Weller,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heDissolution of the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2, Vol. 86, No. 3, pp.569-607.。但克劳福德(Crawford)教授坚持认为,有效控制是政治实体取得国家资格所必需的条件,不能任意对政府的有效性做扩张性解释;否则,将不利于国家维护其主权与领土完整。他指出,作为国家构成要素的“政府”应当具有两个方面内涵:实际行使权力,有行使权力的权源。克劳福德进而提出了认定有效政府的标准:第一,政府必须排他地有效控制该国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相应的政权机构。第二,应当结合具体情况确定政府对特定领土实施有效控制的严密程度:(1)考察相关实体取得国家资格是否违反国际法:如果是,那么判断政府对领土有效控制的严密程度和要求就高;(2)考察宣布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否获得其母国的同意:如果没有,那么要求政府更加有效地控制有关领土;(3)考察新国家是否通过分离或分裂的形式成立:如果是,那么认定政府的有效性与独立性标准则应当更严格一些。克劳福德指出,只有具备上述条件的政府,才有资格和能力代表国家对内进行管辖,对外进行国际交往,从而可以作为国家的构成要素(58)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M]. 2nd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p.57-59.。按照国际法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不是国家构成要素意义上的有效政府。
(一)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不具有独立性
1.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模式,基本上沿袭清制。1751年,清乾隆帝颁行《钦定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确立“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而噶伦不致擅权”(59)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532-533.的政教合一制西藏地方政府行政体制,赋予达赖喇嘛兼管西藏地方政教两权的地位与职权。但为了加强西藏行政管理,清廷又将西藏地方之宗教、设官、兵政、财政、交通、外交等权,统统收归中央政府执掌(60)黄维忠.西南边疆卷·十四清代驻藏大臣考[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24.。清廷还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因此,终清一朝,西藏地方政府都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只是清朝皇帝的一个臣子而已。例如,清朝灭亡前夕,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清廷于1910年2月25日下旨,宣布革去达赖喇嘛名号(61)《宣统政纪》卷三〇,宣统二年正月辛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中央政府沿袭清代旧制,以立法的形式允许原西藏地方政府继续统治西藏,并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1912年10月28日,中央政府恢复达赖喇嘛的名号(6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354.。1913年4月1日,中央政府加封班禅额尔德尼“致忠阐化”名号。此后,中央政府还按照历史定制,追封先后圆寂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发布命令认定达赖与班禅的转世灵童免于金瓶掣签;派员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大典。另外,国民政府还册封了西藏地方的两位摄政。
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均设立了管理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例如,北洋政府于1912年设置蒙藏事务局,专门管理蒙藏事务。1914年北洋政府又将蒙藏事务局升格为蒙藏事务院。到了国民政府时期,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审议关于蒙藏行政事务,计划关于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民国治藏行政法规[Z].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1-2.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以上史实证明,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沿袭清朝旧制,在册封西藏地方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摄政等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坚持行使了主权,西藏地方政府只是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当局(64)周伟洲.西藏通史·民国卷(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235-275.。
2.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不拥有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1942年7月,在英国的教唆下,西藏噶厦(65)噶厦是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制西藏地方政府中政务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非法成立所谓“外交局”,并向中央政府提出:“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洽办。”(6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842.此后西藏噶厦又阻止修建中印边境公路,严重影响中央政府的抗战。为了遏制噶厦的分裂活动,并彻底解决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控制相对松散的局面,1943年中央政府准备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后来,迫于中央政府的武力威慑,西藏地方政府只得同意不再强求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外交局”往来,并重开中印驮运线。西藏噶厦企图走出“独立”的第一步的图谋破产了(67)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851.。由此可见,尽管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斗争,但中央政府的命令与意志在西藏还是能得到实施的(68)孙镇平等.民国时期西藏法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311-312.。
3.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虽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其外交事务仍归中央政府负责办理。民国时期,西藏噶厦从未与外国政府建立过外交关系。英国虽然一直企图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也承认噶厦不具有与他国交往的能力(69)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M]. Surrey: Curzon Press, 1997, p.197.。1941年,达札活佛继任摄政以后,噶厦中少数亲英分裂分子得势。他们企图通过“拓展国际关系”,在国际社会鼓吹“西藏独立”。但除英国和印度以外,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与噶厦有过官方的政治往来。例如,1947年10月,西藏噶厦派遣由清一色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成员组成的“西藏贸易代表团”,持非法的“西藏护照”,赴欧美、印度等国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除英国与印度不顾中国的抗议,坚持将该代表团视为“官方代表”外,欧美国家都只给予“西藏贸易代表团”以“非官方”“非正式”代表团的地位与待遇。并且,在中国的严正抗议下,美国还向中国表示:“美国向来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美国政府无意改变其对西藏立场,”“美国今后不再承认所谓‘西藏护照’为有效护照,”“美国总统不会单独接见该代表团”(70)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569-574.。此外,西藏也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后,西藏噶厦多次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求援”,要求它们帮助西藏加入联合国,但都遭到了这些国家的拒绝(71)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主编.和平解放西藏[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241-243.。
(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不具有有效性
如前所述,倘若一国的组成部分企图从其母国分离出来而成立一个新国家,对这个“新国家”的政府的有效性要求将更加严格。清代时中央政府把西藏地方政府等同于达赖喇嘛的拉章(即达赖喇嘛的随侍机构),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从未有效控制整个西藏地区及人口。
清代的西藏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地区与人口主要是1642年固始汗向五世达赖喇嘛奉献的十三万户的卫藏地区。1653年,清朝封赐固始汗与达赖喇嘛金册金印,也承认了当初固始汗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分封。但西藏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已收归清朝皇帝。1728年,雍正帝在平定阿尔布巴之乱后,调整了西藏的封地,将后藏拉孜、昂仁、彭措林三宗改封给了五世班禅额尔德尼(72)房建昌.清代西藏的行政区划及历史地图[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2):59-70.。
民国时期,西藏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沿袭清朝,只略有变革。西藏地方政权机构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以及名义上属西藏地方政府所辖之昌都地区的帕巴拉呼图克图政教系统、察雅洛登协绕呼图克图政教系统、类乌齐庞球呼图克图政教系统、八宿济咙呼图克图政教系统;昌都的德格土司和拉多土司统治区、前清驻藏大臣的直辖区(三十九族地区和当雄蒙古八旗地区)、萨迦法王辖区(萨迦县地区)、拉加里赤钦辖地、波密土王辖地、直贡法王辖地、三岩地区、德格土司部分辖地、巴塘土司部分辖地等行政区划(73)周伟洲.西藏通史·民国卷(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476.。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辖区主要为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地区。西藏地方政府对在班禅堪布会议厅统辖下的以日喀则为中心的部分后藏地区和阿里以及相邻部分地区,以及昌都绝大多数康藏地区,都没有政治治理关系,仅有宗教影响和联系。而且,西藏地方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宗教上对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外宗教的西藏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管辖或领导关系,如波密噶朗第巴辖区(今西藏自治区波密县、墨脱县一带)、萨迦法王领地(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一带)、拉加里赤钦领地(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74)喜饶尼玛等.西藏通史·清代卷(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677-686.。综上所述,旧时西藏分阿里、藏(后藏)、卫(前藏)和康四部(7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地名辞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72.,而西藏地方政府只控制其中卫藏一部,远未达到有效控制旧时西藏绝大部分土地与人口的标准,因而不具有有效性。
(三)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从未宣布独立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派分裂势力虽然从事了一些分裂活动,但他们并不能代表西藏地方政府。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从未宣布过独立。
一些人把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2月13日发布的《水牛年文告》说成是西藏的“独立宣言”(76)例如,范普拉赫在其著的《西藏的地位》以及夏格巴在其著的《西藏政治史》都认为,1913年《水牛年文告》是所谓“西藏独立宣言”。;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文告中用宗教上的“供施关系”来否定历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的错误说法,说成是“西藏独立”的历史根据与理论依据。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并未在上述文告中提及“独立”的意思与字眼,“也没有证据证明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向全世界发表的,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独立宣言。”(77)Alfred p.Rubin, The Position of Tibet inInternational Law[J]. China Quarterly, Vol. 1968, No.35, 1968, pp.122.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就认为,1913年《水牛年公告》在当时西方的术语中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它只是清楚地表达了达赖的愿望——在没有中央政府封号、没有中央政府“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西藏。即便支持达赖喇嘛对抗中央的英国政府也不希望出现“独立的西藏”。英国殖民者的阴谋是:把西藏变成受英国控制的中国“自治地方”,并要限制西藏地方与其他列强“交往”(78)[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M].杜永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21-31.。另外,西藏内部还存在强大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力量。所以,民国时期从未出现“西藏宣布独立”的事件。有学者曾查遍1912—1949年间出版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权威媒体,根本就不存在“西藏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新闻报道或消息(79)[加拿大]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M].伍昆明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351-356.。
综上所述,西藏地方政府在民国时期虽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它仍然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并且,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既不具有有效性也不具有独立性,因而根本就不是“主权国家”的有效政府。
五、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自治权不是国家构成要素中的国家主权
主权是国家所固有的基本属性,是国家区别于其他政治实体和社会组织的根本标志。之所以用“主权”替代1933年《蒙特维的亚公约》中所说的“与他国交往的能力”,一方面是由于主权就已经包涵了能“与他国交往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与他国交往的能力”并非是国家特有的。例如,一些国际组织、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组织,也能与他国交往或参与国际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国家。我国的国际法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主权”才是国家资格要素(80)王铁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239-240.。西藏地方从来就不拥有国家主权。
(一)中国对西藏拥有的是主权而非“宗主权”
清末时期,时任英印总督的寇松,为了让其提出的侵藏战略具有“合法化”,炮制出毫无根据、也未经论证的“中国对西藏只拥有一种宪法上虚构的宗主权”之说(81)张皓.“宗主权”: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西藏地位争论焦点[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13-125.。民国成立后,英国政府仍然坚持以“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唆使西藏先在“自治”名义下图谋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再彻底脱离中国而成为英国控制下的“傀儡国家”(puppet state)(82)梁俊艳.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346-348.。这种由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歪曲国际法而提出的“宗主权说”,不但没有遭到西方一些国际法学家的唾弃,反而被他们奉为“西藏在民国时期是独立国家”的“法理依据”。
而事实是,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非宗主权。在国际法中,“宗主权是指描述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某些国际关系的术语,其中一个国家在保留或多或少有限的主权的同时,承认另一个国家的至高无上。这种关系原指封建君主对其诸侯的统治权,后来扩展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既可能是宗主国监护和控制其附庸国的权利和权力,也可能指帝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的形式。”(83)Wallwyn p.B. Shepheard, Suzerainty[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Vol. 1, No. 3, 1899, pp.432-438.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不是中国的“附庸国”(vassalstate);西藏的政权机构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而不是独立国家的政府;达赖喇嘛是1751年由清朝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而不是独立国家的元首;清代的驻藏大臣在1751年以后不但是清廷派驻在西藏地方的钦差大臣,还是总揽藏政的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而不是一些人杜撰的“清朝驻藏大使”(84)张新羽.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286-287.。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对西藏就拥有最高的主权权威。
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国力衰微、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再加上英国的阻扰,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对西藏的主权。因为,国家主权具有可分性。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对领土的主权包括对领土的所有权(dominium)与统治权(imperium),领土所有权与领土统治权是可以分离的(85)[奥]阿·菲德罗斯等.国际法(上册)[M].李浩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24.。例如,国家的领土可以租借给他国,可以承担国际地役,也可以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下,但这都不影响该国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在国际法中,一国主权所及之领土,即使享有“高度自治”,也很难藉由此历史证据证明此“主权”是完全彻底空洞的“理论上的主权”。况且,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通过“政府宣言和立法”“主持对达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和坐床典礼”“遏制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等等行使国家权威的形式,来宣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所以,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尽管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中国仍然对西藏地区拥有完整主权。这正如常设国际法院在1937年“克里特和萨摩斯灯塔案”中指出的那样:“尽管克里特具有自治权,但是它并未停止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的地位。即使苏丹在克里特岛行使主权权利时受到重要的限制,克里特岛的主权从未停止为苏丹所有。”(86)Lighthouses in Crete and Samos, P.C.I.J., Series A/B, No. 71, 1937,p.117.
(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拥有的是自治权而非国家主权
在国际法中,“主权是最高权威……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87)[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M].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92.西藏只是中国一个省级建制的特殊行政区域,其所拥有的权力是由中央政府所授予、认可的管辖权,因而对内不是最高的。并且,西藏地方政府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参与国际关系,更遑论取得“与外国平等之国际地位”。
民国初年,英国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以中国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自认对西藏只有“宗主权”,作为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先决条件。北洋政府严正申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驳斥了英国的无理要求(88)多杰才旦.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852.。此后,英国又组织召开了由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英国人企图一方面在新订的条约中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另一方面抬升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让西藏地方政府以所谓“平等者”的身份与中国中央政府、英国政府缔约,以实现其企图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阴谋。但中国政府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西藏地方代表无权直接参与谈判的严正立场,拒绝批准西藏地方代表与英国代表私下签订的协议,使英国的阴谋破产(89)卢秀璋.论“西姆拉会议”——兼析民国时期西藏的法律地位[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135-138,170-189.。国民政府成立后,它汲取了北洋政府的经验教训,拒绝与英国讨论西藏问题。国民政府认为,西藏事务为中国的内政,应当直接由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国家内部加以解决。国民政府还一再向图谋分裂中国的英国表示:“西藏并非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90)陈谦平.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83.
达札活佛继任摄政以后,西藏噶厦中的亲英分裂分子得势。在英属印度驻藏的殖民主义者的鼓动与教唆下,他们企图通过“拓展国际关系”,在国际社会鼓吹“西藏独立”。但这些分裂活动都被国民政府有效遏止了。例如,1947年中国政府代表在印度召集的“泛亚州会议”上成功地制止了印度企图制造“西藏独立”的闹剧;1948年国民政府挫败了以夏格巴为首的藏独分子窜至英美宣传“西藏独立”的阴谋。可见,中央政府所许可的西藏地方政府自治,是以不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为前提的。
(三)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不是独立的
“主权在国家间关系中意味着独立。”(91)Island of Palmas Case,R.I.A.A., Vol. 2, 1928, p.838.缺乏独立性,则不拥有主权;以至于可以否定不独立的实体的国家资格,而只将其认定为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作为国家资格要素的“独立”,不同于作为国家基本权利的“独立”。在“奥地利—德国关税同盟案”中,国际常设法院的判决认为“独立”是指“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在其当前的边界内持续存在,且在经济、政治、金融以及其他领域的所有事项中拥有唯一的决定权”(92)Austro-German Customs Union Case, P.C.I.J.,Ser. A/B,No. 41, 1931, p.45.。安吉洛蒂(Anzilotti)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对“独立”这一术语所做的界定,被国际法学术界奉为经典:“独立实际上仅仅是国际法规定的国家的正常状况,它可以被理解为主权或外部主权。也就是说,除了国际法以外,国家不隶属于其他的权威。对一国自由的限制,不论是由一般国际法或条约约定引起的,都可能不影响其独立性。只要这些限制不将国家置于另一国的法律管辖之下,无论这些义务多么广泛和繁重,前者仍然是一个独立国家。”(93)Austro-German Customs Union Case, P.C.I.J.,Ser. A/B,No. 41, 1931, pp.57-58.因此,一般认为,“独立”包括两个因素:第一,一个实体在确定的领土内是独立存在的,即能对确定领土及其上的定居人口行使实质性政府权威;第二,除国际法律义务以外,它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约束,即国家能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
西藏地方政府并不具备上述“独立”的两个要素。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虽然认可西藏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这以西藏地方政府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自认为中国的一部分为前提。并且,倘若西藏地方政府妄图分裂中国,中央政府会采取包括武力方式在内的手段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这让西藏噶厦中分裂势力不敢为所欲为,从而有效地遏制了他们的分离活动。并且,民国政府还采取了种种措施,逐步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正常往来。例如,民国政府先后派遣李仲莲、朱绣、刘曼卿等人入藏,会晤达赖喇嘛等西藏政教上层人士,宣讲中央治藏政策,解释嫌疑,疏通关系,消除误会,使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大为改善。十三世达赖喇嘛先是按旧例派遣三大寺堪布赴雍和宫常驻,以恢复西藏与内地的宗教联系;后又设立西藏驻京办事处,并多次派代表谒见蒋介石、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向他们面陈藏事,申明西藏地方不背中央(94)祝启源.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86-121.。
综上所述,西藏地方在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这种管辖权是经中央政府授予、认可的,它对内不是最高的、对外不是独立的,因而不是国家才能拥有的主权(95)Barry Sautman, Tibet’s Putative Statehood andInternational Law[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No. 1, 2010, pp.127-142.。
六、结论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9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M].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1.在民国时期,英国为了将西藏变成由其控制的“缓冲国”,一直竭力干涉、阻拦中央政府恢复对西藏地方的正常统辖。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国民政府无力也无心将治理西藏作为其最紧迫最重要的政治任务(97)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 [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86-98.。但是,西藏仍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所控制的人口与土地,所设立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行政权力都不是国家构成的要素。西藏不具有国家资格,不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总而言之,所谓“民国时期西藏事实独立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