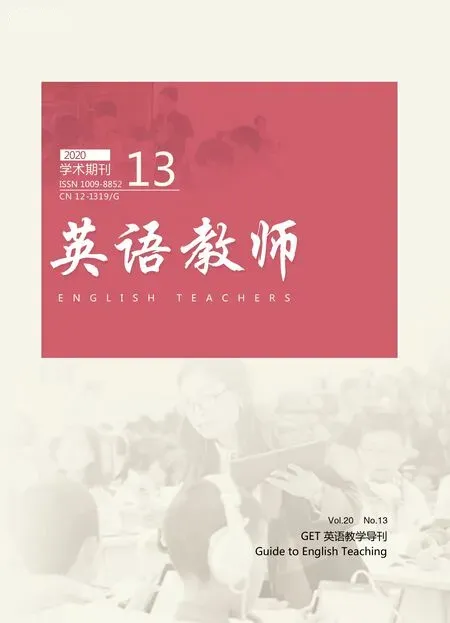基于语言—文化—交际维度分析《活着》英译本
徐意想
引言
余华的小说《活着》从故事主人公的视角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富家子弟徐福贵由于染上了赌博和嫖妓,赔上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和一百多亩地,沦落为一穷二白的农民。在徐福贵的一生中,他目睹了身边所有的亲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小说文理深刻,反映了“只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生存哲学。
这部小说以通俗朴实的叙事风格描写了时代背景下的人物,时间跨度涵盖中国新、旧社会的交替变革,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极具鲜明的中国社会文化气息。这部小说先后被翻译成多个语言版本,其中由美国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的英译本最具影响力。这部英译本一经出版便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作品能被西方社会接受主要是由于白睿文在翻译过程中经过对小说的解构还原文化,有效地完成了不同语言之间文化差异的传递。
小说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种重要形式,相对于非文学翻译,译者更需要关注其文学性的表达,并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剖析。也就是说,小说的翻译不能抛弃原文的文化属性。相对于文本信息,译者更需要关注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和文化特质。能否实现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差异的平衡,是译文能否为读者所接受的重要原因。白睿文在《活着》译本中注重语言—文学—文化的统一,努力实现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还原,传播中国本土文化,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同时,这部作品又引发了译者如何运用贴合文学的翻译策略把中国本土文学推向世界文坛的深思。
一、生态翻译学中翻译的三个维度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归依,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是一项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作出符合生态理性的综观和描述(胡庚申 2013)。王宁(2011)认为翻译同时要兼顾主体(译者)和客体(文本)之间的平衡,任意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会对译文有所破坏。语言、文化和交际是生态翻译学提出的翻译三大维度,从这三个维度出发能够指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现最大化的适应和选择。
(一)语言维
不同的语言对比分析有助于语言交际。通过对比分析,译者可以进一步认识外语和母语的特性、共同点与不同点。英语和汉语的区别体现在词形、词性、语法、句子结构、意合形合、静态与动态等方面。因此,译者在不断“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过程中要重视语言维度的转换和适应。
(二)文化维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仅仅要重视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更要注重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于阐释文化。尤其对文学翻译来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变迁,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形成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文化体系造成的文化差异是文学翻译中一直研究和待攻克的难题。因此,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根据翻译的生态环境在文化维度上实现翻译策略的选择和适应。
(三)交际维
翻译活动中的交际维度要求译者通过翻译实现源语的表达目的,在目的语中为读者创造一个与读者或作品人物交流的环境。汉语和英语在时态、语义、表达方式、修辞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地域特色,往往在俗语、谚语、方言、土话方面的词语含义和表达效果与西方国家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必须从交际维度上体现翻译策略的选择和适应。
二、《活着》英译本在语言、文化、交际维上的转换
(一)语言维的转换
语言维的转换主要是针对中、英两种语言体系在语言结构形式和语言表达上的差异而进行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英语在语言形式上变化灵活,而汉语则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
原文1:我曾经遇到一个哭泣的老人,他鼻青眼肿地坐在田埂上。
译文 1:I once came across an old man with a bloody nose and a swollen face sitting atop the ridge crying.
原文2:我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时,是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
译文 2:It was just as summer arrived that I met an old man named Fugui.
原文3:家珍怀着有庆有六个月了,自然有些难看。
译文 3:Because she was six months pregnant,Jiazhen was naturally no treat for the eyes.
原文4:四十多年前,我爹常在这里走来走去,他穿着一身黑颜色的绸衣,总是把双手背在身后。
译文 4:Forty years ago my dad often stroll back and forth across this land.He would be in a black silk outfit and would always have his hands clasped behind his back.
在原文1中,用“哭泣的”“鼻青眼肿地”描写老人遭儿子毒打的情况,白睿文在处理这些描写性词汇时,把“哭泣的”译为伴随状语crying,把副词“鼻青眼肿地”分别用bloody和swollen来形容,通过词性和词形的变化,通畅地表达原文。而在原文4中,白睿文也是通过词性转换,将原文的“走来走去”“穿着”“背在身后”分别用 across,in,behind 三个介词表达。
译文2中使用了“it was...that...”的表达结构,使得译文在内容上更加简洁、逻辑上更有条理,结构上更加紧凑。
汉语为意合语言,逻辑结构相对模糊,一般从语境和上下文中推断,而英语是思维性语言,注重逻辑表达,这一点从原文3和译文3中便能发现。因此,白睿文在翻译时,添加了because,使行文逻辑更清晰。
在充分理解和把握原文的基础上,译者通过在语言维上对原文内容进行合理编排,实现语言符号的转换和适应,将原文和译文有机结合,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二)文化维的转换
白文昌(2002)提出了除语言掌握程度和翻译技巧外影响翻译交际的另外两大因素——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因此,在关注语言差异的同时要理解不同语言所蕴含和积淀的文化。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是作品文化的阐释者,即读者可以从余华的《活着》中窥见其中所蕴含的独特、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象。
原文5:于是村里人就知道那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的人又来了。
译文 5:And so the people in the village knew that the man who told dirty stories and sang sad songs had come back again.
原文6:“福贵,我收山啦,往后再也不去赌啦。赌场无赢家,我是见好就收,免得日后也落到你这种地步。”
译文 6:“Fugui,I’ve given up.From now on I’m not going to gamble.No winner in the gambling house.I’m quitting while I’m ahead so as to avoid ending up like you someday.”
刘法公(2009)认为隐喻是一种文化喻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传递特殊的文化意象。不同语言体系所呈现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它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距离感和疏离感。因此,译者必须要恰当地处理这些文化喻体,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在原文5、6中,“荤故事”“酸曲”“收山”“沦落到……地步”是中国特有的表达,有其特定的文化意境。“荤故事”指不雅、下流、不健康的小故事;“酸曲”指的是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咏唱的伤感爱情故事;“收山”指某人决定不做某事了;“沦落到……地步”指由于错的事情导致一个凄惨的结局。白睿文通过归化策略,把这些词汇相应地转换为dirty stories,sad songs,given up,avoid ending up like you someday,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形象进行替换,避免产生歧义和造成读者理解困难。
原文7:我还蒙在鼓里,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光耀祖宗了。
译 文 7:I was left in the dark,all the while thinking that I was just about to bring honor back to my ancestors.
原文8:我从小就不可救药,这是我爹的话。私塾先生说我是朽木不可雕也。
译 文 8:Ever since I was little I’ve been hopeless,as my dad would say.My teacher used to say I was a rotten piece of wood that could not be carved.
有时归化能够减轻读者在理解不同文化指代现象时的困难和疑惑,但如果译者不考虑原文的整个生态环境,抛弃原文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一味求“同”,必然会致使原文文化损失,难以传达目的语文化特色。从以上两句译文中可见白睿文充分尊重原作和中国文化,他在翻译过程中妙用异化手段,注重传递原作的文化语境,还原文化意象。白睿文将原文的“光耀祖宗”“朽木不可雕也”直接译为bring honor back to my ancestors,a rotten piece of wood that could not be carved,生动形象地保留了原文形象,不但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读者,还加深了读者对这些意象的理解。由此可见,在文学翻译中,通过生态翻译学文化维度上作出翻译策略的适应和选择,能够实现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差异的平衡,以“同”化“异”,以“异”传“同”。
(三)交际维的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维的转换要求译者在文本或篇章的生态环境下侧重交际层面,传达原文的交际目的和源语的特征与风格,注意源语内部语言系统和使用规则,力求目的语符合源语说话人的身份,达到交际目的。余华的《活着》文风朴实,用词通俗简明,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乡土气息。而白睿文考虑到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在翻译过程中也都是用短句和简单词汇最大化地还原原文风格,大大缩短了原文与译文的距离,使读者读起来如读原文那般亲切、朴素。
原文9:“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译 文 9:“Oxen plough the fields,dogs watch over the house,monks beg for alms,chickens call at the break of day and women do the weaving.Have you ever heard of an ox that didn’t plough the land?This is a truth that has been with us since ancient times.Come on,let’s go.”
原文10:我点点头说:“我想租几亩田。”
龙二听后笑眯眯地问:
“你要租几亩?”
我说:“租五亩。”
“五亩?”龙二眉毛往上吊了吊,问:“你这身体能行吗?”
我说:“练练就行了。”
他想一想说:“我们是老相识了,我给你五亩好田。”
译 文 10:I nodded my head,explaining,“I would like to rent five mu of land.”
Long Er smiled slyly and asked,“how many do you want to rent?”
“Five mu.”
“Five?”Long Er’s eyebrows shot up,and he asked,“Can you handle that?”
“With a little practice I’ll be fine.”I answered.
He thought about it and said,“Because we’ve known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I’ll give you five mu of good land.
原文9用几个短句描写福贵用讲道理的形式对疲倦的老牛吆喝,流露了福贵与老牛的惺惺相惜,同时也表达了对作为牛不得不去耕种的无奈。而白睿文也连用五个主谓并列短句以求更好地传达作者简明朴素的写作风格。
原文10中的“往上吊了吊”“能行吗”“就行”这几个词语原本是很口语化的词,白睿文用shot up,handle,fine适应原文,清楚地说明了他熟悉如何适应原文语调和叙事风格,从而更好地达到交际的目的。
原文11:凤霞说起来又聋又哑,她也是女人,不会不知道男婚女嫁的事。村里每年都有嫁出去娶进来的,敲锣打鼓热闹一阵,到那时候凤霞握着锄头总要看得发呆。
译文 11:Fengxia may have been a deaf mute,but she was still a woman,and she had to have known that it was only natural for men and women to get married eventually.Every year there were village women marrying out and other new brides who married in.During the excitement of the drums and gongs,Fengxia would always stand there holding on to her hoe as if in a trance.
汉语和英语在时态上存在巨大差异,汉语时态多靠语境来表达,而英语时态富于变化,如果在翻译时不协调好中英文在时态上的表达,必然会使读者混淆,达不到交际目的。在原文11中,首先是用一般现在时叙述凤霞的情况,但随着出现“到那时候”,要表达过去的时态时,白睿文考虑到整个篇章时间脉络都是在叙述过去的事,便统一时态,解决了中英文时态冲突问题,增强了可读性,易于读者理解。
结语
小说翻译策略不能抛弃原文的文化语属性而进行,相对于文本的信息,译者更需要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和文化特质。通过分析白睿文译本《活着》如何实现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的适应和选择,提出译者应根据翻译文本生态环境,以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视角的转换为指导,采取合适的翻译动机、原则和策略,实现翻译过程中最佳的适应和选择,以此达到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