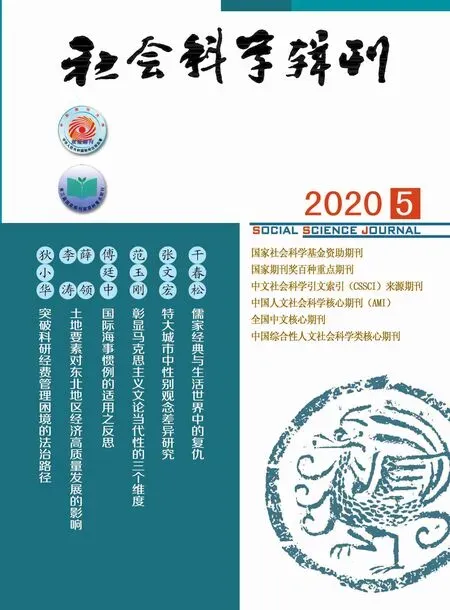用心若镜与消极自由
——《庄子·应帝王》的政治哲学
朱 承
《庄子·应帝王》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政治哲学意义上 “应对世界”的问题,常常被认作是 “外王”的治理之道。宋代林希逸说:“言帝王之道合应如此也。”〔1〕近人锺泰认为:“《应帝王》明外王也。”〔2〕陈鼓应认为:“《应帝王》是古代民主政治色彩极浓的一篇作品。”〔3〕杨国荣也指出:“《庄子·应帝王》涉及政治哲学方面的观念……其中既涉及天下治理的前提和条件,也关乎政治实践的方式,与之相互关联的是天下治理的原则、理想的政治形态,等等。”〔4〕如上诸家所述,该篇表达了庄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是他对如何应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回答。人在公共性的政治世界如何度过?这不仅是帝王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普通人要面对的问题,郭象说:“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5〕锺泰提出:“应亦当为因应之应,非谓如是当帝王也。”〔6〕《应帝王》不仅是在告诫帝王,同时也是在为民众实现自我主宰而发声。在这一篇中,庄子既从应然和理想的层面表达了治理世界的帝王之道,同时也为普通人应该如何更好地生活在充满机巧的政治世界提供了智慧。帝王应该以无欲无为获得天下之治,普通人通过顺应自然、处在浑沌之境,以有限的人生消极地应对无限变化的世界,也可以成为自己世界里的“帝王”,从而避免外在的干扰,更好地主宰和把握自己的生活。换言之,《应帝王》既关涉帝王君主的治理之道,也关涉普通民众应对政治生活之道。对于君主来说,要放弃干涉民众生活的政治行为;而对于民众来说,也应该顺应本性,拥有避免被强制干涉、侵犯的自由。以赛亚·柏林曾指出:“政治自由简单地来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7〕“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而正是他的那些自然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追求或领会各种各样人们视为善良、正确或神圣的目的。”〔8〕柏林称这一领域的自由为 “消极自由” 〔9〕。从不被干涉和尊重自然本性的角度来看,《应帝王》中庄子所设想之浑沌式的不被干涉的自由以及 “随物自喜”的无为之治,就具有了消极自由的意味,这种消极自由的实现,既需要帝王采取不干涉的无为之治,也需要民众自身的无心任化与淡然处世。
一、“不谴是非”与 “游于无有”
政治生活中充满了是非之争。究竟什么是正确、正义和正当?人们往往莫衷一是。而言语上的冲突和行动上的敌对,也会因为要维护某一特定立场而产生。除此之外,人们还习惯于将自己坚持的立场与信奉的观点施与他人,希望他人能够与自己一致,对他人的干涉与制约由此产生。庄子一贯认为,是非之争是人为造成的,并非自然之道形成的,偏执于 “己是人非”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他在 《齐物论》里集中讨论了认识意义上“齐是非”的问题。在 《应帝王》里,庄子又将“不遣是非”的思想运用到政治领域。
一般情况下,关于是非的讨论都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人们为了表达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而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因而出现了相对的是非。庄子则试图消解对某一问题持有看法的意义。庄子杜撰了啮缺与王倪的对答来表明是非问题的无意义。“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庄子·应帝王》)这一对答已经在 《齐物论》里出现过一次。“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是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庄子·齐物论》)《应帝王》 开篇又将此哑谜式的答问提出,本身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确定性的答案 (是非)真的非常重要吗?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有太多的问题与莫衷一是的答案,往往让人们无所适从。作答者,无论怎么表明自己提供的答案只是多种可能性的一种,也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影响到别人。庄子选择了回避作答,其实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应对。拒绝回答乃是需要问者自明,同时也避免卷入是非循环的漩涡。王倪拒绝答问,就是要避免卷入“己是人非”或者 “己非人是”的局面,或者说王倪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答案未必比别人高明,也可能仅仅是一种 “以我观之”,这种 “以我观之”的答案不必施之于人。蒲衣子看到了这一点,用有虞氏和泰氏的不同来讲明这个道理。有虞氏“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非始出于非人” (《庄子·应帝王》)。有虞氏自以仁爱之心来笼络他人并获得拥戴,但是以 “己之所欲”来 “施之于人”,故而还是没有摆脱 “己是人非”、物我两分的定势与困境。而泰氏与物同体、不分物我,“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庄子·应帝王》),将自己混同为牛马,进入知性浑沌的境地,一任知性的浑沌而恪守整全之道。有虞氏和泰氏都是上古帝王,有虞氏希望以 “仁”来感化人,泰氏完全放任他人的自我治理,不以 “己是”来 “非人”。在庄子看来,求问于人、求证于人往往是是非的开端,因此 “四问四不知”中的 “四不知”,也即不参与到是非中去,才是真正的应对世界的智慧,所谓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
就政治生活而言,是非意味着对于一些观念、行动的判断,或者意味对于政治统治、政治人物、政治组织的认同与否,是与非的选择意味着立场的选择。政治上的冲突往往就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于观念、行动、组织、统治等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故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其极端形式就是战争。在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战乱频仍,很多是围绕是非的冲突而引起的战争。人们都执着于“若我互胜” (《庄子·齐物论》)的是非循环圈,在求是求非中争个你死我活,人被是非的执念限制住了,丧失了精神自由,甚至会在战争中丧失生命。庄子认为,人们完全可以退一步,放弃求是求非,一是因为是非本来就未有定势,二是人们都容易陷入 “己是人非”的偏执,争论是非变得毫无意义,不如放弃是非的念头。引申到公共生活中,庄子的主张在于放弃政治立场,因任自然的选择,因为立场就意味着是非,就意味着人要有所依归和束缚。只有自然的 “道”才对偏狭性的立场有所拒斥,在世俗的是非面前,帝王和常人都要“以道观之”,放弃人为意志的干扰而静待自然的“裁判”。
这种政治立场上的 “不谴是非”,还与政治活动中的不居功、不恃才的 “游于无有”的心态相关。庄子描述了一个具有杰出为政才干之人,并追问这种人是否就可以是 “明王”。“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庄子·应帝王》)有人敏捷果敢、鉴物分明、学道不倦,应该堪称 “明王”吧?这类人在现实世界中往往受人瞩目,既聪明又勤奋,应该是人之模范。但庄子认为,这样一个积极参与世界的人,未必是最为恰当的为政者。“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曰虎豹之文来田,猿狙之便、执嫠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庄子·应帝王》)在庄子看来,这种有才干的人,要么是有才智而供人役使的小吏,要么是占卜的小官,都只是技术官吏而已,他们劳形劳力,日子还过惴惴不安 (“怵心”)。而且这样的人生活有风险,虎豹有花纹招致猎杀,猿猴敏捷可爱招致猎玩,长毛牛奔走迅疾招致绳套,上述的人与这几种动物的命运往往差不多,因为卖弄才智而招致杀身之祸。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 “明王之治”?庄子的正面回答是:“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应帝王》)真正具有智慧的帝王,功盖天下而不居功自傲、自美,化贷万物而民不知。在这种治理下,民众不会被帝王干涉,万事万物各居其所,一切顺其自然。这样的效果,老百姓认为是因循自然,而不是靠君王的恩德。“明王”明白了人民的自我决定性,不再去干涉他们,因而立乎不测、深藏若虚、“游于无有”。从表面上看,才智过人的人应该是理想的为政者,但是庄子认为,才智过人的人往往会遭受厄运,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去干涉他人,不可能成为 “明王”,只有顺应自然、不以人力干涉民众生活的人才是 “明王”。干涉往往从自恃才智开始,他们认为以自己的意志干涉民众是为民众着想。因此,在庄子的视野里,放弃世俗的才智、放弃干涉他人才是好的为政者,因为有这样的为政者,人们才会获得自作主宰的自由。
放弃立场,拒斥是非,放弃干涉,“游于无有”,在政治治理和政治生活中,庄子既放弃是非观念上的判断,又放弃了权力运用上的介入,选择了以自然作为一切的裁判、将 “使物自喜”作为最好状态,并希望由此能避免人因立场、是非而遭受到约束以及被干涉,获得一种 “自作主宰”、发挥自己自然能力的自由。在庄子看来,统治者不遣是非、“游于无有”,看上去虽无所作为,但民众却因不被干涉而能够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才能免于被卷入公共生活而被迫进行立场选择以及免于被他人意志所左右而获得了自由,顺应自然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二、“正而后行”与 “顺物自然”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往往会强调圣王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圣王因突出的能力和高尚的品性被人们拥戴,所谓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如儒家、法家、墨家为了实现政治理想,都主张将圣王的良好政治意图贯彻下去,这种贯彻,或通过教化或通过礼法。但是在老庄道家政治思想里,则希望为政者不要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民众的意志,而是尊重民众自己的意志,让他们自然而然地生活在自己喜好的方式中,《庄子·胠篋》里甚至不无极端地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把所谓圣王的干涉作为民众生活无序的根源。庄子认为,圣王不企图去干涉民众而是顺物自然,才是 “天下治”的前提。
在 《应帝王》中,庄子给试图影响并掌控人们意志的统治者们取了一个 “日中始”的名字,如日方始,自以为是,似乎很了不起,代表着一切拥有巨大权力并陷入傲慢的权威。“日中始”认为:“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 (《庄子·应帝王》)他的政治思路是:以自己自认为强大而正确的意志和法规来从事治理,人们会俯首帖耳地听从,社会从而得治。庄子借楚狂接舆的话认为 “日中始”的政治主张 “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庄子·应帝王》)。换句话来说,这种政治统治是不正当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庄子认为,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治天下,如同涉海、凿河、使蚊负山一样荒谬,缺乏合理性。那么恰当的治理是什么呢?庄子认为:“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庄子·应帝王》)即恰当的政治治理不是要改变他人,不是让世界听命于自己,而是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王博指出:“因此对于庄子而言,成为帝王或者做世界的主宰并不意味着必须像霸主那般让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也许刚好相反,因应而不是想改变这个世界,才可以达到上述的目的。”〔10〕统治者要明确地知道,虽然“我”拥有权力,但是人们并不是轻易接受 “我”的意志,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亦如此。“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庄子·应帝王》)鸟知道高飞以避弋射,鼷鼠知道挖很深的地洞来避熏凿之患。鸟兽犹如此,何况乎人?其潜台词是,一旦人们的生活被君主的意志过度干涉,人们可能会消极对抗、摆脱控制。好的治理,应该是端正自己而任人自化。帝王遵循无为无私之道,这可能会更符合政治治理的本质。在这样的治理下,人们有免于被看上去正确的 “经式义度”干涉的自由,能自主地施展自己的自然天赋,而不是被傲慢的 “日中始”们打上印记。
一般来说,帝王意味着主宰,但对于被其主宰的对象而言,就意味着奴役和受控。帝王容易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作为共同体的意志,要求人们服从这一意志。不能不说帝王从动机上可能是好的,也就是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意志是正确且正义的,既然是好的,那么就可以要求所有的人服从这一意志。然而,即使是好的意志也不一定对所有人都适合。在庄子看来,理想的状态不是由他人为自己做主,好的生活应该是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为自己做出决定,这既是对帝王们的要求,也是对普通人的要求。“正而后行”不是以自己的意志去 “端正他人”,这与儒家修己而后安人的思路明显具有差异,儒家的 “修己安人”要求自己端正念头,然后希望他人效法自己,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庄子看来,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然本能进行生活,每个个体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由某个外在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免于被外在的意志所干扰,按照自己的意志自觉自愿地行事,自己对自己负责,不需要一个 “以己出经式义度”的救世主出现。
与 “日中始”干涉主义统治相对应的是 “无名人”顺应自然的无为之治。无名人连名字都没有,可以说是 “低到尘埃里”,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有大智慧。天根问他如何治天下,无名人的回答是: “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琅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庄子·应帝王》)“平治天下”这一如此重大的问题,在无名人看来根本是无稽之谈,从而化解了一般人眼中的治理神圣性问题。“治国平天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神圣的话题,但对于无名人来说,是无聊至极的。因为无名人说他正在与造物主结伴神游,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可以乘着莽渺之鸟,出六极之外,游无何有之乡,处圹埌之野,心神自由至极。在无名人看来,个体精神的自由要远比所谓的 “治天下”有意义得多,人在自我私人领域的放达要比参与公共事务更加重要。庄子以个体的精神自由抵制了儒家的 “平治天下”的问题,在公共性和个体性的选择上,庄子选择了个体性的满足而消解了公共性的神圣。
虽然庄子认为公共事务远比不上个性自由重要,但他还是要表达对公共治理的基本态度,而这一态度的表达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自由。在 《应帝王》中,无名人实在熬不过天根的纠缠,勉强告之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无名人指出最好的统治,并不是强人从己,而是统治者没有偏私、放任人民依自然而行。“顺物自然而不容私”,顺应物性和人性的自然能力而不是像日中始那样按照自己的私意来统治天下,让民众自己决定自己,而不是由帝王决定民众的生活并给民众指出一条康庄大道。“无治”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无为而化,任百姓自治而使天下太平,当然自可作为帝王的万世之师了”〔11〕。如上所言,庄子不要统治者以是非来要求人民选择立场,更不要用 “经式义度”来主宰人民的意志。统治者要习惯于物来顺应,廓然大公,放手让民众自己发挥聪明才智,过他们自己喜欢过的日子,如是,则 “天下不待治而化也”〔12〕。
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民众,以自然无为的办法来保证安存于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未尝不是一种政治智慧和处世智慧。当然,我们知道,庄子在抵制为政者干涉民众自由的同时,也使得为政者的责任无处安放,而民众的随心所欲,也将导致共同体的分崩离析从而导致文明的衰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批评庄子 “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子·解蔽》),是具有一定针对性的。
三、“立乎不测”与 “浑沌处世”
在生活世界中,人们之所以被控制、被干涉,除了帝王的意志以及背离自然之道外,还与人们被人迷惑或者被 “好意”损害的情形相关。为了破除这类形式的控制和干涉,庄子通过 “神巫”与 “浑沌”的寓言来讲述在政治世界中以浑沌姿态 “立乎不测”的重要性,并期望由此来摆脱被迷惑和被干涉的生存状态,保持不被干涉的自由。季咸是神巫,据说能知生死、存亡、祸福、寿夭,带有神秘而权威的光环。这种能力,对于对未来一无所知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因此人们对这些似乎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奉之若神。当一般人无法把捉自己命运而又遭受困厄之时,就倾向于把猜测命运的权力托付给这些人。在庄子笔下,壶子的学生列子就很相信,“见之而心醉”(《庄子·应帝王》)。“醉”字将列子背离自然质朴的心智状态表达得十分传神,这种迷醉的状态是由于放弃了自己的独立理性能力而表现出来的,但对于普通人迷信权威却有着一定合理性。列子将季咸的神迹告诉了壶子,壶子认为:“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庄子·应帝王》)壶子作为体道之人,对这种装神弄鬼行为的本质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批评列子只看表面而不知其实质,也看不到事物的两面性。壶子认为,神巫之所以能相人,是因为人能够 “被相”,如果人按照道而不是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来行事,就不可以被相,“立乎不测、深藏若虚、游于无有”,神巫又能奈何?正如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里引述李希屯伯格的话:“要承认相面家真能通过相面而理解人的内在,并不困难,只要勇敢地决心使自己重新成为千百世代所不能理解的人物就行了。”〔13〕只有人们自己愿意将其心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他人才能由此判断并进而干涉其生活;反之,他人是无法通过外在的判断来影响人们心志的。
在庄子的描述里,季咸与壶子的 “斗法”颇具戏剧性。二人会面四次,壶子始终以虚与委蛇的姿态应对季咸,使其摸不着底,最终使季咸败下阵去,“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庄子·应帝王》)。壶子能控制自己的心神本色,随物而迁,不让季咸摸清其真实的本质,于是季咸在真人面前溃不成军。杨国荣将季咸与壶子的对抗称之为巫术与道术的对抗,并指出 “作为巫术之士的季咸,受经验的限制,既未能把握整个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也无法进入到精神世界的内在层面,从而完全为外在形迹所支配”〔14〕。真人能从经验生活中超拔出来,摆脱物的纠缠,直接回到作为物之本原的 “道”,因此可以 “物物”而不 “物于物”,无为而无不为,按照其真实的自然本性生活,实际上是其自己世界的帝王。郭象评注道:“变化颓靡,世事波流,无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应世变而时动,故相者无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应帝王者无方也。” 〔15〕壶子能够依照本性随物迁化,能主宰和把握自己的命运,这超出了季咸的经验认知范围,故而季咸无法揣测、干涉与影响壶子。唐代成玄英认为:“而壶丘示见,义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虚凝,寂而不动;第二,示垂迹应感,动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动寂一时;第四,本迹两忘,动寂双遣。” 〔16〕壶子的 “四示”,向世界所展现的形象表现为动寂不定,完全由其自身把握自身的在世状态,而不受季咸以及外在世界的干扰,实现了意识的自主与显现的自由。在这场道术和巫术的对抗中,自作主宰的道术战胜了试图掌控他人的巫术。列子由是看到了老师壶子的真本领,再不信季咸的神鬼学说了,开始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庄子·应帝王》)。列子从被人迷惑的公共生活退回到自然淳朴的自我生活世界,从公共场域退回到私人领域。瑞士汉学家毕来德认为这是一种 “退隐”,“反归自我、反归‘自身’,恰恰是要与接受最谦卑的生存相辅相成”〔17〕。所谓 “最谦卑的生存”,在列子这里就是回到家里三年不出,给老婆做饭,像对待人那样对待猪,一无分别地对待他人,破除了世俗的人伦之别、人禽之别、人我之别,不分偏私对待世事,扫除世俗生活中违背自然的雕琢和修饰,恢复到本然的质朴和纯真,以自然的形骸独立于世间,知晓世间的纷扰但依然守住自然的本真。列子因消极地应对世界而回到古朴的原初状态,封闭心窍,不染世尘,并 “一以是终”。换言之,列子对于应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不是让别人来揣测自己的命运进而来主宰自己,也不被人干涉而改变自己生活,而是返璞归真,去除世俗公共生活中的是非好恶,无知无识、无聪无明,按照自然本性生活,真正做到了无为,从而享受 “不去做什么”的自由,从有限的世俗生活通达到无限的精神自由。
如果说列子是从被权威迷惑的状态回到了自然生活状态,实现了消极意义上的人生自由,那么 “浑沌”则是从消极自由的自然状态被裹挟进了人为的束缚状态,丧失了本真的自由。“浑沌”本来无知无欲,出于自然的本能随物自喜、善待万物,然而他人要以自己的喜好来改变 “浑沌”的自然状态,“倏”和 “忽”干涉了 “浑沌”,类似于 “以己出经式义度”,从而决定 “浑沌”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在庄子的语境中,“浑沌”处在自然整全的状态,与物同体,无所闻见亦无烦恼,但不妨碍他出于自然本性而以友善的姿态对待 “倏”与 “忽”,因为这是其最本原、最本真、最自然的品性。但是,“倏”和“忽”以世俗的知恩图报来理解和处理与 “浑沌”的交往,将 “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在人类的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自己喜欢的以为别人也喜欢,自己认为对的也武断地认为他人也应该认为是对的,这往往是干涉主义的最初动机。以己度人,在 “善”“道德”的热情下毁掉了 “浑沌”,破坏了 “浑沌”不受干涉的自然状态,七日而 “浑沌”死。“浑沌”的状态消失了,自然的状态没有了,由于闻见聪明所带来的纷繁复杂之人为世界产生了,而人之本真自由也就消失了。人们在人为世界中努力去做什么,但却没有了不做什么的自由。“浑沌”之死,意味着人类自然状态的终结,从道治变成了人治,从自在世界进入了公共生活,个体丧失了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被裹挟着进入人为的世界中,在圣王的意志、是非的争辩、权威的迷惑、机敏的才智中成为另一个“我”。
理想中的世界是 “浑沌”的,没有机巧,人们一任自己天赋的纯善应对世界。“浑沌”也观照世界,但世界在他那里只是过影而已,“浑沌”从来不想将世界留藏,对世界也不作评判。“不留藏”“不评判”并不等于他对这个世界 “不了然”,否则也不会 “用心若镜”,其实他是洞若观火。但是,“了然”之后如何?这是应对世界需要回答的问题。清代诗人赵翼化用庄子 “心斋”一词而作诗云:“身退敢谈天下事,心斋惟对古人书。”(《岁暮杂诗》之一)只有退居世界之外,才能更好地看清这个世界。庄子并不想通过自己的刚健有为干预这个世界,只是想消极地免于外来世界的事务,从而主宰自己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像季咸那样拥有度测生死祸福的能力,不是真正的自由,而 “浑沌”可以不去做什么还能有尊严地活着,才是最大的自由。当然,在人为的世界里,“浑沌”不可避免地消失了。
小结
人在公共性的政治生活里,容易为声名所累,为谋略所困,成为世事的负担、机巧的主宰。这些都要求人们放弃自我的本然状态,要么积极参与,要么乐于被他人干涉或主宰,逐渐丧失了免于做什么的消极自由。庄子认为,避免这种状态,就是像 “至人”那样做到 “用心若镜”:“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庄子认为,人们应对世界不要藏着名与谋,不要被事和知牵绊。要成为自己的主宰,就要 “无心应世”:“帝王之道,至于无心,而使人不得而相,而后不为名尸、谋府、事任、智主之所累也。”〔18〕在世界面前,不要有任何机心,要与世界融为一体,“磅礴万物以为一”(《庄子·逍遥游》),要虚游无迹,不要理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那一套,更不要所谓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不过是一场虚妄。人的生命秉乎天道,只是虚而已。世界在镜子里呈现,不会受到镜子的评判,“虽知妍媸而不是妍以非媸” 〔19〕。洞达世情而不留心于世情,因任世界的自我流变,而自己也将随世迁变、无所寄寓。世界并不在镜中停留驻存,万物呈于镜中,不增不减,不生不灭,而心也对万物没有挂碍。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自我世界的主宰,不被外在的压力所干涉,就不要试图去主宰世界,只是去虚心地观照世界。一旦试图主宰世界,其结果是反过来被外物所主宰。在这里,庄子给世人描绘了一幅消极自由的图景,按照崔宜明的解释,“不再拥抱生命的一切所有,既不欢呼创造,也不赞美毁灭。他的宁静不再是高贵的静穆,而变成了孱弱的麻木。他的生命不再追求永恒,只是希望不要受到伤害。呜呼,自由,这一神圣者,堕落竟一至如斯” 〔20〕。作为一种免于干涉的自由,其表现的确是不再对创造、毁灭有所动容,但这应该不是 “自由的堕落”,而是一种不受干扰的消极自由,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实现起来难乎其难,但庄子的意图就在于不受外界的干扰和主宰,而按照自然本性如其所是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总体来看,就如何应对外在世界特别是政治性的公共生活而言,庄子的答案是:不谴是非、正而后行、顺物自然、游于无有、立乎不测、浑沌处世。帝王以不干涉的顺应姿态、以自然无为应对政治世界,普通人 “用心若镜”,按照自然本性生活、避免被他人干涉,不对外在的权力、地位产生欲求,这既是帝王的治理之道,也是普通人主宰自己、获得自由的至上之理。当然,这种无为而治、免于干涉,否定了人们的公共责任,客观上会以损害人类的文明进步、社会的大同团结为代价,因而无疑也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