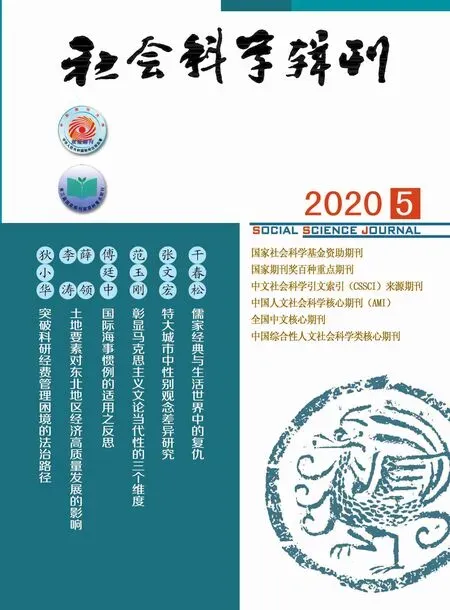儒家经典与生活世界中的复仇
干春松
引子 来而不往非礼也:怎么理解儒家的 “直”与 “报”
任何社会活动都存在一个报偿机制,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与市场交换体系中的等价交换相一致的是,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这种报偿机制背后也存在着义务、公平和契约等因素。与市场关系直接体现为交换特质所不同的是,人际的报偿机制被赋予道德和责任等情感、伦理因素,故而会出现许多 “中间”形式,来掩盖交换过程中的利益诉求,这就是仪式甚至表演性节日的意义,这让人类社会充满温情与友爱。对此,社会学家莫斯曾经通过对 “礼物”现象的分析,提出给予、接受和回报这样的 “总体性呈现”的社会现象,背后是存在着义务的。〔1〕在传统中国,这种给予、接受和回报的社会交往方式及其价值,比较充分地体现在礼仪活动中。《礼记·曲礼》中说:“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的特征就是往来,即给予与回报。往来并不一定要即时的或等价的,若只有单向度的给予,礼仪活动就存在着缺失,因此,儒家十分强调 “报”的重要性。在 《礼记·表记》中,报是与仁、义相并列的重要道德原则:“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在其他文本中,施与报被看成是礼乐文明的整体性纽带。在有些经典文本中,给予和回报构成施和报,分别体现了乐和礼的精神,是彰显人的德行和情感丰富性的重要方式。“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礼记·乐记》)这令我们想起 “乐善好施”这句成语,施与报是责任和义务,不过并非是强迫和被动的,而是自愿和主动的。对给予和回报过程最为文学化的表达是 《诗经》中的名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施与报的原则在家庭内部体现为父母对于孩子的慈爱和孩子对于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如此,孝道也内含施和报的原则。[1]虽然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往往具有德性至上的基础,拒绝从功利性的角度来讨论其出发点。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孝”上面。人们倾向于认为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和孩子对于长辈的敬出于“良知”之天成。但现实的家族财产原则又确立了父母所创造的财富是在家族系统内传递,而儿子对于父母的赡养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因此,杨联陞在讨论“报”的观念的时候指出:“交互报偿的原则又转而加强了家族系统。例如,孝道即是还报原则最恰当的说明,即使以最严格的交易来说,做儿子也应该孝顺,因为受到了父母如此多的照顾。”其实我们从《论语》中孔子与宰予对于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孔子也不排斥从“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来证明守丧三年的正当性。参见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9页。《礼记·祭义》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在家国一体的原则下,臣民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是孝道的社会化。在封建制所确定的家天下的原则下,家国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情感逻辑的一致性。这一点,《大学》阐发得最为彻底:“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虽说事父以恩、事君以义,在正当性的论证上有时有所不同,不过,家国一体的原则让 “施”与 “报”找到了一致性,比如,为父服丧三年,为君也要斩衰三年,以示家国在伦理原则上的同等化。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兴起,它力图剥离社会关系中的道德因素,而将之归结为基于利益的契约关系。这种做法并没有颠覆给予和回报的义务原则,只是让人们理解礼乐文化是对这种利益关系的纹饰而已。
到了汉代,在天人哲学的影响下,董仲舒将施报关系上升为 “天数”,进一步强调礼仪活动的天赋性。董仲舒说:“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 〔2〕人通过对天意的体察来感受天道,于是,报的观念有了感应论的色彩。董仲舒尝试建立一种人类活动和自然意志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同类相感”可以理解人的行为与自然现象的给予和回应的关系。比如董仲舒说:“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 〔3〕也就是说,天通过灾异等方式来 “回报”人类对于天道的奉行。
与董仲舒不同的是,刘向的思想中掺杂更多的黄老道学的因素。他试图剔除法家对施与和回报关系的解释中过于强调市场行为的倾向,而将之视为不同地位和角色的人对于自己使命的认识。圣王是社会关系中的独特存在,圣王之造福百姓,祭祀山川,并非是要从百姓和神祇那里获得回报,在动机上是无私的,尽管他依然相信积善行义的人必能从鬼神和百姓那里获得回馈。他说:“圣王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报于鬼神也。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4〕
除圣人以外,世俗的君臣之间存在着施与和回报的契约关系:“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源基,由不报恩生矣。” 〔5〕进一步说,如果把君臣关系视为市场交换关系,那么臣下所付出的必然与君主之赏赐成正比。若有精神上的契合感,那么就会不惜牺牲生命来回报。“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 《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县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6〕
在理解施与报关系的时候,并非都是施与和回报的正向关系,还有一种反向的关系,即如果有人剥夺了你本来所应该保有的利益,人应该如何 “回报”。对此,早期儒家强调的对等性原则经常会遭到现代人的质疑,《论语》中提出 “以直报怨”的问题。《论语·宪问》中记载着孔子与人的对话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对此问题,《礼记·表记》中孔子的对话呈现了这个问题的多重面向,即如何理解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可以被视为是对 “直”的观念的展开。
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
在这里孔子所强调的是等值性的社会交往原则。孔子提出,“以德报德”会鼓励百姓性善,遵循同样额度原则,对那些伤害别人的做法,则应该让行为者付出代价。“以怨报德”固然是卑鄙小人之所为,但 “以德报怨”也不值得提倡,是对于伤害行为的纵容。孔颖达的解释值得注意:“以德报怨,但是宽爱己身之民,欲苟息祸患,非礼之正也”,所以,孔颖达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是孔子提倡的 “以直报怨”。[1]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59页。孙希旦则认为“以怨报德”是不可接受的,但“以德报怨”则可以化解天下的仇怨,大致也体现了后世对于早期儒家的“直”的观念的消解。见孙希旦:《礼记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00页。《道德经》79章中老子说:“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有注者对此文是否符合老子的原意提出疑问。
那么,如何理解 “直”呢?《论语》的注家都关注了直的原则。邢昺的解释是 “当以直道报仇怨”,并没有具体解释何为直道。而朱子在 《四书集注》中,以 “公”来解释直,“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7〕。这就是说,直所体现的是无私的态度,在朱熹的解释中,强调了直的公义性的一面。认为爱憎取舍不能基于私心。清人刘宝楠的解释或许更为接近直的原始意义。他说,如果心里存有怨恨,那么就应该去复仇,如果硬忍着不报,但心里却充满着怨恨,那么反而变成了虚伪。这就违背了直的原则。〔8〕直所体现的是对等性原则,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就成为 “过直”[2]如果手段失当,破坏了对等性原则,则可谓“过直”。比如《汉书·地理志下》说:“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对等性的原则在孟子那里就体现得很清楚,在讨论 “杀人之亲”的严重性的时候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9〕。可以想象,这样的复仇原则可能是早期中国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原则。
儒家认为一个具有完备人格的人,应该能爱人也能恶人,最能体现这种原则的行为就是复仇。
一、儒家经典中的复仇
儒家经典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尽管经典中一些具体的制度规范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再适用于后世的社会生活方式,但并不意味着经典的价值观也会随之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典与秩序之间的紧张。在这一点上,复仇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在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复仇的讨论,尤其在 《春秋》中,十分褒扬复仇的价值。[3]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参见苏舆:《春秋繁露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页。《春秋公羊传》尤其褒扬复仇的精神,不惜以牺牲生命的复仇行为尤其得到肯定。另一方面,汉以后的大一统国家建立,“法律机构发达以后,生杀予夺之权被国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杀人的权利,杀人便成为犯罪的行为,须受国法的制裁。在这种情形下,复仇自与国法不相容,而逐渐的被禁止了” 〔10〕。复仇观念可能是最能体现儒家经典价值与现实法律直接冲突的例子。更有甚者,复仇事件并没有因为法律的禁止而消失,文人们不断讴歌复仇所体现的孝道和勇气,故而不断有思想家们介入复仇所体现的情与法冲突的争论中。
(一)仇恨的血缘亲疏属性
传统中国的礼制秩序最为关键的是建立亲疏尊卑不同的关系形态,从而确定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反映在复仇观念上也是这样,复仇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与复仇者的血缘关系形成正相关的关系。《礼记》里记录了孔子的两段话,就是讨论不同血缘关系所采取的复仇方式的差异的:“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父子关系是血缘关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由此,杀父之仇是所有仇恨中等级最高的。史籍中所记载的复仇故事最牵动人心的都与复父仇有关。父之仇不共戴天意指每个人负有父仇必报的伦理责任。而兄弟之仇则采取 “不反兵”的方式。对此,孔颖达解释说:“‘不反兵’者,谓带兵自随也。若行逢仇,身不带兵,方反家取之,比来则仇已逃辟,终不可得,故恒带兵,见即杀之也。” 〔11〕这里的解释很具有情景性,既指出兄弟之仇也在必报之列,又表明在行为上是时刻做好准备,甚至不能留给仇人逃避的时间。而朋友的仇,虽然也要报,但若仇人已避仇而去往他国,则可以不报。但 《礼记·曲礼上》中尤其强调了一个前提条件:如果父母健在,就不能以身死为代价为朋友报仇,这样会使父母陷入无人供养的窘境。由此可见,在复仇和孝亲相冲突的情况下,就要以孝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与 《礼记·曲礼》中内容接近的是 《礼记·檀弓》中所记录的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其解释更为详细,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复仇的亲疏属性的逻辑有其一致性,所差别的只是在细节的设置上,如关于兄弟之仇的处置方式。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12〕
上文强调了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为了报仇,不出去做官,每天在草垫上枕着武器睡觉。在街上遇到仇人,立刻拿起武器动手。在这里,“不反兵”的状态用于报父母之仇。而兄弟之仇,相当于 《礼记·曲礼》中所谈到的朋友之仇,即不跟仇人在一个 “国家”里生活。如果是因为公事去往仇人所住之国,且在路上遇到的话,也不应该立刻复仇。对于堂兄弟的仇恨,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应该让真正的复仇者去完成使命,他在后面帮忙就可以。
按照亲属关系的服制排列,那么 《礼记·檀弓》所涉及的父母、兄弟、从父昆弟更符合血缘关系的序列。但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为朋友复仇也多有;而且五伦中也有朋友一伦,《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就是将父母、兄弟、朋友、族人并举:“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13〕
有人认为 《大戴礼记》和 《周官》都是战国晚期或更晚的作品,如果接受这样的说法,可以推论出亲疏性原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详细。比如 《周礼·地官调人》中,“调人”的功能之一就是倡导复仇之前先调解,这样就为复仇设置了更为复杂的步骤:
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眡父,师长之仇,眡兄弟,主友之仇,眡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14〕
在这段话中,首先对国君、老师、朋友在伦常中的地位做了规定,即国君与父母一致,老师与兄弟相当,朋友则等同于从兄弟。在复仇的程度上,总体原则是反对直接 “反杀”而倾向于“避仇”。父母君国之仇避之海外,兄弟之仇避之千里之外。该文强调了尊重调解的意义,如果百姓私下斗狠,不服从约定而先动手的就要被诛杀。所以 《周礼·秋官·司寇》中,将复仇程序化了,“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15〕。其实,按贾公彦的解释,“凡仇人皆王法所当讨,得有报仇者,谓会赦后使已离乡,其人反来,还于乡里,欲报之时,先书于士。士即朝士,然后杀之无罪” 〔16〕。与 《礼记》中所记述的孔子复仇论的酣畅相比,这里已然将复仇行为纳入制度性治理的一个环节,这也反映了随着法制的发达,经典中对于私相复仇行为的肯定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克制。
(二)君国之仇
在家国一体的传统观念里,家恨经常跟国仇联系在一起,因此,君国之仇就是当国君被诛杀时候,君子是否应该担负复仇的义务。在经典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首先,若君被臣下弑杀,其余臣下是否有讨伐的义务。其次是君主诛杀臣下或其他人,如若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是否同样构成仇恨而要付诸复仇的行为。
我们先来考察第一种情形。针对鲁隐公在隐公十一年薨而没有记载下葬的事例,《春秋公羊传》的解释是:
公薨。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17〕
鲁隐公被姬挥所弑杀,作为一场实力不均衡的宫廷政变,不可能有人出来主持正义。然 《公羊传》认为,如果国君被杀,作为臣子不去讨伐弑君者,就等于断绝了君臣关系,甚至臣下就是间接的弑君者。公羊学家经常将之与许止没有亲尝给他父亲的药而致父亲病死的事例相类比。对于这个案例 《穀梁传》的解释与 《公羊传》的立场一致。对于其中所包含的伦理准则,《白虎通》做了系统的解释,强调了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在伦理关系上的等值性:
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故曰:父之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朋友之仇不与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邻。故 《春秋传》曰:“子不复仇,非子。”檀弓记。子夏问曰:“居兄弟之仇如之何?仕不与同国,衔君命,遇之不斗。”父母以义见杀,子不复仇者,为往来不止也。《春秋》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18〕
臣子有为君复仇的义务,这是比照父子一伦来的。不过这样的比照会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是国君杀了臣子,臣子的儿子是否有复仇的权利呢?对此 《春秋》各传的立场有很大的差异。
因国君杀臣而由臣之子复仇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当推伍子胥。对此事,《公羊传》《榖梁传》《左传》都有记载。按 《史记·伍子胥列传》的记载,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楚平王时期的太子太傅,因被人诬陷而致父兄丧命,伍子胥投奔吴国欲为父兄复仇。阖闾称赞其 “士之甚,勇之甚”。并准备为伍子胥兴师伐楚:“子胥谏曰:‘臣闻之:君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弗为也。’于是止。” 〔19〕也就是说,诸侯不得为匹夫复仇,不能因公托私。君臣一伦其重要性匹之于父子,不能亏了君臣之义,来为父复仇。
后来蔡昭公去见楚平王,因为拒绝将身穿的美裘送给楚国的官员而被拘押数年。蔡昭公回国之后,试图联合别的诸侯国伐楚。此时伍子胥提出,蔡昭公并没有任何过错,无端被楚拘押,如果吴王要维护礼制秩序,这是最好的机会,于是兴兵伐楚,父兄之仇得报。对此 《春秋公羊传》的评论说:“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也。’”〔20〕
这个设问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关涉忠孝的问题。如果事君等同于事父,那么伍子胥为报父仇而背君之行为是否正当?《公羊传》认为,如果父亲是因不白之冤而被诛杀,那么就可以复仇。此为“推刃之道”,也就是咎由自取。复仇完成,但并不斩草除根。复仇之事,朋友之间要互相助力而不是替朋友出手,这才是符合正道的。
对于伍子胥之复仇行为,《春秋穀梁传》在总体上也是肯定的,不过对伍子胥 “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的行为并不认同,并认为楚昭王虽然兵败于吴,但并没有失去楚国人的支持。在 《穀梁传》看来,吴国虽然是以维护华夷秩序为名出师楚国,但在战胜楚国之后,“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 〔21〕。其作为反倒像夷狄之行。
《左传》的观点与 《公羊传》《穀梁传》并不一致。虽然 《左传》讨论的案例发生在吴国打败楚国之后,并不直接跟伍子胥有关,但所要针对的复仇合法性问题却是一致的。话说楚怀王曾经杀害郧公之父蔓成然,故而郧公之弟想借此机会诛杀楚昭王。虽然仇恨的主体不复存在,但可以通过诛杀仇家的儿子来完成复仇的目的。对此:
郧公辛之弟怀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唯仁者能之。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女。” 〔22〕
郧公反对复仇的理由是认为君主之地位是天命所归,因此,在君臣关系的序列中,君杀臣并不能构成一般意义上的罪[1]对于君臣之仇是否可复,历代注家多有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诸侯之君与王者异,王者得天命,四海之内为家,所以君臣之义无所可去。而诸侯之臣,则可以视情形采取灵活的手段。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要化解《公羊传》《榖梁传》与《左传》之间的差异。见陈立:《公羊义疏》69,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822页。,因此,也就反对由此而带来的复仇行动。由此可见,不同的经典对于复仇的态度也是有所不同。
(三)复仇的期限
经典中对于复仇的讨论也会涉及到 “期限”,也就是说复仇不仅有亲疏之别,也会存在时间上的限制。这符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亲情不断稀薄化的宗法原则。但是,在《春秋公羊传》中,我们也看到对于时限的极端化表述:
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23〕
这则材料要传达的信息很丰富,齐襄公是淫佚之君,行同鸟兽,但在灭纪国这事上却因复仇而享受 “为贤者讳”的待遇。齐襄公的远祖因被纪侯陷害而被烹杀,所以齐襄公一直存有复仇之心,即使是占卜的结果是出师将丧失军队的一半也无改复仇之志。当问及这个远祖已经有九世的时候,便出现一个问题,即九世之仇是否还可以再报。回答是可以,甚至说国家之仇百世也可复。
这就引发第二个问题,齐襄公之远祖被烹之仇所依据的是 “君国一体”的原则,这表明如果国家存在,这个仇就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而卿大夫之家的道德责任则要按照服制而递减,家仇就不能持续九世。不过这段文字并没有讨论家仇可延续多长时间,而是强调了如果是国仇可以无限延续。
当然对于这个原则也多有争论,前文所指的“君国一体”亦可能受到 “君命如天”的挑战,更为直接的挑战则来自于君父同等化的礼制。所以,《五经异义》等比较各部经典异同的作品就认为应该是五世。贾公彦说:“依 《异义》古 《周礼》说复仇可尽五世之内。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所复者,惟谓杀者之身及在,被杀者子孙可尽五世得复之。” 〔24〕
在通经致用的原则下,经典所载通常会被制度化而施行于社会生活中。而复仇的原则与其他的礼制规则有所不同,比如,不同经典所提出的复仇原则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复仇行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公共管理体系未臻完备的时候,允许私人了断恩怨是情有可原的。然而随着专制政权的建立,生杀予夺的权力被国家收回乃是势在必行。从汉代开始,不断有法令禁止私人复仇,但是,在法律儒家化的背景之下,法律对于报仇事件的处理因与儒家经典结论冲突,而多陷入矛盾和冲突之中。
二、儒家的 “爱”与 “恨”:经典与法律的张力
《春秋》尚复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旺盛的复仇之风。至汉初,严刑峻法被认为是秦亡之原因,因此法律总体上倾向于宽泛[1]《汉书·刑法志》说:“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兆民大说。”,主要依靠萧何对秦律的改变而制定 《九章律》。对于复仇并无专门的法律条文来应对。随着 “公羊学”的兴起以及强调动机论的 “原心定罪”原则被普遍接受,汉以后的复仇风气一直高炽。[2]对于公羊学与复仇之风的关系目前认识有分歧,有人肯定其正相关的倾向,但也有人根据《汉书》等史料的追踪,“得知《公羊》与两汉风气的关联性并不密切”。但如果我们读《汉书》的人物传记,随处可见仇杀与避仇的记录,如杨雄的父亲就在汉武帝时避仇四川,而睢孟的侄子官至齐郡大守臣,也被仇家所杀。可见复仇之风深入人心,并没有因为国家统治制度的转变而减弱。见李隆献:《复仇观的省察与诠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编》,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142页。不过,大一统政治所要求的惩罚手段的垄断,导致大多数复仇者并没有因为 “孝”的动机而被赦免。
一般认为,东汉的复仇风气要盛于西汉。[3]虽然东汉公羊学之风渐息,但因读《公羊传》而立志复仇之事亦有史载:“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克斗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对于复仇正当性的讨论也多起来。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孝道之情和法律严肃性的冲突。比如,桓谭就强调了法不容情的观点,认为纵容私相报仇导致子孙无法完成孝道的悲剧。“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25〕
他认为法律所禁并不能面面俱到,关键是看对于治理国家是否有利,目的是要让善人得到保障,恶人受到惩罚。他对于复仇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杀伤行为,应由法律来处置,而不应该再私结怨仇,这种子孙相报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灭户的后果。因为世俗的褒扬,生性怯懦的人迫于社会压力也只能勉力复仇,法律的尊严也受到损害,因此必须严厉禁止私相复仇行为产生。复仇者即使自己已经逃亡,其家族成员也要受到徙边的惩罚。
不过桓谭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相反这个时期的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西汉更多的复仇记录。不但有通常的为父复仇的记录,甚至还有许多为朋友复仇的故事。比如:
恽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恽往候之。子张垂殁,视恽,歔欷不能言。恽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子张但目击而已。恽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恽因而诣县,以状自首。令应之迟,恽曰:“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26〕
郅恽治 《韩诗》和 《春秋》,时致仕归乡,看到朋友不能亲身完成复仇之志,所以一定要在其临终前替其完成夙愿。在他看来,为朋友完成复仇之事是私人的选择。复仇违反法律,则是公义,他不愿意以私人的原因来亏公义,所以复仇完成后就去自首了。这类复仇故事并不完全秉承经典的内涵,而是有了侠义之气。类似的故事还比如:“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也。少游学洛阳。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 〔27〕
东汉士人有重视名节的倾向,社会风气中弥漫着轻身尚气的习俗,甘愿为朋友赴死,这甚至违背了早期儒家经典中所强调的为朋友复仇要考虑赡养父母的问题的原则。
除了为朋友复仇的,还有为兄弟之子报仇的:“荆少为郡吏,兄子世尝报仇杀人,怨者操兵攻之。荆闻,乃出门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训导。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许掾郡中称贤,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誉益著。太守黄兢举孝廉。”〔28〕
在这个故事中,报仇的故事被描述得十分和谐。不但仇家放弃了再度复仇的想法,而且许荆还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名誉,被举为孝廉。
汉章帝时制定了 《轻侮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复仇的合理性,因此有一些复仇被宽宥的记载。对此,和帝时张敏提出了驳议,他说:
夫 《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 “在丑不争”之义。又 《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29〕
按张敏的说法,虽然 《春秋》中有 “子不报仇,非子也”这样的说法,但后世并没有因此而宽宥杀人者,主要是虑及私相复仇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如果复仇杀人可以得到赦免,那么便会鼓励那些妄杀之人;而由此引申出的其他宽恕法令,也会造成法令体系的复杂化,难以成为后世的典范。经过张敏的反复申说,最后和帝听从了张敏的建议,废弃了 《轻侮法》。
东汉时候,还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荀悦直接从经典和法律原则的关系来讨论复仇的合理性问题,他从 《周礼》对复仇的一些规定来进行申论,认为对经典的解释要与时俱进,古代的典章不一定全都符合当下的政治现实,因此复仇不可取。他以对话的方式展开他的论证:
或问复仇。“古义也。”曰:“纵复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制之以义,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曰:“何谓也?”“依古复仇之科,使父仇避诸异州千里,兄弟之仇,避诸异郡五百里,从父从兄弟之仇,避诸异县百里;弗避而报者无罪,避而报之,杀。犯王禁者罪也,复仇者义也,以义报罪。从王制,顺也;犯制,逆也,以义顺生杀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为弗避。〔30〕
他指出:按照古代所规定的复仇原则,杀父之仇要避到千里之远,兄弟之仇则是500里,从兄弟是100里,如果不避的话允许复仇。但这种做法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现实。如果说复仇是一种责任,那么首先应该报告官府,服从法律规范,这是顺,而违背法律则是逆。这是公共的规则,人就应该遵循。这就直接否定了复仇行为的正当性。
到三国时期,国内战乱频繁,曹魏政权严禁报仇。但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赵娥复仇的故事。《后汉书·烈女传》记载:
酒泉庞淯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闾。[1]此故事在《三国志》和皇甫谧的《烈女传》中都有记载,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民间故事化倾向。虽然这个故事原型在酒泉,但后在浙江亦流传一个曹娥投江救父的故事,并将那条河命名为曹娥江。参见〔南朝〕范晔:《后汉书·烈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96-2797页。
这个故事表明杀人者李寿了解复仇的必然性,但看到复仇的主体三兄弟病死,他以为没有可复仇的人,仇怨可以了结。不料,其女儿却替父亲完成了复仇,并在完成使命后束身就刑。当时的官员不忍烈女受死,甚至想与之一起逃亡。赵娥坚持不能因复仇而枉法,事实上既承认了经典的意义,也接受法律的规则,属于公私兼顾。虽然故事的结尾是赵娥被赦免,但礼法之间的冲突已经表现得很充分。
法律史大家瞿同祖先生指出,东汉之后的法律,一般都禁止复仇[2]“曹操、魏文帝、元魏世祖、梁武帝,都曾下令禁止复仇。魏律对于复仇的处罚重至诛族,元魏之制尤为严峻,不但报仇者诛及宗族,便是邻伍相助者亦同罪。北周时代的法律对复仇者,亦处死刑。唐、宋以后的法律都一贯禁止复仇。”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5-86页。,不过晋代的法律一度受传统复仇观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复仇。但有一个附加条件是,对于已经赦免或因失误致死的案例则禁止复仇。“贼斗杀人,以劫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 〔31〕
汉代至魏晋,法律儒家化不断推进,儒家的价值逐渐在法律中得到体现。不过,复仇现象因为直接挑战国家对于刑事裁量权的垄断,构成了公权力和私仇之间的尖锐对立。所以,大多数的时候,法律是禁止复仇的。不过在价值观上,复仇背后的忠孝意象则始终被表彰。这样的矛盾和紧张在唐宋时期依然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得到呈现,而且参与争论者越发具有社会影响。
三、唐宋时期的文人学士对于复仇的争论
唐代统治者对于复仇的态度因时而异,初唐时复仇者多得到嘉勉。武则天到唐宪宗时期,陈子昂提出对复仇者需加以惩罚的奏议,官方意识到复仇与官府的权威体系之间的冲突。后又因宪宗时期的梁悦案,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肯定复仇的奏议,宪宗对于复仇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3]学者归纳史籍所载从唐初到唐末的15件复仇事件,发现唐太宗时期复仇当事人多被宽宥,在武则天到高宗时期则伏法,宪宗之后再度倾向宽恕。参见李隆献:《复仇观的省察与诠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编》,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238页。
关于唐代如何对待复仇事件的法律后果的讨论很多,参与者多是我们熟悉的人物。在 《旧唐书》和欧阳修主持的 《新唐书》的 “孝友”类中收录了许多复仇的故事。
讨论比较集中的案例有三个。其一是山东即墨人王君操的复仇故事。王君操之父在隋朝大业年间被乡人殴杀,其母告官又被收捕,年幼的他便四处流浪并寻觅机会报仇,最终在贞观年间复仇成功。不过,这个时期的史书倾向于渲染复仇过程的 “酣畅”,也可窥见对复仇行为的肯定。王君操为报父仇,在仇家已经投案自首的情况下,仍手刃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被视为孝的表现,而列入 “孝友”录。他在面对州司时慷慨陈词:
州司以其擅杀戮,问曰: “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对曰:“亡父被杀,二十余载。闻诸典礼,父仇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亡灭,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据法处死,列上其状,太宗特诏原免。〔32〕
唐太宗赦免王君操体现唐初对于复仇的宽宥态度。但这种态度在唐代并不常见。武则天时期,下邽人 (属今陕西渭南)徐元庆之父徐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隐姓埋名做驿家保。过了很久,已经做了御史的赵师韫正好入住此驿站,徐元庆手杀之,然后去官府自首。对于该如何处置徐元庆引发了巨大的争论,首先是左拾遗陈子昂提出:“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干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圣人修礼治内,饬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33〕
但具体到徐元庆的案例,陈子昂认为,徐元庆为父复仇,然后束身归罪,其行为堪比古代的烈士;按法律,他必须服罪就死,但如果按 《公羊传》“父仇不同天”的古训,则应该赦免。刑罚的作用是防止社会动荡,而教化的作用是养成崇德的社会风气。徐元庆的复仇行为不能称之为触犯刑律,而以复仇行孝道,仁义之举。如果把这样的仁义之行等同违法而加之以刑,则难以为社会树立道德标准。然而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 〔34〕
陈子昂主张让徐元庆伏法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在礼与刑的紧张中主张维护法的权威性[1]陈子昂的奏议,“终究强调了‘法’的权威性:‘法’才是国家公义之‘纲’,才是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量;‘礼’则是非强制性的,‘礼’既无权,也不应介入‘法’的运作,‘礼’所表彰的行为,若不合法,仍应依‘法’诛之。”参见李隆献:《复仇观的省察与诠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编》,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240页。,作为对其孝义行为的肯定,可以在徐元庆的家乡和墓地表彰他的行为。对此,许多人并不认可陈子昂的主张。到中唐之后,关于复仇的礼法争论重回人们的视线,时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再度从礼刑的关系立论来反驳陈子昂的观点:“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不得并也。”〔35〕按照柳宗元的看法,如果法律要诛杀道德高尚的人,就会让法律与道德相违背,是对刑罚正当性的损害。如果表扬该杀的人,就是直接冲击社会价值。具体到这个事件本身,如果赵师韫是借助公器来泄私怨,虐杀无辜,而他的上级机构不加以纠正,不能倾听受害者的申诉,那么徐元庆精心谋划以复父仇,是守礼而行义。执事机构才应为这一切的发生承担责任,怎么能对徐元庆处以极刑呢?如果是徐元庆的父亲不免于罪,而被赵师韫诛杀,并不违背法条,“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由此,徐元庆的复仇行为就是与法律乃至国家秩序为敌。“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36〕
柳宗元认为礼书中对于可复之仇是有严格规定的,是指 “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不是指那些犯法违禁而被诛杀之人,不能不管曲直、盲目行动。柳宗元总结说:“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37〕
柳宗元的结论是,像徐元庆这样的行为可以称是 “达理闻道”之人,如果这样的人反而要被诛杀,这不可以成为典例,要改变的是律法,不应以陈子昂的奏议从事。
唐玄宗时一件比较复杂的复仇事件也引发朝廷的关注。有山西人张琇,其父张审素为巂州(今四川昌西一带)都督,被陈纂仁诬告私人佣兵,唐玄宗起疑而派监察御史杨汪前去调查。这时陈纂仁又进一步诬告张审素和他的总管董堂礼谋反。于是张审素被收监,董堂礼气愤之下杀了陈纂仁,并领兵围困监察御史试图让其释放张审素。很显然,这一系列鲁莽的举动似乎坐实了陈纂仁的告发,最终官兵剿杀董堂礼,并处斩张审素。张琇和他的哥哥逃往岭南,伺机报仇。在他们兄弟还只有13岁和11岁的时候,就返乡杀杨汪,并向官府自首。对此,中书令张九龄等称其孝烈,宜赦免。侍中裴耀卿等则认为应该处死,唐玄宗也同意此主张,并对张九龄说:“孝子者,义不顾命。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律。凡为子,孰不愿孝?转相仇杀,遂无已时。”〔38〕虽然当时有不同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杀了他们兄弟二人。
从唐玄宗的决定看,对于复仇之事在法律上该如何处置,不同的皇帝虑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会作出不同的决断。不过,高扬道德的赦免派的观点一直有支持者。张九龄、柳宗元的态度影响到韩愈对于复仇的态度。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当时有梁悦为其父复仇,对于这件事,宪宗下诏说,按法律杀人当死,而按 《周礼》则父仇必报,对于此礼法之间的矛盾,责令尚书省提交意见,当时还任职员外郎的韩愈写了奏议说,子复父仇是“大义”,在 《春秋》《礼记》等经典和史书里都有记载,一般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对于复仇,理应有专门的法律条文来处置,但律无其条。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39〕。韩愈认为,经典之大义虽然由圣人阐发,但执行的则是具体的司法部门。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经典所载情况有充分的了解。韩愈举 《周官》中的话 “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指出,复父之仇是有明确范围的,如果不是枉杀,就不能视为“仇人”。即按 《公羊传》的解释,只有父亲受冤而死,而致父死之人没有被惩处,才可以进行复仇,而且进行复仇之前,需要告知相关机构。
韩愈认为,复仇行为要考虑到具体的情景,即使是经典中所列举的状况也难以完全覆盖现实的多样化。所以,对于复仇者,“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也就是说,所有复仇事件的处置要上报到尚书省,根据经义和现实的情景来判断。另外,“《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40〕。这属于特别的状况,即那些为复仇而一直隐匿自己志向的人,肯定不会先向官府备案,对于这样的情况,赦免与否,也要经过尚书省的讨论,再来作决断。
唐代的思想史展现出比较明显的礼法冲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韩愈所说的 《唐律》中并无明确的关于复仇的条例。间接与复仇相关的如 《唐律·斗讼》中有关 “祖父母为人”殴击部分,核心的内容是长辈之间的争斗,子孙不得参与;如果祖父、父母被别人打,子孙必须是随后赶到解救才符合减轻处罚的条例;如果在解救祖父母、父母的时候,不慎致人死亡,也会按 “杀人者死”处置;最关键的是,只允许有血亲关系的人复仇,如果是佣人或部下,则只可以解救,不能帮忙。〔41〕
宋代的哲学是中国思想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就复仇而言,王安石的观点延续了唐代韩愈等人的讨论。王安石并不肯定复仇,认为 “非治世之道也” 〔42〕。他说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应该各修其职,犯罪的事件必然会得到惩处,即使是有冤屈,也有申诉的地方。《春秋》和 《礼记》之所以强调复仇,是因为属于乱世,人人相为仇敌,由此才会让复仇合法化。
王安石指出,即使在 《春秋》《周礼》中,对于复仇也有一定的规定,甚至有严格的程序性的要求。而且儒家总体肯定恩而非仇,暴力复仇恐怕并非周公之法,所以王安石认为有仇不复固然是 “非孝”,但并非一定要通过复仇而导致 “殄祀”。也就是说断绝对祖宗的祭祀,也不是孝顺的行为。“仇之不复者,天也;不忘复仇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亲,不亦可矣。” 〔43〕
与王安石在社会变革等方面有很大争议的北宋理学家并无专文讨论复仇,只是在与学生讨论经义的时候会涉及。比如程颐就与学生谈及复仇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问:“周礼有复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亲被人杀,其子见之,不及告官,遂逐杀之,此复仇而义者,可以无罪。其亲既被人杀,不自诉官,而他自谋杀之,此则正其专杀之罪可也。”问:“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获免,便使避之也。” 〔44〕
这则对话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案例,不过程颐谈及了几种可能性,即如果亲眼所见亲人被杀,肯定来不及告官,这时的复仇行为应该被赦免。而如果知道消息的时候,亲人已经被杀,就应该告官而不能 “专杀”。程颐还肯定了 “避仇”。
至南宋,因靖康之耻,故而治 《公羊传》的胡安国侧重发挥了 《公羊传》中的复仇观念。胡氏特别强调臣复君仇的意义,认为复仇即使失败也值得肯定。为了强调复仇的迫切性,他支持《春秋》中的九世复仇的主张。
对于复仇观念的讨论,到明末和清末再度兴起,黄宗羲与章太炎等思想家都有专门的论述,但其重点并不在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紧张,而是关涉到民族矛盾和统治权力的转移,其讨论的理论背景也并不直接与经典中的复仇表述相关,当有另文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