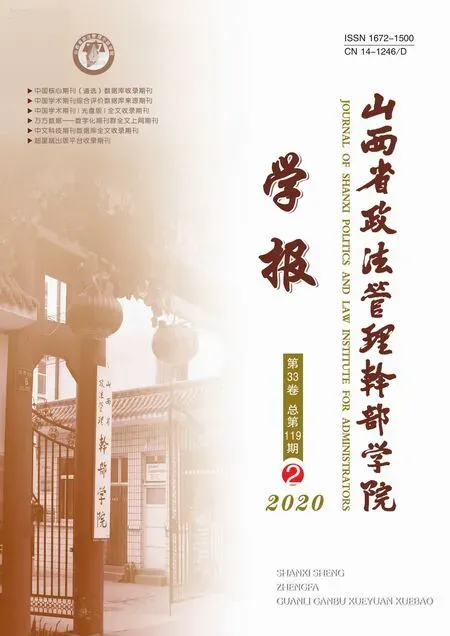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确立路径
张 璐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00091)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是中西方法律文化交流的研究重点之一。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或批评或赞美的整体判断,但认识与评价只是呈现在眼前的静态结果,而交流本身是一个双向的、漫长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在动态中以他者视角为观察点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值得研究者们投入更多注意力。
中国传统法律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形象的构成之一。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历史,应当将其放在中国形象史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其中有四个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是如何产生的;第二,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第三,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1]第四,在当今资讯传播条件下,中国如何主动塑造并传达自己的法律形象。因篇幅所限,本文着重探讨西方文化中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确立路径,传统法律形象的延续及评价分析,将在其他文章中继续讨论。
一、传闻中的中国法律
欧洲对于中国的最初印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希罗多德的叙事长诗《阿里玛斯贝亚》中记载了诗人阿里斯特浪漫的远东之旅,其中多次提到希伯波里安人,诗中描绘他们居住在北风吹来的地方,是一个神秘的、热爱和平的民族。
公元前五世纪,丝绸已经传入欧洲,成为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奢侈品,他们将这种昂贵的织物称为赛里斯(Seres)。在关于远东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中,能看到很多关于赛里斯人的记载,颇富传奇色彩。赛里斯人能够生产漂亮的织物,所用的原料是从森林里一种特别的树上长出来的如羊毛一般的叶子。对于西方人来说,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的人都被称为Seres,译为“赛里斯”人。在罗马人的概念中,赛里斯已经代表着世界的边缘,自然而然地成为罗马人对照的对象,想象的他者。
在帝国后期的文献中,赛里斯被描绘成人间天堂来反衬罗马的衰败。“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2]这段摘自三世纪初的文字被很多古文献引用,颇受赞美的异教徒形象跃然纸上。
到了公元七世纪,西方流传起关于“桃花石”的传说。后世学者指出桃花石与隋唐之际的中国多有相似之处。[3]记载中出现了对当时中国法律的描述:“这一民族崇拜偶像,其法律是公正的,生活中充满着智慧。”[4]
因为地域和时代的局限,这时的中国形象大多是零散的、片段式的,偏重通过对于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细节性描述传达出来。这些文字描绘出的形象,既像一个有人居住、秩序井然的现实国家,又像一个寄托美好期望的理想国。赛里斯、秦尼城(Thinai)、库博丹(Khoubdan)、桃花石、在大地的尽头、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遥远的东方国家在激越的想象中被塑造。这只是小心翼翼地接触和好奇地观望,远远称不上交流,包括传统法律在内的中国形象只是一个虚幻摇曳的影子。
二、亲眼所见的中国法律
历史继续向前,文献中陆续出现了突厥(Turcs)、鞑靼、契丹、蛮子这样的称谓。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打通了陆上通道,快速推进了亚欧文明一体化进程。十三至十五世纪,更多欧洲人来到中国,一篇一篇的游记、书信与报告使得中国形象逐渐清晰。此时的主角是使者、教徒、商人,他们往往有丰富的游历经验,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用生花的妙笔向西方描述这个富饶、神秘国度,有纪实,有虚构,但常常是纪实与虚构纠缠在一起。这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
蒙古人的扩张,震惊了整个欧洲,引起了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的不安。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全欧主教大会,商议防止蒙古军队进一步入侵等问题,会议决定组织以柏朗嘉宾为首的使团出使蒙古。两年后使团返回欧洲,其沿途见闻都记录在了《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
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份关于远东地区的详细报告。身为圣·方济各会修士的柏朗嘉宾写到:“契丹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字母,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同时也有使徒传、隐修士和修建得如同教堂一般的房舍,他们经常在其中进行祈祷。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惟一的一尊神,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举行任何洗礼。”[5]
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对于异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在基督教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当中,有上帝之城,就有地上之城;有基督徒,就有异教徒;有天使,就有魔鬼。柏朗嘉宾理所当然地用自己的叙事模式去介绍契丹人,他们是异教徒,但似乎阅读《新约》《旧约》,敬重基督和圣徒,这已经是一位基督徒最为宽容的理解,但显然是一厢情愿地虚构。
大量的信息无法纳入已有的知识体系,于是任其呈现本来面目。落入空白的信息就很可能成为关于事实的知识,中国形象及传统法律在外国人的笔下显现出来。柏朗嘉宾的报告用大量篇幅详细描述蒙古人军队组织、武器装备、作战策略,这与欧洲对于蒙古骑兵的忌惮不无关系。文中只有零星的语言涉及蒙古人的习惯与法律。根据记录,当场抓获偷盗农作物或在他人领土上行窃者,都要毫不留情地杀死;泄密者,尤其是泄露了军事秘密者,要在臀部打一百杖。
在此之后,又一位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奉法兰西国王圣路易士九世之命,于1253年开始了出使之旅,其使命除传教外,还包括了解有无可能拉拢蒙古统治者参与十字军东征。使团返回欧洲后,鲁布鲁克用拉丁文写成了名为《鲁布鲁克东行记》的出使报告。
鲁布鲁克断言契丹就是古代的赛里斯人。他将契丹纳入了赛里斯的知识体系中,复活了西方文化中对于赛里斯人的幻想。“有人告诉我,该地区有一个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他们还告诉我如下的真事:在契丹的那边有一个省,不管什么年龄的人进到里面去,他的年龄将永远和进去时一样”。虽然鲁布鲁克自己也强调“不过我不相信”,但他仍旧在不自觉地重复着赛里斯人富足、文明、长寿的固有形象。
鲁布鲁克是一位严肃的旅行者,他没有能够超出赛里斯的幻象,但还是竭尽所能地用细节描述契丹。他在旅行报告中特意列出标题介绍蒙古人的法律和审判,只是篇幅很短。他记录道,两人聚斗时,任何人,即使是父亲都不能干涉,受害的一方可以向宫廷申诉,加害方会被判处死刑;对杀人和大盗窃也处以极刑,但是诸如盗窃一只羊之类的小偷小摸,只要不是屡次被抓,痛打一顿也就放了;在婚姻方面,儿子可以娶除了他生母外父亲所有的妻妾。
如果说传闻当中的中国形象只是若隐若现的虚像,那么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看到的中国开始有了细节,但是这细节仅仅局限在固有印象和与自己文化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好奇之上,有了一两笔清晰刻画,但整体而言还是模糊的。
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写的是关于出使蒙古的报告,其后的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则进入到了中国腹地,写成了中国内地的报告。成书于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是中世纪欧洲了解中国最重要的窗口,他用华丽到夸张的词汇为欧洲描绘了一个更为鲜活的中国。
异乡人来到迥然不同的世界,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人们认识一个新世界,总是从最直观最简单明了的器物开始。山川河流,楼台亭阁,衣食住行,一一记录下来,向同类展示一个令人着迷的他者。相对于中世纪贫穷落后的欧洲来说,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城市繁荣的东方国家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财富与秩序的天堂。元朝历史虽然不长,但蒙元的天堂形象却在西方社会各个阶层广为流传,延续并强化了赛里斯神话,这是西方中国形象的起点,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慢慢建立。
三、亲身经历的中国传统法律
与十三、十四世纪欧洲人通过西亚的陆路进入中国,且来者寥寥行色匆匆不同,十六世纪随着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殖民势力的扩张,欧洲人大多从海路造访,其活动范围和时间都超过以往。此时来华的欧洲人主要是称霸于海上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益于新航线的开辟,这些人以政治家、传教士、商人和冒险家的身份陆续进入中国,成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而中国则在日记、见闻、信件、报告等等多种多样的叙述方式中,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西方。这时,中国的形象“在被更正、被确认或被推翻,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实现神话,提供范例,造就乌托邦。”
这一时期欧洲人对中国法律的总体判断趋向良好,“公正”是不约而同被屡次提及的一个词。“(中国)司法极为公正,判决的依据从来不是一方或另一方说的话,而是站在局外形成的看法,这样就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并允许当事双方保留权利。”“我要谈谈中国人在司法方面的措施,应该知道的是,这些异教徒在这方面是多么超越基督徒,比他们更讲公道和事实。”“在主持司法方面,这些人是独一无二的,胜过罗马人以及其他任何一种人。”“大自然赋予中国的其他东西亦都是如此,无论是健康清新的空气,还是社会文明、物质财富以及景物的宏伟壮观,都无可比拟。为了使这一切更加光辉灿烂,这里的人们极其守法,政府的治理又极其公平卓越,令其他所有的国家羡慕不已。倘若一个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哪怕具备其他所有的各点,哪怕地再大物再博,仍然黯然无光。”公开审判和官员异地就职是欧洲人赞扬中国法律公正的有力例证。亲身经历过中国司法审判的伯来拉对审讯印象深刻,认为审判官员在提审时具有极好的耐心,每一个人被带到面前时都会受到仔细询问,而判决时并不偏听偏信,以局外人的观点做出公正判断。每次审讯和讯问都是公开进行的,这有利于避免“将很多人的生命、财产和名誉置于某个没有良心的书记官当中”,而在葡萄牙的法庭上,证人说的话只有审问者和记录员两人知道,用钱贿赂作弊的现象屡见不鲜。官员异地就职是很多报告都提到的一点,“没有一个官员被派往家乡或有亲戚的地方任职,这样就不会涉嫌包庇,在司法上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四、中国传统法律形象分析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理论前提上有两种不同的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立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客观反映这一假设,关注观察者根据自身经验,对中国做出或真实或错误、或全面或片面的理解与曲解。而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则是立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一前提,与客观和虚构无涉,关注观察者对于中国的自我构建,甚至创造。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时,这两种知识立场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侧重。在形象确立阶段,观察者更多出于自身经验,在表述中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法律形象。
赛里斯是位于遥远东方的奇幻乐园,距离间隔出充分的想象空间。古代西方关于赛里斯的传说,总是离不开羊毛树的故事。此后六百多年间虽然有桃花石、秦奈等零星信息带去了天子统治、人口众多、繁荣富饶等新元素,丰富了对于遥远东方的认知,但西方人一直无意打破关于赛里斯人间天堂的迷梦。直到十三世纪初,德国文学家仍然在骑士文学中将赛里斯作为富有异国情调的点缀,将其与华丽的丝绸衣服和异国风情主题联系起来。这一时期是中国形象确立前的准备阶段,西方人给中国预留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形象。
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带着教皇的使命来到了蒙古,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进入到了中国腹地,他们将亲眼所见的繁华富有的东方国家带进了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视野。鲁布鲁克的论断将契丹纳入到赛里斯的知识体系,这个东方世俗乐园唤醒了以往的记忆,并大大扩展了基督教束缚下西方人狭隘的世界观。中国形象逐渐确立:这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威仪的大汗的统治下,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人民富足。此时的西方处于中世纪晚期,民生凋敝,需要建立一个美好的他者作为对照,来批判现实,来寄托向往。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大汗是权威的象征,中国形象传达出西方人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追求,目光集中在器物层面。法律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但在只言片语中传达出“完备”“公正”的信息,与美好的中国形象大体保持一致。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人才在亲身经历中描绘着中国法律的形象。
地理大发现时代,海上交通的便捷使得更多西方人获得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新消息冲击着旧有传说,新知识颠覆着固有印象,“大中华帝国”的形象已然建立。平托在《游记》卷首献词中提到“东方的大帝国”,在文中也多次使用“中华帝国”来指称中国。从类似《游记》这样关于中国的畅销书中,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观念在17世纪初的欧洲已经开始流行。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和文化中确立了清晰完整的形象,这一形象是完美的、优越的。它无意提供某一方面真实的信息,更倾向于总结性地树立起一个标准化的中国形象。这一标准化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契丹传奇,但用中华帝国取而代之,也为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新的起点。与此同时,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们也亲身经历了中国古代的法律,法律公平有效、政府治理卓越、人民克己守法。中国传统法律的形象与中华帝国形象相得益彰。
五、结论
中国传统法律形象在西方文化中是随着中国形象的确立而确立的,其发展也大致延续赛里斯——契丹——中国这一路径。十六世纪后半期来华人士的报告和记录,使得中国形象第一次清晰地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我们还不能就此夸大这些对中国法律零星的描述会对欧洲产生如何深远的影响,但是,这毕竟是第一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从这里开始,中国传统法律将慢慢为欧洲人所知晓,为此后的批评或赞美树立起明确的形象,中西方法律文化交流的大幕缓缓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