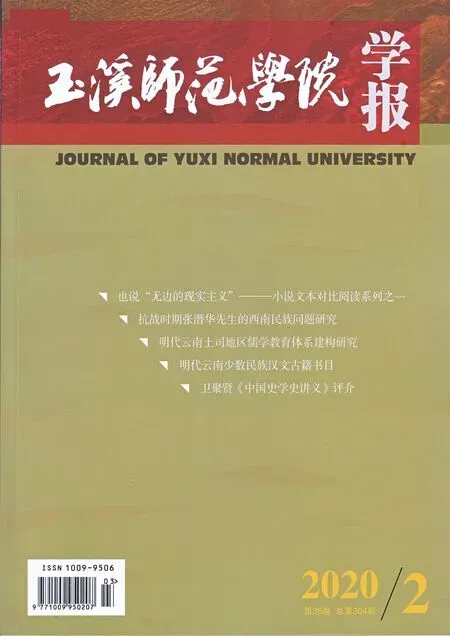抗战时期张潜华先生的西南民族问题研究
王 倩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张潜华,字黔化,出生于1904年,吉林省永吉县人,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早年为奉系军阀重用,后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层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40年,张先生完成《西南民族问题》一书(1)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345.。《西南民族问题》于1941年出版后,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影响力持续到当代。此书前言部分有张先生代序《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民族政策》,正文内容主要论述西南民族概况、各省施政方针、最近的民族纠纷等,另有附录十五则,多录自古籍、档案、报纸报道、政府调查报告等。民族纠纷是此书的核心内容,主要研究了湖南“永绥抗租”、广西“桂北瑶变”和云南“邱北苗变”。该书是首部系统研究“永绥抗租”“桂北瑶变”和“邱北苗变”的专书,但目前学术界缺少对张潜华先生及此书的专门研究。
一、《西南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张先生于1939年发表的《今日的苗夷》,是他最早进行西南民族问题研究的成果,主要内容是强调西南苗夷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简述了西南苗夷的起源、发展;叙述西南苗夷当时的状况,按地区分为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展开;把苗夷问题的症结归为边官的压迫、土司的淫威、奸民的盘剥、豪绅的掠夺、生活的贫困、知识的简单;讨论对苗夷应有的态度;从党务、政治、经济、教育方面提出解决苗夷问题的方法(2)张潜华.今日的苗夷[J].新政治,1939,1(5):22-30.。《西南民族问题》是在此文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必要性及西南民族概况
张先生首先强调了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必要性。当时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它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决不问你为汉,为满,为蒙,为回,为藏,或为西南民族”(3)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2.。但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导致西南民族问题十分严重,张先生认为:“完成国内少数民族的统一与协调,并进而动员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战,实吾人当前最要的急务。而西南民族问题的解决,尤为急中之急。”(4)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2.在此危急存亡之际,若不能加紧解决西南民族问题,将加速中国四分五裂的趋势。而解决西南民族问题,既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抗战力量,又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协调与统一,实现全民族抗战。
然后,张先生对西南民族的概况进行了简述。他把西南民族分为“湖南民族”“广西民族”“云南民族”和“贵州民族”,并分别从种类与分布、生活与习尚、政治与文化三个方面大致介绍了西南民族的概况。接着,张先生总结历代对西南民族的政策是武力的征服、政治的羁縻、经济的剥削,认为国民政府对西南民族应该采取的态度,首先是解除上述带来剥削和压迫的政策,其次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再者是要设法扶持西南民族,使其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
(二)三次民族纠纷及各省解决办法
张先生在此书中主要探讨了三个事件:湖南“永绥抗租”(1936~1937)、广西“桂北瑶变”(1932~1933)和云南“邱北苗变”(1933),简单提及了贵州石门坎苗民异化事件,这些事件对后来西南各省的民族政策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一是“永绥抗租”和湖南省政府的屯田政策及教育政策。“永绥抗租”是指1936年和1937年湖南省永绥、保靖等县要求废除屯田的事件。湖南省的凤凰、乾城、永绥、保靖、古丈、泸溪和麻阳共计七县为苗民聚居地,这些地区的屯田制度到民国时期已经废弛,但屯田佃民照旧纳税。1936年6月屯务处清查1935年以前积欠的屯租,苗民无力缴纳,遂爆发“永绥抗租”事件,经二十八军军长陶广调停,未致发生火拼,苗民递交废屯呈文(5)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永绥苗人废屯呈文[M].重庆:青年书店,1942:331-337.,要求改租为粮。1937年1月爆发二次抗租事件,双方进行武装对抗,不久又发生龙云飞等人起事。这时南京战事严峻,地方政府采取和平方式解决纠纷,而实际上苗民废屯抗租的目的并未实现,广大贫苦苗民依旧深受压迫。
“永绥抗租”事件后,湖南地方政府进行了屯田改革,1936年下令豁免屯田七县前三年欠缴租谷,并减免借贷,剔除屯田之各种陋规,整理屯军。1938年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号召屯田七县举行解决屯田纠纷的会议,决定在永绥、保靖县政府征收租额的百分之三,并照每石一元五角折算,解交省府。湖南教育厅1937年1月于乾城创办特种师资训练所,招收苗族优秀青年入学,毕业后分派苗区各学校执教,同时拟定了《苗民小学六年实施计划》(1937~1942),在苗民聚集寨落逐步从短期小学到完全小学的过渡。
二是“桂北瑶变”和广西省政府的民团政策及教育政策。“桂北瑶变”是指1932年和1933年在广西省兴安、全县、灌阳、龙胜等县发生的两次瑶变。张先生分析其原因概括为生活苦闷、妖巫蛊惑、皇谣发生、团绅压迫。1932年春爆发首次瑶变,广西省政府起初采取和平方式,派指挥官张淦调解宣抚,惩办团绅,对叛变领袖进行适当的罚款处分,并制定善后办法。但不久又爆发了二次瑶变,反叛瑶民内部形成严密的组织,设置官员,有旗帜文告。当地政府在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下,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最终解决。
广西省政府受到兴、全、灌、龙等地的两次瑶变的影响,清楚省内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单纯依靠武力解决,实施了民团政策和特种教育政策。组织民团方面,广西省政府颁布了《广西省各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和《化瑶大纲》来推动实施。《广西省各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中规定:完全苗瑶民户的乡村甲由上级机关委派一人协助办理公务,其费用由上级机关支给;防止与医治传染疾病费用由公费支出;苗瑶学生免除学费,并供给书籍和笔墨纸张。《化瑶大纲》的目的是加强对苗瑶的同化,强制乡村甲的编组。教育方面,广西于1933年4月制定了《广西特种教育实施方案》,并于1934年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1935年3月在南宁设立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在苗瑶聚居地广设小学(6)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章程择要[M].重庆:青年书店,1942:316-318.。
三是“邱北苗变”和云南省政府的党化政策及教育政策。“邱北苗变”是指1933年云南省邱北县苗民反抗地主剥削的武装斗争事件。其起因主要在于土豪劣绅对于苗民的盘剥和压迫,邱北地区有一种“舖小票”(7)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191.按:“舖小票”为邱北特有土地凭证,苗民多居处深山峻岭,开耕荒地后,土豪劣绅即相率而来,拿出所谓“舖小票”,便认该山为其祖先遗业,勒令苗民必须逐年出租,方能耕种,苗民处其势力威胁之下,遂不得不成为土豪劣绅的佃户了。,迫使大量苗民成为佃户。再者邱北地区自古以来汉苗冲突不断,仇恨极深,以致苗民频频反抗。此外,邱北苗民多种烟苗,而不知政府禁烟条令,因而还要缴纳罚金,而1933年邱北雨量稀少,春收产量受损,更成火上加油之势。
三月初,王相、侯保全以“小皇帝”的迷信方式,宣传王相为“丞相”,侯保全为“大将军”,吸引了许多苗民相邀奔赴、举家而来,规模逐渐扩大。邱北县政府起初采取调解劝抚的和平方式,3月13日进行武装围剿,但败北而归。不到一个月,苗民已从数百人发展为15 000余人,且组织严密、训练有素。3月28日,十七团第三营抵达邱北,4月12日击溃苗民部众,6月1日缉获叛首侯保全。1933年“邱北苗变”期间,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曾组织宣传大队到达邱北一带,并拟定《抚绥苗夷民族实施纲要》(8)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云南各县抚绥苗夷民族实施纲要[M].重庆:青年书店,1942:325-330.,确定此后云南各县党部的苗夷工作方针:筹措专款聘请熟悉苗夷语言文字的专家经常进行相关活动,宣传抗战,教化苗夷。
云南省的苗夷教育发展最早,早期外国牧师到云南传教,在边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深山地区广设教堂和学校。云南省政府也于1931年公布《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规定各县办学经费自筹、师范学校对土司及地主子弟优先录取,但受经费限制,边地教育尚未充分发展。直至“邱北苗变”后,教育部于1935年8月拨款9万元给云南省,指定其中2万4千元用于设立苗民小学,2万5千元用于发展苗民师范教育,云南省教育厅也拟定《云南省政府实施苗民教育计划》,云南省的苗夷教育从边地教育进入了苗民教育的新阶段。
四是石门坎苗民异化和贵州省政府的党化政策及教育政策。石门坎位于贵州省威宁县,是花苗聚居区,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对当地苗民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异化教育。1904年英人柏格里来到此地后,建立教会,兴办学校、医院,传教士们对苗民实施异化教育,包括信仰之异化、文字之异化、以苗教苗(9)娄贵品.红军长征时期国民党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认识及其影响[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2):228.,这种异化教育导致石门坎苗民不仅缺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自称外国人。1936年春杨森将军到石门坎,他谈道:“地方土人在欢迎会席上致欢迎词竟称:‘我们外国人,从未见过中国官长,今日杨将军来,实为来此地的第一个官长’……威宁地方土人,亦有忘却其自己所居的住地为中国领土者,云南昭通,也有同样情形。”(10)杨森.促进边胞文化运动之意义[J].边铎月刊:创刊号,1946(1):5-6.同年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向蒋介石汇报:“(石门坎)一般民众……不知有县政府,更不知有国家,加之英人自柏格里深入苗寨,改英文为苗文,该花苗只自认为苗文,老幼男女皆能通习。”(11)民国时期经营威宁石门坎地方办法档案一组[J].贵州档案史料,1990(1):2.张先生并未对石门坎苗民异化事件进行详细研究,但提及石门坎教会时曾写道:“他们积极的从事于宣传教义和创设学校之工作,这种文化侵略之尖锐,与云南教会的活动并无二致。”(12)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137.
张先生尽管认识到石门坎教会对苗民的异化教育是文化侵略,但并未进一步分析这一事件对地方、中央的影响,仅简要论述了这时期贵州党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变化。党化方面,1935年以后,贵州各地党部逐渐建立起来,其推进计划分三个方面:一是开拓党部,在贵州各地特设党部办事处;二是训练青年,吸收优秀苗夷青年入党,设立“边区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招收苗夷青年或通苗夷语言的汉族青年;三是加强同化,1937年制定《贵州省各县苗夷族同化工作纲要》,组织各县夷族文化促进会,在苗乡发动农会。教育方面,1935年春蒋介石到贵州,提出从贵州的教育经费中每年拨款10万元用于苗民教育,贵州的苗民教育也被并入义务教育共同办理,1936年在青岩镇创办青岩乡村师范学校,于苗民数量最多的12个县设立苗民四年制初级小学,特设民俗研究会,又于青岩镇设立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对石门坎苗民异化十分重视,除张先生所提及的在教育、党化政策上的调整,还实施了其他措施。杨森将军在石门坎地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一是强调民族主义;二是选拔苗夷青年送入中央政治学校读书;三是派专人在石门坎做督导工作(13)娄贵品.红军长征时期国民党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认识及其影响[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2):231.。蒋介石命令“边政设计委员会”处理石门坎事宜,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向蒋介石提交了调查报告和处理办法,提出《经营石门坎的办法原则》,内容包括文化和政治方面,在这个原则的指示下,贵州政府又提出更为详细的治理方案,经蒋介石同意后,1937年在石门坎设置了“石门设治局”,专门治理石门坎事宜(14)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895-1945)[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21-123.。
(三)西南民族问题的症结及解决办法
当时正是抗战十分危急之际,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纠纷,有人以为只要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便能解决,而所谓“民族自决”,即“国家分离的自决的权利”。张先生感叹:“那么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运用‘民族自决’的口号来欺骗和分化我们民族的今天,如果我们不顾事实,自己还在高叫‘民族分立’,这不正是替敌人提出欺骗和分化我们民族之理论上的根据吗?”(15)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前言[M].重庆:青年书店,1942:4.张先生通过研究以“永绥抗租”“桂北瑶变”和“邱北苗变”等为代表的西南民族问题,分析其症结可归纳为六类:贪官的压迫、土司的淫威、汉人的盘剥、豪绅的掠夺、生活的贫困、知识的简单,认为这些也是西南民族问题发生的最基础的原因,都是政治、社会问题。张先生解释:“永绥抗租,是为反抗湘西屯务处的非法横征暴敛,这是政治问题。兴、全、灌、龙瑶变,是基于巫觋的蛊惑和团绅的压迫,这又是社会问题了。‘邱北苗变’,他们要求交出大地主杨映池、杨天池等,还不是因为邱北豪绅常以‘舖小照’的手段压迫苗民之反动吗?所以这依旧是社会问题。”(16)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205-212.因而张先生总结:“西南民族问题是存在的,不过并不是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只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已!所以绝不能把它提到正式民族问题的程序上去谋解决。”张先生的分析为反对西南地区实施“民族自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症结已明,就要对症下药,张先生从党务、政治、经济、教育方面提出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方法。
党务方面,中心工作是开展对西南民族的政治教育。具体来说,包括成立西南民族特别党部、中央制定统筹计划、以种族为标准区分西南地区的苗夷工作、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政治方面:(1)设立一个西南民族能参与其中的中央机关,或将蒙藏委员会加以改组;(2)解决土司问题,由中央政府明令各省,确定土司地位与职权,同时奖励苗夷社会团体;(3)打击土豪劣绅。
经济方面,核心是改善西南民族的物质生活,具体方法是:(1)改良生产方式、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成立农村贷款社;(2)开发矿藏、森林资源、药材等;(3)开辟重要公路;(4)发展其他事业,如畜牧业,制革业,及各类轻工业。
教育方面,苗夷教育已有所发展,但是存在几个问题需待解决:(1)经费的分配问题,应普遍分配于苗区所有学校;(2)师资的训练问题,西南各省都设立有特种师资训练所,但其学生是汉人多于少数民族,可由教育部设立“国立特种师范学校”,面向西南各省苗夷青年招生;(3)教材的编辑问题,应根据苗夷的具体情况编辑教材;(4)教育实施情况,进行生产教育、公民教育及卫生教育(5)学校的设置问题,应优先设置于苗夷聚集的寨落,其次才是汉苗杂居的地区,如果苗夷分布零散,应施行巡回教育;(6)学生的待遇问题,目前各省对于苗夷学生待遇的规定都比较合理,但应严格禁止汉人子弟冒充入学。
二、当时学者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评价
《西南民族问题》于1941年和1942年经重庆青年书店两次发行,一经发售,便销售一空(17)端木阳.立院有个张潜华[J].中国人物,1949(5):6.。此书不仅论述了当时西南民族的分布与类别、政治与文化、民族纠纷等,且为解决西南民族问题提供了切实的建议,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著名史学家罗香林、署名“玄默”和“燕”者都对此书进行了评价。
一是史学家罗香林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评价。罗香林先生将关于西南民族的研究分为三类:(1)采用西洋人类学或语言学的调查方法,着重实地考察,而缺乏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掌握;(2)重视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考据,附益时人的调查报告,易穿凿附会;(3)作者为一时对于民族问题的热情,自身无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的相关知识,主要依据对西南部族的实地调查和问题讨论,瑕瑜互见。罗先生认为《西南民族问题》属于第三类,并进一步分析了此书的优点与不足。
优点是:(1)张先生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提出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建议是建立在实际情况之上的。“这一本书……大部分的材料,却都是经过了实地的调查与访问,对于西南民族问题的解决上,或可提供一些实际的意见。”(2)西南民族种类繁多且复杂,分布范围广,实地调查难度大,新旧资料的排比与对照也很困难,从事这种繁重的工作,张先生的精神足以令人敬佩。(3)填补了西南民族研究的空白,如叙述湘西苗瑶的地理分布,亦比较详实,如各省施政方针,“亦多为普遍言西南部族问题之人士所未及综合论述者”。
不足是:(1)界说不明。“湖南民族”“广西民族”“云南民族”“广西民族”之标题不适宜,建议改作“湖南之苗民”“广西之苗瑶侗僮”“云南之苗民倮倮与僰夷”“贵州之苗民倮倮与仲家”。(2)分类错误。“广西民族”的内容中,把白倮倮、黑倮倮、花倮倮等与苗瑶僮相混,又“举汉人中之一重要支派,亦混入于苗瑶僮诸部族之中”。(3)在叙述西南各部族的“生活与习尚”内容时,含混不清,“独举其一支派之景况,固不足以尽概其余。而任举其一派景况,不标明系属名称……则尤足引人发生误解”(18)罗香林.新书介绍:西南民族问题(张潜华撰)[J].图书月刊,1941,2(2):20-21.。
二是“玄默”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评价。署名“玄默”者,非常赞同张先生把西南民族问题归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绝对不是民族问题的观点,认为这是此书的最大特点,“是每一个研究‘西南民族问题’者应有的根本认识”。但是“玄默”认为第二章“西南民族概况”的标题——“湖南民族”“广西民族”“云南民族”“贵州民族”之类的说法并不恰当,“不仅令我们看着有些刺眼,也许将来会发生难以设想的流弊”,建议保留地名而不采用民族两字(19)玄默.西南民族问题[J].蒙藏月报(副刊),1941,13(5);转引自:娄贵品.“中华民族是一个”观念的萌生与确立[C]//汪宁生,主编.民族学报:第10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81.。
三是“燕”对《西南民族问题》的评价。署名“燕”者,主要介绍了《西南民族问题》一书的内容,也对标题“云南民族”“贵州民族”等提出质疑,并建议改为“云南境内之少数民族”“贵州境内之少数民族”等更为恰当(20)燕.新书介绍:西南民族问题(张潜华撰)[J].图书月刊,1941,2(8):30.。
可见,以上三位学者都认为原书中“云南民族”“贵州民族”等标题不恰当,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建议。罗香林先生建议改为“苗瑶侗僮”“倮倮与僰夷”“倮倮与仲家”等,此外罗先生将中国境内各族群称“部族”而非“民族”,在他所著的《中国民族史》(1966)一书中,强调中华民族与各部族的联系。“玄默”也强调中华民族,还建议不能把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群称为“民族”。“玄默”和罗香林先生的主张都是响应了1939年顾颉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主张的背景是因为日本将中国境内各族群定义为“民族”,鼓吹“民族自决”来分化中国(21)马戎.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问答与讨论[J].青海民族研究,2014(1):73.,因而不采取“民族”的说法,强调中华民族。而“燕”建议改为“少数民族”,是因为其赞成所谓“西南民族问题”并不是民族问题,因而不担心为敌人所利用,不仅承认了“民族”,还强调标题“云南民族”“贵州民族”等,结合原书内容,这里的“民族”应指的是各省内的非汉人群体,改作“少数民族”更为恰当。他们对此书的评价较为中肯,所提出的建议也都有合理之处。
三、张先生西南民族问题研究的价值
张先生对“永绥抗租”“桂北瑶变”“邱北苗变”的系统研究填补了当时西南民族研究的空白。他的研究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参照了大量的文献和档案资料。基于西南民族问题的解决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张先生进行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解决西南民族问题、团结抗战力量的建议。他对西南民族问题的根本认识,即以“永绥抗租”“桂北瑶变”“邱北苗变”等为代表的所谓“西南民族问题”并非是民族问题,强调正确认识涉及民族因素的事件这一点,对现在正确辨析民族问题有积极作用。张先生的民族观与后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共通处。
一是学术价值。《西南民族问题》一书是首部系统研究“永绥抗租”“桂北瑶变”“邱北苗变”的专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系列事件的影响重大且深远,不仅使中央加强了对西南民族的重视,也使地方政府调整了对西南民族的政策。关于这三个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原因分析及对西南各省政策的影响,张先生首次作了综合论述,填补了当时西南民族研究中的空白。
张先生对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已逐渐为人所重视,部分文献目录中收录了《西南民族问题》(22)录有《西南民族问题》的文献书目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编的民族史类《中国史学论文索引(1937-1949)》,康恒基1984年主编的民族史料《贵州省地方文献目录》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84年编的《社会学参考书目》,贾忠科1984年主编《民族研究资料索引(1933-1983)》,老彭1988年编的《民间文学书目汇要》,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1991年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近代、现代少数民族”和“评介序跋”),周焕强2009年总编的《重庆市志·民俗志》。。
同时,《西南民族问题》的参考价值也逐渐被人重视,如吴荣臻主编的《苗族通史》和龙伯亚、吴曙光、吴荣臻主编的《苗族通史》(讨论稿)中关于“永绥抗租”事件的经过多次引用张先生的论述,《苗族简史》(修订本)关于“邱北苗变”事件的内容参考了《西南民族问题》,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写的《湘西苗族革屯史录》,引用了此书附录部分的《永绥县解除屯租愿团呈文(之二)》(23)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湘西苗族革屯史录[M].贵阳: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5:96-97.,温春来教授《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中,提及教育部拨款发展贵州民族教育的过程中,黔西北没有设立少数民族师范学校的论述(24)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2008:314.参考了此书。除了民族纠纷的内容外,《西南民族问题》中关于西南民族生活习尚的内容也多被引用,如管彦波先生的《文化与艺术: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研究》和吴山、陆原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容美发美饰辞典》,引用了此书关于广西少数民族头饰的论述。此外,王文光教授《民族史研究论稿》(2007)论及研究西南民族史的主要论著时提及张先生的《西南民族问题》(25)王文光.民族史研究论稿[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66.,白兴发《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2011)论及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的专著时亦提及此书。
二是文献价值。张先生的研究注重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他明确说过自己到过云南,“此次吾人留滇考察,在一个月内,便发生两次苗瑶作乱。”(26)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201.“此次吾人曾赴昆明县属苗区各小学考察施教情况……”“在昆明时,曾遇到几个苗夷优秀青年……”(27)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135-136.在《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中,关于西南民族生活习俗的记载,大多依据的是张先生的实地考察。除了实地考察之外,张先生还参考了大量的文献。
参考文献可分为五个类别:(1)古籍方面,参考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皇清职贡图》《滇略》《黔苗图说》《百苗图说》《黔书》《黔南职方纪略》《平黔纪略》《东轩笔录》《湖南通志》《广西通志》《贵州通志》《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融县县志》。(2)时人的研究成果方面,参考了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察记》(1933),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1933),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1936),石宏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1936),范义田《云南边地民族教育要览》(1936),申廓英《汉译苗疆民歌集》(1937),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1938),陈廉贞、黄操良《抗战中的中国民族问题》(1938),王建光《苗民的文字》(1938),黄尧承《贵州苗夷琐谈》(出版时间不详)。(3)外国人著作方面,参考了[英]瓦特著、杨鹏云译《西康神秘水道记》,[法]费亚《苗文字典》。(4)调查报告方面,参考了1931年《贵州自治筹备处关于贵州民族的调查报告》、1936年《广西省民政厅关于苗瑶分布的调查报告》。(5)报纸方面,参考了1938年10月和11月《时事新报》、1938年8月21日和24日《云南日报》。
此外,附录所附文献共17篇。包括《〈苗黔图说〉所载贵州少数民族种类分布表》《〈续云南通志〉所载云南少数民族种类分布表》《云南省昆阳等五十三县局少数民族统计表》《云南现有土司调查表》(1927)《费亚所著苗文择要》《〈大清一统志〉所载贵州少数民族分布表》《〈贵州通志〉所载贵州少数民族概况》《明清两代贵州土司官制表》《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章程择要》《云南义务教育委员会对于苗民教育之解释》《云南苗夷学校一览表》《云南各县抚绥苗夷民族实施纲要》《永绥苗人废屯呈文》《桂北瑶民旗帜之书式》《桂北瑶民文告之内容》《王成保事件》《红头瑶事件》。
张先生所参考的文献类别丰富且数量颇多,既有正史、地方志、档案,也有马长寿、江应樑等汉人学者和曲木藏尧、石宏规、范义田、王建光等少数民族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有外国人研究著作、政府调查报告、报纸等。这在当时艰难的抗战条件下,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工作。遗憾的是张先生并未明确标明他所参考古籍的版本。附录十五则多是张先生的考察报告、对古籍的重新整理和对政府调查报告、报纸等重要文献的摘录,这为现在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据张先生的“后记”,此书写作中所参考的档案材料及意见,湖南方面的可能来自曾任乾城县长和创办特种教育学校的石宏规先生;广西方面的可能来自曾主持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刘锡蕃先生和曾主持“开化”大瑶山教育工作的唐兆民先生;关于西北地区的资料,可能来自于曾到西北地区负责战时巡回教育和宣传工作的著名学者卫惠林先生和战时曾任边疆教育委员会秘书编有《西北问题图书目录》及《西北开发》杂志的王文萱先生,因而此书写作所参考的档案资料比较详实可靠。
三是历史意义。张先生认为:“抗战胜利最重要的关键之一,便是动员整个的民族。”因此张先生以西南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希望能为西南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切实的建议,推动全民族的团结与合作,为抗战胜利做重要准备。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地区成为抗战的根据地,联合西南民族实现抗战胜利已经为国人所重视和实践。这一时期,极少数的夷苗精英已经意识到数千万的西南非汉人群体是被遗弃在“五族共和”这个体系之外的,他们也正在积极争取平等的权利,而更多的夷苗却缺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如曲木藏尧体会到在“五族共和”的框架下,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西南非汉人群体什么也不是,凉山夷人李仕安也谈道:“那些年,民族关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大家都晓得,除此之外,哪个晓得其他少数民族?彝族大家都不晓得。孙中山的旗帜,都是红黄蓝白黑,五个颜色,代表五个民族。像彝、苗,没有人知道。”(28)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8-41.曲木藏尧、高玉柱等发起了西南夷苗请愿运动,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西南夷苗与汉满蒙回藏一样的地位,保障其应有的权利。
而更多的夷苗却缺乏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同,共产党人彭宇鸣回忆他在西南地区的经历时谈道,抗战时期他在阿坝地区做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卓克基有土司索观瀛受过教育、粗通汉语,已然算是西南少数民族中思想开化者,在抗战问题上索观瀛却说:“日本人来了,我还是当我的土司。”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怎能将西南民族隔离出去?直至彭宇鸣先生进行了思想工作,索观瀛方转变思想,感叹道:“那样的日子,我这个蛮子也不愿意当亡国奴。”(29)彭宇鸣.我在阿坝地区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373-374.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抗战根据地转移到西南地区以后,抗战与西南民族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但在团结西南民族共同抗战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张先生所谈到的西南民族问题。这个西南民族问题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夷苗精英要求平等和权利,另一方面更多的夷苗并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如何解决这个庞大的问题?张先生便写了《西南民族问题》一书,希望能够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在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办法上,张先生提出中央应该设立一个西南民族能参与其中的中央机关,这无疑是与曲木藏尧等人的政治诉求是相同的。
四是现实意义。什么问题可认为是民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问题,有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懂法或者不守法酿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虽然带着‘民族’字样,但不都是民族问题。”(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9-90.而张先生对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也早就明确了这一点,强调“谁也没有办法否认西南民族问题的存在”,要正确认识涉及民族因素的事件。
关于如何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强调“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31)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1939-2-13(4).。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从欧洲人类学的理论来看,不同历史、语言、宗教、体质的群体就是不同的民族,后来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但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个整体——中华民族。顾颉刚先生只注意到国家危机与“民族国家”理论,而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中整体之下存在差异(33)潘先林.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27.,费孝通先生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为中国历史演进的特点,使中华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肯定了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张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他的观点:“西南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构成单位之一,其地位和其他的汉、满、蒙、回、藏诸族,一点也没有差别。”(34)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M].重庆:青年书店,1942:204.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这与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有共通之处。但此书以《西南民族问题》为名,在书中仍旧采用了“民族”的说法,张先生言:“这些民族,因为血统、文字、语言、宗教以及风俗习惯和汉族不能全同,自然不免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形态……”(35)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民族政策:前言[M].重庆:青年书店,1942:1.强调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的各部分存在差异,尊重中华民族整体中各部分的平等,这与顾颉刚先生的主张又有不同之处,更相近于后来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符合当代正确的中华民族观。
四、结 语
1939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原边疆问题讨论会改组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张先生被选为该会第一届委员,任期一年。根据1940年5月该会修正的章程,“其组成人员,系由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各派主管人员二人,经济部,内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治学校及中英庚款董事会各派代表一人,并由教育部聘请其他熟悉边疆情形之专家十二人至十六人充任之”(36)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边疆教育概况[M].重庆: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3:41.。这几类组成人员中,张先生应属于“教育部聘请其他熟悉边疆情形之专家”,此外在教育部组织的西南边疆教育考察中,张先生的名字曾出现在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秘书处预拟的参考团员名单上,这些都说明教育部认可张先生对西南边疆有一定研究。
正是中国抗战十分危急之际,西南地区成为抗战根据地,而日寇却以“民族自决”为幌子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挑拨与分化。在此背景下,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而张潜华先生也于同年发表《今日的苗夷》,次年完成《西南民族问题》。两人原本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都有着局限,但正是因为拳拳爱国之心,使他们转而从事民族研究,希望能于抗战救国中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