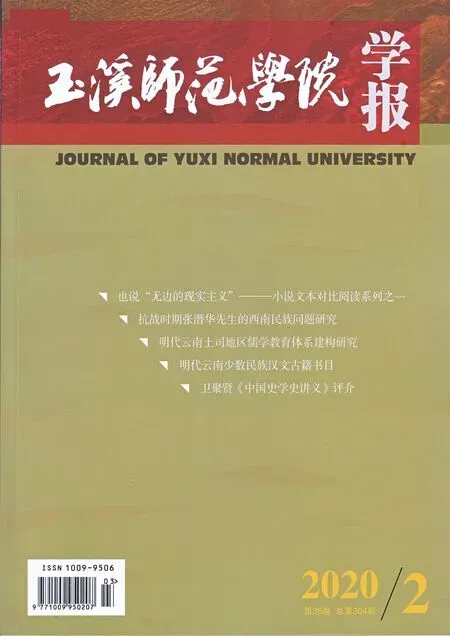火塘边吟唱的“巴哈阿依”
——哈尼族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桂芬访谈录
杨骁勰
(云南民族大学 文传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巴哈阿依,哈尼语音译词。巴哈,指月亮、月光;阿依,指美丽动人的姑娘、女神。
张桂芬,女,哈尼族碧约人,1944年出生于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初小文化。7岁开始向其母李琼及民间艺人鲍李氏(1)鲍李氏,女,已故,哈尼族碧约支系人,1916年出生于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新发社区辛路组,知名哈尼族民间艺人。学习演唱哈尼族民间叙事长诗《阿基·洛奇洛耶与蜜扎·扎斯扎依》(后文简称《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学习与悉心研究,她全面掌握该诗的表演技艺,不仅能用哈尼族碧约人的“腊达调式”(2)腊达调式,哈尼族歌谣的固定曲调之一,可配合不同的唱词,吟唱的时间、场所受限制的格调,主要运用于单人独唱。演唱,而且能以“木叶”(3)哈尼族、彝族、白族、傈僳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吹奏乐器,是男女青年用来表达爱意的一种乐器,通过运用适当的气流吹动某些植物的叶片,使其震动而发音。为伴奏,是滇南地区哈尼族中备受尊重的民间艺术家。她长期致力于此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2009年民间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被国务院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2年张桂芬成为此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位该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哈尼族民间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全诗共10章,2 000余行,主要章节有“开头的歌”“赶街相会”“秧田对歌”“串门求亲”“成家立业”“领头抗租”“不死的魂”“结尾的歌”等。此诗通过讲述民族英雄洛奇洛耶与少女扎斯扎依从出生成长、婚恋成家、领头抗租、死而复活到英勇牺牲的人生历程,歌颂哈尼人民朴实、淳厚、纯真和倔强的民族性格。该诗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鲜明,语言质朴凝练,是一首极具文学价值的民间叙事长诗,因此被哈尼族碧约人世代传唱,成为众多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中的一朵“奇葩”。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与多元文化的碰撞摩擦,哈尼族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叙事长诗一样,陷入固守传统与开拓创新的两难境地中。如何保护、传承这笔宝贵的哈尼族文化遗产,并适度地对其进行创新、改造,令它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发挥新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深入思考、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带着对哈尼族叙事长诗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及发展方向的思考,笔者于2019年12月7日赴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采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桂芬及其徒弟鲍永贵、胡德温,就哈尼族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相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为全面呈现张桂芬和《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奇妙之缘,笔者将访谈录音整理成稿,以飨读者。
一、师承:哈尼山寨成长的“小阿依”(4)小阿依,哈尼语音译词。阿依,指美丽动人的姑娘、女神。
大山与古歌是走进张桂芬故事的钥匙。上世纪40年代,张桂芬出生于哀牢山中的一座小城——墨江,这里山脉延绵、地势陡峭,有十一个哈尼族支系聚居于此。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孕育了张桂芬“大山儿女”的奔放个性。由于家庭环境影响,张桂芬自幼就受到音乐启蒙,沉浸在喜好音乐的家庭氛围中。年仅七岁的她,拜入民间艺人鲍李氏门下,开始学习民族舞蹈和“腊达调式”的哈尼古歌。也正是从那时起,她与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结下了跨越世纪的不解之缘。
杨:张老师,您好!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张:好的。我出生于1944年12月,属猴,今年有76岁了,是哈尼族碧约人。阿妈会说汉语,所以当时没按哈尼族的习俗来取名,而是取了一个汉族的名字——桂芬。
杨:请问您最早接触《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是什么时候?
张:要问最早的话,我已经记不清,没什么印象了。那时候我还是小娃娃(孩子)呢,后来长大听阿妈和寨子里老人说起才知道的。我阿妈年轻的时候很俏(漂亮),是唱歌、跳舞的能手。在我们姊妹兄弟中,她最喜欢我,每次去插秧田、摘野菜、捡菌子,阿妈都会背着我去。我们哈尼族天生爱好音乐、喜欢唱歌,大人们一起劳动的时候就会对唱山歌,有时候是即兴演唱,有时候是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里“秧田对歌”“赶街相会”的片段。我就这样从小在阿妈的背上听,跟着瞎哼,慢慢就对唱歌、跳舞有了兴趣。而且,那时候电灯还没普及,到晚上寨子里会堆柴生火,大家就围着火塘取暖聊天,我们小娃娃也会一场(群)跑到火塘边玩,阿叔、阿孃就经常讲故事给我们听,最爱说的就是诗中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为大家反抗地主的故事,每次都讲一点,从他们俩出生的章节开始讲起。慢慢听多了,对故事也就熟悉了。
杨:既然您从小就知道这个故事,那么您是从何时开始正式学习演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呢?又是何种机缘开启了您这段不平凡的艺术人生?
张:大概是在我七岁多的时候吧,最开始是阿妈在家里教我一点简单的调子,因为当时年纪小,所以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学。后来家里大人都说我嗓子好,有演唱天赋,就送我去拜李孃孃(鲍李氏)做老师。李孃孃是我们寨子里最能唱会跳的,她还参加“民间文艺队”,是队里的骨干。她主要教我跳民族舞,唱“腊达”调。我跟她学的最多的是古歌(5)哈尼族的传统歌曲,有固定的调式,但没有歌词,主要靠哼唱、高低音转换完成表演。,像《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桌席间的欢乐调》《情调》《哭嫁调》这些。后来学的时间久了,会唱的歌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寨子或者周围寨子但凡有活动,李孃孃都会带着我和文艺队一起去。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害羞,比较拘束,不太跟队里人交流,不过慢慢熟悉了以后,我也会向文艺队里其他老师请教演唱的技巧。
杨:我们来之前听说,您的家族和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有很深的渊源,之前您也提到过除了老师鲍李氏之外,阿妈也是您学艺生涯最早的老师之一。可以请您给我们讲讲您的家族与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之间的故事吗?
张:我们家先后有三代人学习演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我阿婆学唱这个长诗,是在她还未出嫁以前,那时候她一有时间就跟着寨子里的老人学习演唱。但那个时候大家还不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都忙着做活计、讨生活,只有在婚丧嫁娶、祭祀农闲的时候才会唱适合的片段。她在家里的同辈中排行老大,平时有许多活计要干,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只能利用空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学,所以只会一些片段,唱得不完整。在嫁到阿公家以后,她一直没有孩子,时间比较多,就爱在寨子里到处串门。恰好认识了寨子里的一个老摩匹(6)摩匹,哈尼语音译。又记作“斯匹”“刹匹”等。旧时哈尼族社会中负责主持原始宗教各种活动的男性祭师,分神授和师传两种,他们使用师徒联名制度,多者连名数十代,少者有几代或十几代。内部没有等级之分,只有掌握各种祭仪多少、水平高低之别。在哈尼族社会中,“摩匹”作为原始宗教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以及古老文化的传播者,该职业一直沿传至今。,于是就拜他做老师,开始好好学唱长诗,最终把整个长诗学会了。听我阿妈说,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阿婆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在阿妈大概三、四岁的时候,阿婆领(带)着她唱“腊达调”,到她八、九岁时,就已经能够完整讲述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故事,在她10多岁的时候已经能演唱全诗了。后来,阿妈有了我,又把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本事传给我了,我们家就这样代代相传,与这首长诗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杨:这样看来,您演唱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技艺主要是由老师和母亲传授的吧?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该诗的主要传承方式是母女传授、师徒传授?另外,在选择传承人时,是否有性别的要求呢?
张:我现在唱的《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确实是由师父和阿妈教的,阿妈先教了一些,师父又教了一些,不过还有一部分是后来我自己修改的。其实,演唱这首长诗的方法并不死板,只要故事的主干是对的,其他的细节还是可以由我们演唱者自己自由发挥的,不一定非得严格按照学到的来唱。这首诗主要还是师徒传授,我属于特例,阿妈教娃娃唱这首诗的情况并不算很多。至于说究竟选谁来教唱这首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想学都可以教。在我们寨子里女娃娃想学的比较多,男娃娃就不是很喜欢,一般只有被选做“摩匹”的才要学习。不过,唱这首诗,尤其是“腊达调”,对嗓音的要求比较高,不仅声线要高,而且嗓门要大。
杨:刚刚听您多次提到了“腊达调”,请问这是属于哈尼族音乐里的一种调式吗?是怎样演唱的?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张:我们民族歌曲有很多的唱调,像“过山调”“过门调”“古根调”“嫁女调”“喜庆调”“哄娃娃调”等等,但这些调都只是作为演唱时衔接前后两句歌词的过门,没有实际的意思,仅仅是随着场合的不同而更换相应的唱调。比如“过山调”只有在年轻娃娃对唱情歌的时候才用,在老人面前是不能随便乱唱的。“喜庆调”是在请客的时候专门为祝酒歌做引子的。“腊达”实际上就是一种过门唱调,这个词是哈尼语,用汉语翻译过来就是“过门”的意思,所以“腊达调”也就等于是“过门调”,一般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单独演唱的时候使用,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唱歌时最常用的曲调。
杨:刚刚您谈到了许多自己与家人在学艺生涯中的故事。由此为基础,我们还想请教您作为一名初学者,在学习演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时,经历了什么样的学习过程?
张:这要看个人的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程度了。我现在教徒弟,开始的几个月都要先教会他们怎么吊嗓子,因为这是基本功。然后开始学习演唱“腊达调”,只有掌握好调式才能更好地把握演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时的节奏。等“腊达调”掌握了以后,就要开始学习讲故事,从“开头的歌”开始,把每一章的主要内容都串连起来,让他们一边听一边记在心里。等学生能把整个故事的主要内容都复述下来,就会清楚地知道第一章该唱哪些,第二章又该唱哪些,这样就能按着自己记忆的顺序唱下去了。如果把《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比作一棵树,故事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的主干,以他们的出生、结婚、抗租、牺牲、复活、纪念六个方面串连起来。而枝干则是每一个唱段中的细节,主要靠演唱者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比如“秧田对歌”这一段,如果我很熟悉插秧,就可以自己添加许多东西(元素)进去,像在劳作过程中腰怎样弯、手怎么分或者秧田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鱼。这就是说,细节并不是固定死的,不超出正常生活的范围,只要符合日常生活劳作常识就可以。
杨:谈到学习话题,今天我们见到的两位老师应该都是您的爱徒吧,听说您一直致力于《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传承人的培养。目前为止,您培养了多少位徒弟?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完整演唱全诗?
张:这些年,正式收的徒弟前前后后有二十几人,能完整演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差不多有十个,包括永贵和德温。而且,只要家里没有农活需要做、也不跟着歌舞团表演的时候,我就抽时间去墨江县城小学给娃娃们上音乐课,算是他们的特聘老师。主要讲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故事,也教他们唱简单的哈尼古歌。现在的娃娃不像我们小时候了,大部分都不会说哈尼话,但我教的哈尼歌,他们多少都能唱几首。现在年纪大啦,越是这些一代传一代的东西,不敢忘记,希望娃娃们长大以后也能记着。
杨:那除了学生外,您有几个子女呢?现在您主要是和谁在一起生活的?儿女中有学习和演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吗?他们的下一代呢?
张:我一共生了四个娃娃,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大的两个儿子住在墨江县城里,小儿子在景洪打工,姑娘很早就嫁到外地啦。老伴不在了,现在家里就我自己一个人(住),娃娃年节的时候才回来。他们都不学了,三个儿子忙着打工养家,姑娘嫁得远,顾不到啦。
二、史诗:伴随哈尼历史的“启波然”(7)启波然,哈尼语音译词,意为标志、纽带、共同体。
在张桂芬心中,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是融入血液里的精神皈依。对于与她相同的哈尼族碧约人也一样,他们用这首长诗迎接着新生命的来到,也将离去的灵魂送归“诺玛阿美”(8)诺玛阿美,地名,出自于哈尼族迁徙史诗《诺玛阿美》,诗中形容其四面环山,一江奔流,是哈尼人世代追寻的理想家园,已成为哈尼族强大的生命力和躬耕梯田、坚守稻作、向往幸福生活的民族精神代表。。可以说在哈尼族碧约人一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里,都伴随着这熟悉的旋律,就像一条长而坚固的纽带,牵起属于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张老师,能请您介绍一下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由来吗?
张:好的。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哈尼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大部分人又很喜欢唱歌跳舞,特别是农闲时节的晚上全寨人会约着找一块空旷的地方搭火塘,老老小小聚一起聊天、唱歌、弹琴、烧烤、喝酒。《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就是在火塘边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创作出来的故事,但是那个时候只作为传说故事,没有人把它当做长诗来演唱。随着这个故事的传播越来越广,我们民族里最有知识的“摩匹”开始把《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改编成长诗用于诵经,这最接近我们现在演唱的版本。
杨:我们听说完整的演唱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耗时很长,想问问您,具体需要多久呢?
胡:嗯,要三天三夜才能唱完,但全诗只有一个人不间断地唱几乎不可能,因为唱诗很费力气也伤嗓子。而且,仅第一章“开天辟地”,就有三个多小时,内容也比较复杂。“开天辟地”的内容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女娲娘娘造人,但初期的人类是泥巴捏出来的,阴阳不分,他们和任何动物都可以相亲(结婚);第二层是因为最初的人类不完美,于是自然神放了一场大火“翻天覆地”,让阴阳不分的泥巴人消失;第三层是“翻天覆地”后期的新人类的诞生,也就是一对叫阿齐、阿撒的两兄妹成了夫妻,并诞下一个大葫芦,哥哥阿齐将葫芦摔碎以后,葫芦里跳出来了傣、拉(祜)、佤、哈尼几个民族兄弟。
杨:还想请问您,作为传承人,演唱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禁忌吗?例如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张:生活习惯上的禁忌没有,但如果传承人到其他地方去表演或者帮忙,开场会有一些讲究。比如我家住在回回冲寨,到别的寨子去表演《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在演唱之前首先要夸这个寨子风景优美、稻谷丰收;如果寨子里有长寿的老人,为表示尊重,会先唱些祝他们健康长寿的调子,然后祭祀他们寨子里的竜树,才能正式开始演唱。
杨:那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一般会在什么场合演唱?选择哪些唱段呢?
张:我们需要演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场合很多,比如,十月年、祭竜神、矻扎扎节、结婚、孩子出生、丧礼、收稻谷、扫屋、招稻米魂、叫猪牛羊魂、打牛皮鼓送鬼神的时候都要用到。选段也要依场合而定,有喜事的时候就唱“接亲”的片段,祭竜神的时候就唱“祭祀”的片段。
杨:张老师,您之前为我们详细介绍过“腊达调”“过山调”等几种哈尼族的常用调式,刚刚又提到了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演唱的各种场合。想请教您,对于不同的场合演唱该长诗在调式上有所区别吗?比如祭祀时“摩匹”演唱的版本和生活中用于娱乐的版本是否一致?
张:有区别的,我们在演唱时会依照不同的场合选择相应的调式。比如,“摩匹”用于送祖归宗、叫魂、祭水神、祭竜神等祭祀场合演唱的是“祭祀调”,演唱的速度很慢,而且每唱一句尾音都会拖得很长,听起来像是在哼唱。平日里,个人为了娱乐而演唱时,多用“腊达调”,速度要快很多,语气也比较欢快。还有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是两人对唱的“过山调”,一般要配合着牛腿琴来弹唱,而且比其他调子多加入了一段关于牛腿琴来历的介绍,比如对唱开始前,弹琴的一方要先讲讲制作牛腿琴的树是谁砍的、用的是一棵树的哪个部分、这棵树长在什么地方等等,然后才开始对唱。
三、突破:困境中求发展的传承人
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口传史诗从各个民族形成的初期便开始萌芽,在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更替中,被一代又一代的传诵和记录下来。但由于近年来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碎片化知识的日益膨胀,古老的史诗正在经历一次全新的挑战,怎样更加有力的保护、有效的传承和有用的创新,都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虽然已年近耄耋之年,张桂芬却仍在为保护和传承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辛勤地工作着。比起彷徨,我们在她的眼里看到的是笃定与坚毅,她多次提到,自己一定能和这个相伴七十载的老朋友一起“过关斩将,再创辉煌”。
杨:张老师,听说您多次参与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搜集、整理和补充工作,可以聊聊您印象最深刻的经历吗?
张:应该是北京来的专家和县政府的领导领(带)着我们去搜集整理的那次吧。当时我年纪还轻,白阿叔(9)白杨才,男,已故,哈尼族碧约支系,普洱市墨江县人,知名哈尼族民间艺人,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最早版本整理传唱者。他们人也还在,后来《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能出版成书,底子也都是那一次打下。还记得那些北京来的专家和我们一起围着火塘,边聊边唱,由白阿叔领唱,我们在旁边跟唱补充,然后县城里会说哈尼话的记者李胖做翻译,最后记录了厚厚的一本笔记,有些汉字和符号,前几年我还在墨江哈尼文化研究所见过那本稿子,很旧啦。
杨:那您对于少数民族口头叙事长诗用汉语搜集、整理、写作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您认为用汉语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口述长诗在内容上还能保持原貌吗?中间会不会出现什么误解或者“言不达意”的地方?
张:能记下来当然是好事情,我希望这些稿子和书能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并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比如说现在最新出的书,里面汉语、英语、哈尼话三种版本都有啦。而且,不仅在墨江,《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在红河的哈尼族里也有传唱,还流传到越南、泰国、老挝的哈尼人那里。我认为用其他语言翻译记录,大概意思还能保持相似,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了。比如“我们两个”这一句,用哈尼话来说,就只有一种说法,我们一直都用相同的词来表达。可是,到了汉语里“我们两个”有好多种表达的方式了,每一句都用不同的词代替。特别在书里面,换来换去的,和我们原来唱的就不一样了。
杨:张老师,2009年是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之后,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对于我,更多是一种爱好、平常生活里的娱乐方式。后来墨江县哈尼文化研究所联系到我,说《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变成国家的“非遗”项目了,省内外有好多比赛和展演都来邀请我去参加,而且身边了解和对它有兴趣的人也多了起来。对于我自己来说,首先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国家给我们传承人许多补助经费和传承经费,一年有两万,生活质量也提高起来啦。另外,得到重视以后,我和其他传承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传承和保护《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工作。比如,每年组织大家参加“传承人培训”,各村寨的传承人都会聚在一起交流、表演。以前大家没有这么多时间,也没有这么丰富的活动,都各自忙着家里的事,插秧、种菜、碾谷子、捡菌子忙都忙不完。
杨:如今,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都面临着困境,您认为《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年轻人都不想学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而且现有传承人的年纪都比较大啦。年轻人不愿意学,主要原因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初学者是没有任何补贴的,因此仅靠学习演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没有收入保障、不能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是寨子里大部分年轻人去省外打工,没有时间和兴趣学习了。
杨:张老师,那您觉得人们对《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关注程度怎样?
张:在我们哈尼寨子,大部分人都知道《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故事,但是周围汉族寨子里只有很少数人清楚,墨江县城里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不过,近几年墨江哈尼文化研究所很重视,每个月都领(带)着我们传承人进入社区、村组去进行表演、推广、传唱《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每次去,住在附近的人都会集中起来看表演,大多数还是很感兴趣的,可是真心想学的人不多。
杨:您刚刚提到,对于史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而言,传承者的年龄断层、所受关注度不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您认为想要突破当前的困境应该如何做?
张:最重要的还是加强传承人的培训,同时吸纳一些年轻人加入我们。到了我这个年纪,更多想法是把自己会的东西都教给年轻徒弟们,也把这种热爱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给他们,并且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是哈尼族碧约人不能断的根,只有记得这个根,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才能永远在。在它还不是国家级“非遗”的时候,白阿叔带着我们唱给知识分子听,主要也是为了把嘴上传的变成汉语写下来,就可以不担心失传啦。年轻的时候,白阿叔和我阿孃也时常说,要把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故事讲下去,不然有一天我们会没有根了。所以我一直去县城小学给学生娃娃上课,为的就是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哈尼族的英雄人物,培养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兴趣。
杨:我们了解到,近年来墨江县政府、墨江哈尼文化研究所对于史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以《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为蓝本改编的原生态歌舞剧,一经演出之后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点赞”。请问您去实地看过演出吗?对于这部原生态歌舞剧有什么观后感和建议呢?
张:歌舞剧《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是前几年墨江县旅游的宣传节目之一。刚开始排练时,县文化馆就邀请我去做了特别指导,不过很可惜,排演了几次之后因为文工团的演员太少,没有再进行现场表演,而是录成了视频。其实歌舞剧只选取了诗歌中一个比较经典的片段“挑山填火”,并不是全篇内容的呈现。该片段讲的是当时着了大火,英雄洛奇洛耶为了救周围受灾的人,就挑着两座大山去填火。他在里面多次说寨子里的人们都想过不受地主压迫的独立生活,等山火灭了,他们就去人烟稀少的地方重新建个寨子。这一段感染力很强,每次我唱的时候心里就像被火烧着一样,感动于他们的勇敢,也想用最美好的语言歌颂和赞美他们。
四、坚守:十余载专执一事的守望者
用一句话来概括张桂芬七十多年的从艺生涯:“始于兴趣,忠于使命。”她因儿时的兴趣与之结缘,却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成为叙事长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把传承与发展的责任扛在肩头10余载。促使她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除了兴趣与责任,还有长诗本身。作为目前为止哈尼族保存较完好的英雄叙事长诗之一,《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价值也一直在变迁与完善着,如同一口古老的井水,源源不断地迸发着新的生命力。
杨:作为史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您认为该诗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张:在哈尼族心里,《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就像我们的眼睛,在所有器官里,眼睛是最珍贵不过的了。它代表着一种勤劳、勇敢的精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宝藏,男娃娃要像洛奇洛耶一样勇敢无畏,女娃娃要像扎斯扎依一样勤劳美丽。每次参加“传承人培训”,新加入的新传承人最爱问我一个问题:“张老师,这首诗是不是用来纪念洛奇洛耶和扎斯扎依的?”我都会告诉他们,其实不需要说纪念不纪念,只是要把他们的英雄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听,让后代想起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时候,心里也会像被火烧着一样,即使遇到困难也不害怕啦。洛奇洛耶,他有英勇就义的精神,敢于和压迫斗争,带头抗租抗税。扎斯扎依则是哈尼族最美的女人,她不嫌洛奇洛耶不好看,眼睛像淘米盆,鼻子像装酒瓶,脚就又像中柱一样,都说是最漂亮的女人嫁给最丑的男人,还和他一起反抗坏人,是最漂亮、最勇敢的女英雄,值得我们自豪。
杨:当前,云南各地少数民族史诗的传承与保护也和哈尼史诗《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一样,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机遇和新挑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张:主要是现在能听能学的东西多了,年轻人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比较大,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选择单一,外界的干扰也少。所以目前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情节上需要创新,不能像过去那么木(刻板),本来它的情节就是很灵活的,只要故事的主干在,枝枝节节里面可以放的东西有很多,我们如果把故事更加生动地讲出来,就可以激发更多人的兴趣。另一点就是表演形式上我们也要创新,比如原生态歌舞剧、动画片等等,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就像之前我们的那个歌舞剧的视频很受欢迎,舞台花花绿绿的,有了好多年轻观众。最后,可以把书做成不同的版本,比如前两年我们就请画家把《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改成了连环画书,放在各个学校的阅览室面,好些被都学生娃娃翻旧啦,连我们寨里面的大人也买了看,说是很有趣。
杨:张老师,最后想问问您如何评价自己70年的从艺之路呢?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吗?对于新一代云南少数民族史诗传承人的培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或者说,您认为一个优秀的史诗传承人应该具有哪些品质?
张:这个问题我之前提到过一些(笑),还是爱好和坚持。首先要自己有兴趣,没有兴趣的话不愿意学。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懂少数民族语,像我们《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不用哈尼话唱出来就不正宗(标准)了,当然只有能听得懂内容,而且对这个故事感同身受,才会想学,我的好几个徒弟都是这样开始学的。然后是嗓子,《洛奇洛耶与扎依扎伊》用得最多的还是“腊达调”,但这个调子比较高,嗓音不好的人很难唱上去,有的人虽然记忆力很好、会讲故事,但嗓音条件不行慢慢就放弃啦。现在我年纪大了,自己唱的时候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有些音很高的地方唱起来力不从心。最后是要有时间和规划,有时间就有更多钻研和练习的机会,规划合理就学得快。
五、结 语
采访快结束时,张桂芬老师再次向我们表达了对《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传承问题的忧虑。由于身体的原因,老人家现在很难再唱“腊达调”那么高的调子了,但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听一段年轻传承人胡德温老师的演唱。胡老师是典型的哈尼族汉子,方脸圆眼、黝黑壮硕,笑起来很腼腆。他抱来牛腿琴,吊完嗓子之后唱了起来,先唱了《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的选段,又唱了两首哈尼古歌。与采访时的腼腆相比,弹起牛腿琴、唱起“腊达”调的胡老师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用浑厚、悠扬的歌声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古老民族充满风霜雨雪的历史中。此时,张老师一直含笑看着这位年轻的徒弟,口中跟着哼唱。这一幕,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他们是两代人的交替和延续,张老师正在竭尽全力地倾囊相授,而胡老师也如旭日一般慢慢升起,这就是师徒传承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哈尼叙事长诗《洛奇洛耶和扎斯扎依》才能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地延续和丰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