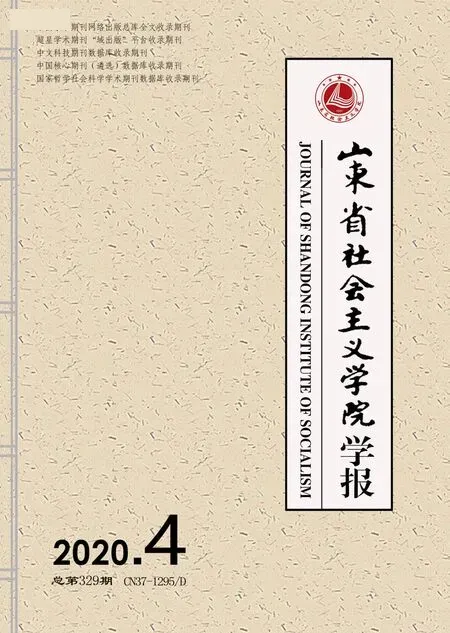文化塑造视域下中华传统道德教化的当代重构
沈小勇
当代中国,道德和价值建设特别需要从“教化”的视角来探究其社会实践问题。不同于一般的规范论和目的论,道德教化论主张把道德问题作为整体精神进行塑造和培育。“教化”是通过道德教育民众,塑造人心风俗,达成“化民成俗”的效果,道德教化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培育和文化塑造的过程。“以教化民”是建立在个体和社会交往互动基础之上,把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有效传递给社会个体,并由个体认同升华为普遍认同,最终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出来的过程。道德教化过程“在个人层面上即是心灵的涵养与精神的提升,是个体性向普遍性的提升,指向一种至高的善;在社会层面上,是对人之精神世界的整体建构,塑造和谐的精神共同体,指向一种社会的和谐。”[1]
一、中西方教化语境的比较
在西方,“教化”一词产生于中世纪的宗教神秘主义,与宗教相联系的“教化”概念当时主要指“人性”可以通过不断的精神转变达到“神性”的完满。自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性在西方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把人从专制和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走向对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的发现和张扬。启蒙运动对人性的倡导也使“教化”一词逐步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尔就强调教化是人通过自身精神培植达到人性完满,他把人性和谐看作人的最高精神成就,主张要进行“人性的崇高教化”。洪堡特也曾这样强调:“当我们讲到德语的‘教化’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同时还连带指某种更高级、更内在的现象,那就是‘情操’,它建立在对全部精神、道德追求的认识和感受的基础之上,并对情感和个性的形成产生和谐的影响。”[2]黑格尔将“教化”的概念推进到一个顶峰,甚至统一了他那个时代人们对“教化”概念的理解,黑格尔强调“教化”的要旨在于将人从个别状态提升到普遍性状态之中,他明确指出:“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3]黑格尔认为,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不断趋向普遍性,从而使人从特殊精神逐步过渡到普遍精神,从“所是的人”变成“应是的人”。在黑格尔看来,普遍性是教化概念的本质,一个人如果沉湎于个别性而看不到普遍性,就是没有受到教化。
不过,现代性自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酝酿了一场持久的关涉道德和教化的精神危机。近代社会的教化一般被看作是“启神性之蒙”,而现代社会的教化则往往被看成是“启社会性之蒙”,拒绝对真正人性的遮蔽,拒绝“伪教化”,“发现存在先于本质,确证个人不可让渡的独特性”[4]。在现代启蒙反思和道德重建中,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承续黑格尔、狄尔泰等人开启的“精神科学”之路,重启“教化”概念,把“教化”认定为精神科学的本质,一种精神的造就或陶冶,“教化”概念被赋予崇高的地位。伽达默尔的“教化”概念与黑格尔有所不同,他更强调历史性的含义,同时与“普遍性”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的教化哲学更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内在的“转变”,他强调教化的旨趣着重在通过持续不断的“谈话”而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而非“发现客观真理”。与启蒙理性的认知型模式不同,教化哲学更看重生命的实践性、整体性、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和把握事物的在场感。不难看出,在西方教化话语演进中,从传统的教化概念到解释学的教化概念,再到罗蒂的教化哲学的观念发展有其内在的根据。“消解传统哲学,使人们回到现实生活成为趋势”,不过尽管教化哲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展示了新的世界景象,“但由于它过分强调多样性、个别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它在理论上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之嫌,实践上则有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的可能”[5]。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教”与“化”意义略有不同。《礼记·经解》中就有“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的系统论述;在《周易·贲卦》中提到“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化”一词见《毛诗序》中“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论述,这里的“教化”有教养和化育的含义[6]。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在治国安民的重要作用,传统教化哲学更加强调知行合一的“成人”“成德”教育。其实不难看出,无论是中国传统还是西方话语,道德教化的共同之处都普遍强调“人性”的崇高教化,都普遍强调通过“教化”转变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可以说,中西方的教化话语都涉及“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但区别在于,在中国主要是“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7]的人伦传统,在西方则主要是城邦的善、共同的善、伦理精神、伦理实体等表述。与黑格尔追求“普遍性”本体的教化概念不同,与罗蒂“教化的哲学”所倡导的相对主义、非基础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教化概念在价值取向上更加突出个体性和整体性的融合,更加注重从“心灵秩序”到“社会秩序”的整体有机性。“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它要在人的实存之内在转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8]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建构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文教”系统,通过道德教化、礼乐教化等深深影响着传统社会治理。儒家文化重视以德为先、德礼并重,力图恢复百姓内在的生活根据,通过其特有的教化方式给予丰厚的文化滋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家国情怀。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宗教的世俗伦理文化,世俗化和伦理化是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但是作为“非宗教”的儒家文化却始终重视“德治教化”的社会功能,通过“文以化人”的教化实践,追求“化民成俗”和“以文化天下”的人文境界。按照钱穆先生的理解,中国文化整体上虽然缺少如基督教一样具有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但是却有一种入世的、人文的宗教特点。在儒家文化系统里,中国人追求的“天堂”是立足人间的理想社会、小康社会,中国人的“教堂”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教堂,现实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就是人们需要修炼的“大教堂”。与世界其他民族宗教信仰不同,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在精神底色上主张“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的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灵魂世界与肉体世界没有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如《中庸》所言乃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9]。这种“人文教”的特色与基督教文化区别很大。在中国,从来都是世俗文化主导宗教,而不是宗教主导世俗生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精神品格上也充分彰显了道德主体性和世俗伦理性,如主张追求君子人格,弘扬家国情怀,注重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强调人伦日用的秩序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中华传统德治文化的价值追求和人文传统。
二、重构道德建设的“中国现代性”
从文化塑造机理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建设,有利于深化对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把握伦理共同体的精神塑造维度。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必须满足当代公共生活的交往需要和担当现代复杂社会的道德使命。我们倡导“最美现象”,但我们反对“道德说教”。在我们看来,无论是“最美现象”的塑造还是核心价值大众化的探索,当下社会期盼一种真正有效的道德教化,要关注如何塑造共同体的精神空间,形成一种现代性的、民族性的伦理精神,不断引领现实的人走向一种崇高的善的生活。“教化论主张一种大道德观,不把道德问题只限制在遵守规范、追求成功和对现存道德观念体系的论证等上,而是把道德问题看作是整体精神的塑造、培养、陶冶、教化过程及其结果。”[10]从教化论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特别需要这样的教化精神,在个体层面涵养心灵和提升精神,在社会层面塑造和谐的精神共同体。
当然我们也看到,现代性社会以其祛魅性、个体性、多元化特质带来了价值神圣性的丧失、人伦共同体的失落、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合理传统资源被抛弃等问题。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11]如何回应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局以及如何有效培育社会核心价值成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关键议题。之所以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剖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恰恰不是因为回避现代性,而是要重新思考中西方教化哲学尤其是中国传统教化哲学的智慧,重构道德建设的中国现代性,真正发挥道德教化在价值培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重要作用。无论是拒绝现代性,还是改造现代性,现代性都没有走向终结,寻求一条走出困境的中国式道德教化之路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构建中国式的道德教化之路必须在学理上深入探究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的道德教化话语体系。当代中国,如何在传统教化话语与西方现代伦理话语之间,构建体现中国现代性的道德教化话语在理论上显得特别重要。传统道德蕴藏的价值本体和个体内化机制已经被击打得支离破碎,中国传统的教化哲学和教化方法等需要系统化梳理;现代西方伦理话语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话语又存在一定程度的时空隔阂,学术界不能再简单地讨论西方教化话语而忽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建设。基于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本土性、有效性考量,我们认为,必须重塑中国式道德教化的价值内涵,要力求进行规则伦理与德性伦理的本土融合和话语重塑,特别要激活中国传统教化智慧,探究传统道德教化的现代化,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塑造的秩序机理,以此构建当代中国道德教化的话语体系与实践价值。我们强调道德教化的中国式之路,是基于对传统教化概念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强调道德教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基于对道德教化的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期待。当代中国的道德教化话语建构要真正体现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融合融通,通俗言之,既要体现现代性、时代性,更要立足于当代中国本土,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体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真正实现在传承中创新,从而推动道德教化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探究中国式的道德教化是以教化应对道德困局、融合中西教化智慧、以现代性眼光继承创新中华民族的教化之路。
今天,通过比较中西方教化哲学,一方面是从“教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当代道德建设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凸显传统教化哲学的现实意义。今天的道德建设要探索德性基础上的、基于伦理传统的现代道德认同,要重构传统德性伦理和教化智慧,构筑当代道德共同体。我们通过社会教化拓宽社会文化心理空间不能脱离历史文化基础和社会实际,我国的社会道德教化既要走出道德理想主义、普遍理性主义,又不能陷于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当下中国社会期盼一种真正有效的文化塑造和道德治理,这种治理智慧扎根于中华大地和乡土传统,真正关注伦理共同体的精神空间,旨在形成一种重构中华传统“以礼为教”“化民成俗”教化智慧的民族性伦理精神,从而建构起现代性的中国式道德教化话语。
三、从话语建构到实践创新
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研究缺少中国元素,特别是缺少对“活着”的传统的考察和研究,还“没有弄清和有效借鉴传统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机理和传播机制”,“将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机结合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有关儒学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及其教化机理的研究、将儒学价值的当代转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结合的研究则更少见到”[12]。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方法来对“活着”的文化传统开展反思和研究非常必要,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大关键点。
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角度来看,重塑传统德治教化话语有一系列学理问题需要我们去回应和思考。比如,现代性视域下,当代中国道德教化的基本价值理念如何传承和构建?当代中国道德教化在价值层面如何体现现代性、本土性和有效性要求?中国传统教化思路为何在现代社会“中断”了?当代中国道德教化又面临哪些现实困境?如何通过重塑教化精神来回应这些道德困境?再比如,我们要接续什么样的教化传统?如何在哲学层面认识当代中国道德教化的定位问题?超越道德教化困境的基本路径是什么?中国传统德性伦理资源尤其是传统教化智慧如何重新解读?作为规则和美德有机统一的儒家教化伦理如何与当代中国道德教化对话、融合?又比如,当代中国道德教化模式如何在实践层面进行重构和深化?当代中国社会“教化”的真正动力和出场主体如何构建?如何践行核心价值观以形成现代性、民族性的中国精神?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追问,道德教化的现代话语建构不仅有哲学层面的必要,也是本土道德文化资源当代激活和价值转化的需要;既有“话语建构”维度的需要,也有“实践创新”维度的需要;不仅涉及价值内涵问题、现实困境问题,还涉及文化定位问题、传统重构问题、实践路径问题等。中国式道德教化中“中国式”内涵主要体现在深入探究中华传统德性伦理和教化智慧,挖掘中华传统治理之道,其“当代性”主要体现在要赋予其现代性价值意蕴,以现代的视角深入研究传统德治文化的当代境遇以及与当代对话的可能,用现代的眼光审视传统道德教化智慧,从而力求活化传统的文化塑造与文化治理思想。中国传统德治教化智慧彰显的是国家治理的文化塑造特质,探究传统道德教化的现代化,需要系统剖析文化塑造的内在机理,并上升为中国式的当代道德教化之道,建构道德教化的现代之路。
从实践创新角度来看,不仅要深化对当前社会道德治理、价值观建设特别是核心价值大众化的规律性认识,还要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提供更多的中华传统智慧和现代化转型路径。一方面系统认识中华“文教”体系的形成特色,把握中华德治教化智慧资源;另一方面力求在中西方秩序建构的异同比较中,在法治文化建设的背景下,重新解读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价值内涵,并力求从治国理政的中华智慧和东方治理品格中深入理解传统德治教化的人文精神。如,传统伦理功能的机理问题,礼法文化资源的转化问题以及传统社会教化的方法论启示问题等。同时,还要系统提出中华传统德治模式如何与当代对话,如何在实践层面进行重构和深化,如何从实践层面系统提出中华德治教化智慧的转化路径和实践创新等。
总之,立足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中国传统德性伦理资源,积极重构中国传统的德性教化智慧,是基于文化自信哲学主体立场的自觉考量。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之间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关联,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挖掘传统德治文化资源,塑造治国理政的东方治理品格意义重大。我国文化建设应进一步准确把握文化治理之道,重点探究文化塑造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建构和道德实践问题,构建中国式的道德教化当代话语。核心价值观的当代建构体现中国元素、中国精神和中国传统,应避免道德说教,体现道德温情,融入“文脉”和“血脉”。以传统创造性转化的视角,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需要,系统研究传统德治智慧的传承与重构问题,系统剖析文化塑造视域下当代中国道德教化话语的传承与重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