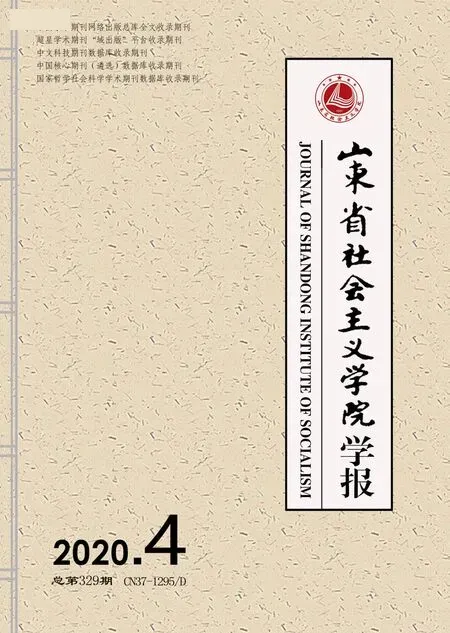加强“五观”教育 提高宗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主动性自觉性
冯永昌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标志着“坚持中国化方向”已经成为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指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宗教工作成功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也是新时代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我国宗教自觉服从服务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战略。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并主动融入和推动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于团结和引领信教群众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宗教中国化首要的问题在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宗教界人士的主动性自觉性。为了解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本文选取了山东12个地市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部分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对于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中国化还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存在抵触情绪,不知道为什么要中国化、怎么样中国化。因此有必要加强宣传教育,帮助宗教界树立“五观”——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国家观、法治观,提高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主动性自觉性。
一、加强全程历史教育,树立全面客观的历史观
中国各宗教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历史上都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全面了解各个宗教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有助于我们树立客观的宗教历史观。
(一)客观了解评价本宗教发展史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上层建筑之一,这就决定了宗教史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历史。了解宗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宗教界人士客观评价各个宗教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理解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确定位宗教。
调研发现,很多信教群众对本宗教的历史知之甚少、语焉不详,主要原因在于平时的宗教活动只注重对经典、教义、礼仪的学习,很少学习宗教史,或者以经过神化的历史代替信史。对本宗教的传播,只讲和平发展的一面,不讲借助武力强迫的一面。如,对于中世纪的历史,只讲世俗政权对神权的臣服,神权如何至高无上,不讲异端裁判所对科学的迫害和扼杀。
现阶段各宗教对于本宗教的历史往往采取神化、美化的方式加以宣传,对负面的历史事件选择性忽略,有选择地强调神圣性、忽视世俗性。导致宗教信众对所信仰宗教了解不全面,不能正确评价宗教社会作用两重性,甚至认为其他宗教都有不光彩的历史,只有本宗教是完美的。要开展全面的宗教历史教育,引导信教群众全过程认识本宗教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对用非和平手段传播、维护宗教信仰的历史时期要有正确的认识。
(二)客观了解评价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史
各宗教在中国发展、传播的历史实际上是同中国社会、文化不断适应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比如,佛教自两汉之际、公元前后传入中国,既有成功融入本土文化的经验,也有“三武一宗灭佛”的冲突;既有禅宗等推动宗教中国化的行为,也有白莲教等利用教义冲击政权的行为。道教既有与佛教和平相处、相得益彰的阶段,也有相互竞争、竞辩先后的历史。伊斯兰教既有以儒诠经、会通儒学主动中国化的进程,也有新中国成立后门宦制度的不适。基督宗教的传播几经波折带来了西方科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地位的沉浮。
历史是一脉相承、紧密联系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5所高校的调研中,我们就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不了解近代史上宗教在侵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不了解青岛开埠过程中的宗教因素,导致无法全面理解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反对在宗教史教育中只讲现在、不讲历史,只讲片段、不讲全程,只讲经验、不讲教训的倾向,要树立全面客观的历史观。
二、加强中华文化浸润,坚定自信包容的文化观
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根本标准是思想、教义上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中华文化浸润、与本土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反思文化自卑、反对文化自傲。
(一)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领跑位置,中华文明的成果不仅哺育教化了一代代中国人,还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我们不仅有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产生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中华文化是富有生命力的伟大文化,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受尽欺凌的历史,但并不是文明落后的历史。我们有些宗教信众片面地把外来宗教等同于西方文化、先进文化,认为从发达国家传来的宗教就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象征,从而产生对宗教文化的自傲和中华文化的自卑,甚至产生一种歧视链,即认为信仰西方宗教的可以轻视信仰本土宗教的,信仰宗教的在道德上优于不信仰宗教的。针对这一现象,首先,要让群众了解西方宗教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一定程度上是去宗教化的历程,比如西方文艺复兴的过程其实就是摆脱神权统治的过程。其次,要让群众了解西方文化也不能等同于先进文化。西方近现代的领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坚持文明互鉴,促进各种文化平等交流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要引导各宗教之间平等交流对话、与本土文化相互借鉴吸收。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从冲突到融合,从借助玄学的“格义”到中国化理解的“得意”,从具备中国特点的“师说蜂起”到中国化佛教形成的“宗派林立”,都离不开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互鉴。宋明以降,儒释道三教合流,中国化佛教又反哺了本土文化,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中华文化格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是与中国本土文化适应融合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是在组织形式上本土化的过程,如“开学阿訇必自外方延请,不许扶立长教致令把持”的阿訇聘请制度就避免了世袭制带来的弊端。
宗教中国化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是基督宗教,与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时中国发展居于领先地位不同,基督宗教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造成了基督教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假象。纵观世界上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其实不少国家仍然处于发展中甚至是欠发达状态,说明基督教文化与生产力发展缺乏正相关,没有必然联系,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三、加强核心价值引领,培养和谐向上的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是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根本要求,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至关重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阶段全国人民对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的表述,包含了各族人民对于价值标准的判断和追求,也涵盖了各宗教文化最核心的价值标准,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导力。当前,部分信教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还不够深刻,认为宗教本身就是教人向善,在行事为人方面比一般人要求更严,甚至认为宗教教规完全可以替代甚至高于核心价值观要求。有的群众就讲,“你们说的那些,跟圣经讲的一样,圣经上都有了”,所以认为宗教场所“四进”活动没有必要或存在抵触情绪。这里的误区就是颠倒了主次关系,没有认识到是核心价值观统摄了包括各宗教文化在内的各种价值标准,而不是相反。没有看到,虽然宗教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一定程度上与核心价值观契合,但是并不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更不能用宗教价值代替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中华民族一分子,宗教界人士也应当有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担当,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与祖国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社会层面,要发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积极融入社会、服务人群,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在公民层面,要遵纪守法,提升法律意识、公民意识,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因此,在信教群众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增强群众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和个人担当。
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至上的国家观
“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3],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深入理解这一科学论断,是我们正确把握和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思想前提。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大国博弈更多表现为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软实力的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就已经明确界定中国是“竞争者”,由于竞争性因素的存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快对民族宗教等领域的渗透,持续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实质已经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但是,部分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没有看到宗教背后的国际竞争因素,以至于在“爱国爱教”的问题上出现根本性错误,认为爱国爱教是道选择题,可以先“爱教”后“爱国”,先是一个“教民”后是一个“公民”,把教规置于国法之上。一方面享受国家的普惠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境外组织的小恩小惠来者不拒,认为自己占了便宜,不了解东欧剧变中天主教等宗教组织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没有意识到宗教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宗教背后隐含着的激烈国际竞争。“最关键的是教育群众”,所以一定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群众树立起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国家观、利益观。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4],脱离了具体国家制度的完全抽象的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就是爱社会主义中国。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要引导群众学习党史、国史、新中国史,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救亡图存之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认识到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必须长期坚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理论体系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必须长期坚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伟大创造,必须长期坚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认识到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和灵魂,必须长期坚持。引导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守护好、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
五、加强全民守法宣传,明确政教和谐的法治观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在宗教领域的体现,也是政教关系和谐的法治保障。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使信教群众了解政教关系是宗教关系和谐的关键,只有全民守法才能维护政教关系和谐,为宗教有序健康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我们一方面致力于保护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用法律调节与社会相关的宗教涉俗事务。部分信教群众错误理解了中央政策,把“宗教信仰自由”简化为所谓的“宗教自由”,追求不受法律约束的“完全自由”,个别宗教工作干部也把“宗教信仰自由”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对立起来,以至于在宗教工作中“一放了之”。在处理基督教临时聚会点审批等问题上,出现了把关不严等问题。还有的干部一味强调宗教的特殊性,认为宗教问题敏感复杂,不敢管不想管不会管,导致在宗教领域出现了“法外之教”“法外之地”“法外之人”,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环境。因此,要加强宗教法治化宣传教育。
首先,要让群众了解宗教事务也是社会公共事务,必须接受法律管理。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宗教具有特殊复杂性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宗教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这个“特殊”强调的是重要性而不是个别性,更不是例外性。宗教事务作为影响社会影响他人的社会公共事务,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的一般性特征,要按照公共事务的规律进行法治化管理。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基础上树立全民守法的法治观念,树立起“没有法外之教、没有法外之地、没有法外之人”守法观念。
其次,要让群众了解法治是宗教有序健康发展的保障。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的公共生活都要依法而治,即依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来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法治提供的是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这种确定性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纵观中国政教关系发展的历史,既有某种宗教获得帝王青睐支持而超常规发展的例子,也有失去政权支持一落千丈甚至走向衰亡的情况,这说明把宗教的健康发展全都寄望于人治是不可靠的,只有法治才能提供具有确定性的制度保障。此外,还要让信教群众了解“三武一宗法难”等大规模政教冲突的原因都在于宗教的无序发展危及了政权的生存,只有政府和宗教组织都强化法治思维、尊重法治,才能维护政教关系的和谐。
再次,向群众介绍世界各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情况,消除对西方国家所谓宗教“完全自由”的误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对宗教的治理方式基本上都倾向于依法治理,其中有一部分国家采取了对宗教事务单独立法进行规范,大部分国家未单独立法,而是采用管理一般公共事务的方式进行治理。比如,部分传统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墨西哥、秘鲁等国家在宗教世俗化后,通过宗教立法确立政教关系;美国等国家则是运用一般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社会关系。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对宗教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更不存在所谓的“宗教自由”。
外来宗教中国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关键不在于建筑、服饰、装饰、仪式等外在形式的本土化,而在于教义思想的本土化。如何使外来宗教尤其是强势文化适应中国国情,主动推进中国化进程,人是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加强“五观”教育,引导使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树立起正确全面的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国家观、法治观,可以提高宗教界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主动性自觉性,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加包容的态度面对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