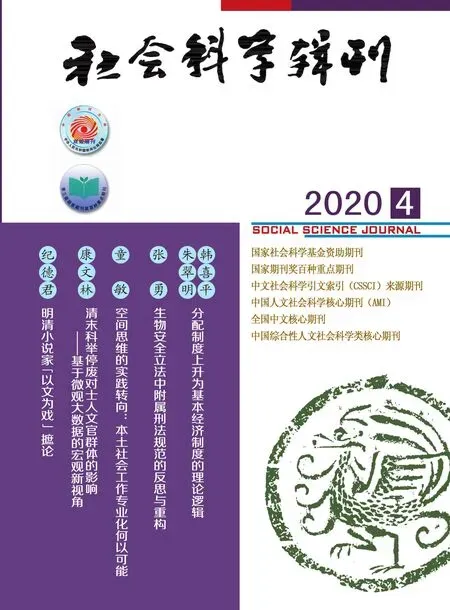《金瓶梅词话》叙事建构的文艺渊源刍议
——以取径武松打虎故事的属性为中心
徐大军
《金瓶梅词话》(下文简称 《词话》)是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章回小说的新篇章,这既指它的叙事成就,也指它的成书属性,比如韩南说它是 “一个人想象出来的产品”①韩南《中国小说的里程碑》指出:“与早先的小说相比,它当然有一种显然的不同之处——写作方式的不同。别的长篇小说都属于传统的章回体故事,有些小说至少是先前书面作品的改写本,而《金瓶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人想象出来的产品。”见包振南等编选:《〈金瓶梅〉及其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页。,商伟在《复式小说的构成:从 〈水浒传〉到 〈金瓶梅词话〉》中说它是 “一部面目全新的章回小说”。确实,《词话》讲述了一个全新的西门庆故事。但是,这个新故事却架设在旧有的武松杀嫂的故事框架上。这部新小说,以民众烂熟的武松打虎故事开篇,且此后的10回在情节框架、文字表述、主要人物等方面皆有明显移植 《水浒传》的现象。②《金瓶梅词话》中的武松打虎、遇兄、杀嫂一系列情节,普遍的说法是来自于今本《水浒传》,黄霖、王利器认为它所依据的版本是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本。参见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第1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32页;王利器:《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0页。但也可能是来自《水浒传》的早期版本,或者此前流传的其他作品中的武松故事,参见侯会:《〈水浒〉源流新证》,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词话》使用了水浒故事的材料,说明它与 《水浒传》的关系,但如何使用这些材料,则与文学经验、文学传统有关,其中包括前人对于水浒故事的重述经验,以及处理现成文艺材料的叙事传统;它们对于后生文艺来说,既存在着启发作用,也存在着限制作用。
那么,对于西门庆故事这个新篇章来说,武松打虎故事这个旧篇章的存在说明了什么?对于《词话》这部新作品来说,《水浒传》的存在又说明了什么?我们即以 《词话》取径武松打虎故事的属性为中心,来谈一谈它叙事建构的文艺渊源问题,来看一看它所面对的文学经验、叙事传统是怎样影响它的叙事建构和文本形态的,以及它于其间寻求突破的努力和成就。
一、武松打虎故事在 《词话》中的作用
《词话》取径武松打虎故事的属性,依立足点的不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对于 《词话》的主体故事来讲,说明了什么?二是对于 《词话》这部小说来说,说明了什么?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词话》第1回在解释了开篇词中所说的 “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之后,有这么一段话: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衒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1〕
兰陵笑笑生开篇讲的这段话,宣示了 《词话》这部小说的三个重要信息:一是题材属性——一个风情故事,二是主要人物——一个好色的妇女和破落户 (皆未具姓名),三是故事地点——东平府清河县。但接下来,作者并未让他说的这两个主要人物登场,而是开始讲述武松登上景阳冈打虎,然后被猎户们带下山。根据此处有大段文字与今本 《水浒传》相同,可推知这段情节叙述袭自 《水浒传》;但 《词话》与 《水浒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武松下山来到的不是阳谷县城,而是清河县城。
接下来,《词话》叙述武松在清河县城经历的游街遇兄、为兄报仇、发配孟州等情节 (中间有潘金莲的戏叔、私西门庆、杀夫等情节),仍是移植了 《水浒传》的武松故事。只是武松向西门庆寻仇时,并不似他在 《水浒传》中那样斗争经验丰富,而是误杀了李外传,致使西门庆侥幸脱身。更为重要的不同是,当武松仍像 《水浒传》那样被发配孟州时,《词话》的叙述人并没有像 《水浒传》那样追随着武松的脚步而远走孟州,行走江湖,而是留在了清河县城,开始讲述一个完全没有武松的清河市井中的风情故事。由于不用追随武松这个江湖好汉的大步纵横,这个讲述人也就从容悠闲了许多,他漫步于清河县城的大街小巷,就像张竹坡说的那样,“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2〕。
站在武松因发配孟州而离开清河这个叙事节点上往回看,我们会发现,如果单独看武松打虎至发配这段情节,清河县城一直存在着武松活动的身影,那么,即使这段情节有一些改造、增益,如第7回西门庆迎娶孟玉楼,也仍属于武松故事的框架内的变动或填充。但是,如果联系到武松因发配而彻底离开清河之后,西门庆家庭内的妻妾们、家庭外的帮闲们马上簇拥着登场亮相,这个清河县城才正式开始上演一个没有江湖英雄的市井社会的风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时候,作为小说主体故事的西门庆故事的框架才算真正摆出来。所以,在 《词话》中,武松来到又离开的这个清河县城,并不是为了表现武松行走江湖、展示英雄气概的场地,而是为了表现西门庆及其家庭内外市井百态而搭建的舞台,相应的人物行动、事件演进,都是为了引出、布置这个舞台的手段和工具。因此,由武松打虎领起的这段故事就是一个叙事策略上的结构设置,作者即由此引入到自己新创的西门庆故事,也就是他在开篇就标明的那个风情故事,它有自己的人物体系、故事体系和主题立意,展示了西门府内外的社会世情。
当然,武松打虎领起的这个让主体故事登场的引入部分,对于 《水浒传》有情节上的移植和文字上的抄录。但以此为基础,我们不应只看到《词话》移植、抄引 《水浒传》的踪迹,还应看到它为了自己的叙事建构目的,在借用这段原本充满着江湖豪情的情节时进行的那些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造;有些改造甚至可称为挑丝抽线的筋脉缝合,在粗放的移植中蕴含着作者精致细腻的心思和创意。比如对武松打虎下山到发配孟州这段情节中的节令时间的改造:一是改动了故事演进的时间,把潘金莲挑帘到武松出差返家安排在三月阳春到八月中秋;二是改动节令时间编排的思路,把节令的文化含义与人物的行为、情绪相配合,如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初遇是在阳春三月,武松得知兄长死亡的消息是在中秋佳节前;三是运用了节令意象的蕴含,把武松自京城返家、后被发配远方的时间设置为八月中秋,以这一蕴含着团圆之义的节令意象来衬托武松的相关行为和情绪。这正体现了小说作者在节令时间安排上的精细之思。①这种节令景象与故事进程、人物情绪的配合关系是《金瓶梅词话》通篇使用的表现手法,浦安迪即注意到了这部小说在主要情节展开的三四年内“对一年四季时令转换的巧妙处理”,以及“西门庆家运盛衰的时刻与季节循环中冷热变化常常是配合一致的”(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65、66页)。这种季节变化的冷热转换、节令意象与人物处境的冷热配合,正照应了张竹坡所谓《金瓶梅》是一部“炎凉书”的蕴含。
与这种时间序列上有意识的改造和文化意象上有目的的设置相适配,《词话》对于 《水浒传》武松故事的借用和改造,也显示出了特意的考虑,其目的是为了推出它在第1回开篇所说的那个风情故事。为此,作者做了三个方面的改造。
一是在场境方面,武松打虎下山来到了清河县城,即把叙述人的眼睛引到清河县城的市井社会,并驻留于此,悠闲而透彻地为我们描述了那侥幸躲过武松复仇钢刀的西门庆、潘金莲的市井生活,而没有像 《水浒传》那样追随着武松因发配而远去的身影,继续为我们展示那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江湖英雄的世界。因此,《词话》中武松因打虎下山而遇兄、寻仇、发配的这段清河县城的奇闻异事,已不是为了刻画武松而开演的英雄世界的江湖之事,而是英雄武松在行走江湖的过程中驻足市井、脚步轻点的一圈涟漪。对于清河这个小县城来说,英雄武松的到来只是一个变奏,随着武松发配孟州而远去的脚步,英雄传奇小说所喜好的江湖气味也被全部带走了,清河县城于是只弥漫着属于西门庆、潘金莲的市井生活气息。
二是在人物方面,武松打虎下山来到清河县城,引出了以市井人物代表西门庆、潘金莲构建起的西门府内外的人物体系。武松打虎情节领起的这段故事,包含了以下情节:始于武松打虎、遇兄,中经潘金莲戏叔、私西门庆、杀夫,最终武松寻仇杀人而发配孟州。在 《水浒传》中,这段故事的所有设置,都是为了展现武松的侠义形象。而在 《词话》中,以上的情节框架全部存在,但最根本的区别是这些情节存在的意图并不是为了叙写武松故事,而是为了引出它的西门庆故事。张竹坡曾谈到了笑笑生的这一叙事策略:“《金瓶》内之西门,不是 《水浒》之西门。且将半日叙金莲之笔,武大、武二之笔,皆放入客位内,依旧现出西门庆是正经香火,不是 《水浒》中为武松写出金莲,为金莲写出西门。却明明是为西门方写金莲,为金莲方写武松。” 〔3〕张竹坡此论即是着眼于 《词话》中引入情节部分与主体故事在叙述策略、叙述结构上的关系。
三是在故事方面,作者以这个人物体系为基础构建起一个不属于江湖好汉的市井社会的故事。《词话》即以西门庆、潘金莲为主人公呈现出新的故事系统、新的人物体系。这是一个有别于 《水浒传》题材性质的新创故事,它的主人公不是水浒英雄,而是市井人物;由此也决定了这个故事不是一个江湖世界的英雄传奇,而是一个市井社会的风情故事。这正是作者在小说开篇即明确宣示的故事属性。
据此,我们可以领会作者对于武松打虎情节领起的这段引入情节部分的设置,并不是随意的借用和改动,而是有着小说叙事结构、叙事策略上的通篇考虑的。对于社会盛传、民众熟知的武松打虎故事来说,《词话》的西门庆故事并不是“接着说”,而是 “借着说”。如果是 “接着说”的思路,《词话》就会沿着前代各版本武松故事的方向和框架来展现自己的故事,如此则西门庆故事就是由武松打虎、遇兄、杀嫂故事演化而来,延续着相同的主题、格调、趣味等。如果是 “借着说”的思路,《词话》就会按着自己构想的方向和框架来展现自己的故事,如此 《词话》就会在自己的构思方向上驱使材料,在自己的故事框架中熔铸材料。作者在使用 《水浒传》武松打虎情节时注入的那些新质,决不是想编写一个新的“武松传”,而是意欲按照自己构想的方向和框架来利用武松故事,来使用前代文艺材料的。如果没有自己构想的方向和框架,即使如沈璟 《义侠记》那样也对武松打虎、杀嫂故事作了类似 《词话》的改造①沈璟《义侠记》叙写了武松打虎到投奔梁山的过程,共36出,分上下两卷。上卷18出演述了武松之打虎、遇兄、杀嫂、发配这段情节,对《水浒传》原有情节进行了适当的变动,注入了自己的创造,主要有:一是依循传奇生旦离合体制而增设了武松未婚妻贾氏一线,以及因为作者思想表达的需要而增添的吴下贤人叶子昼情节;二是在整体上改变了故事演进的时间序列,有序地把武松打虎、杀嫂等事件安排在从暮春到深秋的季节变换中,并让这一节令轮换的景象有效地配合、烘托着人物的行动和情绪。参见傅惜华编《水浒戏曲集(二)》校订的明万历年间继志斋刻本。,也仍是行走在 《水浒传》的方向上,徘徊在 《水浒传》的框架内。
所以,同样要讲述武松打虎下山来到一个县城之后的故事,《水浒传》让叙述人的眼睛关注于武松行走的身影,而 《词话》却使得叙述人眼睛凝视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他按照作者的旨意,追寻着西门庆的身影,引导出来一个以西门庆故事面目出现的风情故事。而对于作为 《词话》主体故事的西门庆故事来说,武松打虎领起的那些叙事建构则是作者特意安排的一个让主体故事登场的引入情节部分,他意欲由武松引出潘金莲、由潘金莲引出西门庆,为此作者对 《水浒传》武松打虎情节作了上述那些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这些改造都是为了把叙事之眼引向清河县城这个市井社会以及在此发生的充满欲望和挣扎的西门庆故事。而 《词话》对武松打虎的行程方向和行程路线的那些改变,也提示了这部小说所要走的不同于水浒系列武松故事的路线和方向:不是写一个江湖世界的英雄传奇,而是写一个市井社会的风情故事。
二、《词话》为何要使用楔子类引入情节
《词话》取径武松打虎故事作为引入情节来领起和导出小说的主体故事,而且还对移植过来的《水浒传》武松故事情节进行了合目的性的改造。尽管如此,《词话》在文字、情节、人物上还是表现出了对 《水浒传》的明显抄录,故而后人有附骥 《水浒》之评、《水浒》外典之称。②“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金瓶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52页。有人还对《词话》的这种做法感到不解,因为根据小说主体故事的编创成就,作者完全有能力自构开篇、整体原创,为何要如此依托现有的熟知故事呢?而且作者在小说开篇就明确强调要写一个风情故事,那么又何必花费近10回的篇幅来重复一个武松打虎领起的烂熟故事,用它来作为主体故事的引入部分呢?正是基于这些疑惑,崇祯本的改订方案开篇即直接让主要人物西门庆领着众兄弟登场,而武松打虎一事只在他们的谈话中一语带过,武松游街一事只是作为他们眼中的场景得以展示,如此设置就开门见山地端出了小说的主体正篇——西门庆故事。崇祯本这样做,体现了它的改订者对词话本以武松打虎情节领起引入部分以推出主体故事的做法的一种理解,这与他删削大量与情节无关的诗词曲赋、修改那些粗劣不对仗的回目一样,是希望能使得小说的叙事建构更为清晰利落,文字叙述更为顺畅简洁。但崇祯本这样的改造,乃是后人对于小说叙事建构的认识,而不是笑笑生的叙事构想,也破坏甚至抹掉了词话本的叙事建构所负载的相关信息。
《词话》的叙事建构,自有其得以生成的时空维度,它的独创性和模式化都要依赖于这个时空维度的文学传统、文学经验。作者对于他的 “风情故事”的构想,肯定受启发同时也受限制于他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但若考虑将这个构想呈现出来,则要受启发同时也受限制于当时已有的叙事经验、文学传统的影响,这包括前代叙事文艺承续下来的体例、规范、格式、套路等。比如,《词话》每一回都以诗词韵文开篇,正文中随处可见 “看官听说”“话说”这类说书人语气的套语,以及写人绘景时使用的大段韵文曲词,都是沿袭自宋元以来白话小说叙事建构的通用体例,而更为深隐的脉络则是宋元以来民间叙事传统一线的文学经验。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崇祯本在改订词话本情节、结构、文字的同时,还删掉了小说题名中的“词话”二字。而对于兰陵笑笑生在小说题名中特别使用的 “词话”二字,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表示它的成书过程中有过一个 “词话”讲唱的阶段,后来被加工成书面的小说作品。但 《金瓶梅词话》的叙述形态并没有 “词话”伎艺那样的韵语讲唱格式①“词话”这个说唱伎艺与敦煌遗书所说的词文、宋代的陶真、涯词这些说唱伎艺渊源相承,关汉卿《救风尘》杂剧有“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明刊说唱词话16种是以唱词为主,都说明它是以唱为主的说唱艺术。而据现存16种明刊词话,可知元明词话之“词”实因“唱词”而起,唱词以七言韵文为普遍形式,间有少量十言韵文,故词话当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的说唱艺术形式。参见李时人:《“词话”新证》,《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并且至今仍无文献证明在 《词话》成书之前存在过这个故事内容的口头讲唱形态。其实,对于这部小说题名中使用的 “词话”二字,更适当的含义应是指它的编写沿袭了 “词话”二字所指向的民间叙事传统,这包括运用现成文艺材料的思路和方式,以及建构故事叙述的套路和结构,而不仅仅指它的叙述形态中采用了那些来自民间讲唱艺术的情节内容和时兴的散曲俗唱材料,也不是意指它是一部 “词话体”的小说作品。
依循这个民间叙事传统,我们就会对 《词话》叙述形态中那些芜杂的韵语曲唱内容有另外的认识和理解。《词话》中存在的那些与小说情境不合的韵语曲唱内容,大致有以下两类:一是频繁插引现成的韵语曲唱材料,包括戏曲、散曲、讲唱艺术 〔4〕,尤其是明代时兴的剧曲和散曲;二是人物话语采用戏曲格式的韵语曲唱,这又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人物对话使用曲唱格式,即以曲代言,甚至要标明曲牌,另一种是戏曲丑角自报家门式的自贬品格、自暴劣行的人物自我介绍,比如第61回赵太医受邀为李瓶儿诊病而上场时那段自我介绍的韵白。
站在书面作品编创和阅读的立场,那些游离于情节之外的无节制的大段抄引,那些与小说整体叙述格式、格调不统一的以曲代言,显得琐碎、累赘,对叙事的顺畅、清晰造成了干扰,也造成了书面阅读上的剥离感、阻塞感,甚至有观点认为 《词话》是由主体故事情节和一些无情节意义的小说佐料组成的混合体。
但是站在说唱伎艺表演和观看的立场,这是吸引听众、活跃气氛的惯用手法、必备手段。对于说唱艺人来说,熟悉讲唱的程式格套、掌握大量的韵语曲词材料是其必备的艺能。口头说唱表演之际,艺人们会根据故事情境,随意取用,捏合成章,而不会当场进行合乎故事情境的文字剪裁、内容照应。而且,在讲听的情境中,艺人们为了渲染现场的气氛,调节讲唱的节奏,会不时地插引大量的韵语曲唱内容,会经常穿插大段的科诨调笑情节,这是戏曲、说唱伎艺娱乐听众、活跃气氛的一种惯用手法。《词话》所表现的那种杂取现成文艺材料以建构叙事,那种不避格式格调不合而使用韵语曲唱以表情达意,那种随时使用插科打诨的戏谑情节来调节叙事节奏、活跃叙事气氛的做法,正与这些民间叙事传统一路的表述手段精神相通。
当然,《词话》沿袭民间叙事传统的表现并不只有这些,还有一些更能体现其叙事策略的手法,比如设置主体故事的引入情节。在民间叙事传统这条线上,《词话》取径武松打虎情节来设置主体故事的引入部分,这一叙事建构的思路和方式也有其文艺渊源。
元明话本小说在叙述策略、叙述结构上有一个习惯做法,就是安排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情节来引入主体故事,既能吸引阅读者的兴趣,也能表明其故事渊源有自。比如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刊刻的 《三国志平话》,它的叙述形态并非如后世嘉靖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氏评改本《三国演义》那样以主要人物刘、关、张登场桃园结义开始,而是以司马仲相阴司断狱故事开篇:上天判韩信、彭越、英布三人转生以报被刘邦、吕后屈杀之冤,来照应主体故事中曹、刘、孙三分汉室天下的局面。
玉皇敕道: “与仲相记,汉高祖负其功臣,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曹操占得天时,囚其献帝,杀伏皇后报仇。江东孙权占得地利,十山九水。蜀川刘备占得人和。……” 〔5〕
平话在这段阴司断狱故事之后,便是对黄巾叛乱、桃园结义的叙述。对于 《三国志平话》的主体故事来说,这段司马仲相阴司断狱故事既引出了魏、蜀、吴三国争战之事的前世纠葛,也点明了曹操、刘备、孙权的身份前缘,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神谕故事。从叙述结构上看,这个引入情节与说话伎艺、话本小说的入话头回故事相类。但从与主体故事的内容关联来看,这个引入情节并不是话本小说的头回故事,因为头回故事虽在内容上“正面或反面映衬正话,以甲事引出乙事,作为对照” 〔6〕,但它所讲述的人物与正话虽有相类之处,却无亲缘关系。比如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头回故事是孟浩然因写诗触犯了皇帝而终身禁考科举,由此引出正话故事柳永因填词而沉抑下僚,终被罢职,致使他纵情酒色。小说是把两个怀才不遇的诗人放在一起,用头回故事以作为正话的叙述启动和人物映衬。而 《三国志平话》这个神谕故事中的人物却与主体故事中的人物有着亲缘关系,它指明了曹操、刘备、孙权的身份与功业是来自天国的授予,三人与汉家王朝的纠葛是来自前世的恩怨。这种引入情节的设置,体现了天人感应、因果报应的观念。
这种在叙述结构中设置神谕故事作为引入情节的做法,也是明清章回小说惯用的叙事策略,《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都安排有此类引入情节,以表明主体故事的人事前缘和因果报应。比如与 《词话》最为亲缘的 《水浒传》即以 “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情节,来照应主体故事中水浒一百单八条好汉的作乱。对于 《水浒传》所设置的 “洪太尉误走妖魔”情节,金圣叹批改本即对它所体现的叙事策略作了明确的揭示和标举。在 《水浒传》简、繁诸本中,一般是以 “引首”和第1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作为小说主体故事的导引部分,而从第2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才开始转入到主体故事的叙述,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即如此。而金圣叹在批改时则把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标为第1回,而把此前通行本的 “引首”和第1回予以合并,冠以“楔子”标识,并由此而引出主体故事的叙述。金圣叹在小说情节结构上的这一改动乃是看到了通行本第1回并不是小说的主体故事,而是主体故事的引入部分,并且它在情节结构和内容关联上不同于话本小说的入话头回功能,而类同于金元杂剧的楔子功能。
楔子体制来源于金元杂剧。元人杂剧的演述体制多在四折之外另加一个楔子,楔子或居一剧之首,或处两折之间,而以居剧首者为多。处折间者在杂剧演述结构中起到过渡作用,而居剧首者在演述结构中具有引入正场的功能,在情节结构中则有铺垫故事前奏、交代人物前缘的作用。比如元杂剧现存的6种水浒戏 (据傅惜华 《元人杂剧全目》,现知元人水浒戏有23种),有的标明楔子 (李文蔚 《燕青博鱼》、李致远 《还牢末》、无名氏 《三虎下山》),有的未标明楔子 (高文秀《双献功》、康进之 《李逵负荆》、无名氏 《黄花峪》),但无论有无标明,都有一个楔子类情节,即宋江上场自报家门,讲说一段内容基本相同的开篇词,叙及宋江上梁山落草的原因以及梁山队伍的规模,然后即以各种理由让一个或几个水浒英雄下梁山,由此引入到正场故事的演述。比如李文蔚 《燕青博鱼》的楔子部分,宋江在上场自报家门之后,责问燕青延误一个月假限的原因,并按律脊杖六十,燕青因此 “感了一口气,内瘴气坏了眼”,宋江即让他下山寻医治疗眼疾,于是燕青下梁山来到了汴梁城,遇到了燕大、燕二,杂剧正场便展开了燕大之妻王腊梅与杨衙内私通,并陷害燕大的故事。
这种剧首楔子与正场故事间所表现的结构意义和内容关联,正是金圣叹引入金元杂剧的楔子体制来改写并标举 《水浒传》开篇 “洪太尉误走妖魔”情节的用意。金批本把通行本第2回改为第1回,意指此回才是小说主体故事的开始,而它所单列的 “楔子”则是这个主体故事的引入部分,为主体故事提示情节要旨 (群雄作乱),简介人物关系 (一百单八个魔君),由此而引入主体故事的叙述,其意图即如金圣叹对楔子意指 “以物出物”的解释:“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7〕《水浒传》业已隐存的这个楔子部分就这样一步步地导引出了水浒英雄的主体故事。而金圣叹正是看到了 《水浒传》情节叙述所存在的这种结构关系和叙事策略,才会在批改 《水浒传》时引入金元杂剧的楔子概念并以 “楔子”标显其意。
由此可见,金圣叹把 《水浒传》通行本的第1回改易为 “楔子”,即是用杂剧楔子体制来体现他对于 《水浒传》设置 “洪太尉误走妖魔”情节的叙事策略的理解。这种由一段情节 “楔出”主体故事的叙事思路,正如金圣叹 《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言之 “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8〕金批本化用杂剧楔子体制,把小说叙述结构中引入主体故事的情节段落标称为 “楔子”,其目的就是揭示《水浒传》实际上存在的以 “一段小文字”引入“一段大文字”的做法,以此彰显这种楔子类引入情节与主体故事的结构关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叙事建构意图。
金圣叹批改本 《水浒传》所强调的杂剧演述体制和情节结构中剧首楔子与正场故事的关系,所揭示的 《水浒传》小说中楔子类引入情节与主体故事的关系,正是笑笑生在考虑如何呈现他所构想的 “风情故事”,如何表述他的 “一个人想象出来的产品”时所面对的文学经验。对于喜爱并熟悉通俗文艺的笑笑生来说,这些小说、戏曲的表述手法、叙事策略所构成的民间叙事传统的创作实践经验,既起到了启发作用,也起到了限制作用。尤其是后者,因为作者在考虑如何把自己所构想的风情故事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所熟悉的这些表述故事的体例、规范、格式、套路,实际上已经对他设想的表述故事的方式、策略形成了一种引导,进而影响他在 《词话》的叙事建构时设置了楔子类引入情节,以之来照应主体故事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前缘,以及由此而来的欲望纠葛和因果报应。
三、《词话》为何要使用武松打虎故事领起楔子类引入情节
宋元以来的通俗叙事作品,无论是口头创作还是书面编写,都喜欢把新编故事架设在具有民众影响力的流行故事上,在旧有故事框架内构思新篇,即使反映现实问题也会如此。在 《词话》以前,借用有影响力和民众基础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来呈现、负载新故事的创作方式,已有非常多的实践经验。比如元代的三国戏中,就有取关羽为形象而生发的新故事,《关大王三捉红衣怪》(戴善甫)、《关云长大破蚩尤》(无名氏)、《关大王月下斩貂蝉》(无名氏)、《关云长单刀劈四寇》(无名氏)、《寿亭侯怒斩关平》(无名氏),实际上皆是把新编故事安放在一个著名的人物形象身上。这种情况在水浒故事作品的编写中也大量存在,比如李逵就是一个箭垛式人物,人们不断地以他为主人公编创新的英雄传奇故事,仅现知元杂剧就有李逵戏15种,民众在他身上寄寓了自己熟悉、亲近的性格和情趣,写出了他粗暴又纯朴、憨直又细心的可爱形象。这与上一节中谈到的通俗文艺叙事建构中使用楔子类引入情节一样,都是承续、因应民间叙事传统的表现。这是当时通俗文艺叙事建构的一个大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大传统之下,还存在一个与水浒故事有关的小传统,即在水浒故事流播的背景中,取其人物、情节以作重述改编。这样的作品在 《词话》之前已十分常见,编演者们就是看中了水浒故事的民众基础、题材特性能够让他们的作品取得良好的社会接受效应。因此,这种取用水浒故事题材的重述或改编,在小说、戏曲中形成了一个取材喜好上的小传统。
兰陵笑笑生在考虑使用楔子类引入情节时,之所以选用 《水浒传》的武松打虎故事,肯定与水浒故事的社会影响力和 《水浒传》的传播深广度有关。否则,作为一个风情故事,作者完全可以选用其他类似的作品,比如宋元话本 《刎颈鸳鸯会》,笑笑生即在 《词话》开篇抄引了它的入话部分的文字。有的学者即因此认为 《刎颈鸳鸯会》是 《词话》的一个重要蓝本,比如韩南指出:“作者在卷首引用这个故事意义重大。这表明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和这个故事的构思相似,一个性欲异常的女人使拜倒在她裙下的男人家破人亡。”〔9〕范丽敏在细致比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从故事内容来看,《金瓶梅》可说是 《刎颈鸳鸯会》的翻版,只是 《金瓶梅》篇幅较长,《刎颈鸳鸯会》篇幅较短而已。二者的近似度极高,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10〕既然如此,笑笑生完全可以把自己构想的风情故事负载于 《刎颈鸳鸯会》的蒋淑珍、朱秉中身上,由这篇话本小说引导出以蒋淑珍、朱秉中为主人公的主体故事。然而,《词话》还是选用了武松故事来作为楔子类引入情节,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都与 《水浒传》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有关,与那个有关水浒故事的浓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虽然不会认为 《词话》是水浒系统的作品,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出现与这个有关 《水浒传》、水浒故事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而这个文化氛围是由众多演述水浒故事的作品来营造和支撑的,尤其在文学领域内,历代众多的水浒系列作品对于水浒故事的深入人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作品之所以都喜欢把新编故事安放在水浒英雄的头上,就是看到了水浒故事、《水浒传》广泛的传播范围和深厚的民众基础。
当然,这个 “小传统”还包含了历代众多水浒作品的叙事建构方式,这来自于通俗文艺反复不断地对水浒故事的重述实践。它们一方面为后来者拓展了编创思路,积累了叙事经验,另一方面自身也借助水浒故事情节、水浒人物形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获得了理想的社会效应。这些水浒故事的重述实践在编创思路和方式上大致有“接着说”和 “借着说”两条路径。
“接着说”的路径,是沿着宋元水浒故事 “说话”及其话本的方向和框架,以水浒英雄人物为中心,在英雄传奇的故事范畴和题材特性上不断地翻腾,《水浒传》的最后编定即是这条路径上滚雪球式累积的典型代表。而在其前后的口头讲唱领域、书面编写领域,这条路径上的水浒故事作品还有不少:《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部分,反映的是宋代水浒故事 “说话”的面貌;元代康进之 《李逵负荆》、高文秀 《双献功》,明代朱有燉 《黑旋风仗义疏财》、李开先 《宝剑记》、沈璟 《义侠记》,则是众多元明水浒戏的代表作品。
当然,这些元明水浒戏并不是简单地仅按水浒话本、《水浒传》重述,而是隐显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在人物形象上,朱有燉 《黑旋风仗义疏财》中的李逵、鲁智深完全偏离了水浒英雄的形象,李开先 《宝剑记》中的林冲则是一个心怀天下、勇于直谏的忠君文臣形象。而且 《宝剑记》所设置的人物活动场景已不是水浒英雄行侠仗义的江湖世界,而是扭结着忠奸斗争的朝廷官场,明显地表现出直面现实、反映现实的创作意识,只是它最终没有离开水泊梁山,尤其是没有舍弃逼上梁山这个故事发展方向和情节框架,所以仍然是延续了 《水浒传》的方向和框架。
对此表现出变革意味的是元人杂剧中的水浒戏,它们已能很好地体现出 “借着说”的路径,即按照自己的方向和框架来使用水浒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如前所述,现存6种元水浒戏都有一个水浒英雄下梁山的模式。元人水浒戏中梁山好汉下山的情节设置,在叙述结构上可以由此引入正场故事,在故事情节上可以由此导入另一个场境的事件。承续这种结构方式,现存明人杂剧中有7种水浒戏,除了凌濛初 《宋公明闹元宵》外也都有这个模式化的宋江开场情节。但不同的是,明人水浒戏叙述的梁山好汉下山后的行动都是反抗官府、掠州劫县,这仍然还是延续了宋元水浒故事话本、《水浒传》的主题和格调,而现存6种元人水浒戏的正场故事,却不是江湖的英雄传奇,而是市井的世情纠葛,涉及到家庭、司法、冤案等因素——
《李逵负荆》写强徒宋刚、鲁智恩抢走王林的女儿满堂娇。
《黄花峪》写蔡衙内强抢刘庆甫之妻李幼奴。
《双献功》写孙孔目之妻郭念儿与白衙内私通,孙被白打入死囚牢。
《燕青博鱼》写燕大之妻王腊梅与杨衙内私通,陷害燕大。
《争报恩》写赵通判小妻王腊梅与丁都管通奸,陷害大妻李千娇,言其与梁山有染。
《还牢末》写李孔目之妾与赵令史通奸,谋害亲夫,告发李孔目私通梁山。
现存的这6种元人水浒戏中,前两种叙述的是权豪势要欺压良弱的恶行,后4种叙述的是由男女奸情而引起家庭冲突,并由此造成了负冤不平之事。这些水浒戏虽然还包装着梁山好汉惩治豪强、扶助弱小以伸张正义的情节框架,但主体故事着眼的事件则是市井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尤其涉及到家庭纠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因此,元人水浒戏所表现出的格调就与宋元水浒 “说话”大不相同了,它改变了宋元水浒故事话本的主题,不再是 “朴刀”“杆棒”类的英雄传奇,诉求武装反抗朝廷,重建社会秩序,而是水浒英雄参与市井社会的人事纠葛和伸冤理屈,诉求社会的公理正义。如《黄花峪》中刘庆甫的妻子李幼奴被蔡衙内抢走,他不去官府申诉,而是直奔梁山 “告状”,宋江便派李逵和鲁智深下山捉拿蔡衙内到梁山,最后由宋江作出判决。这种情节模式与当时的包公戏异曲同工,只是最后断结案情的不是包公的开封府,而是宋江的梁山泊。这样的剧作虽然是把故事架设在水浒英雄身上,但又按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进行了适当的开掘、发挥,因此在人物性格、故事主题和情节设置方面已溢出了水浒话本的英雄传奇范围。所以说,元人水浒戏是在宋元水浒故事 “说话”广泛流播氛围中的开拓和发挥,并且注入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表现出了关心现实生活、时代主题的倾向。
而且,元杂剧水浒戏所表现出的这个变化,还在于它们所设置的故事场景已不是英雄的江湖,而是民众的市井。在这个市井社会的故事情境中,梁山好汉也表现出了不同于 《水浒传》的一面。比如刘唐在 《宣和遗事》中是最早上梁山的头领之一,他参与了晁盖智劫生辰纲的行动,还奉命给宋江送金钗致谢,是一个富有义气的人,但在水浒戏 《还牢末》中,他身为东平府的 “五衙都首领”,心胸狭窄,性情残暴,挟私报复,为了几两银子就置李孔目于死地。燕青在 《水浒传》中是一个武功高强、英俊潇洒的青年豪杰形象,但在 《燕青博鱼》中却豪气全无,懦弱困窘,因欠房钱饭钱而被店家驱逐,以致冻馁街头,沿门叫化;后来行走 “博鱼”,杨衙内折断他的扁担,摔碎他的瓦盆,也只是哀求乞怜:“这是借的波,爷饶了我罢。”关胜是 “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在 《水浒传》中的身份相当高贵,但水浒戏《争报恩三虎下山》中的 “大刀关胜”只是一个市俗的流浪汉形象,他下梁山打探事情,因病重险些丢了性命,病好后又无盘缠回山,就在晚间偷了人家一只狗,“煮得熟熟的,卖了三脚儿”,正要卖第四脚儿时,就惹出来一场官司。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杂剧在水浒故事的情节框架中所架设的新故事,不但表现了市井社会中的水浒英雄,而且还表现了市井社会的市井小民,甚至是把市井小民设置为故事的主人公,比如《还牢末》中的正末李荣祖、《争报恩三虎下山》中的正旦李千娇。李荣祖是东平府六案都孔目,偶然机会结交了李逵,但其妾萧娥与赵令史通奸,谋害亲夫,告发李孔目私通梁山。李千娇是济州赵通判之妻,她先后救助了下梁山而落难的关胜、徐宁二人,但赵通判之妾王腊梅与丁都管通奸,意欲陷害大妻李千娇,言其与梁山有染。此二剧中,李荣祖、李千娇都是杂剧的主唱人物,是正场故事的主人公,但他们的故事却是由走下梁山的水浒英雄导引出来的。
对于杂剧要演述的正场故事来说,下梁山的水浒英雄既是主体故事的一个重要人物,又是楔子类引入情节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那么,宋江开场情节就表现出两个叙述结构作用:一是交代主体故事中重要人物的来历,二是让下梁山的水浒英雄把叙述之眼引入到正场故事。如此一来,在故事内容上,宋江上场的自报家门是为观众展示了一个水浒故事的背景,而他派遣下山的英雄人物又把观众带入到市井社会的故事场景中。这个市井社会故事所展示的事件、环境和人物相对于典型的水浒故事作品都有了变化,尤其是表现出了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关注。而在叙述结构方面,现存的这6种元人水浒戏都表现出一种模式化的结构格套:以水浒英雄的下山情节导入正场的市井故事,以水浒英雄的行走路线引入正场的市井社会。
由此可见,在 《词话》之前,众多水浒作品的反复重述实践已经营造了浓厚的水浒文化氛围,锻炼出明确的叙事建构格套,其中元明水浒戏就对此做了很好的促进。这些创作实践不但表现出借用水浒英雄人物生发新作的思路,还表现出对现实生活和时代主题的关注,它们所负载的叙事经验、文学传统对 《词话》的故事构思和叙述策略产生了影响。因为在 《词话》大量取用的繁杂的文艺材料来源中,戏曲是一大宗,尤其重要的是它对于戏曲材料 (如剧名、曲名、曲词、戏曲人物、戏曲情节等)并非只是简单的抄引,而是能够根据小说情节、人物、主题的需要而进行有意识、有目的选择与改造,以达成自己的故事建构目的,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张竹坡即坚信《金瓶梅》中每一支曲子的引入都有寓意性:“《金瓶》内,即一笑谈,一小曲,皆因时致宜,或直出本回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当于其下另自分注也”〔11〕,“凡各回内清曲小调,皆有深意,切合一回之意” 〔12〕。
那么,当兰陵笑笑生考虑着如何呈现他那个来自于对社会生活深刻观察和思考的风情故事之时,他身处于有着深厚民众基础、社会影响的水浒文化氛围,面对着通俗文艺编演改写水浒故事的风气,前代作品对于水浒故事的利用思路,尤其是元明水浒戏 “下梁山模式”在故事情节、叙述结构上不断开掘的编创经验,受此启发,受此引导,才会在承续小说、戏曲、说唱等通俗文艺叙事设置楔子类引入情节的体例基础上,取径《水浒传》武松打虎情节以引入他所构想的风情故事。由此使得他在第1回利用了有着深厚民众基础和社会影响的武松打虎故事,让武松走上景阳冈打虎,但其目的不是为了展示一个江湖英雄的胆气豪情,而是为了让武松下山,来到清河县城遇兄,以引出潘金莲、西门庆,并藉此把我们带入一个市井社会,展示他自己所构想的风情故事。
四、结语
《金瓶梅词话》的出现,得益于当时社会文化土壤的孕育,也得力于已有文学传统、文学经验的滋养。其主体故事的创造性构想,是来自作者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观察、思考的结果;而其杂取众材的过渡性质的叙事建构,则受到了民间叙事传统的影响。小说中出现的那些丰富、繁杂的前代文艺材料虽然能够说明这一点,但其取径武松打虎故事的属性则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影响在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上的积淀。
《词话》取径武松打虎故事作为楔子类引入情节以领起和导出小说的主体故事,一是借用现有熟事以引入主体故事的结构方式,二是借助有民众影响力的经典故事以创作新编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建构的思路和方式乃承续于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建构叙事的大传统和众多通俗文艺作品取径水浒故事以建构新故事的小传统。支撑起这个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历代众多文艺作品对于叙事建构的编创经验,对于水浒故事的重述实践,必然会对兰陵笑笑生的 《词话》创作构思起到启发、引导和限制作用。
兰陵笑笑生选取了民众熟知的武松打虎故事,由此引领我们来到一个新创的市井风情故事。于是,《词话》在武松打虎下山之后,没有像 《水浒传》那样让武松来到阳谷县城,而是来到了清河县城,这在叙事建构的意义上,就宣示了与 《水浒传》武松故事的殊途分道。对于 《词话》的叙事建构来说,《水浒传》的存在意义也如武松打虎情节之于 《词话》主体故事的存在意义一样,是一个叙事策略上的问题。无论笑笑生在 《词话》中使用了多少 《水浒传》的故事材料,皆与第82、83回使用的 《西厢记》材料、第61回使用的 《宝剑记》材料、第1及100回使用的 《志诚张主管脱奇祸》材料、第98及99回使用的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材料一样,都是作为呈现其自己的故事构想的便利材料,它们在 《词话》中的使用属性、叙述地位处于同一层面,共同指向作者 “借着说”的主体正篇——西门庆故事、风情故事,而不是要 “接着说”武松故事、水浒故事。所以,在 《词话》的叙事建构意义上,无论是取径武松打虎故事,还是附骥 《水浒传》,都是承续宋元以来民间叙事传统的表现或结果。
据此而言,《金瓶梅词话》开篇以 《水浒传》武松打虎情节引入到小说的主体故事,应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做法和思路。《水浒传》的武松打虎故事引导了西门庆故事的叙述,民间叙事传统引导了 《金瓶梅词话》的叙事建构。这个叙事建构所体现出的成就或特色,乃缘于民间叙事传统经由作者笑笑生的熔铸而在此获得了一个相对整合、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既包含了文学传统催化出的新创,也包括文学传统驯化出的限制。
基于此,对于 《金瓶梅词话》存在着的大量前代文艺材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当其编写时,它的开创意识是如何面对这些现成的文艺材料的?把这些文艺材料聚合起来靠的是什么?《词话》的编成不能只靠 “个人独创”这个理由即可解释详备,还需要勘查它具体组合了哪些已有的文学经验和文学传统。对于 《词话》的编写,众多前代文艺材料在此体现为一个组合,而这些文艺材料所负载的叙事经验也在此体现为一个组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作者兰陵笑笑生所要面对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经验。对于后生文艺来说,已有的文学经验、文学传统既存在着启发作用,也存在着限制作用;它们给出的可供依赖、遵循的表述手法,是一种召唤力量,也是一个评价体系,让编创者在构思或呈现时难免兴生因循依傍之念。这在《金瓶梅词话》的叙事建构中就有典型表现,而这也是决定它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