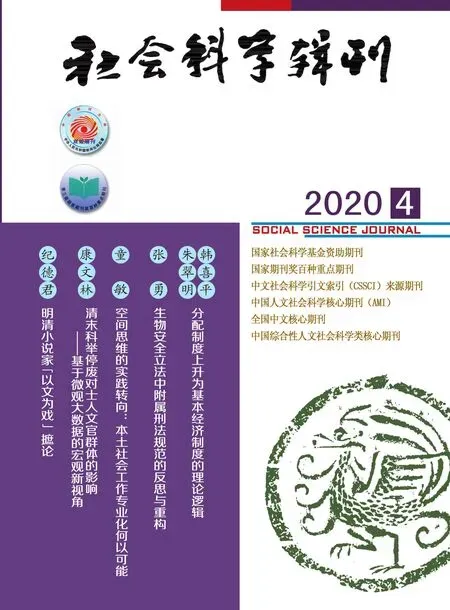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
——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
〔美〕 康 文 林
1900年以来,作为尝试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清廷对政府机构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项是1906年起科举考试的废除。为代替科考制度,清政府尝试开辟新的取仕渠道以录用有新式教育背景的人才,例如授予留洋归来的学子相应的科举出身。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增设了考职场次以保证旧学士子有机会获得在官僚系统任职的机会。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制,一部分旧有机构被更名或裁撤。①新内阁设十部,即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和理藩部。关于官制调整,参见〔日〕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50-45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372-1385页。
本文将以由缙绅录构建的中国政府官员数据库清代部分为主要材料,尝试通过对文官群体整体的构成和变化来检验并分析上述改革对文官系统的影响。①本文作者在此特别向沈钰莹、陈必佳表示感谢,她们对本文的完稿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本文的主要数据分析和结构由作者在2018年6—7月间完成中文初稿,沈钰莹在此基础上添加了背景材料和引用文献,后由陈必佳对初稿的文字部分进行了改写和梳理,添加更多历史背景和相关细节性论述的引用文献,并将作者新增添的文字由英文译为中文。王婷也在初期帮助编辑文章。同时感谢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其他成员提供的建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胡恒老师和其他匿名审稿人在文章完善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缙绅录是按季出版的职官名册,在清末由于有大量书坊刊刻印行,存世版本多,质量也较高,是构建量化数据库并用以分析追踪官员群体或个人仕途迁转的理想材料。
本文利用最新构建的中国政府官员数据库清代部分 (CGED—Q),对清末十余年间清政府文官群体的数量变化进行了追踪统计。②中国政府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部分,主要根据大象出版社的《清代缙绅录集成》录入建设,数据库的具体内容和详情参见任玉雪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僚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统计结果表明,京师的文官群体自1907年起数量上出现迅猛增长,而同时期地方官员数量上有略微的减少。本文将根据全体文官在京官和外官系统中的出身、官职分析其数量和构成比例,并探索此种现象的原因,以冀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为传统史学方法研究清末新政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在文官群体中,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进士和举人出身的官员。拥有科名的官员在这一时期的仕途变化是我们研究新政改革中最重要的科举革废核心,也有助于了解取而代之的新取仕途径之执行状况。晚清进士群体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尤其是清末的几科进士 〔1〕,更有围绕进士馆的建立始末展开的研究。〔2〕类似关于举人出身的官员研究则由于材料不足等原因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分析进士和举人群体在清末获得官缺任职的机会、所任官职、离任可能性、占文官群体之比例及上述各项指标的时间变化,进一步补充上述研究之不足。
本文同时也关注除进士、举人以外其他科名出身的文官在新政期间的变化,例如较少受到关注的贡生、监生群体。研究对象包括正途和异途出身的贡生官员和监生官员。经过分析发现,这些官员在1907年开始的官员规模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分析了上述群体在新获任的文官中所占比例、迁转以及就任之官职类型。相较于近期发表或出版的其他关于清末进士的研究,笔者在此更全面地关照到了文官系统整体面临改革前后的变化。一系列量化分析揭示了1906年科举制废除后,清朝文官系统的组成最显著的变化来自于京师官员群体中举贡生和监生数量的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京师官员中进士出身的官员数量是稳定的。
本文的分析方法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一方面,官员纵向的个人数据允许我们同个案研究一样,从微观层面分析官员出身、获任的可能性;不同的是,大数据的基础令研究者还能同时将不同研究对象纳入考虑范围,对整个文官系统进行整体分析。另外,文章对整个文官系统进行了宏观层面的分析,比较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他们置于更大的文官系统变革情境之中。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希望为利用历史量化数据库进行定量分析并将其与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取得互补提供范例,同时展示该方法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随着数据库录入工作的推进,中国政府官员数据库清代部分即将分时段对学界逐步公开,本文旨在通过展示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在大数据方面可以进行的统计分析,抛砖引玉,鼓励更多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的学者应用于更为具体的研究课题当中。
一、背景
针对科举制度废除后旧学士人 (进士、举人、优贡、拔贡和生员等)于清末政府体制中的角色流变,基于各方史料与既有研究成果,本部分将围绕清廷相关善后措施与士人境遇表现两方面展开。
科举停废后相关措施具有因 “人”制宜的特点。清廷针对旧学出身未获最高功名然学习适应能力较强者,安排其入读各级师范学堂和简易科师范,并予优先录取;或使其出洋学成归国后,经学部考验用科名出身作为奖励并授职。而对于中年以上难再适应新式学堂的士人,清政府则另辟通道,包括1905年后开设的举贡、生员考职、优拔贡考试和孝廉方正科等。〔3〕入仕条件上的优厚表现,以举贡会考为例,在京 (内)官方面,成绩靠前者享有废除科举前常见于进士却鲜少见于举贡的 “以主事分部”的待遇;外官方面,包括给予此前新科进士任知县才能享有的 “即用班”待遇。〔4〕
至于废除科举对士人的实际影响,学界较趋向于从不同维度讨论士子在科举废除前后的境遇对比,结合清末新政的背景,进而获得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图景。整体可见两种切入点:一种为从士子个体视角出发考察科举废除之影响;①主要著作包括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 期;Henrietta Harrison,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1857—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李长莉等:《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等。另一种则以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整体考察,根据既有文献可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基于自18世纪中叶以来仕途实缺难求、异途对正途出身者比例渐有压倒之势的背景下,科举废除后清廷 “宽筹出路”,“优贡照原取例额加四倍考取,拔贡照原取向额加取一倍……同时岁贡并在本省照原额倍取,不送京试”〔5〕。部分士子通过数额放宽的优拔贡、举贡会考和生员考职等方式,获得了比以往同等条件下更便捷的进入文官系统的途径,或经入读新式学校辗转于政府中获得职位。另一方面,数额限制的放宽并不等于士人在官场境遇的改善。“有人统计近年新登仕版之官可达五千人以上。”〔6〕从数字上看,对已有功名者而言,废举后进入仕途较废举前难度变小,但人数上升在仕途本就拥堵的前提下很有可能恶化整体环境。
其二,官制变更对于士人的职业机会带来的影响亦受到关注。改革合并了职能重复的官署,同时增设了新的部门。中央部院明显扩军,加以破格用人,京官的升沉颇异于往昔。首先是新部“捷径”,“商部、巡警部、学部、邮传部即其显例”,“由旧部改为新部,职能扩充,用人增多,以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新设各级审判厅,以及户部改度支部最为典型”〔7〕。面对新政实施过程中譬如警务、司法等相关部门人才紧缺的局面,一方面根基未稳的学校体系所培养的毕业生未能满足实际需求,而此时旧学出身者亦有相当人群接受过新学方面的训练,最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官缺由旧学士子或有旧学根基的人才补充。〔8〕
其三,清廷在废除科举后于人材选拔上的倾向性变化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旧学士人的地位。有悖于传统上直观认为的科举废除后新式人才更受青睐的观点。既有文献表明,清廷在废除科举后显现了着意优选旧式学人,特别是兼有旧学根基与留洋经历人士的趋向。有学者结合报章分析,认为传统出身的举贡比留学生更受垂青。〔9〕
综合以上学界论述,客观因素从不同层面促成了科举停废前后中央与地方文官体系内各层次出身人员的变动趋向。
二、数据
文官的出身及官职信息均来自中国政府官员数据库清代部分 (CGED—Q),暨原 《缙绅录量化数据库》。②任玉雪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僚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相关项目细节请参考康文林、李中清:《China G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Qing(CGED—Q)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2020年 2月 1日,http://www.shss.ust.hk/lee-campbell-group/china-government-employee-database-qing-cged-q/,2020年4月 5日。为了深入分析新政时期官员的任命与迁转政策之调整对官员群体的影响,本文使用数据时间上的覆盖面为1900—1912年——除1912年仅有春季、1900年缺冬季、1901年缺夏秋二季、1904年缺秋季外,其余年份四季皆齐全。〔10〕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取得科举功名的民人文官,因而排除相关年份内来自中枢备览记录及有相同功名的旗人官员,数据最后包含有关35621名民人文官任职信息的465004条记录。①虽然小部分旗人也会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但旗人科举选拔标准及缺额与民人不同,且科举并非旗人官员入仕的主要途径。新政时期旗人官员的变化另参见陈必佳等:《新政前后旗人与宗室官员的官职变化初探》,《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为了避免不同版本在内容上的差异影响到数据信息的连续性,分析中同时排除了只出现于坊刻本的官职、机构及对应的官员记录。②参见任玉雪、陈必胜、郝小雯、康文林、李中清:《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缙绅录1900—1912时段公开版用户指南》,2019年7月1日,https://dataspace.ust.hk/bib/E9GKRS,2020年4月5日,以下简称《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使用指南》,不再一一标注网址。坊刻本与官刻本内容差异的比较基于光绪七年春的坊刻本和官刻本。在此感谢缙绅录录入人员葛晓东先生对版本内容比较提供的详细报告。数据库1900年后的版本中同时包括官刻本及坊刻本。坊刻本所包含的机构内容较官刻本更为详尽,特别是京师各部的额外司员和候补官员的记载要更多,因此相邻季节坊刻本的记录数通常多于官刻本1000—2000条。缙绅录数据库基于版本清晰度和内容准确度的考虑,优先录入清华版 《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官刻本,其余录入坊刻本。③大多数情况下官刻本的书名为《爵秩全览》,且无出版书坊信息,书名为《大清缙绅全书》《爵秩全函》等情况的皆为坊刻本。由于坊刻本偶尔也借《爵秩全览》之名出版,故本文对官刻本和坊刻本的区分和定义除参照书名外,还加入是否有出版书坊信息、变量内容特征等标准,具体书名和版本的分类详情可参见《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使用指南》。相邻季节中因版本差异而导致的记录数的巨大变化使得时间趋势变化不定。分析中排除了未出现于更早缙绅录的官职,留待以后另行分析。④主要包括御前侍卫、花翎侍卫、蓝翎侍卫、行走和司乐等;排除的机构包括内务府、神机营旗都统和坐粮厅衙门等。另排除只出现于最后两种版本的新机构,包括检察厅、提法司。以上新机构与所列官职绝大部分是近代化的新机构。
本文分析中使用的关键变量为旗分、出身与官职。⑤变量为量化数据库中表格的表头或栏位名称,对应缙绅录每条官员信息的相应内容。我们用有无旗分信息来区分缙绅录数据库中的旗人与民人官员。由于缙绅录中记载的出身种类较多,笔者基于分析比较的需要将其分为七大类:进士、举人、贡生 (正途)、捐纳贡生 (异途)、监生、其他及无出身。⑥科举中翻译科的进士及举人,只要缙绅录中明确记为“翻译进士”“翻译举人”,即归类在“其他”而不归在进士、举人中。贡生包括岁贡、拔贡、恩贡、副贡和优贡在内的正途五贡。捐纳贡生包括廩贡、增贡、附贡等由生员捐纳所得的出身。生员在缙绅录官员中所占比例较低,因此暂归在“其他”。官职的名称较为繁复,且同样的官职在不同版本中顺序格式上时有变动,但是少数常见和主要官职占官员任职的大多数。分析之前,我们已将官职信息做了简化处理:去除兼任及其他临时职务,排除官职中包含的一些荣誉性质的虚衔。本文关于若干科进士甲第的材料,用到了清代进士题名录数据库,通过姓名和籍贯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连接,在进士官员的仕途分析中加入了甲第维度。⑦进士题名录数据库由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任玉雪老师提供,根据江庆柏《清代进士题名录》录入并进行了校对,参见江庆柏:《清代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三、量化分析结果
1.时间趋势
新政前后,清政府官员人数在京师与地方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新政后,在京师机构的任职机会有明显增长。1907年前,根据缙绅录内容,每季度有3000—4000名官员在京师任职,如图1所示,其中民人京官只占京师官员的1/3左右,其余皆为旗人。1907年后,京师官员的人数有明显的增加,到1912年已多了一倍:在1907年春季的缙绅录中,京师官员的人数仅包括3524条记录,而1912年春季的职官录中,京师官员有7116条记录,旗人在人数上基本没有变动。京师官员人数整体增长主要是基于民人人数的增加:1907年春季的缙绅录中包含2208条京师旗人官员的记录,1912年春季的职官录中,这一数字为2254。在同样的时段,民人官员在上述前后两个季节缙绅录中的京师官员人数从1316增至4682。至宣统末年,民人在京师官员中所占比例已升至5/7。这一现象与清政府在科举废除后,在各类录用考试中提升旧学士子录取名额并提供录取条件方面的优待有关。与此同时,除了1906年以后数量上有略微的减少之外,外官的数量在这一时段内整体保持了稳定。在1907年春季,缙绅录中有8139名外官记录,而这一数字到1912年的职官录中,则为7447。

图1 官员按季节京官/外官、旗人/民人分布

图2 京师民人官员按季节出身分布

图3 地方民人官员按季节出身分布
新政时期,京师和地方民人官员的出身分布也有不同的增长趋势。图2与图3展示的分别为清末十余年间京师与地方民人官员出身分布变化之时间趋势。图1显示了京师官员人数的增长,图2进一步说明了京师民人官员的出身分布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变化。进士出身的官员人数维持不变。因为1905年科举取消后,未有新的进士。新就职者应皆为1905年以前已获得科名但仍在候缺待任的。举人人数的增长最为明显:京师的民人官员群体中,举人出身的官员增加了三倍左右,贡生也多了数倍,但由于贡生出身的官员总体人数较少,故其对京师官员人数增长的影响不如举人显著。可将举人的变化与科举废除后官员录取政策对举人的待遇有变化相结合。①具体可参见政务处:《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朱寿彭编:《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489-5490页。譬如1907年举贡考试后,在京官层面的录用中,举人贡生录取者中得 “以主事用”待遇的人数,较此前有大比例的升幅。此待遇在废举前常见于进士,却鲜见于举贡。除此之外,监生与捐纳贡生多了几倍,其他出身官员的人数未变。无出身官员的人数多了几倍,但是人数较少。图3显示地方官员的出身分布并未发生类似的变化。进士以外出身的官员皆略有下降。因进士人数没变,进士占的比例略有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学堂毕业生、海外游学毕业生等亦可得举人、进士等出身并获得职位,本文涉及的分析中排除或单独区分这一部分人。但依据商衍鎏所述,由学堂毕业生或海外游学毕业生获取举人、进士出身的人数由光绪三十一年 (1905)的14人,至后来的31人、40人,增至宣统年间每年200—400人。粗略估计七年内由此途径获得举人、进士出身者应当在千人左右。〔11〕
为验证和阐明获举人、进士出身的学堂毕业生、海外游学毕业生是否包含在图表分析中,进一步检索追踪毕业生在缙绅录数据库中任职情况的记载有助于对此进行查验。根据对商衍鎏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中所提及的获授进士出身的三位游学生在缙绅录数据库中的任职情况和出身的核对,最终发现仅有一人的一条记录中出身录入为 “游学进士”。
具体核对的三人情况如下:金邦平,安徽黟县人,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录取的游学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出身,任职翰林院检讨。缙绅录数据库中共录得24条关于金邦平的任职记载②因此处所引皆为数据库中录入的内容,具体书名和版本可参见数据库对应内容。,其中仅光绪三十二年夏出身记录为 “毕业学生”,光绪三十二年秋的记录中标明 “乙巳”,其余的记载中皆将出身直接记为 “进士”。宣统二年夏季至冬季,官职记载变更为资政院试署秘书厅秘书长,后一直任秘书厅秘书长直至清末最后一季。陈锦涛,广东南海人,自光绪三十三年秋起任职记载为度支部衙门主事,属于额外司员,同年秋任七品京官,三十四年春任郎中,仍属额外司员,同年夏季官职改为参议厅郎中。宣统二年夏起官职记载为郎中署银行副监督。宣统三年冬季的记录中官职改为度支部度支副大臣。上述记载中该名官员的出身皆为进士。章宗元,浙江乌程人,光绪三十四年春起官职记载为翰林院编修,出身为进士,同时兼任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科员、外务部候补主事。宣统三年冬季开始,官职改任为度支部衙门财政处总办。可见游学生获授进士后,大多立即得到任用,迁转频率也相对频繁。
2.举子就职的可能性
为了理解科举停废对进士与举人就任机会的影响,本文比较停废之前不同科年的进士及举人之就职累积比例。若科举的停废也影响到停废之前已有科名的举子就职机会,进士与举人的就职比例应该于停废后出现明显变化。因为进士的授职与甲第密切相关,分析中将进士分为两组:一、二甲及三甲。分析中包含的进士样本为1894年以后参加会试及殿试的各科进士:1894、1895、1898、1903及1904年,共有2239名进士的资料。①本文的分析还用到了包括进士题名录、乡试录与乡试同年齿录在内的其他材料。将其中的进士及举人作为“分母”而根据缙绅录匹配的结果计算这两大群体的就职比例。为了分析进士获任官职的可能性,必须将缙绅录的任职数据和题名录等科举名录数据进行匹配并形成整合数据库,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士子的就职可能性、考取科名与任职之间的候缺时间以及科场表现对任职机会的影响。②各类科举名录与缙绅录都包含的基本信息为举贡生员的姓名与籍贯。对民人来说,姓名与籍贯组合后的唯一性相当高,因而利用程序对两种数据库进行匹配的准确率也很高。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的籍贯信息分别录入在“人省”“人县”两个变量下,题名录、乡试录的录入格式也基本一致。
笔者依据所掌握的材料,计算了1905年科举废除以后,不同甲第的进士获任官职的比例变化。具体操作上,本文对1894年及以后各科进士在1905年以后获取官职的情况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同时控制了他们考中进士以来的年份。在1905年以前,殿试以后的五年内获得官职,或者说出现在缙绅录中的进士官员比例高达63.1%。获得官职的机会根据甲第的不同而差异显著:一、二甲进士官员比例高达84.5%,而三甲进士的比例仅为48.4%。在1905年以后,考虑并控制会试科年,鼎甲和二甲进士获得官职的比例从2.98%增至87.51%。三甲进士获任官职比例增长更为明显,拥有官职的三甲进士比例从3.92%增至 52.3%。进士官员受科举废除的影响较小,因为旧学士子中的鼎甲和二甲进士依例在科举废除前已有很高的比例入选翰林院并在散馆后得到任用,所以这些进士在获任比例上的增长空间小于三甲进士。另外,我们利用由河南乡试各类同年录、齿录构建的数据库,对河南乡试举人群体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计算。数据分析的对象包括了1893、1894、1897、1902和1903年各科乡试中举的举人。分析发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这些举人五年内获得任职的预期比例从8.09%增至11.5%。
(1) 迁转
根据图3我们发现,京师民人官员在1906年前后呈现出显著变化。我们首先按出身类别分析不同时段官员进入和退出文官系统的比例分布情况。这里的退出比例,指相对于在缙绅录数据库中特定季节出现的官员在以后各个已录入的季节中皆不再出现的比例。缙绅录材料本身并没有记载或者说明某名官员是否致仕,或提供任何他们离任的原因,我们的计算是根据季度之间的人员匹配进行的推断。相应地,这里的进入是指在实际数据库的分析中,首次出现在已录入的缙绅录季节中的官员群体。①我们不排除这些官员在此之前曾经在武官系统任职,亦或由于时间覆盖的不足,并未追踪到该官员真实进入文官系统的确切时间和季节。但由于清末十余年数据库录入在时间覆盖上较为完整,后者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节分析中的官员进入比例所代表的是某季缙绅录中相较于之前所有已经包括在我们数据库中从未出现过的官员比例。
根据数据分析的情况,我们认定了在数据覆盖范围内四个官员流入和流出率较高的时段,分别为:1902年春季、秋季,1906年秋季,1907年秋季和1911年春季。官员流动率最高的时段是1907年秋季,可见表1。在1907年夏季,38.9%的民人官员并未在之后的缙绅录中出现。在这一时段中官员退出的比例因出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进士作为民人京官的主体是最不可能退出的,只有32.2%的官员此后没再出现在数据库中。监生的流动性最大,他们之中有63.5%在缙绅录数据库中最后一次出现。1902年春夏秋三季、1906年秋季和1911年春季缙绅录的退出率尽管高于整体的平均值,但要远低于这一时段。在1906年秋,正途和异途贡生的退出比例都尤其高,几乎1/3的贡生在此后的缙绅录中再未出现过。同时,在1907年秋季至1908年春季的缙绅录中,有16%的官员是新出现的。从表格中可以看出,除了进士,每一个出身大类的官员比例都受到了影响。

表2 按时段进士官职分布 (1900—1912年)

表3 按时段及出身京师官员官职分布 (1900—1912年)
(2) 官职
清末进士出身的文官官职分布相当稳定。根据图1、2、3显示的趋势,表2、3将1900—1912年划分为三个时段。1900—1907年中官员人数与出身分布很平稳,因此定为第一个时段。1908年起,官员人数显示明显地膨胀,尤其是京师,如图1所示,我们将1908年定为第二时段的开始。而1910年以后,京师官员的出身分布出现显著变化,如图2所示,我们将1910年定为第三个时段的开始。虽说三个时段的官员人数和出身分布不同,但是进士在三个不同时段中不同官职的比例与排名,无论在地方或京师都很稳定,如表2所示。尽管政策和体制变化,官员产生大量流入与流出,但进士任职分布在新政时期未变。
(3) 京师
举人出身者的官职分布在不同的时段变化非常明显,尤其是小京官的出现。表3显示三个时段京师举人官员的官职分布。因为图3显示地方官员的出身分布未变,但图2显示京师官员中的举人有巨大的膨胀,表3内容是对京师举人官员加以分析的结果。1900—1907年,根据计算,小京官只占京师举人官员的1.18%①此为对于数据库中京师举人官员记录在相应时段的单独计算结果,并未包含在表格分析中。,但从表3来看,在1910—1912年,小京官占京师举人官员的1/3。原因或可能为,其一,不同于其他在京官职,小京官的录取人数本无明确定额,故数目调整相对灵活,尤其在需要给予更多官职的情形下。其二,官制变更的影响。“各部主事下原有笔帖式,皆改为小京官 (七品)录事 (八、九品)人数不等。” 〔12〕此项举措亦增加了小京官的比例。其三,如前文所述,在 “宽筹出路”宗旨下,原本仅常见给予进士就任京官的待遇,自1907年起在更低层次功名者身上变得并不鲜见,尤其是举人和贡生。〔13〕值得注意的是,1907年恰为举贡考职的年份,时间点和数据所显示的变化节点具有一定的关系。确切因果关系有待未来进一步考证。虽然小京官数目的扩张为举人出身官员人数增加的重要因素,但是其他官职的扩张也是因素之一。1910—1912年九个季度里举人一共有9410条记录,多于1908—1909年八个季度的一倍。
同举人相比,贡生有类似的趋势。表3显示三个时段京师贡生 (正途)官员的官职分布。贡生官员约1/3任为主事。贡生小京官数目的变化趋势跟举人出身的不一样。第一时段的差异相当明显。虽然我们的计算显示1900—1907年,举人官员约有1.18%被任为小京官,但是同时段贡生官员中19%已任为小京官。之后,贡生中小京官的比例也不断增长,最后升至41%。此外,另有其他新官职的出现,如录事及主簿。同样类似于举人,最后时段的贡生人数高于第二时段一倍,因此尽管官职所占百分比没有明显变动,但是官职人数大部分都增加了。
整体而言,小京官群体在1907年以后的文官系统人员扩张中占主要部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1907年以前,京师新任职的非旗人文官中,仅有1%—2%是小京官。在1907年,该比例为5.27%,而且这个比例在此后稳定增长。在1910年,25.9%新任职的官员是小京官;在1911年这个比例增至36.4%。这些小京官的出身以举人和贡生为主导。在1910—1911年间,将近2/3的小京官为举人出身,略高于贡生所占1/4的出身比例。这些新任小京官,在农工商部衙门、邮传部衙门、民政部衙门、学部衙门、度支部衙门和法部衙门均有一定的比例。在个别部门,小京官占的比例尤为高——在1910和1911年,农工商部衙门下属官员中小京官的比例最高,占衙门全体官员的45%左右,次之的是学部衙门 (37.5%)、邮传部衙门 (26.09%)、民政部衙门 (21.05%);法部衙门和度支部衙门中小京官的比例相当,各占11.7%和11.4%。
监生与捐纳贡生的趋势不一样。表3显示三个时段京师监生及捐纳贡生官员的官职分布。第二时段开始,主事的比例有明显的增长,约为一倍;录事开始出现和增长。到1910—1912年,类似于举人与正途贡生,最后时段总人数多了约一倍。因此,尽管其中存在官职百分比下降的情况,如员外郎及郎中,但是实质人数却增加了。与举人和正途贡生相比,监生与捐纳贡生的小京官比例一直较低,到第三时段,根据独立的分析计算结果小京官的比例仍为1.76%。
四、结论
本文利用大规模的数据样本,揭示新的史料形式和研究方法,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基于传统文献及个案研究的视角。我们通过分析缙绅录的微观数据,包括民人官员群体人数与不同出身官员的比例变化,取得对清末政府体系改革前后制度的连续性与变化的宏观认识。藉此有助于取得新政时期任用、提升政策与措施调整对官员群体影响的新理解,尤其是对政策与措施的实际成果方面的理解。
本文的主要发现有三点。首先,新政时期进士出身的官员群体未见受政策调整的影响,京师与地方进士官员的人数、官职分布均相对稳定,不同科年进士的任职机会大体相近。其次,虽然举人与贡生在地方官员中所占人数未变,且不同科年举人的就职机会亦未出现明显变化,但其在京师却显示巨大的变化。随着1907年后京师官员人数的增长,京师举人与贡生官员人数有相当明显的增长,且官职分布也有变化,如小京官所占比例有显著增加。最后,监生与捐纳贡生呈现出与进士和举人不同的另一种模式。1907年后监生与捐纳贡生人数增长了,但是分布的变化与举人和贡生的变化不同。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笔者及其合作团队计划更深入地分析新政时期不同出身的文官群体在新旧交替的改制背景下官职的变迁趋势。真正对清末新政中文官系统的嬗变有全面认识,还需将此类微观数据分析的方法与传统的制度史研究相结合,互为参照,分析系统内部包括旗人官员在内的各个群体、机构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笔者亦希望通过本文探索性的分析激发学界对相关主题更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所使用之中国政府官员数据库清代部分 (CGED—Q),1900—1912年录入完成的各季将以数据库的形式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平台上公开,供学界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展开研究。目前数据库的进一步公开正在有序规划和进行,1900—1912年的各季数据及相应的录入说明、使用指南已于2019年公开。本文的分析旨在展现本数据库在实证分析方面的潜力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