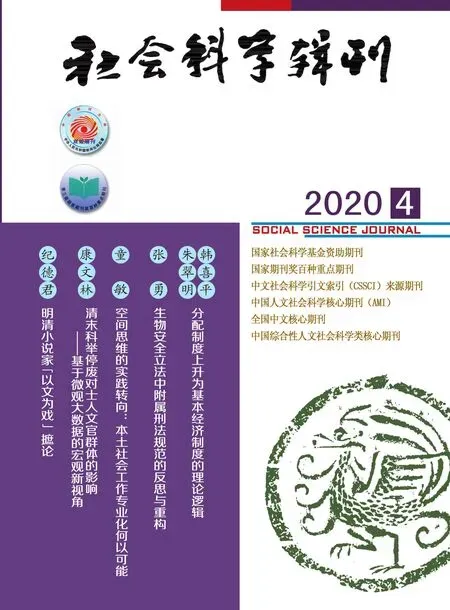《文心雕龙》声律理论三题
于景祥
《文心雕龙》中包含了较系统、完整的声律理论,自成体系。其中既有借鉴、吸收他人理论成果的一面,又有作者自己开拓、创新的一面。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分析和梳理,以便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刘勰及其 《文心雕龙》的巨大价值。
一、《文心雕龙》声律理论的基本内容
《文心雕龙》中关于声律的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 《声律》篇,归纳起来看,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音律本源及乐器与人声之关系
音律本源及乐器与人声之关系,不仅是音韵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是诗歌脱离音乐限制、走上声律化的道路之后,诗人和批评家对此十分关注。刘勰 《文心雕龙·声律》首先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1〕此处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阐释音律的本源,认为音律起源于人的声音,人声本身已经具备宫商等音律特质,古圣先贤正是利用人声中天然的音律制作乐调,写成诗歌。第二,揭示人声与乐器之间的关系,指出乐器是写人声的,而不是人声学乐器,强调应该以人声为主导,使音律服从于人声。唐人孔颖达也说:“原夫作乐之始,乐写人音……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人,是乐本效人,非人效乐。” 〔2〕很明显,这是继承了刘勰的论断,所以黄侃说:“案冲远此论,与彦和有如合符矣。”〔3〕然而,刘勰关于音律本源及乐器与人声之关系的论断,不只是阐明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即认为乐器写人声,以人声为主导,随人声内具的宫商而抑扬起伏,这是自然天成的;而人声学乐器,以人声的自然音调去迁就乐器,会使人声受到拘束、限制,失去自然之态。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勰是推崇自然天成的声律效果的。这是 《文心雕龙》声律理论的一个要点。
(二)文章和律之难及原因
《文心雕龙·声律》指出:“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摛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4〕先以乐律比较文章之声律,揭示教歌与作文在声律上存在的差异:古代教人歌唱,首先按照乐律,使强音合于宫音,弱音合于徵音。宫商音强,徵羽音弱;伸喉转舌不同,蹙唇齐齿有别,这样人的发音与乐器的发声可以清楚地加以辨别。一旦弹出来的琴声与人声不和谐,弹奏者懂得调整琴弦,使歌者的发声与伴奏的琴声和谐悦耳。可是相比之下,作文之时声律不和谐,一般作者却不懂得协调。为什么呢?刘勰认为外听 (即音乐的乐音)容易辨别,而内听 (文章所反映的作者的心声)却难弄明白,其中原因主要在于外听通过琴弦来表现,可以由弹奏者的手工操作来决定,依照乐律,容易协调;而内听准乎心、依乎情,而心、情纷繁复杂,变化不定,所以难以把握。因此文章和律是相当困难的。对于刘勰此论,曾有多人作过阐释,其中当数刘永济所论最为深刻,其 《〈文心雕龙〉校释》云:“舍人 ‘内听’之说最精。盖言为心声,言之疾徐高下,一准乎心。文以代言,文之抑扬顿挫,一依乎情。然而心纷者言失其条,情浮者文乖其节。此中机杼至微,消息至密,而理未易明。” 〔5〕 着重阐释 “内听之难”,抓住 “言为心声”这一要点,说明人的心绪、情感复杂多变,所以协调音律比较困难。概括而言,刘勰是由乐律而谈文律,强调追求文章声律和谐境界之困难,和是 《文心雕龙》声律论的总体目标。
(三)声律规则与协调方法
对声律规则与协调方法的深入讨论,是刘勰声律理论的核心。他采取正反对比的方式对此进行分析:“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6〕这里主要论述了两点:第一,声律的基本规则和方法。刘勰首先指出声调有飞声、沉声之别,音响有双声、叠韵两类。所谓 “飞”“沉”,指文字声调的抑扬,“飞”为扬上,当是上声;“沉”为抑下,当是去声。“双声”者,二字同纽;“叠韵”者,二字同韵。然后采取对比的方法,阐述声律的基本规则和协调方法,即两个双声字不能被隔开,两个叠韵字中间也不能夹杂别的字;一句之中,不能都用下沉的音,也不能都用上扬的音;协调方法是讲究声调的变化与和谐统一,概括起来就是 “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即不同声调的字要交互错杂地使用。否则,“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一味用 “沉”,“则响发而断”;一味用 “飞”,“则声飏不还”;如果两者配合不当,读起来绕口,就像人说话口吃一样。第二,文章声律失调之病及解决方法。刘勰从文章中的 “口吃”现象即不合声律的状况入手分析,指出其原因在于违背基本的声律规则和方法,盲目地追求怪异和新奇。刘勰提出总的解决这一弊端的原则和方法就是 “刚断”。“刚断”即态度坚决,具体方法是 “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这样便会收到声音悦耳、圆转如珠的艺术效果。所以,刘勰认为文章声韵的好坏,关键在于和谐与押韵。要想声韵和谐,须 “异音相从”,也就是不同的声调巧妙地配合,在文句之中讲究平仄,使之有相间、相重之美;而押韵则是 “同声相应”,即相同的韵字巧妙地配合,即文章中各收句之末字要同韵。
刘勰认为,在诗文创作中,押韵容易,音响配合则困难;措辞工巧容易,使音调和谐则比较困难。刘勰既是理论家,又是作家,这是他的甘苦之论。刘永济说:“齐梁之际,四声始分,韵书未定,作者每苦不能分别,故曰难也……此事必在四声既定之后,古人不知也。” 〔7〕认为在齐梁韵书和四声未定之时,刘勰对声律规则及协调之法的探讨不免存在时代局限。其实,刘勰论述的要点是 “和”与 “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既讲究平仄,又讲究押韵,事实上已经建构了格律诗的声律框架。我们不能不承认刘勰是中国诗歌格律化的重要奠基者,其声律理论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四)推崇自然音律
在 《文心雕龙·声律》中,刘勰分析了自然音律与人工音律之间的差别,并品评高下优劣:“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一。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8〕刘勰以吹竽比喻陈思、潘岳之文,因其音律自然天成;以调瑟比喻陆机、左思之文,因其音律人力加工的特点比较突出。纪晓岚评云:“言宫商虽和,又有自然、勉强之分。”〔9〕黄侃也指出:“案此谓能自然合节与不能自然合节者之分。” 〔10〕其实,刘勰不仅分析了自然音律与人工音律的差别,还表明了自己对这两种声律的不同态度,暗含褒贬:称陈思、潘岳之文为 “宫商大和”,“无往而不一”,明显是褒;称陆机、左思之文乃 “翻回取均”,“有时而乖贰”,明显是贬,高下优劣清晰可见。很明显,刘勰扬曹、潘而抑左、陆,推崇自然和谐的声律。
(五)标举正音,重视才识
刘勰还从创作实际出发,结合前人作品,对正音与讹音 (方言)的区别以及作者才识与声律协调之关系作了分析。他说:“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余声,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 〔11〕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揭示正音与讹音之差别,强调诗文用韵应该用正音,不能用讹音。刘勰以具体作品为例,指出 《诗经》为正音,正音之韵,圆转自如;而 《楚辞》则多用讹音——楚地方言,难免方凿圆枘。显然,他强调诗文押韵当用正音,不该杂用讹音。纪晓岚批道:“此一段又言韵不可参以方言。” 〔12〕黄侃也指出:“此言文中用韵,取其谐调,若杂以方音,反成诘诎。”〔13〕都把握住了刘勰的主旨。其二,重视作者才识对诗文声律协调的影响,认为作者才识精深,作文时就会剖析字的音韵,取得声律协调的效果;才识粗疏,则驭音无术,为识者所笑。在此基础上,刘勰以 “古之佩玉”为喻,强调声律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声律是用来 “律文”的,是诗文创作不可或缺、不能忽视的要素。
二、《文心雕龙》对前人及时贤声律理论的借鉴
刘勰的声律理论并不是一空依傍、独立创造的,而是在借鉴前人及时贤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一段,明显借鉴了韩非子《外储说右》的有关论述:“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日,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与为同教。” 〔14〕黄侃就此解释说:“彦和引用以为声音自然之准,意与韩子微异。” 〔15〕前者与后者虽然有微小的差异,但是大体相同,借鉴、吸收的痕迹比较明显。再如 “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两句,显然借鉴了陆机 《文赋》“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16〕,正如黄侃所云:“此与士衡‘音声迭代,五色相宣’之说同恉,究其治之之术,亦用口耳而已,无他妙巧也。”〔17〕
刘勰对沈约等齐梁时贤的声律理论借鉴更为突出。其一,《文心雕龙·声律》中有 “声含宫商,肇自血气”之说,这与王融的声律理论有密切关系。钟嵘 《诗品》曰:“齐有王元长者,常谓余云: ‘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擗绩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18〕钟嵘对当时极力追求声律的做法颇有微词,但是这段话中却透露出 “声含宫商,肇自血气”一说来自来王融,这一点是得注意的。郭绍虞在其 《声律说考辨》一文中也谈到这一点:“在这儿,‘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即王融所谓 ‘宫商与二仪并生’之意。” 〔19〕刘勰的声律理论显然借鉴了王融之说。其二,《文心雕龙·声律》中说:“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20〕此论显然受萧子显文学理论的影响。萧氏在其 《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 〔21〕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声律》中有关声律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主张,对沈约等人 “四声八病”等声律理论多有借鉴和吸收。第一,在阐述字调的问题时,其 “飞声”和 “沉声”受沈约的 “浮声”和“切响”之说的启发和影响。沈约指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2〕刘勰此处之 “飞声”与沈约之 “浮声”指的都是平声,而刘之 “沉声”与沈之 “切响”当指上、去、入三声,也就是后来的仄声。刘勰强调 “飞声”和 “沉声”要 “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即间隔运用,使声调在变化中达到和谐,其观点也显然借鉴了沈约等人的“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和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主张,其实质都是强调诗文的声韵要有变化,还要和谐。第二,刘勰关于声律协调方法的论断,要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韵的问题,一个是和的问题,这两点都明显受到沈约等人 “四声八病”之说的影响。所谓“韵”就是 “同声相应”。那么,如何达到 “同声相应”呢?沈约等人在其 “四声八病”之说中提出:“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 〔23〕这为刘勰解决“韵”的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刘勰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解决文章用韵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其中的继承关系显而易见。就“和”的问题而言,刘勰提出的办法是 “异音相从” 〔24〕。沈约等人在 “四声八病”之说中早于刘勰提出了 “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 〔25〕的方式和方法,其中关键就是 “异音相从”。可见,刘勰之 “异音相从”说是在沈约之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三、《文心雕龙》在声律理论上的创新
《文心雕龙》中虽然对其他人关于声律问题的研究成果有所借鉴、有所吸收,但不是兼收并蓄、无所创造,而是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又特别注意自主创新。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字音的阐释有所创新
字音的剖析是声律的基础,沈约等人在声律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创造 “四声八病”之说,其中对字音的剖析主要是其 “四声”论。所谓 “四声”就是对古汉语声调的四种分类,以表示音节的高低变化,划分为四个单元,即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平声、上声、去声三者一般统称为舒声,而入声则为促声。舒声与促声在韵尾上有明显的区别:前者韵尾以元音或者鼻音结尾,后者韵尾以塞音结尾。入声除了是一个声调,还是一系列以塞音收尾的韵母的统称。在字音的分析上,沈约等人的贡献主要是对这四个音阶的划分,在字音三要素 (声、韵、调)的调的方面有开创性意义,但是在字音的阐释、剖析上成就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文心雕龙》声律理论首先是在这一方面超越沈约等人,其突出的表现是对喉音、牙音、舌音、齿音、唇音的分析,以及对字音的声、韵、调三个方面的阐释都超越他人,特别是沈约等 “永明体”的创立者。“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音韵学家顾炎武注意到刘勰的这一划分,所以在 《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条下说:“五方之音,有迟疾轻重不同。……注家多有疾言、徐言之解;而刘勰《文心雕龙》谓‘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原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有此语。)夫一字而可以疾呼徐呼,此一字两音三音之所繇昉也。”〔26〕大略说出这一划分在文字学、音韵学上的意义,但是还不够具体、不够深入。如果我们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便可明白看出刘勰在字音的剖析及对文字声、韵、调的阐释上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其一,刘勰对喉音、牙音、舌音、齿音、唇音的分析非同凡响。从语音学的角度上讲,刘勰此处的所谓 “抗喉”,点出了喉音;其 “矫舌”,又点出舌音;其 “攒唇”,说的是唇音;其 “激齿”点出了齿音,这几点分析正是声纽分五音,即喉音、牙音、舌音、齿音、唇音的分析。其中没有谈到牙音,应该是将其同齿音合二为一,同时,因为其行文用的是骈体对偶的句式,限制在两联对偶句中论述,不便再拆出一个单句。其二,关于 “廉肉相准”的分析是又一个重要贡献,这是关于音韵学中韵部的基本分析。其中 “廉”即谓瘦,“肉”即谓肥,其实就是宽音和窄音的区别。从语音学的角度上观察,这应该是韵部中元音的洪细分别。纵观中国古代语音学史,《切韵》的反切下一字,即分元音洪细这个秘密,长期以来无人知晓。一直到宋元时期的音韵学家才揭开这一秘密,把韵部元音划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但是,这四等的意义,当时还没有确切的解释。直到清代,音韵学家江永才把这四等的意义解释清楚:“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27〕其实,这个解释的重大意义是把高元音、低元音、前元音、后元音的区别讲明白了。而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在其 《文心雕龙·声律》篇中,通过 “廉肉相准”数句论述,早就对字音的三方面,即声、韵、调,都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而且还点到了元音的洪细分别,这实在是突出的成就。由此可见出刘勰在字音及其声、韵、调的阐释上难得的创新与超越。《文心雕龙》在字音研究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这样两点:其一,揭示出语音的洪细之别,对语音的分析更加精细;其二,对字音的声、韵、调三个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明显超越了前人,特别是齐、梁时代其他人的声律研究水平。
(二)在解决文章病犯问题上有所超越
随着声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诗文创作中如何解决病犯问题便成为焦点。针对这一问题,刘勰在其 《文心雕龙·声律》中提出了解决方法:“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首先,文章病犯的具体表现是 “吃文”。所谓“吃文”,指的是文章音韵不协调,读起来像口吃一样别扭,并且指出这一病态是由作者喜欢诡异造成的。刘勰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病犯问题的方法,其方法对陆机的《文赋》有所借鉴,所以詹锳特别指出:“《文赋》云:‘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殆为此节命意之所本。” 〔28〕说明刘勰此论在立意上确实有师法陆机 《文赋》的一面。黄侃在其 《〈文心雕龙〉札论》中也指出:“‘左碍而寻右’二句,此与士衡音声迭代,五色相宣之说同旨。”〔29〕但是,公平地说,刘勰此论虽然受陆机 《文赋》的启发和影响,但又不是简单照搬,而是有所发展和创新。其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措施上强调 “刚断”,即坚决去掉喜欢诡异的癖好,决不因词害意。这是其解决病犯问题的基本主张。二是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病犯问题的方法:“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意思是句左有病在句右寻找办法,句末有病在句前寻找解决办法。此法开了此后唐诗中拗救的先河,因为唐人拗救之法主要是两种:一是当句救,即一句之中前后相救;二是对句救,即上下对句中相对互救。显然,这是在刘勰解决病犯问题方法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这比陆机解决病犯的方法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从音韵学史和文学史上看,这一方法的提出意义非凡:它下启唐、宋文人的拗救之法,在声律学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三)《文心雕龙》声律论的核心思想更为科学合理
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发现 《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侧重于自然声律,其核心思想是追求和,与沈约等 “四声八病”的人为限制有明显的区别。刘勰明确反对 “好诡”和 “逐新趣异”,揭示出由此造成 “喉唇纠纷”,也就是 “文家之吃”的毛病,并且明确指出这种毛病的根本点就在于不循自然,过于讲究病犯,人为的限制太多。所以,《文心雕龙》声律论的主要倾向是讲究自然声律,其突出特点是和律,追求的是字句的流畅,音调的和谐,在吟咏诵读之间来分辨其 “声画妍蚩”。落实到文学创作上,就是追求语句之自然,声调之和谐,进而达到 “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的音乐般的美学效果。这就是 《文心雕龙》声律论求和与追求自然的核心思想,与沈约等人特别注重人为限制的音律说有明显的不同,也是明显的超越。
事实上,沈约等人以 “四声八病”为核心的声律论问世之后,并不为所有的研究者所接受,当时就出现明显的分岐。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三个派别:其一,力主派。这一派极力倡导并推行以 “四声八病”为核心的声律论,代表人物是沈约等 “永明体”文士。其二,反对派。这一派以钟嵘为代表,认为 “四声八病”限制太多,其主要观点见于钟嵘的 《诗品》,在此书中,他明确指出沈约等人的声律论“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30〕。其三,折衷派。这一派以刘勰为代表,既不反对声律,又不完全赞成沈约等人那种限制太严的声律规则,有取有弃,折衷其论,形成自己声律论,其特点就是侧重于自然,追求和,即强调平仄抑扬、调配得当的科学的声律法则。沈约等人主要关注的是声律上的病犯和规则,而刘勰所关注的是在声律上如何求和。虽然其求和的方法当时尚不完备,但他提出了抑扬的方式和方法,也基本能够达到求和的目的,并且为以后唐人的平仄抑扬律开启了门径,推助了格律诗的产生。我们知道,唐代的格律诗,解决的格律问题主要就是韵与和两个关键点。其中韵的关键是句末押韵,当时韵书出现了,照韵书押韵,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而和讲究的一是一句中要平仄抑扬,二是句和句之间也要平仄抑扬,两者都要协调,这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到了唐代,在刘勰 “和体抑扬”即平仄相间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特殊的抑扬律,所以和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其一,以平仄相间之法,在一句中做到了一扬一抑,平仄搭配,音调和谐,实现了句中的和;其二,在一联之中,上下两句平仄交错,即上句和下句的平仄大体相反,实现了一联中的和协;其三,联与联之间也平仄交错,即第一句平起的,第三句要仄起,于是联与联之间也实现了和协。这样,唐代的格律诗就正式形成了。这说明刘勰的声律理论和方法较沈约为代表的 “四声八病”一派更加科学,更加先进,而且在中国声律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郭绍虞先生曾对这一点有过专门的论述,其 《蜂腰鹤膝解》一文中说: “作家所注意的只在去病,理论家所注意的则在求和。求和的方法一时虽不能逐条举出,但只须注意 ‘抑扬’两个字,自会达到求和的目的。这就是刘勰比沈约更高一着之处。此后发明平仄的抑扬律,就是朝这条路线进行所获得的成就。于是,很自然地从 ‘永明体’演进为律体了。律体既规定了求和之法,也自然简化而易于奉行了。”〔31〕这一对刘勰声律理论的解读,尤其是对其地位和作用的阐释是精当准确的。
可见,《文心雕龙》的声律理论体系一方面继承了他人的理论成果,特别是齐、梁时人声律理论的合理成分,同时又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创新,总体成就超越了其他人,在中国古代声韵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