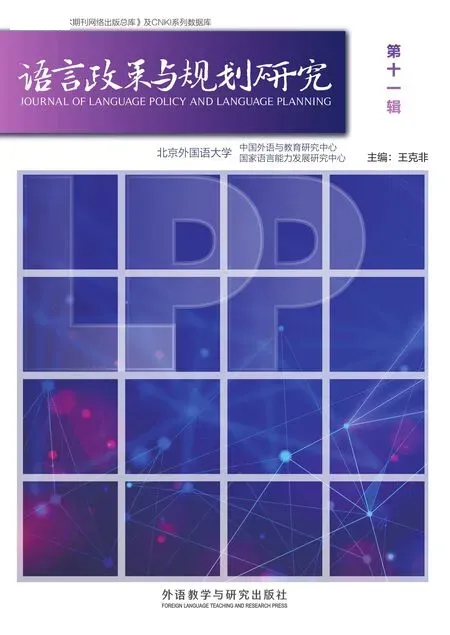美国手语语言政策与规划
上海大学中国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 陈雅清
提要:从早期聋教育开始到近两百年的美国聋教育历程中,不同时期的聋教育政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与美国手语相关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活动。纵观整个美国聋教育的发展历程,美国手语经历了发展与高峰期,也经历了挫折与低谷期。本文通过对美国聋教育历史发展及相应时期美国手语政策和规划活动的简单梳理,讨论美国聋教育中手语地位的变化情况,总结其相关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促进我们对中国聋教育和手语政策的思考和探索。
1 引言
语言使用与政治权力、社会经济发展、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的密切关系使人们日益意识到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其在教育领域的地位尤其重要,被公认为能“带来改变的有力工具”(Kennedy,1983)。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指通过研究社会使用的各种语言或方言,制定其选择使用的符合现实的政策,力图解决社会的各种信递问题,通常也被称作语言工程(language engineering),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指政府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和措施,体现了国家或社会团体对语言问题的根本态度。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两者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提供理性与有效的标准,后者验证前者的思想和理论模式(Hornberger,2006)。而教育语言规划(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侧重于教育领域中的语言规划,是国家语言规划活动的分支。诸如在教育过程中“某一社群最需要的是哪些语言”“这些语言要承担怎样的功能”等都是教育语言规划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Kaplan et al,1997)126。聋教育的历史就是探索帮助有听力障碍的儿童参与社会的最佳方式的历史。而语言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则是聋教育的核心问题。“我们应该采用什么语言来教聋人学生?他们应该采用什么语言来交流沟通?”诸如这些问题都需要聋教育者给出合适的答案。对此多位学者(如Reagan,2010;Swanwick,2010)都指出,手语在教育中的功能以及聋孩子发展双语能力(包括手语和社会主流有声语言)的机会和条件都是聋教育者需要考虑和解决的。语言教育是聋教育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最初对手语语言规划的探索也始于聋教育活动,手语政策的出台与聋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聋教育政策中的语言规划活动来了解和探讨手语的语言规划与政策。
手语作为自然语言的地位得到语言学界的肯定最早始于美国学者William Stokoe对美国手语语言结构的描写。同时,美国手语作为目前多学科角度(如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手语之一,其作为聋教育中语言规划和政策的研究对象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探析美国手语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发展过程也能为我国制定相应的手语语言政策及聋教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启示。本文以美国的聋教育政策为突破口,对美国的聋教育政策及其体现的手语语言规划和政策进行梳理和探讨。
2 美国聋教育与手语语言政策的发展
2.1 早期的美国聋教育与美国手语的起源
1817年,康涅狄格州聋哑人教育福利院(the Connecticut Asylum for the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of Deaf and Dumb Persons),现为美国聋人学校(the American School for the Deaf,以下简称ASD),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成立。这所学校提倡在聋人教育中使用手语,各种历史因素在该校融合,美国手语应运而生。随后,这所聋人学校的毕业生不断将美国手语发扬光大。许多聋人毕业生陆续在各个州开办聋人学校,分享和传授手语教学法,同时也致力于不断发展和传播美国手语。
美国早期聋教育确立了手语的重要地位,并采用了基于手语的双语教学法。依据Nover(2000)45-46的记载,康涅狄格州聋哑人救济院采用了四种沟通模式进行教学,分别为手语、方法性手势(methodical signs,即为适应书面英语的表达而对手语语言结构进行过调整的手势)、手指字母和书面交流(笔谈)。这种教育模式承认了手语在聋教育中的语言地位,并为后来美国境内多所聋校开展聋教育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1867年,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在意识到聋人无法说话或清楚地发音这一现象,且当时的聋教育并未将教授聋童发音和开口说话作为聋校的教育目标这一情况后,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关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设立了一所新的聋校——克拉克聋哑学校(Clarke Institution for Deaf-Mutes),并采用口语教学法,只将英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到1868年,全美28所聋校中,两所仍坚持使用手语教学法,两所使用口语教学法,剩余23所则采用了爱德华·加劳德特推崇的“组合模式”(combined system),即手语教学与英语口语教学相结合,两者同时作为教学语言(Nover,2000)。“组合模式”原本基于“教育方式要能最好、最适当地满足个别儿童的需要”的基本认识,提出在特定情况下对个别符合条件的聋童采用口语法进行教学(Reagan,2010)101。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大力宣传了口语教学法的背景下,大多数聋教育者误认为所有的聋孩子都应该进行发声学习和口语训练。
等到了1880年,全美的聋教育形式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以手语教学法为基础的共识已不复存在(Nover,2000)105。
2.2 作为“分水岭”的米兰大会
1880年,第二届国际聋哑教师大会(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nstructors of Deaf-Mutes)在意大利米兰召开,即通常所说的米兰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口语教学法支持者们的巨大成功,并成为了欧美聋教育史上的一个分水岭(Van Cleve et al,1989)120-127。1926年,美国聋人学校的校长会议“正式投票决定所有部门取消手语作为教学手段”。米兰大会提倡的“口语主义”不仅对美国聋教育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也给所有聋人的语言生活带来了广泛的消极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手语面临的另一威胁来自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他是口语主义最执着、最专注的倡导者,是在聋儿教育中以任何形式使用手语的最严厉的批评者(Reagan,1989)。在语言政策方面,贝尔不遗余力地参与了语言的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和态度规划,以确定美国手语在语言政策中的消极地位,保障英语在聋教育中的积极地位。在各种形式的“手口之争”中,“尽管聋人社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口语主义在接下来的六十多年中仍然占了上风”(Jankowski,1997)28。
2.3 美国现代聋教育及手语语言政策
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聋教育进入了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而美国手语也开始了合法化的进程(这里的“合法化”主要指对手语自然语言地位的认识,而非立法手段上的承认)。
美国现代聋教育主要遵照2004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法改善法案》(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mprovement Act,以下简称IDEA)和《联邦法规》(the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34号法令《教育部办公室条例》(the Regulations of the Offi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IDEA概括地陈述了残疾学生的教育权利,而第34号法令则提供联邦一级对IDEA的解释,并阐明IDEA在各州、地区和学校层面实施的过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共同构成了聋人教育政策的立法框架。
IDEA针对残障学生的教育活动提出了两项基本要求。其一,为满足每一位残障学生的特殊需要,必须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年度教育计划(Individualised Education Plan,以下简称IEP)。个性化教育计划工作小组的成员由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共同组成,并确立学生年度的学习目标,既包括学术方面也包括社会功能方面的目标,如语言学习目标。其二,工作小组必须决定并提供适合残障学生接受教育的最佳场所以保障其年度学习目标的实现。适合听障儿童的教育场所包括常规固定的、能满足个人需求的学校课堂、相应的区域性课程计划以及聋校。
从IDEA的政策来看,美国联邦政府也会为聋人设立特殊教育学校,但只有在“最小限制环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以下简称LRE)条款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此类措施,优先的教育政策仍是全纳教育,即鼓励特殊学生融入主流普通学校的教育环境。
LRE条款要求:“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全国各类公立和私立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中的残障学生与健全学生一起共同接受教育,让残障学生在受到环境最小限制的情况下接受主流教育。创建适于残障学生的受教育环境,使学生在其中感受到最小的限制,从而能最大限度地融入主流普通学校。只有当残障的性质或程度的严重性导致学生无法在常规教学场所接受教育,且相关辅助设施和服务也无法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时,才将其送至政府专门设立的特殊学校。”(20 U.S.C.§612(a)(5)(A))据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提倡的教育政策即全纳教育,主张把特殊儿童接纳到普通学校,并通过特殊儿童对各种文化、课程、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融入普通学校。同时我们也可以总结出美国手语语言规划活动的两项显著特征:(1)优先提供或选择常规的主流教育场所,并提供相应的辅助设施及服务,如听力辅助设备和手语翻译服务;(2)残障学生的同伴是同一年龄段的健全学生,从而避免将残障学生完全排除在公共学校系统之外。虽然“最小限制环境”条款使得聋生能相对平等地享有国家公共教育资源,也保障其在接受主流教育时享有相应的支持措施和服务,但对于聋生来说,这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运用手语和同龄聋孩子以及成年聋人教师进行交流的机会,从而导致接受主流教育的聋童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全面、均衡发展手语能力的机会。
根据加劳德特研究机构的记载(Gallaudet Research Institute,2008),在IDEA颁布以前,聋生都在为聋孩子设立的特殊学校——聋校接受教育,他们的同伴是和他们一样的聋孩子。在法案签署以后,大部分聋孩子都被转入普校学习,和听人孩子一起接受教育。由于英语口语是主流课堂的主导教学语言,关于聋孩子课堂的重新安置也可以看作是管理语言的一种实际形式(Siegel,2008;Spolsky,2009)。在IDEA中并没有关于手语使用的明确规定,但第34号法令确立了手语作为聋人母语的语言地位:“对于耳聋或失明的个人,或没有书面语言的个人,其首选沟通方式即个人通常使用的方式(如手语,盲文或口头交流)。”(34 C.F.R.§300.29(b))同时,《联邦法规》也明确规定了“手语相关服务作为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在主流环境中可要求提供的相关支持服务”(34 C.F.R.§ 300.34(4)(i))。
3 20世纪的语言政策与美国手语
20世纪针对美国手语的语言规划和政策工作主要关注以下几类问题:(1)围绕美国手语官方认可问题的讨论,即美国手语的地位规划活动;(2)美国聋教育政策体现的美国手语习得规划策略;(3)美国手语的本体规划(特别是在教育场景中的运用);(4)与美国手语相关的语言教育项目。
3.1 美国手语的语言地位规划
语言地位规划(language status planning)指政府或相关机构关于不同语言在特定场景和维度下的使用情况的决策,如对国家官方语言或教学活动所使用的语言的指定。而教育中的语言地位规划解决“教什么语言、学什么语言”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认可美国手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但在州一级,截至2006年,全美已有四十多个州制定了有关美国手语语言地位的立法。具体立法内容因州而异,依据其关注点和影响的不同可大致分为若干不同类别。一类是单纯地认可美国手语为一门语言,如亚利桑那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马里兰州、俄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另一类是承认了美国手语作为一门外语(foreign language)的语言地位,如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俄亥俄州、俄勒冈州、宾夕法尼亚州、佛蒙特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还有几个州仅在教育层面认可了美国手语的语言地位,肯定其在实现教育目的中所起的作用,如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夏威夷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蒙大拿州、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和罗德岛州都在立法文件中承认美国手语“有着自身的语法和文化传承,是发展成熟、自主、自然的语言”。只有少数州,如阿拉巴马州和缅因州,在法律上承认“美国手语是该州聋人的官方语言和母语”(Reagan,2010)114-115。
虽然各州针对美国手语的立法角度不同,但对美国听人学生学习美国手语的能力和机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Rosen(2008)17,20-22的记录,2004—2005学年,美国有700多所中学提供了4,000多课时的美国手语课程。同时,申请美国手语课程的学生从往年(2002—2003年)的56,783人增加到了73,473人,而这些课程雇用了725名全职教师。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立法层面的措辞不一,但其对美国手语在教育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积极的。这不仅从实际上扩大了手语在听人社会的知名度,普及了手语作为独立语言的认知,也提高了听人社会对手语的接受度。
针对美国手语的地位规划,IDEA与《联邦法规》都未出台专门的语言政策,但《联邦法规》承认了美国手语作为美国聋人母语和首选沟通方式的语言地位,IDEA也要求主流普通学校必须配备专门的手语翻译等聋人学生需要的支持,从而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融入普通学校的主流教育。
Reagan(2010)157-162指出,针对手语在教育领域的地位规划既要考虑教育环境中所使用的语言(口语和手语),也要考虑学生个人发展过程中需要的语言。前者包括教育活动中作为教学工具和教学目标两个方面的语言,后者指学生脱离学校场景后参与社会和职业生活所要掌握的语言能力。而目前不论是各州级的立法文件还是教育政策中对手语地位的认可都更侧重于第一个方面,而忽略了聋人手语能力全面发展的相关问题。
整体而言,美国并没有国家层面的立法将手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只是各州级政府各自出台了相关的法令承认美国手语作为真正的语言,享有在课堂中作为外语教学的语言地位。同时,美国也出台了全国性质的教育法案要求各类学校为听障儿童享有平等的教育权提供资金和行政上的支持。
3.2 美国手语的习得规划
语言习得规划解决“如何学习这门语言”的问题。手语语言习得的规划主要涉及“如何在学校实施语言教育、开展语言发展活动的问题,包括如何在教学活动中使用手语,以及学生获得的特定语言形式(手语)的学习材料和教学支持”(Spolsky,2009)101-108。
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可选语言库(linguistic repertoire),语言库中的不同语言用于实现或辅助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言语交际活动。对于聋人学生来说,手语翻译与可选语言库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手语翻译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聋人学生的社会交际活动及其社会交际能力的发展。因此,Kaplan &Baldauf(1997)126认为手语翻译是一种从学校发展而来的交际资源,并且这种交际资源在学生日后的社会活动中会有更广泛的应用。
同时,在Kaplan & Baldauf(1997)130-133的教育语言规划框架中,语言习得规划也包括提供人员和人事上的支持以满足学生的语言需求。应对这一点,IDEA对培养教育口译员提出了直接的要求,以满足聋人学生多载体交际的语言需求。IDEA规定:“学校应配备合格的专业教育口译员(即手语翻译员),以协助不同年龄层次的听力障碍学生参与学校举办的各类教育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包括学龄期的听障学生,以及参与早期干预计划和学前项目的听障婴儿、幼童和学龄前儿童。”(20 U.S.C.§662(c)(2)(E))
《联邦法规》也对手语翻译服务给出了详细的定义,将其分为了针对听力障碍儿童的翻译服务和针对盲聋童的特殊翻译服务。针对听力障碍儿童的翻译服务又进一步包括了“口语音译服务、提示语音翻译服务、手语音译和翻译服务和各类转写服务,如通信访问实时转换、语句输出和打字服务等(34 C.F.R.§300.34(4))。以上这些措施都是聋生在教育活动中有权享受的获取主流听觉课堂信息和资源的辅助措施,以达到IDEA要求的“最小限制环境”。
语言习得规划还应包含“课程大纲设计中分配给语言教学的空间”的相关决策(Kaplan et al,1997)127。IDEA有一条关于残疾学生的交际需求条款便提出要为有听力障碍的学生提供双语发展的环境,培养他们的双语能力:“考虑听力障碍儿童语言和沟通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在学术上及各类需求方面与同龄人和专业人士进行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保障他们享有以自己的语言和沟通模式获得直接教学的机会。”(20 U.S.C. § 614(d)(3)(B)(iv))虽然“最小限制环境”条款提出常规的主流教育课堂是对聋生进行课堂安置时的首要选择,IDEA同时也要求在对聋生进行课堂安置时要充分考虑聋生的语言交际需求。在主流课堂接受全纳教育的聋生享有和健全同伴平等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而在聋校接受教育的聋孩子享有与同龄儿童和专业人士直接进行手语交流的机会,这种差别和矛盾使得个人在选择何种方式来支持手语习得时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这种自由选择的空间也部分回应了上文Reagan提出的关于聋人手语能力发展的问题。
3.3 美国手语的本体规划
语言本体规划(language corpus planning)通常是语言地位规划的结果,指对某一特定场景使用语言的标准化、发展或“净化”。
针对美国手语的本体规划基本上都是非正式的,主要体现为全美各级聋校中的教育形式和各类教育活动。其中最极端的体现即手势符号系统(manual sign codes)的创造和发展。手势符号系统指用于在视觉—手势载体表征有声语言的手势交际系统——英语手势编码(Manually Coded English)。这一系统的创造和发展在各个方面都暴露了问题,但它确实是实际进行中的语言规划的突出表现。
作为语言规划活动,手势符号系统的发展及其在聋教育中的使用实质上提出了两项议题。显性议题即如何向聋童教授英语。另一项隐形议题实则为聋教育活动中自然手语的贬值与听力霸权化(Ramsey,1989)。同时,有声语言手势编码系统的发展也体现了“聋”在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想意识中所处的地位及聋人社群在聋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Woodward,1982;Padden et al,1988;Sacks,1989;Schein,1989;Lane,1992;Parasnis,1998)。另外,不同版本的美国手语词典和用于美国手语教学的各类教材和辅助材料也是手语本体规划的重要体现之一。
3.4 作为外语教学项目的美国手语
各类将美国手语作为外语进行教授的语言教学项目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手语的语言政策。
根据Wilcox & Wilcox(1997)51的报告,20世纪80年代,申请美国手语课程的听人学生在五年间增长了181%。且自那时起,申请人数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同时,新墨西哥大学的教员Sherman Wilcox还保留了一份全美接受美国手语作为满足其外语要求的大学的名单,该名单上共有160多所美国高校,其中不乏如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等之类的美国名校(Reagan,2010)120。
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发布的《外语教学标准》(the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为全美的外语教学和学习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对于美国外语教学中教学方法和课程的制定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该标准在全美的外语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在培养未来的外语教师和开发、编写当代外语教科书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007年至2009年间,美国手语教师协会(th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以下简称ASLTA)与全国口译教育中心联合会合作制作了《美国手语学习标准草案》。与此同时,许多州,如加利福利亚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北卡罗莱纳州和德克萨斯州等,也基于《外语教学标准》制定了各自的美国手语教学标准。
以上关于美国手语作为外语的发展情况和相关教学举措虽然不是正式形式的语言政策,却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手语在听人社会的语言地位和被认可的情况。
4 结语
通过对美国聋教育历史发展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美国的聋教育活动中手语地位的变化情况大致如下:19世纪早期的手语教学法—19世纪中期的口手之争—盛行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的口语主义—20世纪中期以后的综合沟通法—英语手势编码系统的创造和发展—双语教学项目。从早期聋教育开始到近两百年的美国聋教育历程中,美国手语经历了发展与高峰期,也经历了挫折与低谷期。纵观整个聋教育发展历程,每当美国手语的地位受到挫折的时候,都反映出了共同的突出问题,即消极的手语发展和规划过程都缺失了语言实质的使用者——聋人社群的意见和诉求表达。英语手势编码系统不被接受的本质问题也在于它们“反映和服务了听人社会的符号需求,而非聋童的语言和教育需求”(Ramsey,1989)146。因此,美国手语所经历的挫折及手势编码系统的发展和强制推行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制定语言政策、进行语言规划活动时,要充分发挥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保证他们在语言规划活动中的参与度。好的语言规划需要语言使用者的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更公正、更人性化和更合法化的社会与教育政策。而美国聋教育中的双语项目对于教育语言政策的启示在于,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时,不仅仅要关注其听和说、读和写的能力,还应关注与听说读写能力同等重要的手语能力。而且对于聋生而言,手语能力的培养应该优先于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在保证学生语言能力均衡发展的同时,教育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聋生手语能力的发展。
同时,手语立法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聋人语言权利的问题(Siegel,2008)。目前美国各州现有的关于美国手语的立法更多地强调美国手语在教育场景中如何达到外语教学的要求,这更多地体现了听人享有语言教育的权利而非聋人在各种场合享有便利沟通和信息传递的语言权利。因此Cokely(2008)指出,从语言权利的角度来说,比通过立法承认美国手语语言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确保聋人在各种场合都能获得经过专业培训的、手语技能娴熟的手语翻译员的服务,如司法场合和教育场合。关于司法场合的手语翻译服务,美国司法部已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当处理有听障人士参与的法律事务时,相关执法机构应提供合格的手语翻译员(受相关认证机构认可的专业从业人员)以协助机构与听障人士的有效沟通。当听障人士使用美国手语进行交流时,‘合格的手语翻译员’意味着熟练使用美国手语进行交流的手语翻译从业人员。执法机构有责任确定听障人士是否使用美国手语。”(Reagan,2010)116教育场合的语言权利问题则更为复杂。包括如何保障聋人学生交际需求、语言发展需求、社会情感和文化需求、学术发展需求等,这些都与使用的语言密切相关。同时,手语翻译的质量和能力水平、聋生手语语言能力的发展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总的来说,IDEA和《联邦法规》都强调保证聋生平等享有国家公共教育资源的权利并保障聋生在接受主流教育时享有相应的支持措施和服务,给予了聋人选择语言的自由度。同时,将美国手语作为外语教学项目的政策大大提高了美国手语在听人社会的语言地位和被认可度,从而使得聋人有更多的教育选择,为聋人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教育(不论聋听)中的手语政策与规划都侧重于如何帮助聋人融入听人社会,而忽略了聋人,特别是聋童,全面均衡发展手语能力的重要性,削弱了成年聋人教师在聋童语言、社会能力发展过程中的模范作用。同时,美国手语相关政策中都缺乏恰当的手语本体规划,这既不利于聋教育中教学语言的确定与发展,也是高质量手语翻译服务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