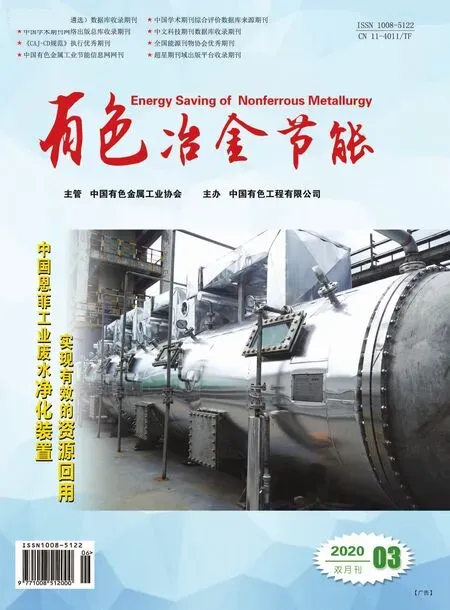铝电解槽大修渣的环境风险管控思路浅析
熊仁艳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2)
0 前言
众所周知,铝行业电解槽平均运行5~7年后,就需要进行内衬更换,这种大修产生的废阴极炭块和耐火材料等固体废物,在2016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中已被明确列为危险废物(废物类别HW48,代码为321-023-48)。一般吨铝大修渣的产生量约20~30 kg,按照2019年我国电解铝产量3 504万t计[1],整个铝行业年产大修渣量约为70~105万t。铝电解大修渣的浸出液中可溶氟化物和氰化物浓度较高,处置不当将对土壤、水域、动植物等产生很大的危害[2]。
近年来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置不当造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案例屡见不鲜,为此,国家重点推进了清废行动和净土保卫战,2020年4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订(以下简称“新固废法”)。新固废法除了要求产废单位践行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外,还强调要建立健全固废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尤其是对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和处置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管控要求和更加严格的罚则。因此,如何依法合规对铝电解大修渣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管已经是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1 铝电解大修渣环保管理现状
1998年之前,我国没有标准和规范定性电解槽大修渣性质;而在1998年出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1998版)后,国家明确将含无机氟化物的废物(氟化钠等)列入危险废物名录,但尚未将电解槽大修渣列入危险废物名录;2008年修订了危险废物名录,即《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08版),将粗铝精炼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电解电池列列入危险废物名录;直至2016年国家再次修订危险废物名录,才将电解铝过程中电解槽维修及废弃产生的废渣明确列入。
1998年后至2016年前建成的电解铝企业大多根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通过浸出试验类比分析数据,将铝电解大修渣比照危险废物管控要求进行项目设计、处置及管理。2016年以后建成的电解铝企业已明确将大修渣按照危险废物开展“三同时”工作。
按照“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国内外对铝电解大修渣的处置技术进行了不懈的研发和推广。目前对铝电解大修渣(含铝电解废阴极炭块及废耐火材料两部分)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火法、湿法、临时堆存、填埋和外委危废中心等[3]。其中火法技术主要包括高温除炭加酸法回收氟、化学弥散固定法、等离子焚烧法、回转窑烧结法等;湿法技术包括浮选法、硫酸分解法、高温水解法、碱液浸出法、碱液加石灰分解法等。
2 铝电解大修渣管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铝电解大修渣管控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2.1 配套基础设施弱
随着我国电解铝行业的快速发展,全国电解铝产量从2015年的3 141万t上涨到2019年的3 504万t,铝电解大修渣的产生量也随之迅速增长,涨幅超11%。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对新建大修渣贮存场所的行政许可收紧,大修渣年产生量的不断增长对现有渣场的库容冲击较大,存在超库容、无地贮存的风险。部分企业所在地方或工业聚集区普遍存在危废处理能力不足、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地区危废处置能力缺口较大,大部分依赖外运转移处理,甚至部分地区无危废处理处置设施,危废处置全部依赖转移外地处置。
2.2 缺乏成熟经济稳定且可持续的处置技术
虽然大修渣的处置技术实现了多样化甚至获得了工业化实验和应用,但火法技术投资大、资源利用率低;湿法技术需要对废阴极炭块进行有效破碎,大多数仍然停留在对废耐火材的处置;外委危废中心处理的费用高昂,个别地区可高达5 000元/t,企业生产成本难以负担。以上情况导致铝电解大修渣实际无害化和资源化比例并不高,大量仍以贮存或是填埋的形式处置。无论是贮存还是填埋,都将存在长期的生态环境污染风险,且占用大量土地资源,渣场的基建和日常运行管理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并不是持续经济可行的处置手段。
2.3 缺乏技术规范标准的引导
自2016年我国将电解铝大修渣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后,大修渣处置配套的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和最佳利用技术等没有及时发布,企业在大量尝试资源化和无害化后,各地区环保主管部门对大修渣处置后残渣的属性认定存在显著执法差异。
2.4 协同处置和利用难
电解铝大修渣的产生存在周期性,单个企业单一年份大修渣的产生量可能较小,每个企业都对应配套处理或利用生产线将面临处理能力不能高效发挥、重复投资等诸多问题。尤其是集团公司内部不同法人单位间的电解铝生产企业,生产工艺类似,但因为跨省转移手续审批时间长难度大,而且不同法人间协同处理存在没有危废经营许可证等问题,大修渣的协同处理利用开展困难。
3 环境风险管控建议
按照新固废法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和全过程管控的立法思路,企业需要从铝电解大修渣的减量化上下功夫,建立起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各环节相应的责任制度,大力研发和推广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可行技术路线和方案,依法合规进行铝电解大修渣的环境风险管控和处置。
3.1 源头开展减量化
从铝电解大修渣产生环节可知,延长铝电解槽的使用寿命,可从根本上减少槽大修的频次,从而减少铝电解大修渣的产生量。根据郑冬[4]和王强华[5]等人的科研成果,企业可从源头上对阳极质量严格把关,减少炭块开裂和脱落,进而有效降低效应系数;正常生产过程中对电解槽的槽温、电流强度、分子比进行稳定控制,保持电解槽稳定的热平衡和槽膛内形,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铝电解槽的焙烧、启动工艺和阳极更换、出铝、抬母线、熄灭阳极效益作业等,有效延长铝电解槽的使用寿命。
3.2 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责任
新固废法明确要求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且对涉及到危险废物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惩重罚,不仅提高了涉事单位的处罚金额上限,还对除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外的单位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责任人员追究责任和处罚。由此可见,铝电解大修渣的环境风险管控,不是单一部门或个人的责任,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全过程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明确各环节管理的具体责任人,在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明确各环节应采取的污染防治和应急处置措施。
3.3 全过程管理合规化
电解铝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铝电解大修渣的管理计划,建立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铝电解大修渣的产生量、运输、贮存和处置等信息。在大修渣收集、贮存(含临时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的设施和场所规范设置危险废物标识。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和危废经营许可制度,在委托第三方处置大修渣前,严格核实其危废经营许可证等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依法签订书面处置合同,并在合同中对污染防治要求进行约定,避免因委托的第三方违法违规处置大修渣带来的法律连带责任。
3.4 推进技术攻关和协同处置规模化信息化
鼓励企业特别是大型集团公司类企业,通过产学研结合和国际合作交流等方式,大力推进大修渣处置专项技术攻关,及时了解、跟踪国外危废管理利用处置经验和新动向,积极消化吸收。探索跨行业协同发展,挖掘已有设施的处置潜能,如开展燃煤锅炉协同处置技术、钢铁等行业冶炼窑炉焚烧处置技术和水泥窑协同处置范围拓展的研究。支持大修渣利用处置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开发和推广。
鼓励集团公司实行跨区域统筹布局大修渣处置能力,加强集团内成员企业间大修渣集中处置合作,减少处置生产线的重复资金投入,提高单一处置生产线的产能利用率,并可借助大数据云平台信息化系统,做到大修渣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和处置全过程信息可共享、可追溯,助力跨区域企业间大修渣处置能力的共享合作。
3.5 合理预提大修渣处置费用
近年来,电解铝企业多向清洁能源优势明显的区域和环境容量大的区域转移,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关停并转时有发生。在兼并重组前的尽职调查中,应将生态环境内容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将大修渣处置费用计入收购成本;在关停并转电解铝企业过程中,应合理预提大修渣的处置费用,为大修渣场的退役或大修渣外委处置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3.6 积极为相关政策制修订提供技术和实践支撑
我国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已编制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稿)》(二次征求意见稿)[6]、《危险废物环境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7]等危险废物相关的法规文件征求意见稿;同时委托行业协会牵头编制铝冶炼行业危废环境管理指南、电解槽大修渣和铝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等技术规范和指南。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将深刻地影响企业铝电解大修渣的处置路线、管控方式和费用成本,企业可通过生态环境部官网和行业协会等途径,积极反馈意见和建议,为铝电解大修渣相关政策的制修定提供更夯实的技术和实践基础数据支持;探讨铝电解大修渣经济可行的利用处置方式,为大修渣找到合理出路;协助政府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理清大修渣产生节点、产污系数及利用处置方式,找到重点监管环节,统一各地的生态执法监管标准,从而进一步提升铝行业危废规范化管理水平。
4 结束语
铝电解大修渣依法合规有效处置需要企业时刻牢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推动大修渣环境风险管控工作再提质、再提档、再提效;同时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标准和规范的配套出台以及科研院所的相关技术攻关。总之,铝电解大修渣的环境风险管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