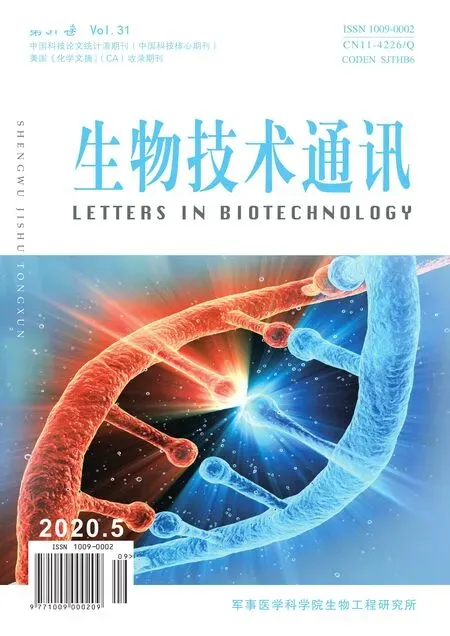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的研究进展
杨阳,赵玲,杨宗璐,柯亭羽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云南 昆明 650101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是一种流行性代谢性疾病,会严重损害患者的生活质量。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全世界每年有150万人死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是发达国家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1],到2030年,糖尿病的发病率预计约为3.66亿[2]。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大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神经病变等。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是一种蛋白多肽物质,可诱导细胞增殖、分化、存活和迁移以及维持细胞功能[3]。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病机制极其复杂,目前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很多研究发现IGF-1参与DM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本文主要介绍IGF-1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的研究进展。
1 IGF-1在糖尿病中的研究
DM患者血清中许多凝血因子的浓度是增加的,使患者机体处于高凝状态,这些凝血因子主要通过促进Ca2+的动员增加血小板反应性。最近发现来自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高水平血小板表达可以活化P2Y12受体[4],使得DM患者血栓形成风险增加。IGF-1以内分泌、旁分泌或自分泌方式通过IGF-1受体/胰岛素受体底物/磷酸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途径作用于血小板,最近发现血小板也可以通过存在于血小板表面的α5β1整合素特异性结合IGF结合蛋白3、IGF结合蛋白1,从而使IGF-1更加接近IGF-1受体[5]。由于IGF结合蛋白3、IGF结合蛋白1与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的相互作用,IGF-1的局部浓度可进一步增加[6]。一项关于IGF-1对糖尿病小鼠血小板的影响研究发现IGF-1能增强小鼠血小板的活化[7]。最近,一项研究探究了IGF-1对控制不佳的T2DM人体内分离的血小板的影响[8]。该研究用125I分别标记IGF-1和胰岛素,发现125I标记的IGF-1和胰岛素均与分离的血小板结合,125I标记的IGF-1与T2DM患者血小板的结合明显大于健康个体的血小板;健康人群中血小板结合IGF-1和结合胰岛素的相对比值为1.87,而DM2患者结合IGF-1与胰岛素的相对比值为4.97,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8]。这些实验数据间接表明,血小板对外源性IGF-1的敏感性高于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并且这种影响在糖尿病患者中比健康人更明显。该研究还发现外源性IGF-1增加了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凝集的初始速率,并且在T2DM中这种作用明显更为明显[8],提示循环中IGF-1的浓度可能是影响糖尿病患者血小板活化的因素之一。然而,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来研究IGF-1在与糖尿病相关的血栓性并发症中的潜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小组发现IGF-1和糖尿病患者血液中HbA1c浓度之间存在弱正相关,这反映了T2DM的严重性可能与IGF-1的作用有关,由于糖化血红蛋白通常用于监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因此研究HbA1c含量与IGF-1对血小板聚集作用之间可能的相关性似乎是合理的。IGF-1除了可以参与细胞生长、分化、迁移外,还可以促进伤口愈合,其与IGF-1R结合受损会导致DM患者皮肤损伤的修复延迟[9]。研究发现低水平的IGF结合蛋白1与患DM风险增加有关,并且低水平的IGF结合蛋白1可以预测老年人患DM的风险[10],这可能是因为IGF结合蛋白1会迅速调节游离IGF-1的可用性,增强胰岛素敏感性[11],从而使高IGF结合蛋白1对糖尿病具有保护作用。
研究发现成功移植胚胎棕色脂肪组织(brown adipose tissue,BAT)的糖尿病小鼠血浆中血糖恢复正常并且使IGF-1含量增加,而没有成功移植胚胎BAT的小鼠血浆中IGF-1进行性下降,胚胎BAT移植可以使白色脂肪显著恢复,从而使炎症减少,而胰岛素却没有增加[12],并且IGF-1在胚胎BAT中大量表达。所以成人BAT中缺乏胚胎组织中丰富的IGF-1可能是DM患者移植成人BAT失败的原因,并且BAT在健康成人中的存在及其在对抗代谢性疾病中的重要性在最近的文献中得到证实[13]。综上所述,在BAT移植早期,IGF-1的存在似乎是建立交替激素的新平衡的关键,IGF-1的增脂和抗炎特性可能会使WAT恢复,进而分泌其他胰岛素模拟脂肪因子来补偿胰岛素的功能。IGF-1也可能通过葡萄糖转运载体1和3对胰岛素非依赖性葡萄糖摄取途径直接降糖[14-15]。基于上述理论和数据,Gunawardana等将健康成年小鼠的新鲜BAT移植到1型糖尿病(T1DM)小鼠皮下,移植后施用外源性IGF-1,发现补充了IGF-1的成年BAT移植后的T1DM小鼠产生了快速且持久的正常血糖,成功率为57%,而仅接受成年BAT或仅接受IGF-1或不接受治疗的T1DM小鼠对照组没有恢复血糖[16],但相关机制在本研究中并未深入了解,后续研究可以围绕该机制展开。在T2DM中的胰岛素抵抗与IGF-1和脂联素降低有关[17],增加IGF-1和脂联素可以缓解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并且发现主要是通过包括一些胰岛素非依赖性机制实现的,虽然IGF-1或脂联素的单一疗法治疗T2DM中受到副作用的限制,包括低血糖、心动过速、水肿、面部疼痛或瘫痪等[18],但在BAT移植中这些副作用不可能发生,因为IGF-1水平的增加不是超生理的,仅仅是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考虑到在T1DM中施用外源性IGF-1是通过改变全身新陈代谢并建立新的生理平衡而起作用的治疗方法,所以涉及许多变量和未知因素,可以在大规模研究中进行测试和调整的变量包括供体年龄、从供体组织分离到移植的时间、移植部位、IGF-1剂量、IGF-1施用时间。对于T2DM需要更多研究来探讨增加IGF-1对缓解疾病的利与弊,并进行深入的机制探讨。
2 IGF-1在糖尿病相关并发症中的研究
2.1 IGF-1在糖尿病肾脏病中的研究
糖尿病肾脏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显著影响糖尿病的死亡率。DKD的特点是肾小球肥大继而硬化,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导致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和肾小管萎缩,临床上以肾小球滤过率进行性下降和蛋白尿为特征。IGF-1在啮齿动物DKD的肾脏中过度表达[19],并且发现DKD患者血清IGF-1的表达也升高,且随着DKD的进展IGF-1的表达水平更高[20]。IGF-1通过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直接或间接作用影响肾血流动力学,降低肾血管阻力和诱导肾小球内高血压,导致肾小球滤过率升高和蛋白尿的发生,足突细胞来源的IGF-1已被证明刺激细胞外基质蛋白的产生,促进肾小球硬化。IGF-1还可以通过触发AKT介导的GSK-3β磷酸化来抑制GSK-3β蛋白,从而导致Snail1的稳定和下游的促纤维化作用[21]。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了IGF-1/IGF-1受体在DKD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发现糖尿病小鼠发病16周后,DKD肾脏中IGF-1的表达升高,此外肾脏中Snail1 mRNA和蛋白的表达显著增加。抑制IGF-1R可改善糖尿病肾病的尿白蛋白排泄和肾脏组织学改变,包括肾小球肿大、炎性浸润和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抑制IGF-1R还可以有效阻止Snail1的过度表达,减轻了肾小管上皮细胞的E-钙黏蛋白和纤维连接蛋白表达的改变。体外培养的肾上皮细胞实验进一步表明IGF-1沉默明显减弱了Snail1的表达,并使肾小管上皮细胞的E-钙黏蛋白和纤维连接蛋白表达模式接近正常化。进一步的Snail1沉默可以阻止高糖诱导的改变,而不会影响IGF-1的表达,这与Snail1在IGF-1下游的作用是一致的[22]。进一步说明DKD中IGF-1的激活通过Snail1上调诱导了纤维化形成,抑制IGF-1/IGF-1R可以减轻DKA相关的组织和功能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减轻DKA的纤维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抑制IGF-1/IGF-1R这些效应从未在DKD的其他治疗方式中表现出来,例如ACE抑制剂、ARB或胰岛素。鉴于这些结果,应进一步探讨选择合适的剂量和持续时间进行治疗,以防止DKD中IGF-1的过度激活。选择合适的剂量和持续时间内阻断IGF-1的联合疗法,除了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和血糖控制外,可能会扩大治疗效果,但还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索。
2.2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中IGF-1的研究
糖尿病作为一种高血糖代谢综合征,可能导致骨代谢失衡,最终致骨丢失和骨质疏松,很多证据支持糖尿病可能导致骨代谢紊乱[23]。几项研究表明,DM导致骨丢失,降低骨机械性能,并降低成骨细胞骨形成率[24-25],并且DM患者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都显著增加[26]。有数据报道,血糖控制不佳的DM患者发生骨折的风险增加,与血糖水平控制良好的DM患者和非糖尿病患者相比,该风险增高了47%~62%[27]。糖尿病引起的骨质丢失或骨质疏松称为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diabeticosteoporosis,DOP),其特点是骨愈合和再生不良,骨折风险增加[28]。IGF可以在骨基质中产生和储存,参与了血糖的调节,并在骨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29]。IGF-1通过磷酸肌醇3激酶通路激活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的表达,从而刺激成骨细胞增殖和分化,因此IGF-1/磷酸肌醇3激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通路被认为参与了糖尿病骨质疏松的成骨细胞骨形成的调节[30]。血清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作为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在糖尿病患者中已被广泛研究,糖尿病患者中这些标志物似乎都较低,但动物研究中存在很大的异质性[31]。Xie等研究发现T2DM大鼠血清中血清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活性显著降低[32];相反Gong等[33]的研究采用高脂饲料喂养大鼠4周,然后用链脲佐菌素诱导糖尿病大鼠,注射STZ 8周后,糖尿病大鼠血清血清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水平均升高。血清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的这种变化可能与成骨细胞分泌和释放IGF-1有关,IGF-1在成骨细胞中分泌并且高度存在,但DM大鼠骨骼中IGF-1的表达显着降低,这可能导致骨吸收加速[34]。从骨基质吸收部位释放的IGF-1诱导成骨细胞的碱性磷酸酶活性,从而增加骨基质的矿化[35],随着骨吸收的增加,骨钙素也从骨基质释放到血液中,导致DOP患者和动物血液中骨钙素水平升高[26]。血清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的增加促进了骨矿物质的过度积累;另一方面,高血糖抑制了骨桥蛋白等骨基质蛋白的合成。这种骨矿物质的过度积累和基质蛋白的失衡最终导致更高的骨折风险[28]。植物化学和药理研究表明,地黄具有抗糖尿病、抗骨质疏松、抗血液病和妇科疾病等多种生物活性[36],可能是通过上调IGF-1/磷酸肌醇3激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途径实现的[33]。需要更多研究探究糖尿病大鼠血清中血清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变化与IGF-1的关系。
2.3 IGF-1在糖尿病周围性多发性神经病中的研究
糖尿病多发性周围神经病(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是DM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长期的高血糖症会导致晚期糖基化终产物的积累,对周围和中枢神经系统肌细胞和神经元的线粒体功能和氨基酸代谢产生有害影响[37]。DPN的临床病理特征包括痛觉异常、痛觉过敏、节段性脱髓鞘所致的神经纤维异常或感觉丧失、轴突变性和神经纤维丢失[38]。除了肝脏外,神经组织是产生IGF-1的第二来源[39],IGF-1还被认为是控制肌肉生长的肌动蛋白,在维持神经肌肉系统的正常功能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40]。胰岛素信号和IGF-1有关的神经营养支持受损被认为是糖尿病神经退行性变的原因[41]。除了在神经系统发育和婴儿出生后早期生长中的关键作用外,IGF-1还促进感觉、运动和交感神经元的轴突生长。此外,施旺细胞还需要IGF-1和IGF-1R信号来维持生存、运动、细胞增殖、表型重塑和髓鞘形成。在DM动物模型中,发现背根神经节存在神经营养因子信号转导、AMP依赖的蛋白激酶活性和线粒体功能受损,而DM大鼠全身注射IGF-1可显著提高感觉神经再生率,其激活AMP依赖的蛋白激酶,从而增强DM大鼠感觉神经元线粒体功能和纠正神经元代谢[40]。Zebrowska等的研究表明,T1DM患者中等强度连续运动可能更有效地增加IGF-1的可用性,从而可能有助于更有效地控制血糖[42]。研究发现小檗碱对DPN有明显的神经保护作用,可能是由于它能上调坐骨神经IGF-1 mRNA水平而实现的[43]。
2.4 IGF-1在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障碍中的研究
近年来,T2DM相关的认知障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认知功能障碍也被认为是糖尿病的慢性神经系统并发症。轻度认知障碍被认为是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过渡阶段,其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增加。流行病学和基础研究表明,T2DM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学[44]。然而,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障碍的潜在机制是复杂的,尚未被完全阐明。IGF-1在各种中枢和外周组织的分化、增殖和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45]。以前的研究表明,低IGF-1水平可能与老年人认知功能差有关[46],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血清IGF-1水平会发生变化并且IGF-1还可以预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功能[47]。然而,相关研究数据并不全一致。最近的一项研究就指出,IGF-1浓度并不能为认知能力下降的患者提供额外的诊断信息[48]。有研究证明,维生素D可能影响IGF-1的合成和/或活性[49],并且维生素D缺乏与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高风险之间存在联系。因此,维生素D、IGF-1及其与糖尿病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需要更多的研究。25(OH)D是维生素D代谢中间产物,有研究将T2DM病患者分为轻度认知障碍组和正常认知组,测定并比较IGF-1和25(OH)D水平,分析IGF-1、25(OH)D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轻度认知障碍组IGF-1和25(OH)D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50]。以上研究表明IGF-1可能在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障碍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需要进一步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
3 结语
综上所述,DM及其并发症的发病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升高,这就迫切需要更深入地研究DM及其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从而研发针对性药物,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已有研究发现IGF-1在DOP、DPN、DM相关认知功能障碍中是一种保护因素,但在DKA中,IGF-1的激活诱导了DKA肾脏的纤维化,抑制IGF-1/IGF-1R可以减轻DKA相关的组织和功能改变。国内外关于IGF-1在DM和DM并发症中的研究有限,因此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IGF-1有望成为改善DM及其并发症的治疗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