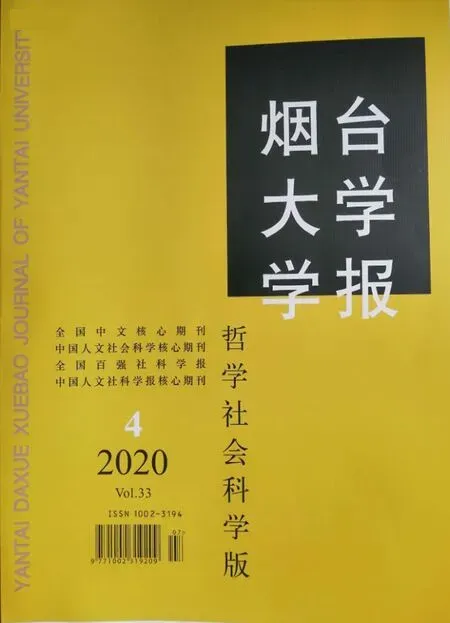“体”的困惑
丁金国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一、“体”的释义
“体”在汉语里,是个多义歧解的词。《辞源》给出11个义项,33个复音组合;《辞海》给出了16个义项,32个复音组合;《现代汉语大词典》给出了13个义项,54个复音组合;《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7个义项,49个复音组合。基础义项均源自古代典籍,指人的手足、四肢,赅而指首、身、手、足的人体总称,抽象化为体魄、体质、体态、体型、体势、体力等。由人“整体”义中转指物的整体总称或其部分,并由此引申出形体或形状,进而又衍生出格式、规矩。从格式、规矩等义项,衍化出专用于言语表达上的“体式”“体制”“体貌”“体裁”“体势”“体性”等。“体”的意义不断孳生,引发出我们对词义演变规律和方式的思考。那些与人体最近的相关概念,都先行孳生或转化。从《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礼记·大学》“身广体胖”,都清晰地指明人的身体。由于人是理性有机体,故而经由心理认知过程衍生出与人体相关的动作义项,如:体验、体谅、体悟、体察、体会、体认、体恤、体究等。这些动作性的认知活动,进而凝结为带有特定涵义的言语,因而有“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易·系辞下》),从“辞寡”“辞多”等评价性话语,体认出“辞尚体要”(《尚书·毕命》)的命题。“辞尚体要”者,指政务或个体,为文发语应切中要义而论之。辞者既然要中规中矩,那么言语或语篇必定有规矩可鉴衡,故而派生出一系列与语言行为相关的“规矩”,即体式、体制、体貌、体裁、体势、体性等。“体要”源自“体统”,进而又化出“大体”“大要”。单音“体”,在复音化的过程中,随着不断增加的义项,其活动空间也随之扩展。如前置“体”,变为后置,其言语性义项就有文体、语体、辞体等,话语里有“散体”“韵体”“赋体”“骚体”,甚至有齐梁体、唐宋体等不一而足。最早以“体”来描述语文现象的是刘勰,《文心雕龙·附会》有言:“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仅就“体”的言语性义而言,可归为三种情况:一是从语篇的结构方式归类,有体裁、体制、体式;二是从语篇的功能类型归类,如语体、文体、辞体;三是从语篇外显审美形态归类,如体貌、体势、体性等。从审美形态所概括出来的概念,其上位都可以用“风格”来概括。从风格的语义类聚中,又触发出“风貌”“风韵”“风致”“风姿”“风骚”“风骨”。与言语相关的“体”概念如此众多,学界对其诠释,自然存在着公婆之见。这种众说纷纭的学术形态,虽有利于学术生态的活性游动,但也无可否认,阻碍着现代汉语语体与风格研究的进程,既不利于语言科学的发展,也延缓了本学科对语用实践和语文教育作用的发挥。
二、析“体”的大家
上述以“体”为核心的各言语项,其之间的关系和涵义的阐释,历朝都有人做过。然史上对其梳理用功最勤者,笔者认为古代有刘勰,现代有陈望道,当代有童庆炳。
童庆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其对“体”及与“体”相关概念的研究,自然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这一重要的言语现象。童先生在其《文体与文体的创造》(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提出的体系是以文体为统领,下辖体裁、语体、风格,三者与文体之间关系是有序的,文体是上位,顺次是体裁、语体、风格。童庆炳对“文体”的界定是:“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童庆炳的定义,实际上有两个层次:底层是由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表层是附着在文本体式之上的著作者独特的内在认知结构及其所营造的社会历史风貌。文本体式是由物质性的语言所营造,正是通过这一物质形式,展现出作家的认知结构和社会历史形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童庆炳的意识里,文体分广狭二义,狭义即专指文学文体。文学文体是一个层级体系:由体裁、语体和风格逐次构成。各层次间递次相接,组成一个连续统。体裁是基础,风格则位在连续统的顶端,文体就是凭借这一连续统得以显现。只有文学体裁的语篇,才有文体问题,非文学体裁语篇,则根本登不上“文体”的殿堂,因为非文学语篇无风格可言。既然文体是由体裁、语体和风格构成的连续统,没有风格自然也就没有文体。既然风格这一重要范畴不具有普遍性,那么由风格构成的文体,自然也就没有普遍性。可见,在童庆炳先生那里,文体是个非遍指性概念。所以他特别强调:只有具备“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的作家和批评家,其作品才具有文体。
体裁是童庆炳文体层级体系中的第一层级,他认为“这一层次的问题并不复杂”,故未作发挥,只作了粗略点评,但用了大量篇幅述介了从《尚书》以降至民初的梁启超两千多年的体裁发展史。中国确乎是文体大国,从《尚书》始,所论均在体裁、体制,重点论述体裁的意义及体裁明辨和体裁的分类。作为体裁理论,源于《尚书》的六类,接踵于《诗经》《尚书》的二分,崛起于两汉,繁荣于六朝。尽管所归体制,由二及十、百,文体论从未离开过文章的体制。体裁既然附着于物质性的语篇,所以论者称之为“文本体式”。从现代语篇学来讲,体式的差异取决于语篇结构的不同构式。通常,“构式”由四个主干成分所组成:起、承、转、合。起承转合的变化,必然引起体式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体裁。
第二层级体系是语体,童庆炳在论述体裁时,点评为“规范”,这无疑是正确的。及到语体,则用了“创造”一语,这就意味着,体裁是已存言语事实,研究者只是对其“规范”而已,而语体则不然,是语用者在语篇制作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非语篇固有。童庆炳认为古代对“体”的研究,内涵跨度太大,从体裁一下子就跨越到风格,缺少中间概念,没把“文体”说清楚,故而提出了“文体风格”这一概念来接济。我们认为,所谓“文体风格”古人从未提出过,据查,此概念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外语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短暂流行过,实际上其所指依然是语体。童庆炳说,“最早把体裁和语体联系起来考虑的是《周礼》”,及至《诗大序》提出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三种体裁,赋比兴则是语体,赋为叙述语体,比为明喻语体,兴为象征语体。曹丕《典论·论文》中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四科八体。八体是八种不同的体裁,对应四科“雅、理、实、丽”是不同的语体。步其迹的陆机《文赋》列出十体依然是体裁与语体的对应关系。童庆炳赞曰:“曹丕、陆机等人把‘体’、‘文体’分为体裁和语体两个层次,并且又把两个层次联系起来,揭示体裁要跟语体相匹配的规律,这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功不可没。”(2)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26页。
对童先生的“语体论”,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思考:一是语体概念,分为广义语体与文学语体。广义语体是一种规范语体。规范语体作为一种成规,是一种保守力量,一种惰性。文学语体是一种自由语体。它不受成规约束,由语篇制作者因个性不同而不同,时时在更新、创造,它已是一种准风格,成熟的风格就产生其中,是体裁向风格过渡的一种语言形态。既然是过渡,而且表现千姿百态,“自由”到了只能意会的地步,还到哪里去找语体呢?二是关于风雅颂赋比兴的结论。笔者认为“风雅颂”其体裁均为“诗”,是《诗》的第二层级的功能或语域分类,自然可理解为功能类型或功能语体,而非体裁。赋比兴则不然,赋者,系指言语过程中的铺排方式;比者,即比喻之意,用比喻的方式发言表语;兴者,系以象征的方式表情达意。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借“关雎”达“男女婚恋之意”,是典型的言语表达,连语体的影子都没有。三是曹丕的“四科八体”和陆机的“十科十体”之论。曹、陆的“科”均指体裁,而其“体”,绝非语体之意,是特定体裁所要求的审美形态,所谓“奏议宜雅……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论精微而畅朗”。“雅”“丽”“绮靡”“畅朗”都是各体的语篇风格,与语体无涉。魏晋时期虽学界公认是理论觉醒的时代,但无论曹丕、陆机抑或刘勰、萧统,他们尚缺语体观念,只有风格意识,但其体裁自觉却非常强烈。说彼时语体如何如何,显然有点强加于古人。
第三层级体系是风格,童先生认为:“风格是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作品内容与形式统一中的体现”,“语体若想完全成熟,就必然转化为对文体的最高和最后范畴——风格的追求”(3)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30-31页。。由此,他咬定:风格是文体完全成熟的标志,是文体的最高体现,没有风格的作家和作品,也就谈不上文体。童先生的这段论述里,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疑问:语体如何才能完全成熟?如何成熟到风格的境界,风格又如何成熟到抵达文体的水平?可见,童庆炳的论述只是个理论假设。所谓“风格是文体完全成熟的标志,是文体的最高体现,没有风格的作家和作品,也就谈不上文体”。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风格是普遍存在于语篇之中,还是只有成熟的作家作品才有风格可论?我们认为风格普遍存在于言语活动之中,即使是插科打诨、打油俳语之类,也都毫无例外有风格伴随,所以,风格存在的确定性只有形态上的差异,不存在有无;二是风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应该说风格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说其是主观的,是因为风格的决定性要素是创作主体,主体的智能结构和社会经历决定着语篇的审美形态;然风格还有客观性的一面,任何风格都要接受言语社群所俗成的规约,即所谓的社会性,另外还有接受者个体的价值选择,以及话语发生的临境生态。凡此种种,都对语篇风格具有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
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积极改革者、现代修辞学的开创者和现代语体风格学的倡导者。陈望道先生对“体”相关问题的研究,自然着眼于语文教育和言语实践。在八股取士制度消亡、新的为文论道的语篇体制构建之际,先生应莘莘学子和芸芸众生的要求,在新旧语文教育体制转换之际,连续写作了三部著作:《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和《修辞学发凡》(4)三著均见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陈光磊等编:《陈望道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作文法讲义》最先于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连载,1922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该书的基本框架是:结构、体制、美质。结构从词始,逐次词——句——段及篇;体制,依据旨趣和功能,将语篇的体制分为:记载、记叙、解释、论辩、诱导等五类;美质是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分类,分为:明晰、遒劲、流畅三类。结构承嗣王充以降的传统,以组字成句,组句成章,联章成篇的格局铺开。体制是在整理传统语篇理论中的言语方式基础上,吸收了外国作文法中的有用的东西,提出五分体制。与当代理论比较:记叙即记叙或叙述,记载是“记载人与物底形状与性质”,可以并入记叙中;解释即说明;论辩即议论;诱导可归为抒情。美质是将《文心雕龙》风格论的四科八体,总括为三,其意不在建立理论体系,而在利于语文实践。
《美学概论》首次将语言运用中的言语,纳入“美”的哲学境界来审视,将修辞风格现象,站在美学的高度来评议,是修辞研究的新视角。全书七章,始于“美及美学”等基本概念的阐释,收于美的类型的“审美判断”。
1932年《修辞学发凡》问世,该书将《作文法讲义》中的语文体制,改为“三种境界”:记叙的境界、表现的境界和糅合的境界。三种境界囊括了五种体制,意在突显修辞的两大分野:积极和消极。将《作文法讲义》中的美质,专设第十一篇“文体与辞体”。目的在于深入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格学。
语体与风格问题是陈望道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夙愿。陈先生对语体风格的“钟情”,源于对民族语文的深度钟爱。他17岁时(1907)走出庠塾就创乡学,启蒙幼童,开始了其语文教育生涯。从1919年起,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师范(1919)、复旦大学(1920)、上海大学(1923-1927),抗战爆发后,辗转广西大学(1931)及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1945年随复旦回上海,此后就一直在复旦执教直至逝世。除耕耘于杏坛外,还参与各个层级的语文教材的编撰。1931年陈先生与傅东华联手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了初中《国文》课本。 统领课文的是记叙、说明、议论、描写的语文体式。这就意味着“语体为先”的思想,已开始进入语文教学。1934年与叶圣陶、夏丏尊、宋云彬合作,编写了一套专供青少年自学的中级《开明国文讲义》,仍以语文体式为先,科普文与应用文酌量选入,更有“史话”、“文话”、写作技巧和文章风格的讲解。直到上世纪末,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还争相再版此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语体与风格对于语文教育和言语活动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故才使陈望道先生投注几乎是毕生的精力来探究。其探究的轨迹,从《修辞学发凡》第十一篇标题的屡次修改中,显现得一清二楚。《修辞学发凡》1932年初版时的篇目为“语文的体类”,1945版改为“辞白的体类”,1954年上海新文艺版易为“语文的体式”,1959年上海文艺版变更为“文体或辞体”,并指出“文体或辞体就是语文的体式”。在1954年变动时,并特别加注说“语文的体式就是语文的类型”。所谓“语文的类型”,就是“语文的体式”;“语文的体式”,也就是文体或语体。陈望道认为,文体或语体已经被辨体者“辨”得琐碎混乱不堪,故索性称为语文的体式。从《修辞学发凡》“语文的体类”“辞白的体类”“语文的体式”到“文体或辞体”的四次变更中,不难看出陈望道先生对此问题的纠结,直到晚年,对此类语文现象,如何作理论界定,仍处在深探潜索中。窃以为,陈先生之所以反复斟酌更换篇目,是在寻找更贴近汉语语用事实、更能全面反映与继承魏晋以来传统语体风格论的精华、更能统摄语篇理论整体的概念。
语篇理论整体指哪些,《作文法讲义》开篇即点出:构造、体制、美质。《修辞学发凡》是《作文法讲义》宗旨的延续。《作文法讲义》的“构造”,由《修辞学发凡》的“消极修辞”续释,“体制和美质”则由“文体或辞体”来接续阐发。由此可征:一方面反映了陈望道治学的精细,另一方面则映透出作者对语篇全局性的深度思考。就所论内容而言,如果说“文体或辞体”指的是“语文体式”,在逻辑上应与《作文法讲义》中的“体制”对接,因为二者都是着眼于语篇的形式结构。然而使我们感到错愕的是,《修辞学发凡》在“文体或辞体”的题目下,其内容却转而从审美形态入手,沿着刘勰的“体性”分类框架,将“体”分为简约与繁丰、刚健与柔婉、平淡与绚烂、严谨与疏放。为什么会有如此转向?这八体既非体裁的“体”,也非语体的语境功能类型,是实实在在的可感可知的美质,为什么不直接用“美质”或“风格”来界定,仍采用“文体或辞体”为题?作为专攻语篇修辞现象的专家,对《文心雕龙》以来对风格现象的各种论述,了如指掌,心如明镜,然而又为何避而不谈“风格”?窃以为,陈先生不谈论“风格”,可能因为“风格”已被阐释得更“繁繁琐琐”,既可用以解释人的品格,也可用以解释物的形态风貌,还可用以描述一切艺术体貌和风采,坊间大众对其既熟悉又陌生,易于引起歧解,故而缄口不谈风格问题。避开“风格”设置“体性品类”,目的在于服务于语文教育。为达立意宗旨,着力解决“意会”与“言传”这对经典性的悖论。陈望道认为:“凡是可以意会的一定可以言传。”研究修辞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意会与言传的问题。对于解决的途径, 陈望道先生的方略是:语言化、科学化。语言化就是从现实语篇的语言构成各要素间,寻找具有特征性的语言表现;科学化是在语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具象性的语辞进行物质化分析,用语义特征理论作微观透析。传统的风格论经姚鼐的发挥,刚柔两极对立几乎已成定论,步其踵者均从表现体性的物质要素中寻求不同范畴间的差异。为此,陈望道先生在传统刚柔两极对照映像中建立起陈望道风格体系,对各范畴确立的标准,则明确予以标注:
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分为简约和繁丰;
由气象的刚强和柔和,分为刚健和柔婉;
由于话里词藻的多少,分为平淡和绚丽;
由于检点功夫的多少,分为谨严和疏放。
两极对立,就语品而言本无优劣可论。所谓“对立”,“只是假定的两个极端或两种倾向”,实际上现实语篇中的风格形态多是位于两极之间广阔的中间带。陈望道先生在嗣承《文心雕龙》《诗品》之绪,何以从众多的风格范畴中,选择此八品来构组《修辞学发凡》的体系?窃以为陈老是经过了认真慎重地甄选,一是与现实社会语文形态相契合,切实反映社会语文形态的状况;二是更利于普罗大众能从物质性的语言中,尤其是极性对照中,学到语文实践的知识和能力。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苏联曾进行过历时三年的风格大讨论,内容涉及语言风格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全民风格与个体风格、体裁与艺术风格的关系、划分风格原则及风格类型等一系列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的语言学家开始将“大讨论”的信息陆续介绍到中国。并于1960年始,由中国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语言风格与风格学论文选译》(5)苏旋等译:《语体风格与风格学论文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编译者在“译序”中写道:“尽管我国语言学家注意到语言风格问题对改进文风所能起的作用,我们却不知道如何研究语言风格问题,因为我们还缺乏对语言风格问题的科学知识。”陈望道先生受“中国缺乏科学风格论”言论的激惹,愤而疾呼:中国不仅有,且比外国的久而深!故从六十年代起,在课堂、研究室或辅导研究生等多种场合开始谈论风格问题。其所论内容,依据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陈光磊等编辑的《陈望道文集》(6)陈光磊等编:《陈望道文集》第二卷,1980年。,讨论了如下内容:
(1)“风格是修辞特点的综合表现”,对于汉语修辞研究与言语运用意义重大;
(2)“我国古代关于风格的研究材料,是我们丰富的修辞学遗产当中一宗宝贵的财富”;
(3)我们对“风格的问题还研究得很不够”,需要加强,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亟盼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的语体风格学;
(4)研究方向“要从篇章着眼”。
陈望道先生的有关风格问题的历次讲话,为汉语风格学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就是:中国特色,科学性,从语篇入手,逐次进行,最终建立自己特色的体系。何谓“自己特色”,我们认为,即揭示汉语风格存在形态和运行方式的本质要素:a.语体、风格依存的理论形态;b.阴阳对立的风格体系;c.以象表义的阐释手段。在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优秀东西,逐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论体系。
为什么抓着语体风格不放,是因为风格是修辞特点的综合表现,也就是说,要把修辞问题说清楚,就必须抓着这个综合特点。纵观陈望道先生的修辞理论,要害是在《修辞学发凡》中未出场的“语体风格”。
刘勰是世所公认的大家,是古典文论集大成者、汉语修辞理论开山之祖、汉语文体论的奠基者。刘勰于公元501—502年间写就的《文心雕龙》(7)本文所论《文心雕龙》均凭借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被赞为“深得文理”(沈约),“议论精凿”(胡应麟),“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心雕龙》以其博大精深熔史、论、评为一炉的特征崛然于世,为汉语语篇学、修辞学和语体风格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名副其实的汉语语篇学的开创者。“体”作为《文心雕龙》的核心,主导着三万余言五十章的巨制运行。在刘勰心目中的“体”,即现代的语体、体裁、文类、体式、文体、语类、风格和体制。《文心雕龙》全书从体类角度说“体”,初略计之有一百四十七处。把“设情以位体”置于“履端于始”。在华夏语篇研究史上,虽此前有墨子的“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其类,则必困矣”(《墨子·大取》四十四)的议论,但如此明确地提出“位体为先”的言论,则是首次。在刘勰的意识里,体类是毂轴,是枢纽,《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二十一篇是分门别类谈论各体语类。分别是: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以今人的眼光看,属纯正文学论,只有辨骚、明诗、乐府、诠赋四篇;杂文、谐隐,从愉悦性情来说,亦应归入文学论里;史传、诸子属社会教化,余者均可归入应用语类里。刘勰在《熔裁》篇里,特别提出制篇三准则:首先“设情以位体”即根据内容选择合适的体类;其次“酌事以取类”选择切合体类的事例;最后则“撮辞举要”以凸显语篇的要义。《知音》再次强调“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即为题旨置厝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与特定语类相适应。
刘勰所处的时代,“风格”用来阐释审美形态虽已显现,但刘氏并未采用,而代之以“体性”“体貌”“体势”“风骨”等来指称风格类型。
《文心雕龙》有三篇专论语篇风格,分别是《体性》、《定势》和《风骨》。虽三篇都在论风格,然各有专司,内在关联。
《体性》集中论述风格的发生,以及语篇主体个性要素对风格发生的能动作用,认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拟,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尽管“笔区云谲,文苑波诡”,鉴于主体生存客体的同一性和生理结构的相似性,人们在长期言语活动中自然趋归为类型化。“体性”实际上是个复合概念,“体”者,存在于言语社群集体意识中的言语体式;“性”者,指表达者个体在言语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由个体性情所决定的语篇风格。故而“体性”涵括了语体和风格,将其仅释为风格之意,显然失之偏颇。“体”最早用以论文说语的是曹丕,《典论·论文》认为“文非一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进而确认“体有万殊”,其原因是客观世界“物无一量”(《文赋》)。可见,这种“体”,不为个体所左右,是一种客观的为言语社群所公认的体裁类型。由体裁决定风格的命题,到刘勰《体性》篇中,始将“体”所对应的风格作了系统化整理,单独抽出来创建为汉语风格论体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并作了正负相对的处理: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指出“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这就说明,八体是总其统分,各体均可变乃至于无穷。
《定势》与《体性》不同,集中强调的是语篇风格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定势》开篇就提出:“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以题旨情趣要求,选择与之相谐的体裁;而特定的体裁,有与之相适应的“势”(即风格)。可见,势不自成,随体而立,以体定势,势不离体。所谓“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就是对体裁制约风格的论证。“循体成势”重在对风格形成的客观要素的剖析,因为不同的体类,其自身要求语篇制作者必须顺应本体所需的风格。“体”既然有社会性,故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对体裁虽无专论,但其对34种体裁的分述(《文心雕龙》中,体裁专列篇目二十一,余者遍散于其中),已将各类体裁的源流、特征、演变以及体势表征等讲述得一清二楚。《体性》《定势》篇中的所谓“体”实际上是一个存在于言语社群的一类语篇所显示出来的气势、格调,这种气势格调所凝结的是个体与社群、客观与主观、语体与风格的精髓;一个则重在强调个体才、气、学、习主观因素的差异,因此形成的风格也就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的无穷多样化。
《风骨》篇云:“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 黄侃认为刘勰之于风骨界定,皆“假于物以为喻”,从譬喻中黄氏推导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即“舍辞意而别求风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与黄氏意见相左者,在学界可以十计之。笔者认为,黄侃先生所论切中“风骨”肯綮。《风骨》篇意在强调“辞意”,辞意即语篇的语义结构,风格之所以得以形成,全在语篇的语义结构的主导作用。风骨与风格的关系,既非同位异称,亦非下位类型,而是为一切风格所含有的一种“含量”。刘勰加意赞誉的阳刚类,诸如雄健、旷达、典雅、遒劲、挺拔等气清骨峻的风格,其风骨含量就高;相对繁缛、新奇、轻靡、远奥等或“风藻克瞻,风骨不飞”,或“瘠义肥辞,无骨之征”,其病在“腴辞弗剪,颇累文骨”(《文心雕龙·时序》),其风骨含量自然就低。
在刘勰风格论中,风格是上位概念,其下单体有气、势、风、调、力等;合体有气势、风气、风力、风骨、体势、格调等。“风格”作为集合概念,指语篇的整体风貌,是一种形态,那么支撑形态的构架的要素里就有“骨”,即语篇得以构成的物质要素。核心是语篇各层次的物质结构,正是这物质结构背后的深层语义及其不同的构成方式而造就了形态各异的风格。纵观刘勰的体类论,其内部系统是:上位是体类,即所谓“位体”,体类下辖体裁、体性、体势和风骨。在这个体系里基础是语篇,语篇由具体的体裁所置厝,体裁进入语篇后,则必定“因情立体”“循体成势”,形成特定的体性和体势。刘勰没有专论“体裁”,而是将其分布在各篇章里,尤其是“论文述笔”,则是就各体语篇进行论述。体性、体势、风骨则有专篇论述。体性、体势和风骨对于具体的语篇来说,不是有无,而是潜入其中,游走于语篇始终,以其特有的“筋骨”主导着语篇运行的始终。
三、“体”的集解
上述所介绍的方家,分别代表了中国的文艺理论、语文教育和语体修辞及古典文论界。在当代的学术论坛上,不应缺略的还有翻译界。此界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在关注翻译中的风格问题。其对语体与风格的释解,也很值得注意。
远在1963年,中国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就发表了《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8)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年,第111-132页。提出文体和风格应是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倡吁翻译界予以重视。所憾王佐良的论文对文体与风格虽然分列,但并未区分。25年后,由王佐良和丁往道牵头,编撰了国内第一部文体学教科书——《英语文体学引论》。(9)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只提“文体”,不谈风格,特别突出了“语言学”的特征,虽分述了各体英语,然并未使用“语体”这一重要概念。及到1995年,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问世,该书虽名为“文体”,实际所论均为语体,可贵的是该书在最后一章,抽出部分篇幅“论翻译的风格”,虽然篇幅不长,但说明作者已意识到文体与风格的差异。及到1988年侯维瑞的《英语语体》(10)侯维瑞:《英语语体》,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语体”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全书以情境语域为根基,详尽地讨论了口语体与书面语体、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功能变体,更难能可贵的是还专辟一章,论述英语的历史变体。《英语语体》是一部较为系统的“语体论”著作,尤其是情境和语域的引入,则为本学科理论建设助了一把力。接踵王佐良、侯维瑞者有秦秀白(11)秦秀白:《英语文体学入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秦秀白:《文体学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秦秀白:《英语语体与文体要略》,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钱瑗(12)钱瑗:《实用英语文体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世生(13)刘世生:《西方文体学论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胡壮麟(14)胡壮麟:《理论文体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等。他们强调的是文体,除刘宓庆、侯维瑞外,其他人等疏于论及语体与风格。
中国的汉语学界,从1959年高名凯的《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15)高名凯:《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载《语言学论丛》第4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年。的报告发表后,旋即在华夏激起了研究语言风格的浪花。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断流了二十年,直到1985年,由程祥徽的《语言风格初探》(16)程祥徽:《语言风格初探》,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重新激起语言风格研究的高潮,先后有张德明的《语言风格学》(17)张德明:《语言风格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18)郑远汉:《言语风格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黎运汉的《汉语风格探索》(19)黎运汉:《汉语风格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问世。其特征是均以“语言风格学”或“言语风格学”称之,从不使用“文体”,但黎作不同的是,专列“表现风格”一章,接续了《文心雕龙》以来的体性论。“表现”一语,源自西方美学,西论中将“美”的显现,分设为“再现”和“表现”两类。前者重在对已存事实的模仿,后者则着重主体内在的独特心理认知。表现风格的分设,为深入研究语篇的风格形态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方向。1987年因《语体论》(20)袁晖、李熙宗等编:《语体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此书系1986年于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语体风格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语体”这一学术概念开始流行。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十年,是语体风格繁荣的二十年。辛勤耕耘者有李熙宗、袁晖、丁金国、曾毅平、祝克懿等。汉语学界虽然也有“体”的纠葛,然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是“求同存异”。“体裁”属语篇的结构类型,是语篇的形式问题,并无异议;“文体”与体裁同义,虽有争论,但鉴于史上已习惯与体裁同称,现已存疑求同;“语体”是后现者,严格讲是俄语界在介绍俄苏语言风格大讨论(1953-1955)时引进国门。在语义阐释上,异于体裁、文体的语义结构,是专从情境功能域的角度,对语篇的功能所进行的分类,故在汉语学界有人称为是工作分类。这就意味着,并未完全进入学术体系。究其原因在于宏观上过于概括,微观上疏于精准。过于概括主要表现在语体分类上,无论是四分、五分,或是六分,最后还是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汉语“文体”分类,从没有这么多的“交叉渗透”,几近泾渭分明。原因就在于:微观区别性特征显著,各文体间无论形式特征或是语义特征都所指明确;宏观上概括程度低,几千年来的文体分类,少者几十种,多者百以上。概括程度低,类间的分辨率就高。如《红楼梦》几乎囊括了所有文体,但从来没有人说它是戏剧或者是公文、新闻之类。相较语体研究,无论是公务语体或是科技、谈话语体,严重的类间“交叉”正是其病根所在,缘由是缺少区别性特征。高度概括的语体类型,一是难以付诸语文实践,二是对内部纵横交错的要素难以梳理。
“风格”至今仍人言人殊,有人说风格就是文体,文体就是语体,语体就是风格。外语学界则索性将其与文体合一,统称文体,或文体风格。揭开风格的面纱,关键在于揭示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首先显现物质化的是由“体裁”所制约的语篇或话语,语篇为什么要受体裁的制约?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言:应情立体,即体成势。“体”从何而来?当然不像刘勰说的“征于圣,宗于经”,源自圣人的经典。而是人们在言语活动中,经历史的筛选和磨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社会约定俗成的语用范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风格与体裁有对应性的一面,如曹丕《论文》、陆机《文赋》所论;也有龃龉的一面,刘勰就比曹、陆多了些辩证意识,其在论述风格的体类时,就取消了这种对应关系,而加意设置了《通变》篇,专论“常”与“变”的关系。认为“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语用事实也确乎证实:同一种体裁可有不同风格表现。我国古代的韵语体,就几乎包容了所有风格形态。如史上盛传的唐代张打油的《咏雪》:
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而与其同时代的柳宗元,也有一首《咏雪》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两相比较,同为韵语体的“咏雪”,竟然相差如此之大。前者俗不可耐,后者高雅清纯。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同一种体裁,同一个词牌,其风格形态也完全可能迥然。如苏轼曾用词牌“江城子”写过多首词,其主流风格形态是婉约,而恰恰在婉约中,却出现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既要“亲射虎”,又要“射天狼”,其豪情壮气,表现得畅酣淋漓。与“十年生死两茫茫”“天涯流落思无穷”“相从不觉又初寒”相较,显现出冰炭之别的风格差异。所以我们说,风格与体裁、语体、文体不是同义异称,而是各有专司。体裁就是由语篇结构方式的差异形成的体式;文体专指书面形式的语篇;语体可兼容书面和口头的语篇,但其更强调语篇存在的功能域;风格与体裁、语体、文体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是位在体裁、语体、文体之上的审美形态,体裁、语体、文体具有言语社群所公认的俗成性,风格则更着重在个性的差异性。在传统的文体论中,“体”与“性”,一向形影相随,从未合二而一,在言语生活中,也从未发生过纠结,各自出现的语域都非常清晰。自“语体”译入后,语用中与传统以体性为核心的文意产生了乖谬。本来汉语中的风格、文体、体裁尽管多解,但在语言与文学研究及语文教学领域,其语义还是清晰可辨,很少发生抵牾。西论中的“功能语体”和文论中的“文体”涵义开始进入国人的学术视野,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至今也没有融入汉语的文体论体系,仍然游离于体裁、文体和风格之外。可见,外来的东西,唯有经过民族化的改造,方可为我所用。笔者认为,体裁、文体和风格,可依旧按传统语义规范使用:体裁即语篇的形式结构,文体即书面语的体裁分类,风格即凸显个体语篇的表现风貌。“语体”在我们的言语生活中,既然存在了多半个世纪,且正在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与当代社会的语境磨合,萌生出以语用功能为前提的所谓“功能语体”。语言学界已开始接受功能语体,并尽量使其位得其所。就目前的存在形态来看,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语体为先”的语用意识,正被语言学界和语文教育界所接受,并实际指导着语言教学和语言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