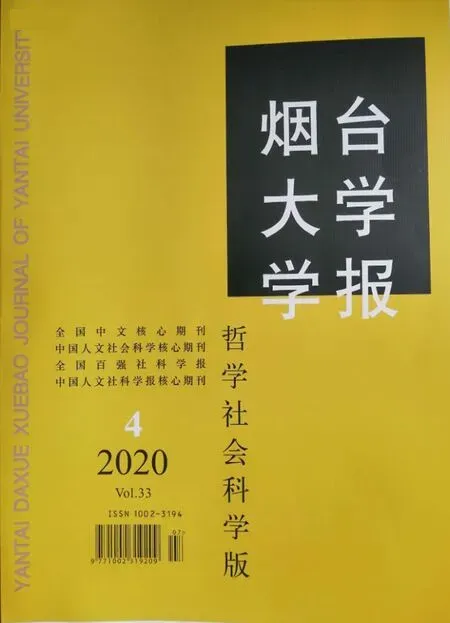张谦宜格调诗学的构成与渊源
黄卓颖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引 言
从中国古典诗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以格调论诗,起源较早。刘勰《文心雕龙》就已经提出“风格”、“辞调”的说法。(1)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二《乐府》、卷八《夸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上册,第82、465页。至唐代皎然论诗,开始区分“五格”,(2)皎然:《诗式》,载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29页。宋人姜夔则明白宣称诗歌“意格欲高”,“句调欲清、欲古、欲和”,(3)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载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682页。而严羽又将“格力”列为诗歌五法之一(4)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页。。尽管这些概念的内涵和指向还没有具体展开,但是作为一种诗学观念,格调说已经在逐渐成型。当然,真正让其声名鹊起并且广泛影响诗坛的,是明代前后七子。在明朝这个复古笼罩一切的时代,前后七子为了诗学操作的便利,将前代一切诗学活动和诗学现象进行了法度化总结和程式化运用,从而建立起了其极具特色的格调诗学体系。入清以后,虽然前后七子的诗学功过一直存在争论,但是其格调诗学的影响却丝毫不见减损,相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举例言之,如申涵光、归庄、毛先舒、张谦宜、沈德潜、李重华、乔亿、黄子云、潘德舆、朱庭珍等都曾追随七子的步调,坚守着格调诗说的立场。其中,明末清初的几位格调论者,由于起着联结前后的中间链条的作用,所以地位尤其关键。不过,与前后七子相比,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学理的衍变,他们的格调诗说也多少带上了几分独特的色彩。本文所及张谦宜,就是其中一个。
一、风格的论述与理想的审美
张谦宜在诗学上的格调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不仅标榜“格调”这一范畴,围绕它进行诗学体系的建构,而且还对这个范畴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和说明:“格如屋之有间架,欲其高竦端正;调如乐之有曲,欲其圆亮清粹,和平流丽。”(5)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三《学诗初步》,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标点本,第782页。从这一说明来看,张氏所谓的格,显然主要是指诗歌的体格,调则主要指声响效果,体格要高大端正,声响要清亮和平,这是他对诗歌格调所要达成的理想状态的总体要求。围绕这一总体要求,张氏才展开了其格调诗学体系的具体建构。
首先是关于风格的评述和论定。如果说格主要指体格(具体又由字句、篇章结构、立意以及将这种种要素绾合在一起的法度),调主要指声响(具体包括字韵和音节)的话,那么由特定的体格和声响熔铸结合在一起之后,最终呈现出的艺术形相,就是种种不同的诗歌风格了。所以,不同的风格,可以说就是格调在具体化过程中生成的各种特殊艺术形相的外现。这些风格如何形成?哪些可以作为理想的类型加以标榜?这是张氏在论述格调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从《絸斋诗谈》来看,张氏论及的风格范畴主要有清、和平、老成、老辣、蕴藉、平淡、温雅、沉著、高古、豪放、清奇、浑、含蓄、疏野、飘逸、旷达、流动、冲淡、雄健。而张氏在阐述这些风格范畴的时候,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认为任何一种风格,要真正能立得住脚,产生活力和生机,就必须通过抒写自我真性情,将其与自我才性、气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那些通过模仿和虚伪做作造出的风格,即便不是死的,迟早也会因为是赝品而被历史淘汰。所以张氏说“诗要老成,却须以年纪涵养为洊次,必不得做作装点”;诗要老辣,“然苦者自苦,酸者自酸,不相假借处,各有本等”;“诗要温雅,却不可一晌偏堕窠臼”;又说高古乃“韵趣天然,从容缥缈,脱尽皮毛,直溯本根”;疏野是“天然率真,才用意便是假”;冲淡为“性情心术上事,不洗自净,不学而能”;雄健要“充口而出,不待做作”。(6)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三《学诗初步》,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84页。总而言之,风格出于性情,而大体离不开一个真字。二是尽管张谦宜论述到了众多的风格范畴,同时也承认这些范畴如果出于真性情,便自会产生其独特的价值,可是不管以怎样的标准衡量,它们却永远也不会等价。至少对于张谦宜来说,他所论及的风格,在他的诗学观念中,地位就不平等。从“诗品贵清”、“诗贵和平”、“诗要老成”、“诗要老辣”、“诗贵蕴藉”、“诗尚平淡”、“诗要温雅”、“含蓄二字,诗文第一妙处”这些言论来看,他最推崇清、和平、老成、老辣、蕴藉、平淡、温雅、含蓄,再加上后来他在评述具体作家作品时反复叹美的“沉著”,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风格尽管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美学效果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指向,或者说,我们可以将它们划归到同一个大的审美类型即内向式审美中去。
其实,不仅在论述风格时如此,张氏其他一切诗学行为无不强烈地表现出对蕴藉节制的内向式审美的推崇,对发扬蹈厉、声气怒张的外向式审美的拒斥。如论诗法,便强调“汁厚而不胶,锷敛而力透”,认为只有“用力向里收”,才能使“锋敛而味长”。(7)张谦宜:《絸斋诗谈》卷八《杂录》,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889页。论诗作,便看其是否“气静”,是否“神凝”,是否“敛华蓄味”,是否“精神沉著”、“气象凝定”,如果能做到,则必“机到神流”,臻至含蓄极境;(8)张谦宜:《絸斋诗谈》卷四《元次山》,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95页。不然,“心粗手滑”,“意思太爽快,才气太迅发”,“筋脉怒张”,那就必然导致“格低”。(9)张谦宜:《絸斋诗谈》卷六《刘子羽》,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847页。由此波及到对诗人的评价,也发生了绝大的反转,像韩愈、苏轼由于才大、豪纵,作诗“无收敛渟蓄,一泄而尽”,竟然“不如韦苏州远甚”;而名不见经传的元末诗人葛逻禄,由于其诗作“语短而味长,蕴藉风流”,在张谦宜看来,反倒“能轶宋超唐”(10)张谦宜:《絸斋诗谈》卷八《杂录》,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864页。。这些论断恰不恰当,暂且不管,但是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张氏在审美标准的选择上,是以内向型审美为理想的。
二、诗体的辨析与诗法的构成
由于张谦宜将格调之格主要看成是诗歌的体格,所以具体到格调说的建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诗体进行辨析和规范,其《絸斋诗谈》论说丰富。首先总论古诗:
古诗如厨人作清汤,重料浓汁,以香蕈渗其腻,鲤鱼血助其鲜,其清如水,滋味深长。
古诗写景如写意,山水林木水石,不须细细钩勒,屋宇人物,不须琐琐描画。然须一气磅礴中苍厚浑成,当于此等处会心。
分论《选》体:
《选》体如盛世士夫,精神肃穆,衣冠都雅,词令典则,所以望之起敬。
《选》体凝而不流,全在精神收敛,意思深沉,不然亦是死胚。
《选》体诗全要典重深厚,须以学力胜,枵腹掉笔者,遇此必不支。
论歌行:
歌行亦论品格,不得耑以豪壮括之。
凡称“行”者,音调贵乎流走。
论七古:
七言古,须如狮子出入山中,行常不发怒也。须有千斤气力在。
七言古,须有峰岚离奇,烟云断续之妙。
通首五言,著七字一两句收,便是七言古诗。自唐已定此例,再申之。
七言六句古诗,妙在上四句说尽题意,更添不得。
古诗之外,兼论乐府:
乐府主于痛快淋漓,若以闷木不尽言为上,先不知古今之变已。
通体动摇,趁口快吐,故是乐府调。
又论古诗与乐府的分别:
古诗与乐府分界,只是动气、静气之交。
乐府与古诗不同,故有时痛快言之。
其次,论近体的几种主要格式。如五律:
五言律,须字字如浑铁打就,力大于身。
五律一团筋力,又须有弦外传音之妙。
七律:
七言律,鋩欲韬藏,巧须贯串,造势固费经营,相机尤当详审。大约以古为律,俗艳方得脱落。
七言律,全要真体内充,大用外腓。
排律:
原排律立名之意,自取排宕排闼之义,一物一事,必换意分层以尽其致,填砌典故,点缀浮艳,非诗也。排律之有应制应试,又自一派,谓足以尽诗之用,误矣。以格律过严,绳检太拘,虽三唐高手为之,未能淋漓满志。说者谓词取颂扬,体取骈俪,以饾饤目之,亦未得其本旨者。揭其大法,不离乎起承转合。即以十二句言之:二句起,四句承,四句转,二句合,此一例也。或用四句起,二句承,二句转,四句合,此一例也。或通体铺叙,自以浅深次第凑泊成篇,无起承转合之痕,而法自行乎中,又一例也。
作排律,局要阔大,思要绵密,次第中有总分串递之法,方为当家。
绝句:
绝句不要三句说尽,亦不许四句说不尽。
绝句一句一转,却是四句只成一事,著重尤在第三句一转,方好收合。虽只四句,与律法无异,意不透不妙,意已竭亦不妙。上二句太平,振不起下二句。下二句势高,恐接不入上二句。用力要匀,如善射者之撒放,左右手齐分,始平耳。
从学理上来说,张谦宜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各种诗体作出详细的规定,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初学诗者或者处于诗学进阶中的作者提供一系列标准的诗歌型式,通过这些标准型式的规范,尽量引导诗家走向矜贵典雅的正途,避免堕入各种诗学魔道。但从其论述的过程来看,他却又在有意无意之间凸显了两种立场:除了乐府“主于痛快淋漓”,歌行“音调贵乎流走”,排律“取排宕排闼之义”之外,其他如《选》体、七古、律诗、绝句这几种最主要也是最常用的诗体,依然以内向式审美为祈向,此其一。其二,在诗体的辨析中,张谦宜的逻辑进程总是沿着“诗法—诗美”的模式展开,如论乐府,由于诗美上要求“痛快淋漓”,所以在诗法上必须“趁口快吐”;古诗,由于诗美上要求“滋味深长”,所以诗法上就必须“一气磅礴中苍厚浑成”;《选》体,由于诗美上要求“凝而不流”、“典重深厚”,所以诗法上就要“词令典则”、“精神收敛”;五律,由于诗美上要求“一团筋力”,所以诗法上必须“字字如浑铁打就”。也就是说,特定的美学效果一定关联着特定的法度运用,诗美就寄寓在诗法之中。这就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法度在某种意义上规范和成就了诗体。由此引申开来,重法的观念也就自然产生。的确,落实到张谦宜格调诗说的具体论述,他有关用字、炼句、构篇、发题、用韵等方面的法度说明正好构成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
首先论字法和句法。对于炼字炼句,尽管张谦宜提出了很多具体、实用的技法,如炼字方面有“烘染”、“化俗为雅”、“点腐成新”、“虚字在腰,上下开生”的方法,炼句方面有“侧注”、“互勾”、“倒叙”等技巧,但是从总体原则和最终效果上来看,他无不在反复强调一种观念:稳(有时又将其称为“紧致”)。他说“所谓炼字”,不过是“无处不明净,无处不牢固,然后托得我意思出,藏得我意思住”;又说,“所谓琢句”,乃“务使五七字内,线穿铁铸,一字摇撼不动,增减不得为度”。这里的“无处不牢固”、“一字摇撼不动”,实质就是“稳”的另一种表达。那么如何达成“稳”?无非做好两点:第一是下字造句要切合情境。下字造句切合情境,就能将意义和氛围恰当妥帖地传达出来,诗歌的意义和氛围能恰当妥帖地传达出来,则内容上必定圆活饱满,也就不至于使诗歌因为意义的缺失、空白或游离而造成体格的动摇、脱节。如丁澎《至日》:“冬至参芒白,灯昏雪片青。”光芒在“白”、“青”二字,“切至日,移用不得”,所以“稳”;张谦宜自作《寄贺车双亭生子》,第一首颈联初作:“青莲别有种,明月自成胎。”后改为“书香原有种,浩气自成胎”,改稿“从双亭身上说出,才是亲生”,同样因切合情事,也达到了“稳”的效果。第二,下字造句要“稳”,还必须在字与字、句与句、意象与意象之间形成照应、关会、映衬。一首诗,如果用字造句,前言不搭后语,小则枝蔓、冗杂,大则龃龉、矛盾,这必不能达成“稳”的效果。苏轼《白水仙佛迹岩》“潜潭有饥蛟,掉尾取渴虎”,之所以紧致圆密,被赞为“炼到之句”,就因为其中写虎因渴而临潭,潭因深而藏蛟,而蛟则因饥而取虎,是“字字照应”,圆密联动,没有罅漏。同样,丁澎《寒食简严颢亭》“崖冰断垄惊新草”,“断”字呼“惊”字;“野烧空林废禁烟”,“空”字映“废”字,皆互相关照而一团筋力,所以牢固“妙绝”。谢连芳《雪霁》:“雪霁曙光凝,渔蓑漾初日。隔浦一帆斜,前村钓船出。”用“钓船出”照会“霁”字,则不仅稳固,而且“活甚”。可见,“处处关会,互相助势”,是使炼字造句达成“稳”的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当然,如果处理不好,“稳”也很容易流为平板、滞塞,尤其是在造句的时候。张谦宜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论句法时就特别强调,诗家一定要有意识地去变换诗歌的氛围与节奏,所谓“上文气紧,须用缓句;上文气重,须用劲句。下文向里,则上句放开;下句拖漾,则上句捲收”。总而言之,要形成错综变化的形相,只有这样,才能在追求“稳”的同时,不至于丧失紧致、流动、弹跳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论篇法。虽然诗歌的篇章有长短,但结构篇章的方法,在张谦宜看来,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孔雀东南飞》极长,《龙洲无木奴》极短,须看成一副机轴,方可谈诗。”排律的经营,要“有层次,有转接,有渡脉,有盘旋,有闪落收缴,又妙在一气”,绝句同样要“一意一气,而起承转合之界,各自井然”,“与律法无异”。所以,从总体上来说,诗歌篇法就是一个格套。当然,在微观的视域中,这个格套又可以分为三个段落:首(起)、腹、尾(结)。这三段如何来抒写?张谦宜在具体做法上并没有做死板的规定。但大体而言,起法要“陡健”,中间“宽裕流行”,令其势“纡徐”,结法则欲“如盘弓勒马”,在干脆中不失余味(余力);至于从首至腹,从腹至尾,为了避免文气的断裂,则还需有过脉联结,而过脉的安排,则是“一句挽上,一句生下”,虽然“用之有明暗、曲直、断续、飞黏之不同”,但大致是“一意分数层,一事分数段,须依法逐节说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诗歌在一气贯注中形成“饱满流动”的生气。可见,张氏论篇法安排,是极重节奏的错综变化的,而错综变化之中,相比于平铺,又尤其著意于转笔的使用。因为转笔多,不仅使诗篇“陡健”,有气力,而且“跌宕断续,生出波澜”,波澜大,则“使人寻味无穷”,“笔墨自添光景”。当然,无论结构如何转,如何错综变化,从整个篇法的体格和用力来看,应该是要通体均匀的。因为只有“通体匀圆”、“精力匀”,才能“劲弦一激,旁风不挠,捷于中人”,“如善射者之撒放,左右手齐分,始平耳”。否则,措意于首,则头重;著力于尾,则尾大;专注于腹,则腹胀,这都是诗病。所以张谦宜在评骘杜甫《登岳阳楼》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二诗时,就扬杜而抑孟,因为“杜诗用力匀,故通身重”,而孟诗则“力尽于前四句,后面趁不起,故一边轻耳”。(11)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五《孟襄阳》,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817页。
再次论立意。张谦宜认为,一首诗歌的立意,主要分为两种情况:联句立意与篇章立意。所谓联句立意,就是指一联之中,意义如何表达的问题。张谦宜最推崇的一种方法就是“形对待而意侧注”,“形对待”则体格匀称,“意侧注”则意义递进,气脉流动,可以给诗歌带来一种牢固而内敛的美,这是符合张谦宜诗学趣味的。因此,像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李商隐《题白石莲花寄楚公》“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刘翼明《寄怀胶西谈禹臣》“人如陶靖节,酒对菊花枝”、王之邻《竹崖探江干微月》“空山闻瀑布,满地滴花香”等因在表意上都采用了侧注的方法(从第一句至第二句有一种前驱的力量,致使诗意重点往往落在第二句),故被张氏称赞为“无排砌之病”,而有流动之致。与联句立意不同,篇章立意是指一首诗总体意旨如何表达的问题,它往往与诗题相关,所以谈论篇章立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探讨如何相题与发题的问题。那么具体如何操作呢?除了“字字是题”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莫过于配合篇章结构的多转而形成意义的多层次性。张谦宜说,凡做诗,先要“相题之来处去处”,配合“吾之颈联腹联起承转折章法”及“吾之起结所从生”,以“搜题之层数,与夫内境外境”,然后“或由外看进,或自内看出”来决定诗意的抒写。(12)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三《学诗初步》,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84-785页。如果“看题无层次”,思路便不开,思路不开,意义必定死实、单一、浅薄,诗篇当然也就不入高流了。所以,不管是联句立意的“侧注”,还是篇章立意的“多层”,张谦宜都推崇一种递进式的表达,这种递进式的表达不仅可以造成意义的流动,同时,也会带来一种凝聚和沉著的形相,从而赋予诗歌以内在的气力和筋骨。这显然又呼应了张谦宜内向式审美的理想。
最后论用韵。韵法是张氏格调之“调”的主要内容。因此他在《絸斋诗谈》中曾集中笔力对其进行过阐发。这主要涉及两个内容:一是用韵的总体原则;二是用韵的具体技法。首先在总体原则上,张谦宜非常重视古今字的变化以及雅俗(即方言与官话)读音的不同,一再告诫初学诗者既不可以今字通古韵,也不能不作检阅,轻易地认为“口头熟字”与“领韵”声近,便认定是一个韵部而发写下去。因为这两种行为都会带来一个严重恶果——“走韵”。(13)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三《学诗初步》,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90页。所谓“走韵”,通俗地说,就是自以为押韵,而衡之以标准韵书,实质不入韵。这是“不入门”的低级错误,人人得以“诧之笑之”。所以,如果不是老于韵法,精于诗学的名家,千万不可随便叶韵。其次是具体技法,他强调押韵要“浑成妥确,开阖点缀务与本章机扣相通”,也就是说,诗歌押韵要配合诗体结构的设计和诗情的表达;“和韵”要用“自己意思管领,首尾一气,勿带应酬俗套”,“又要与和人之情暗暗关会”,所以和韵最看重同韵之中,己情与人情的巧妙激射和暗合;至于“换韵”,首先要陡健,令界画分明,其次在转换处要适时“接一句”,令气味贯注,如果不接,转换太陡则“暴”,而所接过多或不时,又会导致“漫”、“弱”的毛病,无论“暴”与“漫”、“弱”,都是用韵上的不精。(14)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二《统论下》,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76页。可见,从韵法的阐述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张氏诗学观念中的几个焦点:程式化、标准化、正统性以及内向审美中“转”与“流”的和合处理。
其他尚有论对偶之法的:如错对、离对、流水、隔句、以衬作对等。虽也重要,但在具体论说上并没有高出前人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张谦宜将诗法分解为字法、句法、篇法、立意、用韵等不同的项目,但这仅仅是为了言说的便利,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他还是强调不同的诗法应该交织融合在一起,放在同一个框架中去考量;因为字法只有放在句子中去锤炼,才能安排妥当,而句法也只有置于篇法的语境中,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所谓“积字成句,一字不稳,则全句病,故字法宜炼;积句成章,一句病,则全章亦病,故句法不可不琢。且句之布置起落,即是章法,非句外另有章也;字之平排侧注,虚实吞吐,即成句法,非字外另有句也”(15)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三《学诗初步》,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83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用韵与表情立意、结构设计的关系,前文已经论及。
三、承变之间:张谦宜与毛先舒
蒋寅先生在考察张谦宜的诗学渊源时,曾比较详细地论证了他与乃师杨师亮、明七子诗学以及山东地域诗学之间的关系。(16)蒋寅:《张谦宜〈絸斋诗谈〉与清初格调诗学的承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但是有一个人他却忽视了,这就是比张谦宜稍早的毛先舒。为了避免重复,我们在蒋文的基础上考察张谦宜的诗学关联,将略其所详,而详其所略,将重点落在张谦宜与毛先舒的关系上。
张谦宜在阐述自我诗学观念的时候,有两个人的话语引述最多,一是其师杨师亮,共11处,张氏全部持受教和赞同的态度;一是毛先舒,引用6处,加上评述毛先舒诗学成就的一则文字,共7处。其中3处在分析具体诗作的技法和效果时,张氏对毛先舒提出了质疑和反对,包括论杜甫《秋兴八首》,“‘秋兴’二字,或在首尾,或藏腰脊,钩连甚密。毛稚黄嫌其若无题者,何也”;论王维《送杨长史赴果州》“鸟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时”一联,“一直说出,险怪凄凉,味在言外。毛稚黄以为意兴欲尽,非也”;《送丘为落第归江东》“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一联,“‘五湖’宽说具区,‘三亩’方切本家,‘万里’,约举往返,‘一归人’紧贴本身,并非堆垛死胚。毛稚黄以为病,何也”。此外几处都是赞同的态度。特别是在评述毛先舒的诗学成就时,张谦宜明确指出,尽管毛先舒个人因为“才力不济”、“手拙”,故所作之诗“无精彩,亦无力量”,“佳处不可得”。但由于其眼光高,学识“亦正亦深”,所以在论诗时,“见地本高”,而能精彩迭出。这让张谦宜相当倾倒,因此,张氏在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时,很多地方就或隐或显地秉承了毛先舒的精神和观念。当然,在这个承袭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张氏根据自己的偏好而作了一些变换和调整,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论及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张谦宜在审美理想上对毛先舒的继承。从明代前后七子开始,到明末清初作为七子派拥趸的云间派为止,格调诗学在主流审美上一直标榜一种高声大气的雄壮之美,而这种雄壮之美因为以“盛唐范式”为标的,所以又总是呈现出外向、发扬的面貌。至毛先舒重塑格调诗说,才开始一改传统,转而推崇一种内向式的审美,他说“文妙在不大声色”(17)毛先舒:《东苑诗钞》题序,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594页上栏。,又说作诗文应该“用力于内,以敛以积”,通过“敛气于学”、“藏态于法”的方式来达到“不流”、“不露”的效果,(18)毛先舒:《潠书》卷六《与友论诗文书》,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727页下栏。因此,他非常反对那种张扬、发皇的诗歌,将其贬斥为“供笔端以自见而博声誉”的小家数。(19)毛先舒:《小匡文钞》卷四《作者说》,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74页上栏。很明显,这些言论及其透射出来的诗学精神直接构成了张谦宜所谓“气静”、“神凝”、“敛华蓄味”的内向式审美的理论先导。当然,尽管二者都重视内向式审美,但落点又各有不同,毛先舒在追求内向审美的时候,不重气力筋骨而重神韵,所以他说“魏人气高于汉,唐人气高于六朝,盛唐气又高于初唐,愈高愈出愈漓”,认为气力越大,格调反而越低;只有“不乏神韵”,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高笔”。(20)毛先舒:《诗辨坻》卷三,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标点本,第51-52页。而张谦宜标举内向式审美,虽然不反对神韵,但重点却落在气、力、骨的讲究上。所以他一则说“后生学诗,急宜讲者,气骨耳”,再则说“力与气缺一不可”,三则说“气所以贯格调”。(21)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三《学诗初步》,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81、784页。如此苦口婆心,足可以见出他的用意。
其次是在诗写性情上表现出对毛先舒的呼应。对于格调论者来说,由于大多数人强调复古,强调模拟,强调诗学的程式化,所以往往忽视对自我性情的表达。毛先舒和张谦宜超越流俗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突破格调的牢笼,而表现出对自我性情的重视。不过,这并不能有力地证明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承续关系,因为像前后七子中的李梦阳、谢榛也曾有过重情的主张。如李梦阳提倡“格古调逸”,要求“情以发之”,(22)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记》,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六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446页下栏。谢榛说作诗要“情融乎内而深且长”,(23)谢榛:《四溟诗话》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118页。就是明证。所以张谦宜在诗写性情这一点上对毛先舒的承续和沿袭,不在此而在彼:接受并复述了毛先舒提出的诗虽然可以而且必须写情,但绝对不能流于情,要对情进行节制的观点。毛先舒说,诗歌在表情上应该“深于情,不及于流”(24)毛先舒:《潠书》卷七《十才子赞》,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第750页上栏。,如果“胸贮几许,一往倾泻”,那必然像瓠子泛滥,造成恶果。(25)毛先舒:《诗辨坻》卷一,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第9页。于一往吐尽之后,“几亡诗矣”。所以诗歌“发乎情者必有所止,固不在一往而深”(26)毛先舒:《潠书》卷二《蒋子西湖竹枝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第635页下栏。。张谦宜对此毫无异议,他说:“人生喜怒之感,不可毕见于诗。无论一泄无余,非风人之致,兼恐我之喜怒,不合道理,不中节处多,有乖正道耳。”(27)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一《统论上》,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66页。所以在诗写性情这一点上,他强调必须要懂得“自摄”与节制。这与毛先舒的立场完全一致。
再次,在诗学评价和经典的树立上,大体上表现出对毛先舒的认同。在中国古典诗学领域,唐诗与宋诗作为两种极具特色的诗学范式,常常被后人置于经典的视域中进行优劣异同的对比和评判,发展到明清时期,更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尽管范围小、时间短),往往以一种范式的经典性否定另一种经典范式的合法地位。对于张谦宜和毛先舒来说,他们有关经典的认定和榜样的选择是一样的,都推崇唐诗而反对宋元,甚至对宋诗的“伧”的评价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涉及到明清诗歌时,二者就产生了分歧。毛先舒重明诗,欣赏的却是明初四子(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前后七子、薛蕙、顾璘、高叔嗣、王廷陈及刘基、卢柟二十四人,其中大多是名家;而张谦宜重明清诗,推奖的却是葛逻禄、王僴、丁澎、刘翼明、杜濬、丘元武、李国宋等声名甚微的小家。其实不仅对明清诗人如此,在评价唐宋诗人时,张氏也多多少少表现出这种倾向,如论唐诗贬斥韩愈,而推举元结;论宋诗贬斥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而推举文与可、唐庚、孙觌。这种做法,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张谦宜欲标新立异,希望通过翻案来引起他人关注的诗学意图。
最后,在推崇一种矜贵品格和雅化情怀上,表现出对毛先舒的追随。毛氏论诗,最重典雅的气度,所以他区分诗歌为八品,对最上的两品——“神品”与“君子品”就做了这样的规定:“神品”要“于物无择,而涉笔成雅”,“君子品”则须“泽于大雅,通于物轨”,都是以“雅”作为准绳的。(28)毛先舒:《诗辨坻》卷一,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 2016年标点本,第10页。落实到具体的诗学操作,就是一要避免俗,二要反对奇。所谓“文不尚奇”、“文不尚怪”,如果“发口凡近”,则诗品就“最劣”。因此,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俗与奇的最突出代表白居易和韩愈,毛先舒便每每施以贬词,如论白居易,讽刺其“诗索媪解,岂称高唱”;论韩愈,则贬斥他“以文法为诗,大乖风雅”。至张谦宜论诗,立场基本相同:从总体要求上来看,他也强调作诗要“词雅而意正”,要“不伤大雅”。落实到具体的做法,他也从反对俗、反对奇入手,认为作诗不能作“街谈”,不能为“负贩市语”,“不求奇谲”,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做到“品高”。(29)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一《统论上》,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二册,第765页。而在反对俗、反对奇时,同样以白居易和韩愈作为典范的反例进行批判,说白居易诗“语直而味短,与诗人之致不同”,“气格全低”;说韩愈有意“生新”,久而成病,“自我作古”,“不可为训”。因此,张氏不仅在具体观点上,且在论说的逻辑上,都与毛先舒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当然,两相比较,毛先舒在诗学上的精英立场和贵族化倾向更明显,也更绝对一些,他几乎不允许任何通俗或者违背古典标准的诗学行为出现。而张谦宜相对来说要通达、宽容,比如他尚能局部允许俚俗的词语和意象出现在诗歌中,只要“炼得雅”或“自然高妙”即可。这也正是为什么陶渊明还能在张谦宜的诗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但在毛先舒那里却被完全忽略了的重要原因。
以上是关于张谦宜格调诗学体系的构成,以及它与毛先舒格调诗说之间存在的承变关系的简单考察,从中不难看出,张氏在重法度、重辨体、重声调、重典雅品格这个格调诗学共有的框架中,试图将七子重气力的格调说与毛先舒重内向审美的格调说结合起来,(30)七子以格调论诗,专门推崇一种外向、发扬的气力,比如李攀龙编选《古今诗删》标榜格调,许学夷就指出其“专尚气格”。谢榛倡言格调,鼓励人“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即是其中代表。以内向式审美纠正前者的浮夸叫嚣,以气力挽救后者重韵致所带来的薾弱疲软,从而新建一种正大、紧致、匀称、陡健之美的格调新说。很显然,这种诗学建构的方向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体系中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只不过由于张谦宜人微言轻,又偏居山东荒隅,当时未能将其诗说刊刻出来作广泛流播,所以对于诗界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和显著。但是他的正统立场,对诗体和诗风的辨析,对性情的强调,对诗法的建构,以及对人格与诗格关系的论证,都丰富了格调诗学的内容。而从沈德潜、李重华、乔亿、潘德舆等人对这些论题的反复回应来看,张谦宜的格调说毕竟有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