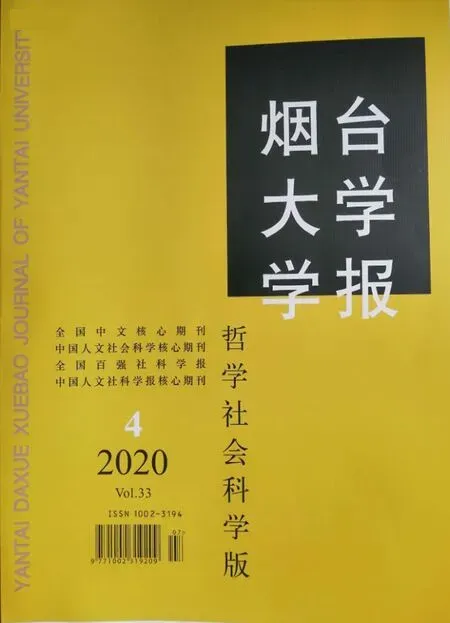论我国中止犯刑事责任的争议问题
陆诗忠
(烟台大学 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一、关于“中止犯与既遂犯竞合”的问题
“中止犯与既遂犯竞合”是指如下情形:被告人在特定犯罪故意的支配下,按照其犯罪计划实施犯罪行为,后来基于其本人的意志不再实施该犯罪的预备行为或者实行行为,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预期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此一来,被告人既成立预谋犯罪的中止犯,又可能同时成立另一犯罪的既遂犯,这就会出现“中止犯与既遂犯竞合”。(1)参见李兰英、林亚刚:《犯罪中止形态若干争议问题的再探讨》,《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根据上述界定,“中止犯与既遂犯竞合”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情形之一:犯罪人基于本人的意志自动中止了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但是其中止的预备行为成立另一犯罪既遂犯。比如,行为人甲基于故意杀人的目的而盗窃枪支,但在着手实行杀害行为之前,或者实行过程中自动停止了杀人行为。在该情形中,甲的行为同时涉嫌两个犯罪行为:盗窃枪支罪(既遂)、故意杀人罪(中止犯)。
情形之二:犯罪人为了中止犯罪,而实施了某种手段行为,然而该手段行为又构成另一犯罪既遂犯。比如,在投毒后,行为人乙见被害人极端痛苦而心生悔意,为将其送往医院不得不将其汽车撬开驾驶。在该情形中,乙的行为涉嫌两个犯罪行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既遂)、故意杀人罪(中止犯)。
下文即对上述两种情形,分别进行讨论。
(一)对“中止犯与既遂犯竞合”中的第一种情形如何处理
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对行为人是以“A罪中止犯”论处,还是以“B罪既遂犯”论处,抑或是进行数罪并罚?对此我国刑法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有学者认为,针对该种情形,应以B罪的既遂犯论处,而不应当追究A罪中止犯的刑事责任。还有学者认为,应当根据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予以处理。(2)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2页。另有学者认为,“中止的效果不能及于其他犯罪,也不能被中止之罪所吸收,例如,为了诈骗而伪造公文,虽中止诈骗行为,但仅就诈骗罪是中止,伪造公文仍然是既遂。”(3)黎宏:《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258页。但其对最终处理的意见没有明确表态。有学者则进一步明确了处理问题的路径,即对其应当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在预备行为单独可以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施预定之罪的实行行为,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预备后进入实行过程中的,则可以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实施数罪并罚也未尝不可。(4)参见林亚刚:《刑法学教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8页。应该说,该学者认识到“中止犯与既遂犯竞合”的复杂情形,并进行了较为精致的分析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笔者看来,该学者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一,“在预备行为单独可以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施预定之罪的实行行为,可以成立想象竞合犯”的认识,恐怕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通说,想象竞合犯是指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形态。例如,一次开枪射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情形;违章驾驶机动车辆肇事造成乘客重伤,又撞毁路边通讯适配箱,造成数千户通信中断的情形,这在刑法理论上均被理解为想象竞合犯。然而,行为人所实施预备行为(即为故意杀人而盗窃枪支的行为)并不能同时构成故意杀人罪(中止犯)。这是因为,只有当行为人盗窃枪支之后,基于自动性而没有进一步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时,才成立故意杀人罪(中止犯)。而“为故意杀人而盗窃枪支”的行为无法同时被评价为“基于自动性而没有进一步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为故意杀人而盗窃枪支的行为”同时就是“基于自动性而没有进一步实施故意杀人行为”。该学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以致于得出不够妥当的结论。
本文认为,当行为人已经完成犯罪的预备行为,而基于自动性没有进一步实施犯罪的,这应属于刑法理论上的吸收犯,即对行为人应当按照吸收之罪予以追究刑事责任。进言之,由于行为人完成犯罪的预备行为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是不可能造成“损害”的,因而其成立的中止犯是“被免除处罚的中止犯”,自然应当属于“被吸收之罪”。因此,对行为人应当按照预备犯罪(即吸收之罪)定罪处罚。
其二,“预备后进入实行过程中,则可以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实施数罪并罚也未尝不可”也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
首先,该学者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理解为牵连犯中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这是存在不少疑问的。这是因为,牵连关系并不是主观推理、主观认识中的思维联系,而是客观现实的关系。即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应当坚持客观判断的标准,不能采取“主观说”。而该学者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采用的则是“主观说”。(5)该说认为,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有无牵连关系应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为标准,即行为人的行为应由一个犯罪意思统一起来。见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毋庸讳言,牵连关系的认定是一个仁智互见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主观说”已经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普遍抨击,(6)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683页;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15页;刘树德:《牵连犯辨正》,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吴振兴:《罪数形态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279-281页;姜伟:《犯罪形态通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446-447页。仅仅具有知识论的意义。
理论上一般认为,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应当采用“通常方法结果说”:“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才宜认定为牵连犯。例如,非法侵入住宅杀人的,宜认定为牵连犯;但非法盗窃枪支后杀人的,不宜认定为牵连犯。”(7)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73-374页。但是该说被认为缺乏一个明确的判断资料和判断基准,会导致认定的难题。比如,什么是“通常的方法”?什么是“通常的结果”?在此情况下,“犯罪构成要件说”则应运而生,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8)该说认为,只有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才能作为认定牵连关系客观的标准。见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本文赞成“犯罪构成要件说”的基本立场,它完全克服了“通常方法结果说”的固有缺陷。
其次,该学者认为对“牵连犯”的处罚,既可以从一重罪处断,也可以数罪并罚,这也存在商榷的余地。这是因为,对同一种犯罪形态主张采取不同标准的做法,这不具有科学性。从法理上来讲,对同一性质的犯罪形态的处断,应当适用同一种处断原则,否则将有违于罪刑平等的刑法理念,会使得刑法的适用丢掉了彼此的一致性、协调性、统一性。
再次,刑法学上创制“牵连犯”,其目的就在于确定哪些数罪可以不予数罪并罚。如果对某些“牵连犯”进行数罪并罚,其本身就无多少意义了。诚如学者所言:“假如对牵连犯予以数罪并罚,那么牵连犯在法理上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主张对牵连犯予以数罪并罚,这是对牵连犯传统理论所提出的严峻挑战。然而,这种挑战就其本质而言是建筑在否定牵连犯存在必要的基础上的。”(9)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本文认为,上述情形同样应当被认定为“吸收犯”,这属于实行阶段的中止犯吸收预备犯的情形。(10)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受“重罪吸收轻罪”这一基本原则的制约,当实际发生的实行阶段的中止犯轻于预备犯,造成吸收不能的状态时,则应当是预备犯吸收实行阶段的中止犯,以此作为实行阶段的中止犯吸收预备犯的一种例外。
(二)对“中止犯与既遂犯竞合”中的第二种情形如何处理
此处的第二种情形是指,犯罪人为了中止犯罪,而实施了某种手段行为,然而该手段行为又构成另一犯罪的既遂犯。对此种情形如何处理?在我国刑法学界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被告人通过损害A法益避免B法益受到侵害时,则应当将损害A法益的结果归责于他。例如,被告人甲以故意杀人的目的将被害人乙硬性锁在房屋内,在打开天然气后离开现场。离开现场不久,甲便对乙产生了怜悯之心、同情之心。甲于是将被害人乙家的玻璃门窗砸碎,被害人乙得以生还。但甲的行为使得被害人遭受较大数额的财产损失。在本案中甲构成两个犯罪,一是故意杀人罪的中止犯,一是故意损害公私财物罪。(1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377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对该情形应当按照一罪的中止犯予以论处,对构成既遂犯的其他罪可不予处理。但是完全按照一罪的中止犯予以论处,会存在不妥之处。比如,被告人中止故意杀人犯罪行为但又构成其他重罪,如对被告人仅仅以中止犯论处,这可能会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基于此,可以不考虑中止犯的情况,直接依据其他罪既遂犯处理。(12)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483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此种情况应按照吸收犯的“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处理:“上述情况符合吸收犯条件,即在特定情况下为中止犯罪,不得不有此行为时,符合‘前行为吸收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成立吸收关系。”(13)林亚刚:《刑法学教义》,第439页。
在本文看来,如果对“为了中止犯罪,而实施的某种手段行为又构成犯罪”的情形,不加分析地一律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理,这是不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因而,第一种观点并不可取。
第二种观点提出对上述情形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该观点也存有可疑之处:为什么构成既遂犯的另外一罪在一般情况下可不予追究,而在特定情况下应当追究?我们须知,“有罪必究”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
第三种观点将此种情形认定为吸收犯,不符合“吸收关系”的基本要求。在理论上,判断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吸收关系,必须以一个犯罪构成依附于另一犯罪构成的法定性作为判断标准。换言之,构成吸收犯的数个犯罪行为在犯罪构成的关系上,要么是同一性质的基本犯罪构成与修正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此修正犯罪构成与彼修正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14)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7页。然而,“为了中止犯罪,而实施的某种手段行为而构成的犯罪”与中止犯罪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在犯罪构成的关系上并不具有上述意义上的依附性。因而,本文对第三种观点并不赞同。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对“犯罪人为了中止犯罪,而实施了某种手段行为,然而该手段行为又构成另一犯罪的既遂犯”这一情形的处理,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实施某种手段行为”而构成的“既遂犯”,如果符合紧急避险条件的,则对其不以犯罪论处。也就是说,对行为人只是按照中止犯定罪,并予以减轻处罚。如果不符合紧急避险条件的,则对行为人进行数罪并罚,即对行为人既要追究中止犯的刑事责任,也要追究避险过当的刑事责任。该处理意见能较好克服上述三种观点的不足:既能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也不会放纵犯罪分子,又不会将其认定为吸收犯。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该种情况不能被解释为牵连犯。这是因为,此处的“手段行为”是出于避免危害结果的目的而实施的中止犯罪的“手段行为”,并非基于某种犯罪目的而实施的“手段行为(方法行为)”。一言以蔽之,此处的“手段行为”并非牵连犯意义上的手段行为(方法行为)。
二、关于“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问题
“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是指这样的情形:由于手段错误或者工具错误(含对象错误)的原因使得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客观上无法实现犯罪既遂,但被告人对此并无认识而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自动放弃了犯罪的实行,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15)李兰英、林亚刚:《犯罪中止形态若干争议问题的再探讨》,《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对于这种犯罪形态的竞合如何处理,从目前来看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种情况下的未遂与中止的竞合,应当以犯罪中止论处。其理由是,既然危害结果没有发生,并且被告人主观上又具备成立犯罪中止的主观要素,那么就应该对其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这一主观愿望,以及其已经采取措施的积极方面进行肯定。(16)张宏:《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竞合应当以中止犯论处》,《人民检察》1994年第4期。并进一步指出,“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表面上要求中止行为与没有发生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上是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做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真挚努力,并不是要求中止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17)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第372页。不难看出,这一观点对“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处理,也是以犯罪中止予以认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种竞合应当视行为的发展进程来决定。论者认为,属于绝对不可能达到犯罪既遂的,应视不同情形予以不同处理,即在尚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而自动放弃犯罪意图的,应当以犯罪中止认定;相反,则以犯罪未遂论处。属于相对不可能达到犯罪既遂的,则无论是否实行终了,自动放弃犯罪的,都应当以犯罪中止认定。(18)参见林亚刚:《刑法学教义》,第441页。
本文认为,在“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以中止犯论处。这是因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成立中止犯要求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或者(采取措施)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换言之,危害结果的没有发生,必须与中止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然而,在“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情况下,由于手段错误或者工具错误(含对象错误),危害结果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在“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情况下,中止行为自无存在的必要,中止犯没有存在的可能。此为其一。其二,对中止犯之所以减免处罚,其根本理由就在于刑法试图通过与被告人的“妥协”、“让步”来降低“既遂结果”的量甚或避免“既遂结果”的发生。既如此,当犯罪客观上无法完成时,即客观上存在着约束、遏止犯罪完成的外部因素、外部条件时,我国刑法是不可能借助于减免处罚的“优惠措施”,鼓励、褒奖被告人自动停止犯罪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既遂结果发生的。因而,在本文看来,出现“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但行为人自以为能够将犯罪完成而自动停止犯罪的情形,不得被认定为“中止犯”,否则这将违背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存在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真挚努力”即可构成中止犯,这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即便这种“真挚努力”能够成立中止犯,也是针对客观上能够出现犯罪结果的情形。该种意义上的中止犯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被称为“准中止犯”。所谓“准中止犯”,是指当行为人在主观上真诚希望能够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客观上也作出了足以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真挚努力,而且按照通常情况,这样的真挚努力按照因果流程能够避免犯罪结果发生,只是因为其他原因,使得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的没有发生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难看出,“准中止犯”并不适用于“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准中止犯”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得到认可:“在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准中止犯并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应建立对准中止犯与中止犯同等评价的制度”。(19)张平:《中止犯与未遂犯的竞合形态研究》,《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由此看来,在既定的立法规范中,“有效性”是成立中止犯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将“真挚努力”认定为中止犯,这将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冲突。
本文同时认为,第二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二种观点提出在“实行终了”的情况下是犯罪未遂,在“实行未终了”的情况下是犯罪中止。该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表面上看是公允的。可令人疑惑的是,在“实行未终了”的情况下,何以就认定为犯罪中止?难道说,在“实行未终了”的情况下,行为人就实施了“有效”的中止行为?在“实行终了”的情况下,行为人就没有实施“有效”的中止行为?对此,我们不得而知。在本文看来,无论是“实行终了”还是“实行未终了”,都无法改变“由于手段错误或者工具错误(含对象错误),危害结果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在“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情况下,对行为人应当按照犯罪未遂处理为宜,并不存在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在“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情况下,对行为人应当按照犯罪未遂予以定罪处理,但应当考虑行为人“真挚努力”这一基本事实,将其视为酌定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三、关于中止犯中“损害”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不难看出,认定中止犯是否造成了“损害”,这对于确定中止犯的刑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拟研究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损害”的范围
“损害”仅限于行为所造成的实害,并不包括行为所造成的危险。如将与之对应的“危险”也归入“损害”的范围之中,这将意味着中止犯没有免除处罚的余地。这样的认识在刑法学界恐怕不存在任何质疑。但是在如下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1.“损害”是否必须为刑法规范禁止的侵害结果?
对此有学者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如果某种结果并不表现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就不能说明刑法意义上的违法性程度,不能成为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20)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其基本理由在于,不进行如此的限定将导致刑法规范并不禁止的结果成为处罚的对象,导致犯罪构成丧失了罪刑法定主义的机能。(21)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将“损害”限定为刑法规范禁止的侵害结果,的确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主义,是一种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但其问题在于,将“损害”限定于“构成要件”的侵害结果而忽视“非构成要件”的侵害结果,这并不能全面评价中止犯的社会危害性,将会忽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中止犯领域的具体应用。我们知道,在刑法理论上,危害结果有“构成结果”与“非构成结果”之分。前者又被称为定罪结果,是指成立某种具体犯罪必须具备的危害结果;后者又被称为量刑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引起的某种具体构成要件危害结果以外的,对于该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及其刑事责任大小具有一定评价意义的一切现实损害。事实上,在中止犯中,同样会造成“非构成要件”的侵害结果。比如,甲使用暴力强奸妇女,在奸淫之前实施了猥亵行为,后来放弃奸淫行为的。根据前述论者的理解,这里的“猥亵”行为是“损害”,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了“强制猥亵罪”。对此,本文并不持异议。不过,有另外一种情形也不能忽视。即甲在强奸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奸淫行为。其在强奸过程中,并没有对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但其强奸行为诱发了被害人自杀或者自残。我们能否认为该中止犯就没有“造成损害”呢?能否对其免除处罚呢?这显然是不能的。
本文认为,将中止犯中的“损害”限定于刑法规范禁止的侵害结果是不够全面的,还应当包括“非构成要件”的侵害结果。
2.“损害”是否仅限于物质性结果?
有学者认为,物质性法益、非物质性法益都是我国刑法的保护对象。因而,不管是刑法所禁止的物质性危害结果,还是刑法所禁止的非物质性危害结果,都应当属于实害结果的范畴,因而都属于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22)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刑法是要保护非物质性法益,非物质性危害结果是法益受到侵害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非物质性危害结果”是否就能归入到中止犯中的“损害”的范畴呢?这恐怕存有商榷的余地。这是因为,“非物质性危害结果”往往就是犯罪行为本身,具有抽象性,感官不可以直接感知,不具有可测量性,需要根据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进行判断。按照论者的逻辑,中止犯在犯罪过程中所构成的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损害”,这将大大缩小对中止犯免除处罚的范围,进而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在此意义上,我国《刑法》中犯罪中止中的“损害”应当理解为可以为刑法所评价的有形的、可以测量的物质损失。
本文也注意到论者的担心,即如果将中止犯中“损害”理解为有形的、可以测量的物质损失,将会损害刑法的公平正义:单纯对妇女进行强制猥亵的,可以按照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犯罪既遂予以处理;而企图对妇女进行强奸的被告人在强制猥亵妇女后中止奸淫行为的,反而被免除处罚。这显然是不合理、不均衡的。(23)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但在本文看来,中止之前的行为能够成立另外一种犯罪行为,也是存在疑问的。就论者的举例而言,以强奸的故意对妇女进行强制猥亵的,本身就不能另行成立强制猥亵罪,其仍然是强奸罪。这不会出现“明显不均衡”的问题。再者,即便成立强制猥亵罪对其不予追究,也符合刑法功利主义,这样能够鼓励行为人停止实施重大犯罪。一言以蔽之,将中止犯中的“损害”理解为有形的、可以测量的物质损失,并不会出现论者所担心的问题。
3.“损害”的对象是否限于被害人本人?
有论者认为不应当限于被害人。即除了对被害人自身造成的危害结果之外,对被害人亲属造成的结果、对无关的第三者或者一般人造成的结果,都应当属于“损害”范围。(24)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
但在本文看来,该种见解是存在疑问的。其一,如此理解违反刑法中的责任主义。责任主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它包括两层含义:如果行为人对某危害结果既没有犯罪故意,又没有犯罪过失的,其行为就不成立犯罪;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某危害结果既没有犯罪故意,又没有犯罪过失的,该危害结果就不能作为量刑的根据。然而,不管是“对被害人亲属造成的结果”,还是“对无关的第三者或者一般人造成的结果”,行为人对此都可能不存在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是不存在责任的。其二,中止犯的“损害”,无疑应当是行为人在犯罪中止过程中所造成的。在犯罪中止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对象不可能包括被害人以外的人。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将中止犯中的“损害”限于被害人本人,这是针对中止前的犯罪行为而言的。如果中止犯中的“损害”是由中止行为造成的,则应另当别论。
(二)“损害”的原因
在此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是仅限于中止前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还是也包括中止行为(即中止过程中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在我国,有论者持“否定说”,认为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的行为只能是中止之前的犯罪行为。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我国《刑法》第24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既然中止行为有两种表现(一是“自动放弃犯罪”,二是“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那么中止行为本身应是避免法益侵害结果的行为,绝非造成法益侵害结果的行为。(25)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对此本文认为值得商榷。从该条规定来看,犯罪中止应该包括两个类型:一是自动停止犯罪的犯罪中止,二是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第一类型的犯罪中止无疑有可能造成损害,这自不待言。而在第二种类型的犯罪中止中,行为人为了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既遂结果)的发生而实施的某行为同样也会造成某种损害,因而有可能构成另外一个犯罪。在此,我们不妨仍以前述“被告人甲以故意杀人的目的将被害人乙硬性锁在房屋内”为例予以阐释。在本案中,甲为了中止犯罪,避免被害人死亡这一犯罪结果的发生,而实施了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此处的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便是中止犯中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是仅限于中止前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呢?
其次,论者认为采取“否定说”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行为人在实施较轻犯罪的过程中,其实施中止行为虽然避免了轻罪结果的发生,但是其中止行为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损害结果。针对此种情形,只有采取否定说,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比如,“夜间陈某某到某仓库内窃取财物。当其将价值8000余元的贵重金属工具装入麻袋后将要搬出仓库时,顿生悔悟之心,便决定将所盗财物放回原处。然而在放回原处时,贵重金属工具砸死了正在熟睡的仓库保管人员。如果根据否定说对案件进行处理,那么陈某某的行为应当成立两个犯罪,即盗窃罪的中止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这样对被告人就可以判处公正的刑罚。如果认为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包括中止行为,那么对陈某某就应按照盗窃罪(中止犯)减轻处罚,即在低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裁量刑罚,这显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26)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很显然,论者所指出的采取“否定说”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这只是适用于那些意图避免“轻罪结果”而出现了“重罪结果”的情形,但并不适用于其他的情形。这说明,“否定说”是存在片面性的。再者,对那些意图避免“轻罪结果”而出现了“重罪结果”的情形不采用“否定说”,承认损害的原因包括中止行为同样能够做到罪刑相适应。这是因为,为避免“轻罪结果”而实施的行为,可以成立避险过当,应当对行为人进行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对行为人既要追究犯罪中止的刑事责任,也要追究避险过当的刑事责任。以论者所举的案例而言,不采用“否定说”,承认过失致人死亡行为(中止行为)是“造成损害”的原因,也同样能够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根据前文的论述,陈某某的行为应当成立数罪,即盗窃罪(中止犯)与(避险过当)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其予以数罪并罚。只不过对盗窃罪裁量刑罚时,要减轻处罚。
再次,采取“否定说”有利于处理第三者参与救助造成损害的案件。(27)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为此论者举例说,“钱某往被害人的食物中投毒,导致被害人疼痛难忍。此时钱某产生悔意,便立即请邻居孙某帮忙开车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在车内由钱某扶着被害人)。在开往医院的路上,孙某驾驶的车辆撞在电线杆上,结果导致被害人死亡。在这种场合,如果采取否定说,本案的定罪与量刑问题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得以解决:钱某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中止犯;孙某成立交通肇事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诚然,如果肯定中止犯中‘造成损害’的行为包括中止行为,也许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但问题在于,如此一来则与其对被告人本人在中止过程中造成损害所得出的结论明显不协调。”(28)张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损害”》,《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本文认为,钱某的行为并不能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中止,这是因为其行为并没有有效避免被害人死亡犯罪结果的发生,并不具备成立犯罪中止的“有效性”条件。也就是说,被害人的死亡仍然是钱某在中止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不存在论者所说的“与其对被告人本人在中止过程中造成损害所得出的结论明显不协调”问题。至于孙某的行为,则应当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或交通肇事罪)。
四、关于中止犯中“减轻处罚”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的规定,对于造成损害的中止犯,应当减轻处罚。可是,对这里的“减轻处罚”,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还是比照未遂犯、预备犯“减轻处罚”?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中止犯的处罚应当以未遂犯、预备犯作为比较对象:“将未遂犯与预备犯作为中止犯的比较对象,有利于实现对中止犯的合理量刑,即为了诱导行为人自我否定,对于中止犯的处罚应当轻于同类型的未遂、预备案件,这样才能表明减免处罚是对行为人的奖励。”(29)李立众:《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及其意义》,《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可是,论者所提及的比较对象于法无据。我国《刑法》第63条对“减轻处罚”有明确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不难理解,根据规定,“减轻处罚”的比较对象应当是既遂犯而不应是论者所言的未遂犯、预备犯。
再者,对中止犯比照同类型的未遂犯、预备犯减轻处罚在学理上并无充分的根据。这是因为,在某些刑事案件中,中止犯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总是轻于未遂犯、预备犯的。比如,在未遂犯、预备犯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而中止犯造成损害的刑事案件中即是适例。
在此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将“减轻处罚”的比较对象理解为“既遂犯”,也同样能够做到“处罚的均衡”,同样能够使得同类型的中止犯的处罚轻于同类型的预备犯、未遂犯。这是因为,“减轻处罚”的幅度是具有弹性空间的。在司法实践中,做到对中止犯“减轻处罚”的幅度大,而对预备犯、未遂犯“减轻处罚”的幅度小,这同样是“处罚的均衡”的表现。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在对中止犯适用“减轻处罚”时,审判机关还应当充分考察被告人(中止犯)所实施的犯罪性质、犯罪的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此综合判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犯罪行为,对被告人(中止犯)的“减轻处罚”应予从严掌握,不宜过度减轻。相反,则可以从宽掌握,可较大程度地减轻刑罚的适用。这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