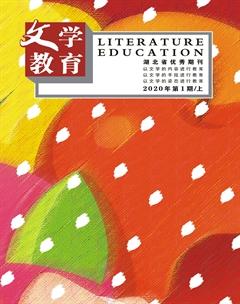宽恕
陶丽群
她不知道是不是想见他,分开四个月了,他们没通过一个电话,一直靠微信联系。当然不是每天,隔两三天,他给她发个问好的表情,你来我往上三五句,关于他那边和她这边的天气之类,最后毫无例外是关于她妈妈的病情。
“今天她怎么样?”他问。语气平淡,他们都听出来了。
“挺好,正在恢复。”她回答。
“能吃上东西就没事。”他说。
“她一直都能吃。”她叹着气回答。
“能吃就好。”他答。
“是的。”她答。
交流就此结束。
两三天之后,轮她主动向他问好,她给他发了一个太阳的表情。她其实不喜欢这个表情,像个笑脸,示好的笑脸,她在内心里从来都不想向他示好,然而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表情了。假如上次是他主动问好,而这一次她没主动,那么他们之间将会这样一直沉默下去,像两个极为遵守规则的人。
规则!她心酸地想,最终她还是按照规则来,轮到她向他问好。她觉得他们之间不柔软,他们的婚姻不柔软。但何为柔软?该怎么柔软?她一时也无法说得清楚。模模糊糊觉得两人之间隔着一层很坚固的玻璃,彼此看得见,但无法真正触摸到对方,似乎也没什么办法打碎这层玻璃。每每想到这些,她心里便隐隐泛起怨恨。
昨晚他们刚刚进行例行交流,他在即将结束谈话时说,老杜离婚了。这是他们四个月交流以来的新话题。她有些惊讶。老杜是他的朋友,据说做建筑材料生意,来他们家吃过一次饭。她对他的印象几乎是模糊的,只记得他的老婆很年轻,当然是第二任老婆。她的惊讶并不是因为老杜离婚,而是,他不是个在意这些琐事的人,不明白他为何要特意告诉她,似乎他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她本来打算昨天晚上收拾东西的,但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再也没心情收拾那几件皱巴巴的灰黑色棉麻料衣物。那几乎是她全部的夏季衣物。她回莫纳镇时才三月份,但这个靠近热带的小镇一年似乎只有两季,从寒冬直接进入炎夏,每年过了元宵节,镇上人就开始拖鞋配短袖,所以她带回了她大部分的夏季衣物。
如今已是如火如荼的七月,莫纳镇上没有一个角落是阴凉的。
一早起来,她就开始收拾衣物。按照规矩,他们这两天不会再联系了,不过她昨晚告诉了他今天的行程,她将乘今晚八点半的火车,五个半小时后,也就是在下半夜回到市里。当然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毫无理由停下来半个小时的慢车,坐在这趟车上,任何人的脾气都将被磨没了。
六十八岁的妈妈在今年三月份时摔坏了髋骨,不算很严重,但以妈妈这年龄,也是相当危险的。她以为这件事将会结束每年三次的例行回家,是的,她以为妈妈的生命会被这件事情带走(宽恕我吧!她想),很多老人不就是一摔就没了吗?然而妈妈却顽强地从床上下来,并恢复到逐步能自理的程度,这令她大为惊讶。在妈妈能自行洗澡后,她决定返回市里。
“我的腿脚渐渐使不上劲了。”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她的房门。时间还很早,不到七点半,然而墙壁摸起来已经开始有暖意了。刺目的阳光从窗外投射到房间里的地板上,屋子里非常明亮。她很早就被这个繁忙的边防镇吵醒了,重型货车的喇叭声惊天动地的,从口岸那边拉满满的从越南进口来的货物,经过她的家门运往内地的中国市场。
“你正在恢复,而且恢复得很好。”她说,望向门口一眼,接着继续收拾东西。那只棕色的拉杆箱倚窗而靠,在四个月的时光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这是一栋二层的楼房,妈妈住在楼下,而她住在楼上一间临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有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时光。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她几乎不怎么回忆那些过往的时光。
“我老了。”妈妈说,走进来坐在她的床上,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套被单是她从市里带来的,她不是嫌弃妈妈会弄脏她的床单,而是不适应她有这种亲昵的行为。她想起那些过往的时光,妈妈总会站在房门口对她吩咐什么,或仅仅只是因为心情不好而上来呵斥她,也许也是因为她在家里妨碍了她,总之,她几乎不进她的房间,总是满脸怒气地站在她的房门口。
“你不老,”她说,把丝袜和袖套塞进了拉杆箱的隔层里,她还很想对她说,你一顿饭吃得比我一天的还多。但她把这话咽下去了。妈妈六十八岁了,喜欢吃焖排骨,或者排骨炖莲藕,总是埋怨她不该把排骨炖得太烂,没有嚼头。她那口牙齿多么坚固啊,她怎么会老呢?
“每天晚饭后,你到河边走走,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她说,“你比大多数的同龄人要健康得多。”
“去河邊走?你怎么想得出来?你不怕你妈一头栽进河里?”她说,一只手抚在床单上。那是一套净色的棉麻床单,暗暗的蓝色。四个月来她只洗了两次,家里没有洗衣机,她拿到莫纳河边的码头上捶打。上个月她来例假时,不小心漏到了床单上。她本来打算拿去清洗的,但不知为什么事情所耽误,她拿来湿毛巾和一把旧牙刷轻轻刷洗,但还是有淡淡的印痕。妈妈皱巴巴的右手中指戴着一只金戒指,这让她隐隐有些不快。这个镇子上的老人,没有哪一个到了这岁数还戴金银首饰的。这会被认为自私,五十知天命后,老人就该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卸下来赠与儿孙了,否则会被认为这个家的老人要把金银带进棺材里,遗留给儿孙的只有代代相传的贫穷。
她当然不稀图妈妈的金戒指,她对金银饰品没有任何兴趣,更讨厌从她那里接受任何东西。她在这几个月甚至暗暗想,假如这一跤把她带走,她肯定会卖掉镇上的房子,然后迁走父亲的遗骨,永世不再回莫纳镇了。妈妈的家族在镇上还有些不远不近的族亲,也许每年的三月三他们会给妈妈以及她的父母烧一炷香的。这些,她无暇顾及,也不会挂心。对于妈妈这边的族亲,甚至妈妈本人,她没什么感情,甚至几乎谈不上感情。
“你不会栽到河里去的,你的心脏还很好,这你知道,医生给你测过了。你也没有低血糖和高血压。”她说,把一双半高跟的淡棕色皮鞋放进一个塑料袋子里,然后也装进拉杆箱了。
“嗳,这东西我五十五岁那年就没有了。”妈妈盯住床单上那摊隐约的污痕。
“你并不知道我几岁来的,对吗?”她问道。开始从布衣柜里取出衣物,一件件摊到床上。
妈妈沉默起来,她确实不知道。她是初中一年级放寒假时来的例假,她穿着脏了的裤子跑到邻居家找芳婆婆,那时候她还活着,是这个镇子上唯一真正关爱她的人。一直到她来例假的第二年,妈妈看见她扔在茅坑里的卫生棉垫,才知道这个家里有一个已长大的女儿。
“当妈的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哪能什么事情都顾得上,谁都是这么稀里糊涂长大的。”妈妈说。
她抬头看了妈妈一眼。妈妈的额骨一直很高,现在老了,皮肤下的脂肪日渐减少,皱巴巴的一层皮肤薄薄包裹住高额骨,使她的面相看起来很不协调,酸楚中带着刻薄。她记得她年轻时的样子,皮肤紧绷着,略高的额骨反而使她有种别样风情。长年累月一头大波浪卷,随意盘在脑后,用一个点缀有各色细小珠子的网兜兜住。那时极为流行这样的发兜,妈妈至少有三个。不知道为什么,她很讨厌妈妈这些漂亮的发兜,她脆弱而敏感,隐隐觉得这些好看的发兜散发出令她极为不安的气息。后来,她偷了一个她认为最好看的发兜,往里面塞满小石头,奋力扔进镇子后面从越南流淌过来的莫纳河。妈妈还喜欢穿水红色的衬衫,那时候流行喇叭裤,她的水红色衬衫是掐腰的,衣服下摆刚刚遮住裤头,紧窄的喇叭裤勾勒出她丰腴的下半身。她总是记得妈妈披散着刚洗好的半干卷发,慵懒地走在莫纳镇街上,去买一斤水豆腐或者一两条巴掌大的罗非鱼。她那时几岁呢?八岁,也许是十岁吧,她的寿短的父亲也还在。在她十一岁半时,父亲便和她们阴阳两隔了。她记得他总是咳嗽,后来咳了血,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父亲得的应该是肺结核,镇上的人称为肺痨,可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年纪轻轻的父亲便这样离开了。
“实际上我觉得你并未真正为我操心过什么,我一直都很安静,从不惹事。”她平静地说。是的,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平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有些东西结成了疤痕,依然触目惊心。
“嗤,”妈妈笑起来,眼角的鱼尾纹变得深而密集,“你见过哪个孩子能自己长大的?我可没少吃苦头。”
“你的意思是,把我生下来,然后最好是我自己成长?”她尖刻地说。一直以来她尽量避免和妈妈过于针锋相对。并不是她怕她,而是不想和她一般见识,她不想把自己弄得等同于她,她一直觉得她是个刻薄而自私的女人,不想和她进行没有理智的争吵。但今天她似乎难以克制,一种莫名的怒火暗暗在心里燃烧着。
“我没那样说,但你得承认,我落得晚年孤苦,和你有关。”妈妈说。
妈妈的意思是,她就是个累赘,可难道是她要求来这个世上的吗?
“我能阻止你做什么吗,假如你想做的话?”她说,把最后一件灰白色的麻料裙子胡乱卷起来放进拉杆箱里,把里面一包用了一半的卫生护垫拿出来塞进手提包里。她知道再把这些衣物拿出来时,它们将会像抹布一样皱巴巴的。棉麻料的衣物好穿,但极易打皱,难以打理。她并不是一贯都穿棉麻的,结婚后的第三年,她便放弃了所有以前穿戴的衣物,洗干净后全部打包捐给爱心机构,选择了朴素低调的棉麻。这些颜色偏暗的衣物很好地包裹住她并不张扬的肉体和低落的情绪。她会动不动把这些棉麻衣服从衣柜里取出来,堆在床上,一件件耐心细心打理熨平,种种突兀的情绪往往能在漫长的熨烫过程中平复了。
假如妈妈再辩驳,很可能今天会和她吵一架。她暗暗想。妈妈好像看透了她的心思,静静坐在床上,不再言语,看她把软底拖鞋也包起来,装进一个已经破了洞的黑色塑料袋里,塞进拉杆箱,然后是一面镜子。其实这面镜子完全可以不要的,甚至拖鞋毛巾都可以不要,包起来放进布衣柜里防尘就好,只要妈妈还在,总归还是要回来的。假如妈妈不坐在这儿,很有可能她就这样做了。但在妈妈面前,她似乎不想留下任何预示着“会再回来”的迹象。
妈妈一直缄默着,而她一直在等。她怎么做到一声不吭呢?她绝望地想。
妈妈咕哝着撑着床慢慢站起来。这几个月来,前面两个月,她甚至像抱个孩子一样抱着妈妈方便。还好妈妈一直很瘦,服侍起来倒也不太吃力,让她感到难堪的是去接触她的身体。前两个月她一直卧床,她在妈妈的床边支了一张折叠床,折叠床和妈妈那张宽大的床之间有一把椅子。妈妈半夜喝水和上厕所需要她搀扶时,她迷迷糊糊中不小心就会被椅子绊倒。但她不肯把椅子拿开,她觉她们之间隔着一点什么东西更好。
妈妈扶着楼梯慢慢下楼去了,她的脚步很轻,比猫走路轻不了多少。她一直倾听着下楼的脚步声,一直到脚步声平缓地落在楼下地板上。她把拉杆箱里包好的拖鞋拿出来,尽量往床底下最深处推。假如不弯下腰趴在地板上看,是不会被发现的。她坐在地板上,微微喘气。
她为什么能做到缄默不语?她的心该是多么硬呀!她想着,心里的难过越积越多,终于从眼眶里溢出来。她的一生,嗯,她四十岁了,总是这么不顺心。在芸芸众生中,她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甚至比大多数人卑微渺小得多,总是悄无声息活着,极力避免生活里的锋芒刺伤自己,然而总是在所难免。
午饭时,她做了西红柿焖豆腐块和鸡肉炒木耳。大米粥熬得很烂,她在粥里放了点儿枸杞,雪白的粥里有点点暗红,很诱人。
“胃不好的人才吃粥,”妈妈却说,“人原本和动物一样是吃生冷的,吃得太精细,胃就退化了。”她只喝了两口,而多半带着骨头的鸡块被她吃了。她的牙齿真好!她暗暗叹气,看着她唇上的油渍,心里涌起一阵浓浓的悲愁。
“其实,完全可以把这里的房子卖掉的。”妈妈说。这几个月来她一直向她做这样的暗示,比如说市里更適合她生活,看病容易,乡下的草包医生总有一天会要了她的命(她觉得很可笑,总有一天?她已经六十八岁了,草包医生不要了她的命,老天爷也可随时拿走)。甚至有一次说镇子里有人威胁她,要趁着黑夜一把火烧掉她的房子,理由是见不得她一个老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她当然知道妈妈在暗示什么,当她谈到类似话题时,她总是沉默不语。她发觉她们在性格方面,有些地方很相似,当话题不利于己时,便选择沉默。这让她感到非常沮丧。
现在,妈妈终于明确表明了她的意思。她望向她,她脸上的皱纹里有令人诧异的坚定表情,显得凶巴巴的,仿佛她必须得按照她的要求做。她斟酌着说:“每年总得回来扫墓的,没地方住。”她是指给早逝的父亲扫墓,也仅仅只是指这个。至于妈妈的父母,也就是她的爷爷奶奶,是的,她称妈妈的父母为爷爷奶奶,因为她的父亲是上门来的。她每年三月三回来扫墓,总是把父亲坟墓上的杂草清理得一干二净,给他献上一束采来的野花,她没带任何祭品。爷爷奶奶的坟墓上到处是老鼠打出来的洞,坟头也塌陷了,然而她无心顾及这些,她觉得胃口还极好的母亲应该还有能力清理自己父母坟头上的杂草。她一直觉得父亲的早逝,和他们,妈妈以及妈妈的父母打心眼里瞧不起他有关,父亲短暂的一生一直活在令人心疼的委屈当中,积郁成病,终于早早离世。而父亲的早逝让自己的孩子吃了不少苦头。
妈妈很快发现这句话有漏洞,她捉住漏洞飞快地说:“房子也可以不卖,租出去,老早就有人问过了,跑长途的说要拿来堆放药材。”她放下筷子,一副要认真谈这件事的表情,“这样也可以补贴生活,我也不算白吃饭。”
她沉默了,一股冰霜一样的寒冷爬上她的脸。跑长途的?这个一生都在和跑长途的男人苟且的女人,在她十八岁离开莫纳镇之前,东西南北来做口岸药材生意的长途司机,把她们家的门槛都快踏平了,腰包鼓胀的货车司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妈妈胸前暗红色的胎记。镇上的人管她们家叫“和平饭店”。
她恨透了这个称呼。
“听着,我最讨厌你们这副表情,你和你老子一样,碰到事情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来。我从来不觉得这算什么本事,你们的嘴巴只是用来灌吃灌喝的?不能痛痛快快给个话吗?”妈妈终于发起火,高额骨上弥漫上一股病态般的红色,双眼满含咄咄逼人的怒火。她本来想一口回绝的,但见她为他们(她和早逝的父亲)恼火,她觉得这真好。她一直认为无论她和父亲做什么,甚至她和父亲两个大活人,在她眼里都成为透明的空气的。她也放下筷子,转身到灶台边洗刷炒菜锅和案板菜刀。
“这么说你算是同意了?”妈妈近乎尖叫起来。
她们的厨房后面是菜地,菜地出去是莫纳河。这条脾气温顺的河流,流淌着她和父亲难以忘怀的快乐。父亲会砍下竹子扎成竹筏,夏天时带着她在河里划竹筏。她记得河里泛上来的清凉气息,她总是脸朝下趴在竹筏上,清凉的水汽直接钻进她脸上的毛孔里,够凉爽。河里会有从越南那边漂过来的巨大芭蕉树。假如运气好,他们甚至能打捞到带着芭蕉坠子的芭蕉树,砍下芭蕉坠子带回家,捂在稻草堆里几天,芭蕉便熟了。但父亲带回从河里捞起来的越南芭蕉坠子时,往往会遭到妈妈强烈的冷嘲热讽,说父亲就是一辈子乞丐的命。她始终无法理解,那些芭蕉坠多好呀,芭蕉个大饱满。如今那河面,铺着一层闪闪发光的阳光,粼粼波动,父亲和她的笑声好像还荡漾在河面上……她难过极了,几欲落泪。一只褐色的猫从菜园的杂草里窜出来,吓得她双眼一闭,泪水被挤了出来,她默默洗刷着菜锅,泪水落进洗碗槽里。
她回到房间,再一次环视房间,再也没什么遗留在房间里了,被子也已经用塑料袋子扎起来,假如能带走,她真想把被子也带走。门边刷着石灰粉的墙壁上有两只鞋印,都是右脚,很小的鞋印,她不记得是几岁时留下的印记了。她真希望能记住那些该记住的,忘掉该遗忘的。
午后的阳光变得炽热起来,她不打算午休了,这会影响她晚上的睡眠。半片右佐匹克隆已经对她发挥不了作用,她服了一整片。那药真是太苦了,假如吞咽不快,嘴巴会一直苦到第二天早上。一整片,她的睡眠也依然越来越糟糕,白天的疲倦常常让她怀疑生活的意义。那是一种低烧般的眩晕,而眩晕又造成虚脱般的疲劳,使你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连夏夜浓郁的茉莉花香都闻不到,无可救药的倦态令她对周遭的一切麻木无觉。
她把手机从包里拿出来,屏幕上的信息灯一闪一闪的,她立刻解锁屏幕翻看微信,却不是微信信息,而是一则推销保健品的垃圾短信。她失望了,握着手机静静站在窗前,她觉得他应该主动问问她,东西收拾好没有之类的,然而没有。她拿着手机站在窗前,隐隐地看见莫纳镇古老教堂的一角。她思索片刻后,决定去看看父亲。四个月里她去过一次,这次回去,假如妈妈没有什么意外,她打算连大年初二也不回来了。
她下了楼梯,路过妈妈的房间时,看见她正从衣柜里倒腾她的衣服,一个灰褐色的帆布包敞开着放在地上。妈妈听见脚步声,朝门口望了一样,四目相对那一瞬,她把目光移向地上敞开的帆布包,然后再一次望向妈妈。她明白她正在干什么,然而她无动于衷。
“得收拾收拾。”妈妈说,她的手臂上搭着一件花里胡哨的线衣,那应该是冬天穿的。她近乎毫无觉察地笑了笑,妈妈严厉的目光显然捕捉到她意味深长的笑,一下子把搭在手臂上的线衣往床上甩。她转身离开了房门。
“白眼狼,都是白眼狼!”妈妈的尖叫声从身后扑来。
镇子这两年扩建了不少,镇子附近的几个小村庄也拼到镇上来了,比小时候的莫纳镇大了不止一倍。很多人她不认识,旧时的很多镇上人依靠边贸生意发了财后,都到县里买房去了。他们在这里发财,但生活在别处。很显然,她的妈妈也想离开这里,把后半生安置在城市里,况且她还是在市里,而镇上的人最远的也只是在县城里买房,这得多给她长脸。
她穿过人流不息的街道,在一个摆地摊的越南女人那里买了一顶遮阳帽。出门时,热辣辣的阳光使她懊悔没带遮阳伞下来,但她却不愿返回楼上去取,那需要经过妈妈的房门。
遮阳帽是露顶的,她感觉到炽热的阳光直射在头顶上的热辣,头发散发出一股焦糊味儿。街道两边摆地摊的越南女人戴着巨大的尖顶斗笠,盘腿而坐,整个人都缩进斗笠下的阴影里。七十年代末那场中越战争使得越南南部的男人锐减,因此越南南部几乎全是女人养家糊口,而男人则在家养尊处优。路过莫纳镇幼儿园时,她忧心起来。她是一家私人幼儿园的副园长,三月份那時候刚开学,事情很多,她却申请了长假。园长是个坚强的单身妈妈,但幼儿园并不是她开的,她只是负责管理,幕后老板另有其人。她申请的长假园长并无权批准,她不想让园长为难,于是干脆打了辞职报告。报告尚未获批准,她就离开了。那是一家管理和薪资都很棒的私人幼儿园,上个学期来了两个应聘的北师大研究生,竟没聘上。而她这个本科生之所以能在那所幼儿园站稳脚跟,靠的是她和幼儿园一起成长的资历,没错,她是那所幼儿园的第一批老师,她在那所幼儿园整整待了八年了。
眼下七月了,九月份开学时,她希望能重新找到一份幼儿园工作,假如可以,她希望能重新回到原来的幼儿园去,不管怎样都要试一试,哪怕是当一名普通老师也好——比普通教职工多了将近五百块薪资的幼儿园副园长职位,不可能还空在那儿等她。她喜欢孩子们,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让她感到安全,她总是能在孩子们活泼的笑脸和幼稚可笑的话语里获得对生活的热情。
她没有孩子,结婚九年了,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丈夫把太多的爱给予和前妻所生并随前妻生活的孩子,对于另外一个尚未降临的孩子,他并无太多的热情,而她不是一个强人所难的人,于是他们就这么过着,不冷,也不热,遵守一些各自心知肚明的规则。
她再一次望向幼儿园,黯然神伤地叹了口气。幼儿园过去就是镇子的班车停靠的地方,往里是镇子的教堂。她远远地瞧了一眼,在炙热的阳光下,古老的教堂显得极为肃穆。她很快越过了教堂。前几年她在父亲的坟墓边上种了几棵蓖麻,如今已长得非常巨大,像伞一样覆盖出一片完全可以遮住几个人的阴凉,在蓖麻的阴凉里打个盹打发掉炎热的午后未尝不可。不,她并不惧怕墓地,死人的地方通常要比活人的地方安宁清洁得多,再说父亲就在那里,怎会惧怕。
她很快出了镇子,沿着一条并不太宽的沿田路慢慢朝挨在镇子边上的土坡往上走。早先这条通往墓地的沿田路有几棵高大的苦楝树,如今全被砍掉了。她不明白那些树到底妨碍了什么。她记得苦楝树的花是淡白色的,初夏时满树一簇一簇的花朵,远远望去仿佛一层薄雾笼罩在树冠上。
隐隐的,她感觉有谁在跟着她,然而每次回头身后的沿田路总是空荡荡的。她并不惧怕什么,只是这种感觉让她很不舒服。这个镇子没有谁跟她走得很近,儿时的玩伴,自从出了那件事情后,渐渐疏离了。并不是伙伴们嫌弃她,而是她主动远离了她们。
也许是一条狗吧。她想。沿田路两边的稻田开始成熟,假如有一个人蹲在田埂上,她是看不见的。这些稻田并不属于镇上的人,而是属于镇子周边的农村人。炙热的空气中流淌着稻子芬芳的气息,她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渐渐拐上往坡上去的小路,稻田甩在身后了,已经可以看见父亲坟墓边上高大的蓖麻。蓖麻在莫纳镇有庇护阴灵的寓意,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阴气太重的植物,假如不是故意种植,大都会被砍掉。她觉得委屈了一辈子的父亲,在那一世的灵魂需要庇护。她把蓖麻种植在坟墓边上,因此无人去砍。
等她爬到父亲的坟墓边上,站到蓖麻下的阴凉里时,整个莫纳镇子就在她的眼下,镇子的教堂尖顶在一片高低不平的房子中显得格外醒目而庄严:那里装了太多的忏悔。这时她才看见那个人影,戴着一顶草帽,可以看出是个男人,脸部笼在草帽阴影下,显得黑乎乎的。那人影离得尚远,但她立刻认出他是谁了。一个人即便老了,但走路的样子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自从她离开镇子后,每年按习俗回三次娘家,总会有一次碰见他,他会主动打招呼:回来了?或者:多久回来的?也仅仅只是个招呼,她盼望的那句话始终没有得到。
她的眼睛湿润了,想起丈夫有时候喝了酒,会拧住她的手腕愤恨地质问她:你那时候那么小,那么小呀,他们说你十五岁,是真的吗?亏死老子了,老子二十二岁才谈恋爱,十五岁,我可什么都不懂,你说,我亏不亏,嗯?她极力想要挣脱他的手,但酒后他的力气像魔鬼一样大,她两眼含着泪水,哀求地望着他。他似乎忘记自己已结过一次婚,并有了孩子,他有什么理由对她的过往耿耿于怀?况且那并不是她的错。
他走到她跟前,草帽下的臉汗津津的,灰色T恤胸前一片暗湿。
“我在镇上看见一个人影往这儿走,我想肯定是你。”他望着她说,很自然地就钻进蓖麻的阴影里。
他该六十多了,但肯定比她的妈妈稍微小些,也许三岁,也许五岁。他因为打群架伤人命,在里头待了十二年。她十五岁那年,他刚从里面出来不久,她记得他胳膊上刺的那条青龙,整天黏着她的妈妈。她并不介意,她觉得那是妈妈的生活,和她无关。他还会打她的妈妈,妈妈抱着他的大腿拖住他,哀求他别走。她在楼上的房间里,听见他们在楼下打骂和哀求。那时候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想总有一天她一定会离开这个镇子的。
后来她确实离开了。
他没怎么显老。
“你回来好几个月了,我知道的,但一直没碰见你。”他望着她说,然后摘下草帽,拿着当扇子,他用力摇着,手臂明显朝她这边倾斜,她顿时感到一阵凉爽扑面而来。
“是的,我回来了。”她简短地说,往一边挪了挪,想离开他扇出来的风。
然而他突然做了一个让她吓一跳并对他彻底绝望的动作,他用胳膊肘很暧昧地捅了她一下,并快速地向她挤眼睛:“喂,你干嘛总躲着我,我可没一天忘记过你。”
她惊骇地望着他,并倒退了几步,一把捉住自己的胸口,她捏到了胸口衣服下的挂坠。
“你要干什么?”她满眼含怒地瞪着他,“我父亲在这里。”她说。
“嗨,那就是一堆骨头,我们可以到别处去。”他又朝她靠过去。显然他误会了她。
“不!”她几乎跳起来,并且快速地折断一根比拇指大的蓖麻枝丫,枝丫折断的清脆声在炽热的空气里格外响亮。她拿着断枝戳着他。
“你,赶快离开!”她几乎喊起来,连声音都颤抖了,背后的汗珠子快速向腰际滚动。
“你这是干嘛?哎,你和你妈一点都不像!快放下,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我可从来没强求过你。”他后退几步,草帽捂住胸口,仿佛那是一件牢靠的防御器。
“闭嘴!”她愤怒得几乎要哭了,他在说什么?他居然还有脸说出口。“滚,快给我滚!”她呵斥起来,声音里带着哭腔。
他重新把草帽戴上,脸上带着怏怏的表情。
“真是,这样子迟早要吃亏的。”他咕哝起来。她一直瞪着他,蓖麻的枝丫直直戳着他的胸口,直到他走出蓖麻的阴凉,顺着小路慢慢下坡。
她一下子瘫坐到地上,靠在蓖麻粗壮的躯干上哭起来,一只手紧紧捏住胸口衣服里的吊挂坠子。她泪眼婆娑地望着身边的土堆,父亲就葬身在这之下,和她一层黄土之隔,然而再也无法看到她的悲伤和泪水。
她抽抽搭搭地哭着,午后的阳光热烈而白亮,莫纳河在山脚下闪闪发亮,从山脚下的河边吹过来的带着河水气息的风湿润而温暖。整片坡地空无一人,隐隐地从街上传来嘈杂声。她哭累了,有点儿口渴,淡蓝色的衬衫后背湿透了,然而她却不愿返回去,靠在蓖麻的躯干上,慢慢开始打盹,额头的发际线晕出一层细密发亮的汗珠。正当她模模糊糊想要睡过去时,她感觉到有个阴影慢慢朝她逼过来,她在迷糊中突然浑身剧烈的颤抖了一下,整个人像突遭电击般猛的清醒过来,心脏猛烈跳动着,像刚刚做了什么剧烈运动,瞌睡刹那烟消云散。她蓦然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刺目的阳光,什么也没有。
她望着身边父亲的坟墓暗暗叹了口气。脑子里飞快转着,其实不一定非坐火车,可以坐班车的,从莫纳镇到县里,只要到了县里,去市里的办法就多了,可以继续坐班车,也可以和别人拼车。到了县里如果能顺利搭上往市里去的车,甚至比火车还能更快回到市里,火车只不过是免了换乘的麻烦罢了。她豁地站起来,惊得脚边的昆虫四处飞散。在坡上就可以看见肃穆的教堂前面的简易车站,在那里,四十分钟就有一班汽车发往县里。
回到家里时,她一眼就看见漆皮剥落的沙发上妈妈那个鼓囊囊的褐色帆布袋,而她本人则坐在铺盖已经掀起来的床边上。她望了她一眼,匆匆上楼梯,一会儿就拎着拉杆箱下来。经过妈妈的房门口时,她停了下来,把拉杆箱放好,妈妈从床上慢腾腾站起来,显然没料到她会这么快离开,她执拗地盯住女儿,脸上是那种令人反感的强硬表情。
“这就走了?”她问。
她点点头。
“我还没收拾好。”妈妈说。
“你不用收拾。”她说。
“这么说你还是要扔下我?”妈妈又尖叫起来,“你想都别想!我已经等得太久了,天下没有不照顾母亲的孩子,天理不容。”
她又一次摸了她胸口衣服下的挂坠子,直直盯住妈妈,妈妈被她固执的目光钉在了原地。
“你们,后来为什么不结婚?”她终于问了出来,触及到那件似乎妈妈一直在回避的事情,当然可能也是她并不在意。
“和谁?”病态般的潮红又蔓延上妈妈的高额骨。
“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她说,“你允许他上楼的?对吗?后来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她说着,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于是紧紧捉住箱子的拉杆。
“瞎说,谁说我要嫁给他?”她妈妈疾口否认,她背对着窗户,面朝着客厅的大门,她否认时,她還是看见妈妈目光里一闪而过的慌乱。
“难道不是?你允许他上楼,然后他会答应娶你。那时候我几岁?我才十五岁,我什么都不懂,他扇我的耳光,你知道吗?后来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她尽可能轻描淡写地说。
“你恨我,我知道的。你一直在恨我,你不知道生活多么艰难,你不懂,你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了养活你夜里流多少泪水。”妈妈又恢复那副理直气壮。
“你可以直接掐死我,假如你觉得我是个累赘,但你不能那样做,你不该让他上楼,我是你的女儿。”她说,她快要哭出来。
“我觉得我没什么错!你别想我会觉得那有什么错,是我把你养大。”妈妈语气铿锵地说。
“你把我养大的,所以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情,对吗?”她绝望了,紧紧捂住胸口,在眼泪溢出眼眶之前拖着拉杆箱转身走了。
那句话,他们是永远不会对她说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把它当成一件荣耀的事情来描述,很快全镇子的人全都知道了。从此,她每天的日子都像在水深火热中度过。
“你就这么扔下我不管?瞧瞧,瞧瞧吧,我生养的白眼狼,还有天理吗?”妈妈在背后尖声叫骂。她很快出了家门,走进炽热如火的阳光下,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泪水亮闪闪地流着。她穿过人群,很快到了教堂前的简易车站。班车敞开着门等客,车上空无一人,司机不知哪里去了。她把拉杆箱安放到车上,然后下车,朝紧闭着门的小教堂走去,她知道有一个侧门,可以从那里进入到教堂里。她很快进了那个侧门,进入阴凉的教堂里。教堂空无一人,巨大的十字架立在教堂的宣讲坛前。她一下子跪在十字架前,颤抖着摸索出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她哽咽着,泪流满面,把十字架挂坠举到唇边亲吻,默念起来:主啊!宽恕我这颗耿耿于怀的卑微的心吧!宽恕那些有罪的灵魂吧!宽恕你可怜的孩子,宽恕一切吧……
她呜呜咽咽的,渐渐放声哭了起来。
(选自《飞天》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