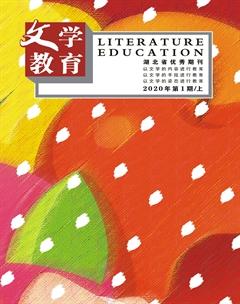黄榆笔记
葛筱强
麻 雀
要说些什么呢?一看到黄榆林里纷飞的麻雀,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在与土地难分难解的命运里,我一直觉得麻雀和乡下普通的人群最为相近相亲。
在某种意义上讲,麻雀就是在土地上劳作的人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因为,“它们是鸟在世上的第一体现者。它们的淳朴和生气,散布在整个大地。它们是人类卑微的邻居,在无视和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它们以无畏的献身精神,主动亲近莫测的我们。没有哪一种鸟,肯与我们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苇岸《大地上的事情·三十》)
看到麻雀,我就想到自己在乡下院落里日渐衰老的父亲母亲,以及众多仍在乡下瘠薄的土地上不倦地进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四时劳作,为了填饱肚腹的亲人们。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和念头,是因为麻雀仅在有人类活动的环境出现,一般营巢于人类的房屋处,如屋檐、墙洞。即使在野外,它们也多筑巢于有人类出没的、有很多洞的老树群中。它们的巢不工整,筑巢材料的种类很多,包括干草、羊毛、羽毛等,很像东北乡间农人用泥土筑成的房屋那样,疏阔随性。同时,它们性格活泼,胆大,易近人,好奇心较强,像乡下野性十足的孩子。一年四季,除了繁殖、育雛阶段之外,麻雀是非常喜欢群居的鸟类。每当秋季来临,数百只乃至数千只的麻雀翔于蔚蓝的天空之下,是极其常见、也是极为壮观的景象。在白雪皑皑的冬季,它们则结成十几只或几十只一起活动的小群。值得一提的是,麻雀和其它许多小型雀不同,聪明机警,有较强的记忆力,如得到人救助会对救助过它的人表现出一种来自天性的亲近,而且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在文学家和诗人的笔下,麻雀虽然是一个弱小的代名词,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它也有伟大的一面,特别是在育雏时往往会表现得非常勇敢。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曾在他的短篇小说《麻雀》中记载过一只亲鸟为保护不慎坠地的幼鸟,以其弱小的身体面对一只大狗而不退缩的感人场面,不能不让心怀悲悯的人们感动。如果把麻雀喻为一种乡下的植物,我认为野葵花最为恰切,它们的形象,如同当代诗人蓝蓝笔下写的那样:“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回来。天色已近黄昏/她的脸,随夕阳化为/金黄色的烟尘/连同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
喜 鹊
在漫漫的榆林上空,最常见的鸟还有一种,就是喜鹊。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在我居住的这个地方,对人类尚有一丝亲近之感的东北留鸟里,除了麻雀,就要数喜鹊了。在辽阔的北方,哪里有村庄,哪里就有喜鹊黑白相间的曼妙身影和单调响亮的叫声;哪里有高大的白杨林,哪里就能看到喜鹊用枯枝、杂草和泥土建造的家。
虽然喜鹊在自己安居的巢穴内壁和巢底垫有兽毛、鸟羽和纤维等软质材料,但它仍显粗糙简陋。每次望见它,我就会不期然地想到乡下贫穷人家破败的、几近倾颓的土屋,令人担心它是否会抵挡得住下一场大雨或下一场暴风雪的袭击。而实际上,喜鹊搭建的这个看似简单的巢穴,非常结实耐用。一个朋友和我说,她小时候曾拆过一个被喜鹊废弃的巢穴,枯枝与杂草交织在一起,真可谓盘根错节,拆起来并不十分容易。
作为北方的留鸟,喜鹊的外形美丽大方,头颈皆油黑发亮,在阳光的照耀下微微闪着紫色的光辉;背部虽也是黑色,但散发着蓝、绿的光泽;腰部灰白,肩羽纯白,整个身体远远望去像披了钢琴的键子。喜鹊多栖息和活动在村落旁边、空旷的田野或稀疏的树林子里。如果是在秋天,并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漫步于乡间的村旁或树林间,你就会看到成群的喜鹊时而缓缓地鼓动双翅飞起在空中,时而又落在田地里进行觅食。落在地上的喜鹊,前进的姿势一般是跳跃的,并不时地上下摆动如燕尾服后襟般的尾巴,彰显出一种乡间士绅的派头。
出于对喜鹊的喜爱,我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诗中写到过它。记得是前年吧,我在乡下,望着风中翻飞的成群喜鹊,内心无限温暖,充满了说不尽的柔情。回到家后,我在当天的日志里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是你,让我在黎明的风中/醒来。//草原上的野葵花,/卷起大片大片令人颤栗的/金黄……/仿佛秋天中的深渊。//这就够了。被阳光加冕/爱就不再卑微。你/划破天空的翅膀和/黑夜般喑哑的倾诉//让我心怀疼痛/和无尽的羞涩/并把目光深深地垂向胸口。/仿佛一瞬间/就把一生的守望交付……”(《风中的喜鹊》)
百灵鸟
夏天来了,我选了个晴朗的日子又一次来到兴隆山镇——这个座落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东部边陲的小镇,也是黄榆林漫山生长的地方。
这是上午,走在绿荫垂地的黄榆林里,我的耳边忽然传来蒙古百灵高亢嘹亮且婉转动人的叫声。这亲切久违的百灵鸟的叫声,在我小时候家乡的草甸子上是经常能够听到的。而现在,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几近成了绝响,更不用提居住在城镇里的人们了。一看到蒙古百灵在天空中载歌载舞的模样,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在这样一幅场景:蓝天白云之下,碧绿草原之上,衣着朴素的、聪慧而美丽的蒙古族少女,骑在疾驰的马背上,随风摆动的裙襟和明亮清澈、音域宽广悦耳的长调一起翻飞。草原上的蒙古少女和天空中的蒙古百灵鸟真是声气相求的天然姊妹。
在我简单的心里,一直觉得,作为生活在广阔草原上的留鸟,百灵鸟才是大草原真正的“主人”。它们食性博杂,既食草籽,也食昆虫,且对气温适应性极强,既抗严寒,亦耐高温,更为可贵的精神品质在于,它们对于自己所居何处,哪里饮食,皆了然于胸,尽在掌中。每天天一亮,这些超级歌手就会成群地飞翔于草原上空,给田间辛苦劳作的人们带来一场盛大“音乐会”的快乐。然而令人心忧的是,近些年来,在辽阔草原上出现了难以觅见百灵鸟踪迹、难以听到百灵鸟美妙歌声的现象,主要缘于一些人受经济利益驱动,“良心被铜臭粘封”,他们或布下大网,或下药毒杀,猖獗地盗猎百灵鸟,使这草原上的精灵每年在数量上锐减得惊人。
真是无法想象,没有百灵鸟的草原还是草原吗?没有百灵鸟的黄榆林还会充满灵动的气韵吗?耳朵听着百灵鸟迷人的音调,我在心里默念着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那句话:“我逃往何处?你充满了世界,我也只能到你身上逃避你。”
小毛驴
我的父亲老了,年至古稀,腿脚不再灵便,重体力的农活都干不动了,田间耕种对于他来说已是陈年旧事。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出行方便,他养了一头毛驴。
在我看来,这头毛驴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也很讨人喜欢,铁灰色的皮毛,四蹄雪白、结实,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不像我,眼睛小,还近视,离开眼镜世界就变得模糊和暧昧,也分不清杨树和柳树。更重要的是,我离老家远,家里的琐事出不上力,还不如这头毛驴,让父亲有个生活中的依靠。从某种角度上看,对于晚年的父亲来说,我这个儿子还不如这头驴管用。所以,每当我回到老家,面对这头忠实可靠的毛驴,就想起安德烈·纪德说过的那样:“愈是虔诚的人,愈怕回头看自己。”我觉得我不是怕回头看自己,而是怕看到这头毛驴,虽然我发自内心地对它有着无比的尊敬甚至敬重,因为它对我的父亲来说太重要了,但它像面镜子,能照见内心日渐虚弱的我。
这个秋天,当我再次面对它,为它拍几张照片留念,也表达一下我对它的亲近之意,但它不理解,也不屑于此,并扬起骄傲的鬃毛向我踢出愤怒的蹄子。它之于我的陌生感,乃至激烈的敵意,我并不在乎,毕竟我是人,有思想,不像这头驴,头脑简单,思维单一,即使它不理解我,我也能理解它,我不仅理解和敬重它,还发自内心地在暖暖的秋阳下为它写了一首短诗:“今天,你不必再负重于轭下/在宁静的院子里,你甩一甩/毛茸茸的尾巴,你敏感的睫毛上/因为有小小的幸福留存/日子就忽闪闪地发亮//我深深地弯下疲倦的腰身/并且,动情地张开双臂/揽住你柔软的颈项,甚至/想亲吻你的泪水/可今天,忽然流泪的/为什么是我呢?”(《小毛驴》)
野 兔
我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遇见它的。看到它,我不禁想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的一句话:“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我想,在这个冬日的下午,不是我遇见了温柔的奔跑的野兔,而是野兔出于某种神示的信任,故意遇见了我。
在我的眼里,这个浑身几乎没有脂肪的小家伙儿实在是太可爱了,它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出来并帖着草丛奔跑,一定是为了寻找带着露珠的可口食物。此刻,它和我有了短暂的相遇,并让时间定格于我们的相互对望中,虽然这样的时刻有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但在我的心里,却长似千年,超越了我有生之年度过的所有时光。它的目光多么柔和啊,因为我一脸的平静,它的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之色;我也因它毫无敌意的眼神和灵巧的腰身内心充满无边的喜悦之情。
记得荣格还曾这样说过:“一种有人引导的生活比起一种缥缈的生活要好得多,丰富得多,而且健全得多了。”那么,因为有野兔的指引,我心向自然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好起来,丰富起来,健全起来,有野兔偶尔相伴的生活,或许才是真正的生活,因为有了野兔的存在,并且我热爱着它,它也不惧怕我,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得了永生的人,就像《五十奥义书·大林间奥义书》中说的那样:“导我出非有,以至于至真。导我出黑暗,以至于光明。导我出死亡,以至于永生。”
(选自《芒种》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