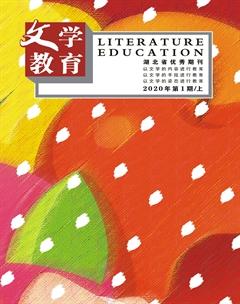诗歌是一种反熵的媒介
熵本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术语。如果能量在空间中分布得越混乱,熵就越大。从物理学的这种规律中进行迁移,耿占春看到了话语、文字、真理、思想等也难逃这样的“晚景”和命运。因此他认为,一个活着的人要具备反熵的意义。
活着的人只有具有一种责任感、正义感、神圣感的时候,才可能具有一些反熵的力量,尽管到最后也是“安静如同宇宙最终的沉寂”,或者难逃一死,或者被人遗忘,或者在某种历史书中只占据零星页面的叙述。而一个诗人,要想具有反熵的价值,也必须使自己的思想一开始出现就摆脱“闲谈的面孔”,摆脱使思想一出生就徒具形式的窘境。在诗歌中,耿占春写下了许多“为之担忧的话语”。比如在《旅途之歌》中,他为身处困境中的自我担忧;在《盛世危言》中,他从盛世看到潜在的危机,为此写下了警世的话语:“我唯一所求的,是别堵上/那些还能说话的嘴,别侮辱//本来就有限的智商,我承认/它是几希禽兽的最后一点区分。”其实耿占春深明拿破仑“当代的悲剧,就是政治”这句话的含义,他深知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境况之一。在《论恶——读〈罗马史〉》中,他担忧“每个信仰强权的人/都在为新神开光要求血的祭礼”;在《论语言》中,他深深地为语言带来的各种危机担忧。当权力成为最高真理,成为唯一正确的意志,它便会成为一种绝对的存在。于是,强权可以强迫他人流血牺牲,可以制约新闻自由,可以拿语言来控制思想,甚者暴力判决、杀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在这样无法摆脱的境况当中,作为有某种角色的个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耿占春在近二十年前就曾为我们传达出其内心的这种普遍性体验:“在无处不在的吞并一切的权利组织和网络中,一个人难能有自由的本真的生命形式,也许他只有可以称之为失去自我丧失灵魂的那种体验。”对于这个不甚理想的世界,他是有深切感知的。
此外,在《世界美如斯》中,他还曾担忧“惊梦的阐释者/曾经改变过/人类的编年史”,担忧“如今只有一个魔咒/还未曾实现——‘美,能拯救世界”;在《论快乐》中,他也指出“当快乐出现在有权力感的地方/它就与厌倦等同”。总之,耿占春在他的诗歌中不厌其烦地表达着他的担忧,他不希望看到熵在最后的狂欢。尽管在谈论传统读书人责任的时候,他认为阅读与书写可能是对责任的一种逃避或偏离,“把阅读与书写转变成一种快乐,把责任降低到自身的快乐或‘语言的欢乐”但这无疑也是“他的自卑自谦”。但至少语言可以帮助实现对良知的一部分救赎。
耿占春指出,诗歌是一种反熵的媒介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非封闭、反耗散的结构。“伟大诗篇的话语是一种非封闭的象征结构。”耿占春认为,诗歌要保持持续性的能量,要在历史中一直保持它的“秘密”,就要持一种开放的结构,否则当它封闭、固有的意义分散殆尽,其生命也就结束了。为此,耿占春喜欢诗歌持一种旁白的姿态,青睐诗歌的画外音,期待诗歌成为“未完成的陈述”,厌倦诗歌“没有个性的经验”及其“致命的单调”。鉴于这样的诗歌认知,耿占春在写作中也贯穿了同样的理念。他的《一首赞美诗》,其实并不是一首用以赞美的诗。在这首诗中,诗人其实是在进行一个诗的呼唤,是以一首诗来唤起另一首诗:“浮云诡秘看苍山,忆起一首诗——”这即是一种“未完成的叙述”。从结构经营上看,他的《精神分析引论》也具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架构,尽管全诗前三节均以理性的逻辑在建构一种“瞻对”的视角,第四节又以理论归结的方式收束了全诗,这种推导思路分明,并无任何向外突破的“犄角”,然而一旦联想到诗的题目“精神分析引论”,我们的视野就豁然打开了:全诗与“精神分析引论”是一種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一个人就必须是又不是另一个人”?它与弗洛伊德有内在思想上的一致吗?此外,《辩护词》一诗也是如此,前两节还在探讨人类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第三节就以比喻的修辞引入了诗人和上帝,最后一节又抛出了“漫游奇境的爱丽丝”的“辩护”。那么,诗人到底意在以什么为镜,又想鉴照出什么呢?他期望以“辩护”为幌子来达到什么样的“修行”?这首诗制造了美妙的画外音,它寄望他的读者去进行一番有趣的找寻。
诗的这种开放性结构当然与语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占春对于语言是敏锐的。他看到了语言有一种分裂的力量。这是他的诗歌写作的一个秘密所在。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