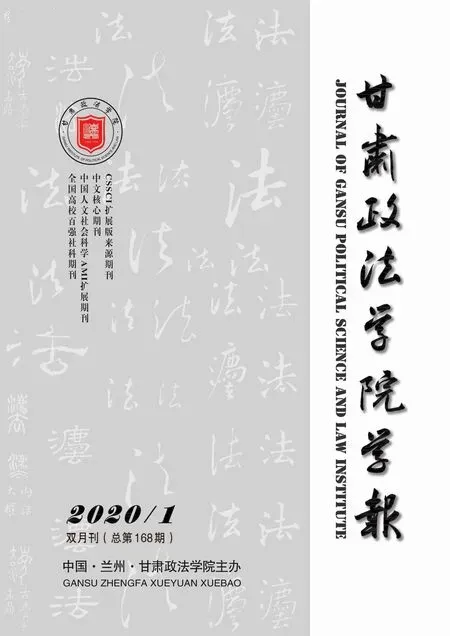复合性不作为强制执行制度之体系化构建
王 慧
不作为请求权强制执行(以下简称不作为强制执行)属于非金钱债权强制执行范畴,是指“实现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容忍他人之行为,或禁止债务人为一定之行为之权利而为之执行。”(1)根据不作为给付内容的不同,债务不履行的情形可分为一次性不作为债务、反复性不作为债务和继续性不作为债务。债务人一旦违反一次性不作为义务(如不得泄露商业秘密、不得演出等),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即告消灭,无实施强制执行的必要,债权人仅得另诉请求赔偿。本文所探讨的仅指反复性、继续性不作为的强制执行。参见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0页。基于不作为请求权面向未来的预防属性,法院所作出的不作为裁判具有“展望性”(2)陈石狮:《不作为请求之特定》,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三)》,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57页。特征,既包括要求被告停止正在进行的、可能再次(或首次)发生的侵害行为;亦包括为真正实现实体权利,要求债务人实施的除去有形侵害行为结果(如阻碍通行的建筑物、侵害商标权或专利权的产品等),或者采取预防反复性、继续性侵害行为的措施(如安装防止噪音的设备、实施防止环境污染的技术方案等)。由此,不作为强制执行的执行内容具有复合性特征,且有时不是一次强制执行即告终结。质言之,不作为强制执行在执行标的的特定、执行措施的适用以及执行完毕后反复、继续侵害行为(以下简称重复侵害行为)的应对等方面存在诸多难题。(3)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教授曾指出,在当今私法中,不作为请求权是“最为晦暗不明的领域,从理论基础到构成要件乃至法律后果,无不疑窦丛集、聚讼纷纭”。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
近年来,我国不作为强制执行案件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加,已成为“执行难”的重要成因之一。(4)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强调执行标的复杂是“执行难”的成因之一:“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形式除金钱给付之外,还包括腾退房屋、赔礼道歉、赡养老人、抚养及探视子女等行为给付,执行难度较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018年10月24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例如,物权纠纷中停止侵害相邻权、防止不可量物侵害等裁判的执行,人格权纠纷中针对停止侵害健康权、信息隐私权、环境权等裁判的执行,知识产权纠纷中停止侵权、停止销售等禁令裁判的执行,以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股东制止董事会违法行为、制止解任的董事执行事务的执行等。然而我国立法并未明确不作为强制执行制度,学理上亦缺少对不作为强制执行的系统化研究,特别是未厘清不作为与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本区别。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六稿)》第244条(5)《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六稿)》第244条:执行依据命令执行债务人不得为一定行为或者容忍他人为一定行为,执行债务人不履行的,应当责令执行债务人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依妨害强制执行的有关规定对执行债务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以依执行债权人的申请,责令执行债务人交付费用,除去执行债务人行为的结果。在《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第323条基础上,对不作为强制执行程序作出专门立法设计。但是该条文缺乏与实体法规定中预防型民事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有效衔接,且有待于结合司法实践以及域外最新立法与理论研究成果加以完善。
由于立法供给与理论研究的不足,司法实践中,执行机关仅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52条、第25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03条、第504条关于可替代行为执行与不可替代行为执行的条款实施执行。因此,执行机关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不作为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处理、执行程序的不规范等产生的执行异议不在少数。例如,在宋成民等与异议人候泳及刘梅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6)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8执复1号执行裁定书。类似的案例参见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执复41号执行裁定书、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9)湘0321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等。中,法院判决被告“对位于雅安市雨城区中大街95号底楼与七被告商铺相邻的交通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执行机关将上述执行内容解释为“拆除门面的卷帘门和通道的隔离墙,并清除堆放的杂物”,被执行人认为执行机关解释执行依据给付内容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遂提出执行异议。再如,在王春泽与王金章排除妨害纠纷案(7)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2执复47号执行裁定书。中,执行机关按照执行依据所载内容“清除堆放在王春泽房屋东侧、原排水沟处的杂草堆,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终结执行后,被执行人实施在相邻公共道路上挖深水槽、种蔬菜等侵权行为,申请执行人遂对终结执行裁定提出异议。上述两个案例均属于不作为强制执行中的“执行难”,前者系不作为执行内容不明确所致,后者因不作为义务的反复性、持续性而产生。
在“着力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加快制定强制执行法”的背景下,对不作为强制执行制度进行专门立法,进一步强化执行工作的精致化与科学化,应为势之必然。本文拟从不作为请求权基础出发,界定不作为给付义务的复合性,并以此作为实体基准,提出构建复合性不作为执行措施与程序规则的具体建议。
一、 复合性不作为执行内容之具体化
(一)不作为执行内容不明确与执行补正应对方式之不足
按照依法执行原则,执行机关必须依照执行依据所明确的给付内容确定执行标的,并对其采取执行措施,从而保证生效法律文书的稳定性、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以及公权力的公信力。(8)肖建国:《民事执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97页。按照审执分离原则,生效裁判文书“给付内容明确”是执行依据成立的实质性要件。由于不作为给付义务是具有预防性质的消极给付,既可以通过积极的作为(除去行为结果或采取预防措施)完成,亦可以通过消极的不作为(停止一切行动或容忍)完成,因此,较之金钱给付、物之交付等裁判内容,不作为裁判主文给付义务的具体化颇为困难。加之不作为具体履行方式的多样性与可变性,司法实践中,不作为执行内容不明确问题屡见不鲜,“严重危害了司法权威,也成为引发申诉信访的重要来源”。(9)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5页。例如,上述共有权纠纷案中,执行机关对执行内容进行解释,引发执行异议。又如,王某与朱某民事执行案(10)象山县人民法院(2013)甬象执民字第1111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内容为“停止侵害”,执行机关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朱某已自行对电梯设施进行了改造,且噪音有所下降,遂裁定终结执行。申请执行人王某以未执行到位(未到达停止侵害的效果)为由,提出执行异议。
为解决上述问题,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以下简称《立审执协调运行意见》)规定了不作为裁判的具体化要求,即“明确停止侵害行为的具体方式,以及被侵害权利的具体内容或者范围等”“明确排除妨碍的标准、时间等”。同时,针对基准时后可能出现执行内容不明确的情形,规定根据作出法律文书法院的不同,执行机关通过书面形式征询审判部门意见,由原审判部门进行答复或补正。这种审执衔接的补正机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由于缺少具体的操作说明和相应的救济机制,实务界难免产生“如坠云雾之感”;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学和强制执行法学原理。(11)陈斯、谢奕:《论执行依据不明的救济机制构建——以审判权与执行裁决权“相容解释模式”为视角》,提交首届民事执行论坛论文。邱兴美:《执行权与审判权之界域研究——以执行救济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第106页。
事实上,不作为执行内容的特定难题根源于不作为请求权面向未来的预防属性,涉及民事诉讼法理与立法技术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认为无外乎两种解决思路:一是考虑不作为强制执行的复杂性,赋予执行机关实体裁判权,重新确定不作为实质内容,使执行程序具有灵活性和简化性;二是为了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特定不作为给付内容,即法院通过释明,允许原告补正诉讼请求,从而避免裁判中作出抽象的略式表述。任何一个思路都不是唯一准确的,只可作为法律解释来处理。各国可结合本国的立法、诉讼文化以及习惯等,探索本土化的做法。(12)[日]丹野達:《抽象的差止判決の執行》,载《东洋法学》1995年39卷1号。本文主张,应从我国不作为请求权实体基础出发,结合审执分离改革,通过裁判主文的具体化与审执分离的宽缓化系统性予以解决。
(二)不作为请求权内涵的复合性与裁判主文的具体化
不作为强制执行的实体法基础是民事实体法上的不作为请求权。不作为请求权作为法律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第1款(13)《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第1项:“所有权以因侵夺或者扣留占有之外的其他方式受到侵害的,所有权人可以向妨害人请求除去侵害。所有权可能继续受到侵害的,所有权人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参见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全条文注释》(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67页。,该法条前段规定了排除妨害请求权(Beseitigungsanspruch),后段则规定了不作为请求权(Unterlassungasnspruch)(14)《德国民法典》的不同译本对第1004条第1款第二句的翻译内容有所不同。陈卫佐教授将其译为“不作为请求权”,郑冲教授将其译为“停止侵害(妨害)请求权”。在相关译著中,张双根教授在翻译鲍尔·施蒂尔纳所著《德国物权法》(上)时,将其译为“妨害防止请求权”;吴越教授和李大雪教授在翻译沃尔夫所著《物权法》时,将其译为“不作为请求权”;郑冲教授在翻译施瓦布所著《民法导论》时,则将其译为“停止侵害请求权”。。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不作为请求权被扩张解释为排除妨害请求权和不作为请求权的上位概念。其中,排除妨害请求权针对已存在(或正在进行)的妨害,权利人可以据此请求义务人除去该妨害;(15)王洪亮:《论侵权法中的防御请求权》,载《北方法学》2010年第1期。不作为请求权是真正意义的不作为请求权。(16)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09页。从19世纪开始,德国所有权保护中的不作为请求权出现一般化趋势,即以物上不作为请求权为基础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不作为请求权理论体系,包含了侵权法、知识产权法以及商业竞争法等多个领域。例如,在人格权保护方面,法官通过整体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承认对人格权的保护,即“广泛采用停止侵害的方式,预防侵害人格权行为的发生”“请求撤回声明权利的行使”以及“补充、更正等请求权”。(17)王利明:《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在商业竞争法方面,《德国不作为之诉法》规定不作为请求权包括不作为请求权、排除请求权及信息请求权三个层面的内容。(18)吴泽勇:《德国群体诉讼研究——以德国法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日本在德国法基础上,通过现行《日本民法典》第414条(强制履行)第3项(19)现行《日本民法典》第414条第3项:“以不作为为标的的债务,可以请求用债务人的费用,消除债务人行为的结果或者请求为将来作适当处分。”参见《最新日本民法》,渠涛编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2017年,日本法务省同时修改民法典与民事执行法,删除现行《日本民法典》第414条第3项,将其归入《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1条第1项。进一步厘清不作为请求权的多元化内涵。详言之,日本法上的不作为请求权包括单纯的不作为,以及因违反不作为义务而在现实履行中需实施的除去处分或预防处分。例如,债务人因侵犯专利权,不仅需要停止销售侵权产品,还需废弃判决书载明的侵权产品(20)东京地方法院平成4年10月23日判决。参见[日]增井和夫、田村善之:《日本专利案例指南》(第4版),李扬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页。,即为除去因违反不作为义务所产生的行为结果;又如,为防止噪音侵害,可要求债务人安装一定的设备,即为将来作适当处分。日本学者中野贞一郎教授指出不作为不同于一般“给付债务”,其具有执行法上“形成债务”的性质。(21)[日]中野貞一郎、下村正明:《民事执行法》,青林书院2016年版,第810页。
我国民法体系中未规定物权请求权,而是将其法律效果作为侵权责任形式,在《民法通则》中首创了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我国实体法领域并未正面规定不作为请求权,而是采取直接规定预防型民事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方式迂回认可了不作为请求权。(22)王利明:《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例如,我国《民法总则》第179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19条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民事责任。《著作权法》第47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均规定了“停止侵害”民事责任。我国民法学界和实务界关于不作为请求权的具体意涵存在多种解释。魏振瀛教授将停止侵害解释为针对正在进行的、准备进行侵害或有继续侵害可能的行为;(23)魏振瀛:《民事责任与债分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王利明教授主张停止侵害针对已造成实际损害,“受害人有权请求法院制止正在进行的损害”;(24)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张谷教授则主张“停止侵害”可能是本土化产物,也可能是受到东德立法的影响,旨在扩张排除妨害请求权和不作为请求权的适用范围。(25)张谷:《作为救济法的侵权法,也是自由保障法》,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将《民法总则》中的“停止侵害”解释为适用于“正在进行或者持续进行的侵害民事权益的行为,目的在于制止侵害行为”;排除妨碍“主要是针对静态的行为适用”;消除危险适用于“行为人的行为或其控制的物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造成危险的情况”,“具有典型的预防性特点”。(26)同前注〔9〕。
无论上述何种解释,不作为请求权内涵的复合性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本文认为,根据侵害行为的发生时间和结果样态,不作为请求权包括针对已发生侵害或侵害处于持续状态的不作为请求权,针对已发生侵害且存在侵害结果的除去性请求权,以及针对具有重复发生危险或未来具有首次危险的预防性请求权。不作为请求权复合性内涵促成不作为给付内容的复合性,包括作为基准性的停止性不作为,以及具有派生性的除去性作为和预防性作为。因此,法官作出不作为裁判时,须“清楚地确定不作为义务的具体内容,以使得任何人都理解其含义”,从而对“债务人或代替履行的第三人给予指引”。(27)同前注〔8〕。申言之,不作为裁判主文包括实现不作为请求权的具体行为方式(停止性不作为、除去性作为、预防性作为)以及实施上述行为的样态、场所、措施等。(28)[日]小山昇:《訴訟物論集》,有斐閣1966年版,第47页;[日]村松俊夫:《法律実務講座民亊訴訟第一審手続(一)》,有斐閣1984年版,第97页。转引自[日]金炳学:《知的財産権侵害差止請求における訴訟物の特定と執行手続について:生活妨害訴訟における抽象的差止請求との比較検討を中心として》,载《法政研究》2006年第72卷,第615页。
《立审执协调运行意见》仅仅要求裁判主文明确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与“被侵害权利的具体内容或者范围等”,尚未达到具体明确的标准,仍存在发生执行内容不明确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在诉讼阶段,法官需通过履行释明义务,保证当事人之间充分的攻击防御,实现不作为裁判给付内容的具体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关于民事判决书的撰写要求,在不作为裁判主文中可采用“括注”的形式详细说明不作为给付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对于仅需债务人停止侵害行为的,可表述为停止侵害(停止实施的具体行为内容或容忍他人行为的内容)。例如,停止侵害(禁止采取20点至24点之间让债权人听到狗吠的饲养方法)。
第二,对于正在实施或可能持续实施侵害行为、且存在有形侵害物的(如阻碍通行的建筑物、侵害知识产权的产品等),可表述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包括除去特定妨害物、销毁特定物品的具体方式、标准等)或消除危险(包括安装特定设备的具体规格、对侵害源技术处理的具体方案等)。例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拆除特定位置的特定搭建物)(29)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韶中法民一终字第1032号民事判决书。;又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更换特定位置空调外机的朝向)(30)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213号民事裁定书。。
第三,对于可能持续实施的侵害行为、且不存在有形侵害物的(如噪音侵害、知识产权侵权等),可表述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具体方式同上)。例如,立即停止侵害申请执行人和美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第3052162号、第3052163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即停止在经营场所使用“如家”文字和服务标识及变更字号,变更后的字号不得含有如家文字。(31)海宁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1执1172号执行裁定书。
(三)执行机关特定不作为执行内容的宽缓化路径
在不作为强制执行阶段,对执行要件的审查涉及较多的实体问题,包括债务人是否已停止裁判所禁止的行为、实施除去性作为或预防性作为,是否可以变更具体履行方式以及下文所探讨的是否重复实施侵害行为等。例如,原告与被告就生产、销售“卡通澳妮”牌产品侵害“奥妮”等涉案商标发生争议,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涉案商标的侵权行为。一年后,被告在其网站上宣传“卡通澳妮”。若原告以该不作为判决提出执行申请,对于该侵权行为是否属于执行内容的识别,即为实体裁判问题。(32)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18号民事裁定书。
对此问题,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趋向于缓和审执分离原则,赋予执行机关一定的实体裁判权。例如,德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承认抽象的不作为诉讼请求和裁判的合法性,规定作为、容忍及不作为的强制执行由受诉法院而非司法辅助官行使管辖权。(33)德国设置了执行吏、执行法院以及受诉法院的三元制执行机构,其优点在于可依执行对象的种类、执行方法以及内容的差异,根据执行机关的特点,分别实施强制执行,以确保执行的迅速与实效。参见张登科:《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2012年版,第565页。同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1条规定了受诉法院对于作为及不作为执行做出裁判前,应讯问债务人。日本在借鉴德国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34)日本学者的相关著作参见[日]竹下守夫:《生活妨害の差止と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案要綱案第二次試案における関連規定の検討》,载《立教法学》1973年第13期;[日]丹野达:《抽象的差止判決の執行”》,载《东洋法学》1995年39卷1号;[日]川嶋四郎:《差止救済過程の近未来展望》,日本评论社2006年版;[日]安永祐司:《抽象的不作為請求?判決と強制執行に関する考察》,京都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在生活妨害和公害诉讼中承认执行机关对于抽象不作为执行内容作出实体裁判,例如“尼崎大气污染公害案”“名古屋南部公害案”等。(35)谢航:《日本法上的差止请求权》,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20页。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学者指出,在不作为强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并非单纯从事强制执行的机关,而有介入债权人与债务人间事物义务为审酌的空间,从而有缓和向来严守的‘执行依据作出机关’与‘执行机关’分离理念的可能性。”(36)刘玉中:《不行为(不作为、制止)请求诉讼与强制执行》,载《月旦法学教室》2014年第143期。
有鉴于此,我国在审执分离改革中有必要考量不作为强制执行案件的特殊性,对审执分离原则做宽缓化处理,可考虑以下两种解决路径。第一,实现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层面的宽缓化,即引入执行听证制度,由执行裁决庭的执行法官负责听证程序的实施。可借鉴德国立法的相关内容,通过审询程序判断实体问题(如必要措施的内容、已履行的抗辩是否妥当等),从而确定执行标的并适用相应的执行措施。第二,执行机关与审判组织分离层面的宽缓化,即借鉴德、日等国家的做法,将行为请求权执行案件交由审判法官负责。事实上,在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中,针对环境案件的特殊性,部分地方法院采用“四合一”模式,即民事、行政、刑事、执行均由环保法庭负责,可作为审执分离改革中的例外尝试。
二、不作为执行标的之本旨执行
(一)本旨执行与代偿执行并行的现状
执行标的是指“民事执行行为作用的、用于满足债权人实体权利请求的客体。”(37)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执行标的是确定执行措施的基础。根据执行机关所确定的执行标的是否与执行内容相符合,大陆法系国家的执行标的确定原则可分为代偿执行原则与本旨执行原则。(38)德国学者将执行措施适用原则分为关涉执行标的确定的实质性原则,以及关涉执行措施适用顺序的体系性原则等。参见许士宦:《金钱及物交付执行之间接强制》,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08年第37(2)期。代偿执行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旨在将作为与不作为给付转化为支付金钱,并依照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使债权人取得金钱以满足其债权。日耳曼法上的本旨执行原则是通过对债务人实施人身自由或金钱上的压迫,迫使其履行义务。代偿执行的优点在于尊重债务人的人格,但金钱代偿不利于行为请求权的真正实现;本旨执行虽能够保证债权人实现请求权本来的内容,但“有违尊重债务人人格之理念”。(39)同前注〔33〕。
我国尚未明确不作为执行标的的确定原则,执行机关对执行标的的确定以及执行措施的适用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根据现行立法内容,执行机关可适用间接执行和替代执行实现不作为的本旨执行。其中,间接执行措施包括对债务人财产和人身产生不利益的措施。对债务人财产方面的执行方法包括罚款和迟延履行金。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05条的立法内容,对于不可替代行为和不作为,执行机关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1款第6项规定,对债务人采取罚款措施。罚款须上缴国库,不具有充抵债务的作用。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07条规定了适用于非金钱给付义务的迟延履行金措施。迟延履行金不同于罚款,应参考损害的存否和大小直接向执行债权人支付,具有督促债务人自动履行义务和填补债权人损失的双重作用。(40)同前注〔37〕。对债务人人身自由的执行方法包括拘留以及限制出境、纳入征信系统以及限制高消费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对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可根据妨害民事诉讼的规定,对债务人适用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强制措施。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231条规定了对被执行人限制出境、纳入征信系统及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的执行措施。2010年和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颁布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41)2015年,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1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和《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4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1条:“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对不作为派生性执行标的——除去性作为和预防性作为,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2条采取替代执行措施。
然而,实践中部分执行机关为便于执行,直接将不作为执行标的转换为金钱给付义务。例如,在申请复议人与申请执行人王正元相邻通行纠纷一案中(43)文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文中执复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判决主文为:“由原告王正元与被告王正权保持位于××市×××办事处×××区×××村相邻居住通行道路的通行现状”。文山市法院“为了确保案件的顺利执行”,在执行中直接作出冻结债务人存款的执行裁定,债务人对此提出的执行异议。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上述裁定。此外,在混合给付义务执行案件(44)所谓混合性给付义务是指在一个案件裁判中,同时包括广义上作为义务(含金钱支付义务)和不作为义务。参见洪文澜:《民法债编通则释义》,会文堂新记书局1993年版,第189页。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知识产权案例的诉讼请求进行梳理,约98%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原告同时提出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中,部分执行机关所作出的执行通知或执行裁定仅包括针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回避不作为义务的执行。例如,在南京妍之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武佩梅侵害商标权纠纷案(45)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执50号执行裁定书。中,执行依据为停止侵害商标权及赔偿损失,但是执行裁定书所确定的执行标的仅为赔偿损失。此种处理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是,无法实现不作为判决的预防性机能,债务人可能继续违反不作为义务。
(二)本旨执行原则的确立
现代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中,注重“调和尊重债务人人格尊严原则与实现债权人权利的实效性与本旨性”(46)赖来焜:《强制执行法总论》,元照出版社2007年版,第692页。,倾向于适用本旨执行原则,即通过制定有效的执行措施保证行为请求权的完全实现。换言之,关于作为与不作为请求权执行的发展趋势是朝着扩大本旨执行原则的方向发展。
德国在编纂民事诉讼法时,确立了本旨执行原则,对于全部债务原则上承认本来的履行请求权及执行请求权。为确保执行依据所载债权的真正实现,《德国民事诉讼法》针对特定的请求权规定了对应的执行措施,“表达了强制执行制度以实现私法上权利为其本旨的基本观念,恰当地反映了强制执行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内在关系”。(47)江伟、肖建国:《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载《法学家》2001年第4期。《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87条规定了适用于可替代行为的替代执行措施;第888条和第890条(48)《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0条:“(1)债务人违反其不作为或容忍某作为的义务时,第一审受诉法院应依债权人的申请因每一次违反行为对债务人处以违警罚款,如仍不遵行,处以六个月以下的违警拘留。一次违警罚款的数额不得超过25000欧元,违警拘留不得超过两年。(2)在宣告义务的判决中如未对被告进行警戒时,第一审受诉法院应依申请在判处之前,预先进行相应的警诫。(3)法院依债权人申请,根据债务人以后所违反义务的行为发生的损害,判令债务人在一定期间提供担保。”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丁启明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分别规定了适用于不可替代行为、不作为及容忍义务的间接执行措施,分别为强制措施(Zwangsmitteln:强制罚款或者强制拘留)以及违警措施(Ordnungsmitteln:违警罚款或者违警拘留)。其中,强制罚款和违警罚款均需要上缴国库,不具有代偿执行的作用。如果债务人仍然不履行不作为义务,执行法院仍可再次选择罚款或者拘留进行处罚。日本最初奉行代偿执行原则(49)日本旧《民事诉讼法》第734条规定:“第一审受诉法院应依申请以裁定相当之期间,债务人如未于其间内履行,则命令按其迟延之期间为一定之赔偿或迳行损害赔偿。”其中,该损害赔偿金具有代偿执行作用,是法定或者裁定的违约金。,1979年日本制定民事执行法时,因受到德国立法思想的影响,转为奉行本旨执行原则。《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1条(替代执行)和第172条(间接强制金)分别规定了对于不作为派生义务——除去结果和预防处分的代替执行和间接执行制度。(50)现行《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1条第1项:“为实现民法第414条第2项或第3项规定的请求而实施强制执行,执行裁判所依据民法规定作出决定的方法实施。”第172条第1项:“对于无法依前条第1项的规定进行强制执行的作为或不作为请求权,可依以下方法强制执行,根据迟延的时间或者被认为适当的一定期间内未履行作为或不作为时,执行裁判所可命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可确保债务履行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典》,曹云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2页。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不作为执行标的的确定原则,亦经历了由代偿执行向本旨执行的转变。1942年,民国时期颁行的《民事强制执行法》第128条(不可替代行为请求权之执行方法)规定:“依执行依据,债务人应为一定之行为,而其行为非他人所能代为履行者,债务人不为履行时,执行法院得定债务履行之期间及逾期不履行应赔偿损害之数额,向债务人宣示或处或并处债务人于1千元以下之过怠金。”其中,过怠金具有代偿的性质,归债权人所有。1996年,我国台湾地区在修订“强制执行法”时,由于“赔偿数额难以估算,且易滋生争议,所以实务中几乎没有使用的案例,形同虚设”,故取消了过怠金和损害赔偿措施。(51)《“民事诉讼法”分类小六法》,元照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现行“强制执行法”第127条规定了替代执行措施,第128条及第129条(52)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29条:“执行依据系命债务人容忍他人之行为,或禁止债务人为一定之行为者,债务人不履行时,执行法院得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之怠金。其仍不履行时,得再处怠金或管收之。前项情形,于必要时,并得因债权人之申请,以债务人之费用,除去其行为之结果。依前项规定执行后,债务人复行违反时,执行法院得依申请再为执行。前项再为执行,应征执行费。”分别规定了适用于不可替代行为及不作为的管收、怠金等间接强制措施,旨在保证债权的现实履行。其中,怠金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故“归缴国库”,其数额以债务人对法院命令履行的怠慢程度及处以怠金后履行义务的可能性综合加以确定。(53)耿云卿:《实用强制执行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24页。
我国在不作为强制执行立法中,宜契合“民事执行法的发展趋势”,“贯彻债权人中心主义”(54)黄忠顺:《中国民事执行制度变迁四十年》,载《河北法学》2019年第1期。,确立本旨执行原则,规范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按照民法等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内容、期限、形态,以忠实地实现债权。(55)[日]竹下守夫:《日本民事执行制度概况》,白绿铉译,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6期。
三、间接执行与替代执行之顺位适用
(一)不作为执行措施适用原则比较与顺位适用原则之选择
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执行立法经验,为保证不作为执行标的的本旨执行,最为关键的是,确定与其执行立法指导思想与民事执行基本理论相符合的执行措施适用原则与程序规则(见下图、表)。根据执行措施是否与实现债权具有对应性,德国确立了执行措施特定原则(亦称为“一请求权一执行方法”原则),即法律明确规定对于特定类型请求权的执行措施,债权人对此无选择权;(56)江必新主编:《比较强制执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法国和日本施行执行措施并行原则,即当事人可任意选择适用间接执行或替代执行;我国台湾地区采用了执行措施顺位原则,即明确间接执行和替代执行的适用顺序。(57)同前注〔38〕。

图:执行措施适用原则之比较

国家或地区执行措施体系类型执行措施体系性原则执行措施的具体内容相关法条德国单一性执行措施特定适用原则间接执行(违警罚款、违警拘留)《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0条日本复合性执行措施并行适用原则间接执行(强制金)替代执行(除去结果、预防处分)《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1条、第172条、第173条我国台湾地区复合性执行措施顺位适用原则主:间接执行(①怠金;②怠金/拘留)辅:除去结果、替代执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29条
表:不作为强制执行措施具体内容之比较
1.德国:执行措施特定适用原则
德国立法者“在设定执行种类时,并没有单纯地从程序本身出发,而是更多地考虑执行程序所追求的私法上的目标。法律上所规定的执行种类是封闭的规范,既不可以被扩展,也不可以被彼此更换。强制执行的法定性比物权法中的物权种类法定性更为严格。”(58)同前注〔56〕。由此,在执行措施的适用方面,德国奉行执行措施特定原则,法律明确规定对于特定类型请求权的执行措施,债权人无权选择适用。换言之,“对每种执行种类适用的规定都是专属性质的,原则上无法适用于其他的执行种类”。(59)同前注〔56〕。《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0条规定了针对违反不作为义务的具有“惩罚性”的违警措施,包括每次不超过 25000 欧元的违警罚款以及6个月以下的违警拘留(不得超过两年)。违警措施发挥着多重作用,迫使债务人“停止不当行为”的同时,主动实施除去性作为或预防性作为。换言之,债务人出于恐惧心理,消除“维持侵害的状态”或“源泉”,除去“强制执行之前债务人已经实施的不当行为所引发的后果”,以及预防将来再次重复实施该不当行为等。因此,德国的“不作为强制性包含了要求债务人积极作为的内容”。(60)同前注〔8〕。
2.日本:间接执行与替代执行的并行适用原则
日本通过《日本民法典》第414条第3项以及《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1条、第172条构建了复合性不作为强制执行措施,包括概括适用于不作为的间接强制金,以及对于除去性作为和预防性作为的替代执行措施。同时,《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3条(61)为应对“执行难”,日本改变间接强制金的补充性。2003年,增加《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3条,扩大间接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对不作为、可代替行为及物之交付债务,经当事人申请,均适用间接强制。参见[日]谷口圆惠、筒井健夫:《改正保·执行法解说》,商事法务,第126-128页。转引自许士宦:《金钱及物交付执行之间接强制》,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08年第37(2)期。《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3条(节选):“第171条第1项规定的强制执行,当债权人提出申请时,执行裁判所可依前条第1项规定的方法实施。”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典》,曹云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3页。确定了执行措施并行原则,即债权人具有执行措施的选择权。对于不作为义务,债权人既可向执行裁判所提出间接执行申请,命令债务人向其支付一定数额的间接强制金,迫使其履行不作为义务;亦可申请代替执行,委托第三人或执行裁判所代为履行;抑或同时申请适用替代执行和间接强制金。
3.我国台湾地区:间接执行与替代执行的顺位适用原则
不同于德国对于“一请求权一执行方法”的恪守,亦不同于日本对于当事人执行措施选择权的充分保障,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29条确立了不作为强制执行中间接执行和替代执行的适用顺序,即对于不作为执行标的原则上采取怠金(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管收等间接执行措施,辅以除去债务人行为之结果及通知有关机关协助等方法。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不作为执行措施及适用原则存在不同的观点。李浩教授较早地提出不作为执行措施的复合性;(62)李浩:《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曹志勋教授则主张借鉴德国的执行措施特定原则,适用间接强制解决复合性停止侵害判决执行难题。(63)曹志勋:《停止侵害判决及其强制执行——以规制重复侵权的解释论为核心》,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六稿)》第244条设计了包括迟延履行金、罚款、拘留等并行适用的间接执行措施,以及针对除去性作为的替代执行措施,采行执行措施并行原则。本文主张,根据我国不作为强制执行的司法实践经验,需建立包括间接执行与替代执行在内的复合性不作为执行措施;在此基础上,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作法,确立间接执行与替代执行顺位适用的程序规则。详言之,首先采取间接执行措施,通过对债务人的心理压迫,促使其主动实施停止性不作为、除去性作为或预防性作为;若未实现执行效果,经债权人申请,可适用替代执行措施。
(二)第一顺位:间接执行措施的概括性适用
间接执行是通过对债务人的心理压迫,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其有利于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且有利于保障执行依据所确定给付内容的迅速实现。执行实践中扩大间接执行的适用范围,无论对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还是对于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权益,均具有合理性,且符合现代法治基本理念的要求。上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立法均明确了间接执行可概括适用于停止性不作为与除去性作为、预防性作为。例如,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实务经验,管收措施是制止债务人停止侵害行为的最有效执行方法。(64)赖来焜:《强制执行法各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20页。然而间接执行措施广泛适用的前提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间接执行的具体内容和程序规则,从而保护债务人的基本人权以及防止过于严苛的执行。(65)廖中洪:《民事间接强制执行适用原则研究》,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3期。
近年来,我国为“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不断加强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征信系统记录等惩戒措施的实施力度,加大对拒执犯罪的打击力度。(66)周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研究处理对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对失信被执行人依法适用强制措施,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人,拘留50.6万人次,限制出境3.4万人次,与前三年相比分别上升416.3%、135.4%和54.6%。”但是由于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上述间接执行具体方法的程序规则,债务人很难预知不履行义务所面临的处罚种类,一定程度影响间接执行措施的威慑力。同时,执行机关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存在司法适用上的任意性,从而影响间接执行的实际效果。(67)马登科:《民事间接强制执行比较研究》,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4期。因此,在起草强制执行法过程中,需要遵循执行实效理念、基本人权保障理念以及程序控制理念,通过严密的间接执行程序设计,对间接执行的准备程序、具体执行方法及适用顺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立法规定,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债权人的权利、保障债务人的基本利益。(68)同前注〔64〕。
首先,完善执行通知制度,规定间接执行预告程序。我国现行执行通知制度旨在保障债务人的知情权,其承载了通知、督促履行等多重功能,风险提示作用发挥有限。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内容仅仅告知债务人可能被纳入失信人名单,并未充分发挥其他间接执行措施的威慑功能。立法中,可借鉴德、日等国家相关立法,在间接执行通知书中,详细载明间接执行方式的具体内容,以及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0条规定了违警措施前置程序,即在对债务人实施违警措施前,如果判决中未对被告予以警诫,执行机关须预先进行威慑和警告债务人,迫使其出于恐惧而积极履行不作为义务。又如,《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72条亦规定了间接强制金支付预告程序,通知债务人因不履行不作为义务将被征收强制金的数额(包括日罚金数额或一次性给付数额两种计算方式)。
其次,梳理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在征信系统记录、悬赏执行等方法,将具有长效性的经验做法纳入间接执行措施范畴;同时,将上述执行方法与拘留、罚款等传统的间接执行方法相衔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间接执行措施体系。
最后,规定间接执行具体方法的适用顺序。我国间接执行的具体方法种类繁多,为规范执行行为,有必要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明确具体执行方法的法定适用顺序。德国法规定执行机关在选择具体的间接执行方法时,应首先适用违警罚款,债务人仍不遵行时,再处以违警拘留。我国台湾地区理论界经过多年探索,(69)针对不作为义务的三种间接执行措施的选用或者并用,有观点认为可任意选择一种或几种并用,从而强化执行效果;亦有观点认为管收与怠金,仅能选择一种或者先后适用不得并用,但是“除去行为结果”的执行措施可与管收或怠金的一种并用。赖来焜教授赞同第一种观点。参见林昇格:《强制执行理论与实务》,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694页;陈荣宗:《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612页。赖来焜:《强制执行法各论》,元照出版社2007年版,第720页。于2011年修订“强制执行法”时,确定了金钱处罚优先原则,管收作为强制执行的最后方法。详言之,对违反不作为义务的债务人先处怠金,债务人不履行时,无需债权人申请可再处怠金或直接适用管收。(70)黄荣坚、詹森林、许宗力等:《月旦简明六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肆-171。我国在不作为间接执行程序立法设计中,可借鉴上述“由轻到重”的规范性设计,即首先适用金钱类处罚措施,债务人仍不履行义务时,再对其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措施。
(三)第二顺位:替代执行措施的辅助适用
上文所及,对于正在实施或可能持续实施侵害行为的,不作为裁判主文需明确除去行为结果或预防侵害发生的具体方式。若执行机关采取间接执行措施后,债务人仍未主动实施除去性作为或预防性作为,债权人可申请适用替代执行措施。
除去性作为和预防性作为的替代执行程序,与一般可替代行为的替代执行并无二致。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替代执行程序具有较强的公权力性质,执行机关不仅具有指定代履行人的权力,而且承担监督替代履行行为的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2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03条的规定,代履行人由人民法院选定,债权人对于代履行人仅有推荐的权利(可以推荐法院代为履行)。代履行费用的数额由执行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并由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预先支付。在执行实践中,为提高执行效率,执行机关较多地通过执行人员赴现场拆除侵权建筑物、腾退房屋等方式代为履行。(71)贵州榕江:依法对两起排除妨害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 http://jszx.court.gov.cn/main/ExecuteNewsletter/194919.jhtml,2019年8月1日最后访问。此种执行机关作为代履行人“主动执行”的方式,势必增加执行机关的负担。
与我国上述执行方式相类同的是日本的替代履行程序。日本法规定债权人或第三人实施代替行为时,“系执行法院之辅助机关,亦属公权力之行使”(72)同前注〔33〕。,当受到阻碍时,可以向执行官寻求帮助(《日本民事执行法》171条第6项、第6条第2项)。但是与我国执行机关指定代履行人方式不同,日本授权债权人确定代履行人,其可选择执行官或第三人替代履行。经授权的债权人具有执行法院辅助机关的地位,具有授权范围内除去违反行为结果或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权利。日本关于替代履行的立法内容可能对我国强制执行立法提供有益参考,执行机关可积极探索委托债权人或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方式,从而进一步提高执行质效。
四、重复侵害行为之再执行
金钱执行案件执行完毕后,债权人的权利即获实现,不会产生重复侵权与执行的问题。然而,不作为裁判所确定的不作为义务具有面向未来的特征,其履行从根本上取决于债务人的主观意志,因而极易出现反复、持续侵害行为。例如,上文所述王春泽与王金章排除妨害纠纷案中,执行终结后被执行人重复实施相同的侵害行为。泰州中院认为“执行法院在执行期间,被执行人王金章仍在原通行路上重新设置障碍,阻止申请执行人通行,虽属于新发生的侵权事实,但与已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侵权事实并无区别”,“应在执行期间一并加以排除”。
《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21条将重复侵害行为界定为“在执行终结六个月内”“对已有执行标的”的妨害行为,债权人可申请“排除妨害”。最高人民法院主张“如果发生在执行终结后很短的时间内,一般人会认为这是公然对抗原执行程序、破坏原执行目的的行为”,理应被再次直接予以排除。但是如果行为发生在执行终结很长时间之后,由于时间的流逝,该行为与原执行程序的联系不再密切。“在一般人观念中,妨害行为就成为新的侵权行为,也就失去了再次直接排除的合理性与必要性”。(73)同前注〔9〕。毋庸置疑,将重复侵害行为距执行终结的间隔时间作为衡量再次执行的标准,有利于执行机关的审查。浙江省高院《关于妥善处理知识产权重复侵权行为若干问题的纪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重复侵害行为的认定标准,要求只有同一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在执行完毕后六个月内再次发生,才可以依据现有的判决进行第二次执行,超过六个月的期限,则必须提起新的诉讼。
理论界对此提出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应该允许权利人不受时间限制地申请执行不作为判决,因为“新的侵权事实并不必然导致新的诉讼的产生”,而完全有可能是执行力的向后扩张;如果被执行人认为其在判决生效后所从事的行为不构成判决所禁止的行为,则应由被执行人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机关有权判断新旧侵权行为是否属于同一行为。(74)曹云吉:《论裁判生效后之新事实》,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 年第 3 期。另有学者主张应“对于相同或实质相同的重复侵权都应当直接通过执行程序加以救济,既没有划定诸如 6个月界限的必要,又不必通过另诉浪费司法资源。”(75)曹志勋:《停止侵害判决及其强制执行——以规制重复侵权的解释论为核心》,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亦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贯彻“裁判一次性解决原则”,建议将《民诉法解释》第521条“执行终结六个月”修改为“终结本次执行”。(76)廖中洪:《不作为请求权“潜脱”执行问题研究——兼论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一条的完善》,载《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本文认为,关于规制重复侵害行为的讨论,仍需回归其实体基础——不作为请求权。德国法上的不作为请求权实质上是面向未来的具有预防性的请求权。例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不作为请求权指向未来,即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包括已经实际发生,并且有“重复发生的危险”的违法行为,以及尚未发生,但有“首次发生的危险”的违法行为。“重复发生的危险”或者“首次发生的危险”的判定,以法院最后一次事实审理或者口头辩论期日的法律关系状况为准。(77)吴泽勇:《德国群体诉讼研究——以德国法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又如,《德国著作权法》第97条第1款规定:“受害人可诉请对于有再次复发危险的侵害行为,即刻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害行为系处于故意或过失,则还可以同时诉请损害赔偿”。
对于面向未来的请求权,德国自然未在程序法上对其做时间上的限制,债权人可连续申请强制执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0条规定一审受诉法院应依债权人的申请,对债务人的“每一次违法行为”处以违警罚款或违警拘留。同时,对于每一次违警罚款的数额限定在25000欧元以内,违警拘留不得超过两年。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修订“强制执行法”时,规定债务人连续违反其不作为义务时,可以不经债权人申请,执行机关可连续对债务人进行怠金处罚或管收,从而强化执行效果。(78)修改此条内容的背景:“目前社会,工商业日益兴盛,臭气、噪音、废水及其他制造公害之事件,随之与日俱增。而此类事件之性质,每多一次违反,对于实力雄厚的企业连续处以怠金,实际上也难收到遏制的效果”。参见《“民事诉讼法”分类小六法》,元照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但是在实施管收时,须遵守第24条第2项的规定,即再次管收不得超过三个月,且两次为限。怠金可连续适用,且无次数限制。(79)赖来焜:《强制执行法各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721页;张登科:《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2012年版,第572页。针对债务人复行违反再次产生的行为结果,经债权人申请,执行机关可再为执行。
本文认为,《民诉法司法解释》第521条旨在通过时间限制,简化执行机关对于重复侵害行为的审查。然而,若“执行终结六个月”后的重复侵害行为被排除于再次申请执行范畴之外,不作为请求权以及不作为裁判的预防性机能将无从发挥。为防止不作为裁判形骸化与空洞化,本文赞同学界的观点,对于重复侵害行为,债权人可再次依据不作为裁判提出执行申请,从而扩大裁判主文的辐射范围。
对于重复侵害行为是否与不作为裁判执行内容相同,实属实体性裁判内容。如上文所述,可通过审执分离的宽缓化方案,赋予执行机关特定不作为执行内容的实体裁判权。此外,基于对债务人实体权益的程序保障,债务人可针对重复侵害行为的再执行,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申言之,债务人于再执行程序终结前,可主张执行依据与债权人在实体法上权利现状不符,请求排除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时,除执行机关认为必要情形或依申请为担保,一般不停止强制执行。如债务人异议之诉败诉,仍可另行起诉请求损害赔偿或返还不当得利。
结语
不作为请求权的预防救济功能,符合日益尊重当事人主体性、面向当事人需求、强调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现代诉讼观念,构建不作为强制执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起草过程中,需要对不作为请求权进行深入研究,构建具有实体基准性的不作为强制执行程序。详言之,在确立不作为本旨执行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复合性执行措施体系,包括第一顺位的、概括适用于不作为执行标的的间接执行,以及第二顺位的、适用于除去性作为与预防性作为的替代执行。在审执分离改革中,针对不作为与作为强制执行的特殊性,通过引入执行听证制度或执行机关的例外设置作出宽缓化处理。与此同时,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需充分考量预防型民事责任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实现方式,从而实现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有效衔接。
- 甘肃政法大学学报的其它文章
- 民事执行调查社会化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