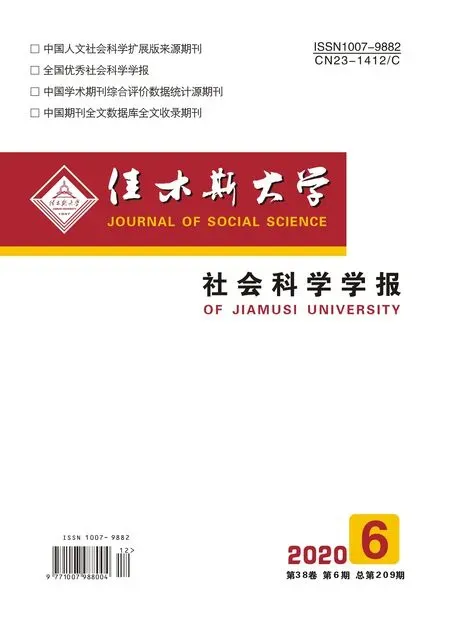嘉庆二十三年“暴风示儆”始末初探*
孙圣惠
(东北师范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00)
一、嘉庆年间之时代背景
清王朝在经历康、雍、乾三朝的繁荣以后,至嘉庆朝便已经逐步呈现出由盛转衰的颓势。伴随着嘉庆帝嗣位,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已有五位皇帝先后登基。此时距离清王朝建立全国范围的统治已达一百五十余年,在经历如此漫长的积累与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矛盾已在此时大大地激化起来。
嘉庆时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越发尖锐,起义频发,战乱不止。可以说,嘉庆朝是清王朝开始中衰进程的重要节点。此时,接踵而至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广东天地会起义、天理教起义、豫鲁冀农民起义等集中反映社会矛盾的产物,常常使统治者难于应对。然而,统治者在各种问题之间疲于奔命的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从容面对日趋严重的殖民主义侵略威胁。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嘉庆帝自登基以来,始终都面临着如此严峻形势的困扰。
时至嘉庆末期,嘉庆帝仍需面临嗣位初便存在的问题“兵事”“河槽”和“吏治”三大困扰。就“兵事”而言,“苗事”湘黔苗民起义、“教事”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海事”以蔡牵、朱濆为首的海上武装斗争最为之过。虽然,“苗事”“教事”“海事”先后被嘉庆镇压和平息下去,然而一阵又一阵的冲击却令清王朝元气大伤,至嘉庆末年,统治者仍需不断为“兵事”所增加的军费开支焦头烂额,并且仍然需要忙于镇压平息白莲教起义余波和因社会矛盾揭竿而起的农民。与此同时,皇帝依旧未能摆脱治河与理漕所滋生的问题。虽然嘉庆帝于治河理漕拨银甚多,但却无实效,以致出现了“欲求两治,转致两妨”、“徒费帑币”的局面。随着问题的增多,为治河理漕进行拨银也终于在嘉庆末年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嘉庆年间的“吏治”为三大困之核心,只要吏治搞好了,兵事不难藏功,河槽亦不难理顺。嘉庆初年,“诛和珅以肃吏治”便成为整饬吏治的第一炮,可并没有达到“杀一儆百”整饬吏治的作用。犯案者接二连三、层出不尽,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吏部书吏欺蒙上司,私用印信舞弊,将告病治中赵曰濂虚选运用事觉”[3]757;十一年八月,“新任直隶布政使庆格,究出司书假雕印信,勾串舞弊。”[4]153直至嘉庆末期,皇帝仍然需要对吏治大加整饬,处理诸如广兴贪赃案之类案件,以图扭转各省、府、州、县的亏空。面对颓势,统治者无时无刻不在为解决问题以延续国祚寻找良策。置身于内外力共同塑造的严苛环境之下,任何一件看似寻常的小事都有可能拉断统治者绷紧的神经。
嘉庆二十三年,一场其象异常的“暴风示儆”,将统治者的神经彻底拨动。一场关乎灾异谴告说的讨论开始在权力中央蔓延。君臣纷纷借助这场“天灾”,用以谋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
二、“暴风示儆”之始末
嘉庆二十三年,京城近畿一带出现了骇人的天灾——暴风。嘉庆二十三年夏四月丙子日,谕内阁“昨日酉初三刻有暴雨自东南来。俄顷之间,尘霾四塞。室中燃烛始能辨色,其象甚异。”[5]501该暴风由于其骇人景象,将皇帝的敏感神经挑拨起来。在君主受命于天的思想观念下,天人感应作为儒家政治学说也始终钳制着嘉庆的言行。信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1]29的嘉庆试图采取各种措施修正统治政策,以求消弭天变。
嘉庆二十三年夏四月诏:
“有言责者,体朕遇灾而惧之心,剀切论列,无有所隐。即下民有冤抑者,亦可据事代为直陈,以副朕修德弭灾之意。”[5]501
此外,命人于近幾一带偏行查访,另命“钦天监衙门职司占验,于星象风信休征咎佂,皆应据实入告。”[5]501-502夏四月乙卯日,钦天监奏:“详查《钦定天文正义》,内载‘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雨,不沾衣而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又为米贵等语。’本月初八日酉刻,暴风骤至,尘土晦蒙,与正义所载风霾之象相同”[5]503。而正是因为钦天监极具象征的占语,将嘉庆心中的“天人感应”观念与《钦定天文正义》中所蕴含的理论相结合,而更加坐实了统治者所信奉的“天灾示警”观念。为此,一场有关灾异谴告说的讨论,在自皇帝本人下至道府属吏之间逐步蔓延。
“暴风示儆”是灾异谴告的外显,在古人的观念里属于天人感应理论,天人感应理论是一套儒家政治学说。在君主受命于天的理论护佑下,历代君主以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自居,容易导致皇权膨胀阻碍政权正常运转,为此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理论,借天意对君主的行为加以限制。君主受命于天,他的言行皆能感应上天,若顺天而行,为政为德,就会受到天降祥瑞的庇护;反之,若逆天而行,施暴施虐,上天就会降灾示警。因此每当遇到灾异发生,作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和辅佐天子的大臣,就会采取各种措施修正统治政策,以求消弭天变。“暴风示儆”后,君主认为近日频发的案件便是天降灾异的原因“且如近日人心险恶,匿名讦告之案接踵而至。良民受其拖累,以致荡产之身,皆足以召灾沴!”[5]501为此,朝廷上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求消弭天灾。
(一) 省察自身
天降灾异是对天子统治中某一方面的否定,因此,当灾异出现,作为天子的皇帝就要检查自我德行,反省自己违背天意的地方,并要改过自新挽回天变。“暴风示儆”后,嘉庆最激烈的反应便是下诏罪己,嘉庆二十三年夏四月,谕内阁“朕心中震惧,夙夜不遑,惕思上苍示警之因,稽诸洪范咎征恒风为蒙之象。皆朕办事不明,用人不当之故。或意存怠忽,不能力勤;或有下情不能上达者,其政事阙失,无所匡正欤;抑小民怨苦,壅遏莫闻欤;或内外大臣有奸佞倾邪,而朕不及觉欤。”[5]501面对天降灾异,一向信奉“天人感应”的君主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施政得失以试图消弭上天的怒火。
(二)广开言路
面对天灾示警,皇帝在下诏罪己省察自身以加强自身德业修养的同时,还支持大小臣工上疏谏议,寻找施政阙失。二十三年夏四月丙子日,谕内阁“如朝廷所行之事,有似前代秕政,应行改革者,即剖切论列,无有所隐。下民横被冤抑,有覆盆莫白者,亦据事直陈,代为昭雪。”[5]501
(三)整饬吏治
嘉庆不仅要求大小臣工寻找执政得失,更要求群臣针对吏治问题,弹劾贪赃枉法之人,以求整顿吏治。“其奸邪之病国虐民者,或模棱巧宦,旅进旅退者,即列款纠参,指其实迹,登之弹章,如此则言者出于为国之公心。”[5]501为肃清吏治,消弭天变,嘉庆还下诏对贪官污吏白役人等之事严加惩处,二十三年夏四月戊寅日,谕内阁“若番役兵丁及一切白役人等,再籍捕逆为名,即以叛逆之罪坐之。或将被害之家产抢劫者,审明计赃治罪,仍将该番役兵丁等家产抄没,赏给被害之人。其官弁中有贪功冒赏,诬陷无辜者,该管上司查出,均严参一体治罪。”[5]502
(四) 清理冤狱
此外,中国从古以来便有冤狱弊政导致天变的说法“盖从来况郁之气,最能感召灾沴,故三年不雨,六月飞霜,史册记之。”[2]856鉴于此,历代王朝每逢灾异发生,清理刑狱便成为帝王消弭天变的手段之一。“暴风”起于东南,故皇帝认为“风从东南而来,或东南一带逋逃恶相聚潜藏,地方官不能察觉,以致上干天和”[5]501。另近京之马兰峪、古北口、天津等处,皆回奏暴风之事,夏四月辛巳日,庆惠奏“马兰峪地方,是日酉初后,风自南来”[5]506;徐锟奏“是日酉正初刻,风土自西南而来”[5]507;嵩年奏“亥初北风大作,雨势霶霈,自宵达旦,并无雷声”[5]507;陈预、和舜武奏“山东于初九日,自卯至寅得语竟日,极为渗透”[5]507。据此,朝中合观各处奏报情形,“初八日风霾并非起于东南,乃自东方而至,盛京在京师之东,或该处有弊政冤狱,无以上闻,致有此异”[5]507。于是,嘉庆下令清理刑狱,整顿弊政,“著派奕绍、戴均元,驰驿前往导处。”[5]507夏四月庚寅日,又闻陈预奏“山东海丰滨海地方,于四月初八日申刻,东北风大作,昼夜无息”[5]512,遂命和舜武到任后整饬吏治,清理积案,抚衅灾民,“著和舜武到任后,督饬该藩司迅速确堪,据实奏明,妥为抚衅,勿使灾民失所,用副朕惠爱黎民至意。”[5]512
三、“暴风示儆”之实效
在传统观念中,灾异谴告说作为钳制统治者言行的理论工具,不仅始终在帝王的心中存在,也在大臣之中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在面对灾异时,不仅君王要自我反思施政得失、自身德业修养,作为臣子还需要辅佐帝王反省自身、消弭天灾、顺应天意。
“暴风示儆”后,许多臣工为迎合君主心思纷纷上书奏事,但大部分内容广泛,多为劝谏帝王广开言路,加强德业修养之事并无实质内容。夏四月壬午日,御史汪彦博、吴杰各奏应诏陈言弭变一折就引起嘉庆帝极大的不满。嘉庆本欲就“暴风示儆”一事而广开言路,寻求解决现实之时效策略,但大小臣工大都“惟空言无以责实效”[5]507,使得帝王再三下旨,痛切言之,“必内外臣工,视国事如己事,以民心为己心。如所谓停诿卸,容隐瞻徇各积习,痛加湔除。使吏治日清、民事日厚,则转咎为祥。”[5]507-508有鉴于此,群臣再次上书言事,用以迎合嘉庆。
但是,灾异谴告说与谏诤的实际效果实际上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帝王因灾异而下诏自省、求言,有讲求实效的一方面,也有流于形式的一方面。
夏四月壬午日御史吴杰條奏事宜一折,其请禁差务之累一款便得到了嘉庆帝的采纳,下令“著先期严行饬禁,不得稍事浮靡,致滋扰累。其该省总督藩臬,途中车马供亿,亦应自行备办,不得取给属员,致令藉词苛派。至捐廉一事,久经停止,澄汰捐班,屡经饬谕,均系现行之事。其问刑衙门,不准擅用非刑,如脑箍等项名目。著再行申禁,以慎庶狱而重民命。”[5]508但有些上疏皇帝则是根本不看的,即便皇帝能看,建言能否被采纳,谏言可行与否,更取决于谏言是否和皇帝的个人意愿相符合。
帝王下旨求言,有三人为松筠降谪之事为言,请仍召还内用一事,便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反而大加斥责。松筠因屡次上疏劝阻盛京谒陵大典而被革去大学士之职,降为二品顶带。而“暴风示儆”后,京堂御史之中,竟有三人同时为松筠之事上疏,其目的不过在于节省谒陵大典之开支花费,重用老臣。但却遭到嘉庆帝大加斥责,“松筠谪降,系上年六月之事,彼时何以不见有眚灾告警。且言者果以松筠为屈抑,又何以去年不交章谏诤,坐待今日乃为此无稽之论。况风霾之象专为松筠,必无是理。复召与否,其权在上,岂小臣所得干与邪?”[5]508-509。其被大加训斥之原因不过在于松筠阻碍谒陵大典,违背了嘉庆个人心意。故此上疏未能被采纳。夏四月乙酉日,御史张鉴奏风霾变异,敬陈管见一折也未能被嘉庆所采纳。折中一称方今吏道浊滥,流品混淆,内外官吏,妄于登进。帝曰“其言殊觉无当”[5]509;一称停止添建园座庙宇工程。帝曰“从未添建,不过偶尔修缮”[5]509-510;一称罢贡斥谀。帝曰“来年并不举行庆典,所有金珠玉器陈设等件,早经降旨不准呈进。至国家旬庆及巡幸典礼,臣工进献册页,相沿已久,因近日文体浮夸,曾降旨示以颂不忘规。”[5]510该奏折未被采纳更多的则是违背了嘉庆本人意愿,故此该折批语更为严厉,“该御史谓皆系谄媚之词,太不成话矣!”[5]510
虽然天灾示警的谏诤效果因统治者个人喜好而各有异同,但在借“灾事”解决君主所关注的要事面前,常常屡有奇效。面对自嘉庆登基之初便面临的“吏治”问题,群臣纷纷借“暴风示儆”一事上疏直陈,以寻求良策。
夏四月戊寅日,给事中卢浙奏风沙示警,请禁缉捕员弁贪功冒赏、扰累平民一折。借机劝谏帝王肃清吏治,整顿风气,抚衅平民。嘉庆帝接受其谏议,并降旨对官弁中贪功冒赏、诬陷无辜者,严加处置。夏四月乙卯日,钦天监回奏详查风霾一事,有“君臣乘,大旱又为米贵”等语。是为钦天监大小臣工对帝王的谏议。嘉庆帝也仔细考虑了此项谏议,认为朝中大臣与君主不能同心望治,以致君臣离乘。
“朕详思其义,如前代君臣暌隔,有天子不识宰相之面者,诚不免为君臣离乘之象。我朝家法相承,君臣一体,朕恪遵成宪,每召见廷臣不下十余起,躬亲延访,前席周咨,似与离乘者有别。然诸臣中实与朕同心望治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召对时,虽虚怀访问,总以政治毫无阙失,颂美圣明,谀词容悦。试问其心,岂真以为万几咸理,无可遗漏补阙者乎?不敢面折,退有后言,总回护己之爵位,罔恤政之得失,所谓貌合而情睽,是即乘之义也。即诸臣同僚之中,亦每心知其非,不肯直言匡正,坐视其失而不救,甘为小人之同,而不为君子之和,是亦所谓乘也。”[5]503-504因而,嘉庆帝下令广开言路,命诸臣全心为民,匡正朝廷。
四、结语
“暴风”作为一个极为寻常的天气现象在清王朝呈现颓势的特殊时期里,刺痛了统治者的敏感神经。嘉庆在面对“暴风示儆”这一灾异谴告说的外显现象时,表现得并非如常人想象的如意。虽然“暴风示儆”后,君主省察自身、群臣上疏言事,但并非一一可行。一方面,谏诤的实际效果更取决于谏言是否和皇帝的个人意愿相符合;另一方面,群臣上书多为迎合奉承,在弄清君王心思之前,更多的是更为宽泛的概述之语,甚至有时候上疏“惟空言无以责实效”。此外,灾异遣告说并没有扭转清王朝中衰之局势,乃至其它王朝的衰退。但其作为儒家“天人感应”理论的重要方面,在充满局限性的时代里成为限制皇权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灾异遣告说形成了一个群臣就现实问题上疏谏诤皇帝的机会,虽不能完全奏以实效,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统治者关注,从而起到相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