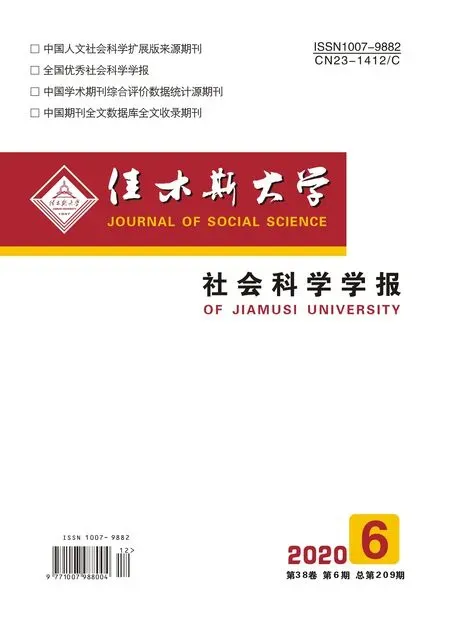苦难中的人性之光*
——基于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浅析《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创作特色
王 晨
(天津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204)
一、引言
杜勃罗留波夫(Н.А. Добролюбов)是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在文艺思想和美学领域的建树举世闻名,其理论思想在俄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杜勃罗留波夫出身于平民家庭,并没有接受传统的俄国贵族式教育,这就使得其在文艺理论追求上更加贴近真实。作为积极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其短暂的二十六年生命中对俄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曾经评论杜勃罗留波夫为社会主义的莱辛[1]84。列宁也对杜勃罗留波夫做出过极高赞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先驱者[1]84。杜勃罗留波夫传承了由别林斯基创立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进行了充实和完善,他认为文学创作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像是在不流血的战场上使用的有力武器。
而进行文学批评时,应当从文学作品出发还是从评论者的主观思想出发,这关系到不同哲学观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在哲学思想上杜勃罗留波夫信奉的是唯物主义,他认为在理解客观世界和研究文学创作方面不应当拜倒在柏拉图和谢林的唯心主义观念下,应当讲求最为真实的客观存在。应将文学作品为依据对生活现象进行描述,而并不是把预设好的观念、好恶强加给作者。要让受众理解,优秀的作品是从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非按照预先的设定。[2]86正因如此,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是以唯物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同时又借鉴了西欧的人道主义思想[3]70。然而不同之处在于,费尔巴哈是从生物特征的角度对人进行哲学思考,杜勃罗留波夫则是从社会环境对人进行文学批评。但需要明确的是,杜勃罗留波夫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哲学基础绝对不是仅仅照搬前人的哲学思想,而是在其基础上结合俄国社会所处的现实情况,需要面对的现实斗争,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文学创作的实际需求等因素发展而来,并以此对文学进行文艺批评。
如今虽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文学即人学的观念始终得到传承,文学要以其特有的形式诠释生活的真谛,传播正确的观念,对人性给予关注,真实地对生活进行反映,启迪对生活的思考,这一切一直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4]12因此,以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思想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进行考量是合理的。但是需要承认的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的文学创作与杜勃罗留波夫的时代相比毫无疑问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由于对杜勃罗留波夫文艺理论不甚了解,或者认为其理论已经陈旧就轻易否定其理论价值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蕴含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是值得被慢慢发现的,就如同四季一般更迭,有的在隆冬时节被雪藏,却在初春被发掘;有的在盛夏被淡忘,却在金秋又被想起。对于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我们可以视其为一条隐秘的通路,顺着它我们将更容易到达文学真谛的终点。
谈及如今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当代的俄语作家中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С. А. Алексиевич)应当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作为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近几年名声大噪,其主要作品相继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中文译本也陆续出版发行。作家凭借其写实的文字,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进入到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成为了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热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多为纪实性文学,这与她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学习以及毕业后以独立记者的身份进行新闻采访的经历有关。阿列克谢耶维奇所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真实的,作家的创作多以采访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者其亲人作为写作素材和创作基础,这样就使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能够最完整地还原现实生活[5]75。
二、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
对于文学的本质,杜勃罗留波夫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肯定了文学和科学都是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再现,它们的任务就在于宣传关于生活的真理,促进社会的自觉发展。杜勃罗留波夫极端反对所谓的纯文学论者把生活和文学创作完全割裂开,认为文学和生活是彼此分离的主张。纯文学论者断言只有纯粹的文学观念才能具有真正的价值。这显然具有了较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杜勃罗留波夫归纳总结前人的理论成果,他认为应当摒弃来自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主观唯心思想,需要明确一个道理,即“生活本身并非是按照既定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而改变,文学所要再现的恰恰是不断变化的生活,是以生活作为创作的蓝本和依据随着其改变而不断发展、完善、创新。”[2]53依据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无论是文学还是科学,所反映的对象都是统一的客观世界,生活的丰富与多样并非是抽象的、先验的概念。
但是文学创作并非是机械式地简单描述现实生活,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文学创作以现实为基础,具有创造性和概括性。文学创作的感性思维具有较强的创造性,需要从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中经过分析、比较、筛选、加工,概括地反映生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杜勃罗留波夫继承了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思想,并从文学作品内容、文学研究对象、文学理论等视角揭示了与科学在其本质上的不同特征。杜勃罗留波夫指出科学是透过事物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现象,舍弃具有偶然性的个别现象,以此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并对反映的内容采取抽象的理论性表达。而文学则不同,它是在一切最特殊、最偶然的事件中,把高尚的思维自由转化为生动的形象,文学具有崇高意义,而这种崇高意义又具有一定普遍性。[6]83杜勃罗留波夫坚信,作家只有反映真实的生活才可以创造出形象鲜明、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根据苏联时期乌克兰境内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作为背景所创作的纪实文学《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就非常好地诠释了文学作品要具有真实性这一重要原则。文学的重要品质之一莫过于真实,就像“美”和“善”同样是文学的重要品质。粗鄙的文学是丑陋的,不善的文学是恶劣的。但是追求真实却并非易事,因为不仅要有创作的动力和热情,更重要的是要勇于面对真实所带来的痛苦、悲哀和伤痛,要有勇气承受一切消极负面的情绪。[4]13摆正文学作品和生活的关系是文章真实性的重要体现,杜勃罗留波夫将文学创作视为生活的“晴雨表”,透过文学作品可以感知社会生活的变换。[6]84正是透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我们了解到了十九世纪俄国贵族青年的生活状态;正是透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我们理解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正是透过契诃夫的《樱桃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变迁;而正是通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我们才能感同身受,了解到那场人间浩劫所带来的无法疗愈的伤痛和苦难。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采用纪实文学的创作手法,即作家通过采访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将其口述的内容进行整理和文学加工最终完成创作。“最伟大的作家也不会构思出绝对的虚伪”[5]77,作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见证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所采访的亲历者一样,有着最真实的记忆。作家尽可能地拜访更多的事件亲历者让他们开口讲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不同的态度进行收集整理。真相与谎言只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讲出事实真相是获得真理的唯一方法,而文学应当在真理和谎言中做出取舍,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通向真理,另一条路是回避真理。莫非要我们重蹈覆辙,在事实面前再一次遮遮掩掩?”[8]184阿列克谢耶维奇要还原事实的全貌,探求真理,她希望那些心中充满苦难记忆的人能够直面那段痛苦的回忆,说出自己的故事。从耄耋老人到懵懂的孩童,从核事故当地的原住民到前往事故现场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从核电站的工人、士兵再到相关领域的学者、核物理专家、大学教授,从因受到核辐射污染而罹患重病的病人到不幸辞世者的家人,从最无辜的普通平民到一直缄默的前政府官员……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而作为采访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添加任何主观评价,不进行任何文学创作美化和修饰,她只是在采访对象的言谈中加入细节的、更为真实的神态或表情描写,例如:“他哭了,她长久不语,眉头深锁,轻轻地叹了一声”等等,将亲历者的喜怒哀乐用文字表达出来。哭泣是许多讲述者真情流露的表现,眼泪不仅仅是对痛苦情绪的宣泄,也是对不幸罹难者的哀悼。通过亲历者真实的陈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这些苦难的故事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受害者内心能得到一些宽解和抚慰,让不曾经历此等浩劫的人了解真相。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创作的方式不同,在描述作品创作背景时阿列克谢耶维奇借用了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相关文献、报道,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从这些资料里选取片段来进行陈述。虽然这样的创作方式很显然是有意为之,但是这极大地加强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基调,纵览整部作品,只有全书中的后记部分是真正意义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原创”。作家把核泄漏事件,核泄漏事件中的亲历者,核泄漏事件中亲历者的经历都不加任何修饰的呈现给读者,把最真切的事实反映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么做是有其用意的,她不想去扰乱受众的视听,只想让读者通过阅读她的文字自行去做出判断,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言“作者在创作时,要紧的是诚实,不能因为顾全自己的想法而歪曲生活的事实。”[6]85
在对作品进行整合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结构,她用两位女性亲历者的讲述分别作为开篇和结语,开篇是一位在发生核泄漏事故后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救援的消防员妻子的讲述,由于不清楚具体爆炸的情况,她的丈夫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就冲进了爆炸后充满辐射的火灾现场。大火得到扑灭,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惨绝人寰的悲剧:丈夫由于过量接触核辐射而身患恶疾,两周后就匆匆离世了。妻子看着心爱的丈夫在痛苦中被病魔夺走生命,却因为核辐射的原因不能靠近陪护。随后出生的女儿,由于在怀孕中代替母亲吸收了过量核辐射而在出生后数小时就不幸夭折。一连串人间悲剧降临在这个本来幸福美满的小家庭中,“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了,走着走着,人就倒下了,再没有站起来。”[9]82而作品的最终章,作家安排了一位应召前往切尔诺贝利进行抢修的建筑工人妻子的讲述,这位工人也是由于过量接触核辐射而不幸离世。很显然,阿列克谢耶维奇希望借助女性视角传达出更为深刻的内心感受,正像作家的另一部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描写的苏联女战士一样,女性作为传统观念中的弱势群体,在面对灾难、战争时所表现出的坚韧往往更加令人动容。
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男人们是要前往切尔诺贝利的,出于责任和信念他们无法回头。而当他们回来之时,所有的人间悲剧都要由他们的妻子独自承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面对亲人的离世,每个人都只能默默地选择坚强。正如作品中描写的一位从切尔诺贝利执行任务回来的飞行员,他无法用语言描述事故现场的惨状,无法用言辞表达心中的恐惧与痛苦,他只能告诉孩子,现在看到的一切就是真实的战争,每个亲身经历者都见证了真实而恐怖的死亡,“他们睡着了,就再也没有起来,去给护士送鲜花,回来就再没了呼吸……”[9]106面对灾难,无论多么强大的内心也绝不会丝毫没有恐惧,无论多么强烈的意志也绝不会丝毫没有动摇,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一个个受访者的讲述向读者真实地还原了那场人间浩劫,令人掩卷而思心中久久悲伤不已,无法释怀。
三、人性至善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特质
提到文学形象的人性问题,杜勃罗留波夫基于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人性是人原始的自然特性,是与生俱来的内在力量。”[2]32在他的论述中经常提及的“自然天性”“本性”“本心”“本质特征”等都是相同的含义。与欧洲传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相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本性要与其行为相一致,尊重人的地位,维护人的尊严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但与启蒙运动中所倡导的人性,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关注有所不同,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性的观点同费尔巴哈更加接近。
费尔巴哈所秉持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人的本质属性更多是基于客观自然属性,是从生物学角度对人性进行解读。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生理机能是相似的,所以按此逻辑,人的本性也基本相同,人类与生俱来的某种动物性倾向,对生存和延续种群有着最原始的需求,费尔巴哈主张作为感性的存在,人具有一切生物都具备的原始欲望。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对人性的理解与费尔巴哈是相类似的,都是从人的客观自然属性来理解人性的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人类的生物属性是相类似的,从而人性的基本表现也是相类似的,但人类最终还是会有彼此迥异的差别。很显然,单纯从唯物主义的视角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而杜勃罗留波夫在接受了费尔巴哈观点的基础上,在其文艺理论体系内对人的差异性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人性的理解不能仅单纯的从客观角度出发,还要将其置于环境因素的维度之内。文学批评本身异于纯粹的哲学理论建构,作品中的人物无法完全超脱出生活,要忠实于其活动的时代。杜勃罗留波夫对文学人物的评论都秉持着建立在对其生活环境的分析上,善良的环境造就天性纯良的人,反之丑恶的环境只会让人性表现得寡廉鲜耻。环境改造人,而人又创造新的环境,如此往复,因此环境和人是和谐一体的。人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得千差万别,但是杜勃罗留波夫始终认为人的原始自然本性是美好善良的,他把善良认为是人性的正常发展,如果与美好背道而驰,被污染的、丑陋的都是恶的表现。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考虑,杜勃罗留波夫把恶行视作是违背人性发展的,这是其文艺理论体系中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10]102。纵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很明显能体会到作者对人性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亲历者对战争和灾难的讲述是人性最直观的体现,面对所有苦难,人类虽然显得渺小,生命也如此脆弱,但灾难中的逆行者们所表现出的善良、坚毅、勇敢是人性中最珍贵的一面。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科技悲剧,面对既成事实的人类灾难,我们可曾有过思考该如何面对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就和潜藏的威胁,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挑战甚至是灾难。核能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赋予人类无上科技力量的同时,是否有朝一日会被夺去并将人类带向末日的浩劫之中,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人间惨剧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再次上演。在作品中,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一个倾听者的视角,让一个个亲历者发声,通过他们的讲述告诉我们在痛苦中人性至善,在绝望中人类可以多么坚强和伟大。事故发生后,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扑灭火灾,在面对不清楚事故现场情况的条件下,切尔诺贝利的英雄们逆行而上,他们英勇顽强,无畏而勇敢地用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创作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形色各异的事故亲历者,其中作家最为关心的是一群极为特殊的居民,他们居住在当年专门为核电站而修建的小镇上,是核泄漏事故的直接受害者,但是荒谬的是他们是最后一批得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人。对于镇上居民的采访几乎占据了整部作品被访者人数的一半,通过居民们的讲述,彷徨、无助、恐惧的情绪跃然于纸上,每天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中让小镇上的居民精神几乎崩溃。他们有的选择逃离,但是未受到辐射感染的其他居民将切尔诺贝利人视为移动的核辐射反应堆,不仅对他们避之不及,还充满了歧视和厌恶,而这种恶意甚至漫延到孩子身上。[11]136切尔诺贝利的居民深切地明白,有不计其数的救援者为他们献出了生命,他们对此心怀敬意。真实的讲述令作家本人也十分动容,对参与救援的数十万逆行的英雄们心怀感激,英雄们身着极端简陋几乎没有任何防护能力的装备,视死如归地制止了核泄漏灾难的进一步扩大,在作品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下了救援士兵的一段讲述:“救援机器人已经无法运转,出了严重的故障,但作为人,我们可以继续工作,这点我是非常骄傲的。”[9]71对于责任的担当,对于职业操守的信仰让一群平凡之人在灾难面前显得异常伟大。畏惧死亡是人性的本能,无惧死亡坚守自己的责任,完成自己的工作则是人性至善的表现。灾难的亲历者讲述着身边一个个伟大的平凡人,他们或许是自己的一生挚爱,或许是自己的亲密战友,或许是自己的和睦邻居,在共同的灾难面前,他们没有退缩。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指出:“冲在最前线的消防员,参与救援的军人、医生、建筑工人,我们要铭记每一个在辐射灾难中罹难者的名字。面对辐射灾难,这里有不断倒下的核电站工人,有前来支援就再没能回去的医护人员,有在反应堆上方投放硼和沙子的飞行员,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守卫了亿万人民,是黑暗时代中苏联的英雄。”[12]89
杜勃罗留波夫所秉持的人性至善思想是建立在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基础之上,跳脱出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人的机械化界定,在变化的环境中追求人性的正向发展,摒弃恶的玷污,杜勃罗留波夫正是基于此种观点来界定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借由文学创作“吐露人民中美好的事物”。[7]13阿列克谢耶维奇则用最朴实的语言,最简洁的创作方法,最纯粹的感情完美地诠释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用最具感染力的人物宣扬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优良品质,这一点与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追求是相吻合的。
四、道德批判与人道主义是文学创作的精髓
杜勃罗留波夫作为十九世纪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一直坚持介入式文艺理论批评,在其观念中文学的魅力、意义和价值在于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深度、伦理意义和情感力量。杜勃罗留波夫不接受纯粹的唯美主义文学创作,他不认同与现实脱离,只追求结构和辞藻的创作,并指出“文学要与社会相关联,要表现人的道德水准,文学应该成为重要的力量让人们可以认识、了解、改变生活。”[2]106文学与其他科学不同,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含有道德批判的精神现象,道德问题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关照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善恶总是相互并存,人的行为中一定包含着道德与伦理,因此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不可以将道德和伦理问题从文学中剥离,否则会从本质上削弱文学的价值。对于创作者而言,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从来都不会回避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性,而且会积极地在创作中表现道德性问题,作家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培养人们心中的善念,提升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和意识,实践文学的社会性和伦理性。[2]132杜勃罗留波夫强调在文学创作中追求道德性,这对整个俄语文学创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只有文学具有批判意识和道德意识,才能视为伟大,杜勃罗留波夫将追求社会性中的善与人道主义思想作为评判文学作品或者作家创作的标准之一。[10]103当代研究俄语文学的学者也十分认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观,认为“俄语文学之魂是人道主义,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伟大的标准。”[13]10人道主义对生命给予关注,对人的命运给予同情,在创作中将人视为核心。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正是具有道德性和人道主义情怀。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非客观的事件。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能抛弃对人内心情感的关注,正如作家本人所言:“我是以一位作家的身份用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一位历史学家更注重客观事实本身。”[14]92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居民被迫背井离乡,对他们而言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苦难,更多的则是心灵上的煎熬。小说中作者利用部分笔墨描写了核泄漏之后的现实环境:农田、房舍、公路在灾民们撤离后被遗弃,曾经兴旺的生活一瞬间变得荡然无存。[15]85但是这种环境描写映射的则是人的内心感受,一片荒凉破败,了无生息,一切都像被埋葬一样。通过讲述者的话语,我们很自然地可以感受到切尔诺贝利居民们四处漂泊无依无靠的无力感以及面对将来未知生活的虚无感。小说中对英雄的赞誉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伟大的要属对切尔诺贝利进行清理的士兵们,他们需要在核反应堆周围清运石墨,灌注石棺,并对辐射数值进行检测。由于不具备有效的防护设施,这些士兵们只能在强辐射条件下作业,令这些英雄们克服内心恐惧的并不是丰厚的奖励,而是一份责任和义务,一份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一腔英雄主义的激情,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是生命。通过亲人们的讲述,我们很难不为这些士兵们的英雄壮举所动容,愿意用勋章换回丈夫的妻子,看着儿子照片痛哭的母亲,无法拥抱父亲的孩子……他们的泪水不禁让我们思考这种近乎于自杀式的牺牲让他们成为了英雄还是受害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文学创作只有对人给予关注,跳脱出一切责任和义务的束缚,才能彰显人道主义关怀。生命的意义不会以时间作为评判的尺度,而是要看它承载了什么,生死考验时所做出的的选择总会让看似平凡的人变得伟大,让看似普通的行为变得高尚。面对核灾难,有的人选择了英勇逆行,有的人选择了歧视冷漠,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做出评判,而是选择让读者,让社会做出判定。
五、结语
十九世纪是俄国文坛英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杜勃罗留波夫以其非凡的文学素养为俄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不仅使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还继承了唯物主义哲学观,开辟了文学批评的全新视角。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基于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将作品对人的关注视作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人性的关注表现了极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批评打破了原本固有对文学创作的纯美学解读,而是将唯物主义哲学、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伦理等要素结合在一起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在短短二十六年的人生里,杜勃罗留波夫为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理论思想被后世奉为文学批评和文艺美学研究的经典。
时隔百年,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但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仍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现今俄语文坛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阿列克谢耶维奇用自己最写实的笔触,最朴实的文字把最真实的战争和灾难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战争的讲述是对人类过往历史的回顾,对核灾难的描写则是对未来的警示,在小说《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展现了核灾难之后骇人的人间惨状,我们应当深刻地反省,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终有一天人类的未来会毁于自己的手中。正如小说中一位亲历者说道:“我们可以赢得哪怕是最为惨烈的战争,战争过后人们心中充满着希望和勇气。但是核灾难之后,心中留存的只有无尽的绝望与恐惧,在这里你会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可能明天就是末日审判,切尔诺贝利它不是普通的名字,它是一个印记,它改变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9]132心中的苦难终有一日会过去,但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她的文字告诉我们苦难的历史不会被忘记,她也一直践行着自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原则,用自己的作品启迪读者思考,为这个时代留下最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