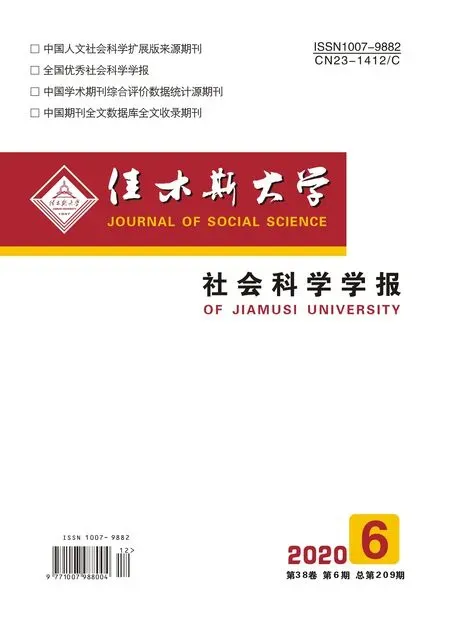论贾平凹《极花》叙事背后的情感暗流*
刘建华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
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力作《极花》自问世以来就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反响和热切关注,赞誉之声有之,批驳之声亦有之。小说写了一个被拐卖女性的遭遇和心路历程,是由一个极为惨痛的案件铺衍而成的故事,更是时代大背景下黄土高原一个濒临凋弊的村庄的生活缩影。纵观整个故事,人物关系的节点似乎都围绕着那双象征着城市的高跟鞋展开。胡蝶渴望城市,偷偷用母亲卖废品的钱买了生平第一双高跟鞋,舍不得脱下,并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城里人身份决心去找工作挣钱,在这一过程中不幸遇到人贩子被拐卖到僻远荒凉的圪梁村黑亮家,命运由此发生根本性转折。之后梦想中的高跟鞋被黑亮强行脱下,乡村哲人老老爷劝她安于天命,忘记高跟鞋。与此同时农村的凋弊也将更加触目惊心,胡蝶与黑亮的孩子——兔子的命运更是前途未卜。这是一种无可言表的绝望,人物在现实的困境中,似乎无论怎样挣扎求索都无路可走,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引发作者深深的质疑和隐忧,胡蝶折翅只好化为蛹,麻木的活下去,黑亮们则将继续群策群力买女人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老老爷风烛残年,最终将渐渐淡出并被遗忘,久远的乡风乡俗也终将如一声叹息、一丝蛛网般淹没在时代的尘埃里。
关于这部新问世的长篇小说,许多研究者已经多角度多侧面的对其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本文拟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去探究一下作者的态度,探究一下被冗长的自语和繁复的民俗描写所遮蔽的作者对被拐卖的胡蝶们,对被困守于行将没落的农村的黑亮们,对智者象征的老老爷们,以及对作者歌哭于斯,生长于斯的乡土的隐含的态度。
一、对胡蝶和城市——暧昧不明,多有微词
胡蝶在作品中是处于受害者位置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亲历者、讲述者和观察者。在作品的后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那位老乡被拐卖的女儿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胡蝶,作者的态度却似乎有些暧昧不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情”所能概括的。
纵观作者几十年的创作,塑造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可以说对女性形象的探索和对城乡之间复杂关系的深描一直是贾平凹创作的两条主线。这两条线时常并不是平行并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共同构筑起贾平凹的文学大厦。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作者的情感态度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生于乡土且热爱乡土的纯真女性一直是作者欣赏和褒扬的,而舍弃乡土、忘记本分的女性则成为其排斥和嘲讽的对象。
(一)“卑微”黯淡的角色定位
胡蝶的形象塑造完全符合作者近年以来逐渐“跌落”的女性人物刻画。纵观贾平凹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呈现一种逐渐“跌落”的状态。由最初美好圣洁的女神跌落至沾染欲望气息的“人间”女性,再由“人间”女性跌落至愈发暗淡的世俗女子。“贾平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阴盛阳衰的现象,女性形象在数量以及刻画的力度上远比男性多且丰满,如黑氏、小水、白香、小月、师娘、烟峰、唐婉儿、西夏、菊娃等。这些山乡中的年轻妇女貌美、善良、淳朴。……贾平凹爱写女性,也写美了女性,女性之于他是‘圣洁的菩萨’。对早期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形象比如小月、烟峰、香香等,作者是带着些微的‘女性崇拜’的感情去书写的。”[1]46-51在此之后,“长期寓居城市使作家对于城市生活更加了解,贾平凹的写作背景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时期作家试图消解理想的女性形象,把目光投向了进入城市之后具有现代都市女性特点的农村女性,女性形象回归到生命的本真状态———‘世俗化’。平凡的女性是世俗中真实的女人,她们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菩萨。”[1]46-51整体上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的创作态度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其笔下的女性人物也由云端降落至到尘土;由乡土社会中象征爱与美的精灵转变为进入城市后被欲望熏染的蒙尘之珠。贾平凹自己也曾说过: “我以前真不愿意把女子写丑,认为女子投世就是来贡献美的。写完《废都》我是立意要写美女人,也要写丑女人。”[2]221世俗化的女性在作者心目中失去了神性的光芒,世俗化下的种种欲望更是让作者的笔调带有了批判的色彩。而在作者心目中世俗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贪慕城市,背弃乡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女性形象逐渐“跌落”的过程也正是乡土逐渐凋敝的过程,正是因为乡土的凋敝,曾经带有神性光芒的女性日益“退化”为渴求城市,贪慕虚荣的世俗女性。
在胡蝶的角色定位上作者不再像以往那样倾注过多的审美情感。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从农村到城市靠母亲捡拾破烂为生,最主要的是她缺乏那种以往作者笔下女性被“审美对象化了”的神性,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子。在故事的最初,胡蝶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浅薄的、爱慕虚荣的、一心只想成为城里人的女孩子,虽经历了被拐卖的惨痛经历,但作者隐含的情感指向却让人很难对其产生真正的同情。在作者笔下,初到圪梁村的她带着城里人的优越,其惨痛的遭遇似乎主要是因为她“不安于室”,歇斯底里,屡屡想要逃跑。为了买一双高跟鞋,把母亲辛辛苦苦收来的两架子车废品偷偷卖掉。穿了高跟鞋的胡蝶“个头一下增高了许多,屁股也翘起来,在屋里坐不住,蹬蹬噔地到街道去,蹬蹬噔地又从街道返回出租屋大院。” 然后“又偷偷买了穿衣镜,每天照脸,照高跟鞋”。在胡蝶心里,自己已然成为城里人。“我已经是城里人了,我就要有城市人的形象……有意小步走,学着说普通话,给弟弟汇学费时偷偷扣下一百元染了一缕黄头发。”在被拐之前,作者展现给我们的胡蝶就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没有深刻丰富的内心世界,只知道从外在将自己包装为城里人的略显“风骚”的姑娘。所有的青春梦想都凝聚在那双象征着城市的高跟鞋上。被拐之后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反复强调其内心苦痛的根源在于城市梦的破灭。
(二)渐变的批判锋芒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做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尽管通篇是主人公的喃喃自语,但其中透露出的却是作者隐含的态度,巧妙之处在于作者并不直抒胸臆,全用人物的口吻让其自说自话,自我表演自我揭示。作者因胡蝶对城市的追逐而对其在字里行间多有微词,时常下意识地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基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一种无意流露,作者甚至小心翼翼地遏制这种不太“妥当”的不满,毕竟女主人公是最大的受害者,理应报以同情,但是我们稍加体会就能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情绪。但这种情绪,这种对胡蝶的潜在态度在作品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随着女主人公对圪梁村、对黑亮态度的变化而逐步变化。胡蝶的态度转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来之时,以命相搏,想要回到城市;被强暴并怀孕后,态度明显和缓;孩子出世后,主动自愿的留了下来,彻底放弃了高跟鞋。相应的,作者对胡蝶的看法也由批判渐渐转变为理解和肯定。
首先,冷眼旁观中的批判。从进入黑亮家的窑洞的第一天,黑亮就脱去了胡蝶的高跟鞋,给她换上了一双布鞋,高跟鞋和布鞋之间的距离就成为城市和农村的距离,成为一个城市姑娘和农村儿媳的距离,胡蝶坚决不穿,因为“失去了高跟鞋就失去了身份”,在与黑亮因为鞋的问题而争执时,胡蝶说“是不是看我是城市人又年轻漂亮就多给了五千元?你就是掏十万一百万,你觉得一头毛驴能配上马鞍吗,花是在牛粪上插的吗?”这是胡蝶对其被拐卖境遇的抗诉和诘问,话语间充满对农村的鄙夷。多掏的五千元被认为是对城市身份的奖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胡蝶内心的自我价值感——尚未分明的城里人的身份,以及稍有姿色的年轻身体。这与其说是在凸显主人公的年轻貌美和不幸遭遇,不如说是作者在冷眼旁观中的隐隐批判。
客观来看,胡蝶的城市梦,只是一个出身乡村的姑娘单纯美好的梦想而已。因为经济条件的困窘她初中毕业辍学到城市帮助母亲收废品赚钱。城市打开她的目光,使她产生强烈的融入和皈依的渴望,渴望拥有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身份,哪怕仅仅是在装扮上。一个年轻的姑娘,怀着对城市的憧憬,对懵懂爱情的憧憬,用一些特殊的小手段、小心思装扮自己,本可以表现的非常诗意和美好,但在贾平凹笔下胡蝶退去了原有的光环,其内在世界也就变得黯淡,庸常,甚至浅薄粗粝。这无疑是作者叙述中投射出的一种略显苛刻的“批判”笔调,是作者对人物的潜在定位。正是这种定位使得读者很难对饱受磨难的女主人公产生真正的“爱与同情。”
其次,渐趋温和的理解与肯定。在胡蝶被强暴并怀孕之后,黑亮将栓狗的铁丝撤了,胡蝶的反抗姿态也变得日益和缓。最初胡蝶眼看着自己由唇红齿白变成头发干焦,皮肤黑黄。但怀孕后胡蝶却转变了心态,不愿自己再继续丑下去,开始洗脸梳头,甚至还要黑亮买回许多化妆品。曾经的胡蝶最触目惊心的反抗不是疯狂的挣扎,而是每天在窑洞的墙上刻道数日子,但怀孕之后她渐渐变得平静,不再刻道,也不再回忆自己被拐的经历。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如今……”。每一次“如今”之后,胡蝶与黑亮的心理距离就近了一些,与圪梁村的距离也近了一些。怀孕后的胡蝶一点点走近她日日夜夜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并开始慢慢说服自己接受并适应自己的处境。一直寻找不到自己的星星的她最终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星,甚至还看到了属于儿子的小星。并由此发出对命运的喟叹和对所处环境的认同。此时的胡蝶逃离此地的信念已经淡化很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腹中的孩子。胡蝶开始警醒自己之前的“过激”行为,怕自己成为一个 “坏灵魂”,并且主动要求承担家务,甚至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她的自我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我厌烦这里,所以一切都混乱着,颠倒着,龌龊不堪。”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改变眼光,那么这种环境并不是无法接受的。 “我开始真正的在村子里的生活,不再隔着厌恶和排斥,先是跟麻子婶儿学剪纸,每天忙于带娃养娃。”此时的胡蝶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圪梁村的一员了。
与此同时作者对胡蝶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观。胡蝴的形象由爱慕虚荣的姑娘变成一个隐忍、包容甚至贤惠体贴的农村媳妇儿。之前胡蝶为变成城里人所进行的“穿衣打扮”的改造,给读者的印象是爱慕虚荣的;而怀孕后的胡蝶由“不修边幅,蓬头垢面”转变为注重修饰在作者看来却是值得嘉许的,因为只有在胡蝶转变了她对圪梁村的态度并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后,她的“美”才是值得肯定的。胡蝶的主动操持家务,胡蝶的主动与村人接近都带有了一种迷途知返、回头是岸的意味。作者对胡蝶态度的转变同样体现在黑亮对胡蝶的看法上,文中黑亮三次夸赞胡蝶。刚被拐来的胡蝶被关在窑洞里,黑亮说“你是炕上最美的花”,“炕上的花”凸显的只是作为女性传宗接代的意义,同时给黑亮带来“得意和体面”;胡蝶怀孕后,黑亮对胡蝶说“你刚才笑了好看的很!”这是他第二次夸赞胡蝶“好看”,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对其外在容貌的肯定,而有了情感的交流在其中。黑亮第三次说胡蝶好时特别强调“你比她(訾米)好”,这次不再单纯局限于胡蝶的好看,而是全方位的深度肯定,肯定胡蝶作为一个人的内在尊严和价值。黑亮的态度实则正折射出作者的态度。在这种情境下作者甚至“既往不咎”地让胡蝶再次穿上了高跟鞋。原本被排斥的高跟鞋在此刻成为了一种带有作者肯定的奖赏和抚慰。
二、对黑亮和乡土——感同身受,既鼓且呼
如果说胡蝶是从城市里飞来的“物种”,那么黑亮则是土生土长的乡土的根苗。一直关注乡土、热爱乡土、书写乡土的作者不得不心痛的面对一个事实——乡土的衰落和凋敝。曾经活跃在其作品中的元气满满的乡土人物慢慢褪色,新的时代洪流下农村成了人们想要奋力逃离的地方,逃不出去而又不得不挣扎求活的就剩下黑亮们。此外还有曾经“辉煌”的见证者,文化之根的维系者——老老爷们。这些人物的哀与乐,歌与哭,失落与向往,绝望与希冀,作者都感同身受。他或许不那么理解胡蝶们,却与黑亮们有着强烈的共鸣,对农村的“荒凉”现状有着切肤之痛。
(一)对黑亮——不动声色中的些微肯定
黑亮作为作品的男主人公,作者在刻画时虽不露声色却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客观而言黑亮是人贩子的帮凶,是拐卖行为的最终接盘者,也是关押、强暴胡蝶的直接实施者。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来讲这都是极其罪恶的行为,理应成为受谴责的对象。可是通观全篇,黑亮却并未激起读者应有的愤怒,甚至会引发一丝理解和同情。我们不禁诧异,为什么作为受害者的而胡蝶未能引起我们充分的同情,而作为施暴者的黑亮却时时让我们产生心有戚戚焉的感受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同样要从探究人物的角色定位开始。
第一, 黑亮之所以特别,恰恰是因为他是村里得城市风气之先的青年。稍稍多上了几年学,开了个小卖部,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好于其他人家。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已经不再完全困守于土地,拥有村里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的“先进“交通工具——手扶拖拉机。正是由于有一点受教育的基础,并且常常与外界(城市)保持联系,因此对女性有着最低限度的尊重,尚未将女性视为纯粹意义上的“物”。这些可以说都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产物和象征。而且如果有可能有机会,黑亮们绝对会抛开农村到城市去寻找出路。摒弃农村,向往城市的胡蝶受到作者的隐含的批判,而根在农村,追逐城市的黑亮却得到作者的隐含的肯定,这其中的态度颇为值得玩味。
第二,黑亮的施暴的“恶行”都是在特定情境下发生的。正是这种特定的情境使得我们不去关注和追究行为背后的个人品性的因素,而是更多地去思考其背后的推动力,思考施暴者的“情非得已”。胡蝶被关押是因为抵死不从,“在窑里狂躁,咆哮,捣乱,肆意破坏。”黑亮第一次动手给胡蝶一记耳光,是因为胡蝶污蔑圪梁村是一个只有“破破烂烂的土窑洞”和“只长着消化器官和性器官的光棍”的村庄。对于黑亮对胡蝶的强暴,同样是在相关情境的铺垫下发生的。胡蝶的“顽抗”使得“同房”有名无实,让黑亮爹伤了心,黑亮爹在“无奈”之下请了村里人,鼓动黑亮“像个男人”,而且正是请来的六个村里的男人“一起嚎叫着在土炕上压倒了胡蝶”并把胡蝶结结实实地捆绑好。黑亮是在众人的“帮助”下,在酒和血葱的共同作用下实施了强暴。而且强暴本身是为着子嗣延续的百年大计,如此一来,“帮凶”们的行径似乎更为让人愤怒和憎恶。可以说作者在对黑亮的形象塑造上处处打着埋伏,处处“留有余地”,因此直接施暴的黑亮的“罪孽”似乎也就冲淡了许多。
而对胡蝶所遭受的暴行,尽管是以第一人称在叙述,但作者冷静的笔触却总让我们觉得那痛苦与主人公隔着一段距离,仿佛是别人的痛苦了。在胡蝶第一次逃跑被捉回遭遇村民们的暴打时,作者是这样叙述的:……脸上有了巴掌扇动,像泼了辣椒水,像烧红的铁在烙,像把脸上的肉一片一片打了下来。……无数的手就伸过来,头发被踩住,揪下一撮又揪下一把,发卡没有了,耳朵拧扯拉长,耳环掉下去了。我抱了头抵抗,左冲右撞,当双手再也护不了胸,胸罩被拽去了,上身完全裸光……如此细致的暴行的描写,笔调却又如此平静甚至淡然,一切都像是被“消化过”的,冷眼旁观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不那么赞成当下流行的“一种用笔狠狠的,很极端的叙述”,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要“暴行”与读者拉开一定的距离,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第三,将黑亮与其他人物进行横向比较。作者在处理黑亮的形象时虽并未将其形象人为拔高,但在字里行间却时时让黑亮的行为透露出人性或人文关怀的光辉,淡化其行为本身的“罪恶性。”黑亮对刚被拐来的胡蝶只是关起来,少有打骂的举动,完全不像村里的其他人为了防止媳妇逃跑甚至动辄将其腿打断。而且除了关起来“软禁”之外,其他方面似乎还有额外的优待。自己家里每天吃荞面土豆却为胡蝶到镇上专门买白蒸馍,保证她每天能吃到两个;被胡蝶抓破脸也不声张,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在胡蝶逃跑未遂,遭村里人肆意凌辱的时候,最终掀开众人扑到胡蝶身上护住她并将其抱回窑里。胡蝶遭受暴行时,本是直接责任人的黑亮却俨然成为胡蝶的保护者。此外,在作者笔下同样是“帮凶”的黑亮爹对胡蝶也有其温情的一面。他告诫黑亮“你要待人家好好的”。胡蝶吃不惯家里的饭食,黑亮爹就想法儿给胡蝶变换伙食花样,把单纯的蒸土豆变为炒土豆丝,焖土豆块,砸土豆糍粑。胡蝶怀孕后,特意将下蛋的黑鸡炖给胡蝶吃并给胡蝶的床加褥子。“你现在地位提高了,就得睡的舒舒服服,一颗黄豆都不能垫着你”。胡蝶被麻子婶儿“做法”之后昏睡不醒,黑亮爹甚至对麻子婶儿说“她哪怕缺胳膊少腿,成了傻子瘫子,只要是咱的人,在咱窑里,我都会好吃好喝地伺候的。”这俨然有一家人不离不弃,相互扶持,风雨同舟的意味了。
(二)对“老老爷”——无限怅惘中的深情怀恋
作为乡土文明守护者和传承者的“老老爷”,更是寄托了作者对乡土的深情怀恋。如果说黑亮的代表受难的农村,代表作者念兹在兹的乡土,寄予了作者隐曲的同情和惋惜的话,那么作者对老老爷则是立场鲜明的褒扬。可以说正是老老爷间接促使了胡蝶的转化。老老爷指引胡蝶看星星;老老爷组织村里人给黑亮家里“送娃”;老老爷劝慰胡蝶接受自己的处境;当胡蝶面对怀孕不知所措时,老老爷对她说 “你才是药哩,你是黑亮家的药”,“这孩子也许是你的药”。而且老老爷也自觉承担起乡土守护神的角色。老老爷捉蝎子给村里人泡药酒;老老爷为每个人编织彩花绳;老老爷为村人调解纠纷、排忧解惑。最重要的是老老爷所代表一种处世观念——达观无为,心怀天地。这种观念饱含生存的智慧,同时也有自我麻醉的嫌疑,很难简单加以评判。最为典型的是当胡蝶追问自己的星星是不是只有在城里才能看到时,老老爷劝慰她说“在哪还不都是在星下啊,胡蝶”。这种理念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同。当胡蝶挣扎着要离开圪梁村,大喊着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黑亮的回答是“待在哪儿还不都是中国”。麻子婶儿回顾自己几段悲惨的婚姻遭遇时感慨“折腾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哪里都睡在夜里。”正是这种生存哲学一方面延续着乡土传统的绵延不灭,另一方面也使得乡土在变革的时代大潮中步履维艰。随着村庄的日渐衰落,老老爷的地位也将愈加尴尬,尽管极力维系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却终究无力回天,淹没在历史的滚滚大潮之中。
三、理性的审视和反思
(一)关于女性
前文提到作者对胡蝶的态度是随着胡蝶对黑亮、对圪梁村的态度而转变的,而胡蝶态度的转变又是其自身心理转变的直接投射。在作者的描述中,胡蝶的几次心理转变都是在几个节点性事件发生后产生的。刚被拐卖到圪梁村的胡蝶是极其尖锐和“强硬”的,完全无法接受被拐后“安分守己”过日子的“奴隶的哲学”。她如困兽般用生命进行反抗。甚至在逃跑被抓受到百般凌虐之后依旧丝毫不妥协。“黑亮每一次打开门锁进来嘎啦一响,我听到了,立即睁大眼睛,拳头紧握,准备着反抗。”为了防止黑亮的“侵犯”,“用布条子把自己的裤子从腰到脚绑了无数道,而且还都打了死结。”但这一切在胡蝶被黑亮强暴后却马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尖锐的棱角似乎一下子被磨平了。身体被占有后的胡蝶“没有了往日的力气去哭,去叫骂,去摔东西,甚至连呆坐一会儿都觉得累。”对黑亮也不再严防死守,只是拿一根棍子象征性地放在炕中间。一夕之间,霄壤之别,完全没有过渡和起伏,胡蝶就完成了她对被拐卖的境遇的根本认同。而在胡蝶怀孕之后,抗争的锋芒似乎愈发消失殆尽,肚子里的孩子越长越大,我竟“收拾了头发,又穿上了那双高跟鞋。”
在作者笔下女性的自我认知、价值取向似乎直接对应于她的身体。这种表达不仅过于简单化,而且有失偏颇。这与贾平凹作品中的女性观也有很大关系。“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女性往往是被亵玩的角色,贾平凹很会写‘你玩女人玩的真好’的小说”[3]7,这一观点尽管有偏激的嫌疑,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的一种“无意识”。正如前文所述,作者对胡蝶的态度尽管有同情的成分,但这同情之中却难掩“责备”的含义,颇有“受害者有罪”的论调。如徐刚在《消极安放乡村女性命运令人不适——评贾平凹极花的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一文中所说,“小说其实意在强调乡村女性对城市的向往本身所包含的罪孽。《极花》的讽喻意义也在于,主人公胡蝶被城市消费文化所裹挟,而丧失了认清自己真正需求的能力,但在她一番苦痛的挣扎和精神历险之后,反而在被拐卖的处境之中意外地体认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进而获得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认同。小说中,胡蝶于惨烈的创痛中重新建立自己与乡村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女性在绝境之中对命运屈服的过程。在此之中,原本是乡村的逃离者,却带着永远无法摆脱的负罪,又重新绝望地回到了乡村。于是“拐卖”之于胡蝶,就变得意义含混起来,它仿佛就是欠缺教训的乡村之女所理应领受的人性功课。这究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复归,还是新的压迫的轮回?无疑是值得讨论的。”[4]16在“责备”受害者的而基础上,施暴者的形象却被作者给予了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作者在后记中写到“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5]207的确,拐卖背后的因素值得我们去深思,但简单地将这一罪行归咎为城乡的二元对立,归咎为单纯的城市对乡村的“掠夺”,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二)关于乡土的出路
尽管作者难以忘怀乡土,但他笔下乡土女性的嬗变却恰恰折射出其矛盾的心态。在采风中,当贾平凹看到长期处于艰苦生活中的农村妇女种种情状,他都想到了那个女孩(被拐卖的老乡的女儿)。贾平凹曾说过,“写作是你能明白历史的整体又不明白个人的具体,都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当亲戚朋友突然去世又都悲痛不已。一个农民儿子的角度,或许与历史的进程相矛盾,但感受却是真实的。”[6]3这就是作者的矛盾所在,明白乡土的千疮百孔,却又割舍不下血脉相连的乡土情怀。作者极力为乡土“鼓与呼”,但乡土上的人们,黑亮、黑父、村长三朵、立春、猴子等等却让人难以看到希望,让人心痛而且无法释怀。尽管老老爷给村里人起名字时忠、智、德、孝、仁等字眼儿统统用上,仿佛用了这些名字,村人们就可以像这名字一样构筑起一个理想国来,但这不过是强弩之末的微薄努力,人们需要这些,却并不把这些当回事。真正生活中村人们还是猴子,毛虫、腊八、满仓、栓牢,有着最原始最朴素的欲望和弱点。毛虫质疑道德象征的老老爷“他能给我一碗饭还是一分钱?我认他了他是老老爷,不认他了就是狗屁。”可见传统习俗道德的规范是多么苍白无力。
作者深知城市化的洪流毕竟滚滚向前,其中出现的阵痛难以作为否定城市化的依据,但对生长于斯,歌哭于斯的热土又难舍偏爱的情怀。可无论怎样凋敝的乡土毕竟一定程度上成为滋长罪恶的温床。“从 1978 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到《浮躁》《土门》《高老庄》,到《怀念狼》《秦腔》《高兴》,再到《古炉》《带灯》《老生》,从土地承包改革到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农村发生的大转折都在他的作品里。他的笔下有对故乡的无比依恋和怀念,也有对人离开土地之后怎么办的迷茫和追问,更有面对商业化浪潮冲击下人性异化扭曲时充满批判的矛盾心情。”[7]10面对凋敝且滋生罪恶的乡土,作者无法为其找到出路,但同时也无法直面乡土无可避免的衰落。于是不得不在叙事中显出取舍间的两难和游移。文中理想化的女性是黑亮娘,“茶饭好,针线好,地里活也好,”并且“长得干净,性情安静。”但她在小说的开始就死去了,留下的是对未来儿媳的期许。尽管在被拐来的媳妇中胡蝶已经是“个中翘楚” ,但胡蝶不是理想的儿媳,麻子婶儿、訾米们更不是。失去了理想中美好女性的乡村还有多少亮色?回到城市的胡蝶无法立足,那么回到农村,回到那片带给她耻辱也带给她割舍不下牵挂的乡土,又将会有怎样的未来呢?
作品中透露出作者的两套法则:城市法则和乡村法则,实则为两种价值评判标准。一种是乡土法则。依照乡土世界的理念和运行规则,为了子嗣绵延,即便是拐卖人口,囚禁妇女,这都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甚至智者象征的老老爷对这一行为都是默许并支持的,没有人对此有反思,似乎这是不得已语境下的天经地义。作者借黑亮之口道出城市对乡土的无情“盘剥”,失去女人的乡土最终的命运将是沉底的干涸和凋谢,在此基础上任何为乡土“续命”的行为都成为可以理解的,其中饱含的是对乡土世界的怀恋、同情、惋惜和怅惘。作者也不避讳村子里男性的集体暴虐,但作者笔下的这暴虐似乎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凸显胡蝶所处环境的相对安逸美好,有对胡蝶“招安”的嫌疑。而对城市作者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质疑,贪恋城市的胡蝶得到的是深重的惩罚,而且胡蝶“回归”的遭遇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城市的不包容和冷漠,这种冷漠使得一心向往城市,拼死逃离乡村的胡蝶寒彻心骨,难以立足,最终不得不回到曾经囚禁她的圪梁村,海纳百川的城市却容不得一个“失足”的弱女子,作者借此传达的是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排斥和深深的迷惘。
但对乡村法则的最终皈依却无法真正拯救胡蝶,对乡土法则的隐含认同同样无法为作者依恋的乡土找到真正的出路。胡蝶脱下高跟鞋安守乡土之后的命运会是怎样呢?无非是另一个麻子婶儿或者訾米。即便成为另一个黑亮娘,最终面对的也依旧是走不出的穷困和无力回天的“绝后”境遇。她的儿子则可能成为另一个黑亮,这种循环令人不寒而栗。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 “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的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5]208。城市化的浪潮泥沙俱下却难以阻挡,无论是阵痛也罢,牺牲也罢,乡土注定要在时代的变革中饱受洗礼,负重前行。当一切归于绝望中的平静,胡蝶几乎忘记了高跟鞋的存在,她的脚步最终停在了圪梁村,城市的高跟鞋似乎就此偃旗息鼓。但高跟鞋的笃笃声却一直敲打着乡土大地的神经,敲打着一颗颗躁动不安而又茫然无措的年轻的心灵。不可抗拒的城市化浪潮终将一浪高过一浪,势不可挡。无数的“蝴蝶”还是振振翅膀,以各式各样的姿态前赴后继飞向城市,禁闭一只“蝴蝶”终究于事无补。胡蝶的出路何在?乡土的出路何在?这依旧需要我们在前行中思索,在前行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