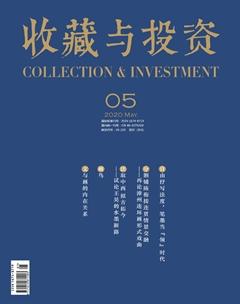浅谈王昊墨荷的现代性
刘枫林

一
当下画荷的人,多如牛毛,以水墨介入画荷的画家也比牛毛还多。如果简单地将王昊所画的荷花归为牛毛的行列,那只能说明你不懂画。阅读王昊的墨荷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问题;一个是,以水墨作为媒介的艺术家切入当下艺术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谈论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但实质上是反思水墨艺术的现代性问题。
在宏观的视野下看待世界艺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特殊性,但像中国这样特殊的实在是不多。从欧洲步入现代化开始,商业文明所构建的商业文化席卷全球,在世界上建立起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各种次生性商业文化,与此同时缔造了相适应的科学、技术、制度等等。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存环境都经历了主动或被动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地区失去了传统,适应了现代。比如韩国艺术家白南准的影像作品,虽然带有现代性,但也缺乏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性。换句话说,以白南准为代表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属于工商业文明艺术的范畴。
而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中国艺术有着深厚的传统,绵延数千年经久不衰。中国的艺术在外来文明的强势侵袭下做出过为了适应生存的改变,一旦生存状态不再紧迫时,又陶醉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从而表现出一种畸态。近代以来对中国画的数次大讨论都在讨论绘画的先进与否、优劣与否,实际上却没有从根本的生存方式转变的角度来认识新旧艺术的问题。在看待王昊的作品时,需要一个阅读的语境,不是停留在欣赏笔墨的表現,哪一幅画的构图等。就像在看刘晓东的农民工人物肖像作品时,透过现代画家所表现的底层人民的复杂面孔可以透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并不遥远的农业文明的底色。再比如贺丹的作品《大合唱》其中每一位少年的面孔中都透出隐隐忧郁,众人在一个极不和谐的氛围下完成合唱。我们不会停留在欣赏他们作品的技法层面。
进一步来说,在面对水墨现代性的问题时,相当多的人还处在农业文明的状态。而文化艺术所反映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就是需要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进程中寻找那些充满矛盾的文化现象。当我们谈论中国艺术的现代性时,我们不得不先反思农业文明的底色。
二
重新理解农业文明是了解我们文化传统的钥匙。对于传统,很多人都觉得并不陌生,甚至很多人依然认为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这种认识,恰恰反映出大部分人对传统认识的肤浅。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简单的诗情画意,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底层生存逻辑。前文谈到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而农业文明又是建立在东亚大陆特殊的人文地貌上的,客观的自然物候条件创造了“两黄文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适应生存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观、物观、人观。靠天吃饭的属性,致使两黄文明最终统一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之下。中国人自古祈雨敬天的观念也是来源于生存本身。所以古人的自我意识不明,天人合一理念才是农业文明的典型思想形态。我们今天全盘西化,很容易用西方的思维来批判中国。故而,很多人会在一个问题上无法理解,即艺术所要表达的对象并不是物象,而是人观,也就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借由艺术表现出来。
古代读书人在中国千里挑一,据1987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明代官民比例为1 : 2299。这些读书人中只有一部分参与到艺术创作之中,因此古代中国的艺术文化是在极少数的人群中发展和流布的。虽然这种判断标准不能代表古代艺术创作者的全部,但可以想见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艺术几乎是在部分地主、官僚精英的群体中发展的。今人看待古人留下来的文献时,不能将其看成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以单一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儒家经典文化传统已经构成了对其他文明的认识遮蔽。这也导致传统艺术在一个单一体系下发展,无法革新。再加上特殊而封闭的东亚地貌,致使中国与外界交流较少,这也在外部无法刺激其发展。
农业文明的生存核心在于耕种,对于农业文明而言,生存竞争就是争夺土地,非商业资源。因此中国不可能在农业文明的根基上发展出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发展出农业文明之外的文化艺术。“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就是这一问题的最有力的说明。英国艺术史学家科律格在《长物》一书中最值得深思的莫过于晚明江南地区的物质生活十分繁荣,但究其根本却不是工商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寄生在广大农民身上的大地主大官僚阶层之间的对于人造物的趣味消费,这样的消费并不能引起大规模生产从而革新生产资料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
三
这样谈论话题的目的在于给读者寻找一个理解传统艺术的脉络。王昊的墨荷所使用的材料就是根植于传统艺术的媒介。而他的墨荷与古人的墨荷有什么区别呢?古人的艺术是在封闭的东亚地貌条件下由极少数艺术家因为生存而产生的文化现象,那古人是如何看待墨荷的呢?这就需要弄清楚传统文化中的“物观”。
古人的物观是艺术表现的主要方面。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物”与西方的物质概念不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层面的意义和内涵。古人对“物”的认知是在长期的经验认知和思想辩证的过程中生成和发展的。作为中国审美传统中的“物”是与审美主体“心”相对应的审美客体之“物”,也即抽象层面的“物”;而作为日常器物的实体之“物”,也即是物质实体层面的“物”则是人们看到的客体。其次,古人对于抽象层面的“物”在表现层面是一种自我关照的心理过程,而在具体的描摹中又表现为独特的生理和心理二者的结合。在心理方面,传统艺术表现为对自然的膜拜,具体是在“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下的美感体悟,表达为诸如壮美、雄浑、冲淡等自然状态之美的总结。再加之古人把书品、画品与人品相对应,结合个体的不同遭遇,来品评人和艺术。在生理方面,传统绘画追求笔墨的表现,比如什么样的笔墨耐人寻味?什么样的用笔值得追求等。“锥画沙、屋漏痕”的笔墨标准是画家在常年用笔、墨、水、纸(绢)等材料进行书写创作过程中所建立的肌肉感觉,这种感觉被描述为一种高超的技巧。由于常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技巧水平,故而在后代的绘画中受到追捧,形成一套独立的绘画技巧体系。
以上皆欲说明中国传统艺术根植于传统物观,在传统艺术的长期流变中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艺术表达范式,尤其是对于线条的钟爱。线条讲究中锋用笔和枯湿浓淡,强调笔笔写就。而写物实际是表达自己的品性而非状物。比如八大山人的绘画用线简约,造型生动,尤其是翻白眼的鱼,后人在解读时都认为其作品反映了他作为遗民身份对清朝的愤懑。由于八大山人的作品并非表达个体觉醒,而对于其作品在形式上具备的某些现代感却不能证明他的作品就是现代艺术的范畴。反观凡·高的作品,他的自我表达、自我肯定、自我怀疑、自我治愈等都通过绘画发泄。两种艺术虽然在艺术规律上有一定的相似处,但其精神实质却相差甚远。王昊的作品是从传统中来的艺术,而读懂传统艺术,需要了解传统艺术存在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先构建一个阅读传统艺术的框架来说明王昊绘画的传统性。
四
王昊的墨荷具备了传统艺术的诸多长处,这与他学艺的路径相关。王昊是郑奇的弟子,而郑奇又求学于董欣宾,董欣宾在南京艺术学院又是刘海粟的研究生。对于中国艺术传统,王昊继承了“南线”一脉,这一脉可以追溯到王维、董源。但王昊并不满足拥有这样的造诣做一个“传统型”画家。关键还要在当下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中把握具体的时代脉搏才能创作出更有价值的作品。
中国处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我们再也回不到纯粹的农业文明形态了,仅仅停留在对传统艺术的膜拜和学习只会沦为传统艺术的背景;另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表达,人的精神状态普遍遭到商品消费的异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看待王昊的作品,可以找出有效的解读路径。
中國人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什么是糟粕?在艺术领域至少那些桎梏艺术发展的均可以算是。什么是精华?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自然观是精华。古人在生存中形成了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这种观念与西方自工商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与自然竞争的观念不同。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生存,文化是人这种质性动物的生存状态。在当下的工商业文明中,愈演愈烈的竞争,已经让很多人在商业社会苟延残喘。保留一部分农业文明的优秀传统将对人类生存十分有益。而当今世界文明只有中国保留了最古老、最完整和最纯粹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样本。因此,我们的艺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所形成的文化无法充分发掘个体的价值,因此人力资源的充分调用将会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产生良性影响和提供持续不断的资源。
在肯定个体价值方面,我们需要人文主义价值观的补充。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就有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实质是“人伦社会关怀”。孔子的学说是在强调人在农业文明形态下社会中的关系,因为资源紧张,所以我们需要一套规范来保障生存。在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人自身的价值,紧接着就进入了对整个农业文明的精雕细琢中。而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则是在人与自然、人与宗教中回归人的价值。对个体的关注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逾越的话题,艺术也不例外。真正使一个人独立是来自于纯粹人格的建立。休谟曾经怀疑一切,是因为人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无法解答。直到康德闭关十年,给出了“理性是人类的认识能力”,拥有理性成了判断人的基准。商业社会所构建的几乎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商品信息的“虚假”社会,人们往往陷入各种商品信息的洪流之中难以判断。在培根的“四个假象”说的论述中,他强调了商品广告给大众带来的认知遮蔽。鲍德里亚的观点则趋向于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中,一切都已经完成,一切都在无限的重复,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未来。后现代社会导致人更像一个消费符号,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人类似乎将亲手葬送在自己寻求自身价值的路上。
工商业文明形成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正将人从愚昧无知变为消极堕落,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产生了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即人对一切都没有欲望,包括繁衍。发达国家普遍的低生育率,宅文化都在描述后现代人类所要面临的问题。
这些问题与王昊的绘画之间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即个人的独立精神世界与商品时代所制造的人的精神追求之间是什么关系?王昊的墨荷回答的是“独立”和“孤独”。
王昊有一幅墨荷,画的是一只孤荷立在混沌的天地之间。那种颤颤巍巍却又无比倔强的一只孤荷,令人动容。在工商业时代,人们在物质欲望的无尽追逐下渐失自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得淡漠而脆弱。如何维护自我不被过度消费的独立性?在商品消费充斥的社会想保持一种独立的自我审视极其困难。正如尼采所说:“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在他周围找不到同类。”所以,王昊的墨荷透射出后现代作为独立个体的时代追问,因而那颤巍巍的孤荷显得格外的倔强而挺拔。此外,我曾在王昊的一部分画作上看到他抄的很多歌词。多是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这种题跋在内容上超越了古人题诗的范围,让传统的绘画在内容上有了流行的可能。这种方式与波普艺术也有一定的内质相似性。不同的是波普艺术是商品社会大众文化所形成的流行艺术,而王昊在水墨作品上抄歌词则体现传统绘画可以表达现代性的文化属性,这是在中国工商业文明发展之下的新艺术。它隐含了消费属性对这个时代艺术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这种水墨艺术所体现出的精神特质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水墨尝试,反而呈现出一种由传统到现代的自然而然的过渡与沟通。
五
王昊的墨荷具备传统艺术的法度,一笔下去枯湿浓淡,一笔下去墨分五色,一笔下去中锋用笔,都在小小的画面之中统一。然而如果想了解王昊作品的当下意义,则需要整顿出由传统到现代的内在变迁。先要说明王昊墨荷的“传统性”,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古人如何看待他们所描绘的物象。从物到象再到超越物象的认识,传统艺术与农业文明之间的悠远历史成为我们现代人认识传统的关键。认识了传统绘画的根本之后才可以读懂王昊墨荷脱出简单的物象描绘成为一种沟通了传统和现代的艺术文本。这种文本不同于刻意求变,而是一种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