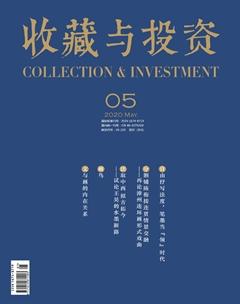托体同山阿
王皓
《国家宝藏》中,国宝守护人梁金生先生说起了他们一家人的故事。他的父亲梁廷炜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参与“文物南迁”的护宝人,他们兄妹五人,都是在押运路上出生的,他们的名字都以所到之处命名。一家人辗转各地,可谓历尽艰辛。但在历史面前,没有人能预测自己的命运。抗战结束,梁先生一家守着文物回到南京,又被指派运送文物去台湾。梁廷炜带着大儿子,再次上路,以为只是完成一项任务,可这一去,就再难回大陆。在浩浩荡荡的文物保护长征中,这不是个例,这样的“护宝人”不胜枚举。
文物是一个时代的浓缩,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不是冰冷的,它们承载的不仅仅是本身的艺术价值,还承载了“人”的温度。这种温度弥足珍贵,既可以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命脉的高度,又可以是来自普通大众的一种深深的微妙的挚爱,乃至为其献身的勇气。历史与文明的意义是个巨大恢弘的主题,而每一个跟文物相关的人,他们的故事,虽然看起来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些小片段,却更会引人落泪。真实、无奈、坚持,大时代背景下仓皇又执着的一生。其实他们的故事,就是文明传承的故事,并且与文明同在。
前面提到的文物南迁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人与不可抗力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史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接到指令,将文物装箱“南迁”。经过反复讨论和斟酌,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择和打包这些南迁文物,就耗费了半年之久,最終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尔后,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南迁南京,再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余里、耗去14年光阴、捱过了那场战争。重返故都时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在旁人看来是个奇迹,其实,是因为那时候的守护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们的崇拜皈于文物。
实现这一奇迹的人,有1933年前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有负责中路迁徙的欧阳道达,以及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一批工人、眷属,以及在各处维保的民众与警察。
在欧阳定武的印象里,父亲欧阳道达即使在暂时结束运输、出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期间,也每天不闲着地巡视。晚年时,庄尚严还自称“守藏吏”。父辈那一代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完整地裹包着文物。把文物交到后人手里,是前辈们的无上荣光,后人们也必须兢兢业业地匍匐上去。
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断,中华永无补救之举。这场文物“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它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哐当而行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迂回曲折于崇山峻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都让和平年代的我们感佩。动荡年代他们无人知晓自己的命运,仅凭借那份责任与信念,就用一生来兑现保护文物的使命。他们深知时代会变迁,自己终将逝去,但这些文物,会承载着千百年历史印记,携带着不舍昼夜的岁月,留下辉煌文明的见证,这就是国之所以为国,家之所以为家的印证。
总有人说,人生不满百,文物和我有什么关系?厮混于和平年代,战争于我何干?
我想每个人存在,都该是历史的一部分,既需要在生命长河里独善其身,也更需要在历史的水文站里做为时代的一份子留下印记来。
颠沛流离后,人生便会陨灭,但文明不会死亡。躯体易朽山河长在,与文明在一起,人就“托体同山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