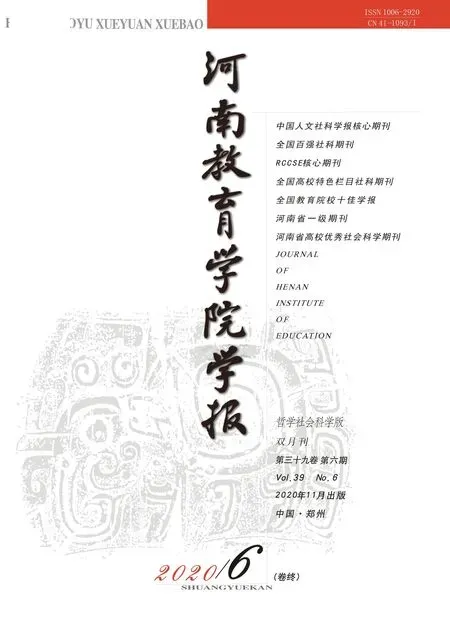抗争与妥协
——论进城农民价值观念差异的乡土书写
姬亚楠
新世纪以降,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给乡土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指生存境遇的改变,更指价值观念的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运转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农民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通过对两代进城农民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行书写,将理论不易把握的现实与情感反映在文字中,对当下进城农民的精神状态与价值观念加以关注,不仅让我们探寻价值观念转变的原因,更让我们反思农民进城以后的未来之路。
一、价值观念差异的根源
农民大批进城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30年的乡土书写,我们在作家笔下能清晰地看到进城农民被自然地分成两代人。老一代农民最初进城的目的单一且明确,只为赚钱养家。那时候,老一代农民并不知道进城能做什么,对城市的认知几乎为零。新一代农民是在父辈们经验的指引下进城,对城市有更充分的认识与了解,他们进城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更具有开拓性,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成为城里人。新一代农民与老一代农民在进城问题上的差异化认识源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差异,新一代农民既没有经历过老一代人在农村生活的快乐和幸福,也没有体验过老一代人在城市的艰辛与曲折。因此,老一代农民对农民身份采取认同的态度,他们深知城市只是赚钱之地,土地、农村才是永久的家、生存之所。新一代农民对城市充满了向往,他们大都对农民身份采取抗拒的态度。在笔者看来,农民价值观念的差异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同的乡土记忆
乡土记忆背后隐藏的是对家的回归,老一代农民“有丰富的农村生活阅历,对农村传统、乡土习性、行为规则等有更坚定的认同,对乡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心理情结”[1]46。在老一代农民心中,乡土的意义非凡,它不仅是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心灵的归宿、生命的归属。就像《北去的河》中的刘春生,乡土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房子,更是土地、树木、山水,是那丝丝气味,即便是死也有痛快的惬意。《拯救父亲》中的周伯以及《大嫂谣》中的大哥、大嫂,他们从心底认同农民这个身份,即使进城打工,终归还是要回乡的,乡土给予他们的温暖与幸福无法被取代。然而,新一代农民出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九十年代,成长于经济飞速发展的2000年左右。现代化进程加速了城市的兴起、农村的没落,年少时父辈们的离乡,亲情的缺席,使他们的成长经历不那么愉快。长大后,他们带着对城市的好奇、憧憬进入城市,城市的繁华、城市的便利、城市的先进,城市的一切都令他们应接不暇。相较于短暂的乡土记忆,城市的光怪陆离深深地刺激着他们,他们渴望在城市扎根,渴望自己漫长的未来能在城市。《极花》中的胡蝶,不认同母亲对自我的价值认同,并发出“我现在就是城市人”[2]18的自我宣言。《明惠的圣诞》中,明惠高考失败后怀着改变命运的想法进城,不容自己有片刻的休息,希望能做个城里人。这些新一代进城农民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安于现状,而是要追求自己的梦想,走出一条新路。
(二)不同的人生阅历
老一代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他们最开心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在农村度过。土地不仅是他们所有美好记忆所在之地,更是他们心灵的居所和灵魂的故乡。中年进城打工,由于社会因素和自身素质原因,他们只能拿最少的钱做最累的工作,无家的漂泊感使他们从心底更加认可农民的身份。正如《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身在城市,但心仍在农村,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故乡。有着在乡与在城双重经验的老一代农民,深刻感受到自己与城市的差距,城市的绚丽与光彩只属于城市,对于城市来说他们只是外来人和暂住者,回乡才是归途。由于生长环境不同,新一代农民往往存在着“回不了家”的心理暗示,是不愿也是不能[3]299-300。不同于父辈,新一代农民大多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他们都背负着家庭的希望,只有他们才能改变家庭原有的面貌,因此他们必须踏上离乡寻求新生活的道路,他们清楚地知道必须留在城市,在城里扎根。他们努力适应都市文化,想方设法成为城里人,但成为城里人又如何,生活仍是一团糟。《出梁庄记》中的正林,是新一代进城农民中的佼佼者,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商装设计师”的头衔使他的工作体面又精致。工作中,他西装革履、潇洒气派,满世界飞,出行尽显高大气派,接触的都是国际奢侈品牌。然而,正林生活的处境与工作环境仿佛两个世界,体面的工作并不能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在城市中,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全家蜗居在城中村的小房子里,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连出去吃个饭都是奢侈,就更别提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了。这种体面的工作与落魄的生活之间的差异使他滋生了自卑感和无助感。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生活令人厌倦,即使如此,新一代进城农民也已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
(三)不同的自我认知
自我认同是指受社会、他人等因素的影响而对自身身份、自身价值所产生的一种主观看法。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农民与城市之间互不了解、互不接受,处在双向隔膜的状态。梁鸿的《出梁庄记》将这种双向隔膜、不接纳的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老一代农民对于打工的城市全然不知、异常陌生,“在说起打工的镇子时,丰定老婆竟然想不起来小镇的名字,而她在那儿生活了将近二十年”[4]11。二十年生活、打工的城市原本应该感到温暖,至少不应该陌生,但在老一代农民眼里只不过是栖身之所。城里人对待他们的异样的眼光,是他们与城市之间的另一个屏障。“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使他们对城市望而却步,像《出梁庄记》中在外打工的梁庄人一样,他们与村庄联系虽少,但心却从未离开过。而新一代农民“我本城里人”的价值认同感极强。在《极花》中,当房东老伯夸赞胡蝶一点都不像乡下姑娘时,胡蝶也打心里觉得自己就是城里人,因为在她看来,她有着城市姑娘梦寐以求的巴掌脸、小细腰。为了能更像城市姑娘,她买了高跟鞋每天穿着,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自信地说:“城市人!城市人!”[2]18这不仅是胡蝶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更是“胡蝶们”对城市身份的内心呼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帆在阅读《极花》后说:“胡蝶们在文化巨变的时代潮流之中,她们能够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从她们身上能够体验到现实的困厄吗?我们从她们的体味中能够嗅到未来文化与文明的胎动吗?”[5]《木兰的城》中的木兰,小时候被母亲残忍地抛弃,本不想走母亲老路的她最终也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笔者认为,两代女性对城市的向往,已不单是城市文化的吸引,更多的是来自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觉醒与追求。
老一代农民离乡进城,因乡土记忆、人生阅历、个体认同等原因,在心理上接受和认同农民身份。这些因素构成了老一代农民的集体文化记忆,这种集体文化记忆“是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身历史的记忆”[6]。这种集体文化记忆不仅是老一代进城农民最终选择归乡的决定性力量,更是令他们在农民身份的价值认同中怡然自得的根本性因素。相较之下,新一代农民有着不同于老一代的文化记忆,他们对城市有新的认知,对自我有新的希望,他们拒绝甚至排斥农民身份,他们力求突破。“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儿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入足够多的工作。”[7]59对于新一代进城农民来说,未来在何方,自我价值如何实现,是他们的人生必修课。他们深陷尴尬境地,却必须找到出口。
二、城市“新移民”:同乡眼中的“体面人”
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农民特别是新一代农民逐渐意识到“农村成为她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8]。城市作为希望之地,是摆脱贫穷的伊甸园,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新一代农民希冀成为城市的“新移民”,进城以后的生活却不尽如人意。他们作为都市异乡人,不被城市接纳。即使他们过上了城里的生活,成为同乡眼中的“体面人”,但在他们与城市之间仍横亘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们必须挣扎、必须抗争,想要融入城市,就必须得到社会和他人的承认。
在喧嚣又孤独,看似亲近实则疏离的城市,新一代农民努力去战胜内心的孤独感、无用感、无力感、无根感与自卑感,苦苦追寻身份、认可、接受这些本应理所当然实则万分困难的生存状态。新一代农民中的“优秀分子”通过读书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如《黄泥地》中的房光东、《出梁庄记》中的正林,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在表面光鲜亮丽、令人艳羡的工作和身份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的心路历程。《黄泥地》中的房光东学业有成,在北京有着体面的工作、稳定的生活,在完成城里人转变的同时,潜移默化地丢弃了作为农民的淳朴的本质。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割断了与乡土的联系,疏远了与乡人的关系,使出浑身解数只为能适应城市生活,变得练达油滑、精于算计。他对乡村事务漠不关心,甚至表现出冷漠,特别是当进京上访的房国春登门时,他明知村支书房守本父子的恶行,却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闻不问。不仅如此,还劝留在在乡村的家人不要招惹是非。这个城市里的“新移民”、乡人眼中的“体面人”在现实生活中选择明哲保身、模糊是非。与房光东相反,在李佩甫的《生命册》中,吴志鹏对养育自己的无梁村给予了自己所能给的最大的帮助,而他对乡土的爱却是他这么一个“新移民”无法承受的,他最终被现实压垮,放弃大学教师这个“铁饭碗”。在城里任教的吴志鹏,在乡人眼中是“官儿”、是“干部”,是能为无梁村办成事儿的“体面人”,因此,无梁村村民无论大事小事都会来找他。但是吴志鹏清楚现实并非如此,在偌大的城市里,他生活得并不如意,也并不容易。他没钱没权没关系,在城市里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对于他来说,越来越多的来自同乡人的请求就像包袱,一个个足以压垮他的包袱。面对这些包袱,别说成为“新移民”,在城市定居了,即使是谈一场恋爱都是奢侈、是奢望,他只能一次次地逃避、退缩,但生活总是将他逼得无路可退。最终,他选择了离开高校,进入社会去打拼。现实的冷漠,命运的残酷使他发出“我已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在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流浪者。并且,永远是一个流浪者”[9]149的哀叹,但是他将继续在城市里漂泊,不能归乡。正如小说最后写的那样:“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9]433城市进不去,农村又回不来,新一代农民终将背负着双重“边缘人”的身份,继续寻求新的生存机遇。
《出梁庄记》中的正林亦是如此,大学毕业后成为商装设计师,拥有着令人羡慕的体面工作,但工作之外的生活却局促不堪,他每天在巨大的反差中频繁切换,工作与生活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落差,这种落差感无形中加剧了他的苦恼,深深的自卑感油然而生。与正林不同,《出梁庄记》中的秀中,可以说是出梁庄人中的“千万富翁”,生活惬意又滋润,在北京老乡圈中有着颇高的威信和地位。他有自己的公司,有先进的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拒绝与众多亲戚发生生意往来,包括亲弟弟、亲妹妹。在与梁鸿的交流中,秀中对弟妹和亲戚的冷漠来自对他对事业的理解,但“也夹杂着他成为新富阶层之后对过去生活的厌弃和对‘农民’身份的回避,他以‘现代管理’的名头遮蔽他的厌弃与逃避”[4]174。这种对自我身份的回避与厌弃,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秀中成为城市“新移民”的“必修课”,但可以肯定这是其价值认同和精神归属的“验心石”。
城市正以巨大的包容性接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新一代农民怀着无限的憧憬、无比坚定的信心来到城市,他们要改变千百年来农民的生存模式,他们要走出一条不同于父辈的路,他们要长长久久地留在城市,在城市站稳脚跟,成为城市的“新移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改变命运,迎来新的生活。即使寻求新路的过程铺满荆棘,他们也无怨无悔。
三、城乡间的“候鸟”:终陷宿命漩涡
新一代农民成长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年少时父辈的离乡使他们对城市充满了好奇。相较于父辈,他们对乡土少了一分眷恋,对城市多了一分憧憬,他们渴望在城里扎根,成为“新移民”,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成为“新移民”,扎根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居无定所、心无所安,这种无家感与无根感又无时无刻不在强化他们内心的宿命感。
新一代农民有着不同于父辈的理想。他们怀揣着梦想进城,不怕出卖力气,勤勤恳恳工作,渴望新生活,但现实却一次次地将他们击倒,城市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待遇与尊重,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仿佛总也找不到出路。老一代农民在城市从事着体力劳动,为城市的发展奉献着汗水,但拖欠工资、暴力相向的事件屡见不鲜。农民“为了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必须如此羞辱、破坏、贬损自己的身体。否则,他得不到公正”[4]54,生存环境的恶劣、生存地位的卑微使得老一代农民不得不放弃自尊,而这正是新一代农民所不愿接受,甚至鄙夷的。新一代农民厌弃父辈们近乎于无赖的招数,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自乐、自轻自贱,他们顶撞父辈、不服管教。他们更清楚,一旦丢弃了厌恶的感受,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父辈们的现在就是他们未来的“宿命”,因此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对抗命运,但又鬼使神差般地掉入被同化的怪圈。
《出梁庄记》中的民中,在面对父辈们用肮脏、可耻、贫穷的手段,靠着作假、偷窃、吵架来赚钱时,他内心极度愤怒,愤怒父辈们的舍弃尊严、丧失自尊。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自己也写道,民中始终不愿正视作为研究者的“我”,仿佛是不愿以自身来印证某一种存在。民中不屑于父亲的生活模式,以霸气、高冷对待生活和世界。当梁鸿向他道别时,他冷漠、诡异地说:“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民中的回答令人惊讶,同时更令人难过,他或许是进城打工者中的“异类”“孤例”,他用自己的方式宣泄着内心对城市生活的不满,他渴望踏出一条出路,但又不知道路在何方。“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4]54民中有自己认识世界的角度,他不愿像父辈那样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他想活出个样子,但一切努力仿佛是徒劳的,他不得不妥协于父辈们的生存方式,接受同化,活成父亲的样子。这才是令人最心痛的。《出梁庄记》中的文哥亦如此,越想走入新的生活就越是被虚妄吞噬。梁鸿笔下的文哥是个高中生,有文化有知识,但却被传销组织骗进去了六次。文哥不是文盲,不是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但在他看来,深深地吸引他的是传销组织宣传的希望、平等、成功、价值和家的感觉。传销组织为文哥构建了一个富裕、高雅、平等,甚至比存活更高的价值空间与世界,而这些正是进城寻求新希望的他所需要的。像民中、文哥一样的年轻人渴求在城市找到新的生存空间,渴望获得事业的成功,但总是事与愿违。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着城市、谨慎地靠近城市,但城市于他们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梦,他们终将如他们的父辈一样,难逃宿命的安排。
在《木兰的城》中,作家以时空错位的叙述手法,讲述了两代人相同的命运。母亲姚水芹在木兰很小的时候进城打工,最终与父亲离婚,彻底离开了农村的家,木兰也彻底被母亲抛弃。儿时的记忆给木兰带来了巨大的伤痛,长大后木兰进城打工,认识了丈夫王小山,本已下定决心不再让悲剧重演的木兰,却在生下儿子小毛头后走上了与母亲相同的道路,离开了丈夫和儿子。在《木兰的城》中,作者没有刻意烘托宿命论,但读者却在涓涓流淌的文字中读到了一种悲哀,一种丈夫失去妻子、孩子失去母亲的悲哀。这不禁令人陷入沉思:时代的进步难道就没有给予新一代农民新的出路?急速扩张的城市难道只能一如既往地吞噬着他们的希望?同样,《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怀着改变命运的决心来到城市,机缘巧合地认识了事业有成的李羊群,过上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但他们彼此知之甚少。一次与李羊群朋友的聚会,面对李羊群和朋友之间的谈笑风生,明惠明白了她无法融入这个圈子,李羊群与自己中间有着永远无法打破的隔膜。在李羊群眼里,明惠只是他的“伙伴”,所有的体贴与温柔只是出于对弱者的怜悯与同情。而在明惠眼里,李羊群是她的爱人,是她融入这个城市的纽带。城市对明惠永远充满了吸引力,身份的差异却使她极端敏感自卑。当明惠看透了李羊群对自己的无爱,看清了难以融入城市的真相时,她极度失望,最终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邵丽以细腻的笔墨写出了城乡人之间,尤其是城市上层人士与底层乡村人们之间难以逾越的精神鸿沟,这恰恰是现代化进程中城乡问题中最值得思考的部分。
对新生活的追求是新一代农民内心渴望幸福的最真实的写照,所以他们宁愿在城市闲逛,也不愿回农村定居。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却是他们即使拼尽全力可能也无法跨越的存在。因此,在他们身上总萦绕着一种“宿命感”,这种“宿命感”又加深了他们命运的悲剧色彩。
四、结语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时代发展的步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相较于老一代农民,新一代农民的乡土记忆淡薄、人生阅历浅薄、自我期望较高,他们进城更具突破性与革命性,他们不像父辈一样安于现状,他们要成为城市的主人,扎根城市,成为“新移民”。在身份转换过程中,他们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他们或许要舍弃农民的淳朴,像《黄泥地》里的房光东一样;或许要舍弃农民的热情,像《生命册》里的吴志鹏一样;或许要舍弃他们自己,像《出梁庄记》里的秀中一样。在作家笔下,新一代农民别无他法、别无选择,因为得到城市的认同,扎根城市是他们这代人的使命,他们必须努力抗争走出一条新路。不然,他们还得妥协,如父辈们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对农民价值认同的关注表达了作家们对现实的深切忧虑,作家渴望为新一代农民找寻出路,但他们就像寻不到道路的探寻者,在这个过程中固然有悲伤、有绝望,但同时也看到希望。在寻找新的生存之路时,新一代农民充满苦痛和艰辛,但仍能看到背后的光明和希望,虽然一次次努力并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每一次尝试都是拼尽全力、有所收获的,这样也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在作家笔下,一个个丰满的农民形象,一次次勇敢的尝试,都浓缩着超越个人经验的肩负历史变革的民族记忆,作家们既是时代文化、时代精神的记录者,也是被动的承受者。在这个意义上,关注进城农民价值观念乡土书写的得与失,不仅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也为文学与社会学的交互考察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