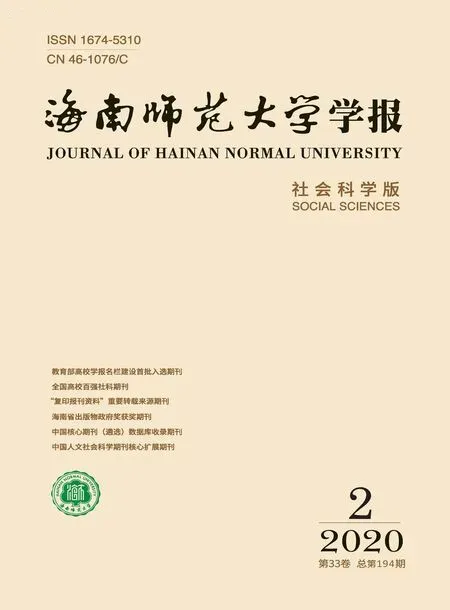苏过海南“志隐”论
阮 忠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苏过,是苏轼的第三个儿子,为苏轼的第二个妻子王闰之在宋神宗三年(1070)生于杭州,人称“小坡”。他陪同父亲到过黄州、惠州和儋州,在儋州侍父时,“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1)[元]脱脱等:《宋史·苏轼传·苏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818页。。苏轼病逝,他与哥哥苏迈、苏迨扶柩到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安葬,之后先是在颍昌(今河南许昌)闲居多年,后来做过太原监税、郾城知县等官,宣和五年(1123)病卒于颍昌,享年52。
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特别是苏轼诗文的巨大影响,遮蔽了苏过的文学光辉,使苏过的文学才能鲜为人知。他叔父苏辙说过:“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2)[元]脱脱等:《宋史·苏轼传·苏过传》,第10818页。这话不尽然,因为苏过在惠州时写的《飓风赋》《思子台赋》都是佳作,且当时还有诗歌传世。不过苏辙的话说明苏过在儋州侍父时,诗文更加成熟。
苏过元符元年(1098)在儋州写下的《志隐赋》(一作《志隐》)。二十年后,他在郾城清理书箧时偶见旧稿,于是写了一篇跋文,说明当时的写作情形。其中说:“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归。盖尝筑室,有终焉之志。遂赋《志隐》一篇,效昔人《解嘲》《宾戏》之类,将以混得丧、忘羁旅,非特以自广,且以为老人之娱。先君子览之,欣然嘉焉。”(3)舒星等:《苏过诗文编年笺注·志隐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 829页。苏过的《志隐赋》及其“志隐”问题,是本文所欲讨论的。
一、“志隐”的自嘲模式与传统接受
苏过说在儋州作《志隐赋》,“效昔人《解嘲》《宾戏》之类”。《解嘲》为西汉扬雄所著,《宾戏》即《答宾戏》,作者是东汉班固。这话稍说远一点,扬雄身为辞赋大家,在创作上最仰慕先于他的西汉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因作赋被授予郎官,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确立了汉代散体大赋的基本格局。扬雄在赋的创作上主要以司马相如为榜样,同时还效法西汉的东方朔。东方朔著《答客难》,开启了“答客体”的先河。其后,《解嘲》《宾戏》及东汉张衡的《应间》相继而生。东汉后,这一文体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唐韩愈作《进学解》影响深远,苏过作《志隐赋》也步“答客体”的后尘,自嘲。
东方朔在汉武帝时有“狂人”之名,自称避世深山中、蓬庐下,不如避世金马门,隐于朝廷中。曾有宫中儒学博士共难之,说战国的苏秦、张仪当万乘之主,居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为何你东方朔自以为海内无双,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东方朔说:苏秦、张仪时,诸侯力征,以决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苏秦、张仪得其用。今天下太平,贤与不贤无异,难以建立功业。如果他们在今天,只怕连侍郎也当不上。东方朔没有想到《答客难》成为辞赋的一种模式,自设问者发难,他则借此婉转地发牢骚,感慨怀才不遇。
扬雄承之,在《解嘲》里写道,“客嘲扬子”,人生一世当上尊人君,下荣父母,为高官享厚禄,你扬雄遇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不能出谋划策而高谈太玄,然官不过侍郎,提拔了也才是给事黄门,“何为官之拓落也”?扬雄笑言,“客欲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然后滔滔雄辩,诉说殷商以来的社会发展史,归结为“世乱则圣哲驰鹜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而他所处的汉成帝、汉哀帝时代,“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既然如此,他就乐于以《太玄》谈玄守道,安于平淡寂寞。随后又以范雎、蔡泽、张良、陈平等人为例,说人生当为于可为之时,不可为之时则不为。说自己比不了蔺相如、商山四皓、公孙弘、霍去病等人,只能独守《太玄》。
从东方朔《答客难》和扬雄《解嘲》,可以清楚看到“答客体”在西汉时最初的状态。不过,“答客体”的主客问答不是东方朔才有的。在他之前,西汉初年枚乘《七发》里“吴客”和“楚公子”的问答,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里“子虚先生”“乌有先生”“亡是公”的问答,可见秉承战国诸子、策士的论辩,以问答成文在东方朔时代蔚为风气,其后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都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苏过提到的班固《答宾戏》,以“宾”与“主人”设为问答;没有提到的张衡《应间》,以“宾”与“余”设为问答。相沿而下,韩愈《进学解》以“国子先生”与“诸生”设为问答;苏过《志隐赋》以“苏子”与“客”设为问答,各自以此构成文章的格局。
这一格局的基本套路是客嘲主,主则以自辩的方式解嘲,也就此形成新的自嘲。客的嘲主,通常认为“主”不进取或应更进取才是。而“主”的自辩则以自我批评委婉地批评社会,最终的落脚点不是从此进取,而是淡泊处世或干脆隐而不仕。如上述东方朔、扬雄的自辩。又如班固《答宾戏》“宾”戏主人身当帝王之世,“然而器不贾于当己,用不效于一世”,应当使计运策,“使存有显号,亡有美谥”。而主人说“宾”见势利而失道德,殊不知功不虚成,名不伪立,怎可处汉世而论战国,耀所闻而疑所睹呢?他以孔子、颜回为师表,表示安贫乐道即足,实际上说的是社会不明自己怀才不遇。张衡在《应间》序里首先就说明了,有人指责他五年没做史官却又回来再做史官,“非进取之势”。而张衡说“时有遇否,性命难求”,何况“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既然如此,何妨效法老子归隐,效法颜回安贫乐道,待价而沽。他还写过一篇《归田赋》,感慨自己无明略佐时而欲归隐,与世事长辞。于是,可见东方朔、扬雄、班固和张衡在自嘲自解中的情怀和立场。
有意味的是,苏过的《志隐赋》以“隐”为主题,比上述数子更为彰扬自己的人生取向。但他在表述上还是因袭了前人,开篇有“客”来海南慰问他,鼓励他进取,说“君子之修身也,病没世而无闻”。这话出自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面目自见于后世哉?”进而“客”说,“古人有言:岁云暮矣,时不我与。如子之年,鸣钟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于世乎?”而苏过回答道:“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枉寻者见容,方枘者必憎。”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固然是观史而见前人的教训,但他截然不同于前人的是,现实中父亲苏轼是榜样。且不谈功高名重,苏轼至少是“方枘者”,他曾说:“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以此尤不可与深中而多数者处。”(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密州通判厅题名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6页。而他正是因为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政见而遭遇了“乌台诗案”,开启了跌宕起伏的流贬人生;晚年北归,途中在《自题金山画像》里写下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却又是平淡之后的极度悲愤。苏过从父亲身上看到的严酷现实,以致说出这样苦涩的话,仍然有前人思维逻辑及语言表达的影子。
苏过《志隐赋》受前人自嘲模式的影响不限于此,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张衡的《应间》,都被归于汉赋中。枚乘在《七发》里说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正是汉赋写作的基本方法。后来传为司马相如的汉赋创作论,即讲究辞藻、铺陈、宫商起伏的“赋迹”说和“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心”说,意味着汉赋写作方法的成熟。但从《答客难》问世起,它就走了与《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不同的道路。这些新体赋用南朝梁代刘勰的话来说,多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诠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4页。,对山川草木的描述以致繁类成艳是不可少的。但《答客难》有战国策士骋辞的风貌,在纵横捭阖的论辩中,以富有气势的铺排表现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认知,理中含情。《志隐赋》“客”对苏过的劝进之辞:“天之生物,类聚群分。蠢动飞走,不相夺伦。鱼宅于渊,兽伏于榛。蚕之于冰,鼠之于焚。失其所则病,因其性则存。且非独虫鱼然也,楚之橘柚不植于燕代,晋之枣栗不繁于闽越。非天地之所私,繄物性之南北,况于人乎。”这番谈物性的话,看似与劝进不相关联,实际上“客”要表达的是,物各有性,性各有属,苏过本非海南人,性不属儋耳,理当离儋而去。去则宜求钟鸣鼎食,身入宦海,得官而传名。它们少了铺采摛文的缛美,却多了内心世界的自我揭示,有辨证法和理性的光彩。
不仅如此,苏过受“问答体”自嘲文的影响,当它离开以文“体物”的时候,把目光转向了历史人物及其生活。上述的东方朔赋里提到苏秦、张仪,扬雄赋里所提及的范雎、蔡泽、张良、陈平等人,班固的《答宾戏》提到鲁仲连、虞卿、商鞅、李斯、仲尼、孟轲等人,张衡的《应间》提到咎单、巫咸、申伯、樊仲、惠施、孟轲等人,而苏过在《志隐》里提到彭祖、老聃、介之推、鲁仲连、接舆、庄子等人。这些都增加了赋的历史厚重感,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追求历史的厚重感而为之,关键还是以历史人物为参照,审视“主人”的人生差距、得失及追求。如《宾戏》的“主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祸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乎。”商鞅佐秦孝公变法以强秦,孝公死后被秦惠王车裂;李斯助秦始皇得天下,始皇死后促成二公子胡亥篡位,后被赵高具五刑且腰斩于咸阳。班固说他们在风云际会中固然有一时的荣华,最终是福少祸多,这高官是可以做的吗?而苏过在《志隐赋》里说:“患难或可与共,安逸或可以长辞。子胥不免于属镂,范蠡得计于鸱夷。萧何缧囚于患失,留侯脱屣于先知。敌国亡而信烹,刘氏安而勃疑。”子胥即伍子胥,助越王勾践灭吴,功成后受人谗毁被赐剑自杀;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吴灭后归隐江湖,号鸱夷子皮,因经商致富,又称陶朱公;萧何为西汉开国名臣,曾因患失上林空地遭囚禁;留侯张良,亦佐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功成后求封于留,隐居自全;勃即周勃,刘邦重臣,为刘氏诛诸吕,刘氏安定天下后曾因谗下狱。这些相当复杂的人及其故事,虽被苏过效仿前人作了简洁的表述,但其用典、铺排的创作风格依然是对前人赋的继承。
总之,苏过《志隐赋》在自嘲的模式上受前人的影响甚深,他对传统的接受让《志隐赋》的创作在形式上没有新意。不过,它毕竟不同于上述作品,主要在于苏过的创作动因和趣尚。
二、“志隐”的娱父情结与岛夷之安
苏过在《志隐赋》里说,他之所以写这篇赋,“将以混得丧、忘羁旅,非特以自广,且以为老人之娱”。这里有两层意思,其“自广”暂且不论,先说“且以为老人之娱”。
班固在《答宾戏》的结尾说,他不能与耳聪的师旷、目明的离娄、善射的逄蒙、能工的班输等人同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静静地为文“自娱”。这“自娱”说有点意味。且不说先秦诗文的娱乐性,西汉枚乘的庶子枚皋在父亲死后受汉武帝征召作赋,武帝有所感辄令赋之。枚皋文思敏捷,受诏辄成,共写了两百多篇作品。但他晚年回顾人生,说自己 “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6)[汉]班固:《汉书·枚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 2367页。。所谓“俳”为“俳优”,“倡”为“倡优”,皆指以歌舞为业的艺人。类似的话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也说过。后来,辞赋家扬雄说:他少而好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7)汪荣宝:《法言义疏·吾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而好辞赋的汉武帝,正是以辞赋为娱乐,难怪司马相如写《大人赋》,意欲奉劝汉武帝不要求仙,但汉武帝读后,居然有飘然若仙之意。因此,班固说出为文自娱的话,也符合这些辞赋的创作实情。客观地说,这些自嘲文都具娱乐性,以自我和社会现实的调侃稀释内心因怀才不遇产生的忧郁之情。他们都是针对自我的,苏过也为自我,但他同时说也为了父亲,让父亲能够享有阅读的愉悦,这就不同于前人。
苏轼贬儋州,是很意外的事。因为他在惠州时,自以为是人生最后的驿站,所以在惠州的白鹤山建了新居,并让长子苏迈等儿孙来惠州生活。当他获旨任琼州别驾、着儋州安置时,顿时心有死志,说到了海南,先当作棺,后当作墓,人生没有归途。他到儋州后上书宋哲宗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8)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到昌化军谢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7页。悲怆之下,所幸有小儿苏过相随。
从苏过现存的诗文看,他在惠州时有诗与父亲唱和或纪行,如苏轼有《和陶游斜川》,苏过则作《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苏轼作《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苏过则作《和大人游罗浮山》;苏轼游罗浮道院棲禅山寺,苏过写了《正月二十四日侍亲游罗浮道院棲禅山寺》。苏轼在儋州,最早提到儿子苏过是在《与杨济甫》的信中。杨济甫亦是眉州眉山人,和苏轼是同乡和朋友。他说“某与幼子过南来,余皆留惠州。”这“余皆留惠州”中,就有苏过的妻子和儿女。苏过陪侍父亲到海南,此一去与妻儿离别也是三年。
苏轼在儋州,生活艰苦,希望北归。他曾对程儒秀才说,在儋州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9)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程秀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8页。他一连用了八个“无”字,说明生活的困境。后来因为有绝粮之忧,甚至想到和苏过一起练“龟息法”度日。虽说苏轼料定自己必死海南无疑,但他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北归中原。他从琼州前往儋州路过儋耳山时,登上儋耳山放眼远眺,写下了“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10)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行琼儋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47页。,对以后的人生是很失望,以致有时难免感慨“久逃空谷,日就灰槁”(1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与张逢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66页。
不过,生活艰苦、希望北归的忧思先后被他化解。前者,当他筑室而有所居之后,渐渐适应了在儋州的生活,与黎民百姓浑然一家,最后说出 “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12)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别海南黎民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3页。,人生的困境不复存在。后者,他以陶渊明为友,遍和陶渊明诗,还在《和陶归去来兮辞》里,“均海南与海北”,且“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1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自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66页。,心态平和。不仅如此,他受邹衍、庄子的影响,认为天地都在积水中,海南在大海中,九州不也在大海中吗?既然如此,身在海南也犹若九州。等有一天水干涸了,到处都会是四通八达的道路。于是北归之际不再说三年之苦,而说“兹游奇绝冠平生”(14)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6页。。
但苏轼曾因苏过的陪侍,引发内心的不安。他有这样的文字说明当时的心情:一是在《与郑靖老书》中说:“闻过房下病卧,正月尚未得耗,亦忧之。”郑靖老即友人郑嘉惠,苏轼在海南与他有多封书信来往。当时从惠州传来消息,说苏过的妻子病了,这时苏轼挂念她,不知她是否痊愈,忧虑不安。二是他读了苏过写的《志隐赋》后,“欣然嘉焉”。与苏过同时的晁说之说:苏过“其初至海上也,为文一篇曰《志隐》,效于先生前。先生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15)舒星等:《苏过诗文编年笺注·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50页。这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苏轼在儋州因儿子苏过的陪侍不安,因为苏过本可不随他在流贬地生活。而苏过说自己之所以写《志隐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且以为老人之娱”。
苏过的儋州娱父,使父亲享有居岛夷之安,这在饮食、读书和作文三方面有所体现。
苏轼是美食家,在黄州时用温火燉肉、焖鱼都是美谈。他在儋州食蚝与一般人不同,一是取其小者,将蚝肉与浆入水,加酒煮食,味道鲜美。二是取其大者在火上烤食,好吃的苏轼调侃、告诫苏过不要对外人说,以免北方君子 “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1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食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2592页。。他在儋州还写过一篇《老饕赋》,以老饕自比,尽叙儋州的饮食之美。而苏过曾出奇想,用山芋作了玉糁羹,色香味奇绝。东坡吃后称赞它是人间没有的美味,高兴地写了七绝《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说:“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再就是读书。苏轼一生与书相伴,来海南诸多不便,只带了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后来向惠州郑嘉惠借书多达千余卷,欣喜之余在《和陶赠羊长史并引》里说郑嘉会 “欲令海外士,观经似鸿都”。鸿都,是东汉皇家的藏书处。还在诗中自喻为老马思服舆,说自己放不下的就是读书。苏过则说“海南寡书籍,蠹简仅编缀。《诗》亡不见《雅》,《易》绝空余《系》”(17)舒星等:《苏过诗文编年笺注·借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29页。,于是借书来读,以免寸阴流逝,没世无闻。还有苏轼曾听苏过诵书“声节闲美”,感慨“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18)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和陶郭主簿二首其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51页。于是想到当年父母也喜欢他的读书声。苏轼还很高兴苏过以抄书的方式来读书。他在儋州的《与程秀才书》中说:“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老拙,一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乐以此告壮者尔。”“穷儿暴富”是很形象的比方,苏过所为契合了他心中所愿,这时倒不是苏过有意识以自己读书取悦于老父。
关于苏过作文,苏轼曾在《与刘沔都漕书》里说:“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这里的“刳形去智”,源于庄子的“离形去知”说,不合时宜的苏轼达不到庄子这样的境界,但他说的“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 倒是苏过以文娱父的很好说明。
苏轼在惠州时就说苏过的诗文写得好,有《游罗游山一首示儿子过》为证。诗中说:“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黄庭》即道教的《黄庭经》,《离骚经》则是战国屈原所作的《离骚》。苏轼诗中说的“凌云赋”指的是苏过所作《飓风赋》,这篇赋长于想象,天上地下,纵横驰骋,笔势真有《离骚》的风采。在儋州,苏轼说小儿苏过时出一篇以为娱,这就不限于《志隐赋》,还包括了苏过的其他诗文创作。这些诗文在他看来也是写得很好的,故以金玉珠贝喻之。
苏过曾寄椰子冠给雷州的叔父苏辙,苏辙写了一首《过侄寄椰冠》,同时还写了《寓居二首》即“东亭”和“东楼”,于是有了苏轼的《次韵子由三首》“东亭”“东楼”和“椰子冠”。苏过和了“椰子冠”和“东亭”。苏辙写了《浴罢》,苏轼有《次韵子由浴罢》,苏过则唱和了《次韵叔父浴罢》。如是唱和,虽然可见亲情交往,但为的是娱人自娱。这类似于中唐元白诗人、北宋西昆体诗人的酬唱,很有游戏作乐之意。还有,苏轼写了《五色雀》,苏过则写了《五色雀和大人韵》。苏过还在苏轼生日时,以诗为父亲贺寿。儋州三年,于是有《大人生日》诗五首(第二年贺寿同题三首),它们的娱情味道甚浓。如他第一年写的《大人生日》,首联说“勿惊髀减带围宽,寿骨巉然正隐颧”。苏轼刚到海南时,听说苏辙瘦了,于是写了诗《闻子由瘦》,说你瘦了我也瘦了,改日重逢,“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苏过说,不要吃惊瘦了,衣带松了,颧骨虽平但寿骨(额骨)高呢。这样的贺寿语,满是戏谑。所以苏过的《志隐赋》“且以为老人之娱”,一点都不奇怪。
苏过娱父之际,自然也少不了对父亲的安慰。在惠州时就是如此,如《和大人游罗浮山》中的“谪官罗浮定天意,不涉忧患那长生”,说人生有忧患可以换取生命的长久,希望父亲不在意贬谪。他在儋州为父亲贺岁时也是如此。如《大人生日三首》其二里写道:“天定人难胜,诚哉申子言。不须占倚伏,久已恃乾坤。” 春秋时晋太子申生遭晋献公宠妃骊姬陷害被迫自杀,死前说天定人胜难,将自己的死归于天意。苏过借此说父亲被贬也是天意而不是人力所为。所谓“倚伏”用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名言,代指祸福。苏过的意思是父亲在儋州没必要探究是祸还是福,时间长了,天地可以证明您的忠心和功德。并以“勿叹乘桴远,当知出世尊”化用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劝父亲贬居海外只当是远离尘俗,可享出世的高贵。
话说回来,苏轼读了苏过的《志隐赋》心下高兴,在海南原本因苏过陪侍带来的不安,现在不再有了。这是因为苏过的娱父情结有赖于思想情趣的流露,让苏轼完全释怀而享受“岛夷之安”。那么,苏过怀有怎样的思想情趣、又怎样在表达呢?
三、“志隐”的物性自然与遐荒养生
上述谈到《志隐赋》铺排的时候,引用过“客”对苏过的劝进之辞“天之生物,类聚群分”一节。这节说明物各有性、性各有所属,接着“客”说自己是蜀人,少游三晋,三晋之地环境太坏,恶水肆流,野兽横行,百姓多病。他作了这样的铺垫之后,再说儋州在广东、广西之南,生活习俗和语言都和内地不同,加之“海气郁雺,瘴烟溟濛。而子安之,岂亦有道乎” ?随之“客”列举了战国时虞卿、娄敬、苏秦、范雎、蔺相如、毛遂等人的例子,说他们“或刀笔以自奋,或干戈以策勋,脱颖者富贵,陆沉者贱贫,希揄扬于鼎彝,耻湮没于埃尘。” 他借此表明的是儋州环境艰苦,不适合你苏过生活;前人多有作为,你苏过也当如此,不能没世无闻。
“客”的这番话在“问答体”的自嘲赋中,是苏过自我的设问,设问中通常有夸张,言过其实,意在使苏过在解嘲时有明确的靶向,能够针锋相对辩驳以表达自己的襟怀。苏过接过“客”的问话,然后说道:
大块之间,有生同之。喜怒哀乐,巨细不遗,蚁蜂之君臣,蛮触之雄雌。 以我观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为朝暮,蟪蛄以春秋为期颐。孰寿孰夭?孰欣孰悲?况吾与子,好恶性习,一致同归。寓此世间,美恶几希。乃欲夸三晋而陋百粤,弃远俗而鄙岛夷。窃为子不取也。
这番话表明了苏过现实人生的理念,他用庄子万物齐同的思想为自己辩解,说人生天地之间,喜怒哀乐、大小巨细,没什么差异。“蚁蜂之君臣”用唐李公佐传奇《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棼的故事。淳于棼南柯一梦,梦中的槐安国君臣,不过是大蚁小蚁而已。“蛮触之雄雌”用《庄子·则阳》触蛮之争的故事,庄子这则寓言的本意是讽刺好战的诸侯,说他们无论战胜战败都是渺小的。苏过讲这两个故事,是说为君为臣,或胜或败,是差不多的。他随后说到彭聃即彭祖、老聃和蟪蛄,老聃即老子李耳,辞了周王朝的守藏史之后,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他这里把老聃作为长寿者。而彭祖和蟪蛄都见于《庄子·逍遥游》。相传彭祖活了八百岁,而庄子笔下的蟪蛄不知春秋,连一年的寿命也没有。苏过借此说彭祖、老聃以寒暑为朝暮,称其寿命很长;蟪蛄以春秋为期颐即百年,言其寿命之短。但他们到底是谁寿长,谁寿短呢?到底谁高兴,谁伤悲呢?这用了庄子的相对论。庄子曾说秋毫之末大而泰山小,彭祖的寿命短而一生下来就死去的婴儿寿命长;曾说人们认为毛嫱、西施是绝世佳人,但鸟见之高飞,鱼见之深潜,事物都是相对的。寿命的长短、人生的悲喜,有什么差异呢?再说,我你同在人世间,好恶性习是一致的,几乎没有好坏的区别。既然如此,三晋与百粤、远俗与岛夷不是一样的吗?
随之,苏过说物性自然。他的这番话同样很有意味:
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知兽之安于薮也,而兽何择于云梦之与孟渚?松柏之后凋,萑苇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岂土地之能殊?子乃以晋楚之产疑之,过矣。
苏过这里表达的鱼安于水、兽安于薮的观念,也本于庄子。《庄子·达生》虚构了孔子观于吕梁的故事,借一善游的男人表达了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的思想,认为这是人或物的自然之性。庄子受老子影响,从道的自然出发,延伸到物的自然,于是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哲学。客观地说,环境对事物的影响是存在的,苏过避开这一点而强调鱼安于水,哪儿的水不重要,河汉与江湖没差别;兽安于草泽,哪儿的草泽也不重要,云梦与孟渚没差别。进而他又说,松柏、萑苇,因物性不同,前者后凋,后者易枯,不是它们生长的土地不同造成的。言下之意,他这个蜀人,现在生活在儋耳,与生活在蜀州之眉山是一样的,不用质疑。
从这些来看,苏过思想受庄子的影响很深。他用庄子万物齐同、物性自然的思想解释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不复有生活的艰难,正是他的“自广”之术。所以,他眼中的儋州,完全不同于“客”眼中的儋州。“客”说儋州艰苦,但苏过说儋州美好,美得像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样:
天地之气,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岁再熟。富者寡求,贫者易足。绩蕊为衣,蓺根为粮。铸山煮海,国以富强。犀象珠玉,走于四方。士独免于战争,民独勉于农桑。其山川则清远而秀绝,陵谷则缥缈而岪郁,虽龙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吾盖乐游而忘返,岂特暖席之与黔突也哉!
苏过告诉人们,儋州因天地眷顾,冬夏天气温度一样,万物生生不息,不见凋零,且冬夏人们穿著一样,稻谷一年两熟。这些的确是“富者寡求,贫者易足”,物产的丰饶与心理上的满足同在。而他的“铸山煮海”、“犀象珠玉”说,用的吴越故事。西汉刘濞为吴王时,曾招人开放铜矿铸钱,煮海水制盐,以求富裕。苏轼也曾说过一句:“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19)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表忠观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9页。当时的儋州还不是如此,苏过夸张的描述,有意彰显了儋州人据山海的富足生活。况且这里没有战争的灾难,百姓努力从事耕织,山川秀丽,山谷幽深,白云飘忽,草木葱茏,犹神仙居所。他笔下的“岂特暖席之与黔突也哉”出自“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2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修务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33页。,说的是孔子没有熏黑的烟囱、墨子的坐席从不温暖,二人汲汲行道于世,在一地不作久留。而苏过表白自己“乐游而忘返”,是甘愿长期生活在海南的。
苏过说,入世者想的是人生富贵和传名不朽,那“纡朱怀金,肥马轻车”不是独善其身、老死丘壑的人可以比拟。但这些人没想到求功名的悲剧,“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这话前人也说过,他重作表述,并列举了历史上一些人物的命运和做法。他提到的这些人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功成亡身者,如伍子胥、韩信;二是功成身退者,如范蠡、张良;三是不好功业的隐者,如接舆、庄子。面对这三种人,苏过表示自己没有过人的才能,不能“自媒”即自我推荐求得一官半职;想到马和猎鹰受人羁绊,会觉得不寒而慄。而良马本可长鸣于冀北,见“皂栈”即马槽马栈而害怕的说法,源于《庄子·马蹄》。庄子曾批评伯乐治马,对马烧、剔、刻、烙,把马编排固定在皂栈里,结果马死去十分之二三。这能不让人害怕吗?苏过说不能自媒,是委婉批评无人引荐他;马、鹰所受的羁绊,正是身入宦海即不自由,为五斗米折腰且性命难保。所以,他说高官是不能做的,何况还有功高身危、名重谤生的事情发生呢?
所以,苏过说身在海南,最要做的不是求取功名,而是遐荒养生。于是,他最后说:“尝闻养生之粗也,今置身于遐荒,殆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寥,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于渺茫,想神仙于有无,此天下之至乐也。”所谓“物之初”一说见于《庄子·田子方》,庄子曾借老聃的口说“吾游心于物之初”,当是游于事物的原始状态;而今苏过在这遐荒之地,犹若是物之初时,是庄子逍遥游时的“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2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逍遥游》,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页。。而“逃空谷之寂寥”语出《庄子·徐无鬼》,庄子原本说在空谷中往往闻人足音而喜,但苏过说自己乐于这虚空寂寥,而与尘世更加疏远。这里,他想到仙人赤松子,自己也有成仙之念却又以“渺茫”“有无”质疑神仙的存在,最终所具的只有顺应自然。他称这为人生“至乐”,而“至乐”说出自《庄子·至乐》,它以人生的富贵寿善为至劳至愚,而以无为自然为至乐。苏过身居海南儋州这原始的荒远之地(不觉与他夸海南之美相矛盾),正可以享受绝对自由的快乐。
苏过对“客”的反驳最后落脚在:你希望我贪图名利,但这玷污了我,是很愚蠢的事。从而把自己与世俗的追名逐利完全割裂开了,彰显他有志于隐而不愿为官。他在《志隐跋》里揭示过为自己的创作用心,称之为“混得丧、忘羁旅”,欲以自广,这也是自广的根本所在。
从上述来看,苏过的《志隐赋》长于用典,除了历史故事之外,主要是用《庄子》之典演绎庄子思想,他内心如是引发了苏轼的共鸣,苏轼甚至有写一篇《广志隐》的想法。
苏轼受儒佛道的影响很深,入世与出世相兼。但他最爱的是《庄子》,曾喟然长叹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22)[元]脱脱等:《宋史·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801页。所以,他很多诗文化用庄子的典故,有庄子式的旷达。如他在儋州因苏过画的枯木竹石写了《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其二写道:“散木支离得自全,交柯蚴蟉欲纠缠。不须更说能鸣雁,要以空中得尽年。”在这里,苏轼用庄子的故事对苏过画的枯木作了解读。其“散木”是《庄子·人间世》里无用于社会,有用于自我生存的无用大树。因为“散木”“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23)[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人间世》,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71页。“支离”出自《庄子·人间世》,是庄子虚构的人物支离疏——一个严重畸形、无用于社会而能尽享天年的人。而“鸣雁”说见于《庄子·山木》:能鸣之雁遭烹杀,不能鸣之雁得保全。苏轼以散木、支离疏转述了无用即是有用的庄子思想,说雁能鸣而死,有用是不好的。而枯木“空中”即没了树心,方得尽天年。这委婉表现出的“无心”也是庄子的重要理念,他讲“心斋”“坐忘”“丧我”,都是修为以求无欲、无心。所有这些,可见苏轼与苏过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苏过说他写《志隐赋》要“混得丧”,而苏轼在流贬儋州时,何尝不是在“混得丧”呢?他在元符二年(1099)和儋州数位老书生游上元夜,归来已是三更,忽放杖而笑,“孰为得失”(2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书上元夜游》,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5页。,流贬之失何尝不是人生之得。
苏过无心官场在很多时候都有表现,他在《正月二十四日侍亲游罗浮道院棲禅山寺》中流露出“人生行乐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怀故乡,吾驾随所税”的情绪。这“税”说的“税驾”即解驾休息,何处不是故乡,何地不能休息呢?
在《椰子冠》里说的“平生冠冕非吾意,不为飞鸢跕堕时”,官可以不做,以免有失官的悲剧。苏过一生不热衷做官,在儋州“盖尝筑室,有终焉之志”;晚年定居颍昌,在颍昌湖的北面种了几亩水竹,过着陶渊明式的悠然生活。并因陶渊明的斜川而写了《小斜川》一首,吟着“胸中粗已了,浩荡欲没鸥。渊明我同生,共尽当一丘”,表白要像陶渊明一样隐居,且自号为“斜川居士”。
苏过与父亲苏轼在尚庄好陶上有一样的志趣,并从庄子的物性自然走向陶渊明的淡泊静穆。而他的《志隐赋》突显出尚庄的一面,希求庄子式遐荒养生的生活,让苏轼受到极大的安慰,他想到苏过心性如此,故说出自己可以安于岛夷的话来。而苏过说写《志隐赋》既是娱父,也是自我安慰。他安于海南,把儋州作为顺适自然的养生地,不以苦为苦。在这一点上,他的人生意趣与东方朔、扬雄、班固、张衡等人大有不同,他是真正的“志隐”践行者,尽管在创作模式上《志隐赋》走了前人的老路。难怪苏轼在儋州《与侄孙元老书》中说自己和儿子苏过家中相对,像两个苦行僧,“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