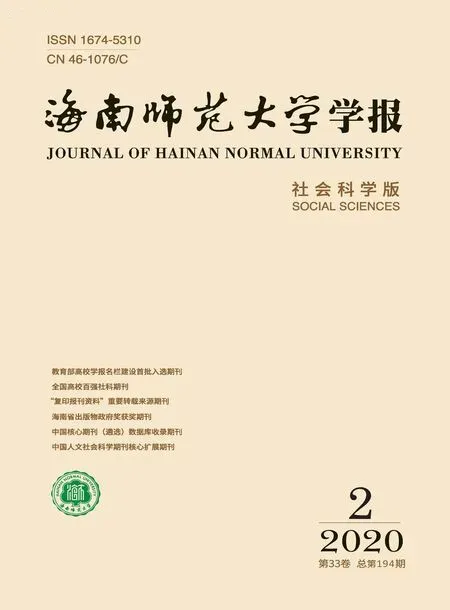边缘作者:汪曾祺与20世纪40年代后期文坛
——以《绿猫》为中心
张晓晴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绿猫》(1)根据文末标识,《绿猫》写于1947年7月2日的上海,初刊于《文艺春秋》1947年第五卷第二期,收入《汪曾祺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19-235页。以下所引《绿猫》的小说内容皆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是汪曾祺早年形态各异的创作中颇为独特的一篇。这篇被归为“小说”类别的作品在作者而言却“有意识不把它当作一个小说写”,大段的议论与抒情、对话与独白、引文与互文不断打乱故事节奏,连同“绿猫”这个标题本身就预示了一种曲折幽微的阅读感受。(2)汪曾祺晚年回忆,“这是一篇很怪的小说。即使在当时看起来,人们都觉得这个小说太怪了。”参见汪曾祺、杨鼎川:《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汪曾祺访谈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相应地,长期以来,这篇作品在汪曾祺研究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20世纪90年代,杨鼎川曾对包括《绿猫》在内的所谓“空灵的一路”小说作了评述,注意到作家精神世界与文本的同构性;但这种探索并未继续下去,而将作品主题归结为抗战后身处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无奈感与荒谬感”(3)杨鼎川:《汪曾祺40年代两种不同调子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需要指出的是,杨鼎川的结论在相当程度上是汪曾祺的晚年自言的重复:“(《绿猫》)应该是写当代知识分子有点茫然的情绪,找不到生活的道路,同时用一种调侃态度对人,有点玩世不恭。”事实上,汪曾祺此时已不记得《绿猫》的情节,只留存一点模糊的印象,故这种追认值得商榷。;近年来则有论者从文献学释读的角度注意到《绿猫》与汪曾祺早年众多作品的互文关系,将之视为“帮助我们解读迄今还不能确知的汪曾祺早期作品的一把锁匙。”(4)裴春芳:《雅致的恣肆与生命的沉酣——汪曾祺早期佚文校读札记》,《上海文学》2014年第8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都认为《绿猫》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我”与“栢”皆为隐含作者汪曾祺的不同分身,肯定其叙述策略和明确的现代小说家意识的同时,亦指出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所带来的阅读阻力。由此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暂且放下评判《绿猫》文体试验的得失,转而探索这种独特叙述策略背后的写作动力。本文认为,《绿猫》不仅是一个前途无着的知识分子“寂寞和苦闷”的产物,也是青年汪曾祺对自己多年来执着的“文学与人生”主题的一次报告,是他彼时创作观念与生命价值同构理想的一次倾吐。此外,《绿猫》还寄寓了汪曾祺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复杂文学生态的思考,隐藏着身处边缘的写作者在说与不说、写与不写以及如何写之间的焦虑和努力。
一、《绿猫》背后的“文学与人生”
《绿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深夜两点一刻,“我”在缺乏灵感与汽车嘈杂声中自我诘问,由高尔基想到了朋友“栢”正在写的小说《绿猫》。第二部分详写“我”在一个梅雨天去看栢的经历。主线是“我”与栢围绕绿猫、师长近况、创作观念的独白和对话,显示了二人惺惺相惜的情谊。同时,叙述视角又不时在栢的童年、大学与如今境况间来回切换,并一再插入栢的文章断片,使这部分故事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意味。在第三部分,“我”从记忆中回过神来,重新陷入种种噪音以及关于高尔基的思考,并为《绿猫》续写了一个《月亮和六便士》式的结局,发现天已放晴。
在整体结构上,第一、第三部分是“我”的意识片段的实时记录,思绪全然敞开,有较明确的时间所指:夜里“两点一刻”到天亮(“隔壁那个老头子咳了整整一夜”)(第235页)。第二部分则插入“我”同栢的一次会面的回忆。但是,“怎么样就从我的住处到了栢的住处了呢?说不上来,我就是已经到了栢的门前,伸手而敲了”(第220页),这部分对二人的对话、神态、氛围的描写之细致已然超越了回忆情境的可能,而更近似于现场实录。作者由此暗示,此番会面实际上就发生在“我”的头脑内部,“我”分身为二,经过对话与独白、理解与困惑、劝导与包容,与自己灵魂的另一面互相慰安,在虚拟的时空中获得了短暂的宁静。而将整个文本统一起来的,是“我”与栢共同面对的“写不出来”的焦灼感。作者所设置的“叙述圈套”与文体形式上的努力,显然是在力图传达一种超越故事本身的东西,为自己内心的隐秘寻找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
解读《绿猫》,必须与汪曾祺这一时期的生活、写作状态相联系。1946年8月,西南联大肄业生汪曾祺自昆明经越南海防、香港,到镇江与七年未见的家人短暂团聚后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年轻的汪曾祺对于前途并没有多少清晰的认识:“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甚么呢?”(5)汪曾祺:《牙疼》,《汪曾祺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55页。尽管此前他已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诸多作品,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认可,途经香港时还偶然发现当地一家小报上刊载了自己的“通告”:“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港”;而现实是这位“青年作家”正寄居在一家下等旅馆里,买了船票后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难怪他看到那条消息时的第一反应是骂了一句:“他妈的!”(6)汪朗,汪明,汪朝:《老头汪曾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汪曾祺初到上海时的遭遇常为研究者所注意。如他曾经历了一段相当穷困的无业状态,睡在同学朱德熙母亲家的门厅过道中,精神颓废消沉到一度有过自杀的打算;尤其是沈从文那封据说将他“大骂一顿”的信,作为师生间深厚情谊的见证被后来的汪曾祺及其研究者们津津乐道。在这封信中,沈从文一改往日的温和训斥道:“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同时又“说了一些他刚到北京时的情形”(7)汪曾祺:《星斗其人,赤子其人》,《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18-119页。加以鼓励。有论者指出,沈从文的“勉励后进”中暗含着一种基于自身经验的“个人奋斗”意识,即把个人前程寄于“一支笔”,藉以安顿自我、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8)张千可:《“旧上海”与“新时期”——在“小生产者”视角下重读汪曾祺》,尤其是注释(13),《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诚然,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文坛与沈从文闯荡北京的20世纪20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沈从文的鼓励在今天看来也许缺乏“对政治气氛的嗅觉”,但客观来讲,这种劝导对彼时的汪曾祺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与他内心的文学认同不谋而合。我们可以在后者1946年初到上海所写的散文《昆明草木·百合的遗像》中略窥这位年轻作者的心理。这是一篇有关理想凋落的诗意寓言:“走了那么多路,甚么都不为的贸然来到这个大地方,我所得的是甚么,操持的是甚么,凋落的,抛去的可就多了”;但他同时也很明确:“我不能完全离开这朵百合”。(9)汪曾祺:《昆明草木》,《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50页。其实,对于“百合”(理想)的书写行为本身就是汪曾祺试图“对付”以“呜呜拉拉焦急的汽车”和“吱吱吜吜不安的无线电”为代表的都市凡俗生活的努力。另一方面,在不少回忆文章中,汪曾祺任教于私立致远中学的情形(1946年9月至1948年初)被叙述得不乏精彩和温情:“汪先生讲课很特别,他很少按照课本的内容讲。而是给我们讲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何其芳、巴金、鲁迅……等许许多多作家作品……(略)汪先生讲课非常引人入胜,所以很少有不安静的情况发生”,尤其是作文课,“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10)张希至:《我的初中老师——汪曾祺》,段春娟编:《你好,汪曾祺!》,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229-230页。但据沈从文致友人托代汪曾祺谋职的信件可知,汪曾祺的这段教书生涯并不遂意(11)沈从文:《复李霖灿、李晨岚》,《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65页。;在他同期的信件中,也不时流露出一种因理想同现实之落差而生出的“委屈之感”:“我得尽量抑压不谈到自己……我久已知道自己的稚弱、残碎,我甚至觉得现在我所得到的看待还不是我应得的。”(12)汪曾祺:《致沈从文(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33页。相对来说,1947年发表的散文《幡与旌》提供了许多更为鲜活可感的细节,从中可以一窥汪曾祺彼时的实际心境。
《幡与旌》开篇即说:“我教书,教国文,我有时极为痛苦。”偶尔讲到得意处时,“我思想活泼,嗓音也清亮”,但讲台下全数木然的学生们令他顿生绝望:“我看到的是些为生活销蚀模糊的老脸,不是十来岁的孩子!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整个的社会。我的脚下的地突然陷下去了!”但“我”仍不甘心,努力在学生的作文中发现“一点火星”,为之欢喜得不能自禁:“这是一种嘲笑,使我的孤独愈益深厚。但一有一片小小的光,我的欢喜仍是完满的,长新的。”(13)汪曾祺:《幡与旌》,《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64页。整篇文章叙述的就是“我”这种竭力传达文学之美而又得不到回应、无处可逃的精神困境;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一次拔牙经历中,汪曾祺试图同一位表面不俗的年轻牙医谈论纪德的《地粮》和上海生活的寂寞,对方却以职业性地“检查牙齿”与24万的预算账单将汪曾祺这种浪漫想法瞬间打破。(14)汪曾祺:《牙疼》,《汪曾祺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56-257页。此篇虽被归入小说类别,却多为实录。不难看出,审美化的文学理想已经成为汪曾祺感知、理解世界的方式,化入到了他的生命中,却常常与现实生活发生错位。在《绿猫》的第二部分,隐含作者化身的栢如此谈及自己的文学观念。
为甚么写?为甚么读?最大理由还是要写,要读。可以得到一种“快乐”,——你知道我所谓快乐即指一切比较精美,纯粹,高度的情绪。瑞恰兹叫它“最丰富的生活”。你不是写过:写的时候要沉酣?我以为就是那样的意思。我自己的经验,只有在读在写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活得比较有价值,像回事。(第230页)
在此,文学阅读与写作被视为“快乐”的源泉,表现为一种“沉酣”的状态,意味着“一种对内在生命的极致状态的感知,一种对艺术的极致之道的体念”(15)裴春芳:《雅致的恣肆与生命的沉酣——汪曾祺早期佚文校读札记》,《上海文学》2014年第8期。,被提升到了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的高度。实际上,“生命的沉酣”构成了汪曾祺早期不少作品的核心情绪,并作为人物的内在精神为作者所激赏;像《艺术家》中有关哑巴画家创作“至矣尽矣”的杰作的想象,《鸡鸭名家》中对民间匠人余老五“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的“炕鸡”过程的描写,一直延伸到1950年岁末对黄永玉画所作的评论:“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的精力充沛的笔墨中融成一气,流写而出,造成了不可及的生动的新鲜的,强烈的效果。”(16)汪曾祺:《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98页。如范智红所言:“在汪曾祺那些平和宁静的人物稳定的神色下跃动着的,其实是一种极为执着的而且有着内在的痴狂的人格。”(17)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而这种“生命的沉酣”“内在的痴狂”正源于汪曾祺自己对于文学阅读及写作的切身体验。正是这种对文学之现实超越力量的确信,使得《绿猫》中的栢尽管备受嘲讽不解,仍坚持要把“那篇了不起的大作”——“文学与人生”完成。
二、“边缘作者”与青年汪曾祺的文学理念
毫无疑问,文学已经成为青年汪曾祺建构主体自我意识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形塑力量。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文学作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行为在遭遇现实时潜在的冲突:“文学阅读行为既有利于和社会融为一体,又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它临时切断了读者个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但又使读者与作品中的宇宙建立起新的关系。所以,阅读的动机不外乎是读者对社会环境的不满足,或是两者之间的不平衡”(18)[法]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于沛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页。;同样,写作亦是如此。所以,尽管来到战后再度复兴的文化中心,汪曾祺对上海的都市风景及文化氛围皆观感不佳,而宁愿侧身一隅、静心写作。《绿猫》中就写到喜好独处、不善交往酬酢的“我”与栢都面对整日喧闹的同事邻居不胜其苦。在1983年创作和发表的小说《星期天》中,汪曾祺亦这样回忆自己当年于“随帮唱影”的日常教学、交游之外的独居生活。
在教学楼对面的铁皮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19)汪曾祺:《星期天》,《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356页。
这座铁皮木棚就是汪曾祺在上海前后一年半间的主要居所,他于此完成了相当数量的小说、散文,仅1947年5月和6月,据说就写了十二万字,甚至还学着画类似康定斯基的抽象画。这间阴湿晦暗的小屋也有了一个相当雅致的名字——“听水斋”——常常出现在他当时的作品中,只是大多呈现为一种消极的形象:“我半年没见过好好的太阳,我那间屋子整天都是黄昏”(《牙疼》);“时方近午,小室之中已经暮气沉沉”(《昆明草木》)。《绿猫》中栢“写不出来”的原因之一,即是“杂,乱,多,不统一,不调和”的居室条件:“这间屋子真暗,真湿,真霉,真——唉,臭!……栢的眼睛落在一本书上:佛尼金·吴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他表情极其幽默。(第229页)”置身于这样的恶劣空间中,无人交谈、无事可忙,文学写作的欲求却始终未熄,“写不出来却偏要写一点”(《昆明草木》)。汪曾祺在此呈现出的形象,令我们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沪上那一个个“亭子间”里兀自写作的“文学青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疏离外界、专注于内心的写作者,正属于柄谷行人所说的“现代文学”制度“生产”出来的孤独的写作主体,即“现代的自我”、一个背对外界的“内在的人”(inner man)。(20)[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学者姜涛曾辨析了20世纪20年代文学中的一个常见形象——“室内的作者”(他幽闭于室内,硬写而不能),认为该形象之所以流行于当时的作品,与“文学青年”群体中文学生活的消费化以及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封闭性有关。(21)参见姜涛:《“室内的作者”与19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5-201页。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的文学写作“丧失了自身的真实性,只能成为一种打发无聊生命的自我消费”(22)姜涛:《“室内的作者”与19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第201页。,甚至沦为孤独穷困的文学青年们换取稿费的“生计”。反观汪曾祺在“听水斋”的写作状态,与这种“硬写”貌似很相像,但似乎又比他的前辈们更多一份理想化的“执拗”。如前文所述,《绿猫》里“栢”的独白包含了广博的中西文化渊源:从瑞恰兹的“最丰富的生活”,到纪德的“要生活里有诗,只有放它进去”(第230页),再到《庄子》《文心雕龙·神思》的大段背诵,文学内蕴的现实超越力量尤其是“心中苟有所开”(第231页)时“灵感”所带来的生命飞扬状态,显示了汪曾祺对于文学之伦理内涵的坚信不疑。显然,这种价值尺度并不属于20世纪20年代囿于自我消费的“室内的作者”群体,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新文学的文学“志业”理念(23)姜涛认为,新文学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除了表达“为人生”的“责任伦理”外,也是一份指向文学者自身的“志业”宣言:“我们相信文艺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并由此分析:“‘终身的事业’即是一种‘志业’,它不同于一般的职业,工作,而是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召唤,在持续不断以致‘终身’的承诺中,具有强烈的价值投入感”。参见姜涛:《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下的文学“志业理念”》,《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27页。在20世纪40年代的回响——汪曾祺终究还是来自西南联大,受业于闻一多、朱自清等前辈的“五四”之子,一个游离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扰攘文坛的“边缘作者”。
三、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文坛
因此,《绿猫》的涵义也要放到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上海复杂的文学场域中来看。小说完成不久,汪曾祺复信沈从文报告近况。其时沈从文久病不愈,汪曾祺首先劝慰老师“还是休息休息好,精力恐怕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涌出来的。勉强要抽汲,于自己大概是一种痛苦”;针对沈从文前信对自己创作前景的预想:“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也许又可稍久些,一直可支持十年八年”,汪曾祺难过之余,期盼老师尽快恢复“战斗意志”:“我是希望您可以用更长更长的时候的,您有许多事要作”。(24)汪曾祺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的信中提及自己“自七月三日写好一篇小说后,我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不难推断,这篇小说即指完成于七月二日夜(或为七月三日凌晨)的《绿猫》。参见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8页。
的确,师徒二人在这一时期各有其隐忧和困境。战后回到北平的沈从文在创作、编辑之外,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杂文,对政治局势、民族命运做出自己的思考。其中,1946年11月由《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版和上海版同时刊载的《从现实学习》,在回顾自我人生历程之余,表达了对内战之于生命、国家消耗毁伤的悲哀,最后将希望寄予“为国家民族求生存求发展”而沉默工作的作家、学人们。孰料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即遭到大规模的激烈批判。充当讨伐主战场的是上海《文汇报》。从史靖(原名王康,西南联大社会学系1944届学生)分五次连载的两万字长文《沈从文批判》(25)史靖(王康):《沈从文批判》,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1-25日。,到岁末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辞年晚会上对文艺界“不良倾向”的检讨:“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26)《作家团年》: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30日。;紧接着又有郭沫若《新缪司九神礼赞》将沈从文称为“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帮凶者”(27)郭沫若:《新缪司九神礼赞》,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0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将沈从文探讨作家和出版间关系的文章《新书业与作家》称为“拙劣的犯罪”(28)郭沫若:《拙劣的犯罪》,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27日。“拙劣的犯罪”是郭沫若针对沈从文文中关于创造社初期历史的一小段客观陈述而发的,其实,郭沫若之所以下如此严重断语,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对沈从文政治、私交等方面由来已久的成见;参见李扬:《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关系》,《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问题层层升级,转瞬已成口诛笔伐之势。沈从文本人则在一次次欲辩废言后,选择对围攻取一种超然态度。
在这里(按:指北平)一切还好,只远远的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29)沈从文:《复李霖灿、李晨岚》,《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65页。
汪曾祺其时正身处“扫荡现场”。据他晚年回忆,在巴金家的某次文艺沙龙上,“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30)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9页。联系到在此前后左翼文学青年们围绕着《寒夜》(巴金)、《女人与和平》(李健吾)以及散文中“新感伤主义”等题目在《文汇报》副刊发起的论争与讨伐,巴、李二人的这种反应便十分自然了。实际上,1946到1947年间发生在上海的这几场集束式的文学论争,并不只是针对沈从文等个别作家作品,而是属于左翼文学界开展已久的清理文坛力量、整合文坛格局的工作,是大时代转换途中一场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较量和构建。
以上的文坛动荡并未直接牵涉到汪曾祺本人,这位年轻的作家当时应该也没有充分理解背后的复杂关系,他只是直觉地感知到上海文坛热闹表象下创作风气浮躁、批判大兴、派系斗争等问题:“上海的所谓文艺界,怎么那么乌烟瘴气!我在旁边稍为听听,已经觉得充满滑稽愚蠢事”,“年青的胡闹,老的有的世故,不管;有的简直也跟着胡闹”(31)汪曾祺:《致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9页。,同时也为老师感到不平。《绿猫》写到一位著作等身、却屡遭批判的“张先生”:“他写了二十年……在外国,这时早到了给他写传记的时候了。要批评他,就正正经经的批评也好——那么轻佻,那么刻薄,当真他的文字有毒么?”愤懑之余,“栢”进一步质问:“现在我们还有比愚蠢、比庸碌更大的敌人么?为什么不阔大些,不看远些?”而他藉以评判作家的标准是“紧张热烈的在工作,在贫穷苦闷中不放下笔来”(第229页)的写作。不难推断,张先生即以沈从文为原型(32)除了二者形象遭遇的重合外,汪曾祺晚年在与杨鼎川的对话中亦承认小说中的张先生即沈从文。,而隐含作者化身的栢这种将创作实绩作为作家立身之道、文学之本的观念亦与沈从文一脉相承(33)比如在1946年9月初,刚刚自昆明返回北平的沈从文在接受采访时毫不客气地批评丁玲等作家“思想进步、艺术落后”:“丁玲他们为什么去了(延安),反倒没有什么作品了呢?”参见子冈:《沈从文在北平》,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19日。,在当时的文坛环境中却显得格格不入。在前述致沈从文的信中,汪曾祺谈到上海木刻界对年青且天才的黄永玉的嫉妒和打压:“因为他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其发展”,并预见到这种排挤将不止于人事上的纠纷,还会上升到对作品背后思想渊源的批判:“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 (我相信他们真会用‘太艺术了’作为一种罪名的。)”。(34)汪曾祺此言很快得到了印证。1948年4月,一篇署名为“公孙龙子”的文章率先发出了对黄永玉木刻艺术的批判,指责其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疲惫,对现实战斗的懈懒,从丑恶的现实世界,逃向轻松的趣味世界”,并将之与沈从文的小说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是有目的地灌输或散播某种思想或毒素”,最后作了措辞激烈的总结:“这种艺术,这种艺术态度,与这种艺术方向,我认为应该而且必须及早彻底给以批判!”参见公孙龙子:《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原载《“同代人”文艺丛刊》第一集《由于爱》,1948年4月出版。此处转引自李辉:《传奇黄永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对黄永玉遭遇的预感隐现着汪曾祺对自身艺术倾向以及文学命运的忧虑,但具体如何应对,他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不无消极的结论:“自己寂寞做一点事,不要和他们太接近。”——树欲静而风不止、欲写而不敢写的矛盾处境正是《绿猫》的写作背景。
四、“高尔基”的焦虑与“如何写”的困境
在上述背景下,汪曾祺也不由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路向。《绿猫》中提及栢因一篇文章被好事者议论有“猫癖”,由此对栢之为人为文大肆嘲讽,那篇饱含个人生命体验和意识流动之美的文章也被指为“是不大壮健,是过了时的东西”,而张先生和“我”也都劝他“换个方法写”,“还是写写高尔基式的小说”(第235页)。栢只能感慨:“不知道甚么时候才写得好,又‘错了’”(第230页)。但栢仍对种种批评怀疑劝告听之任之,试图以坚实的写作安顿心灵:“一切说法只是一种说法,它并不能就限制住写的人的笔”,“我总在这儿写就是了,你知道的。——我这也并不是象征派,我有良心。”(第228页)
那么,“绿猫”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又为什么被汪曾祺与高尔基联系起来呢?在小说中,“高尔基”贯穿故事始终,通过随处可见的画像雕刻和人们的口耳相传时时侵入“我”的思绪,进而构成一种“影响的焦虑”;而“绿猫”并非现实存在,只是来自于栢的冥想,它一方面被指为晦涩难懂、没有“深入于生活”,同时也被赋予一层浪漫感觉、一种灵感,使人“若有所见,若有所感,若有所悟”(第231页),是纪德意义上的放进生活中的诗。故事尾声,叙述者很明确的点出,包括“绿猫”在内的大部分题目,栢写的都是他自己,那么放大来看,绿猫即指汪曾祺此时创作的一系列颇具象征意味和先锋性质的实验作品,甚至“把他40年代的作品加在一起,在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当中,它就是一只绿猫”。(35)在1994年的访谈中,杨鼎川对《绿猫》颇为重视,表示要写一篇文章专门分析,汪曾祺回应道:“这个东西我自己写”。参见汪曾祺,杨鼎川:《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汪曾祺访谈录》。然而,在笔者的检索范围内,并未发现这两篇被列入写作计划的文章。总之,“绿猫”代表了一种与“高尔基式的小说”决然不同的文学观念。众所周知,高尔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高尔基关于文学的社会功用、创作方法等方面的观点,尤其是由他首倡并奠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便在中国文坛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在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又被确立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准则。据学者李今的研究,高尔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只有逝世后的鲁迅才可与之比肩”,而“‘高尔基热’在中国的形成是与中国革命, 特别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36)李今:《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高尔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由此再来看《绿猫》中关于高尔基的描写,会发现这篇作品有意无意中构成了对高尔基形象及其文学观念的微妙消解。无论是将画像、杂志上符号化的高尔基形象与道士“请神”“降神”相类比,还是有关对高尔基灵感匮乏、“写不出来”的想象,突出的都是日常生活里作为一个作者、一个普通人的高尔基,“自也有一种可以令人感动之处”(第234页),但这样的高尔基泰半是为宣传家们所遮蔽的。《绿猫》由此暗含了一种个人化的,却又相当激进的对于战后左翼文坛流行观念的反叛。从这个角度看,汪曾祺1949年后整整三十年的“空白”于此早已埋下伏笔——“因为我写不了那样的小说,所以就不写”——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被确立为最高也是唯一的创作原则,或者说,当只允许一种“高尔基”形象存在的时候,汪曾祺和他的“绿猫”也只能陷入沉默。(37)这并不是说汪曾祺在1949年后的创作完全陷入了“空白”,1949年后汪曾祺亦有一定数量的创作,只是与他早期“绿猫”式的实验写作差别日渐扩大。
最后,让我们回到《绿猫》的文本形式。就故事结构而言,这篇小说明显受沈从文《看虹录》的影响,也应该放在包括沈从文、卞之琳、萧乾、袁可嘉等“新写作”作家群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借鉴的整体潮流中来看。(38)“新写作”是1946—1948年间出现在平津文坛的一场文学试验潮流,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卞之琳、冯至、袁可嘉等,“新写作”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并期望将文学试验同文艺复兴、文化建国结合。汪曾祺即是这场文学潮流中引起相当注意的新生力量。参见段美乔:《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55-178页。汪曾祺早期创作思想的集中体现——《短篇小说的本质》,即是这场潮流的成果之一。在这篇论文中,汪曾祺表示了对国内短篇小说形式凝滞的不满,感慨小说“在东方一个又很大又很小的国度中简直一步也不动”,“此世纪中的诗,戏,甚至散文,都已显然与前一世纪异趣,而我们的小说仍是十八世纪的方法”,他因此呼吁“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39)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5-16页。;《绿猫》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不像小说”的小说。或许汪曾祺自己也意识到这种追求的激进,在《绿猫》的结尾叙述者如此说道:
我曾经警告过他,说这样的小说我没有看见过。这算什么呢,算心理小说?心理小说在中国还是个颇“危险”的东西。中国人大概都比较简单,也许我们的小说家以为中国人很简单,反正,没有这个东西。(第235页)
将这段话与毕基初1948年对萧乾小说《珍珠米》的评论放在一起对读是饶有趣味的:
也许我们中国人不适合心理小说,但问题不在是否适合我们,而是“横在我们眼前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晚近三十年来,在英美被捧为文学杰作的小说中,泰半是以诗的形式,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试验作品”,我们没有理由遮住自己的眼,坚持自己的传统,既不认识也不接受新的空气和血液。(40)毕基初:《从封面的素描像谈起——读萧乾先生的〈珍珠米〉》,《民国日报·文艺》第148期,1948年10月16日。
作为“新写作”后起力量的毕基初对探索文学表现新领域斗志昂扬,展现出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发展的热切渴望,而汪曾祺的表述中则多了一份忧虑。正如《短篇小说的本质》是在“许多方便之下”才开口,还要时时担心有人用“唯美主义”的砖头往自己脑袋上砸,《绿猫》等实验作品亦经历了一番“如何恰当表达而又不招致批评”的写作探索。像《绿猫》中“我”在一个雨夜出入于幻境现实之间,与“栢”就文学观念、个人生活、文坛环境所展开的对话辩驳,无不是汪曾祺在现实生活中所见所感的文本化,其象征形式为作者表达矛盾精神困境和“另类”文学观念提供了一道恰当的保护层,这篇小说的“怪”及为人所忽视其来有自。如果说《看虹录》是“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41)沈从文:《看虹录·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7页。,那么《绿猫》也可视作青年汪曾祺一个夜晚的“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以及“智慧的一种模样”(42)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或许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风云变幻的文坛,汪曾祺只是一个身处边缘、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但是唯其边缘,他所陷入的写作困境及探索努力才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绿猫》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文学和人生的形而上之思,这对理解汪曾祺及其文学理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文坛的处境,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在那个“天地玄黄”的历史阶段的重大转折,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