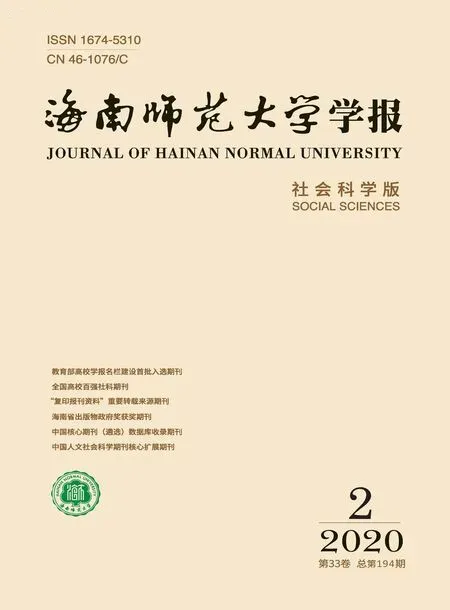《现代评论》与沈从文的早期创作
王玉珠
(西安财经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谈到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起步与大量习作训练,似乎是种种因缘际会合力的结果。在1936年5月所写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在回顾和总结自己第一个十年的创作生涯时,曾诚恳地表示,“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通伯先生,杨今甫先生”,是“特别值得记忆”的,“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的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1)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页。其中,陈通伯、杨今甫曾先后负责编辑《现代评论》的文艺稿件,是该刊在文艺方面的重要力量,而《现代评论》也是除《晨报副刊》之外沈从文早期创作(2)1924年12月,《晨报·北京栏》刊载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直至1929年,才是沈从文自认为作品成熟的一年,据此界定其早期创作为1924年至1929年这一阶段。详见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106页。最为主要的发表平台,该刊同人的提携与赏识对于沈从文的文学起步以及创作的日渐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一、《现代评论》与沈从文的文学起步
《现代评论》周刊创立于1924年12月13日,是一份以政论时评为主,“包含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技各种文字”(3)《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的综合性同人刊物,从1924年12月创刊到1928年12月终刊的四年间,该刊共发行九卷209期,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平台和言论机关,围绕该刊集结形成的同人团体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在该刊同人的话语建构中,作为其自由主义思想感性而内涵丰富的一种记录,文学是颇为生动而重要的一翼。尽管初登文坛的沈从文与该刊同人还远非过从甚密、私谊颇淑,二者之间在学历背景、生活境遇与社会名望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同时其创作尚处于“文字还掌握不住”(4)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的初创阶段,但二者在艺术立场与文学意气上的相合,却使得沈从文引起了“现代评论派”的注意。对此,夏志清曾分析道:“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5)[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社会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社会气氛紧张激越的氛围中,沈从文那种“天生的保守性”所表示出的对当前政治与革命问题避而不谈的艺术态度,以及对人性与人生形式的观照与执着抒写,正契合了“现代评论派”秉持英美自由主义学说,在交锋频仍的公共领域行使和争夺话语权,以引导读者形成政治和审美偏好的使命意识与表达愿望;而他“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和不与过去决绝断裂的文化姿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主张以温和、渐进的改良和启蒙实现自由主义理想之境的“现代评论派”达成了一种颇为相通的心理共性。
就沈从文初登文坛前后的人生路向而言,湘西边地军人政治的蒙昧与残暴,初到北京所感受到的社会的冷酷无情与不合理,以及生活上所遭遇的种种出奇意料的困难,看似会促使其在当时社会革命日渐涌动的环境中,如同他的北大、燕大的不少朋友一般走向革命。然而,沈从文并未做出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选择,恰恰相反,他显示出一种“只想在文学上‘试验’下去”的“不机敏”与“固执”。(6)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演》,《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7页。这或许与残酷的军队生活体验所造成的反弹效应,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沉静旁观的姿态有关。但这种不盲从革命潮流的保守性更多地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色彩,它是从生命源头而来,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另一方面,由于“五四”新书刊所给予的极大刺激与鼓舞使其“进一步明确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学革命对社会变革的显著影响”。(7)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与当初离湘赴京的动机相似,沈从文执着于文学“试验”的保守与固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同时,相比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留学生,沈从文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熏染与浸润并不充分;加之,直到1923年夏,时值“五四”高潮期,他尚在湘西边远僻地浪迹江湖,此刻离湘赴京的沈从文恰恰远离了京沪两地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对于旧文化雷霆万钧般的猛烈抨击与决绝斩断,以及由此造成的激进、凌厉的文化心理氛围,从而形成了他较为稳健、平和的历史文化态度,并在创作伊始即显示出一种远离激进浪潮的倾向。
而在“现代评论派”一侧,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气质风度上,该派同人都受到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形成了英美式的价值理念与绅士风度;在文艺活动中,他们秉持个人本位主义,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立场,追求艺术的健康与纯正,保持与政治的疏离关系,坚守“五四”启蒙传统和对“新文学运动的继承”(8)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72页。,加之英美式自由主义天然的保守性。因此,在氛围激越的公共领域,尤其面对创造社等作家趋向政治的要求以及在方向转换后的激进文风,“现代评论派”表示出明确的警觉与抵制,不仅以创办“思想的杂志”而非“宣传的机关”(9)《卷头语》:《〈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12月。自许,并在整体上呈现较为独立、温和、稳健的话语姿态,显示出制衡话语空间,尤其是对革命文学激进风格进行纠偏的意味。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革命话语不断鸣响,作家热心献身革命事业,而左翼激进文风不断高扬的时代洪流中,沈从文却以其不盲从大时代变革的“保守”和对“五四”文学革命理想的坚守避免了被裹挟而下,并受到了“现代评论派”等英美派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
此外,沈从文在《现代评论》发表作品还得益于该刊着重于文艺且着力提携新人的办刊方针。尽管基于该刊同人对英美式民主政治的羡望与主张,《现代评论》“花了大半的篇幅谈政治”(10)罗家伦:《时局的反照与〈现代评论〉的回音》,《现代评论》第1卷第17期,1925年4月4日。,但同时,在文化自由主义层面进行思想启蒙与文化更新的长期性价值目标也推动该刊“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1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在创刊不久,《现代评论》即以其文艺作品的“新鲜”“犀锐”被寄予了“开一种文学的风采,养出一种文学的体裁”的厚望。(12)罗家伦:《批评与文学批评》,《现代评论》第1卷第19期,1925年4月18日。该刊同人不仅致力于文艺上的批评指导,并且很快就以“现代文艺丛书”的出版发行显示了他们在文艺上“充分的努力”和“真实的贡献”。(13)《现代丛书出版预告》:《现代评论》第1卷第9期,1925年2月7日。自第二卷第38期起,该刊又将内容扩充,“增加文艺及科学方面的文章”(14)《本刊特别启事》:《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1925年8月29日。;而且,在其时同人刊物经费筹措不易,运转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现代评论》却坚持向文艺栏目的作者“酌赠薄酬,聊答雅意”(15)《本社启事》:《现代评论》第6卷第154期,1927年11月19日。,进一步体现了该刊着重于文艺的办刊倾向。不仅如此,《现代评论》自创刊起即显示出对文学新人的关照与重视。该刊“向来志愿介绍新进作家的文字,尤其欢迎创作……亦不因作者不知名而减少注意”(16)《本社启事》:《现代评论》第6卷第154期,1927年11月19日。,这种着力提携新人的用稿倾向使得《现代评论》成为许多文学青年初试身手的重要阵地。在创立一周年之际,负责前两卷文艺稿件的陈西滢在回顾本刊文艺部分一年来的成绩时就曾指出:“在我们发表的文字里,固然有许多名字是家喻户晓的,然而有几篇是我们至今还不认识的朋友的处女作。”(17)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53期,1925年12月12日。除本刊同人外,该刊作者中既有胡适、郁达夫、欧阳予倩、熊佛西等声名显赫、颇有建树的名家宿将,也有沈从文、胡也频、冯文炳、李金发等初登文坛、渐露头角的新进作家,也正是沈从文等年轻的文学力量为《现代评论》“文艺栏”的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整体上增强了该刊的文艺性特征以及文坛影响力。
不过,《现代评论》着重于文艺且着力提携文学新人的办刊倾向只是沈从文得以进入该刊作者群的一般性便利条件,在这一点上并未显示出他受到了优于其他青年作者的待遇。相比其他新进作家,沈从文在精神上的保守与自由趋向,对艺术的挚诚,以及其作品流露出的温柔情调与道德色彩,才使他尤其受到“现代评论派”的赏识和提携。两个颇为有力的明证,即是《好管闲事的人》与《阿丽丝中国游记》作为“沈从文新著两种”(18)《沈从文新著两种》(广告):《现代评论》第8卷第193期,1928年8月18日。曾连续多期在《现代评论》上发布广告,得到大力推介;而在该刊同人隆重推出的《第二周年纪念增刊》上,沈从文更是独享了以不同笔名同时发表多篇作品的优待。(19)其中,小说《入伍后》署名“沈从文”,新诗《曙》署名“甲辰”,剧本《蒙恩的孩子》署名“懋林”。更为重要的是,沈从文还“作过《现代评论》月薪20元的小职员”(20)马光裕:《沈从文谈〈现代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4期,第261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穷极无路”的窘迫状态,并且得以日渐与陈源、杨振声、丁西林等熟识,在其创作早期成为该刊文艺部分的重要作者。
二、作为《现代评论》的新进作家
经统计,从1925年8月《现代评论》第38期始至1928年9月该刊第199期为止,沈从文曾以“沈从文”“从文”“懋琳”“甲辰”“为琳”等为笔名,共发表作品22篇,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样式,其中以短篇小说居多,中篇小说《旧梦》自1928年2月至9月分29期连载于该刊。尽管在数量上难以与沈从文同时期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作品相比,同时在其早期创作中的占比也并不十分突出(21)据《沈从文研究资料》第五辑《沈从文著作系年(1924~1988)》统计, 从1924年至1929年早期创作的五年间,沈从文共发表作品227篇。详见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57-1183页。,但这20余篇作品却构成了沈从文这一时期创作速度惊人、产量丰富的创作“试验”有力的一翼,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沈从文早期创作的成熟程度、意识倾向与艺术特质,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另外,这些作品也显示出他与“现代评论派”在创作立场与艺术追求上的两相契合,并因此成为《现代评论》自由主义文艺创作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沈从文整体上有着坚毅的写作信念,也有丰富的故事和幻想,但由于文字叙述把握不足,其发表于《现代评论》的习作与其它早期作品一样,对于那些丰富的材料还远未能以娴熟的手法予以恰如其分的处理,因而往往是在类似地方志的描绘中匆匆嵌入情节叙述,拼凑成篇。但同时,在《入伍后》《猎野猪的人》《山鬼》《在别一个国度里》等小说中,沈从文将笔触聚焦于曾切身体验过的湘西故乡,抒写至真至纯的童年生活,描摹湘西独特的自然风物与民俗风情,着力刻绘湘西边民纯真、素朴的人生形式以及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优美、强健的人性。这一基本的创作向度不仅在其作品中留下了自我生命历程的痕迹,也因此充分赋予其早期创作的个人特征和地域色彩。
从题材看,沈从文的个人化特质源于他对苗族故事的极力抒写和对苗瑶生活的极力介绍,“对于湘西的风俗人情气候景物都有详细的描写,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22)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第3卷3期,1934年9月。。然而,与其说沈从文的“别具一格”是由于湘西地方的神秘性所致,毋宁说其独异性在于他观照湘西故乡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显示出的文化价值取向。与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登上文坛的乡土小说作家相比,同是抒写自己所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作品也同样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但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批判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师承鲁迅所开创的批判国民性传统,乡土小说作家的创作尽管也浸透着对故土的眷恋,但个人阅历、风格不尽相同的他们却采用了近于同一的方式讲述故乡人事,即对故乡的野蛮陋俗、愚昧乡规,以及残酷的阶级压迫予以批判性审视,并表达对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从而显示出逻辑思维的共同性与价值向度的相似性。而在沈从文早期的湘西小说中,他却以一种强烈的皈依情绪为底色,对现实中湘西的闭塞、落后、愚昧、残暴等作了充分的情感过滤,创造出一个具有理想化形态的诗意湘西世界。《入伍后》以一个初入部队的小兵的视野切入,将现实世界中残忍的农村械斗、混乱的军队移防,以及沉重而辛酸的行伍生活进行充分的净化与诗意渲染,凸显出湘西地方军人重情重义、朴实纯真的一面,全篇兴味盎然,充满纯真稚气。《猎野猪的人》将童年时所经历的原始性的渔猎生活娓娓道来,在对童年生活的记录与回忆中展示湘西民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山鬼》在对毛弟和癫子自由自在生活的描写中构建一个至真至纯的诗意世界,展示了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形式和野趣盎然的生命力,以及充满原始感并具有神话意味的奇异民俗风情。《在别一个国度里》则在对一个落草为王的土匪娶讨压寨夫人的故事讲述中,着重展示湘西草寇王身上的雄强血性与充满温情的人性。沈从文早期的这些作品对湘西边地原始生命形态的抒写,以及对美好人性以及生命强力的开掘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使其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乡土小说作家的审美视角与眼光,但此原始的炽烈情感也意味着其创作对人性和道德尚未能作出富于理性的观察和思考。
沈从文早期湘西小说所刻画的美好人性与雄强气质,无疑可为腐朽颓败的民族机体注入新鲜的血液与充满活力的因子,但客观而论,沈从文并未将其视作某种精神文化资源,因而尚未明确地显示出探求重塑民族品德与重造国民灵魂的创作意识,此时与作为文学世界的湘西的遇合,更多地是基于沈从文自身的个人化体验与一种自然的情感评判。湘西原本是“只能使我近于窒息,不是疯便是毁”(23)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3页。的可怕环境,然而在一种天然而又强烈的怀乡情结之下,羁旅异乡的沈从文在对童年和军旅生活的回忆,以及湘西稀奇古怪传奇的抒写中,完成了对故乡的诗意追怀与眷恋。同时,对于漂泊京城的沈从文而言,更为真切迫近的当下体验是生活上的种种艰难,以及并未被都市所接纳的边缘化心境。因此,在怀乡之外,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反复书写,似乎也隐含着一种刻意为之的努力,以此弥补内心所潜藏的因无法融入都市以及英美派等精英知识阶层而滋生的自卑心理。而这种复杂的自卑情绪的微妙性正在于,一方面,它激起了沈从文追求卓越的自我期望与写作信心,使其“深信这是一项通过反复试验,最终可望做好的工作”(24)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20页。。进而,在其创作中显示出向并不擅长的西方现代小说技法“靠拢”的努力。例如除了尤其明显的《阿丽思中国游记》(25)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连载于《新月》月刊,1928年3月至10月。是对赵元任翻译版《阿丽思漫游奇遇记》的着意摹仿外,在几乎同时期连载于《现代评论》的中篇小说《旧梦》中,无论是人物角色设定上“杰克哥哥”与“杰克母亲”的突兀命名,还是从“我”到“小物件”的叙事人称的生硬转换,抑或是全篇过于随笔化的笔法,都显示出沈从文对于都德及其《小物件》的戏仿与摹拟。另一方面,这种源于不堪都市境遇的自卑情结无疑也隐含着对于都市文化的某种敌意以及难以融入其中的某种焦虑,并因此将沈从文推回其自身所独有的湘西生活体验。“湘西”成为一种有助于沈从文得以减轻焦虑并建立其自尊心的最直接、有效的补偿性写作资源。因此,早期创作中与湘西的遇合,更主要地是为蛰居京城且在生活与心灵上艰难跋涉的沈从文带来精神家园的慰藉。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边城》等作品的创作中,当沈从文明确地以“乡下人”的角色认知表示要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要“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26)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页。时,这种自卑情结才转化为面对都市文化的某种心理优势。而当他自觉地以边地湘西歌者的姿态对人性和道德进行观照和描写时,其创作也才真正具有了对转型期中国文化进行深刻批判的思想力度。
与早期湘西小说相类,沈从文早期都市题材创作也主要呈现为基于自身经历的一种感性记录与表层描写,当客寓京城的个人化生命体验作为沈从文“生命痕迹”的另一阶段与样态得以诉诸其笔端时,无论是对都市生活方式与道德习俗的诅咒,还是对自身漂泊命运的自叹自怜,都充斥着大量纷繁芜杂的情绪、感受和经验。在此期发表于《现代评论》的《岚生和岚生太太》《晨》《蜜柑》《怯步者笔记》《看爱人去》《旧梦》等作品中,沈从文城市表达中的这种经验化色彩与表浅化倾向可见一斑。《岚生和岚生太太》与《晨》写不愁温饱的小职员岚生夫妇剪发、缝旗袍等极为琐碎的生活事件,对岚生的平庸、无聊、毫无追求以及岚生太太的虚荣和空虚极尽嘲讽之意。《蜜柑》描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教授,以及一群表面为学校献言建策而实际思想浅薄的大学生为分蜜柑而进行的无聊的爱情游戏,对教授只是将德行放在嘴上的虚伪灵魂予以讽刺和诅咒。《怯步者笔记》写自己在城郊听到“富于生趣的鸡声”,感慨客寓北京两年有余而未曾听过鸡叫声以及“北京城的古怪”。《看爱人去》充满愤慨和悲哀地展示爱而不得的酸楚,爱情尽管美丽,但“这世界女人原是于我没有份,能看看,也许已经算是幸福吧。”(27)沈从文:《看爱人去》,《沈从文全集》第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旧梦》则将这种悲哀的爱情体验做了进一步的扩张,描写一个寓居城市的文学青年的冶游与性幻想,呈现其“柔弱的性格,潦倒的生活,所遭的命运,所演的悲剧”,着重表现主人公在情欲同理智的纠葛中充满颓丧感与自卑感的“忧郁无用徘徊柔弱”(28)陈子展:《沈从文的〈旧梦〉》,《青年界》第2卷第1号,1932年3月20日。。在这些作品中,面对城市上层生活的萎靡与庸俗,以及知识阶层虚伪而缺少内在生命力的灵魂,沈从文表现出一种相当敏锐的感受力和蓄势待发的情绪力。正因此,沈从文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受情感的支配,对朦胧之中感受到的“北京城的古怪”缺乏理性的审视而无力提取。而那些记录潦倒青年因爱情无可求取而自我哀怨的作品,所潜藏的寓居都市而不被接纳的种种不如意更多地停留于情感肆意宣泄的层面,成为对自身“郁达夫式的悲哀”(《看爱人去》)与自卑情绪的展览和倾诉。无论是对虚伪、卑琐、毫无血性的都市知识分子的描画,还是对自身际遇的叙写,沈从文都缺乏更趋冷静、切实的知识分子自我批评的主体意识。
从整体看沈从文发表于《现代评论》的小说创作,其中所表现的湘西边民优美、纯真的人性与强健、野性的生命力,与充满道德病态的都市人性以及怯弱、颓丧的都市青年已然构成了鲜明对立,由乡土与都市两大基本主题所形成的整体性审美构架已初现端倪。然而,纯净湘西与病态都市的截然对立,以及作品所显示出的作家鲜明而自然的情感评判向度,也意味着这种初现端倪的城乡对比倾向并非作家有意为之,而是基于作家生命体验与情感的一种自然抒写与宣泄。无论是创作意识与心理,还是作品所寄寓的情感形态,都显示出沈从文尚未自觉地以地域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态度对现代文明予以批判,尚且缺少对人性与人生形式富于理性的深刻反思。同时,这种城乡之间界限分明的对立格局,不仅映射出沈从文这个时期颇为孤独、尴尬的写作心境,显示出他与《现代评论》同人之间在文化体验与观念上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上的隔阂与理解的无可企望,而且意味着最终因无法回避的现代意识与外部世界对乡土的影响,他在城乡之间纯粹的情感与价值选择必然予以调整。
三、 “和而不同”
在沈从文开启文学之旅并在文坛艰难跋涉之际,《现代评论》既为其锲而不舍的习作训练提供了发表平台,同时其创作对人的生命与生存的关切,以及对文艺独立与纯正的追求,都表明了他与该刊同人以人为本的立场和自由主义的保守性之间的契合。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与《现代评论》同人的创作都蕴含着通过启蒙以实现民族新生的理想因子,成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守。然而,沈从文绝非一位绅士气派的作家,这种身份的判定,也绝非如沈从文自身所言,是因为那时“只二十三四岁,一月至多二三十元收入,那说得上是什么‘现代评论派’?”(29)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0页。在表面上和谐友善的“友谊”之下,沈从文与这些“名为相熟”的朋友之间在精神层面有着既投合又疏离的复杂关系。
沈从文创作对于都市知识分子读者群的吸引,首先在于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所显示的湘西地方的神秘性。对“现代评论派”而言,除去这种独特的题材领域中陌生经验的吸引之外,他们在文学层面对沈从文的欣赏主要是因为其湘西小说描写田园生活的牧歌性契合了他们对自然自在的理想化生命方式的追寻。与在理性层面受到英美自由主义的熏染不同,在生命方式、个人志趣与情感方面,“现代评论派”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追求一种中国式的自由之境。无论是在艺术还是在大自然中,他们所倾心的是灵肉的充分舒展,内在心灵的充分愉悦,以及内在生命的自然自在,并希冀实现与自然的和谐与感应,到达一种怡然自得、安闲自在的境界(30)详见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2卷第43期,1925年10月3日;陈衡哲:《南京与北京》,《〈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12月;章渊若:《北京与上海》,《现代评论》第6卷第150期,1927年10月22日;袁昌英:《游新都后的感想》,《现代评论》第7卷第176期,1928年4月21日。,而这种情操、趣味和情感上的个人自由恰恰在沈从文笔下的诗意湘西世界中得以抒写。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紧张、残酷、扭曲相背离,表现无拘无束的童年嬉戏,自然舒展的健康人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淳朴与真挚,充满田园牧歌式的温馨与浪漫,也因此投合了“现代评论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化生命方式的思慕与神驰。
然而,在西方新潮流与中国旧传统之间,“现代评论派”对于自由主义理想图式的描画显然存在着一种“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尽管在情感与历史上,在生命方式的选择上,该派同人倾慕于本国传统,但更主要地,他们又是一群曾受学西土、“从欧美回来的彗星”(31)郭沫若:《桌子的跳舞》,《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33页。,是当时“道地十足”的“新人物”(32)钱穆:《我和陈通伯先生》,《传记文学》(台湾)第17卷第4期,1970年10月,第25页。,在理智和价值上,他们推崇曾在留英旅美期间深度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自觉地以西洋近代文明为参照来更新民智、民德,以建立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与价值体系。因此,当他们站在现代价值立场上反观传统时,就在巨大的反差中发现了种种弊端与落后之处,并通过大量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对传统价值体系与伦理观念进行彻底否定,揭示传统文明在整体上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例如针对甚嚣一时的宣扬“农村之国”的主张,陈西滢就尖锐地指出:“主张农治者自然把世风的不古,道德的沦亡,归咎到都会的工业。好像农民个个是天上安琪儿似的!这实在是住在城里的读书人白天的迷梦。……就是农人,我想也没有比他们更自私,更悭吝,更腌臜,更缺乏同情的人”。因此,章士钊等人“不去找适应新环境的新礼教,却想退到适应旧礼教的旧环境”,无疑是“江河倒行”和“开倒车”。在陈西滢看来,农业社会落后、陈腐的旧礼教并不具有任何道德上和精神文明上的优越性,反而显示出种种“与新环境不相合”的劣根性,因此,即便他也明确地意识到西方文明自身在20世纪初业已显示出弊端与危机,“承认欧美人也还没有找到十分满意的新礼教”,但基于对西方文明感同身受的深刻体验,他依然坚信欧美国家“已经得到的成绩,已经很够我们的参考。”(33)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6期,1926年3月13日。
相比之下,“历史与价值的张力”所致的情感纠葛与价值抉择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并不明显,在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他表达出更为单纯的情感与价值向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其独特而又有限的情感与文化体验。正如夏志清所描述的那样,赴京之前的沈从文,“可说与那个当时正受西方精神和物质影响下的中国毫无关系”(34)[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135页。,而在此后漂泊京城、卖文为活的生涯中,他也未曾感受过都市现代文明物质与精神上的眷顾,更未曾真正深入到诸如“现代评论派”等精英阶层体验下的都市生活,在他穷愁潦倒的都市生存中,徒增的只是漂泊异乡的孤寂之感与隐含着某种敌意与焦虑的自卑心理。因此,沈从文与曾直接承受过欧风美雨沐浴的“现代评论派”不同,有限的都市生活与现代文明体验使他未能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未曾意识到传统中国价值在现代世界中已经过时,并因之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恰恰相反,在他天生的保守性以及怀乡情结与自卑心理的助推之下,沈从文在其早期创作中呈现出彼此对立、界限分明的“优美湘西”与“病态都市”两个文学世界,并在其间展示出几近极端的情感与价值判断,而他在城与乡、新与旧之间这种自然而然且极端对立的情感与价值选择也正表明着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也正基于此,我们可以明确“现代评论派”对湘西民间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的欣赏,只是将其作为审美对象而展开的,作为仄居都市、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精英意识乃至优越心理的英美式“智识阶级”,他们对于现实乡间陈旧、落后的道德与价值无疑是持批判的眼光的,但同时,也正如陈西滢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与中国的老百姓之间“非但隔了一道河,简直隔了一重洋”(35)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2卷第45期,1925年10月17日。,这种严重的隔阂与疏离也意味着他们缺乏对于民间疾苦的了解和认知,因而那个经过沈从文净化的“优美湘西”才在情感与志趣的层面上引起他们的审美共鸣。尽管在该派同人自由主义的容忍精神与绅士风度下,他们对沈从文笔下并不完整的都市表达,以及充斥其间的诅咒与嘲讽意味并不难以接纳,但似乎也显示着他们与沈从文之间在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上的极大差异。
而对于沈从文来讲,早期创作中单纯而近乎极端的情感与价值向度似乎可以避免面对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思想困惑与情感失衡。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如同任何一个来自乡土世界的现代中国作家,沈从文也无法回避现代意识与外部世界对于乡土的影响。因此,当原本是一种“可怕环境”而“必需挣扎离开”(36)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的湘西被理想化并得到其完全的认同和皈依后,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湘西”这一前现代性的乡土世界能否成为解决现代性诸种弊端的最终去处,或者说“湘西”能否成为沈从文永久纯粹的价值归属。实际上,“知识分子自觉、作家意识,是妨碍任何一种绝无保留的认同的。那种认同意味着取消创作,取消知识者特性。”(37)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也正因此,我们看到历经心灵层面的艰难跋涉与探索后,在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臻于成熟的创作中,尽管城与乡、新与旧之间的取舍依然非常明确,但在其湘西文本中,一种反映着价值危机的潜在的隐忧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其都市文本也超越了早期情绪展览与宣泄的阶段而富于理性审视与批判色彩,这也意味着沈从文在城乡对照中建构自己审美天地的主体性意识得以确立,而这位当初的《现代评论》新进作家也终于以其纯熟的书写获得了他在整个自由主义文学阵营中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