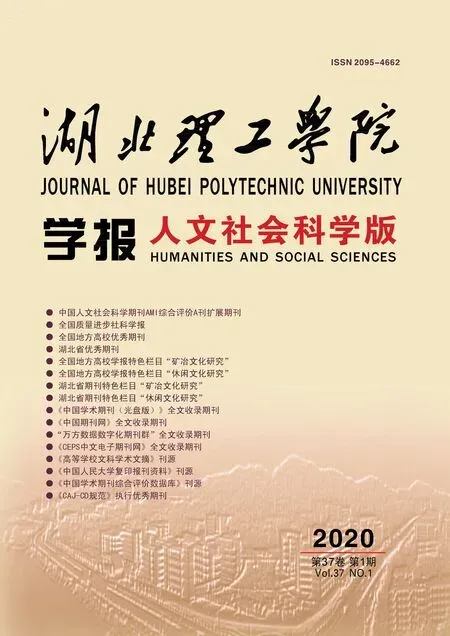从矛盾观的演进视角看习近平外交思想
周子健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演进逻辑
矛盾即对立统一,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和实质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乃至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观理论呈现出一脉相承的趋势,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论述各有侧重。
(一)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改造矛盾观
马克思“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1]13。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批判了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是宇宙世界运动和变化规律的本质的观点,运用唯物主义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倒过来”,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1]388。马克思在阐述黑格尔“纯粹理性的运动”的观点时,提出了对于辩证运动的理解,“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2]225,其一般运动形式是“正题、反题、合题”,“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2]220。马克思实现了黑格尔唯心矛盾观的重新解构,指出事物现象的矛盾必须归结于本质的矛盾,一切事物在产生时就包含了否定自身的因素,事物内部存在的“是”与“否”对立因素会在矛盾运动中“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2]221。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机械矛盾观时指出:“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2]223首先,事物的矛盾绝不是正和反的简单相加,事物在产生时就包含着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双重趋势,导致矛盾双方在运动过程中存在“均衡、中和、抵消”的不同形式,“好”与“坏”的区分既不能揭示矛盾的内涵,也无法理解矛盾的辩证运动。其次,保存“好”消除“坏”无法在本质上解决矛盾,矛盾双方相互共存,“好”脱离“坏”将不复存在,矛盾只能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得以解决而无法消灭,事物也只能在内部矛盾的不断解决中向前发展。总体而言,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矛盾观,对矛盾的内涵和运动形式进行了论战性的阐发,但没有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论述。
(二)恩格斯:深刻系统地阐述矛盾观
“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1]27恩格斯的矛盾观着眼于不断运动和发展着的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的一切现象,旨在揭示整个世界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将三大思维规律强加于历史和自然界的错误论述,强调要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世界中“抽引”出其中的思想体系,而不是将其颠倒放置,他将辩证法的规律总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1]401。
恩格斯深刻系统地阐述了矛盾观,首先,矛盾“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是一种必须被承认的“实际的力量”[2]133,因此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其次,“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1]673,恩格斯谈到的“辩证的否定”,是矛盾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决定了旧矛盾的解决和新矛盾的产生,是事物向前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恩格斯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基本框架下,系统论述了矛盾观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将矛盾运动与事物发展联系起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完善和发展,但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矛盾的定义和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列宁则做了更加深刻的探索。
(三)列宁:提纲挈领地构建矛盾观
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3]192列宁创造性地指出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促成了一切事物的发展与变化,无论是量变质变规律中渐进性与飞跃性的辩证统一,或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都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基础与核心的。
列宁在此前提下提纲挈领地构建了矛盾观,一方面,他将辩证法的实质定义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3]305;另一方面,他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306,事物的发展是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的综合范畴,同一性与斗争性的此消彼长决定了事物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化。列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在理论层面,明确了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了矛盾观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在实践层面,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也进行了初步有益探索,实现了矛盾观与俄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矛盾观学说,马克思将矛盾观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石上,在与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论战中零星阐发了对矛盾内涵及运动形式的理解;恩格斯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框架下,系统论述了矛盾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将矛盾运动与事物发展联系起来;列宁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将矛盾置于唯物辩证法体系中,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的特殊结合。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矛盾观主要呈现出三种历史演进逻辑:从普遍到特殊;从分散到系统;从直观到科学。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呈现的矛盾观原理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4]。立足于当前大发展大变革大挑战的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基础上,把握当前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中的主要矛盾,找寻各国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立志为解决全球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5]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努力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外交思想秉承了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内核,着眼于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实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一带一路”倡议[6]便是中国给国际社会贡献的中国方案之一,通过做好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教育事业,加强经济全球化的互联互通,从而以新增的国际贸易量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二)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人民想的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7]我国积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当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地区热点和冲突层出不穷,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有利于积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在和平与稳定的局势中实现合作共赢。
(三)坚持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统一
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强调:“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8]毫无疑问,国家利益存在同一性与斗争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看到了其中的斗争性,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的短暂发展,但在面临环境问题、安全问题、资源问题等全球性的发展问题时,又不得不以“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的身份来标榜自己。
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了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统一,在竞争与发展的态势中找到了各国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与世界各国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改变了国际社会中“强国必霸”的固有思维,体现了公平开放、共赢开放、包容开放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部分,坚持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两点论”与“重点论”、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统一,是密切联系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指南;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脉相承的矛盾观学说,所呈现出的从普遍到特殊、从分散到系统、从直观到科学的演进逻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锚定历史方位。
三、矛盾观演进视角下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人类文明是在交流互鉴中发展进步的,中国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下,迎来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以矛盾观演进的历史逻辑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利于系统理解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入思考“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9]。
(一)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开放格局
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逐步建立的以中国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吸收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经验,高举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伟大旗帜,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道路。
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矛盾观从普遍到特殊的历史演进逻辑。马克思在对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批判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基石,经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发展完善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在与俄国、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彰显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实现了普遍哲学原理向特殊生产实践的转化。当前,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局势的特殊性,全面开放格局必须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国际社会中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力量。
(二)全面开放新格局是逐步系统化的开放格局
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10]152。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对外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的十个“坚持”[11],构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整体框架和核心要义,我国开放格局在系统化的理论指导下朝着宽领域、多层次的方向有序发展。
逐步系统化符合矛盾观从分散到系统的历史演进逻辑。只有将矛盾观置于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加以研究,才能揭示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反之,只有构建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的开放格局,才能深刻理解我国对外工作中各项决策部署的重要意蕴。
(三)全面开放新格局是迈向科学化的开放格局
全面开放新格局体现了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工作总目标。“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10]154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展现的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态势;另一方面也要求世界各国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12]。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坚持共赢开放才能实现利益共享。
促进外交关系的科学化、长效化和可持续化,符合矛盾观从直观到科学的历史演进逻辑。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从关于矛盾本身及其运动的研究,到揭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再到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在实践中不断自我革新的科学性特征。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样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在总结过去70余年的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未来,全面开放新格局将惠及更多的世界人民,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系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民谋发展。